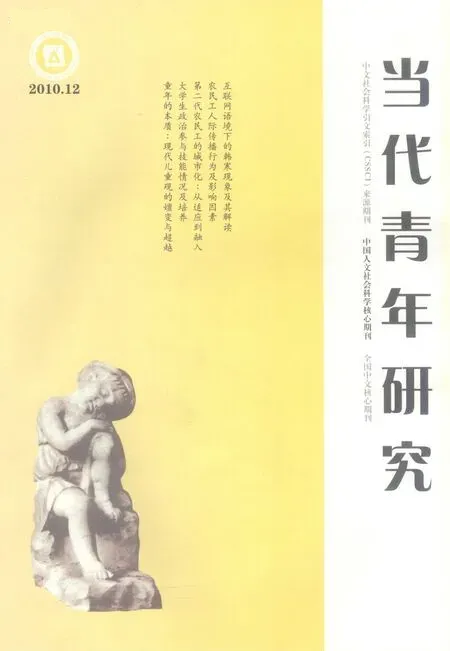农民工人际传播行为及影响因素
◎陶建杰
一、问题的提出
传播与人类相伴相生。传播是人们获得生存资源、发展机会最重要的载体和工具。传播学家库利就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机制,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通过传播形成的,所以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传播的历史。”①人际传播作为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形式,尽管今天的大众传播日益发达,但人际传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我们以个体的形式和周围发生交流时,人际传播便无时不在。而生活中的各种“意见领袖”,也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态度和认知。尤其是现代化的各种传播媒介产生后,克服了通过见面交谈、体态语言等直接传播形式受时空限制的不足,借助于电话、手机、互联网等媒介,人际传播的可能性和随意性更大。
我们发现,农民工来到城市所形成的崭新空间是独特的:大杂居小聚居。农民工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市中无时无刻不在闪现着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城后依然以亲缘、地缘、业缘等传统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镶嵌于城市中的“拟乡村社会”。置身其中的农民工主要通过无时不在的人际传播和市民产生接触。同时,受原有乡村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人际传播在农民工群体内部依然重要。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进城后,出于最基本的生存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以乡土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传播的频度、效率都有了提高。因此,人际传播是农民工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传播方式。
以往探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文献中,大致有两种取向:经济取向和社会取向。经济取向主要从各项经济指标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社会取向,则主要从社会融合、文化融合等角度,审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地位与心理。针对农民工人际传播的研究,也主要从社会取向入手。较为遗憾的是,学者均从质化的角度进行论述,尚未有人对城市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行为进行过实证研究。本文利用2009年11月对在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角度,分析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特征,试图客观、真实地展现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的现状,并从个体因素、网络因素、流动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并解释影响传播频率、传播内容的各种因素。
二、研究方法及指标
(一)抽样方法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笔者于2009年11月对上海市农民工的多阶段分层抽样调查。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截至2007年底,来沪农民工总量已达到403万,占同期上海1858万常住人口的21.69%。②上海地区的农民工,具有来源广(以华东地区为主),年龄结构轻(以青壮年为主),流动频率低、稳定性高,行业分布多样(以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为主)的特点。③选取上海作为农民工研究的调查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街道、居委会、住所三阶段PPS抽样方法,共抽取有效样本500人。在500个选取样本中,成功访问了395人,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35份,其中男性占67.2%,女性占32.8%,样本有效率为67.0%。
(二)主要分析指标
(1)人际传播网络特征
本研究主要从自我中心网络(egocentric network)的角度,考察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的特征。参照国外在自我中心网络特征方面的成熟研究,④⑤⑥⑦⑧本文涉及的指标有网络规模、关系构成、网络异质性。
网络规模:指人际传播网络中成员的数目。采用通行的“提名法”获得每个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成员人数,即让每个受访者列举最近半年内与其交流过各种重要信息的总人数。为了研究的方便,总人数限定在1-5人。然后用“提名诠释法”获得农民工人际传播网成员的基本情况、与受访者的关系等内容。关系构成:指网络成员与自我的关系。研究中分为配偶/同居伴侣、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戚等5种亲属关系,老乡、同学、普通朋友、好友恋人、同事等5种非亲属关系及其他。网络异质性:指人际传播网中全体成员(不包括自我)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分布情况。在本研究中,年龄、受教育年数是连续变量,其异质性用网络成员间的年龄、年数标准差来表示。对于性别、行业等类别变量,用异质性指数表示:D=1-∑(Pi)2,其中P=i组中的数目为占总体数目的比例。异质性指数的分布从0到1,0表示网络成员间在某个指标方面不存在差异,1表示网络成员间在某个指标上完全不同。在计算异质性指标时,排除了人际传播网规模小于2的个案。
(2)人际传播行为
传播强度:分别从认识年数和传播频率两方面体现。认识年数是指人际传播网中每位成员与自我的认识时间,研究中分为“不足3年”、“3-6年”、“超过6年”。传播频率又细分为两个指标:以见面为代表的直接人际传播频率、以电话/短信为代表的间接人际传播频率。两种传播频率均分为:“每天都有”、“每周有几次”、“每月有几次”、“大约每月一次”、“少于每月一次”。传播内容:借用林南对社会行动的划分原则,⑨我们把传播内容分为工具性传播和非工具性传播。工具性传播指为获得自身尚未拥有的资源而进行的传播。非工具性传播指维持自身已有资源而进行的传播。我们又将非工具性传播细分为情感性传播和社交性传播。属于工具性传播内容的有 “求职信息”、“技能培训信息”、“住房信息”、“健康医疗信息”、“法律政策信息”、“投资理财信息”;属于情感性传播内容的有“情感信息”、“子女教育信息”;属于社交性传播内容的有“娱乐消费信息”、“衣着饮食信息”、“时事信息”。
(3)个体指标
年龄,以调查时的实足周岁为准;性别,在回归分析中编码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 0;婚姻状况,将“已婚”编码为 1,“未婚”、“离异”、“丧偶”编码为 0;教育水平,为连续变量,以实际受教育年数为准;行业,根据农民工所从事行业的特点,分为“餐饮/宾馆业”、“娱乐/美容美发业”、“家政/裁缝业”、“批发零售业”、“加工制造业”等 13类;流动时间,以外出打工的累计实际年数计算;流动目的,挣钱养家、挣钱结婚等“经济型流动”编码为1,结婚、照顾家人、见世面等“非经济型流动”编码为0;融入程度,以上海话水平为指标,“会说或能听懂”,编码为1,“基本听不懂”编码为0。
三、研究发现
(一)网络规模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规模平均为3.16人,即在过去的半年中,农民工平均与3.16个成员交流过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56.5%的被访者提到2-4位成员,有31.6%的人提到5位成员。由于问卷限制了最多提名人数为5人,可以推测,如果不限定最多提名人数的话,农民工人际传播网中的成员数,应该会更多。在亲属网络规模中,有32.2%的农民工为0,即人际传播网中没有任何亲属。平均的亲属网络规模为1.26人,平均亲属关系比例占41%,意味着平均每个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中,有41%的成员为亲属。
(二)关系构成
在传统的乡村人际传播网中,成员多以亲属为主。⑩农民工进城后,人际传播的网络结构是否有所变化?调查显示67.8%的调查对象至少提到了1名亲属,74.6%的调查对象至少提到了1名非亲属;43.3%提到了配偶,76.4%提到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近亲;29.9%提到了老乡,39.4%提到了同学,20.9%提到了普通朋友,44.5%提到了好友、恋人,22.7%提到了同事。在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中,非亲属关系比亲属关系更重要。这是他们进城前后的显著变化。在亲属关系内部,最重要的是配偶、兄弟姐妹,在非亲属关系内部,最重要的是好友、恋人。如果以在全部关系中的比例来看,农民工人际传播网中成员的关系比例从好友、恋人、同学、配偶、老乡、兄弟姐妹、同事、父母、普通朋友、其他亲戚、子女依次降低。
(三)网络异质性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成员性别异质性指数为0.44,16.9%的网络性别异质性指数为0,即成员的性别完全相同。网络成员的年龄平均相差4.39岁。成员的年龄较接近,大部分属于同一个年龄组别,有72.2%的网络成员相互之间的年龄差距在5岁以内,表明农民工更愿意与同龄人交往。网络成员的教育程度也较接近,教育异质性为1.42年;行业差异适中,异质性均值是0.43。总之,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各方面的异质性均不高,不同网络成员的个体特征比较接近。
(四)传播强度
从自我与被提名成员的认识年数看,“不足3年”占30.8%,“3-6年”占29.6%,“超过6年”占39.6%。农民工与网络成员间认识的时间普遍不长。这一现象,恰好体现了他们“流动”的特点。无论在城市间,还是同一城市内不同行业、企业间,农民工都较之于其他群体流动更加频繁,他们的人际传播网络成员,处于更多的不稳定状态。与网络成员的见面频率,“每天都有”占36.6%,“少于每月一次”占24.5%;电话/短信等间接传播方式,“每天都有”占14.6%,“每周有几次”占34.2%。总体上看,农民工与网络成员的交流比较频繁,其中间接传播较之于直接传播更频繁。
对传播频率的回归结果显示,仅有年龄、懂上海话的系数达到显著。农民工每年长1岁,其与人际传播网中成员的见面频率增加0.064。懂上海话的农民工与网络成员的见面频率,比不懂上海话的农民工要高52.3%。电话/短信传播,各自变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不同个体特征、网络规模、流动状况的农民工,以间接形式开展人际传播的频率差不多。
(五)传播内容
在11类重要信息中,比例最高的是情感信息,占14.2%,其他比例较高的还有娱乐消费信息、住房信息、职业介绍信息、投资理财信息,分别占12.3%、10.3%、10.2%和10.1%。“法律政策信息”和“时事信息”在农民工人际传播中较少被提及。通过深入访谈,我们发现造成这两类信息关注度较低的原因有二:首先,农民工普遍感觉法律、时事等信息,往往无关切身利益,关注度不高;其次,时事信息主要通过大众传媒获得,而当需要寻求司法救助时,也会通过报纸、互联网、专业书籍等非人际传播形式。从大类看,农民工日常人际传播的内容,以工具性信息为主,占52.6%,社交性信息和情感性信息的比例差不多,各占工具性信息的一半左右。流动原因中,“挣钱养家”和“挣钱结婚”的经济型流动占62.0%,“求学、学手艺”占13.7%,而属于“结婚”、“见世面”、“照顾家人”等非工具性目的,仅占17.9%。在工具性目的驱动下,农民工进城后的人际传播内容,理所当然地会侧重于工具性信息。
对人际传播内容的回归显示,工具性信息,男性比女性高26.3%;网络规模每多1人,工具性传播减少0.083;经济型流动比非经济型流动的工具性传播高28.3%;懂上海话的比不懂的高24.7%。情感性信息,男性比女性低24.5%;已婚农民工比未婚农民工多12.4%,流动时间每长1年,情感性传播减少1.8%。社交性信息方面,男性比女性低14.1%;每年长1岁,社交性信息降低1.1%;流动时间每多1年,社交性信息增加1.2%。
四、结论与解释
(一)“内聚性”传播网络
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有较强“内聚性”:低异质性、高紧密度、小规模、内部交流频繁。传播网络有明显的群体界限——农民工更愿意选择和自己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社会背景相似的人进行频繁的交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提到的人际传播成员中,上海人仅占12.9%。除了工作等关系外,农民工较少与市民进行自主性人际交流。
“内聚性”特点既与农民工的居住方式、职业行业构成等客观因素有关,也和他们的主观心理有关。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分为聚居和散居。聚居主要是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很多聚居的农民工都表示,无论上班下班感觉不大——总是在厂里。有的企业更是人性化地设立了食堂、活动室、阅览室、小超市等,农民工基本上可以不出厂门而满足日常生活的所有需求。如此一来,农民工在接受企业福利的同时,无形中降低了接触更为广阔、复杂社会的需求。散居的农民工,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有足够的自由,但囿于城市高额的房租,他们只能在一些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中简陋地生活。时间一长,境况类似的农民工逐渐汇拢而形成了一个个“安徽村”、“重庆村”、“河南村”。可见,无论是聚居还是散居,农民工的日常交往对象,大部分还是农民工。就行业构成看,农民工的行业高度相近。主要集中在电子机械制造业、建筑业、服装纺织业、家政业、饮食业等。⑪“同乡同业”的情况也非常突出:文印业基本为湖南新化籍农民工垄断,果品批发业多为江西上饶籍农民工,自行车修理业则以江苏南通籍农民工居多。居住方式、职业行业等客观方面的高度趋同,使农民工处于一个巨大的同质性场域内,大大降低了他们与多元社会群体接触的机会。
“内聚性”特点,与农民工的主观心理也不无关系。经历了心理、价值观念、精神生活、归属意识等与城市文化的疏离后,尽管农民工已经渐渐适应城市生活,但内心深处,他们仍有着或多或少的自卑。例证之一便是,本研究问卷中对农民工群体的称呼,根据他们的建议,历经“农民工”、“流动人口”、“新市民”、“外来务工者”、“进城务工者”等多次修改,最终采用了“外来务工者”这一中性称谓。一个称谓的反复修改,足见农民工群体内心之敏感。因此,他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更倾向于与自己背景相近的人,从而避免被歧视。
(二)传播中的“差序格局”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中,也存在着“差序格局”。调查显示,与自我认识超过6年的成员比例,从第一位的41.0%依次降低到第五位的30.0%;不足3年的比例,从第一位的31.3%升高到第五位的45.2%。每天都有见面频率的人,从第一位的41.0%下降到第五位的32.0%;每天都有电话/短信联系的人,从第一位的23.6%下降到第五位的6.8%。提名顺序中,第一至第五位成员中亲属关系的比例分别是49.8%、38.9%、35.0%、34.0%、31.4%,逐步降低,非亲属的比例则从第一位的50.2%逐步上升到第五位的68.6%。从第一位成员是亲属关系的内部情况看,配偶/同居伴侣占23.1%,父母子女占13.8%,兄弟姐妹占9.1%,其他亲戚占3.9%,关系由近及远顺次降低。可见,农民工人际传播网中的提名顺序,会沿着家人、近亲、远亲、非亲属的差序由里及外、由近及远发散。与自我认识时间长的人,越可能较早被提及;与自我传播频率越高的人,越可能被较早提及。
与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稍有不同的是,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的“差序格局”中,主轴是横向的夫妻关系,而不是费老时代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妇成了配轴”。⑫农民工差序格局的重心,从父子、婆媳的纵向关系变成了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其中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又有群体自身原因。以核心家庭、小家庭为主的家庭结构,是现代中国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鲜明特点,在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中,亦如此体现。就群体特点看,青壮年的进城造成了大批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时空与境遇的迥异,使纵向关系产生了疏离。尽管如此,“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亲、熟、信三位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是中国人关系网络的根本特征”,⑬在当代社会依然适用,以亲缘、地缘建立起来的人际传播网,具有高度的可信任感。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民工人际传播网中存在的差序格局了。
(三)影响传播频率的因素
研究发现,仅有年龄、懂上海话对直接传播(见面)频率的影响显著,各变量对间接传播频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年龄不仅是人的具体生命周期的数字表示,更是个人社会资本及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样本中的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加,已婚比例从“25-29岁”的78.1%,到“30-34岁”的86.7%,再到“35岁以上”的95.0%,逐步上升。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日趋稳定,举家迁居城市的农民工比例也不断提高。已婚、与家人共同生活,是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在城市生活中出现的显著变化。近亲属占到了他们人际传播网成员中的大部分,这些人也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见面频率必然较高。
把上海话水平作为农民工融入程度的标志,是有充分理由的。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传播工具,通常决定了传播的规模、频度、内容等其他方面。首先,懂上海话,尤其是会说上海话的农民工,和上海市民的交流更顺畅,越容易和市民建立人际传播关系。其次,上海话能力的形成,既和农民工来沪时间长短等客观因素有关,也和农民工自我学习等主观因素有关。上海话能力越好的人,其融入上海的意愿越强烈。本次调查显示,懂上海话的人,其定居上海的意愿为32.4%,不懂的人定居意愿则为23.5%。再次,上海话水平也影响到农民工与市民交往中的自信心。懂上海话的人,其对上海本土文化有更好的理解领会,更善于用上海市民熟悉的情境、语境与他们交流,农民工主动交流意愿更强烈,心态也更平和,传播频率相应提高。最后,上海话能力也是农民工在上海生活的一项技能,很多岗位招聘,明确要求员工起码能听懂上海话。掌握了上海话的农民工,运用人际传播网寻求职业、住房、投资等发展机会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点从上海话能力对工具性传播内容的回归系数呈显著正影响也可以看出。
(四)影响传播内容的因素
人际传播内容方面的结论有:(1)男性的工具性传播多于女性,而女性的情感性、社交性传播多于男性。(2)已婚者的情感性传播多于未婚者。(3)网络规模越大,工具性传播越少。(4)流动时间对社交性传播有显著正影响,对情感性传播有显著负影响。(5)经济型流动农民工的工具性传播多于非经济型流动,懂上海话的农民工的工具性传播多于不懂上海话的农民工。统计显示,经济型流动的男性占63.1%,女性占57.5%,流动目的的差异,表明男性农民工进城,更多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只身闯荡。工具性传播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性利益,这一点恰好契合了男性。他们更专注于选择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人进行交往。女性农民工中,有一部分是因结婚、照顾家人进城,功利性没有男性明显。再加上女人的天性,她们互相间更容易聊情感方面的话题,更关注包括时尚、娱乐、衣着、饮食等在内的社交性信息。于是性别差异,开始逐渐影响到各自的人际传播内容。
三种传播内容中,与诸因素关系最密切的是工具性传播。这里想特别解释的是,为什么网络规模越大,工具性传播反而越少呢?原因有二。首先,网络规模越大,成员结构越复杂,适合传播不同内容的成员也就越多,从而为进行不同类型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专注于工具性传播的比例就降低了。其次,这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农民工人际传播中的体现。工具性、情感性、社交性内容,其实也遵循着递进的需求层次,只有满足了工具性传播,人们才会更多地考虑情感性和社交性传播。拥有较大网络规模的人,其社会资本也多,在满足基本的工具性传播后,他更愿意主动寻求情感性、社交性传播内容。这一趋势,从网络规模对情感性、社交性传播的正面影响也可以证明,只是尚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而已。
已婚者扮演着更多的社会角色,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他们更需要在工作之余向他人倾诉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情感性内容属于个人隐私,而隐私内容更适合在亲属内传播。已婚者与亲属共同居住的比例较高,这一居住方式恰恰为他们开展情感性传播提供了适宜环境。此外,在已婚者情感性传播中,很大部分包含了子女教育信息。将生活重心偏重于孩子,围绕孩子开展话题,也是该群体的显著特色。流动时间对社交性传播内容的正面影响,也不难理解。流动时间越长,在沪的人脉和社会资源相应越多,融入上海的程度越深,产生社交性传播意愿和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可见,在每一个回归系数的背后,其实都反映了农民工随着个人在城市社会资本、生活状态的变化,而对人际传播网络和传播行为的主动调整和选择。
注:
①[美]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过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56.
②人民网.上海农民工超过 400 万人[EB/OL].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62/7113564.html,2008-4-13.
③钱文荣.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长江三角洲十六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调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45.
④Bott,Elizabeth.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s[M].London:Tavistock,1971:45.
⑤Laumann,Edward O.Prestige and Association in an Urban Community[M].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6:274.
⑥Granovetter,Mark.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1360-80.
⑦ Marsden,Peter V.,and Jeanne S.Hurlbert.Social Resources and Mobility Outcomes: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J].Social Forces,1988(66):1038-59.
⑧Ruan,Danching.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93:35.
⑨Lin,Nan.Social Resource Theory[A].In:E.F.Borgatta and M.L.Borgatta(eds.).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M].New York:Macmillan,1992:1936-1942.
⑩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332.
⑪林建永,周莹.上海奉贤区农民工现状调查[J].经济咨询,2007(2):14-20.
⑫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7.
⑬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