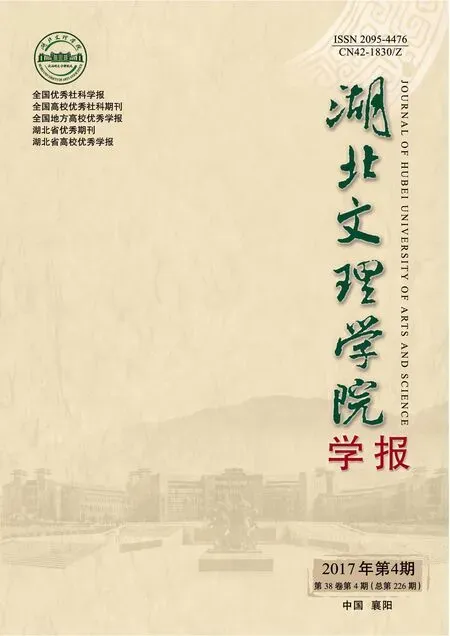立象以尽意
——谈弘仁山水画中的遗民气节与笔墨呈现
李超峰
(巢湖学院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8000)
艺术研究
立象以尽意
——谈弘仁山水画中的遗民气节与笔墨呈现
李超峰
(巢湖学院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8000)
明清之际新安画派的弘仁(渐江)秉持遗民立场,其艺术承继高远之态,标立抽象的线性几何形的巨嶂山水新貌,呈自我之象。立象以尽意,弘仁把笔墨意趣、画面形式和爱国情感完美结合,突破常规,自我作古,并籍此标立新貌,呈自我之象,创作出一个属于他个人的崭新的艺术真境,在明清画坛上树立了新安画派的这一面旗帜,成为同时代的翘楚。
山水画;新安画派;弘仁(渐江)
明清之际,新安画派渐露峥嵘,以弘仁(渐江)为代表的新安画派崇尚简淡,其山水的典型艺术风貌为画坛一面旗帜。弘仁俗姓江,名韬,明亡后出家为僧,释名弘仁,号渐江,主业山水,其与原济(石涛)、朱耷(八大山人)、髡残(石溪)并称为清初四僧,故后世多以弘仁、渐江称之。作为遗民画家的代表,弘仁(渐江)在反清复明未果后,隐居山林,寄情山水,同时又心系大明王朝,在其山水画中以简、淡、直线、少皴的笔墨呈现个人的山水视界。其典型的山水视界使得弘仁(渐江)从古人及同时代的画家中脱颖而出,其标立巨嶂几何山水之象,隐晦地诠释、传达了自己的遗民气节,寄托了其对大明王朝的热爱。本文从具体的山水画作入手,试论弘仁(渐江)山水画中的遗民气节与笔墨呈现。
一、遗民气节——隐而含蓄的情感
中国历史上两次“异族”入侵的时代,一是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一是清代满人取代大明王朝成为天下之主。以渐江为代表的新安画派诞生于明清之交,见证政权的更迭,亡国之痛是他们挥之不去的伤痛。作为有气节的文人,新安画派诸家秉持“遗民”立场,师法先贤,兼师造化,而自张赫帜,引领新安画派成为同时代的翘楚。众所周知,所谓“遗民”是对新朝持不承认、不合作立场,坚决与新朝划清界限。其是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的文人雅士。诚然,王朝的更替使得新安画派诸家怀有着愤懑、不屈的情绪。这种情怀在战乱时期以两种行动状态呈现:一是参加反清复明的抗争;二是隐居避世,不涉仕途。新安画派的弘仁、程邃等为明诸生,既参加反清复明的抗争,又在抗争失败后退隐。如弘仁(渐江)在清军攻破南京后,“自负卷轴、偕其师汪无涯入闽”,程邃在明清易祚曾随黄道周、杨廷麟参加反清复明的斗争。虽然未能光复大明主权,但二人的气节是毋庸置疑的。但迫于清廷统治的渐趋稳定,以及清廷对乱党的缉捕,加之当时的政治原因,迫使新安画派的画家大都选择退隐。从立场来看,弘仁(渐江)属于典型的遗民立场,明亡后,渐江出家归隐,远离朝堂;程邃自号“垢道人”“朽民”,拒绝一切功名利禄,归隐扬州。在清朝统治稳定后,身为遗民的文人阶层,无力改变政治格局,皆选择了退隐。对于大明王朝的怀念没有随着退隐生活而消逝,这种情感在他们的作品、诗词等方面流露出来,其遗民气节以一种隐且含蓄的方式呈现给观者。
为什么新安画派的诸家具有遗民气节,但却以隐而蓄之的情感来传达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促成这样隐晦的情感传达有内、外两种因素:第一,政治因素,这是不可抗拒的外在原因。即前文提到的明亡后清廷统治的渐趋稳定及当权者对反清复明义士的迫害。众所周知,文人追求的理想不外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明亡后,文人的气节使得其“兼济天下”理想的幻灭,那唯有退一步求得“独善其身”。渐江作为同时代的文人,属于典型的遗民画家,其忠君爱国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王泰徵在《渐江和尚传》中言:“论曰:《南华》,世外之书也。而读《人间世》一卷,仲尼之语子高,义命两大戒。父君两大事,娓娓烦言累牍,乃知臣忠子孝,即是世外至人。甚矣,漆园之微于托也。”[2]4复言:“夫师少而养母,壮而羁游,鼎鼎百年之间,与海内名人巨子之交,无不器重师者。乃不婚不宦,赍志以殁,可谓茫然无一寄托,止以翰墨行乎?”[2]5“漆园之微于托也”隐含弘仁(渐江)出家乃是忠于明皇朝,谓之“臣忠”、“师少而养母”谓之“子孝”,弘仁(渐江)的本心是对于明室的热爱,早年习举子业,明室被取而代之,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不婚不宦,赍志以殁”,言明其坚持志愿而不得直到死去。忠于的明室覆灭,其“可谓茫然无一寄托,止以翰墨行乎?”。明亡后,弘仁(渐江)远离朝堂“独善其身”,在精神上无所寄托,唯有在书画世界里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寄托自己对大明室的热爱。但在当时的政治迫害下,“独善其身”亦是不能发声,“隐逸”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这个外在的原因迫使文人画家不得不以“隐晦”的方式来传达其内心的爱国情感。第二,徽州乃理学之邦,在程朱理学熏染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文人忌情感上大起大落,讲究情感的含而不露。作为新安画派诸家也是文人的代表,虽经历明亡的屈辱悲愤,但这种对故国的爱也不是以张扬的表现方式来实现,在情感的传达上也不可能象八大山人那样癫狂。这是情感含蓄表达的内在原因所在。所以,在面对亡国之恨,无论是外在的因素还是内在的因素都使得新安画派诸家不能张扬地表达自己的好恶,唯有借助诗画来寄托爱国情怀。观《渐江资料集》可知,弘仁(渐江)诗文不称之为诗,谓之“画偈”。“画偈”不是佛家的“偈”语,是弘仁(渐江)在反抗清廷而又力求不被迫害的选择,是其个人内心情感的坚守。渐江诗作画“偈”乃是佛理的隐喻,渐江借用佛家“偈”语,行缅怀故国之情。如画偈中有言:“渔舟泊处遍桃花,岸上茆堂是酒家;欲挽秦人来此住,请看鸡犬和桑田。”[2]38复言:“偶将笔墨落人间,绮丽楼台乱后删,花草吴宫皆不问,独余残沈写钟山。”[2]39惓怀故国之情,溢于纸面。“为爱门前五株柳,风神犹是义熙前。”[2]34“先辈曾谭正仄峰,峰前可有六朝松?何年借尔青藤杖?再听牛头寺里钟。”[2]35“卜兹山水窟,著就冰雪卷。言念西台人,将无似君善。”[2]32我们通过弘仁(渐江)的题画诗等都可以窥见他这种遗民情怀。
二、立象以尽意
传统山水讲究以象立意,“象”顾名思义乃是客观事物、自然真景,亦是画家所构建的艺术图示。“立象”乃是画家主观地对自然物象进行提炼,其提炼的客观物形传达画者的情感,是艺术家主观情思活动的结果。古人所谓的“象”就是所谓的物象、形式,中国画历来讲究画者自身的修养,对于主体的“修身”大于对“象”的重视与探讨;但是画者主体情趣及笔墨意趣的表达必须依赖于丰富的语言形式,经营位置中的形式构思。立“象”以尽意,弘仁(渐江)其艺术图式继承了北宋高古的“巨嶂式”构图,是一种标格的展示。受新安自然景观的影响,多石疏树的黄山促使渐江以线条为主的画法来描绘多角的山形,构成了抽象性线构图,使其画面具有了节奏、韵律、对称、均衡、秩序感等形式美的内容。由弘仁(渐江)的绘画作品《天都峰图》《松溪石壁图》《雨余柳色图》《黄山图》等等可以窥见,其作品皆是以徽州、黄山等为蓝本,取黄山之典型的地理状貌,构建了巨嶂式几何山水的真境。
稽古溯源,弘仁(渐江)的巨嶂式山水承源于宋之巨嶂山水,但形态各异,貌合神异。从貌上来看,其山水与北宋的巨嶂山水都以高远之态呈“巨嶂”山水之姿态,这点来看,有其合的元素,但从弘仁(渐江)山水的几何形态、平面、装饰的状貌来看,貌又不合。从神上看,北宋巨嶂山水传达个人的情感和对山水的热爱;而渐江的山水不仅传达对山水的热爱,更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情怀,秉持遗民的立场。程青溪有言:“画不难为繁,难于用简。减之力更大于繁,非以境减,减之以笔。此石溪、石涛之所难,而渐师得之。举重若轻,惟大而化。”[2]237青溪老人对于弘仁(渐江)绘画的繁简之道有高度评价,举重若轻,惟大而化,减之以笔而境界犹在。在极简的艺术特色中,弘仁(渐江)渐江营造了亦真亦幻的山水真境。
黄宾虹曾在《黄山图》中自题:“黄山旧名黟山,林壑幽翳。渐师已倪迂笔写之,可谓得其骨格,而成雄浑厚,似犹未足。余以巨然法图此,山灵当许我也。”[1]214-215这里且不论宾虹老人黄山图如何,就渐江的黄山图而论,侧重点则有所不同,弘仁(渐江)重在构图形式、笔墨意趣与爱国情感的结合,尤其体现了他本人对黄山的感悟,其中黄山骨骼、山灵也尽被揽于画中。如《西岩松雪图》《天都峰图》是极简风格的代表作,亦是遗民气节和极简笔墨完美结合的图例。我们通过这两幅山水来具体分析渐江如何将遗民气节与画面的形式和笔墨完美呈现的。第一,从画面的布局来看,《西岩松雪图》《天都峰图》的构图都是宋之“巨嶂山水”的构成的继承之作,前者以局部特写的形式展现山峰雄伟之势,后者则整体呈现了天都峰的巨嶂雄姿。在构成上二者皆平面,在山体的呈现上二者均施之淡墨,与山相较,树木着墨稍浓。

图1 渐江《西岩松雪图》

图2 渐江《天都峰图》
《西岩松雪图》中,弘仁(渐江)以落雪之白营造整体的画面气韵,雪的清空之疏与树的繁密对比强化了画面的虚实对比,这是画者独具匠心的安排和处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表现出山川景物的浑厚与生动。第二,线性的几何抽象形式。线性的简淡艺术风格是新安画派的主色,尤其以弘仁(渐江)为最。《西岩松雪图》中全画山石尚简,以线构成为主,略加渲染,凸显雪景之白。弘仁(渐江)用干笔淡墨勾勒,浅淡的皴擦目的是为了丰富画面的明暗与质感。而《天都峰图》可谓是弘仁线性的几何抽象形式的代表,远观其线条刚硬挺直,细观之,其线条则是极有耐性的,具有书法笔意式的书写,其画作中任何一根线的勾勒都是极其缓慢而讲究的。状似几何平面,又非生硬的线之集合。研读上述两图可知,弘仁笔下的线条都呈现坚韧挺拔、刚劲凝重之态,即使是纤细如发亦无一丝一毫的媚态。在描写造型时,渐江以涩笔刻画强调轮廓,舍墨皴之法染,取以线制形、平面、装饰之感营造别样的形式美。由此可见,弘仁绘画形式既不是几何形状的简单组合,也不是忠于对象的描绘的写实。在其作品中,既有一点一线的几何块面的归纳,也兼蓄理性思考的审美观念。在弘仁的绘画中,他对大自然如黄山的看法,对艺术的理解、艺术的媒介主体精神等方面都在形式取舍中获得了典型性的表现。“大自然可以随画家的风格而变形,也可以随画家的梦幻和憧憬的转换,而随之变形。换言之,画家可以用一种抽象化、净化的幻化之景来表现现实的世界,弘仁的作风即是如此;借着几何抽象形式所蕴涵的解放力,弘仁显露了他个人内心平静的境界。或者画家也可以将非真实的世界营造的如真实一般,使他们看起来宛如具有实体,且在视觉上具有说服力……”[3]如高居翰所言,弘仁(渐江)绘画借着几何抽象形式所蕴涵的解放力,显露了他个人内心平静的境界。以线塑形,几何山水典型的式样是渐江的个人语言,其画既不是太具体而流于拘谨,亦不因忠于自然而缺乏思想的表面形式,其借“抽象化、净化的幻化之景来表现现实的世界”。第三,从情感、心境呈现上来说,《西岩松雪图》《天都峰图》都是渐江心境的写照,是其遗民气节的外在呈现。黄宾虹先生在《渐江大师事迹佚闻》中说:“世事沧桑,黍离麦秀之慨,至不获已遁入空门,歌泣声沉,寄之于画,偶然挥洒,无非写其心史,不必求工而已无不工者。”[2]214宾虹老人道出了渐江借画写心史的无奈,从表面看,弘仁(渐江)在明亡后出家归隐,不问世事,但实质上,渐江对大明王朝的热爱无处不在,家国已不复,但大好河山依然在。其“歌泣声沉”流露出对大明王朝的热爱,遂“寄之于画”来书写内心的情感,这是具有遗民气节的文人画家所选择的道路。无论是《西岩松雪图》,亦或是《天都峰图》,无不是大山高耸,山石状若刀削。其描绘的山体险峻挺拔,偃松傲立,这些傲立的偃松,险峻的山石是渐江爱国情怀的寄居之所,其刻意将不屈的松树与峭拔的山岩精心布局,在其高度净化后构建抽象、概括、简洁的艺术形象,呈现萧疏、冷寂之高境,得风神懒散、气韵荒寒之奇致。可以说,作为明季遗民,渐江营造的圣洁不污的高境都是其情感依托的形式。
纵观弘仁(渐江)一生,其自幼受儒学熏染,习举子业。明亡后,举旗反清复明,未果则出家为僧,远离朝堂。弘仁(渐江)的忠君爱国立场是鲜明的,在山水画中,弘仁(渐江)承继高远之态,突破常规,自我作古,创作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崭新的艺术视界。弘仁(渐江)在其爱国情怀和黄山真景之间找到了一个的契合点——标立线性几何形的巨嶂山水新貌,呈自我之象,将爱国情怀情感和形式、笔墨完美的融合为一体。正如克莱夫·贝尔所言:“形式与情感意象之间哪怕是一个部分的不想符合,这个形式就会破坏·……”[4]渐江用了“巨嶂几何式的山水”这种典型的形式语言构建了新的山水秩序,与自然真景拉开了距离,并依托巨嶂几何式的山水来书写其内心对大明王朝的热爱和缅怀。就观者视觉而言,这不仅是山水构成的因素,更是渐江树立、造就的稳定坚实的艺术高境。
[1] 郭 因,俞宏理.新安画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308.
[2] 汪世清,汪 聪.渐江资料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3] 高居瀚.气势憾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32.
[4] 克莱夫·贝尔.艺术[M].周金环,马仲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68.
(责任编辑:刘应竹)
J205
A
2095-4476(2017)04-0071-04
2017-03-09;
:2017-03-29
安徽省优秀青年基金重点项目(2013SQRW069ZD)
李超峰(1980—),男,安徽蒙城人,巢湖学院艺术学院讲师。
——赏析《爬天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