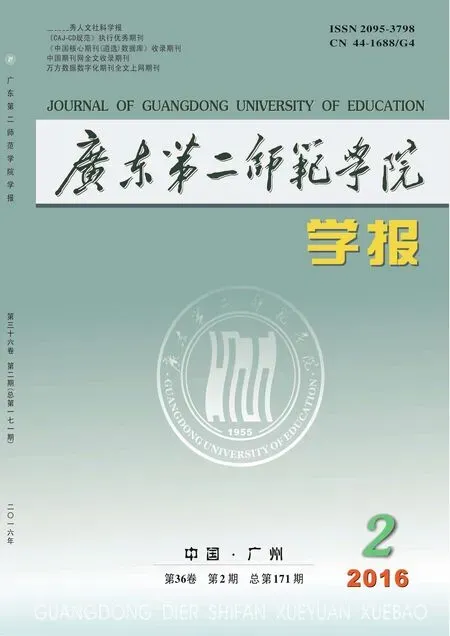焦虑与虚妄的“自我”建构
——米兰·昆德拉小说《身份》细读
郝朝帅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303)
焦虑与虚妄的“自我”建构
——米兰·昆德拉小说《身份》细读
郝朝帅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303)
摘要: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身份》,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个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建构可能。小说在一对中年情侣的情感聚散中,阐明了个人既无法自外于整个世界来建构起自己的身份,也不可能躲进心设的爱情中证明自身的存在,而在来自“他者”的目光凝视下,独立的“自我”身份更是脆弱无比。由此小说中也弥散着昆德拉创作中一贯的虚无感。
关键词:《身份》;自我;外部世界;爱情,他者
“身份”,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它是个人根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1]这是一个人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行的辨析和确认,它不同于外界对其 “角色” 的安排或指定,必须要通过主动的识别才能建构起的自我认同。而且,“身份”是一个只有在现代社会才产生的概念。在前现代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基本固定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很少有机会穿越自身所属的社会阶层和文化环境,在沉滞轮回的生存状态中,一切都可以在既成秩序中找到意义,不会产生身份的焦虑与自我认同的危机感。只有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在重新建构起的社会关系、伦理结构和心理模式中,人们原本稳定的自我认知才可能出现坍塌,才需要进行重新的考量和定位——只有在这时候才可能产生个人身份的焦虑。
当然,理论的解释总是显得枯涩:“理论对身份的处理与小说对身份深入细致的挖掘相比似乎是简化了。小说的挖掘能够在表达独特实例的同时又依靠含蓄概括的力量,巧妙地处理普遍的追求和期望。”[2]于是,我们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身份》*《身份》,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对原文的引用均出自该版本。中发现了这个重要的现代命题被展露得纤毫毕现。《身份》属于昆德拉后期作品,是作家流亡法国、继而被剥夺了捷克国籍后以法语完成的小说。作为一名离散作家,昆德拉在这部作品中表达了他对一个稳定“身份”的强烈不信任。但是,他在这部小说中却并没有征用与自身经验密切相关的、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仅仅是通过一对普通中年情侣的一次情感危机,就将这一命题表达得透彻而无望。在浓浓的哀伤低徊中,始终弥散着一种无可言状的紧张。真实与虚幻、理想与现实、逃避与抗拒、自认与他认、关怀与误解……种种错位与尴尬彼此缠绕,充满了无从把握、无法拥有的不安全感。作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昆德拉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显示了他强有力的深度,或者说,刻毒。
一、 “自我”与世界
小说的开始,是已经不再年轻的职场女性尚塔尔与小她四岁的情人让·马克一起来到海滨度假。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同时对身边这个虚张、刻板的世界充满蔑视。尚塔尔身世坎坷,一直在审慎地考量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博弈力量,在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现实的羁绊间找到心理平衡的支点。她最早生活在前夫俗气热闹的大家族中,每到假期,他们就像一个部落群体一样聚居在一座乡间别墅。在那里她时时刻刻能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窥视和控制欲望。然而,她当时并没有去试图摆脱这种状态,因为他还有一个儿子。“我不可能有了一个孩子以后还去蔑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把孩子送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因为孩子才依恋这个世界,考虑这个世界的未来,参与它的那些喧哗,那些骚动,把它的那些不可救药的愚蠢之事当回事。”这是她最初的妥协,充满母性光辉的妥协。然而,儿子在五岁时夭折了。他的死也带给尚塔尔找回自我的勇气,她决心离开这个家庭。为此,她首先换了一个高收入的工作,这是她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几年之后,在她遇到了现在的男朋友让·马克后,尚塔尔迅速和前夫离了婚并买下了一套公寓房,和心爱的人一起住了进去。
能够看出,尚塔尔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理性的,在缺少足够的安全感时,她不会做出不顾及后果的决绝选择。为了从原先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她会先换个工作,虽然这份工作是她所不喜欢的。“她对自己这样因为金钱而背叛自己的喜好而于心不安,但又怎么办呢,那是她获得独立的惟一办法。”而她没有找到自己所爱的人之前,依然在原先的婚姻关系中维持了几年,这是她的再次妥协。在一次次的妥协中艰难换来目前的稍许理想状态,这决定了她非常害怕失去目前的生活(即与情人的分手),那意味着她之前所付出的一切都化为乌有。对于未来的生活,她也是充满悲观和焦虑的。当和情人让·马克在一起生活很多年后,某一次他们在海边,在一片圣洁的“白色沐浴中”享受着天堂般的纯净与惬意时,她涌现心头的,居然不是幸福感,却是一种不祥的未来展望:“一种难以承受的对让·马克的怀念之情”。面对着自己的爱人,“她隐约看到了爱人会不在的将来。”这种低迷的情绪永远在环绕着她。虽然她在不同场合拥有过、拥有着不同的角色和面孔,可是这些面孔只是为了能够维持她心中的那一副,在心爱的人面前的那副最本真、最放松的面孔。可见,活在焦虑中的尚塔尔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既不是来自于内心对自己的坚定确认,也不是来自与所处社会的互动,只有与让·马克的爱情才能让她能体会到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她热爱她现在的生活,在任何条件下也不愿意将它与过去或将来作替换。”
米兰·昆德拉精细入微地描摹出当代人对于自我生活的无法确信、无法把握感。尚塔尔的状态和心态非常具有普遍性:生活中无数现代人和她一样辗转于现实与梦想之间,在妥协与反抗的交替中艰难地寻找着内心的平衡。对于生活,他们也是小心翼翼,过去的消逝了,无法给现在的生存提供意义,未来的更是无法把握不敢奢望,只有眼前的生活才是真切可感的、唯一显得踏实一些。每天人们都要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中来回游走,而让他们能够脱去重负、回归本真的庇护都是一个心设的“世外桃源”,只有逃进这里才可以无视外面的风雨,才能做到心中真正认同的那个自己。这座世外桃源在尚塔尔这里是爱情,在别人那里也可以是某种其他的事物,在当下甚至可以是网络中一个虚拟的头衔。人们需要它来体会自己的存在,一旦意识到了它也有可能消逝,就会立刻变得惶恐不安。
而尚塔尔的情人,稍许年轻的让·马克却和她完全不一样。他会不顾一切地放弃很多东西,只要他感到这个东西他开始厌恶或者怀疑时。年少时的友情,未来的医生职业,他都可以轻松毅然地抛弃。尽管他知道这样做自己也就被一次次放逐到社会的边缘,但他并不怜惜,反而很享受这种状态。让·马克的人生完全是率性而为的,他换了很多种工作,依然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敏感和厌弃。只是他并没有将这一点做到彻底:他仍然需要爱情。虽然他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两个人志同道合地嘲笑身边的世界,以此滋养面对面的相见时刻。尚塔尔“是他跟世界的唯一感情纽带”,他全身心地爱着她,时刻担心着失去她。但让·马克对两人的爱情没有任何隐忧,或者说对未知将来的提前怀念。在这个爱情结构中,他处于心理上强势的一方。对他而言,整个世界的疯狂和荒谬,只能更加强化自己的优越感,让他保持着足够的骄傲。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看似坚定无比,与尚塔尔的爱情只是这一认同的必然结果,两个人的爱情对他而言只是更加确认了这个世界的可笑。
让·马克代表了现代生活中的另一种人。如果说尚塔尔们是以妥协、躲避来抗衡现实的话,这类人可以说是用貌似超越的虚妄感来抗衡现实。他聛睨一切,游走在社会生活的边缘,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看着人们在身边上演的种种可笑之举。他不愿意负载任何现实的压力,不认可任何对现实的妥协。这样,他虽然活得很轻飘无根,但总以为自己活得很深刻。这样的人不会认为自己存在着身份的危机。
在性格与角色的偏差中,二人间就有了误会/冲突的发生。青春不再的尚塔尔,惧怕他们的二人世界也会有一天变得和海滩上的大多数人一样,沦落到世俗的家庭生活中。而她的情人却误以为她只是在担心自己年华逝去。他用心地编织了一个小花招想哄得她开心,却不想这个游戏也伤害了二人的感情,尚塔尔在愤怒中与情人决裂了。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彼此理解错位的尚塔尔和让·马克,在难以廓清是梦境还是真实的世界中各自经历了一番冒险。离别了恋人的尚塔尔,骤然间被卷入一场荒唐而恐怖的群交游戏中,她惊惧交加,却总也逃不出那所怪异的旅馆,她赤身裸体,被剥光了一切,而且连名字也被人更改了。她彻底地在世界上被取消了,虽然还有肉身的存在。而让·马克,正如他一直在形容词意义上的自我定义那样,在实际生活中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者,一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果然,失去了彼此的依偎,他们就失去了一切,世界对他们变得恐怖无比,而他们的个人存在也没有了任何意义,甚至痕迹。不过,昆德拉没有坚持让自己“冷酷到底”,他用非常传统的方式挽救了他的男女主角。原来那最后惊悚的经历果然是一场噩梦,梦醒处,两个人的爱情依旧,彼此依赖。他们仍然能够在世界的边缘,延续他们的“异端行为,对人类共同体不成文的法令的违背”。
作为现代人生存寓言的《身份》,虽然它留给人们一个温情的结局作为心理抚慰,但其刻毒的手术刀,已然划开了自欺欺人的心理防护层。尚塔尔和让·马克的悲剧性在于,他们都试图站在整个世界和社会的对立面上,建立起个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然而,生存于现实空间中的人们,却都是需要在社会中来塑形定位、来给予自己某种身份,人们的身份识别,可以产生于诸如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等差异维度。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把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认作异己的时候,得到的都只能是一个虚妄的、却自以为是的“自我”。当这种自设的身份与坚硬的社会现实劈面遭遇的时候,顷刻间它就会土崩瓦解。
通过与身外的世界为敌而取得的“自我”身份是无比虚弱的,而二人之间,无论是谨慎理性的尚塔尔,还是放肆不羁的让·马克,其内心都是不健全的,都不能依靠自己健康的人生态度获得完整的自我身份,必须要躲进彼此小心经营的爱情里互相取暖,获取存在感。然而这份爱情又是怎样的呢?
二 “自我”与爱情
在小说中文版的最后,附着一篇评论家弗朗索瓦·里卡尔对本书的评论《情人的目光》。“事实上,《身份》与昆德拉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可以看作是对爱情的思考。”他认为,唯一可以认出自己真正的面孔的,是爱人包容的目光。“两个人的眼睛再不移开,因为他们知道各自的身份就包容、隐藏、寄存在对方的目光中,那脆弱的目光将他们连在一起,并在他们身旁形成一个代表着他们孤独和幸福的白色阳台。”很显然,论者愿意采用一种相对闭合的理解,认为爱情会赋予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确认,藉此带给人们以希望和信心。然而,这绝非是昆德拉的答案,毋宁说,这种视“爱情”为人类最后庇护所的想法,恰恰是昆德拉试图表达生命之无望时最着力消解的,也是这本锋利的小说最初的、残忍的下刀处。
《身份》当然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它更是一部反爱情小说。它让人们看到,当爱情自身也只能是脆弱生存的时候,它对于个人的拯救能够有效吗?更进一步还可以设想,如果解构了爱情,人们还将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还能逃到哪儿去藏身呢?
在叙述的边边角角,小说总是让人看到了这份爱情的脆弱。首先是他们二人并没有真正达到那种“心心相印”的爱情境界。尚塔尔早于情人一天来到了度假的海滨,在等待让·马克的时候,她愕然发现,海滨上的男人们都是和家人在一起,尾随着妻子,推着婴儿车,身上甚至还背着抱着另外的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逃离了世俗生活的尚塔尔被这副场景吓到了,很显然她想到了未来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天,心爱的人像海滩上所有的男人一样,不再沉湎于爱情,只是一味在沙滩上散步、放风筝。这种惶恐刺激了她,当见到自己的情人时,尚塔尔失魂落魄。但又该怎样告诉让·马克自己的失落呢?面对情人的追问,她言不及义地说,“男人们都不再回头看我了。”这句话,于她而言,是预想到爱情消逝后对人生的恐惧,而让·马克无法明白她真正想说的,只认为这是任何一个青春逝去的女人都会有的惯常心态。正是因为这种理解错位,才会引发后面故事的中心冲突:匿名信事件。如果真的是一对彼此完全信任、完全坦诚交流的情侣,根本就不会发生后面一波三折的故事。
而且,由上文分析可知,尚塔尔非常在乎自己目前的爱情,可她对爱情是怎样的心态?当她发现自己的情人为了取悦她设计的花招时,她不能接受的不是情人可能存在的背叛,“假如尚塔尔有一天得知让·马克对自己不忠,她会痛苦,但这可以说是在她的意料之中的。”她不能接受的是认为自己被情人所“窥视”,尤其是他翻动了自己的衣橱,发现了自己不想告诉他的隐私。尚塔尔觉着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个人空间,她告诉让·马克:“没有任何人可以打开我的衣橱,在我隐私的东西中翻来翻去。”“我以前买下这个房子是为了自由,是为了不被人窥伺。”
在这里,有理由认为,尚塔尔对爱情的珍视,说到底还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她真正在乎的,还是自己的自由空间。爱情,在这里好像并不是情感上付出与得到的无私满足,而更像是一种功利性的存在。是为了巩固她个人的自由,填充她那套属于她私人的公寓房间的某种材质。或可说,她其实一直是在利用着爱情,虽然自己也的确在付出。在现代生活中过于沉湎于自我的个体,永远无法走出对一己的关怀。尚塔尔的爱情,出发点和皈依处其实都是对自己的爱,以此对抗对生活的恐惧。
同样,对于让·马克,他对爱情的理解也是非常自我,他总是信心满满地处理二人之间的关系。有一次在餐馆吃饭时,他们看到了旁边一对一直没说一句话的男女,他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没有任何爱情可以在一言不发中存在”。显然,他和尚塔尔远没达到那种情人间常有的“默契”,那种无需语言的情感交流。而他喋喋不休的谈话内容,却总是对这个世界无休止的嘲笑。当尚塔尔告诉他,他们可以一起说些别的话题时,他不以为然。他认为,滋养爱情的就是身边这个让人瞧不起的世界所提供的话题。他也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来处理两人的爱情,并没有尽力走进对方的内心去倾听她的声音。引发决裂的匿名信事件,就是两人互相理解错位的明证(下文将详述)。
而更有摧毁力的是,让·马克的爱情,更在物质根基上就是被抽空了的。在这里,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伤逝》。“人必须首先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让·马克活在对世界的冷嘲热讽中,完全没想到在物质层面,他是处于依附一方。他的工资是尚塔尔的五分之一,两人同居的公寓房,也是尚塔尔买的。这样,当感情危机出现的一刻,尚塔尔会在爱情天平上瞬间转为强势,而热衷于夸夸其谈的让·马克,却只能像任何一位身边的流浪汉那样无家可归。“谁是强者呢?当他们俩处于爱情的土壤上时,可能真的是他。可一旦爱情的土壤从他们的脚下逝去,她就是强者,而他却是弱者。”
昆德拉对所谓爱情的物质性的刻意强调,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在决裂之前,这一点在小说中基本没有被提到过。这是全书中最吊诡的一刻,爱情出现波折的时候,物质性的重要立即在前台呈现。这种安排,其实不是按照爱情小说套路走来的结果。爱情叙事的经典桥段,应该是情人如何解释自己的良苦用心,如何化解开对方的心结,而且经历过这番误会之后,两人的爱情上升到了一个更融洽亲密的阶段,最终彼此的心更近了。可以看到,昆德拉在关键时刻抛出的这致命一击,让躲避在心设小屋中的人们立即回归到对现实的依附,从而宣判了爱情庇护的有限性。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名成年人,一个稳定“身份”的建构,是必然离不开物质化保障的,这虽然不浪漫,然而却是无情的真理。
三、“自我”与“他者”
关于尚塔尔和让·马克之间的爱情,小说还提供了更宽阔的解读空间,可以让人们进一步了解昆德拉对现代人“身份”建构意愿的不信任。小说的中心情节冲突,就是一个典型的“凝视”事件。而男女主角也在不同场景中,彼此对对方也都有一种自觉的“凝视”动作或心理。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在主体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他者的‘凝视’(gaze)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者的‘凝视’促进了个人的自我形象的塑造”[3](存在主义之于昆德拉的渊源与意义学界早有定论,《身份》中也有诸如“您的自由就在这选择之中”这样典型的萨特式表述)。而这个作为凝视行为发出方的“他者”,在存在主义的视域中,可以迫使主体对世界产生一种认识,并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中进行定位。
能够看到,《身份》中这种来自“他者”的凝视目光,首先被昆德拉用了一种巧妙的装置来承担,那就是让·马克杜撰出的那位神秘的仰慕者。当听到尚塔尔说“所有男人都不再回头看我了”后,为了取悦她,让·马克煞费苦心地编织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他杜撰出一位神秘的仰慕者,不定期地给尚塔尔发出一封封充满关注与热情的匿名信,对她生活的点滴细节都给予礼赞。
昆德拉这样处置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一道“他者”的目光,虽然可以说是来自让·马克,但是又以一个陌生人的名义发出,于是在男女主角之外,似乎凭空增加了一个无处不在、却又无可寻踪的第三个人。而这样来自二人世界之外“他者的凝视”,却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尚塔尔个人的自我认同与让·马克对她的身份认同都陷于崩溃之境:这些火热的信件奏效了,尚塔尔变得兴奋而快活,经由这副“借来的目光”,尚塔尔增强了自信,“她从各个角度看自己,慢慢提起衬衣的衣角,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显得过那样修长,皮肤从来没有那么雪白”,甚至当她和情人做爱时,“监视跟踪她的那个人的意象使她兴奋”,这一“被窥视”的感觉激发了她性爱中的激情和幻想。尚塔尔像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女人一样,会为赞美陶醉,会在乎仰慕者的感受,甚至会为了这道隐秘的目光而买了一件红色的睡衣。于是,尚塔尔不知不觉成为“一个不愿意衰老的、绝望地抓住别人的目光以确信自身的存在与美丽的女人的身份”,而不再是那个拒绝了全世界,除了让·马克的独一无二的女人。她表现出来的兴奋反应对于让·马克而言,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悄悄地,它将一个被爱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被爱的女人的虚幻的幌子。而且她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女人,在世界没有价值的一片混沌中,再也没了任何稳定的支点”,“这个尚塔尔一点也不像她;这个尚塔尔不是他所爱的。”当跳出二人固有的彼此欣赏的目光时,来自外在的“他者”的凝视,让尚塔尔的“身份”定位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游移,始料未及地宣判了他们高调的遗世独立姿态的虚弱无比。
当然,在这个作为“第三个人”的他者的凝视目光之外,在男女主角的二人世界中,他们也同样互为凝视的对象,互为他者。小说中也一再强调他们这一行为:“他慢慢走进她,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看着她,目光那样集中,让人不舒服”,“让·马克的脑袋,脖子靠在枕头上,尚塔尔的脑袋,在他上方十厘米的地方俯瞰着他。”而和来自第三方的“他者”不同的是,他们两人不仅在对方的凝视中作为对象建构自我的身份,也在这种凝视中作为主体来确认自我的感觉。
情人间的目光,本应是人群中最传神最会心的对视交流,但他们的彼此凝视却总是让双方都感到局促不安。对于让·马克,他心中的尚塔尔是一个形象,可是他经常见到的、感觉到的尚塔尔却是另一种形象。而后一种形象完全是属于别人的,属于那些在他心中完全只能够提供嘲讽材料的人。而即便在生活中,他也有可能把她和别人发生混淆(他在小说中出场时,就是在海滩上找寻尚塔尔,结果却发生了误认),他为此也感到迷惘和可怕。他会对尚塔尔说:“你成了跟我想象的不同的人。我把你的身份搞错了。”作为“凝视”的主体,他害怕尚塔尔会变成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那样他将失去和这个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他担心“有一天,他会突然认不出她来……她会在他眼中变得跟所有别人一样的无所谓”。
在让·马克的目光中,尚塔尔会拥有不同的面孔。同样在篇末,在尚塔尔对他的凝视中,她说,“我怕我的眼睛眨。我怕在我目光熄灭的一秒钟里,在你的位置上突然滑入一条蛇、一只老鼠,滑入另一个人。”在她作为“他者”的目光中,让·马克是他的挚爱,但对于自己的情人尚塔尔还远谈不上深入的理解,所以她不敢让他脱离视线。这也是他们爱情脆弱的实质。“两个人的眼睛再不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各自的身份就包容、隐藏、寄存在对方的目光中,那脆弱的目光将他们连在一起,并在他们身旁形成一个代表着他们的孤独和幸福的白色阳台。”
四、结语
小说何以如此悲观?难道现代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真到如此虚妄吗?有学者认为,对于米兰·昆德拉而言,从政治信仰破灭、丧失家园,到流亡异邦、身份和作品遭遇双重误读,他面对的始终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异质文化空间[4]——或许正是缘于个人充满边缘化、疏离感的一生,促成了昆德拉对“身份”命题的深入思考,以及过于冷静而残酷的结论。但小说《身份》,作为他后期法语系列创作之一,昆德拉一直刻意将他的笔触离开自身的捷克经验,而关注西方社会现实共同的经验。所以,如果粘涩于作家的个人身世解读《身份》,应该相对偏离了作家的本人意愿。
不过,也许正因为一生的颠沛流离和边缘处境,阅读昆德拉的小说,总是让人感觉到被无边的“虚无”所包围。在他的作品世界里,信仰、政治、爱情、友谊、记忆……所有这些都无法产生正面的意义,而且还总是被举重若轻地消解掉。即便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中,昆德拉依然在说:“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5]有理由为此感叹,作为对人间一切意义都采取消解姿态的小说家,一位资深的诺贝尔文学奖“陪跑员”,米兰·昆德拉的消极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小说的世界和人类精神的世界,彼此又该建立起怎样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美)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8.
[2]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17.
[3] 张剑.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
[4] 解华.米兰·昆德拉的欧洲文化身份建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8-102.
[5] (捷克)米兰·昆德拉.庆祝无意义[M].马振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27.
(责任编辑王玉燕)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xious and Hopeless “Self”—On Milan Kundera’sIdentity
HAO Chao-shua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P.R.China)
Abstract:Milan Kundera’s work Identity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ego identity in modern life. With a story between two lovers of middle age, the writer expounds his view that one is not able to develop his identity while lying outside the world, nor is he able to develop his identity by hiding in love. Besides, the so called identity is very fragile in the gaze of “the other”. Hopelessness spreads in this novel just as in his other works.
Key words:Identity; ego; outer world; love; “the other”
收稿日期:2016-03-02
作者简介:郝朝帅,男,安徽宿州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98(2016)02-006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