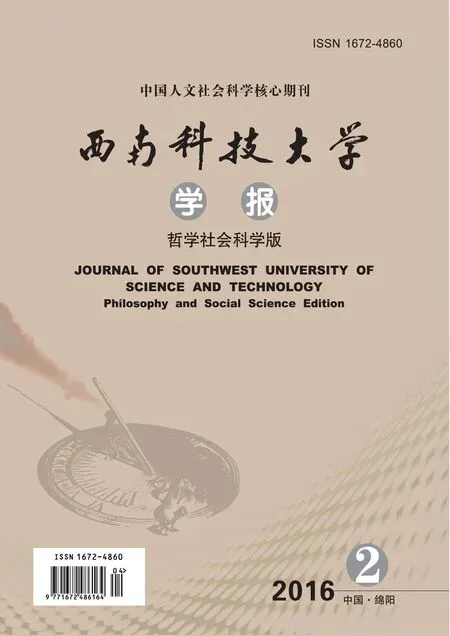《归来》的“超政治化”叙事与“历史屏蔽”
——从《陆犯焉识》的电影改编管窥张艺谋电影叙事模式
尹 兴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归来》的“超政治化”叙事与“历史屏蔽”
——从《陆犯焉识》的电影改编管窥张艺谋电影叙事模式
尹兴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摘要】电影《归来》尝试以光亮的影像外表完成历史的救赎。然而,这种对跌宕苦难历史的想象式解决,只能权作对意识形态的铭文式书写,无法承载历史灾难之重。张艺谋只能在一次次意识形态书写中,以经典的传统叙事方式对历史做出巧妙屏蔽。这部影片在以特殊的叙事模式消弭“敏感政治”强烈压抑的同时,也简化了观众有关复杂中国历史的文化想象。通过进一步反思电影的历史深度,分析影片从小说文本中所选择和加工的事实合理性,可以全息地透视影片所呈现的特定意识形态。
【关键词】《归来》;《陆犯焉识》;电影改编
张艺谋新作名曰《归来》,其中深意不言自明。在创造一次次票房神话的同时,“张艺谋作品”俨然成为商业化媒介产品的代名词。①而在与营销手段备受争议的张伟平分道扬镳后,张艺谋更是对自己的近作公然否定,表示走出商业裹挟的愿望:“商业利益的回报,从开拍起就压在导演肩上,让你的构思和创作发生扭曲……我希望有一个和谐的创作环境,尽量不受太多制约和干扰,提炼自己所有的能量,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拍几部自己喜欢的题材。”[1]123
显而易见,彰显社会价值、改变电影媒介创作政策,俨然成为张艺谋乌托邦式的终极情怀,而电影《归来》的书写正是诞生于上述特殊语境。电影改编自严歌苓的“后伤痕小说”《陆犯焉识》②。影片始于“文革”中“老右派”陆焉识从青海某劳改农场越狱回家与妻女相见,讲述了“后文革”时代妻子冯婉喻和陆焉识的“精神疗伤”故事。影片中的妻子冯婉喻因不堪历史重负而失忆,似乎连回忆历史的勇气都丧失殆尽,只能用“失忆”来对历史做出彻底质疑。陆焉识归来后无怨无悔地陪伴妻子,前提条件却是失去“自我”。与此同时,父亲和曾经出卖自己的女儿冯丹钰冰释前嫌,重新构筑基于亲情、道德、伦理和信仰的坚固之城。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张艺谋的《归来》乃“人性归来”之意。
植根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叙事方式,讲述一段娓娓动听、循循善诱的亲情故事,成功绕过那段无法诉说、却又不能回避的悲惨历史,《归来》的票房破亿与褒贬不一的两极评论,印证着张艺谋“意识形态铭文”的艰辛书写。事实远不像他描述地那般轻松:“之所以选择从陆焉识回家开始拍:第一是政治禁忌,有很多内容不好拍;第二是想和《活着》不一样,不想直接反映时代,用折射、留白的方式,从一个家庭的视角反映整个时代。”[1]124
留白、内敛,把时代浓缩到细节中表现,走入寻常百姓家,不直接描写波澜壮阔、撕心裂肺的悲惨历史,这不但表现张艺谋接受了《活着》禁映的前车之鉴,也恰是小说《陆犯焉识》与电影《归来》形同陌路的原因所在。如何避免在原著“作者风格”与“历史主流话语”的权威张力间失足?如何消解、重新命名、并且赋以惨痛历史全新的价值?影片对全民族苦难史的反思与质疑,就在冯婉喻一次次火车站接陆焉识的温情叙述中;在缠绵的钢琴曲和动听的家书朗读中得到消解。一如导演张艺谋所言:“我小时候听过‘望夫石’的故事,就觉得很生动,一个默默守望的背影,最后变成了一块石头,任凭风吹浪打。这就是中国传统女性对于爱情的态度。其实这种守望和期盼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无论是一战题材、二战题材、‘文革’题材等等,甚至未来的题材都在表现这种精神。”[1]125关注“后伤痕小说”《陆犯焉识》的电影改编,关注那些作为小说文本叙述的前提而存在、却并未在电影文本中出现的要素,无疑是有趣的学术探索。本文聚焦点即以意识形态批评为重要途径:“寻找电影文本中那些未曾说出、但必须说出、而且已然说出的因素……关注它‘没有’讲述的因素——瞩目于文本那些意味深长的空白,瞩目于文本中的‘结构性裂隙和空白’。”[2]从而进一步反思电影的历史深度,分析影片从小说文本中所选择和加工的事实是否合理,进而全息地透视影片所呈现的特定意识形态。
一、 “自由”与“归来”
《陆犯焉识》是一部以严歌苓祖父为人物原型的长篇小说,其中“一个是亲爷爷,留洋10年,会几门外语,16岁上大学,25岁读完博士。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上海,40岁的爷爷自杀了。另一个是爷爷辈的亲戚,在青海的高原监狱里待了27年,就是后来小说里的‘大右派’、‘老无期’陆焉识待的那个监狱。这个爷爷把当时的生活细节写下来,给严歌苓看。”[3]作家不仅讲述了熟识的历史大变局中的女性命运问题,更首次以深远的济世情怀,思索一代如陆焉识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进而在庞大坚硬、悠远辽阔的政治底布上挖掘其精神困境,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小说的笔触自由穿梭于主人公盛年时流连的浮华之地美国、上海,以及其后半生被禁锢的流放地西北大荒漠,世态的炎凉与波谲云诡的命运尽收读者眼底。严歌苓的文笔冷静而幽默、温情而练达,要想将这样“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文字凝缩于胶片之上,难度不言而喻。甚至连作者本人也宣称:“我要写出‘拒拍’性的文字来。”不言自明,关于“文革”的电影题材十分难以驾驭。谢晋的《芙蓉镇》历经一波三折方得上映,张艺谋的《活着》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命运多舛,田壮壮更是因为反映“文革”的电影《蓝风筝》被“禁赛”多年。毋庸置疑,这几部直面“文革”的电影,成为了一代知识分子心中难于逾越的史诗高峰。而改编“后伤痕小说”《陆犯焉识》,再次对准“文革”禁区,张艺谋无疑在宣扬某种“复归”的强烈信号。
谈到小说主旨时,作者严歌苓指出:“陆焉识原本是一个清高、傲慢、脆弱、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到最后他终于意识到什么是自由,自由是自己给自己的。真正的自由不是别人能够剥夺的,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他在内心都能有选择的自由。这个是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获得。”[4]
一如小说开篇的描述:“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5]惟其如此,“曾经有过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能够精通四国语言,而且会打马球、板球、弹子的语言学博士陆焉识,最突出的一个精神特征,就是对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这一点,无论是在早年留学期间,还是在抗战期间,抑或还是在解放之初,甚至于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抓捕关押之后,都有鲜明的体现。”[6]138为了摆脱继母的包办婚姻,陆焉识万里逃亡到美国享受真正的自由恋爱;拒绝大卫·韦参加左翼组织的原因是:“他知道自己无法让大卫明白,他所剩的自由不多,绝不能轻易地再交一部分给某个组织。”[7]39;当他踏上归国的游轮,他会滚出两行泪,因为“五年的自由结束了。放浪形骸到头了。里弄天井迎着他打开门,将在他进去后关闭……他跟谁都没有说过,他多么爱自由。从小到大,像所有中国人家的长子长孙一样,像所有中国读书人家的男孩子一样,他从来没有过足够的自由。因此我祖父在大荒漠的监狱里,也比别的犯人平心静气,因为他对自由不足的日子比较过得惯。”[7]45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小说,全书近40万字。电影《归来》仅仅从小说风云跌宕的六十年里截取了最后一小段,又把这一小段的激烈冲突加以简化和纯化。概而言之,“自由”与“归来”,皆为电影与小说的共同主题,而小说更重“自由”,电影则更重“归来”。小说中的陆焉识性格复杂,对于妻子的爱和愧疚属于“浪子回头”型,远没有影片中那般纯粹完美。为了完成小说,作家严歌苓耗时3年,穿梭于大西北荒漠戈壁、上海和华盛顿3地,借助时空交错的叙事笔调和多重视角的叙事手法,让陆焉识复杂的生活经历融于时代氛围。读者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唏嘘不已,更为当爱人最终“归来”之时而妻子婉喻却突然失忆而痛心疾首。
为此,严歌苓替张艺谋的创作困境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书有比电影大5倍的容量……如果电影要把这些都讲的话,大概需要上中下集,最少是上下集,像《日瓦格医生》那样。就是《日瓦格医生》也没有办法讲得很全面,它讲革命的那些地方都是很漫画式地概括了。我觉得导演肯定是因为这样,他得找一个最能在100分钟体现出来的东西,其他许多故事放到背景去处理。”[8]87
张艺谋本人更是直言不讳:“其实我谈不上对于右派有什么具体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有55万人。这些应该是我的父辈的故事,我不是很了解……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只是选择了这样一段历史,而且是严歌苓的原著提供的,所以我的电影并不是想要评价这个事情。”[1]126电影《归来》在对原著中陆焉识形象做出偏向完美化的改编后,性格复杂的陆焉识被简化为痴情男人,陆氏夫妇纠结的世纪之恋也被纯化得煽情感人。只是观众要问,情从何来?为何演技派明星陈道明的光彩完全被冯婉喻这个角色所遮蔽?故而大有“陆犯归来,焉识丢失”的遗憾。
二、超政治化“历史偿还”与“历史屏蔽”
《归来》尝试以光亮的影像外表完成历史的救赎。然而,这种对跌宕苦难历史的想象式解决,只能权作对意识形态的铭文式书写,无法承载历史灾难之重。张艺谋只能在一次次意识形态书写中,以经典的传统叙事方式对历史做出巧妙置换,消解了需要偿还的历史债务。不同于经典“文革”电影《活着》,《归来》沉重的历史主题在一种超政治、或曰“非政治”的巧妙叙说途径中得以消解。这种“非政治化”的解决方式,暗示着当代中国电影创作语境的“超政治化”叙事方式(以娱乐文化遮蔽历史反思),同时也呈现为对政治现实冲突的有效规避(以曲笔叙事通过电影检查)。《归来》始于陆焉识雨夜中逃亡的全景镜头(为了看望妻女),终于风雪中陆焉识推着冯婉喻接站的全景镜头(最终回归家庭);在寻找完整、闭锁式核心家庭的过程中,影片成功实现历史悲剧主题的超越与“超政治化”的叙事。小说残忍的一面被抛出了历史轨道,观众只能依靠两位明星演员的出色演绎来感受心痛;而人物遭遇的种种磨难早被观众蒙于薄纱之外,柔情到让人不知所措。
在回应记者提到影片中有好几处情感应该激烈爆发的地方,演员为何都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时,陈道明回答:“只要是过去的事情我都用这种轻松的、不经意的处理方式……因为我不想忆苦思甜。我不想把陆焉识变成一个对过去声讨、对自己命运感到愤愤不平的人。这个电影上来就是摆在主人公和观众面前的一道伤痕,它要完成愈合,而不是继续撕裂。”[9]
之所以这样做,照张艺谋的说法,是为了“引申”,“《活着》跨度有50年,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我们直面这个时代的信念,等于是直接拍每个时代,当然就好办一点。《陆犯焉识》这个故事,基本上那个时代的印记都在后头,除了一开始陆焉识跑回来这一段之外,他们所有的细节都在后边的细节中,所以这个就比较难了。既要把时代进行引申,同时又要呈现出来,是特别难的……因为引申,把时代引申到细节中去了,不像《活着》,很直观,当你把一个时代进行引申之后,我们很多有意味的台词、有意味的细节,只有有过那种时代经历、时代历练的人才能理会。”[10]无论“留白”、“折射”还是“引申”,锁闭的核心家庭尽管残缺(冯婉喻已经无法识别丈夫),但终究成为超政治化、远离历史轨道的伊甸园。历史的无端闯入让这个家庭破裂,而家庭既是救赎残酷岁月的避风港,也是归还奉献历史的最终祭坛。飘摇岁月中,它如同一叶蒙难者共渡的小舟,支撑着陆焉识冒领极刑的风险回归,支撑着冯婉喻寻找记忆中的丈夫,也支撑着因出卖父亲、不被母亲原谅的女儿冯丹钰回归家庭。2次归来,已经不仅仅是陆焉识独自一人的回归,而是核心家庭的3人集体回归。
完成历史叙事成功锁闭的同时,“家庭彼岸”的回归将喧嚣汹涌的历史劫难阻挡于门外。一代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精神困境、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艰难苟活的屈辱与痛苦,消融为电影表象之下的冰山一角。值得提醒的是,小说原著着力想要表达的是,“在20世纪的中国,真正控制并扼杀着陆焉识自由的,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社会政治。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特别强调群体意识的政治化国度,陆焉识这样推崇自由理念的个人主义者之所以遭到覆灭性的打击,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6]139具体而言,1936年的上海“天天发生文字战争,文人们各有各的报刊杂志做阵地,你不可以在他们中间走自己的路。但陆焉识还是尽量走自己的路。”[11]112抗战时期的重庆,“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的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了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陆焉识写起文章来,他戏说了迁徙内地的大混乱大无耻,造成‘最不重要’的教科书的丢失,把文章寄到一家左翼小报。”[11]175因言获罪,陆焉识在国民党的半地牢中度过了两年。而出了狱的陆焉识成了无业游民,因为教育部不准他的大学再接受他回去“灌输危险思想”。民族危难,要统一思想,“最不需要的就是个人的自由,慢说自由主义这样的西方垃圾。”[11]179至于1954年,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陆焉识在“肃反”运动中被捕,更是冤枉到了极致:“那个时期被几百辆‘嘎斯’大卡车装运到此地的犯人有不少跟陆焉识一样,罪名是‘反革命’……他囚服背上的2868番号不久就会更改,刚到大荒漠上犯人会大批死亡,死于高原反应,死于饥饿,死于每人每天开3分荒地的劳累,死于寒冷,死于‘待查’(后来待查成了犯人们最普遍的死因)。每死一批犯人,就会重新编一次番号。5个月后,陆焉识的(囚服号)从2868变成了1564号。”[11]2在接下来的10多年牢狱生活中,“正常情况下,能讨到的是臭骂、戴纸镣铐、罚跪、或者罚饭。被罚掉一顿饭,在1961年的大荒草漠上,仅次于死刑。”[11]7
严歌苓小说中的大时代,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记忆里阳光充足到太亮的夏天,更多是由黑色荒诞、出卖背叛、累累尸骨堆砌而成。失忆故事的爱情悲歌包裹于政治的历史中,充满故事张力的戏根也恰恰源自于此。小说将近3/4的篇幅在监狱和过去的生活间不断闪回,人生的是非与政治的是非纠缠叠绕,表象上为有关失忆的个人历史,却实为关于政治的记忆、对体制的无情批判。张艺谋删除了与老几(陆焉识)情同父子、最后却出卖老几(陆焉识)的梁葫芦;删除了按着逮捕名单抓获145人自己却成了第146个、在西北荒漠自杀的上海起义功臣曾是警察局长的刘胡子;删除了哨兵与谭中队长交火事件……却无法删去阻隔陆焉识和冯婉喻的万千沟壑,还有从大洋彼岸、抗日战争、提篮桥监狱的高墙,直到大西北的茫茫戈壁。基于此,张艺谋无法解释陆焉识与冯婉喻之间为何永远隔着一层无法回归的记忆,让不明就里的观众更像是在欣赏一出“世纪之恋”的韩剧。
还是演员陈道明道出了个中缘由:“这其实只是一部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它承载不了中国的历史,也承载不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命运史,它只是个节选,在节选当中有一定的典型性,包括对服装、造型、故事以及精神世界的一些展示。”[12]
三、《归来》叙事模式的检讨
张艺谋《归来》的叙事方式,让笔者联想到了1986年的“谢晋电影模式”之争。当年朱大可《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观点虽然激进尖锐,但不乏让人警醒与沉思的东西。文章检讨了谢晋电影中“俗文化的既定模式”与“情感扩张主义”,批评其“标准的好莱坞式的审美眼光和习惯”成为“谢晋模式的坚硬内核”。[13]不可否认,谢晋电影中被指斥为“儒文化”的地方是存在的,“《天云山传奇》把一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简单归咎于某些政策执行者们的品质,实际上是一种隐藏在深情厚谊中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对‘恶’的‘不抵抗主义’;《牧马人》中许灵均把‘扩大化’看做是母亲错怪了孩子,一旦改正,则‘皇恩浩荡’,‘舞蹈再拜’,反映了艺术家及评论界对二十余年中‘恶’的连锁反应还来不及认真思考,尤其是对‘五十年代的文化遗产’缺少认识。”[14]从最初的《女篮五号》到《高山下的花环》,在谢晋身上可以窥察到中国导演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必须跟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合作、妥协、矛盾、周旋等各种关系……谢晋矛盾的地方就在这儿,他虽然会被官方批判,有时候会有争议,但事后看来,他绝大部分的作品其实都是主旋律。”[15]时至今日,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张艺谋的叙事方式似乎又重回了当年的“谢晋模式”。
当观者批评《归来》没有正视“文革”历史之时,张艺谋的回应多少显得有些无奈:“首先,我觉得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批评,除非他生活在国外,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不是导演的勇气和性格决定的。”[1]126
应该承认,曲笔反映历史也是一种叙事艺术。张艺谋抛弃钟爱的大题材、大场面、大色块、大写意,将沉重的历史化为从容简单的爱情故事,静水深流、大象无形,需要的是一系列精巧的隐喻符号。吴清华的红衣燃烧了冯丹钰的半生,她把自己纯粹地活成了“红色娘子军”,却将父亲陆焉识当作了阶级敌人南霸天。当全场狂热地高举红宝书,背诵领导人最高指示时,唯有她因为不能主演吴清华向隅而泣,失去“精神教父”远比失去“亲生父亲”来得刻骨铭心。可惜的是,这样精彩的叙事昙花一现,影片旋即转入冯婉喻混沌冗长的“找寻”当中,那个让观众不明就里的“方师傅”也永远定格在导演所谓的折射与留白中。
即使不正面描写“文革”的残酷与屈辱,有没有更好的叙事方式重现“后伤痕小说”的精髓?笔者赞同严歌苓的观点,删去原著中冯子烨这一形象,值得商榷:“如果自己是电影编剧改编《陆犯焉识》,我想我会把女儿的哥哥加进来,因为这个哥哥是最不能接受他父亲的。他一家人对陆焉识的归来的反应是很残酷很幽默的。我比较欣赏我这篇小说的那种幽默感……这种接受中的不接受,其实到最后也没有接受,陆焉识还是走了。这种荒唐、幽默、残酷。这20多年的分离是不可能不留下痕迹的,不可能他被一个家庭就这样容易接受了。”[8]88
在以往的伤痕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性格往往扁平单调,当走出“文革”梦魇,知识分子往往成为历史的主体。一如影片《归来》,在街道办领导李主任(闫妮扮演)所代表的组织关照下,知识分子重获新生,美丽新世界全新归来。而作为“后伤痕文学”的代表,“《陆犯焉识》对家庭伦理和亲情的书写,超过了过去的伤痕文学,而且那种创伤性的经验是通过个人投射到整个家庭的。为什么后来冯婉喻失忆了?因为历史不堪重负。我们也再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历史的重演。失忆是虚无,是一个巨大的虚无,是对历史彻底的否定和质疑……陆焉识90岁又去了劳改农场,这有点像托尔斯泰的出走故事。这里面既有《红楼梦》的出走,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有托尔斯泰的家庭伦理的崩溃。我们能够看到文学谱系和生命谱系存在于小说的背后。”[16]张艺谋的《归来》,和他1999年拍摄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样,只想“将历史场景浪漫化”、“把所有的历史记忆都变作细节慢慢地渗透”[17], 惟其如此,《陆犯焉识》中陆焉识心里“那片大得随处都是自由”的草地才会无迹可寻,因为周遭之人“从来不懂,他们的本事孤立起来很少派得上用场,本事被榨干也没人会绕过他们,不知如何自身已陷入一堆卑琐,已经参与了勾结和纷争,失去了他们最看重的独立自由。”[11]413针对《归来》叙事模式的检讨,可以借鉴汪晖先生卓有洞见的批评:“在处理政治历史故事时不断地变换方式,如爱情故事、道德寓言和素朴情感,以压制其政治历史内容,但这种对政治的压制本身既是一种政治性的叙事策略,又包含政治假定的前提(任何观众都可以从那些爱情故事或道德寓言中获得相应的政治信念)。然而这种相当高超的叙事策略既影响了影片的政治深度和历史深度,又影响了他对籍以压制政治又表述政治的那些东西——爱情、道德、民族精神、原始人性和素朴情感——本身的更为深刻的洞察和表现。”[18]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艺谋没有明白小说中的“归来”,其实是“归不来”。
结语
张艺谋的“超政治化”叙事和“历史遮蔽”,让《归来》悬置于后伤痕小说《陆犯焉识》庞大坚硬、悲戚屈辱的政治底布之外,也缺失了对残酷岁月里生命之歌的检视和反思。由此可知,张艺谋的“归来”之路似乎仍然漫长。在纽约库柏联合大学,李安这样评价《归来》:“我觉得不光是那个时代的人,剧中的景,只要是做人,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压抑跟无可奈何,还有对于我们自我的存在,我觉得《归来》是一部很好的存在主义电影,记忆到底是什么?人一直在变,社会在变,我们的印象,我们的记忆到底是什么东西?”[19]“存在即荒诞、存在即苦难”,如果张艺谋有足够的勇气,保持相当的激情和苦痛,在叙事上多加工夫,他也许真能抵达“世界的内部,存在的荒凉地带”。
注释
①对张艺谋早期电影的批评,主要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其“后殖民语境”。代表作为张颐武的《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文章指出:“张艺谋是展示空间奇观的巨人,他的摄影机是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对‘特性’书写的机器,提供‘他性’的消费,让‘第一世界’奇迹般地看着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世界。”而从影片《英雄》开始,对其批评主要集中在跨国传播(西方话语的驯服工具,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女性主义(《金陵十三钗》之“情色爱国主义”)、性别叙事(“伪纯情”的《山楂树之恋》)、意识形态(《满城尽带黄金甲》对权力的异化与扭曲)等诸多方面,缺乏从电影本体语言、风格等要素的具体切入。
②“后伤痕小说”这一提法,可参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一文。陈晓明指出:“包括张贤亮、包括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包括《芙蓉镇》,还有贾平凹的《古炉》,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文革、对五六十年代历史的伤痕的书写。而《陆犯焉识》可以从‘后伤痕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也有创伤性经验,历史确实对他有一种迫害,包括很多身体的创伤,但是更重要的是性格和心灵方面的介入……后伤痕的创伤性结构当中,她的书写是通过写政治对人的瓦解、对人的迫害、对人的压迫,导致的是整个家庭伦理的崩溃。”参见《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第131页。
参考文献
[1]解宏乾. 张艺谋谈新片《归来》,用折射和留白反映时代[J].国家人文历史.2014,106(10).
[2]戴锦华. 电影理论与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9.
[3]刘珏欣. 严歌苓:归来与自由[J].南方人物周刊,2014,390(17):86.
[4]刘心印. 严歌苓:看《归来》感觉非常疼痛[J].国家人文历史,2014,106(10):130.
[5]严歌苓. 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
[6]王春林. 知识分子苦难命运与精神困境的审视与表现: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 [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3:138.
[7]严歌苓. 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8]刘珏欣. 严歌苓:归来与自由[J].南方人物周刊,2014,390(17).
[9]丘濂、周翔. 表演的分寸——专访陈道明[J].三联生活周刊,2014,21:140.
[10] 我的归来:独家专访张艺谋[J].看电影,2014,596(5):24.
[11] 严歌苓. 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2] 归人VS痴人:专访陈道明&巩俐 [J].看电影,2014,596(5):26.
[13] 朱大可. 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 [N]. 文汇报,1976-07-18.
[14] 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556.
[15] 许子东. 越界言论·许子东讲稿第三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70.
[16] 陈晓明.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J]. 小说评论,2012, 04:132.
[17] 归来,张艺谋的视力与方法[J]. 环球银幕,2014, 324(05):43.
[18] 汪晖. 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J]. 电影艺术,1992, 2, 45.
[19] 张艺谋李安纽约对谈实录[EB/OL]. 搜狐娱乐,(2014-03-28).http:// yule. Sohu. Com / 20140328/n397372288.shtml.
ComingHome’sSurpassed Politicized Issue and History Displacement——The Cinema Adaptation of “Post Scar- novel” “LUYan-shi”
YIN X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 movie Coming Home tries to complete history’s redemption by bright image. However, such envision of history suffering can hardly bear the weight of history’s ponderous burdeon. Director ZHANG Yi-mou seeks to permute history tactfully and clear up history intangibly. Such solution means veiled cruel history by entertainment culture, and takes a look of effectively evading political taboo.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lies in studying the movie’s special ideology through the edited facts from the original novel, and so vividly rethink the complicated history.
Key words:Coming Home; LU Yan-shi ; Cinema adaptation
收稿日期:2015-10-11
作者简介:尹兴(1975-),男,汉族,四川西昌市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广播影视文艺学。
基金项目:本文是西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基金项目“‘虚无’世界的‘黑色悲剧’——20世纪‘新黑色电影’研究”(项目编号:11sx7113)阶段性成果之一;西南科技大学“50年代中国的文化、传媒与社会”科研团队(项目编号:13sxt016)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I207.3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6)02-005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