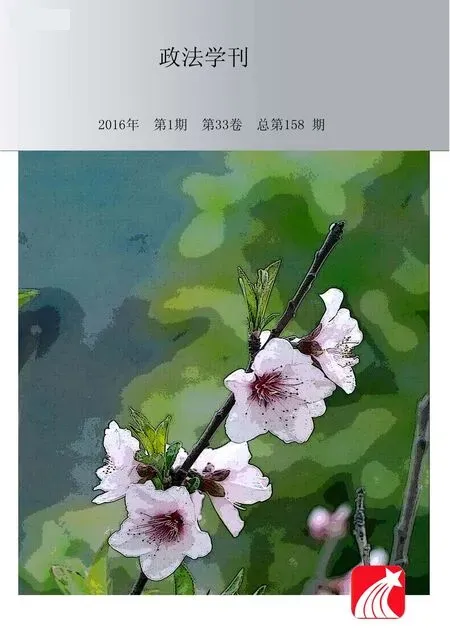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张四化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350)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张四化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通过作为“他者”的西方法律文化的扩张和作为主体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偏离等方面的剖析,以期找到法律史研究中“自我”与“他者”的平衡。探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真知,从精神上疏远“自我”以及以宽容之心接受“他者”均是必要的条件,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之间达到同样的协调和均衡时,才能对“自我”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他者”做出合理的判断。在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进行研究时,我们不仅要“得古人之言”,更为重要的是“得古人之心”。对不同的法律文化进行“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才是我们法史学研究得以正确进行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中国法律史;自我;他者;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对话
长期以来,在法史学界,“中国法律史”存在的“合法性”一直备受争议,不仅如此,关于“中国古代有无什么”的质疑不断涌出,诸如:中国古代有无民法?中国古代有无调解制度?中国古代有无遗嘱继承?中国古代有无私有权?一个时期以来,为回应这些质疑,许多深刻而富有洞见的论著不断出现,学者们或据理力陈、阐幽释微,或交流探讨、质疑商榷,法律史的学术空间里,也似乎因这些争鸣变得更为繁荣生机。在此,我们无意于参与论争,也无意于做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人们可以不厌其烦地对中国古代与西方的法律概念之差异作同异比照,而我们,只强调一个被人们漠视(抑或说已被悄然认可)的问题:既有的西方法学术语、概念普遍存在被简单套用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范式,这一过程背后,文化的“他者”问题。“自我”(the selves)和“他者”(the others)作为现代哲学中重要的范畴,对其关系的探讨,在中西哲学中有不少的论及。在此,我们拟对法律史研究中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做一简要论析,以期对传统中国法律史的叙述范式和书写方法有新的启迪和认识。
一、中国古代有无法学
中国古代有无法学?这是《中国法律史》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的基本前提。对此问题的反思与回答,在持久的争论中始终众说纷纭,杳无定论。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发问之前,必须提到这一问题的前提性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法学”,即“怎样界定法学”。这个前提性问题,不仅是方法问题,它还关涉能否正确反映出中西方不同的法律样式的问题。
这里,我们先不用“法学是什么”来进行发问,而是先讨论一下“法学是怎么回事”。这两种乍看相似的提问语式,深层次来看,却反映出了界定法学的不同标准。不同的界定标准代表着不同的法学思维方法。“法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是针对概念的定义而言,而下定义的方法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方法。亚氏这种典型的“种”(genus)加“属差”(difference)下定义的形式逻辑方法本来就是作为哺育西方文明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两种“逻各斯”(logos)之一的思维方式。这种代表着西方以演绎为主的思维方式在于追求最为普遍、最为一般的概念形式,映射到哲学范畴上,即“寻找最高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真理和知识”。可以说,从这种下定义的方法出发,得出的结果就是我们怀疑“中国法学”的存在。其实,正如严复所说的, 对于“法”这个语词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法”在在中国语言环境里对应“理、礼、法、制”四种不同的译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质疑“中国法学”的存在,但是,不可否认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古代存在“理、礼、法、制”等至少四种有关“法”的形态。
追问“法学是怎么回事”,有一个理论预设前提,那就是先予认可“中国法学”存在的事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为没有相应的逻辑理性思辨方法,与之相适应的是也当然就没有按照理论逻辑的标准设置一整套法学学科体系,如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婚姻法、知识产权法等。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法学思维方法,更不能说没有“中国法学”。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性格作了概括,比如“诸法合一”、“民刑不分”、“德治传统”、“非逻辑化”、“法权缺乏制约”等等论点。这些不尽相同的观点概括得准确精当与否暂且不论,但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对于法、对于社会治理、对于法律形式等独特的思考,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和西方法律不同的价值取向。近年来,这一点也越来越为中外法学界所认同。从文化人类学的层面看,法律与人类的政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对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么,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繁衍不息至今,难道可以说,中华民族没有自己独特的、异于西方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对中国古代有无法学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留给我们这样一个似被暗许的模式化的悖论观点:如果以严格的法律范畴和法律术语来衡量F,那么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就没有所谓的F;但如果把A解释为某种特定情况下的F,中国古代法律中确实存在F。我们以对“中国古代有无法学”的不同回答为例:如果以古代罗马法或者近代法学作为标准的参考系,那么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法学。但从中国历史、政治、伦理等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古代又有法学。 以回答“中国古代有无遗嘱继承”为例:如果把遗嘱继承制度理解为某种特定情形下的遗嘱行为,中国古代法律形态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制度;但如果以自罗马时代确立的遗嘱继承的三个原则(遗嘱自由;遗嘱继承不受法定继承的限制;遗嘱继承的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来界定,那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所谓的遗嘱继承制度。 显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无法再向下进行,一切以西方法律的观点、理论结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来定位、审视和衡定中国法律传统所引发的所有问题都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回答,我们只要从套用这一模式化的观点即可轻松回答问题的成就感中稍微清醒一下,就可以体会到,这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中国法律史领域的沮丧。对于“中国古代有无法学”这一问题,有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概念与形态。例如何勤华就认为,法学是一个历史的、哲学的和文化的概念,讨论“中国古代有无法学”这一问题,要想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们必须从历史、哲学和文化中去分析中国法学的发展形态问题。概言之,在法学形态要素中,有的是一般要素,有的是必备要素,如法学世界观,法律解释学、法学研究作品等,而判断“中国古代有无法学”的标准就是是否具备这些必备要素。这样一来,就把有无“法学”的争议转移、聚焦到其自身的概念上,成功地避开了上述悖论式的回答模式。
但是,中国古代有无民法?中国古代有无私有权?中国古代有无遗嘱继承制度?这些问题是否也可以用“形态要素”的理论来回答?“民法”、“私有权”、“遗嘱继承”的形态要素是什么?其中它们的必要形态要素又是什么?关于必要形态要素的确认有没有为学者所共识的标准?这些问题只会使使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而永无定论。在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私有权、遗嘱继承这些细琐的问题上,“形态要素理论”是无力的。不可否认,“民法”、“遗嘱继承”、“私有权”等这些法学术语如同“法学”这个语词一样,是历史的、哲学的、伦理的、宗教的、文化的概念,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概念都是西方法学意义上的概念。中国古代有无民法,有无私有权,有无遗嘱继承制度,这三个问题,显然是经典的西方法律术语的“中国式表述”。 我们过多的关注了这些问题该怎么回答?却很少去问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私有权、遗嘱继承等这样的问题,却不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去研究中国古代有没有“礼”、“债”、“财”、“‘户绝’时的财产分配”等制度。中国传统法律中形态上与西方法律很不一样,有着完全异于西方的一套法律范畴、法律命题和法律术语,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用西方的法律形式来进行“中国式运用”,那么这种研究范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礼”这个中国语词, 它在西方法律范畴和术语中是自然法,还是实在法?是民间法,还是道德法?乍看起来好像全部都有一些关系,但细究起来却又不是这样简单。
在古代中国,向来都是以天朝大国自居。人们就如同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坚守着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仰,“觉得世上只有家乡好”。在文化上的保守和孤立,使得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还有在本质上与汉民族文化相异质的“他者”。 这种情形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作为文化的“他者”形象才逐渐被一批维新知识分子构建起来。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中的“师夷”,不仅代表中国保守的文化积淀受到猛烈的冲击,更是中国“自我”意识与西方“他者”的形象紧张状态的集中表现。
梁启超在回顾这一思想历史的巨大变化时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1]65与此同时,随着清末中华法系的分崩瓦解,西方的法律制度被全方位移植进来,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迅速弥补了中国在现代法律制度上的空缺,改变了在制度层面上保守与封闭的尴尬局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法学界的学术研究视野也逐渐将中国传统法文化遗忘了,一度完全陷入了西方法律框架下的“认知控制”。近现代以来,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多数是由西方引进,以“大陆法系”为主的法律概念、法律形态无形中成为我们研究的起点与参照。这种以“大陆法系”为主要参照的研究范式引出了一系列伪命题,对这些伪命题的争论不休的态势,使许多本来就不甚清晰的历史存在变得更加模糊难见。西方法律文化“他者”的普遍化,必然使作为“自我”的中国传统法文化置于特殊性、差异性的境地。这样做,其实早已把自我沦为他者,把他者视为主体了。当然,这一价值取向的颠覆,是作为“他者”的西方法律文化的扩张和作为主体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偏离二者双向互动的结果。
二、西方法律文化的扩张和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偏离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走现代化的道路,而西方文明无异就是现代化的代名词,“注意世界一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您所有的思辨推理都将崩溃。远不是固守自我,所有的文明一个一个地承认它们中的一个具有优越性,这个优越的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扩张使自我逐渐失去了抵御的意志,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在逐渐借用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消遣方式直至其服装”,当然,更包括西方的文化,“正如第欧根尼通过步行证明运动一样,人类文化演进的本身,从广袤的亚洲大地直到巴西热带丛林或非洲的部落,史无前例地一致在证明人类文明中的一种形式高于其他一切形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会上所谴责的不是使他们西方化,而是谴责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手段来西方化。”[2]81-82
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西方文化在这一时期扩张的野心也随之来到了中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834年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在来华的轮船上咏吟的诗句中可窥见一斑:“天堂轻风欢畅,伴君横渡大洋。肩负上帝重托,志在中国解放。”[3]西方文化的扩张,不仅使我们从空间模式上认识到有一个西方“他者”的存在,更使我们的认知模式从共时性的地域上的差别转化到历时性的时间上的古今之别,价值上的优劣之别。一边是西方法律文化,充满理性和正义,且合乎逻辑,论证充分,而且这些价值得以持续保持和继承;另一边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仅没有前述这些优点,更多的是义务本位,权尊于法,法律叙述方式古朴晦涩,并且与当代法治所断裂。西方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劣一目了然,
我们也不再甘当如雨果所言的“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未曾长大的雏儿”,相形见绌的比较之下,我们渴望自我更新,并“试图从中国传统或社会中寻找某些据说是具有‘现代性的因素’”[4]2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某些带有比附性质的观点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古罗马用“十二铜表”来公布法律,我国用“铸刑鼎”来公布法律;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出现民本思潮,我国先秦时期就有了“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的重民思想;西方法制文明寻求替代纠纷解决方式(ADR),我国两千年前孔子就发出了“无讼”的呼吁。法律史的研究,似乎还带了些民族英雄意气,中国法史有的,西方法史也有,西方当代的法制文明,一样能在中国法史中找到根源。这些比附性研究,看似是对西方文化扩张的一种抵抗,是为了彰显民族自尊心而扒开历史的废墟去拣拾与西方能“貌合”的史料。实际上这正是另一种以尊中华文明为其表,民族文化自卑心为其里的媚外表现。用崔清田主张的“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5]的文化学研究范式进行分析即可明白。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会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以“仁爱”、“诸法合体”、“无讼”、“和谐”等为特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有明显的差别,要用“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来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分析”,就是把法律传统置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具体分析时代的社会问题及价值取向;“文化诠释”则是把东西方法律传统视为两者相应文化的组成部分,参照其产生时的政治、伦理、人文、哲学、科技等方面的情况,对不同的法律传统给出“成理”与“有故”的解释和说明。用以上文化学研究范式对中国法律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前文所举的我国古代“铸刑鼎”,其实就是贵族内部的权力之争,根本无意于公布成文法;我国先秦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重民思想,其实也无意于民之权利,只是一种君王驭民政策;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无讼”的呼吁,与西方法制文明寻求ADR相去甚远。有的学者基于民族自尊心(或是民族自卑心)或是民族主义出发,似乎总是在有意无意地不去考虑历史背景,不去察古人之心,总是给一些史事贴上先进文明的标签。应当说,对古今中外的法文化进行比较,是我们寻求“自我”的一种途径,但在西方文化强权的语境中,这种比较却往往使我们滑入弃绝自我的深渊。这是我们应当警醒的。
我们终于从“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雏儿”成长为另一个“发现世上所有地方都如自己家乡一样好”的人,但疏离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家园,也就远离了“自我”,满眼都是异质的西方文化的优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彻底转变成了西方文化的“他者”。西方法律文化成为主导者,指挥着一大批学者目标明确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淘金,淘到的当然不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本真内涵与根本特质,而是一些中西法律在“器”层面上的某种契合。很显然,这样的做法,我们是在以西方法律精神为范本和坐标,在西方价值体系、优劣高下标准的指引下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定位,似乎只有找到了某些契合之处,才能证明包括政治和法律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那么一点优越性,才能为中国法律史的“合法性”找出一些理论基础。当然,自身成为“特殊”及本土的“他者”,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与其说是西方文化的扩张所致,换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在现代性扩张的背景下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弃绝自身。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自我偏离。
清末修律活动使得中国古代传统法文化与现代法学领域割裂开来,我们的立法技术、法律规范、法律范畴以及法律术语几近全盘西化,法律史之于今人的价值似乎因近代法治的转型而大打折扣。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一方面不舍于孔子、儒教等“万古不灭”之物,在此文化背景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之自我认同的追寻变得辽远而困难。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描述性的法史学”对现代社会的辐射力已略显不足,从现代哲学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借鉴而来的“解释性的法史学”应运而生, 它没有停留在对法文化中史料的整理与收集,而是“力求从历史之中挖掘出某些具有现代价值的东西”,试图在古今之间建立起某种“对话”机制,因此,需要以“新的学术角度重新审视、解释和阐发一切旧有的法律文化现象”。虽然说“我们每多一种解释的工具,‘历史’便会在我们面前多显示出一层意义,我们也就多一份创造的收获。”[6]4但是越要在法学的“历史”与“现在”建立起某种联系,就越有放弃“自我”的危险,因为“历史”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而“现在”却是在西方法律观念、理论结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下建构的现在。
我们遗憾地看到,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许多学者的思维被塞进西方法律形态的狭小的空间内,鉴于我国现代法治框架很多都是来源于西方,西方对我们法律的强权被人们习以为常地当作真理接受了下来。一系列中西奇怪组合的语词叙述方式出现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如中国古代民法、古代行政法、古代私有权,
这些法律概念的提法缺乏必要的反思和追问意识,全然不顾基于异质文化土壤的中西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一经提出就导致很大争议。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古代行政法”、“私有权”这些用于联通古今中外的语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古代法的形态相符合;中国古代法被看作我们所认识的西方相对物的某种变体,这种提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值得深思。这样的研究方法,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弃绝自身。这样势必使本就不甚清晰的历史存在,变得更加模糊难见,而而不可避免的是,遮蔽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特质,无法“回到历史”的真实,廓清历史的原貌。正如朱利叶斯·科普斯曾警告的那样:“如果我们用已熟悉的专有法律用语简单地叙述与原始部落法律有关的事实时,就可能歪曲了其内容。”[7]18当然,我们愿意相信,人们无意于媚外,只是不自觉坠入了缘附的陷阱,因为中西法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太多的貌合神离。但“惟其貌合,乃可不觉其神离,而惟其不觉其神离,往往沉湎于貌合。这是很危险的现象。”[8]5不可否认,会通与融合中西法律文化精髓,是我国法律“现代化”的前提,但是,寻求中国法律史的“自我”是这种前提的前提。如若沦为西方法文化的“他者”,我们的研究空间就会愈加局促,因为在西方法文化中是找不到阐释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参照系的。
三、“自我”与“他者”的平衡
中国法律史的路在何方?在“自我”与“他者”、“背离”与“跟从”之间,其间的那个黄金分割点停留在哪个刻度上?要想探求中国法律史的真知,从精神上疏远“自我”以及以宽容之心接受“他者”是必要的前提,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之间达到同样的协调和均衡时,才能对“自我”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他者”做出合理的判断。美国学者郝大维(David L. Hall,1937-2001)和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 )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就认为,“自我”与“他者”,唯有在相互观照、互为诠释之中方可看清“他者”的实质与精神,实现扬弃与提升。[9]
对于自我偏执地迷恋,对于他者粗暴地拒绝,这种研究态度几乎绝迹,目前已不是我们在寻求平衡中需加以纠正的问题。与之相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于自我的拒斥和对于他者的迷恋却早已悄然潜入并呈滋生蔓延之态。寻求平衡,我们需要回归“自我”并在“自我”与“他者”的比较中探求真知。应当说,将西方法律术语、概念引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最初的本意并非是厚西薄古,而是为了让我们借用当代的思维方式更加直观地了解传统。但是我们应当阻止将中国法律传统全盘置于现代西方法律语境中。中西古今的法律文化,可置换的概念少之又少,乃至近乎可以忽略。
不遗余力地对术语和概念进行置换和解释,不仅使我们在学术上丧失了本土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家园,更使我们对法律史的研究挂一漏万。以将“法律体系”一词引入古代法制的研究为例,对“某代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提法鲜有人提出异议。但只要详加参究,我们就会知道钱大群等学者针对唐律研究所提问题的症结何在,他说,“律、令、格、式的性质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已成了唐代法律乃至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歧最大、矛盾最尖锐的问题。”[10]98在当今法律的研究中,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构成的整体,其逻辑关联方式是法律部门。言及“唐代法律体系”,也就是唐代应当存在这样的以法律所调整的对象不同而形成的部门法。可是,唐代只有《贞观律》、《开元令》、《贞观格》等,而没有什么“贞观刑法”、“开元行政法”之类,于是,我们就肩负起为唐代划分法律部门的重任,将律、令、格、式拆开了重新归类,如此这般,唐大群所谓的尖锐的“分歧”、“矛盾”自然就接踵而至了。 其实,古文字远没有现今人们想象的那样贫乏,如《唐六典·刑部》中说,“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唐律的理论逻辑关联方式就是“法律形式”,它是以“法律形式”的不同来进行区分,并根据这种区分构建一个“律、令、格、律”的独特体系的,我们完全可以用“唐代法律形式体系”指代唐律的全貌。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法律术语,中国法律史的真相就在古代典籍之中,古文字并非今人想象中的那样贫乏和辞不达意,我们的研究就应该立足于“古人之言”,去“以古解古”,以“礼”、“财”、“债”、“户绝”时的财产分配去研究古代民事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以“民法”、“私有权”、“遗嘱继承制度”等西化和现代的术语来套用。追求“自我”得第一步就是“得古人之言”。[11]161同时,若“古人之言”的确晦涩难见,“我们不得不用西方的术语、概念剪裁中国历史、剖析中国古代法之概念、解释古代法律规范的特征时,怀有一颗理解、尊重中国文化的心及警醒西方法制话语霸权的姿态是十分必要的。”[12]
在法律史研究与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应当注意到,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法律既有共同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有特殊性的一面,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在进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时候,“基于法律文本证据声称中国法律史如何如何也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初步阶段,而且难保客观真实”,[13]所以我们不仅要“得古人之言”,更要“得古人之心”。然而我们理解历史,不是凭空白的大脑和零经验去检阅古人的文化的,我们的脑中带有当代社会智识的痕迹和概念思维的理性。即便怀有再虔诚的“还原历史”的心,依然难逃当代社会编织的理性之网。况且,中国传统的史学的春秋笔法尚“一字之褒,荣若华衮;一字之贬,严若斧钺”,面对史料,带有历史前见的我们更无法使自己的心态达到完全“客观中立”。“得古人之心”是我们尽量保持的一种学术研究心态。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在西方文化扩张的今天,我国在“借鉴了这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14]5我们认为,真正的文化贡献在于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一个给定文化的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应当对所有的“他者”怀有谦卑之感和感恩之心,这种感情应当只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别的文化一定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而且会以最为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四、跨文化的法律“对话”何以可能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看,当今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日益明朗,类似享廷顿“文明冲突论”[15]36的观点也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被人们的思想所抛弃。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对话”成为理论热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法学界也不断被这股全球化的浪潮所席卷,从立法技术、法律范畴、法律术语等方面来看,我国刑事、民事、诉讼法等立法活动又重新开始有了借鉴与融合西方法律的各种形式和方法;作为西方核心价值内容的平等、法治、自由、民主等观念也被我国理论界与现实中所认同,国家层面通过将这些观念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赋于它们新的理论内涵和价值维度。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路在何方?在法律文化“自我”与“他者”、“移植”西方法律与“继承”中国传统之间,两者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其实,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与吸收西方国家部分先进法律文化的同时,做到既不背离中国法律传统又不脱离时代现实性的需求。这个吸收与借鉴的过程,就是中西法律文化“对话”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西方跨文化的法律“对话”可以从四个不同的层次来进行研究:一是“对话”的基础;二是“对话”主体之间的关系;三是“对话”时思维方式的差异;四是用何话语“对话”。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这四个不同的层次。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中西跨文化的法律“对话”的基础。“对话”的基础,也就是这种中西方法律“对话”在什么样的一个观念的指导下进行,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展开。这种跨文化的法律“对话”容易形成一个本土思维偏好,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间形成不同的文化思想观念,当我们在进行跨文化的法律“对话”时,每个民族都代表一个类型文化的主体存在,由于每个民族的法律形态和要素之间的差异性,“对话”的双方都只可以代表自身的文化传统下的法律形态。这样一来,“对话”的主体间,都用自己的思维偏好来进行法律“对话”,显然无法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交往。承认跨文化的中西法律“对话”是可能的,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用西方法律的概念、范畴、术语来解释(或者说解构)中国法律传统,也不能用中国的法律形态和要素来理解西方法律的范畴和术语。如前文我们所提到的赛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西方学者所了解的东方,不过是欧洲的某些“东方学家”用西方话语创造出的一个语词概念。[16]毫无疑问,这部著作对西方中心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反思。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东方学》一书采用的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17]尽管我们用现代西方哲学概念中的“对话”理论来进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沟通和交往,但这样并不表明我们一定要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范式来研究法律文化,“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是缺一不可的,特别是对于跨文化的中西法律“对话”而言,更是如此。
其次,我们讨论中西法律“对话”主体之间的关系。探讨“对话”之间的关系,就涉及到对中西法律“对话”进行定性的问题,也即是这种“对话”是什么性质的对话。“对话”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对话”双方在对话活动中的地位:二者是主从关系还是平等关系;是主体之间的“对话”还是主客体之间的“对话”。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学者甚至包括我国部分学者在进行理论“对话”时,多数是主客体之间的“对话”,而非主体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不同程度地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我们举一个关于“原始思维”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不平等级的“对话”的弊病。法国的列维·布留尔自认为西方思维方式是理性思维方式,而把古代中国人、非洲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等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看成是“原始思维”,他认为:“中国的科学就是这种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 思维习惯太顽固了,它已经产生了号令一切的需要。要使欧洲厌恶中国的学者是容易的,但要让中国弃绝它的物理学家、医生和风水先生却很难。”[18]447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背弃民族文化精神,做列维·布留尔等文化殖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把有些并不了解东方文化的所谓“东方学家”的极端话语当作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这种甘当文化弃儿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是极其可悲的。
再次,“对话”时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进行中西方跨文化的法律“对话”时,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两者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是一个民族异质于另外一个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智”的文化系统,而西方文化是一种“仁”的文化系统。[19]153即是说,西方文化与西方法律更为重视“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构表现”;而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法律形态则更为重视“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理性之运用表现”。中国的这种以“智”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与西方以“仁”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感性、直觉和实用为主,而西方的思维方式以理性、演绎和分析为主。在法治思维成为世界普遍性价值追寻的当代语景中,“对话”双方的思维方式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在进行跨文化的法律“对话”的过程中,双方主体之间必须在“对话”中汲取彼此的积极因素,在沟通和交往中增加法治观念的理解与互信。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用何话语“对话”。我们将用何话语放在后面进行讨论主要的原因在于,要拒斥语言中心主义,摈弃语言的决定性。这里说的用何话语“对话”,是从跨文化的“对话”层面上说的,就是说要选择双方(甚至多方)都可以接受的话语。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用何话语的不同作用。一个时期以来,在国际性的交流与讨论中,经常会面临中国在“对话”中的“失语”,即没有代表中国元素的话语体系。关于这一点,国内学术界也有所认识,并正在通过努力加以改变。这种“失语”的现象并非孤例,不仅汉语如此,在世界范围内,印度语系、阿拉伯国家语系、非洲语系等非西方语系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存在“失语”现象;这种现象也不是我国学者通过省思的自我发现,拉康等人所说的“他人的话语”、德里达的“非中心话语”都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表述。目前,已有学者提出建立一种“普遍语言”[20]314的设想,这种普遍语言不是具体某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语言,而且“对话”的多个主体间普遍共许的符合多方普遍价值追寻的话语。
参 考 文 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于秀英,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George B. Stevens, w. Fisher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M.D.,p.92.
[4]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5]崔清田.中国逻辑史研究世纪谈[J].社会科学战线,1996,(4):7-11.
[6]胡旭晟.解释性的法史学——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为侧重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7]E·霍贝尔.原始人的法[M].严存生,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8]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9]David L. Hall & Roger T. Ames,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p.157.
[10]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2]徐忠明.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J].现代法学,2002,(1):3-12.
[13]陈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J].法商研究,2004,(5) :135-144.
[14]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郭学堂、成帅华译[J].国外社会科学.1998,(6).
[16]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dege and Kegan Paul,1978.
[17]Concepts of Literature Theory East & West, Editor: Han-Li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sity,1990.
[18]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9]郑家栋.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 [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20]方汉文.比较文化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林衍
Don't be an Alien to Cultures: The Predicament of Study on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Thoughts and the Way Out
Zhang Si-hua
(School of Marxism Educatio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ansion of "alien" western legal culture and the departure of study on Chinese legal history and tries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self" and "alien". We shall seek the truth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spiritually drift apart from "self" and accept "alien" with much tolerance. Only when we reach a balance between "departure" and "intimacy" can we give a rational judgment to "self" and "alien" cultur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thoughts, we not only need to know what ancient people say but also know what ancient people mean. Making 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o different legal cultures is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Chinese legal history study to be properly carried out.
Key words:Chinese legal history; self; alien; historical analysi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dialogue
收稿日期:2015-12-16
作者简介:张四化(1983-),男,河南商水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生,河南省法学会社会治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比较法学、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45(2016)01-00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