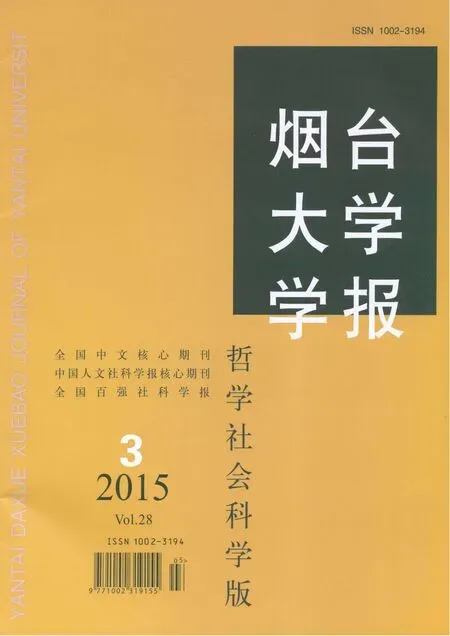鲁迅小说中议论话语修辞的杂文性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鲁迅在谈自己的小说时曾使用过这样的称谓,即“小说模样的文章”或“小说模样的东西”①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并说:“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②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442页。。如何理解鲁迅对自己小说的这些自述,学界同仁曾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过解读,其中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主要是鲁迅谦虚态度的表现,也是鲁迅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种思想倾向的表达。此观点虽然比较中肯,但却不是最贴切的,因为这不是从鲁迅小说文体本身进行的解说,而是从创作主体鲁迅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倾向的层面进行的解说,没有解释清楚“小说模样的文章”或“小说模样的东西”究竟是怎样的文章与东西。事实上,当我们从鲁迅小说文体本身的实际状况进行考察后会发现,鲁迅如此称谓自己的小说,不仅是一种谦虚态度的表现,也不仅具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的作用,而是一种对自己小说文体的界定,而且是十分得体的界定。“‘小说模样’就暗含着‘非小说’的因素,即鲁迅小说作品中有非常明显的小说文体向其他文体的‘越界’现象,比如对散文、诗歌、戏剧的某些文体特征的吸收和使用。在谈到文学的类型时,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说:‘优秀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类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张它。’鲁迅是一位天才作家,他正是这样一位文类的‘扩张者’。”①许祖华,余新明,孙淑芳:《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鲁迅小说文类的“扩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向杂文文体的扩张,而作为这种扩张的最明显标志,就是鲁迅小说中的议论性话语及这些话语所采用的修辞方法具有杂文语体的特点。
一、鲁迅杂文的语体修辞特点及魅力
鲁迅小说中的众多议论性的话语及修辞不仅有效地凸显了鲁迅小说话语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而且还很有效地凸显了鲁迅小说与众不同的文体特征,特别是杂文式的文体特征。如下面的议论性话语:
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的。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零零,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阿Q正传》)
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一件小事》)
这些议论性的话语,虽然采用的修辞手段各不相同,句式的构造中西合璧、古今并存且曲折多变,词语的使用也丰富多彩,意味多种多样而悠远深长,言内之意显豁,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但其共同点就是:都采用了杂文的话语表述方式,具有杂文语体修辞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语体修辞具有什么特点呢?有学者从鲁迅杂文语言的使用方面认为:“鲁迅先生杂文中的语言则不但做到了准确、鲜明、生动,而且还非常简练隽永,充满着机智与幽默。”②钱谷融:《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68页。这种观点不仅在之前研究鲁迅杂文语体修辞方面归纳得较为全面,而且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种观点还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其主要思路是从“风格”的角度展开的,所总结出的鲁迅杂文语言方面的“准确、鲜明、生动”和“简练隽永”、“机智与幽默”的特点,都是鲁迅杂文通过语言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但与“语体修辞”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主要就是没有更自觉地关注鲁迅杂文这种特殊文体的语体特点以及这种语体特点“杂”的规定性。有的学者虽然也涉及了鲁迅杂文的语体修辞,但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仅从语用修辞的角度展开,如“鲁迅更加注重选词用字,或大词小用,或庄词谐用,或俚词庄用,或古词新用,或外词中用。这一切词语的转用、借用,实质上,形成不同程度和不同意味的夸张,有时溶入反语、揶揄、热讽的句式结构中,有时又跟舒徐的白描或峻急的抒情句式相结合,大大强化了喜剧语言的讽刺性。”③朱彤:《鲁迅杂文独创的艺术》,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下,第384页。这些概括虽然精彩,但也有一定的缺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语用(词语使用)的分析往往只注意了词语本身所表达的意义,却没有自觉的语境意识,也没有从词语所处的语境入手揭示鲁迅杂文词语使用的艺术匠心与思想匠心;另一方面是没有更多地从话语修辞的层面来论述鲁迅杂文的语体修辞的特点,尽管提及了鲁迅杂文话语的某些“句式”特点,却也仅仅点到即止,未能展开。较为得体地从话语修辞的角度剔析鲁迅杂文语体修辞的特点的人物是徐懋庸,他在《鲁迅的杂文》一文中,曾很中肯地总结出了鲁迅杂文语体修辞的两个方面的特点,这就是造句灵活与修辞特别。关于鲁迅杂文修辞的这两方面的特点,徐懋庸如此论述:“造句的灵活。这是古文的影响和外国文的影响融合的结果。用文言句而使人不觉其陈腐,用欧化句而使人不觉其生硬,新鲜而圆熟,并且音调流畅,可以朗读,所以特别有味,但跟口语相差很远”。关于鲁迅杂文修辞的特别,徐懋庸如是说:“因为目的是战斗,所以鲁迅竭力要使他的文章的效果增强,而在修辞上特别用功夫。‘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又要然而了,然而……’,‘铺张’或‘扬厉’竟做到这样;特别善于利用‘引用’,对于别人的文章只要用“”一勾,再轻轻一戳,就给暴露出破绽;至于常用‘死话’,‘冷话’,‘倒反’,‘暗示’之处,竟被人们认作是‘绍兴师爷’的特色。”“还有是行文的曲折之多。”①徐懋庸:《鲁迅的杂文》,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9-210页。徐懋庸这些关于鲁迅杂文修辞特点的论述有的是从审美感受上展开的,有的是从遣词造句的修辞方面展开的,有的还是从鲁迅创作杂文的思想与艺术意图展开的,整个论述也呈现出“杂文”杂的特点,却较为得体地剔析了鲁迅杂文在话语修辞方面的特点与魅力,尤其是“造句灵活”与“修辞特别”的特色与魅力。
以此来观照上面所引用的鲁迅小说中议论性的话语的修辞,的确可以找到很多与鲁迅杂文的话语修辞相同的内容。如鲁迅杂文“特别善于利用‘引用’”的修辞手法,如上文中的议论性话语“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子曰诗云”等,同样,在这里鲁迅也使用了“然而”的句式,也进行了铺张与扬厉,如“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这种铺张与扬厉还直接表达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批判中国固有文明的思想,并在这种铺张与扬厉中使用了鲁迅在后来的杂文中“画龙点睛”一样使用的一个词语“乏”。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鲁迅小说中的议论性话语,无论是从表达思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修辞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鲁迅“杂文”的特点与神采。
那么,这个神采何在呢?神采就在于将杂文语体的修辞运用于小说的议论性话语修辞之中,或者说,直接采用杂文的手法展开议论,使这些议论性的话语因为融合了杂文语体的修辞特点,而呈现出多样的审美性,这些多样的审美性借用郭沫若论鲁迅诗稿的评语来说就是“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②郭沫若:《〈鲁迅诗稿〉序》,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下,第380页。
鲁迅在论杂文时曾经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③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鲁迅的论述正指出了杂文在文体方面“杂”的特点,而他自己的杂文在文体方面也的确很杂,举凡论文、随感录、抒情文(如《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随笔、通讯、短评、短论、序、传、书信、启事、答记者问、谈话、讲演、童话、寓言,甚至“青年必读书目”、考据、诗歌,“有的类似小说(《阿金》),有的类似日记(《马上支日记》),有的熔杂文小说于一炉(《写于深夜里》)”④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鲁迅杂文的政治意义与艺术价值》,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下,第33页。等等,无所不包。可以这么说,古今中外已有的“言语形式”,书面的也好,口头的也罢,日常的也好,正式的也罢,我们在鲁迅杂文中几乎都可以找到。也正是因为鲁迅杂文文体本身就具有“杂”的特点,所以,也就带来了其杂文语体修辞“跨语体”的特点,也就是“杂”的特点。其基本表现是:无论是政论语体的修辞,还是文艺语体的修辞,无论是科学论文语体的修辞,还是公文语体的修辞,无论是谈话语体的修辞,还是书卷语体的修辞,无论是书信语体的修辞,还是一般文学语体的修辞,鲁迅杂文不仅几乎都无限制地采用过,而且,常常还是具有创意地使用,并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①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的过程中,收获了虽然“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②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2页。的艺术效果。
不过,鲁迅杂文的语体修辞尽管杂,但这种“杂”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主要有两点:第一,鲁迅杂文在运用其他语体用语手段时,往往根据所谈对象与所论问题及相关语境,经过对其他语体用语功能上的变异形成自己表情达意的用语。对于鲁迅杂文的这种修辞性规律,修辞学家看得最为清楚:“鲁迅杂文中谈古论今,涉及广泛,其中的政治术语、新闻术语,往往根据不同的语境而呈现为或辛辣,或诙谐,或幽默的语言风格,这些术语原有的功能已被鲁迅改造。”③李贵如:《现代修辞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这虽然只是一种概述,却也剔析出了鲁迅杂文语体修辞的一种基本规律;第二,鲁迅杂文在句式构造上,往往是中外一体,文言句式与白话句式杂糅,既遵循了“消极修辞的基本要求是明确、通顺、简洁、平允”的原则,又充分利用了各种积极修辞的手段并对这些积极修辞的手段进行了创造性的使用。但鲁迅杂文的语体修辞不管具有怎样的规律,这些规律都指向杂文生成的思想与艺术的目的,也内在地由杂文的思想与艺术的需要所规约,这正是鲁迅杂文语体修辞获得成功的内在与外在的保证,也是鲁迅杂文语体修辞的魅力之所在。
二、鲁迅小说议论性话语的语用修辞的“杂文性”
与鲁迅杂文语体修辞相一致,鲁迅小说中的议论性话语的修辞也是如此。上文所举的三段议论性话语中,仅从词语的使用(语用修辞)来看就很“杂”,虽然,这些词语主要以日常口语和一般书面语为主,如,“只有自己在上”,每个词语都是纯粹的口语词语,“冠于全球”、“乏”等则是较为典型的书面语的词语,但也同时使用了“文治武力”、“精神文明”等经常在政论文或公文中使用的词语。这些词语在词性方面,或者是中性的词语,如“在上”,或者是具有否定意义的词语,如“乏”,或者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词语,如“冠于全球”、“文治武力”、“精神文明”等,但在这些议论性的话语中,却由于所指称的对象及语境的有力限制,使这些词语原来的功能都发生了变异,变异的基本倾向是:无论是具有中性特征的词语,还是具有表现积极意义的功能的词语,都被贬义化了,而且在这些议论性的话语中还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越是表现积极意义的词语,其被贬义化的倾向越明显,如“文治武功”、“中国的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等。这些词语本来是表现国家、民族、社会的积极意义的词语,可是,在鲁迅小说的这些议论性话语中,不仅变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词语,而且功能也变异为了它们原有功能的反面——表现消极意义,因为,从整个话语的语境来看,所谓“文治武功”对应的是“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对应的不过是阿Q的“永远得意”,都是在讽刺与否定。即使是“乏”这个词语也不例外。本来“乏”是表示“缺少”、“不中用”等否定性意义的词语,但在议论性话语中与表示否定的词语“没有”搭配,在否定之否定的搭配中,组成了肯定性的词组“没有这样乏”,从而不仅使其具有了表示积极意义的功能,也使由这个词组构成的句子“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在语义表层具有了表示肯定的意义。由于语境的作用(因为整段议论性话语都饱含讽刺与否定意味,这正是使词语功能发生转变的环境因素),却也使这个句子的功能发生了变异——从表示积极意义变异为表示消极意义(因为,这个句子揭示的不是什么具有正价值的内容,而是具有负价值的内容,即阿Q身上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之一的“永远得意”),不仅使这个句子成为一句典型的“反话正说”的例子,而且也使讽刺与否定的意味从句子的深层中散发出来。
当然,这些词语在话语中的功能变异,并不是随意的,它们的变异与鲁迅杂文中词语功能的变异一样,都受制于鲁迅思想表达的需要与艺术构造的目的。语言学家们在谈作家运用语言的变异时曾经指出:“作家笔下的变异,是他们在运用语言时,出于表达的需要,故意并且在一定限度上突破语音、词汇、语法等种种常规而采取的一种变通用法,它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艺术手段。”①叶国泉,罗康宁:《语言变异艺术》,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页。鲁迅小说中这些议论性话语中的词语功能的变异,也正因为这些词语在话语中“出于表达的需要”的功能变异,取得了良好的思想表达的效果与艺术构造的效果。
上述《阿Q正传》中的这段议论性话语所透露的思想,不仅与整篇小说改造国民性的立意完全一致,也是对整篇小说改造国民性内容的高度提炼,而且综合了鲁迅所要批判的国民性的主要内容,即自欺与自负。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国民性,尤其是具有劣性的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在各类文章,包括各类书信中所批判的内容是较为多样的,诸如“听天由命”、“卑怯”、“以自己的丑恶骄人”②鲁迅:《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8页。、闭眼不看现实,“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昧,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的把戏”③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上,第123页。,以及“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④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9页。,还有“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⑤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页。,等等。但鲁迅在理智与情感方面最为深恶痛绝并批判得最为频繁和深刻的,即是国民劣根性中的自欺与自负以及由自欺与自负所导致的国民的怯弱与爱国的自大。鲁迅曾在他影响巨大的著名杂文《论睁了眼看》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套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⑥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深入骨髓地直接地批判了中国人由自欺而导致的国民性的怯弱及“日见其光荣”的病态心理。又在《热风·三十八》中列举了由“爱国的自大”所导致的应该改造的五种国民性,其中的两种即“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和“外国的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⑦都属于是自负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国民性内容。而在这段议论性话语中,不仅鲁迅所要批判的这两种国民性都包含在其中了,如阿Q的“永远得意”就正是“自欺”与“自负”的国民性的生动表现,而且鲁迅对这两种国民性批判的意图也通过充满讽刺与否定的议论性话语得到了表达。所以,这段议论性的话语中所使用的词语变异的方法,不仅是符合跨语体修辞规律的词语功能的变异的方法,更是鲁迅根据思想表达的需要而匠心别具地采用的词语功能变异的方法。这种变异方法采用的结果,不仅使小说“改造国民性”主旨的表达更为直接、鲜明、充分,而且也使小说的喜剧性审美特色进一步得到了凸显与强化。
从艺术构造的需要来看,这段议论性的话语是阿Q在欺负了小尼姑后,“阿Q十分得意的笑”,“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不仅词语的使用与上面的话语一样采用了词语功能变异的方法(在所谓“九分得意的笑”中的“九分”就是从“十分”变异而来,“十分”是副词,“九分”则是数量词,而用数量词“九分”来修饰“得意的笑”,则无疑是使数量词的功能发生了变异),而且,其议论的内容也是承续着阿Q及周围人的表现与心理展开的,其讽刺所针对的也是阿Q及周围的人。不过,其艺术构造的分工却十分明确,前面对阿Q及其周围人的“得意”直接通过描写人物自己“哈哈哈”的言语与行为“笑”来显示,而这段议论性的话语则直陈——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更将这种讽刺与小说所要表达的改造国民性的主旨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彰显了对阿Q及周围人们行为与言语描写的意义:原来,阿Q的“十分得意的笑”也好,“酒店里的人”的“九分得意的笑”也罢,虽然都只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但这些行为所代表的正是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种病态的国民性。冯雪峰在论阿Q的这种“得意”的精神状态时曾经指出:“倘将阿Q的自欺欺人办法,仅仅和他自己——一个奴隶,一个做短工的人相联结,这办法就反而教人同情,因为这也是他的一种自卫的战术,否则他就不能生存,而且终于不能生存。然而这是失败后的奴隶,甚至是在做稳了奴隶之后而幸喜着,而得意着的驯服的奴才的意识,而且还说是中国文明的精华!”①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页。冯雪峰的这段论述,正指出了阿Q的“得意”所反映出的“奴才的意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明”的弊端。也正是这段议论性话语所具有的功能,使那些具有幽默感的描写阿Q“十分得意”与酒店的人们“九分得意”的句子及词语,不仅其新颖性获得了思想的支撑而显示了艺术活力,而且其所包含的对国民性深刻而辛辣的讽刺意味也力透纸背。鲁迅在评论徐懋庸的杂文的艺术作用时曾经指出:这些杂文“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移人情。”②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而鲁迅在小说创作中也身体力行,运用杂文式的议论性话语及语言功能变异方法出色地完成了鲁迅曾经说过的“要救正这些(国民性——引者注),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③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页。的小说创作的任务。
三、鲁迅小说议论性话语的句式构造及修辞手段的“杂文性”
鲁迅小说作为典范的白话文,不仅在词语功能的变异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在句式构造及修辞手段的使用上也表现出了强劲而新颖的创造性。这种句式构造及修辞手段使用的创造性,在上面所引用的几段议论性话语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如“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的”使用的是现代白话文的句式,而“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采用的则是文言与白话杂糅的句式。“有些胜利者”和“又有些胜利者”是并列复句,而“死的死了,降的降了”和“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以及“教我惭愧,催我自新”等,使用的是排比句式。“如虎”、“如鹰”和“如羊”、“如小鸡”既是比喻修辞的句式,也是排比与对比修辞的句式。很明显,这些句式的构成以及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从句式、手法、语法形式以及使用的喻体等,都是符合句式与修辞规范的,而句式构造与修辞手法使用的创造性,也就在遵循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形成的内在机制则是小说的思想表达的需要与艺术构造的需要,并非单纯为创造而创造的结果。
有学者在研究鲁迅小说采用比喻的创造性时曾指出:“创新,是自己选择材料,安排情境,设立新喻。鲁迅先生善于广泛而精密地观察周围的事物,因而他所挖掘的比喻材料,数量多,意境新。在先生的笔下,用作喻体的,有人物,有鬼神,有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有器具,有时间,有地点,有动作,等等。鲁迅先生善于大量地选择新鲜的喻体,运用自如地创造出各类比喻,使文学语言不落俗套,别具一格,清新隽永,耐人寻味,从而灵活有力地完成表达任务。”④朱泳焱:《鲁迅小说中运用比喻的特色》,《修辞学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97页。这虽然是仅就鲁迅小说比喻使用的创新而言的,但也确实揭示了鲁迅小说话语构造及修辞创新的普遍性规律,这就是“自己选择材料,安排情境”,“灵活有力地完成表达任务”。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手段的创新,包括采用什么样具有新意的话语构造及修辞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完成表达任务。而在这段议论性话语中所采用的句式构造及修辞手段,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如句式构造:“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的。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复句,使用的是现代汉语通常采用的“之所以”,“是因为”的结构方式,但又创造性地使用了文言句式“者何”的方式。如此文白杂糅的句式构造,是根据“安排的情境”“选择”的句式,根据思想的表达与艺术的目的,即揭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这个判断的荒谬性并由此讽刺与否定赵太爷这个人物而创造的特别句式。
就“情境”的安排来看,所谓“赵太爷是不会错的”这个判断,并不是根据现在的事实及普世的价值判断或者法律条文作出的,而是根据古旧的法则即“未庄通例”作出的,而这个通例的本身就是荒谬的,其荒谬性就在于,有威风的名人“如赵太爷者”,不仅打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更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相反,被打的小人物还会因为被名人打而出名甚至被“载上”人们的“口碑”,受到人们“格外尊敬”。依此类推,自然就推出了“通例”的荒谬性,也使“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这句表明肯定的判断露出了否定的“马脚”:既然“如赵太爷者”打人不仅是“不会错的”,而且似乎还有恩于被打者如阿Q,那么赵太爷就应该多打阿Q几次,因为,按照“通例”的逻辑,赵太爷只打了阿Q一次就已经让人们“格外尊敬”阿Q了,那么,如果赵太爷多打阿Q几次,则阿Q肯定会让人们“格外”又“格外”的尊敬。正因为“通例”是荒谬的,那么,建立在这个荒谬的“通例”基础上的所谓“赵太爷是不会错的”这一判断的荒谬性也就不言自明了。同样,既然这个判断是荒谬的,那么作为这个判断以及句子主体的赵太爷的荒谬性也就同样不言而喻了。这正是此文白杂糅的创造性句式构造的思想匠心之一。
同时,在艺术上,如此的话语构造不仅符合其具体的语境,而且也符合赵太爷这个名人的身份。从具体语境来看,既然“未庄通例”是一种“古法”,是大众都心以为然且习以为常的规则,那么,用一种文言句式“所以者何”就不仅具有“古”意,而且也完全符合“通例”“古”的话语规范。从赵太爷的身份来看,他不仅是“文童的爹爹”,而且实乃“秀才”者也,小说中很含蓄地点明了他的“秀才”身份,即“赵太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赵太爷既然是一名秀才,自然也是通晓古文的,所以,以“所以者何”的文言句式来揭示一个判断的荒谬性,不也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恰到好处吗?更何况,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手法还是鲁迅最常使用的杂文手法,尤其在讽刺与否定所涉对象的杂文中更是经常使用。如在驳斥新月社文艺理论批评家梁实秋的观点时,鲁迅“就这样,‘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梁实秋的辩解,恰恰成了鲁迅的论据”①袁良骏:《鲁迅杂文的艺术技巧》,北京市鲁迅研究学会筹委会编:《鲁迅研究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7页。。事实上,鲁迅不仅在自己的杂文创作中频繁地采用这种“杂文的手法”,而且,在观念上他也很提倡采用这样的手法来回击恶意攻击和自我吹捧,揭露对象的“马脚”及社会的假面具,阐释正面的主张。如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一方面有理、有据地论证了现在还不能一味地“费厄泼赖”的问题,一方面则不仅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方式表示了赞同,而且还直接地使用了这种手法:“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②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所以,鲁迅在小说中采用文白杂糅的句式构造,不仅具有艺术的合理性,彰显了《阿Q正传》中的这段议论性话语的杂文性特点,而且也将鲁迅对这种“通例”及与这种通例密切相关的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赵太爷的讽刺性思想倾向含蓄地表达出来了。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文白杂糅句式构造的艺术匠心与思想匠心就在这里,其魅力也表现在这里。
同样,在修辞手法(包括微观修辞手法)的使用方面也是如此。在“有些胜利者”这段话语中,鲁迅既采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也采用了比喻与对比的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手法的采用,既指向思想表达的目的,也有艺术的合理性与审美性,这些修辞手法的采用与鲁迅在杂文中使用的修辞手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或者完全可以说,鲁迅就是根据杂文的语体特点采用的修辞手段。朱彤先生在论述《阿Q正传》时曾经说:“其实,〈阿Q正传〉的‘序’,就是以杂文方法写的”,这种“杂文方法”就是“将形象勾描和思辨说理高度统一起来。”①朱彤:《鲁迅杂文独创的艺术》,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下,第387、386、387页。用瞿秋白论鲁迅杂文特征的概念来说,就是“文艺性的论文”②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上,第105页。的方法,当今中国大陆学者概括为“诗与政论的结合”。这种方法是鲁迅的杂文能够成为一种文学品类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人们为鲁迅杂文独立为一门艺术辩护,反驳“现代文学史上的某些反动文人一向诬称鲁迅杂文为‘骂人文选’,咬牙切齿地不许它们‘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的重要依据,当然也是鲁迅杂文的重要艺术魅力的表现。“‘诗与政论的结合’,这几乎成了杂文(小品文)的公认的定义。但是,在一般的杂文作者笔下,‘诗’的因素往往是十分微弱的,大多只不过是把一个道理讲得委婉生动一些而已。这样的杂文,很难说它是艺术,也谈不到什么艺术技巧。在鲁迅的杂文中,‘诗’因素是主要的、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这就使它们有资格‘侵入’了‘高尚的文学楼台’,使它们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量,这也就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基本艺术特征。”③袁良骏:《鲁迅杂文的艺术技巧》,北京市鲁迅研究学会筹委会编:《鲁迅研究论文集》,第331、333页。正因为鲁迅杂文的这种方法如此重要,又如此具有魅力,所以,朱彤先生甚至认为将这种方法“即叫做第四种方法也未尝不可”。朱彤先生之所以称鲁迅杂文的这种方法为第四种方法,就是因为,“塑造形象只有三种方法:一是抒情诗;二是叙事诗,包括小说、特写和传记文学之类;三是戏剧。”而这种“将形象勾描和思辨说理高度统一起来”的方法,是继已有的抒情诗、叙述文学和戏剧塑造形象的三种方法之外由鲁迅“独创”并完善的方法。而鲁迅所创造的这第四种塑造形象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的魅力,在小说《阿Q正传》这段议论性的话语中能轻易地寻索到,也能直观地通过审美把握,而寻索与把握的基本路径就是鲁迅在这段话语中所采用的微观修辞。
毫无疑问,这段议论性的话语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具有生动地揭示小说主旨与表达鲁迅思想与情感倾向的功能之外,也同样有塑造人物,特别是阿Q这个主要人物形象的作用。这段话语对阿Q形象的塑造,采用的正是形象的勾勒与思辨说理高度统一的方法,并且,无论是形象的勾勒还是思辨说理,都是对阿Q这个人物形象“深度”的塑造,因为,这段议论性话语所揭示的不是阿Q形象的外在特征,而是阿Q形象特有的精神特征——永远得意。这一段“议论性的话语”,其思辨与说理常常伴随着形象的勾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阿Q这个人物形象的勾勒;第二是采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如排比、对比、比喻等具有形象性的修辞手法。前一个方面的勾勒,是这段议论性话语的主要目的与特色之一,即鲁迅书写这段议论性话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有效地塑造阿Q这个人物,“深度”地塑造这个“国人的魂灵”;后一个方面的“勾勒”是这段议论性话语构成的艺术特色,即鲁迅的议论,无论是对阿Q这个人物的议论,还是对“改造国民性”的议论,都不是生硬地使用政论话语或公文性的话语展开的,而是采用文学作品中最常用的艺术修辞的话语展开的。而这两个方面的“勾勒”又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于这些修辞手法的采用,不仅使思辨与说理消除了生硬性,具有了艺术的生动性,而且使所要塑造的人物阿Q的精神特质得到了多方面的凸显,或者说这些修辞手法无一不具有揭示阿Q精神特质的作用,如句群:“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如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而觉得胜利的无聊。”就综合地采用了排比修辞、对比修辞及比喻修辞的手法。所谓“他才感到”、“他便反而觉得”两句,就既是排比句,也是对比句,即“欢喜”与“无聊”对比;所谓“如虎,如鹰”,“如羊,如小鸡”,则既是比喻,也是排比,同时还是对比,是强者与弱者的对比。有学者认为,在杂文中“鲁迅善于运用比喻,亦复擅长运用对比”,善于运用比喻的结果,“既为文章增加了瑰奇动人的风采,又给读者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特别是与论敌斗争的时候,他往往通过巧妙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事实的实质,揭露敌人的本相,使他们只是望风披靡,无可争辩。”擅长运用对比的结果“则使文章意义更加深刻有力。”①刘绶松:《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下,第207-209页。这些评价,也完全适应对鲁迅小说中这段话语所使用的比喻及对比修辞效果的评价。
当然,鲁迅小说中这段话语所采用的比喻及对比等修辞手法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效果,即这些修辞手法的采用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阿Q的精神特质,即“他是永远得意”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出了一个既不是“无聊”的胜利者,也不是战胜了强者的“欢喜”的胜利者形象,而是一位个性独特——“没有这样乏”而又是某些“中国精神文明”的代表者的形象——阿Q。同时,这些修辞手法的采用,也使这段话语最后的总结以及对阿Q“永远得意”的意义说明——“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有了艺术的依据,同时也消除了这些议论性话语的生硬性以及随意性,从而使这最后的总结、议论成为了整段话语,乃至于整篇小说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也使这些修辞手法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