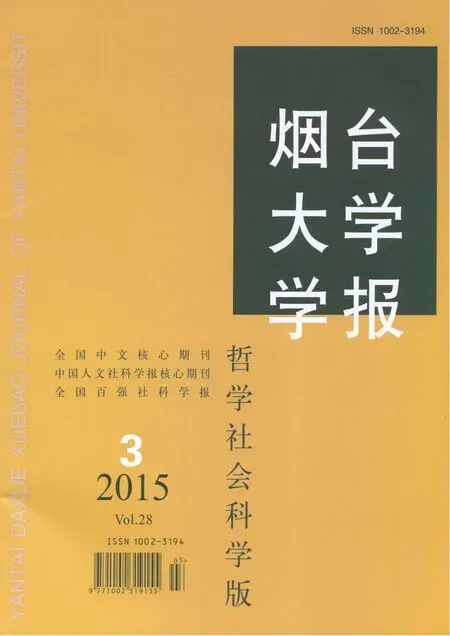印刷媒介的视觉偏向及其美学后果
李昕揆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印刷媒介的视觉偏向及其美学后果
李昕揆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提出“地球村”概念而享誉全球的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继承西方哲学、美学中的视觉-理性传统,将印刷术与视觉、理性相勾连,创造性地阐明了由印刷媒介所强化的视觉感知偏向对于人类思想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此视觉偏向作用于人类的认知模式,表现为对固定视点、可见性和线性思维的强调;作用于美学领域,表现为印刷时代美学范式——“思想的美学”的形成;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体现为“透视法”/“视角”(perspective)这一以理性为主导的表征方式在诗歌、绘画和小说中的贯彻与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无韵诗、玄学派诗歌、自然主义绘画以及西方现代小说的兴起。
麦克卢汉;印刷媒介;视觉偏向;美学后果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3.007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提出“地球村”概念而享誉全球的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被美国庞大的宣传机器打造成一颗耀眼的文化明星。汤姆·沃尔夫更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文将麦克卢汉称作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为重要的思想家”①Tom Wolfe,“Suppose He is What He Sounds Like,”G. Stearn (ed.),McLuhan:Hot & Cool,New York:Signet Books,1967:p.31.。在《谷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1962)这部媒介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中,麦克卢汉创造性地阐明了印刷媒介对于人类思想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开创了媒介研究的“感知效应范式”②注重媒介的“效应/效果/后果”是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重要特征。他指出,“理解媒介实质上就是理解媒介的效应。”金惠敏先生用“后果范式”来概括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他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可以用‘后果范式’来概括。他并不忽视对各种媒介特征的研究,……但其目的是试图说明这种或那种媒介因其不同的特点而对社会构成不同的影响”。见金惠敏:《“媒介即信息”与庄子的技术观——为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而作》,《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笔者认为,麦克卢汉主要关注的是媒介的感知偏向对于人的影响,为此,笔者将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范式统称作“感知效应范式”。。他认为,媒介的影响不是发生在人的观念层面,而在于改变人们的认知模式和感官比率。具体到印刷媒介,麦克卢汉将印刷术的发明视作一场重要的媒介革命,*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p. 141.并将这场革命视作是对人之联觉互动的切断和对视觉感知的强调。在他看来,印刷媒介强化并将表音文字的视觉偏向推向极致,它鼓励人们以印刷书页形态的方式去安排知觉,用视觉的方式去调和日常经验,使人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偏重于视觉感知,“中立而工于计算的眼睛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Tom Nairn, “McLuhanism: The Myth of Our Time”, in Gary Genosko (ed.), Marshall McLuhan: 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 Vol.1 Fashion and Fortu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25.。麦克卢汉将这一过程称作“视觉的‘腾飞’”(visual take-off):“印刷术问世之后不久,视觉经验和组织的新维度随之诞生,亦即所谓的‘腾飞’阶段。”*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p. 99.印刷媒介的这种视觉冲击,作用于认知模式,表现为对可见性、固定视点、线性思维和理性的强调;作用于美学领域,形成了近代西方自勒内·笛卡尔以来发达的“思想的美学”传统;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体现为“透视法”(perspective,在文学领域常译作“视角”)这一以理性为主导的全新观看方式在诗歌、绘画、小说中的贯彻、实施。下面,我们从麦克卢汉的“感知偏向理论”出发,分析印刷媒介的视觉偏向及其哲学根源,探讨印刷时代的美学范式以及“透视法”在文学艺术领域应用所引发的美学后果。
一、从媒介感知理论到“媒介史观”
“感知”是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基本视角,探究媒介影响人类感知的方式,是麦克卢汉媒介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源自拉丁语的“感知”(aisthesis)一词具有“perception”和“sensation”双重含义:“perception”侧重于颜色、声音、味道等感官属性,它为“认识”服务;“sensation”偏重于人们的情感走向,它以“愉快”与否为评价尺度。*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81页。麦克卢汉主要是在“perception”的意义上使用“感知”一词的:媒介重构感知,不同的媒介导致不同的感知偏向,这构成为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在麦克卢汉的著作中,他也偶尔在“sensation”的意义上使用“感知”,比如他说,若要了解人类的感知史(the history of human sensibility),应当注意风行于威廉·布莱克时期的哥特式浪漫在后来的罗斯金和法国象征派诗人手中变成极为认真的美学运动。见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p. 266.在他看来,媒介与人的感知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当一种媒介上升为主导媒介之后,它就会重塑人们的感知,并使整个社会在各个层面呈现出与主导媒介相适应的特征。“任何媒介都必然涉及感官之间的某种比率”*Marshall McLuhan, 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56.,其效应“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层面,而是毫不受阻地改变人们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patterns of perception)”*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64, p. 18.。麦克卢汉提醒人们,主导媒介的变化带来的是感官比例的调整,最终引发的是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力以及思想模式的彻底改变。以此出发,麦克卢汉根据主导媒介的不同,将人类历史重新划定为口传时代、书写时代和电媒时代三个阶段,提出了其影响巨大且极富阐释力“媒介史观”。在口传时代,信息的传播与加工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来完成,口和耳是交流倚重的最主要器官,经验生活由占据主导地位的听觉生活来安排,“部落人”在这种口耳相传的复杂网络中发展起“由复杂情感构成的创造性混成体”*Marshall McLuhan, Essential McLuha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231.。文字诞生之后,以书面形式进行间接交流和沟通成为信息传播与加工的重要方式。此时,先前具有共鸣特征的“听觉空间”被打破,人们对感官的倚重逐渐转向视觉,人类开始步入分割的、专门化的视觉世界之中。具体到西方文化史,麦克卢汉将表音文字的诞生视作“视觉时代”到来的标志,他认为这与表音文字自身的独特性有关:“表音文字不仅将声音同视觉相分离,而且将意义同字母发音相分离,只以无意义的声音去表达无意义的字母。”*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p. 47.从表音文字之音、形、义相分离的特性出发,麦克卢汉得出结论:“表音文字的出现,让同时动用所有感官的机会大幅减少,变成了只使用视觉符号。”*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p. 45.麦克卢汉又将书写时代划分为手抄和印刷两个阶段:手抄阶段的学习方式仍需大声朗读、口耳相传和深度参与,手抄文本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口语特征,由其创造的感知模式亦并未同口语完全决裂。也即是说,由于莎草纸与鹅毛笔等书写工具的落后,视觉并未与听-触觉完全分离,“只有等到大量生产的经验出现,等到单一种类的事物可以重复生产,视觉才能够从其他感官中分离出来。”*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p. 54.麦克卢汉所说的“大量生产的经验”,实即印刷术的复制特性,它“以无穷的数量和前所未有的速度复制信息,确保了眼睛在整个感官系统中的主导地位”*Marshall McLuhan, Essential McLuhan, p. 232.。印刷这种机械方式的兴起,强化了表音文字的视觉化趋势,实现了眼睛从诸感官中的彻底分离,使表音文字的视觉偏向强化到全新的高度。换言之,在麦克卢汉看来,尽管表音文字揭开了西方文化史上的“视觉时代”,但它“只是一种支配性手段而非整全的社会文化形式,它仍与旧的听觉文化遗存共存”*Tom Nairn, “McLuhanism: The Myth of Our Time”, in Gary Genosko (ed.), Marshall McLuhan: 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 Vol I: Fashion and Fortune, pp. 24-25.,只有到作为表音文字的终极延伸——印刷术发明之后,对视觉的强调才达致顶峰。或者说,印刷术以其对书本的标准化生产,以其“统一性、连续性和序列性”的视觉化特征以及对“完整”和“系统”的强调,强化了西方文化史上由表音文字所发端的“视觉革命”。电报的发明标志着西方电媒时代的来临,它打破了视觉的一统局面,开启了人类重返同步、即时的听-触觉世界的历程。简单说来,在麦克卢汉那里,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从口传时代强调诸感官之共同参与的整体感知平衡,到感知分裂、突出视觉和强调专业化的书写时代,再到向电媒时代诸感官深度参与回归的发展历程。
二、从印刷媒介的“视觉偏向”到“思想的美学”范式
麦克卢汉将媒介与感知偏向相结合,将印刷媒介与视觉感知偏向相勾连的思想,受到了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媒介史家哈罗德·伊尼斯的深刻影响。在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两部著作(即《传播与帝国》和《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通过对希腊、罗马、埃及等古代文明帝国历史进程的追溯,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偏向”概念。在伊尼斯看来,石头、粘土、羊皮纸等是时间偏向的媒介,它们耐久性好但不易生产和运输,能够保证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统治的稳固与持续,却不利于宗教的传播和帝国的扩张;莎草纸、纸张、印刷品等是空间偏向的媒介,它们质地较轻,适合于帝国对广袤地区的治理和大范围的贸易行为,有利于帝国的扩张和宗教的传播,缺点是耐久性差且不易保存,使得以此为媒介的政治组织形式往往难以持久和稳定。为此,“必须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去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于时间媒介,也不过分倚重于空间媒介。”*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麦克卢汉将伊尼斯的“媒介偏向”概念称为“解读技术的钥匙”,“凭借这把钥匙,我们可以读懂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之技术的心理影响和社会效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见哈罗德·伊尼斯著:《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伊尼斯的“媒介偏向”概念对麦克卢汉转向媒介研究并开辟出新的媒介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启发,以致麦克卢汉一再谦虚地表示,其整个媒介理论都是伊尼斯著作的注脚。*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p. 50.当然,麦克卢汉并未遵循伊尼斯侧重于强调传播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路子,而是借用其“媒介偏向”概念,并将之与阿奎那的“感知”理论相嫁接,建立起一套强调“媒介自身”及其“感知效应”的全新的媒介感知理论。单就印刷媒介而言,麦克卢汉将印刷媒介与视觉感知偏向相联系,提出了“印刷媒介的视觉偏向”的命题。麦克卢汉以视觉对应书写和印刷文化,将视觉、印刷术与理性文化三者联系起来,从而将“印刷文化”视作一种“视觉文化”。这一结论令人吃惊,在当代许多西方思想家看来,“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是水火不容的一对概念,人们甚至可以引用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话去反对麦克卢汉的见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56页。尽管如此,将印刷文化视作一种“视觉”文化,始终是麦克卢汉的基本观点,也是其整个媒介思想大厦的根基。这种貌似对立的理解,实质在于不同学者对“视觉文化”的理解不同:麦克卢汉所说的“视觉”与“现代性”(或者说“理性”)密切相关,他借助于印刷媒介自身所具有的“同质性、连续性和序列性”等视觉特征,将印刷媒介、视觉文化同理性观念(在他看来,理性即意味着“统一性、连续性和序列性”)联系起来,通过对印刷媒介之视觉宰制的论述,重复并强调了西方文化中的“视觉-理性”传统。由此,麦克卢汉所说的“印刷文化”、“视觉文化”实可理解为一种“理性文化”。他认为,当视觉被强化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秩序”,这一秩序即“理性”。这种“理性文化”在美学领域的表现即“思想的美学”:“印刷时代不是没有‘美学’,有的是具有不同于电子时代的美学,是‘思想的美学’。”*金惠敏:《“图像-娱乐化”或“审美-娱乐化”》,《外国文学》2010年第6期。我们知道,任何符号在本质上都是对事物的“表象”,都是由我创造且亦为我的“可见性”。而由于表象在始源上对美的决定性,我们完全能够说:表象即美,或美即表象。若深究其因,我们可以说,由于表象意味着一个距离性的“看”,一个将对象摆置于眼前的活动,它不是对象的自我呈现,而是再-现,是假定了主客体分立的被-呈现。*金惠敏:《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而正是此“再-现”,此主客体分立的“距离”以及距离性的“看”,让我们清楚地看出:麦克卢汉通过对印刷媒介之视觉偏向的强调,推导出一个以视觉、再现、主体性、距离、理性为要素的印刷时代的美学范式——“思想的美学”。尽管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悖论,由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即理性与感性的对峙和冲突,“思想的美学”成为一个悖论性的说法。*金惠敏:《“图像-娱乐化”或“审美-娱乐化”》,《外国文学》2010年第6期。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在现代性框架之内,理性并不处在与感性相平行和对立的层次上,它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而成为独立“自由”的主体性。*金惠敏:《审美现代性的三个误区》,《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8日,第6版。
麦克卢汉的这一看法在马丁·杰伊那里得到了回应。杰伊认为,谷腾堡的活字印刷革命、艺术领域中的透视法以及笛卡尔哲学的确立,均强化了视觉中心的地位,使视界政体成为主体建构与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器。*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ley, Log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1-148.与将“视觉文化”理解为“理性文化”及“思想的美学”不同,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视觉文化”概念与“感性”范畴或者说“图像的美学”密切相关,确切地说是与伴随影视技术、数码影像、电子网络的出现而兴盛的影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电子媒介或者如波兹曼所聚焦的电视媒介,在印刷媒介所创造的‘思想的美学’之后,复活了‘图像的美学’,在其中波兹曼突显了一个以感性或感官娱乐为主导的审美理念。”*金惠敏:《“图像-娱乐化”或“审美-娱乐化”》,《外国文学》2010年第6期。历史地看,较早提出当代意义上的“视觉文化”概念的是匈牙利学者贝拉·巴拉兹(Bela Balazs)。他在《电影美学》(Theory of the Film, 1952)中认为,所谓“视觉文化”就是通过可见的图像或形象(image)来表达、理解和解释事物的文化形态。他将电影的发明视作新视觉文化形态出现的标志:“电影将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每晚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坐在电影院中,不需要看太多的文字说明,纯粹通过视觉来体验事件、性格、感情、情绪,甚至思想。因为文字不足以说明画面的精神内容,它只是尚不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一种过渡性工具。”*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第29页。可以看出,巴拉兹提倡的“视觉文化”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针对“视觉”或“视觉文化”的研究,而是针对“视觉性”的文化研究,是对“视觉性”的后现代质疑,是对“奇观”社会的后现代逆写。*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所谓“视觉性”(visuality),即隐藏在看的行为中的全部结构关系,或者说视觉对象的可见性机制。用米克·巴尔的话说,这种“视觉性”是“使物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既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看的主体的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场。总之,一切使看/被看得以可能的条件都应包含在这一总体性之内。因此,视觉性必定与某种'视界政体'(scopic regime)是联系在一起的”。麦克卢汉早在1954年发表于《公共福利杂志》的《视像、声音与狂热》一文中就已注意到巴拉兹的说法。麦克卢汉写道:“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在其《电影理论》一书中,注意到‘印刷的发现渐渐地展现了难以辨认的人脸。通过面部表情来传达意义的方法被废止不用了’。印刷的书籍取代了中世纪教堂所起的作用,变成了人们精神的载体。成千上万的书籍把……教义分裂成无数本书。可见的精神因此而转变成可读的精神。视觉文化变成了概念文化。”*麦克卢汉:《视像,声音与狂热》,见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著:《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也就是说,在麦克卢汉那里,“视觉文化”是一种“概念文化”,或者说“理性文化”,而在巴拉兹那里,“视觉文化”则是一种“图像文化”。
在麦克卢汉看来,视觉感官在印刷术塑造的理性文化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与西方长久以来的哲学、美学传统密切相关。在西方思想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视觉传统,从柏拉图到现在,该传统是连续且始终有效的。*Jonathan Crary, “Modernizing Vision”, in Hall Foster (ed.), Vision and Visual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88, p. 29.眼睛、视觉以及与之相关的光、镜子、灯等,均成为普遍接受的隐喻表达:赫拉克利特很早就认识到,“眼睛是比耳朵更可靠的见证”;金口狄奥说,“眼睛比耳朵更值得人信赖这种流行的见解是正确的。但眼睛比耳朵更难加以说服,它要求更大的清晰性”*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93页。,他暗示,眼睛的高度自制力让其能够排除一切肉欲干扰,追求最大限度的清晰与真实;柏拉图划分了肉体之眼和心灵之眼,认为眼睛能够辨识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皆因眼睛之视觉能力;亚里士多德则将眼睛的认知能力与人类的求知本性直接相联,认为“求知乃人类本性使然,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官即是明证。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因为视觉能使我们认知事物,且在显明事物之间差别中,以赖于视觉者为多”*Aristotle, The Metaphysic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99, p. 1.。自亚里士多德起,眼睛逐渐确立在求知和理性方面的地位。这在古罗马时期的奥古斯丁那里得到进一步强调。他说,“我们的心灵中有一种挂着知识美名而实为玄虚的好奇欲,这种欲望虽通过肉体感觉,但目的不在肉体快感。此欲望之本质乃追求知识,而求知的工具即为眼睛”*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9页。译文稍有修改。。中世纪思想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也认识到眼睛和智力之间的亲和关系,将眼睛置于所有感官之首。德国古典美学之集大成者黑格尔,从眼睛与内在心灵的关系中肯定了眼睛的优先地位:“如果询问整个灵魂究竟在哪个器官上显现为灵魂?我们马上即可作答:在眼睛上。因为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而且要通过眼睛才能看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97-198页。译文稍有修改。。可以说,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眼睛既是理性的载体,亦是理性认知的工具和途径。理性的本质和属性皆需借用眼睛及视觉加以解释和确定,眼睛、视觉与理性的思维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有着如此源远流长的哲学美学传统,我们自然不难理解何以麦克卢汉将眼睛和视觉归之于充满理性意味的印刷媒介。就像麦克卢汉所说,“铅字是所有机器的雏形,保证了视觉偏向的主导地位,宣告了部落人的终结。线性、划一、可重复的铅字,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复制了大量信息,保证了眼睛在人类感官系统中的绝对支配地位”*Marshall McLuhan, Essential McLuhan, p. 232.。可以说,麦克卢汉将印刷媒介、视觉、理性三者之间的勾连,他对印刷媒介之视觉宰制的论述,以及以此出发推导出的印刷时代以视觉、再现、主体性、距离、理性为要素的“思想的美学”范式,再次重复并强调了西方美学史特别是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美学传统对于“眼睛”、“视觉”和“可见性”的强调。
三、从绘画到文学:“透视法”在艺术领域的贯彻
麦克卢汉将媒介同感官相联系,将“媒介塑造感知”同作为“感知操练”的文学艺术相联结,并将之置于对西方文艺发展史的考察之中,带给我们一种观看文艺发展演变的全新方式。根据其“媒介史观”,麦克卢汉将文艺发展史划分为口传时代的“听-触觉艺术”、书写时代的“视觉艺术”以及电媒时代向“听-触觉艺术”的回归三个阶段。在口语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类型是诗歌,它们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布和传播。即使口语时代的诗歌被结集之后,它们的口语化特征依然十分明显。流传至今的《荷马史诗》堪称典范,其口语化倾向不仅表现为对口头艺术表现技巧——夸张、烘托、比喻、固定修饰语、套语——的大量运用,也表现在诗歌本身所采取的独特韵律——六步格诗行等方面。表音文字诞生以后,过去完全依靠口传的诗歌体制逐渐崩溃,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即是表音文字发明之后视觉对口语和听觉进行攻击的一次集中反映。麦克卢汉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荷马史诗》是听觉智慧的组成部分,文字文化把荷马一笔勾销。在此之前,听觉智慧就是希腊的教育体制,有教养的希腊人就是能够记住《荷马史诗》并且能够在竖琴的伴奏中吟诵《荷马史诗》的人。表音文字诞生以后,柏拉图立即抓住它并且说,‘让我们抛弃荷马,追求理性的教育’。可以说,柏拉图对诗人的战争,不是对个人的宣战,而是对教育中口头传统的宣战。”*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也就是说,在文字诞生之前,诗歌是口与耳的互动,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教育体制自然是听觉智慧的体现。表音文字诞生之后,部落式的口头传统在书写的挤迫下逐渐衰退,口语化特色随之减弱,对眼睛和视觉的强调开始超出对耳朵和听觉的重视,表现在艺术之中就是“再现性”文艺类型的出现:“被表音文字延伸的视觉感官培育出在形式生活中感知单一方面的分析习惯。视觉使我们能够在时空中将单一事件孤立出来,一如‘再现艺术’(representational art)所为:它从视觉上表现人或物时,总是将人或物的某一状态、时刻、侧面从众多状态、时刻和侧面中孤立出来”。*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p. 334.作为表音文字之终极延伸的印刷术,进一步“促使艺术家尽其所能地把一切表现形式压缩到印刷文字那单一描述性和记叙性的平面之上”*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p. 54.。这在诗歌中表现为“词与乐的分离”和“向更为抽象的视觉效果的转化”(麦克卢汉以伊丽莎白时期出现的“无韵诗”和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进行了分别说明)*Marshall McLuhan, Essential McLuhan, p. 294.;在绘画中表现为“透视法”和“灭点”理论的兴起以及画家在画布中对于叙述性平面的“逼真”展示;在小说及其他叙事性作品中表现为“内视角”、“外视角”的兴起以及对过去“全知视角”主导局面的突破。
以印刷媒介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现代诗歌,在麦克卢汉看来,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印刷媒介的影响。在他那里,“视点”是与印刷媒介的视觉偏向密切相关的一个关键术语。印刷媒介使人们发现“视点”,并把此“视点”应用到诗歌写作之中,从而影响了现代诗歌的模式。这在英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无韵诗和玄学派诗歌中有着清晰的体现。就无韵诗而言,麦克卢汉指出,“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来说,无韵诗(blank verse)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全新发明。它犹如当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二者在夸张和放大感觉方面颇为相似。”*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p. 197.麦克卢汉将无韵诗的出现同印刷术的发明相关联。他认为,词与乐(前者主要诉诸于视觉,后者主要诉诸于听觉)的分离最早由印刷反映出来,而无韵诗恰好出现于二者首次被撕裂的年代,此时,诗歌成为慢下来的话语,其目的在于品尝其间的细节而非主要诉诸耳朵与听觉。在麦克卢汉看来,印刷术发明之前诗歌的出版实际上是诗作的阅读和吟诵;印刷术使得诗歌主要存在于印制的书页之上,这促成了玄学派诗歌的诞生。就像他所说,“十七世纪诗歌典型的形而上风趣效果,是中世纪手稿和木刻的视觉效果向印刷文字更为抽象的视觉效果转化而产生的结果”*Marshall McLuhan, Essential McLuhan, p. 294.,“当诗歌在十七世纪主要存在于印刷书页之上时,便出现了以‘玄学派诗歌’而闻名于世的视听的奇妙混合,这种‘玄学派诗歌’与现代诗别无二致”*麦克卢汉:《视像,声音与狂热》,见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激进的美学锋芒》,第334页。。
从柏拉图到近代的笛卡尔、黑格尔,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即从表音字母发展到印刷术,眼睛在诸感官中的主导地位逐步强化,视觉作为认知工具亦愈来愈脱离肉体的影响,在把身体的作用最大程度地排除干净之际,视觉与对象之间就构成了“一种纯粹的认识性关系”*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页。,影响到艺术创作领域,产生了所谓的“镜子说”以及一系列以“逼真”为审美理想的衍生样式,如模仿说、再现说、典型论等。为了能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世界以制造“逼真”效果,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如布鲁内勒斯基、阿尔贝蒂、达·芬奇等,在长期的艺术探索中总结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及其前时期的视觉操作模式——“透视法”。或如罗杰·弗莱所说,“为了真正发现事物的本来面貌……从乔托的时代起,欧洲的艺术多多少少是沿着这条道路持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透视法的发现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Roger Fry, “Reflections on British Painting,” in E. H.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London: Phaidon Press, p. 247.。在透视主义看来,肉眼直接看到的现象并不真实,真实的事物存在于理性活动中,这是从柏拉图对肉体之眼和心灵之眼的划分中得到的启发。在此意义上,透视法即人之理性信念的外现。透视法发明以后,最先运用于绘画领域,并推动了自然主义绘画的兴起。当时的画家们无不仔细地观察自然,热心地探讨复制自然的技巧与方法,以追求身临其境的“逼真”效果;表现在人体画中,丢勒、弗兰西斯嘉等许多艺术家把“人体比例理论当作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和美的理性基础”,*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以至于文艺复兴时期关于透视的数学精确理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韵律的”细腻描绘均是由精确的几何学构造决定的。对这些细腻描绘而言,那些尺寸必须应用于视平线上的作品中。见Erwin Panofsky,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Princeto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95.,成为一项重大的发明。艺术批评家们亦无不以“逼真”(fidelity)作为艺术批评的最高标准。阿尔贝蒂说,“画家的职责就是以线条和色彩去设计和描绘任何现有的物体,并且做到使人感觉画出来的东西看起来永远就和那些现有的物体一般的地步”;达·芬奇说,“最值得人称赞的画,乃是那与其模仿之物最为一致的画”;瓦萨里也说,“针对一切由自然所呈现之形式,加以密切模仿,使得它们仿佛是自然产生出来那般。谁若达及如此效果,也就登上了完美无比的顶峰”*刘文潭:《西洋美学与艺术批评》,台北:环宇出版社,1984年,第26页。。透视法的发明,帮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使得写实风格的绘画有了长足发展,不仅涌现出了佛罗伦萨、威尼斯、翁布里亚、帕多瓦等众多地方画派,而且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等文艺复兴三杰,达到了西方写实美术的一个顶峰。透视法集中体现了西方绘画的传统审美理想,它的出现不仅使西方美术摆脱了中世纪长达千年的艺术程式,绘画得以重新向写实主义靠近,而且成为文艺复兴之后长期影响西方画坛的最主要表现方式,标志着世界美术史在创作原则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巨大进步。
在小说及其他叙事性作品中,“perspective”一词常译作叙述“视角”,它受到绘画中“透视法”的直接影响。恰如托多罗夫所说,“在此,绘画的历史再次为我们提供了雄辩的例证。只须想想那些变形图画或数字图画就清楚了:若从常见的角度看,它们简直莫名其妙;然若从某一特殊角度观察,那么它们就显示出人们所熟知的物体的图像”*茨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见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在叙事作品中,所谓视角,即叙事者看待世界的特殊眼光,是其将可见世界转换为语言代码的独特角度,主要包括“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以及它们所提供的进入人物内心的方式”*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页。等。也就是说,构成故事的各种事实,从来就不是以所谓“事实本身”的样子出现的,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或某个观察点以呈现给我们。根据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成果,叙述视角一般可分作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三种。但在中西方传统叙事作品中,如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西方的长篇史诗,全知视角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传统的和自然的叙述模式中,作者出现在他的作品的旁边,就像一个演讲者伴随着幻灯片或纪录片进行讲解一样”*Rene Wellek &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 223.,它“往往破坏了故事的幻觉”*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40页。,留给读者的创造性空间极小,作品表现出的个性特色极不鲜明。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以及伴随的自我意识的崛起*麦克卢汉将印刷术看作“促成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的工具”,认为印刷术“催生了隐私权、作者权的观念”,“为作者扩展个人时空维度提供了物质条件”。希利斯·米勒认为“西方文学的整个全盛时期,都依赖于(由印刷术所催生的)自我观念”,他以17世纪第一人称小说、18世纪书信体小说、浪漫派诗歌、19世纪第三人称小说、20世纪意识流小说为例,认为“文学所有的重要形式和技巧,都利用了新的自我观念”。见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p. 131. 和 J. Hillis Miller, On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9-10.,作家们开始突破全知视角的主导局面,并逐渐探索出“内视角”、“外视角”等多种叙事角度。“视角”问题体现出的既是叙述者理性认知多样化的结果,亦是个体意识张扬以及人之主体性地位确证的表现。多种视角在叙事作品中的凸现,使得自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斯威夫特、理查逊和菲尔丁以来,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呈现出异常夺目的风采,并产生了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巨匠。在中国,也正是有了二十世纪初期小说创作中对“视角”问题的突破,才有了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中小说的辉煌。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印刷术对视觉的强调及由此而来的对“视角”问题的探索,极富个人特色的现代小说的兴起与繁荣是难以想象的。
可以说,在麦克卢汉那里,无韵诗的出现是由印刷术所导致的词乐分离的结果,弥尔顿最早在无韵体诗歌中引入“视点”,则是印刷媒介之视觉化效应和线性透视原则渗入语言和文学世界的重要标志;玄学派诗歌的出现,在麦克卢汉看来,则是印刷文字抽象化的视觉效果的产物,就像他所说,“印刷术使得诗歌得以在印刷的书页上存在,这促成了玄学派诗歌的诞生”。透视法在绘画中的应用以及多种叙事“视角”在小说中的贯彻,导源于“书写-印刷”对视觉偏向的强调,它作为“思想的美学”范式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体现,背后反映出的是“相似论”和“符合论”的真理观。最后,尚需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本文讨论了印刷术之视觉偏向对文学艺术的美学后果,但我们对“美学”的理解绝非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在我们看来,“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序”。。也就是说,带有浓厚理性色彩的“思想的美学”范式,不仅仅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更体现在社会文化、认知模式、知识生产、交际方式、媒介环境等更为广阔的文化现代性层面,而此正是我们下一步所要着力探索的工作。
[责任编辑:刘春雷]
Visual Perception Bias of Print Media and Its Aesthetic Effects
LI Xin-kui
(TheInstituteofForeignLiteratur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Marshall McLuhan,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the global village” and then becoming a world-famous thinker of media,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vision-reaso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related the print media, vision and reason together and creatively clarified the effects of print media on the minds and lives of people in the early nineteen sixties. The effect often manifests itself in emphasizing the visibility, the point of view and liner thinking in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s, it shows up as an aesthetic paradigm of the print age, that is to say, “ideas aesthetics”. And the effect re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of "perspective" and the rising of naturalistic method i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Marshall McLuhan; visual perception bias; aesthetic effects; print media
2014-11-03
李昕揆(1982- ),男,河南安阳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媒介文化研究。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现代文论范式生成研究”(2013BWX012)
B 83-069;G 20
A
1002-3194(2015)03-005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