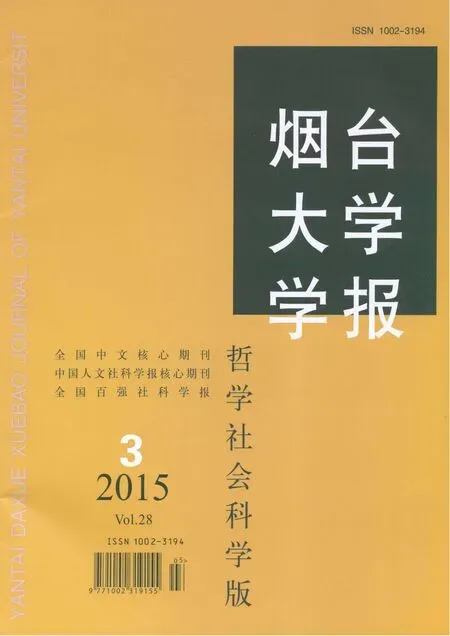谈德里达对文字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孟宪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谈德里达对文字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孟宪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德里达认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重要表现,因此,他在其解构论的基础上批判和解构了结构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形式以及二元对立、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他意欲解构结构主义,而其所理解的结构主义是人的一种先验的建构,而不是具体的实践活动如劳动和游戏的建构,忽视了历史结构性。他反对写作的“在场形而上学”,却把虚无和在场截然分开。他通过“延异”、“痕迹”、“隐喻”等策略反对写作和文字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和基础主义,但并不能就说其具有“意识的虚构性”、“语言的隐喻性”和“叙述的话语性”。
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解构;后现代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3.001
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巨擘之一,德里达对文字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的批判中,另外,还存在于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中。首先,什么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它有哪些特点?简单的说,“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存在于西方思想史中的把理性(逻各斯)作为绝对权威和中心,排斥和压制非理性的东西的倾向和做法,是一种将存在(理性)整体作为在场的思想传统。它认为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之外有一种独立的本源性存在,即哲学本体(如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本文拟分析德里达对文字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及其理路。
一、解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20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几乎涉及哲学及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人类学、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的心理学,等等。结构主义的主要方法论原则就是借鉴和运用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方法,因此结构主义的方法从总体上来看是一种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哲学结构主义是现代科学理性在哲学领域中的极端表现,因此在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多数哲学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具有思辩传统的哲学家如现象论者和存在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和持续批判。
德里达深刻揭示了结构主义的实质和特性。首先,德里达认为,所谓结构,就是具有边缘和中心的整体,是一种认识的“图式法和空间化法”,是“形式和意味的形式统一体”。第一,他认为结构主义有着思想的积极意义:“它激活了我们所称的西方思想,而这一思想的命运是随西方疆域的回撤而向外延伸的……所有时代的文学批评本质上注定都是结构主义的……由于这种多少获得承认的图式法和空间化法,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平面扫视脱离了其自身力量的场域。”其次,他认为,结构不仅是在通常的意义上的相对于内容的形式和方法,它变成了事物本身,变成了“事物的空间化”和秩序。实际上,结构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是一种人所建构的东西。但同时德里达揭露了结构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或终极目的论结构主义”及其把事物数学化、客观化的本质。在德里达看来,“形式主义、终极目的论、对力量、价值和时间的还原都是一回事,因为它们都用几何学制造一种结构。”*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页。而且在德里达看来,结构主义特别是“绝对结构主义”,在拒绝本体论的目的论的同时,也排斥一种生活或实践的目的论,这样就忽视了结构形成的目的性活动的性质和过程,从而陷入了形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并使结构成为一种封闭的东西和僵死的东西。一个“极端的结构主义者”,就是强调事物结构的一贯性和完备性。
那么,如何解构结构主义呢? 首先,在德里达看来,精神无法被结构“同一”,不完全为结构所拥有。精神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而结构只是理性分析的结果,结构只能代表着或表征着精神中理性的那一方面,而不能统辖非理性那一方面,而且非理性是一种非形式化的东西,而结构是理性对事物的形式化的处理的结果,所以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对等的。其次,系统或事物的中心不是一种场所,而是一种功能;而且在符号替换的无止境的游戏中,系统的中心也在不断地移位和替换。德里达说,结构的中心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一个“自然的场所”,它只能存在于逻辑分析的领域中;而且,结构的中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种认识的功能,即方法论的功能概念。在这个结构的中心存在着“符号替换无止境的相互游戏”,在言语特别是在对话中,这个结构的中心或始源作为一种先验所指,常常是缺席或常常被符号替换的。*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05页。最后,德里达指出,写作作为一种痕迹,一种隐喻,是结构和同一性的“他者”,既是形成和表现结构主义的“良药”,也是解构结构主义的“毒药”。德里达说,写作,“作为现世他者可能性的隐喻”,作为一种存在,与结构及其中心和始源并不是“和平共处”的,而是不断地对它们进行质疑和解构。*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第50页。
另外,借助于批判胡塞尔的相关思想,德里达强调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和结构是结构的生成和生成的结构的关系。第一,他认为结构主义必须以先验结构和生活经验的无限开放性为前提。在德里达看来,文本结构的开放性根源于文本共同体的界限的不确定性以及文本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化”。第二,胡塞尔的“先验感性论”意味着先验的结构是生成性的。这当然是德里达发现的胡塞尔思想本身中存在的反对或解构胡塞尔思想的东西,而不是胡塞尔明确表达的东西。德里达首先承认胡塞尔的“先验感性论”是与笛卡儿等人的近代唯理论哲学家乃至康德的先验哲学思想“相断裂”的,体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他们的先验思想的发展。德里达又认为,胡塞尔的先验结构存在着“向生成构成和这种新的‘先验感性论’过渡的必然性”。在这种“先验感性论”,大写的他者和大写的时间也是不可还原为结构本身的。在德里达看来,先验理性是历史生成性的东西,或者说,历史主义是对先验理性的“解毒剂”,因为先验的生成性使得结构的中心和意义的在场不断地被替换和补充。所以,胡塞尔的先验的“终极目的”作为意义的源泉,由于结构的历史性而成为开放性的。另外,德里达认为,在文本的结构中,文字的主体的“缺席”和在语言和语音之间的“间歇”不能被理性还原。所以,德里达认为:对于理解先验的历史性来说,胡塞尔的先验还原作为一种思想的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即深入先验整体及其历史内部的工具,而不是现实和历史实际的过程。
综上所述,德里达正确地抓住了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思想及其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方法论的特征,并进行了分析和解构。在本体论方面,他指出结构主义把结构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忽视或否定了人对结构的建构性质,结构主义所排斥的目的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论。在方法论方面,德里达指出,结构主义拒斥历史主义是片面、不合理的。事实上,结构主义的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源于其本体论的实体结构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既然结构是建构、生成的,它必然就是历史的,结构和历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就连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也明确承认结构主义这一方法论的缺陷,强调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结合*参阅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另外,德里达指出,结构主义的整体是封闭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认为,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解构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本体论方面,他所说的人对结构的建构主要是一种先验的建构,而不是具体的实践活动如劳动和游戏的建构。在方法论方面,德里达没有充分论证结构与历史在实践基础上的辨证关系,只强调结构的历史性和建构性,而忽视历史结构性。这种历史的结构性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历史是一种整体,具有相对客观的结构,二是承认这种历史的结构并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的,而是实践建构、创造的。另外,德里达只反对结构主义的客观的抽象的整体性,而忽视了结构的具体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不仅仅是开放的、无限的,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中介的整体性,是主、客体统一的整体性。相比之下,福柯就反对抽象的理性整体性,而承认和注重具体的理性整体性。有些人只注重从所谓的历史与结构的辨证关系上分析论证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解构理论,而不从实践对象化和内化的基本点去分析结构的整体性和历史性,造成的理论结果是,虽然自称高举实践哲学的旗帜,但实际上仍然落入意识哲学的旋涡而不能自知、无法自拔。
二、反对写作的“在场形而上学”
所谓写作“在场形而上学”是与 “语音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对应的。因为既然根据西方传统思想,语音直接体现了事物和自我的当下存在,而写作是一种“无声的行为”,表现为事物和行动主体的不在场,那么,语音在表现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就优先和优越于写作。
首先,他强调写作是对事物的意义的建构和揭示,是人的生命的价值的一部分,写作是人的一种自由活动,是一种“绝对的说的自由”,一种“视界”的自由。他说,写作之所以是开启式的,是因为“它有某种绝对的说的自由,某种使已在的东西以符号显现的自由,一种承认世界与历史乃是惟一视界的回答之自由”。*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第19页。而且,虽然它一旦写出来,书写的主体就被抹去了,但是,书写创造了意义并把它固定下来,使意义像生命一样具有活力。它存在于经验的有限性之中,却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生命活力;它唤醒言语和意志,达到“那个既不在场又不直接对我发生作用的存在”。德里达称铭写即书写具有“诗的力量”,因为它能“从符号的沉睡中唤起语言”,“重新唤醒了意志的意愿之意:自由”;书写,把意义从感觉的自然约定中解放出来,并且书写“创造意义并把它存录下来”。因此,在德里达看来,书写不是意义的简单记录,而是意义的建构过程,是“纯历史性、纯传统性之源”。*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第19-20页。
其次,德里达认为,与声音和结构相反,文字恰恰表现为不在场,它是一个非理性的想象和体验的世界;而不在场作为对在场的补充,最终成为在场的一部分。在德里达看来,写作作为一种“铭写”,是人的活动的一种“踪迹”;既然是踪迹,就可以被抹去,因而不论是作为事物本身,还是作为自我的主体在文字中的“在场”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写作不仅是一种行为,而且更是一种体验;写作留下一种踪迹,这种踪迹免除了“原初的铭写”和作者的在场。德里达认为,这种“文字踪迹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思考在场、起源、死亡、生命、生存之类的东西,因为既然是踪迹,它就通过指涉另一个在场而分隔自己,使自己成为不是完整在场的东西。
德里达还以梦和象形文字作为隐喻来强调文字的多义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种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是不能被符号的本质所规定和含括的。他认为,象形文字的特点就是“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汇集了梦中符号的多样模式与功能”。 在其中,“任何符号——无论是否词语性的——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被使用,在不为其‘本质’所规定并产生于差异之游戏的不同功能和形状中被使用。”*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张宁译,第396页。他援引弗洛伊德的话解释说,象形文字和梦之所以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是因为象形文字存在一些不是为了被解释和阅读的东西,是一些意义不确定的东西,而梦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多义性与象形文字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在性质上是极其相近的。*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张宁译,第397页。
德里达说,写作文本无确定主体性。因为文字的主体常常是被抹去的,它不是一种实体、一种“僵硬的不变实体”,即具有“古典主体的那种确切的单纯性”,而是一种意义或功能,很难寻找出它的“第一作者”。他认为,抹去当下在场,也就是抹去了作者的特质和名字,抹去文字中的这种孤立、绝对的主体。因为在他看来,传统思想的主体概念是一个实体概念,这是产生自我在场概念的根本原因。文字作为一种印迹,是写作成为一种主体的死亡和保留相结合的过程。在德里达看来,文字作为一种印迹的观点对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印迹摆脱了传统理性哲学即逻各斯中心主义中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论,“并在‘虚无’的基础上使二元论变得可能”*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张宁译,第413-414页。。
德里达还通过对“原始文字”的分析,批判了“写作的在场的形而上学”思想。首先,他认为,“原始文字”既非一个经验的对象,也非一个科学的对象,因为它不是一个确定的客观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历史”的概念;在德里达看来,通俗文字不同于原始文字,原始文字在不断的书写过程中,通过替代和复制而形成通俗文字;(通俗)文字是对“活生生的言语”的否定和超越。他说,通俗文字只有通过原始文字的退隐,通过通俗文字对原始文字的替代,才能近似地把二者等同起来,因为二者之间在现实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某种“最难以消除”的差异和对立,活生生的言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对产生二者的差异和对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抹平这种差异和对立,就意味着对活生生的言语的否定和破坏。*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80页。再次,德里达强调在原始文字中的“非文字形式和实体”的作用: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意义本身“构成将内容和表达式联系起来的符号——功能运动”。因为原始文字及其延异运动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原始综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作为其他部分的基础和整个语言系统的前提条件,也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东西存在于这个语言领域中,因为它在其中没有“现实的领域”和“确定的场所”。*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85页。所以他指出,对概念和原始文字的涂改及其痕迹,是否定“在场形而上学”的有力证明。另外,德里达借助于安托南·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理论,肯定了尼采的艺术的“酒神精神说”,否定西方传统戏剧乃至艺术中那种“再现”和“模仿说”。而且在德里达看来,这种再现和模仿说是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艺术中的生动表现。
哲学的虚无相对于具体实在物的意识和精神,而哲学的存在有具体的存在者和作为整体或本质的一般存在。在存在的在场与虚无的关系问题上,欧洲传统理性哲学始终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它强调存在的意义在于当下存在(事物本身的存在和作为行动主体的自我的存在),如前所述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思想家们又强调存在与虚无的一致性或同一性,强调思想的虚无相对于具体实在物的意义的优越性和优先性,如黑格尔强调虚无是其思辩辩证法的逻辑起点,萨特把存在和虚无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等等。在笔者看来,这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恰恰暴露了欧洲传统理性哲学的二重性的辩证结构和性质。坚持存在的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如海德格尔所言,表明了其客观主义的思想倾向;而强调存在与虚无观点体现了其哲学反思、思辩的特征,因为虚无即思想就意味着对具体存在物的否定和超越,而否定和超越是哲学及其辩证法的本质所在。另外,德里达把虚无和在场截然分割开来:虚无是纯粹的虚无,在场是纯粹的在场,写作是纯粹的虚无,语音是纯粹的在场。而在实践哲学看来,任何现实存在的东西都是虚无和在场的对立统一体,因为它们都是实践建构的东西,同时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的东西。具体说,文字一方面表现为所指事物和文字创造者、使用者的不直接在场,但是另一方面,文字又是人的活动,特别是集体无意识活动的创造物,是渗透了人的精神和主体性的文化产物,因此它又是一种在场,尽管是一种隐蔽的间接的在场。
三、反对写作和文字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和基础主义
写作和文字结构中的二元对立是指,在传统理性哲学看来,它们自身结构中所包含的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能指和所指等等二元因素,是一种绝对对立、互不联结和影响的实体。而所谓理性基础主义则认为,在上述二元因素的关系结构中,理性、意识和能指是优越于非理性、无意识和所指的东西,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础。
德里达首先指出,这些二元因素不是客观实在的不变的实体,而是相互建构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关系。
在德里达看来,言说之于人也体现了人的生命的本质和活力。人与动物,或“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之一,是“扫视与言说的区别”。扫视只是一种自然的外在性和空间性的关系,而外在性是死气沉沉的东西,意味着死亡;兽性是一种“僵死的自然(静止的生命)”,是与死亡没有关系的东西,是“生命无精打采的面孔”。相反,言语是超越自然的外在性和空间性的东西,是与死亡有着本质的关系的东西,因此它是活生生的、内在的东西。在此,人性和兽性作为一般的在场而发生分裂。*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284-285页。而且,生命的活力来源于差异的力量,来源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化运动即延异,“延异构成了生命的本质”。但是,这种生命的延异不是一种在场,不是一种实体,因而是不可还原的,因为“心灵生活既非意义的透明又非力量的不透明,而是那种在力量较量中出现的差异。”*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张宁译,第365页。
其次,德里达通过分析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思想的矛盾性,批判了其理性主义的还原论。他指出,所谓“弗洛伊德式的裂口”即是还原论与非还原论思想的矛盾性:梦之于言语的不可还原性和“梦的书写”之于人的无意识的还原性。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既承认梦对于言语的不可还原性,同时又把梦还原为人的无意识:弗洛伊德反对将“梦的位移”还原为言语和象形文字,但是他又把“心灵书写”即梦变成一种原初性的生产,这种向着“初级性书写”的“逆退”无疑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它之所以是一种不合理的、错误的思维方式,就在于:在个体或群体的“心灵书写”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被编码了的因素(包括词汇和句法等),因此,某种纯粹个体习语是不可还原的,“做梦者发明其自己的语法”,尽管他也使用现存的通用的语法,但做梦者的独特的语法是不能还原为现存的通用的语法的。*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张宁译,第378页。进一步的原因是,在梦中的意符与意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其潜意识即并不确定的表现意符,而是自己生产自己,形成自己的意义的多样性和模糊性。在梦中,符码系统是不在场的,意符与意指间存在着差异,潜意识经验并不借用其他东西,“而是自己生产它自己的意符,当然并不是创造出它们的机体,而是生成出它们的意义性,那么确切地说,它们就不再是意符了”。*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张宁译,第379页。
另外,德里达承认弗洛伊德强调的潜意识具有非当下在场的性质,因为“潜意识文本已经是纯印迹与差异的编织物”,“潜意识文本”的替补“掏空了作为当下在场而以延缓的方式被重建的东西”。“生动的艺术”不是对所谓在场的简单复制和再现,而是对在场的不断补充和改变,是一种对情感、意志等自我的东西进行创造性的再建构。卢梭承认模仿是人“脱离兽性的过程”,但他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复制,是对在场的“替补”而不是补充,因为它对被模仿者不增加什么,不危及“被描述者的完整性”。所以,德里达认为卢梭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最后,德里达通过对勒维纳斯的伦理学思想的分析,强调他人作为“他者”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在勒维纳斯的伦理学思想中,他人不同于一般的他者,而是一个具有独特品质和个性特点的完整的、不可替代和类型化的人。德里达认为,勒维纳斯伦理学中的他人和“无限的差异”的思想体现的是一种伦理学的他者的无限性和对他人的非暴力关系,是打开“超验的空间”并解放形而上学的一种努力。*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第135-136页。对勒维纳斯来说,这种思想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及其伦理学的一种超越,因为它肯定作为绝对和无限性的他者(他人)在伦理观念和伦理行为中的重要性,是对传统伦理学的先验本质论的否定,因为先验的伦理本质并不包含着这种绝对和无限性的他者,而勒维纳斯的伦理学恰恰承认他者对伦理观念和伦理行为的本质的决定作用,所以,他者是一种“逃脱了所有逻辑学、存有论和现象学”的伦理范畴。*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第141-142页。德里达指出,在伦理学中,没有他人的在场就没有文字和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延异”和“痕迹”等,当然,也就没有伦理学——在言语中辨认文字,即辨认言语的分延和缺席,就是开始思考这种诱惑。原始文字是道德的起源,也是不道德的起源。它是伦理学的非伦理开端,是一种激烈的开端。*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203页。德里达认为,在伦理学中,想象、体验、欲望等非理性的东西是相对于理性结构的差异的东西存在的,正是这些非理性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相互作用和渗透,从而构成了现实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德里达把想象、能力与欲望的差别的起源确定为分延,即确定为在场或快乐的分延。*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268页。
可以看出,德里达对“写作和文字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和理性基础主义”的解构,除了在本体论揭示其二元对立的实体实际上是人活动建构的产物因而是可变的二元因素外,在方法论上主要是通过“延异”、“痕迹”、“隐喻”等这些解构的策略进行。在这里,说德里达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说后现代具有“意识的虚构性”、“语言的隐喻性”和“叙述的话语性”的信念,则是不十分恰当的,因为事实上,德里达所代表的后现代只是强调这三者的因素或倾向,而不是承认这是唯一的因素或倾向。否则的话,那就把后现代理论看作是一元论和本质主义而非多元论和非本质主义了,结果就和传统形而上学混为一谈了。而后现代理论不但强调意识的虚构性,而且也承认意识的反映性(如自然科学的观念);不但强调语言的隐喻性,而且也承认语言的再现性;不但强调叙述的话语性,而且也承认语言的(客观的)陈述性。这也是理解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时所应注意的问题。
[责任编辑:刘春雷]
On Deconstruction of “Logocentrism” of Philology by Derrida
MENG Xian-qing
(InstituteofPhilosoph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Derrida believes that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logocentrism”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rationalism,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deconstructivism, he criticizes and deconstructs the form of logocentrism, 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two opposites and foundationalism.
Derrida; logocentrism; foundationalism; deconstruction; postmodernism
2014-10-21
孟宪清(1963- ),男,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
B
A
1002-3194(2015)03-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