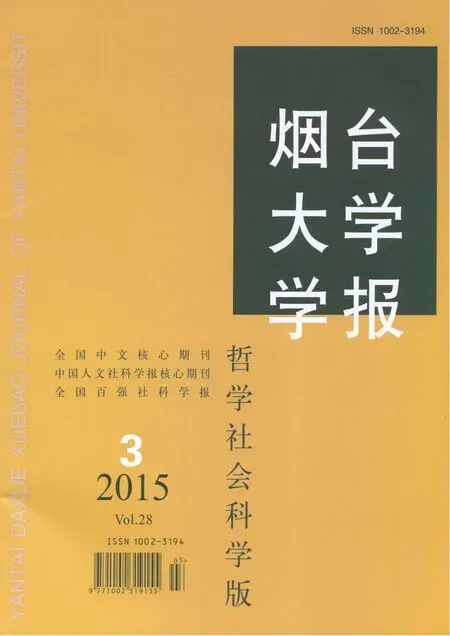“美学信念”与“道德感”——论欧美汉学界对莫言获奖反应的文艺评判标准
王晓平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海外汉学界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反应不一。大多数给予热烈赞扬,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反对意见。这些讨论对于文学批评自身的标准、对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对于文学欣赏标准的确立,都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参照系。而分析这些不同的反应,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文学和文化在世界的地位、甚至包括“中国崛起”本身在世界的形象和地位,进而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不同于主流媒体上褒扬观点的介绍,本文侧重于探索那些不为报道注意的批评意见中的得失。首先分析批评意见中常出现的要求文学作品需要具有“美学信念”和“道德感”,认为其中有一种非历史性的本质论倾向;进而讨论一些意见中体现出的文学写作和政治倾向的复杂关系;最后进一步探讨莫言获奖的意义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目前面临的问题。
一、“美学信念”与“道德感”:何为文学性的评判标准
赞誉之外,对于莫言获奖的质疑从一开始就不绝于耳。这之中最有学术论证系统性的是资深文学季刊《凯尼恩评论》(The Kenyon Review)上发表的孙笑冬(Anna Sun)的长篇文章《莫言的病态语言》。①参见 Anna Sun,“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The Kenyon Review,Fall 2012.这篇文章试图阐述莫言的小说在艺术上的弊病,以及它为什么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孙女士现任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的助理教授,社会学与亚洲研究的专业之外,也是短篇小说作家。她并没有对莫言的某部具体作品进行描述或阐释,但认为莫言作品的语言充满了烦乱,是各种不同语源的大杂烩:翻开莫言的任何一部小说,每一页的语言都“混杂着农村方言、老一套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文学上的矫揉造作。它是破碎的、世俗的、可怕的,以及矫饰的;它令人震惊地平庸。莫言的语言重复、老旧、粗劣,最主要的是没有美学价值。”她认为,莫言的语言脱离了中国文学过往的数千年历史,不复优雅、复杂与丰富,而是一种染病的、“重复啰嗦”和“可预见”的现代汉语。而病源在于长期盛行的工农兵的政治语言。当代作家之中,也有许多人或努力重建与汉语传统的联系,但他们多不为西方世界所熟知。她的要求是“对作家的最高诉求是,不事道德说教而拥有道德力量,并以得自其道德承诺的美学感受来从事写作。莫言及其他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同代作家,已尽力来实现这种诉求。”显然她认为,至少莫言还做得不够。①罗福林指出,“(孙笑东)并没有提出哪位中国作家可以取代莫言,更值得被诺贝尔奖考虑,到文章最后,她不仅质疑莫言的获奖资格,而且似乎觉得这个奖根本就不应该颁给中国作家。”参见罗福林:《莫言的批评者们错在何处》,《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12月17日。孙女士最后说,要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作家必须始终沉浸于更为纯净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溪涧,这是一条长河,即使遭逢最荒芜的环境,也从未断流。”
针对孙所说1949年后对传统的拒斥导致莫言语言的衰亡的论断,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教授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做了有力的反驳:“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拒斥早在1949年前的几十年里就开始了。反偶像在过去两千年来也一直是中国文学和文化里重要的、如果不总是主要的潮流。”②这是金介甫在2012年12月30日在MCLC邮件群里发的邮件里的话。此外,如何定义“文学语言”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概念本身被非常不严谨地运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在《纽约时报》上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莫言的批评者们错在何处》,对莫言的一些批评者做了集中回应。其中也对孙笑东批评莫言作品缺乏道德观念做了详细回答:
对一个21世纪的作家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很奇怪的。一个世纪乃至更长时期之前的英语作家无疑可以通过单一的道德或文化观念照亮自己的世界。然而其后世界历史乃至世界文学逐渐悖离了狄更斯们的那种必然性,这正是工业革命兴起,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道德基础崩塌所带来的后果。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这样的先锋创作技巧思潮的崛起(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等作家)是在“一战”之后,这些技巧被作家们用来书写历史创伤;而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等作家则用里程碑式的荒诞主义来对抗官僚主义与异化的幽灵。③罗福林:《莫言的批评者们错在何处》,《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12月17日。
而针对孙笑冬判定莫言的语言是病态的“割裂说”,罗福林的回答是:
她对那种传统的阐释只局限在其极度抒情的一面(《诗经》、李白、苏轼等诗人、明朝汤显祖浪漫主义风格的杂剧《牡丹亭》以及清朝曹雪芹关于爱情与礼仪的杰作《红楼梦》);但却没有提及司马迁的史诗性巨著《史记》,以及《水浒传》、《西游记》等冒险、大胆而幽默的小说。……但中国文学史上存在抒情和史诗这两大潮流却是被公认的。孙刻意无视了许多中国文学中广为人知的巨著,而它们显然是莫言作品中想象力与风格的源头之一。莫言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成人,但当他成为作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无疑可以接触到中国文学的抒情和史诗两大传统,也能读到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的翻译,更不用说狄更斯和哈代。①罗福林:《莫言的批评者们错在何处》,《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12月17日。
然而罗福林认为,孙笑东论断的最大问题是否认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创造力。她认为新中国对中国语言的摧毁是难以挽回的,渗透到了它的美学术语、概念与基本观点当中:“孙笑冬认为这种摧毁显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刻一举发生的。事实上,自从‘一战’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与文化上打破了旧有的偶像,一度出现繁荣美妙的盛况……以孙的标准而言,就连鲁迅这样的文化偶像,乃至茅盾和吴组缃等著名作家也受到这种病态语言影响。”罗福林还针锋相对地提出“孙笑冬把莫言的病态语言归结为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影响,这个结论非常讽刺——‘毛文体’(MaoSpeak)这一概念正是由莫言这一代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是他们这一代新文学作家所抨击的对象。总之,莫言的小说……把视角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中,而不仅仅局限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内。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小说才显示出多种多样的语言来源。”
孙笑东对于莫言文学语言的衡量,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理念预设上,这一点在她所谓的“美学信念”上见出。她提出虽然莫言小说中的现实或许确为诺贝尔委员会所言的“幻觉现实”,而人们也常拿他与狄更斯、哈代和福克纳等人进行比较,但莫言的语言缺乏上述作家共有的某种重要的东西:美学信念(aesthetic conviction)。孙女士说:“这些作家的审美力量实系火把,为我们照亮黑暗与痛苦的人性真相。而莫言的作品并没有通过娴熟克制的技巧为读者照亮什么,而是充满迷失和沮丧,这都是因为他缺乏前后连贯的美学思想。在莫言的幻觉世界里充满混沌的现实,但却没有光芒照耀其上。”要想有力量去呈现近世的动荡,必须“用一种可以烛照人心的、高尚的审美确证,去书写我们共有的人类境况之悲与美。”而莫言是在“破碎的、世俗的、可怕的”人间中讲故事,欠缺伟大的视野。
那么什么是这种“美学信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从与“审美力量”等同的“照亮黑暗与痛苦的人性真相”的“火把”说起。有意思的是,这种“火把”的意象和原在波士顿大学、如今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的《文学是否还是一盏明亮的灯?》异曲同工:
虽然莫言这一代的小说家们……在成功地解构了这些主流意识形态之后,他们的小说是否除了虚无就是虚无,是否还能够提供了一些关于心灵救援的力量?当文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微弱时,有的作家认定文学应该“回避崇高”,不必再谈“教育”、“拯救”、“责任感”等;也有些作家认为,文学能“自娱”、“自乐”、“自救”即可,完全不必奢谈救人、救国、救治灵魂。这样,文学是否还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便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用意象表述,便是文学是否还可以成为照亮社会的一盏灯?②刘剑梅:《文学是否还是一盏明亮的灯?》,FTChinese(12/11/12),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947。
这样的批评似有道理,但这种对于“文学的救赎意义”的要求是一种不自觉的非历史主义的宣导。我们无法得知卡夫卡式的黑色冷酷(而非幽默)、詹姆斯·乔伊斯的难解的《尤利西斯》是否给人这种“救赎”的力量,这种“救赎”的要求实际上来自现代中国的传统,只不过由现代中国民族危亡前景下的“涕泪交零”的“救人、救国”变成“救治灵魂”,由他们曾经否定的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其实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要求)变成要求是“照亮社会的一盏灯”(这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下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的要求)。而要求文学只能有一种功能,即只应该有一种写作形式,舍此都是不合法的、至少是不高尚的。这些学者没有自省的是,这种反历史、非历史化的态度,与他们批判过的卢卡奇要求资本主义社会作家只能有一种写作形式,而如卡夫卡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都是堕落的、颓废的写作形式的那种过左的、非历史性的批评异曲同工。
这种姿态同时是精英主义的,这体现在刘剑梅对于鲁迅选择的评价:
作为一个启蒙者,鲁迅的姿态是高于大众的,正因为这一“高”姿态,他才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才在《热风》中明确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
这种“救赎情怀”要求“姿态”高于大众,其实是要求延续作家作为社会性领导者的角色。但自从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非政治化后,这种角色已经无可避免地失落。这种非历史化的倾向还表现在对于文学功能转向的去政治性的分析上:“在上世纪下半叶,文学的社会功能被畸形膨胀了。文学岂止可以救救孩子,而且可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作家可以充当‘灵魂工程师’,可以当‘号角’、‘旗帜’、‘阶级斗争晴雨表’。正因为过分夸大、过分膨胀,所以才出现相反的思潮,认定文学的救赎功能纯属妄念,‘救救孩子’的呐喊纯属‘空喊’,文学的救治意义被悬搁了。比如,许多先锋小说更关心的是语言和技巧的更新,而不再关心文学的救赎意义。”社会转向导致的文学功能的变异被认为是“过分夸大、过分膨胀”的后果。其实,先锋小说的去政治性的“语言和技巧的更新”背后恰恰蕴含丰富的政治性。①王晓平:《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历史经验和形式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但这种要求充当领袖与启蒙者地位的呼吁、以及孙笑东要求“美学信念”的“道德感”,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文学与政治、文艺创作者与他们所信奉的政治观念之间,存在不可割舍的联系。
二、写作与权力:奖赏背后的文化政治
其实,莫言获奖的效应无论如何不能不被视为有关文化政治。罗福林直白地说:“诺贝尔文学奖经常授予那些强烈反对政治压迫的作家。如果一个获奖作家来自那些最近卷入政治斗争的国家、受到独裁统治压迫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所受到的关注往往会和他的名声不成正比。就算委员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来自政局稳定、经济发达国家的作家,也往往倾向于授予那些代表着全新的、受压迫或是被边缘化声音的作家,而不是单纯地从文学价值角度出发。因此很多观察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政治化’的。该奖很少授予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并和当局保持良好关系的作家;除了莫言,我想只有1965年获奖的前苏联小说家米哈依·肖霍洛夫(Mikhail Sholokhov)是个例外。”他还耐人寻味地说“如果这个奖是文学奖,那么,莫言是个拥有众多拥趸的高产作家,这样不就够了吗?文学作品本身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吗?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讲中也表示自己希望由作品来说话。”而与此期待相反的现象表明了另类事实的存在。
其实,尽管莫言自己希望强调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就是文学标准,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观念影响,但包括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在内的人都认为,“尤其是在诺贝尔文学奖早期,政治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易见的。比如说,‘人类的进步’、‘最伟大的贡献’这类授奖辞体现了诺奖最主要的标准,这个标准也是明显的政治表达。有时候,瑞典文学院即便不愿意这么想,也还是会受到政治变动影响,比如丘吉尔获奖就与冷战有关。”②石剑峰:《库切与莫言谈诺奖的政治标准》,《东方早报》2013年4月3日。而且,获奖者“必须是和诺贝尔本人世界观相容的作家。”这个世界观就是怀抱“理想主义”。他说“皇家学院努力把即便并非理想主义者的作家也要在授奖词中将他们划入理想主义者。”他举了三个例子:“2004年获奖的耶利内克,2001年的奈保尔和1969年的贝克特……皇家学院下决心从他们作品中看到光明的一面,其实他们每部作品都是相当黑暗。”③石剑峰:《库切与莫言谈诺奖的政治标准》,《东方早报》2013年4月3日。
不管莫言本人是否抱有“理想主义”,早在10月11日获奖当天,《纽约时报》的报道第一句就指出他并不被外界视为“异议作家”。但文章随之仍强调莫言的作品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批评方面,被广泛认为是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的(subversive)。对这样的报道,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的意大利社会学家Sabrina Merolla立刻表达了不满,声明人们不能因为官方是否喜欢莫言而忽视作家自身的价值,或者因为人们通常喜欢挑战当权者的立场而把他看作属于此类;虽然一个作家应该对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丑陋表达批评和愤怒,但这种表达不应该只有一种形式。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邓腾克(Kirk Denton)则指出这种将作家与政府关系作为评判标准的做法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还原论(reductionism),而莫言作品在处理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是新鲜的、具有想象力的,大胆、甚至深具挑战性的;他的文章是叙述实验、故事讲述、社会政治参与的良好结合。①两位学者的反应,以及下列未注明出处的学者言论,均出自MCLC电子邮件群里的讨论。
第二天,《纽约时报》再次刊出长篇评论,这次是名叫塔罗(Didi Kirsten Tatlow)的记者所写的名为“作家、国家和诺贝尔奖”的通讯。她描述了2009年莫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配合官方的表现,对莫言响应官方,在一些“异见者”获奖时与其他代表团成员集体退出现场提出质疑:“(这一)事件提出了关于写作和权力(关系)的关键问题,甚至几乎是哲学性的话题:在一个管理严格的一党统治国家里,能真正自由地表达吗?”她还引用了高行健对莫言获奖的评论。后者认为,在严格审查的条件下,作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一个作家需要“完全的”自由以创作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在官方和文学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有的话只能是官方文学,而这是可笑的。因此文学不能被官方组织认可。文章结尾最后问道:“问题是:伟大的、持久的文学能从(中国)那儿来吗?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可以。你们认为呢?”
这一文章在美国最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团体的邮件群MCLC-List里发出,就立刻引起了美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强烈反应。现任南加州大学东亚系主任的唐小兵教授尤其愤怒,他认为这一批评实际上是对诺贝尔委员会的攻击,他模仿作者的语气讽刺道:“你们怎么能把这样的荣誉授予仍然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作家?一个不是坐牢或被禁的,而是拥有声望和官方地位的中国作家?天哪,你们怎么不懂得,问题的核心与他作为作家写些什么毫无关系,而是一切和他作为中国作家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相关,甚至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目的相关。”唐小兵的话指出了这篇通讯的脱离文学的政治偏向性。他还指出:这些批评者实质上是“从根本上不能接受有一个多彩的、创造性的、有自身活力的主流中国文学,而这是当代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许多机制的活生生的复杂系统。因为他们根本上不能接受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他们拒绝相信那儿的许多文化实践和体制在结构上发挥的功能是和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相对应的。他们仍然把中国看作一个异端、最终是个具有威胁性的秩序,因此他们热切地寻找和支持任何他们喜欢的迹象,将他们不喜欢或不懂的任何对象看成是怪异和无趣的。”他愤怒地抗议道“当你们不喜欢一个作家的政治或政治立场时,你们用纯文学或永恒文学的修辞来贬低他;当你赞同一个作家的政治时,你们表扬他勇敢、与我们时代相关。这个双重语言源自在塔罗全心信奉的自由主义视野里内在的盲点。”华盛顿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教授柏右铭教授(Yomi Breaster)也认同唐小兵的观点:“塔罗在《纽约时报》上对莫言的攻击在许多方面是令人诧异的,如果不说令人反胃的话”;虽然“创作确实总是具有政治性,但一个作家无论如何不必回答(有关)他的政治(的问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教授贺麦晓(Michel Hockx)则认为,塔罗的文章是一个“长篇攻击性演说”(tirade);而对于她所提出的问题只有一个回答:“是的,伟大、永恒的文学可以从那里发生”。他的理由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永恒的文学”曾经在“压迫性的环境”中产生。他举的例子是莎士比亚,他写作的时候英国的审查制度很严。而更切题的回答则是,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莫言和他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众多读者所欣赏。他可能是活着的中国作家里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人,而关于他的西方研究论文也非常之多。因此,值得从他的作品中重建文学美学的评判标准。Wooster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汝杰教授发出的回应邮件则“以毒攻毒”:“不管回答是对还是错,问题本身对我来说让人诧异。我们难道会因为雅典民主只允许成年男性公民有权选举,而后者只占希腊城邦百分二十的人口,并排除了奴隶、自由民(被释放的奴隶)和女性就质疑苏格拉底、柏拉图、欧里庇得斯(希腊的悲剧诗人)和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质量吗?我们难道因为波、爱默生和梭罗这些早期美国作家因为属于一个特殊阶层,并恰巧生活在一个土著美国人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被赶走、奴隶贸易是合法的时代而视他们的作品是不伟大和不永久的吗?……难道我们会因为圣经包含有反同性恋的段落而把他们从书架拿下吗?”王汝杰有理有据的反驳显然使得批评者毫无招架之力。
俄克拉荷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Jonathan Stalling也在当天的回应邮件里指出,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性的劳动,而写作耸动性的作品、将作家当作国际政治棋局上简单的棋子,则会让致力于这种创造性劳动的人泄气。而罗福林则在题为《政治化莫言的反讽》的邮件中提出,“莫言的批评家期待他以文学和影响力来做出正确的政治上进步的姿态,而(他们反对的)毛泽东同样也如此要求作家的政治服从和他们服务于国族政治良心的责任。但莫言和大多数中国作家已经从这个负担中解放出来。今天中国的作家获得他们应有的国际承认,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完全奉献给文学艺术。”
然而,出于不同的文学创作观、价值观,但更重要的是历史观和政治观念的不同导致贬抑和诋毁莫言的学者和作家也大有人在。比如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马尼亚裔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在接受瑞典《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采访时表示,莫言获诺奖对她来说不啻为一种“灾难”,当她得知评委会的这一决定时“差点没哭出来”。柏右铭指出,米勒对政治采取了粗鲁的态度,对任何与共产主义相关联的东西一概拒绝,而这是在罗马尼亚移民中常见的现象。而米勒也承认她对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不感兴趣:“没有任何美学能正当化莫言的选择,他甚至无法说出他想要什么。”
文学和国家以及广义上的政治的关系显然在这里被抬上台面。对于一些人认为的文学与国家(官方)应该毫不相干而应该“完全彻底独立”的论调,邮件群转载的一篇由住在香港的作家和翻译家Nick Frisch在《大西洋报》上撰写的评论里,有一段精彩的关于作家和国家(官方)关系的说明:“不要说唐代大文豪李白和杜甫,或者历史学家司马迁,兼为画家、诗人和书法家的苏东坡和欧阳修,11世纪致力于公共利益的改革者的包拯,或者公元前二世纪的著名反腐斗士屈原。更不用说流浪哲学家孔子”,他们的文学都“不朽而且永恒”。这显示“在中国传统里,文学并不是一个在国家之外的领域存在的。”几千年来的科举考试“更进一步建立了在小部分的文学精英、政府服务部门和儒家正统政治思想经典之间的关联。”①Nick Frisch,“Mo Yan:Frenemy of the State,”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10/mo-yan-frenemy-of-the-state/264233/这种基于历史性的解释使得批评者哑口无言。
实际上,这种批评呈现出对于文学(性)、对于文学和国家以及官方的关系,我们应该秉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西方一直强调的作家应该具有“独立人格”,实际上只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程度加深,西方知识分子不认同当局,但又无力对社会施加影响,对于席卷一切的商业化环境又无可奈何,因此采取了“不合作”的埋头于书斋的行动。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几千年来的传统历来是要求文人身怀家国情怀,即使不能入仕经世济民,也要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牵挂于心。而近代以来中国特有的苦难也加深而非弱化了这一传统。当然,随着八十年代以来去政治化浪潮,认为有一种“纯文学”的思想也曾一度流行,要求文学脱离(狭义的)政治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中国社会还远未达到西方的异化程度。即使是躲避国家政治的知识分子也不会与社会完全脱离。实际上,这些西方学者要求的“独立”毋宁说是反叛,要求莫言持有鲜明的异见者立场。①比如一个中国文化翻译家Martin Winter针对罗福林的评论说到:“作为民族的政治良心”不同于“政治上的服从”,而是相反,因为在中国,由于中国作家的政治顺从,他们不能成为民族的政治良心。
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信念则以高尚的言辞本质化文学的功用,实质上是再度要求文学的政治性干预。一个海外媒体工作者连清川在《我为什么不为莫言获奖感到自豪》中说:“文学乃是一种灵魂拯救的事业,尤其是高尚的文学……对于文学的近乎常识的判断是:它必须具有这个社会基本的道德勇气……我们之所以(对莫言获奖感到)失望与无奈,恰恰在于莫言这个具体的文学从业者,这个小说家,他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个民族得以珍视与荣宠的精神与灵魂象征……他习惯性地沉默于国脉与民瘼,游离于灾难和压迫,失语于公义和良知。他并不是一个施害者,但是他是一个袖手者,甚或有时候是一个共谋者……莫言和他的文学,并不代表中华这个民族的文学精神和灵魂。这只是一些并不体认中国特有的苦痛与拯救道路的人们的一次他者的名利游戏。”②连清川:《我为什么不为莫言获奖感到自豪》(Why I am not proud that Mo Yan won the[Nobel]prize),《纽约时报》2012年10月17日。王汝杰教授对此反驳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好的作家必须表现被认为是他的民族的精神和良心,(因为)另外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已经警告过人们(这样的不值)。”的确,这样再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运用得颇为精彩。
如上所述,更多学者试图区分文学和政治,将作为艺术家的作家和世俗的本人的日常言行相区分。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把莫言比作海德格尔,宣称作品的美学价值不能和本人的政治观点相联。有意思的是,其他一些“自由派”学者在此不可遏制地暴露了其真面目,即要求政治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对记者明确说道:“我不认为可以把文学和政治剥离开来,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学都是人类的生活。在中国,这种政治性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甚。一个作家假装不具有政治性,这只是一种‘政治性’的假装。莫言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家,但他不是我所喜欢的。我认为他很好地意识到了中国的问题,但是却用玩笑和幻想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并不有助于读者们正确地看待它们。”③赵妍、赖宇航:《外媒热情关注莫言获奖》,《时代周报》2012年10月18日。
林培瑞还在《纽约书评》发表了《这个作者有资格拿诺贝尔奖吗?》(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的长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④Perry Link,“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Dec.6,2012.和孙笑东一样,他也认为莫言的语言是病态的,而且上升到一定高度:“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作家的创作怎样乃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体制的影响,以及他或她如何对此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既微妙又关键,莫言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例子。”他认为这种影响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学上的痛苦,甚至有些作家需要同汉语彻底一刀两断才能摆脱”。为此旅美中国作家“哈金走了不寻常的一步,不仅离开了中国,而且离开了汉语;他只以英文写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潜意识的影响也不能干扰他的表达。”罗福林对此在他的回应文章《莫言的批评者们错在何处》中回应道,“我还无法确定这就是哈金以英文写作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作家在面对母语中意识形态的包袱时竟会那么脆弱,以至于不能以母语创作出健康的文学语言,这实在是太可悲了。”
林培瑞认为一些敏感的历史时刻,比如大跃进之后的饥荒和文革时期导致了意识和语言的扭曲,这主要表现在这些时刻“用一种犬儒主义和深刻的不信任毒化了民族精神,直到今天都没能完全恢复”。如莫言这样的作家反抗压抑、大声发言的天性被环境所破坏,变成一种犬儒主义的表达,把这些历史悲剧用幽默的方式平庸化。针对此,罗福林的回答令人深思:
历史创伤必须被纪录和铭记,但是文学和艺术,特别是自从20世纪的那些创伤之后的文学艺术,并不是简单地记录人们的经历而已。和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一样,莫言主要为中国读者写作,而不是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历史上的悲剧。莫言的目标读者知道大跃进导致了灾难性的大饥荒,对历史创伤的任何艺术化处理都会有自己的变化和扭曲:难道林的意思是暗示莫言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在洗白历史,或者向共产党献媚吗?莫言之所以选择书写那些年代,正是因为它们是创伤的记忆,而不是因为它们是欢乐的;基本上,他那一代的所有作家都在书写这个主题。林对这个问题的阐释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流于表面的理解,好像他希望文学创作在处理历史悲剧主题时应该采取忠实纪录的形式,还要附上统计数字、图表和大量叙事者的哀悼。①罗福林:《莫言的批评者们错在何处》,《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12月17日。
虽然罗福林的观点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观点,并举出那些自由主义作家的例子为证:“20世纪一些最重要、最有趣的中国作家并不认为文学要为民族觉醒这个目的而服务(周作人、梁实秋、张爱玲)”,但他也指出“一切文学都有政治性,但每个作家都以不同方式体现政治”:
所有文学都有政治意义。没有任何文学成就是建立在纯粹美学价值上的。我无法想象一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小说称得上艺术杰作。莫言充满人性与良心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紧张局面,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犯的悲剧性错误,虽然他没采取让自己被流放或进监狱的写法。我不同意林培瑞和许多莫言批评者们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他们希望要么一切,要么全无。②罗福林:《莫言的批评者们错在何处》,《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12月17日。
同理,瑞典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期刊主编邓腾克(Kirk Denton)也表示,“在西方有些人批评莫言并没有坦率地说出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但这也反映出了西方大众传媒狭隘的政治偏见。”
三、“活力、动力和创造力”与“混乱、愚昧、充满暴力和极左政治”
回到莫言作品本身再次省察其内容与呈现的中国社会给予外界的观感。美国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迪克曼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与中国文学教授何谷理(Robert E.Hegel)注意到莫言作品对中国形象的影响,认为莫言的作品题材多元,同一部作品中讲述的议题也不只一样,而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似乎重新定义了1980和1990年代里正在崛起的中国力量。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则认为在莫言小说里,“中国语言所负载的巨量的信息和情感交流,包括这个过程中的损耗、污染,显示出当代中国语言的惊人的包容能力、吸收能力、夸张变形能力,戏仿或‘恶搞’能力,这种史诗性的综合包含着巨大的张力。莫言的小说就像是这种语言活力的‘原浆’,其浓度、烈度和质地高于从其它管道(比如互联网)所接触到的新奇语言现象,因为它们被组织进一个系统。这种震撼力对西方读者的影响不可低估。他们会感觉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创造性,莫言的作品再现或者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内在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③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4页。
的确,莫言获奖,对于提高中国文学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不少帮助。德国现年53岁的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德国巴赫曼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伊利斯·拉迪施(Iris Radisch)在《时代周报》上发表了题为《这是世界文学!》的评论文章,“那些原始朴拙、绚烂多彩、惊心动魄的作品完全打破了西方既有的区分现代与前现代、新潮与落伍、精英与大众的文学观念。”评论者往往惯于把他与世界文学名家做对比,也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知名度。比如耿德华认为,莫言和卡夫卡的相同点,就是作品都在描绘人类的无情、残酷,不论书写的对象是个人、家庭或国家的不公,并从怪诞情节下彰显出作品的独特魅力。而两人的差异点,则在于卡夫卡的作品更多超越了任何理性或有意义的秩序,而莫言的作品则比较多涉及人类美感与同情的能力。而将莫言的作品与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名作《百年孤独》、他的“幻觉现实主义”和后者的“魔幻现实主义”相提并论也为人熟知。而且莫言在魔幻现实主义再创造的过程中融入的中国民间文化因子最终成就了他自己的“幻觉现实主义”,“必将汇归世界文学的海洋,成为增进跨国交流、拓展人类经验的公共文化资源。”①亚思明:《莫言获诺奖分裂德国文坛》,《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05日。
这些认识对于打破西方中心论当然有一定好处。拉迪施称,莫言小说中的肉体横陈、鲜血淋漓的刺激性场景鲜见于植根于基督教文学传统的西方现代文学范本。此中的文化差异,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经做出过解释:中国小说家没有经历过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礼仪和教养的驯化。读莫言的作品,时常要闭上眼睛、屏住呼吸。许多荒诞滑稽的情节(如《酒国》)、野蛮残暴的画面(如《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并不符合西方人惯常的轻描淡写、冷嘲热讽的阅读口味。此外,“小说中的鬼气森森、远非田园风光的乡村世界。而更令熟悉柏林、巴黎和纽约都市背景的欧洲读者感觉自己仿佛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光着屁股站在中国的红薯地里。”尽管如此,拉迪施还是认为:莫言的小说是卓越而奇特的:“取材于中国民俗文化的写作内容据莫言推测很难受到西方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喜爱。但他错了:莫言百无禁忌的书写将我们带回那段被人遗忘了的,充满惊悚、魔力和无休无止的故事的生命。”她认为“莫言给了西方读者当头一棒,同时令人感到一种不可理喻、不知所措、痛并快乐着的感官折磨和恐惧。”②亚思明:《莫言获诺奖分裂德国文坛》,《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05日。
尽管莫言的作品随着获奖广泛流传值得欢喜,但认为莫言获奖就对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改观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莫大助益,却是过于乐观的想法。首先,虽然这次获奖“毕竟是一个挟显赫传统与世界性威望的文学奖第一次克服西方人种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价值上的偏见而授给了一位在中国生活和写作的中国作家”,③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第xi页。但诺贝尔奖作为西方授予的奖项,它的西方中心思想无法根本免除。美国杜克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刘康就曾谈到:“毫无疑问,莫言的写作手法、思考角度是非常西化的,他受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很大,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尤甚。他的作品写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故事,所透出来的是通过西方话语过滤的普世价值。”④刘康:《从莫言得奖看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联合早报》2012年10月13日。这当然并非全是坏事,比如:“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奖,它的标准就是作品应关心人类命运。而莫言的作品,则恰恰很好地体现出了对文学本身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⑤刘康:《从莫言得奖看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联合早报》2012年10月13日。但另一方面,这表明话语权和标准仍然在西方手里;而且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中国文学的价值和独特性。⑥刘康就此指出:“瑞典的评委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视角仍没有太大变化,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复杂性。比如贾平凹、陈忠实这些立足中国本土的作家,不那么主动地关注西方或世界的文学思潮,一心植根中国广袤的土地,因此不太可能获奖,因为他们‘太中国’。中国的文明有其特殊的东西。中国太复杂了,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虽然林培瑞的言论常有偏颇,但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他的一些话在这点上还是很有道理的:
说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是给他贴“外插花”,很表面,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是的,莫言本人提过以马尔克斯为师,但这也是常规。中国作家,从80年代以来,常常喜欢说拜读过西方某某的作品,深受过谁谁的影响,但这些话得一一地分析,不能全盘接受。中国作家觉得沾点国际的“光”有一定的时髦价值,同时外国人的虚荣心也得到满足……①林培瑞:《答客问——莫言的写作风格及其他》,《纵览中国》2012年12月10日。其实,莫言自己也承认,“我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拉美有拉美的魔幻资源,我们东方有东方的魔幻资源。我使用的是东方自己的魔幻资源。比如说轮回,这些佛教的范畴,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而且变成了老百姓解脱、表达情感的一部分,他们的思想方法。”见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第178页。
其实,从学院表达有关莫言获奖的理由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在这里一定意义上只是一个陪衬,这表明了一个由他者给予合法性命名的尴尬。②其实,有些汉学家指出莫言作品中中国因素是更多的。如林培瑞指出,“莫言说故事的来源更容易在中国传统找到。山东老百姓说书,向来有夸张、虚构、神话的传统,挺好玩的,把这些因素骂为‘迷信’可以,把它比作‘魔幻现实主义’也未尝不可,但毕竟不是外国的东西。中国书面文学传统里头有‘聊斋志异’之类的‘现实主义里头出现不现实的东西’的现象;又比如,莫言喜欢的血腥描写,残酷武打,‘水浒传’很容易找到,‘水浒’也属于山东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用‘聊斋’或‘水浒’来套莫言呢?非要说他是‘魔幻现实主义’反映一种崇洋媚外的态度。不必要……但莫言的超现实与马尔克斯的超现实是不同类型的。马尔克斯更抽象,更概念化;莫言更具体,更个别。马尔克斯让读者怀疑自己的宇宙观的框架;莫言请读者欣赏一些怪现状。”见林培瑞:《答客问——莫言的写作风格及其他》,《纵览中国》2012年12月10日。
其次,不能说诺贝尔奖这次授予莫言就丝毫没有“政治正确性”的考量。尽管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基本上,选莫言得奖的理由非常简单。我们颁发的是文学奖,所以关注的是文学价值。任何政治辐射和影响都无法左右它。”但他坦然地承认,“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文学视为独立于政治之外,或者今年的获奖者不写作政治文学。”他继续解释,“你打开任何一本莫言的小说,就会发现他对于很多中国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的批评。我只能说他其实是一个批判体制的批评家,只不过身处于体制内。”③赵妍、赖宇航:《外媒热情关注莫言获奖》,《时代周报》2012年10月18日。表面上,这是否认政治考量干预文学,实际上不可脱离的最后一句仍然表明“批评体制”是委员会授予文学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正是在这里,我们对于莫言创作本身的问题需要给予正面的审视。莫言作品本身的中国读者并不多,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中国的“主流作家”。为何他的小说不很受普通读者欢迎?这当然和国人的审美趣味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西化的语言和文学想象方式让中国人不觉得十分亲切。在此看来,甚至那些苛刻的批评也不无道理,比如现在旅居纽约的文学评论家李劼发表的《莫言诺奖:吻合西方想象的中国农民文学》以极为苛刻的语言评论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象”,指认它所提供的隐喻“毫不讳言地指向生存的焦虑、物质的匮乏、动物性甚至生物性的挣扎”。由此,他认为:“以屁股为主体的身体器官,既成了莫言小说的主要叙事对象,也成了莫言小说的基本故事内容。这种意象的隐喻特征在于:既没有精神内涵,也了无头脑之于诸如存在、自由、人性、人格之类生命意义的思考。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那种灵魂的挣扎被全然付阙。”这种以他国历史与文化传统来要求莫言作品也要普世性地进行“灵魂的挣扎”无疑带有批评者本人所批评的西方中心主义。但他的下列言论看来具有部分合理性:“莫言获得诺奖,乃是莫言小说那个野蛮、愚昧、落后的中国屁股意象与汉学家心目中的中国主义之间的一拍即合。”④李劼:《莫言诺奖:吻合西方想象的中国农民文学》,《纽约时报》中文版2012年12月8日,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2/08/cc08moyan/。
那么为何莫言小说经常具有这种“屁股意象”?对于莫言的获奖,瑞典皇家学院的理由是莫言用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现实融合起来。而这里的“历史和现实”则是中国过去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学者在分析他的作品时,大多认为它们“充满了‘我’与家族乡里在共产中国大历史中的小故事”,属于“典型的国家寓言”。因此“要理解莫言,便要把他放回到说书人的处境中去看”。他是以“地方传统”来进行“由官方限定,破碎又不完全驯服的庶民想象”①叶荫聪:《说书人还是知识分子?——莫言获奖后的争议》,《明报》2012年12月31日。。这种“受困或依仗于‘地方传统’”对国族历史进行说明的“诠释者”笔下充满中国人“生存的焦虑、物质的匮乏、动物性甚至生物性的挣扎”,如何能对外提高中国的形象和文化软实力?
我并非说莫言叙述民族的苦难不正当。其实,民族的苦难史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就不断被叙述。但为何当时的民族苦难叙述能振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今天的叙述却无法让人有同样心情?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其实,莫言对于历史的认识和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界对历史的流行看法别无二致。但反讽的是,莫言仍然被讥讽为“没有思想”。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德国之声》的访谈中说:“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曾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稍后,他又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重申:“莫言描绘了他的心灵创痛,他描绘了过去的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他笔下的群像画廊令人眼花缭乱,总是那么恢宏霸气的场面。公平起见,我必须承认,他的确有一批读者,但马丁·瓦尔泽称他是现世最伟大的小说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②顾彬:《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年10月12日。针对莫言的叙述方式,顾彬说道:“莫言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所采用的叙事模式早在1911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就已多见,同时也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示。”虽然这种见解十分苛刻,否认了莫言创作语言的独创性,但他认为莫言在现代小说技法上所做的实验性探索极为有限,其社会批判题材也并未超出鲁迅二十年代的窠臼,却也有一定道理。
那么,莫言的问题在哪里?在我看来,莫言创作的问题更多不是他个人才华的问题,而是时代思潮面临的问题。顾彬对于莫言的批评在于他不够具有现代心智(modern mind),而在我看来,是对于历史的认识,由于过去十几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否定中国近现代以来主要历史经验的倾向,导致人们的认识产生了混乱——当下中国文化界不少人(包括莫言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革命史的认识和西方那些苛刻批评他的学者几无差别,这尤其反映在莫言对于土改历史中偏差现象的“暴露性”(往往以变形的非直接方式)书写趋向于流行观点的单向度演绎;③莫言自己承认,“我写的时候是心目中的历史,我想象的历史;依托的当然是历史当中许许多多的真实的细节,但总体上是按历史的轮廓,假如说历史是线条勾成的图案的话,里面的色彩全是我涂上的,我可以涂五彩斑斓的,也可以涂单调的,个人的情感、主观意图来填补、填满了历史的大的空间。”参见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第176页。而对于当代现实的反映而言,他所反映的是“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诸种碎片化现实”,后者“常常栖身于眼花缭乱的暧昧性、过剩、亵渎、‘无意义’的形式中”。诚如张旭东所言,“对于一个缺乏‘社会—历史构架’和‘道德—政治构成’的时代来说”,莫言作品是“一九九○年代中国诸种失了根的、无家的、彷徨的经验、意象、记忆与幽灵的‘象征性落座’”。④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第2-3页。在作品中,他对于人性的演绎,是基于八十年代开始、九十年代后加剧的去政治化的解释,即去除阶级性的“人道主义”。⑤莫言说:“人道主义超越了阶级性。很多东西是大于阶级的,人性是大于阶级这是我们一直不敢承认的”。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第230-231页。在这种视野下,他所力图呈现的“我心目中的历史”,用小说来“填补被过去革命战争文学、革命历史小说所忽略掉的人的情感这部分”就带有一定倾向性。⑥他说:“经济的、政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仅仅是我的人物存在和发展的背景。”见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第215页。这种描写在有利于当下人认同的“文学性”的同时,只是强化了西方读者对现当代中国是“混乱、愚昧、充满暴力和极左政治”的历史,现代中国人生活苟且、肮脏、愚顽的刻板形象。即使是在单纯的文学技巧上,也有一定负面作用。比如,他承认:
我小说里戏谑的东西很多,所谓拉伯雷式的那种狂欢的、广场的东西我特别偏爱。很多动物描写,经常出现狂欢场面大段大段的描写,像它和刁小三月下的那场鏖战,唱着《草帽之歌》。这个细节完全不真实的,七十年代那会日本的电影《人证》里的草帽歌,根本没在中国放,但是猪王就唱着草帽歌。这种我认为很拉伯雷,这是我个人写作的倾向性,说是弱点也可以。①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第227页。有意思的是,尽管莫言对历史的认识与西方批评者并无太大差别,但他仍被顾彬认为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
这也是林培瑞指出的莫言写作语言中“主要的问题是语言粗燥,写得太快,不小心,语病多,比喻先后不配合”。②参见林培瑞:《答客问——莫言的写作风格及其他》,《纵览中国》2012年12月10日。
结 语
对莫言获奖,刘康认为他的作品“呈现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积极融合的努力”。面对“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软实力或普世价值,依然是为西方所掌握的”的局面,他认为“中国特殊论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应该努力化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中国积极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一个成功。”③刘康:《从莫言得奖看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联合早报》2012年10月13日。但这个说法似乎把普世价值的拥有权拱手让给西方,而中国曾经拥有过的主导世界话语权的历史被有意地遗忘了。
针对莫言作为一个作家获得的荣誉,中国文化界普遍认为,和莫言的创作水平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中国作家还有不少,甚至有些作家可能还另有特色。这次获奖最多只表明了西方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文学创作水平的肯定,这可以坚定我们不妄自菲薄的信心,但对于让西方人更为客观、准确地认识现当代中国和中国人,建立正面的中国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则作用不大。中国人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首要的问题是中国人要对自己的历史有辩证、全面的认识,而非一概否定和漫画化。如何去除一度流行的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建立新中国前后三十年的“连续性”,树立文化自信,建立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文化(政治)认同,或许是当前中国的文化界在莫言获奖引起的热潮后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