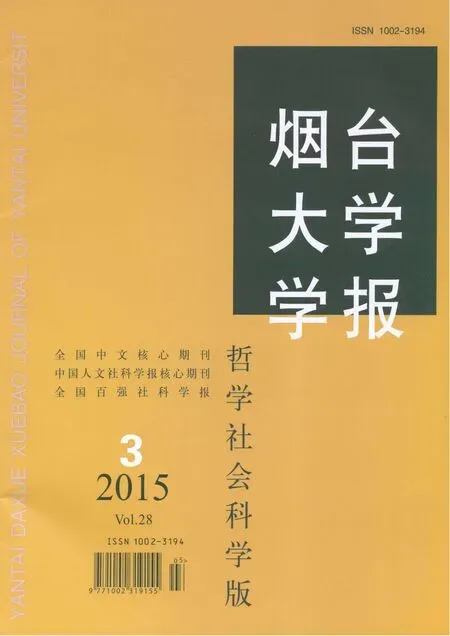论语篇的互文性特征
丁金国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引 言
“语篇”(text)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两个概念,进入华夏的学术视野,前者已有半个多世纪,后者已四十余年,据“中国知网”截至2014年上半年统计,前者的论著已逾十万余篇部,后者也已近半万。然所论,就其主要部篇而言,或深或浅带些“洋味”,转述西论有余,“国产化”火候欠缺,读来总觉有不足之憾。笔者从研习中感到这两个概念均非西人所始创,东土远在汉代即有卓见于世。王充(27-约97)在《论衡》里,就有“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王充:《论衡》卷二八《正说》,黄晖:《论衡校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9页。后经魏晋曹丕、陆机、挚虞等人的阐发,为汉语语篇学的构建熔铸出最初的雏型。逮及齐梁,刘勰《文心雕龙》问世。《文心》五十篇,集此前文章论之大全,对语篇的本体论、写作论和阅读论,均作了系统阐释,为汉语文章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文心》以降,汉语的语篇研究,都在文章论的视野下展开,二十世纪初,已发展成为文章论大国。所憾者,古人的文章论,多着眼于书面语篇,而疏于关注口头言语。之于“互文”,郑玄(120-200)在注释汉文经典时,已发现此一语用现象,并首次命名为“互文”。洎唐,贾公彦释义为:“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云‘互文’。”清人俞樾则提出:“古人之文,有参互以见义者。”后世演化为“参互成文,合而见义”,近百年来一直作为修辞现象徜徉于语文生活中。然研究所及仅限于词、句间的表层语义关系,虽偶涉篇、章层次,但多为就事论事,缺乏从语用整体,作理论梳理,更无哲学韵味。“互文性”作为系统性理论中国没有,是地道的舶来品,是文艺理论界、外语学界作为美学、文学批评、哲学和符号学专属理论概念引入。
笔者在撰写《语篇特征探析》一文时,对语篇特征胪列为四:对话的功能性、语脉的连贯性、结构的层次性、语体的监控性。并在“补记”中认为:“在语篇特征的论说中,最不应缺略的是‘互文性’,但此一课题哲学味太浓重,具有超语言学性质,须参阅的资料浩瀚(古今中外)。如何从文本的海洋中,熔炼出言简意赅的理论体系,还真须些时日,故这里阙如。”①丁金国:《语篇特征探析》,《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1期。经两年多来对“互文性”课题的研习,现将初步心得体会,以作为对该文的补充,并就教于方家。现分四个子题分述如下:互文性的阐释;双值性是互文的根基;主体是互文的中枢;创新是互文的生命。
一、互文性的阐释
(一)“互文性”的始原义
“互文性”概念首创者系保加利亚裔法国学者朱丽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 )。克里斯蒂娃1966年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 -1980)的研究班上,在介绍苏俄学者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1895—1975)的“对话理论”时所提出。正是受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启迪,克里斯蒂娃从中推导出“互文理论”,并自创了法语词“intertextualité”。②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对话论”的消化和反刍过程,中文版详见: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瑾:《互文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辛斌、李曙光:《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互文性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③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实际上克氏对互文性的定义有多种表述,1966年她在阐释巴赫金对话理论时说:在话语中“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背景)重合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或是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一篇文本)。在巴赫金看来,这两个轴代表对话(dialogue)和双值性(ambivalence),它们之间无明显分别,巴赫金发现了两者间的区分并不严格。是他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④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第4页(原文见Seuil出版社,1969年,第115页)。这是克氏在《词、对话、小说》中对互文性的第一次表述。1967年在《封闭的文本》中进一步阐释为:“一篇文本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其丈夫索莱尔斯(Phlippe Solers)1971在《理论全览》里,重新定义为:“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文本,并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1974年在《文学创作的革命》中则表述为:“互文性一词指的是一个(或多个)信号系统被移至另一个系统中。但是由于此术语常常被通俗地理解为对某一篇文本的‘考据’,故此我们更倾向于取‘易位’(transposition)之义,因为后者的好处在于它明确指出了一个能指体系向另一个能指体系的过渡,出于切题的考虑,这种过渡要求重新组合文本——也就是对行文和外延的定位。”⑤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第3、5 页(原文见 Seuil出版社,1969 年,第133、75、60 页)并认为,“无论一个文本的寓意是什么,它作为表意实践的条件,就是以其他话语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是说,每一个文本从一开始就处于其他话语的管辖之下,那些话语把一个宇宙加在了这个文本之上。”“文字词语的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点,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文本空间的交汇,是若干文字的对话,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相关人物的,现在或先前的文化语境中诸多文本的对话。”⑥转引自王瑾:《互文性》,第29页。
2012年岁末,克里斯蒂娃在复旦大学讲座时,对“互文性”概括为:“每个文本都是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交汇处至少有一个‘他文本’(即读者文本)可以被读出。这种文本的交汇被巴赫金称为文本的‘双值性’(ambivalence)……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集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间的关系,巴赫金对此已经有所阐述。我明确地将这种文本对话称为‘互文性’……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是把它们纳入到社会、政治、宗教的历史。结构主义一开始只是一种形式研究;‘互文性’使它得以进入到人类精神发展史的研究。”①丁金国:《语体风格的共性与个性——试论“自己的样子”的语体风格学》,《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2期。
从1966年对巴赫金“对话性”的阐释推导出“互文性”始,40多年来欧美理论界对“互文性”阐释纷纭,克里斯蒂娃面对驳杂理论喧哗,尽管其每次表述语词不一,然核心意旨没变,始终如一坚守“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造”这一经典性的定义。
巴特作为克里斯蒂娃的导师,是“互文性”概念的热心推介者,他本人从《S/Z》(1970)书中使用“互文本”一语始,在多部著述中谈到该问题,在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1973)撰写《文本理论》词条时,则集中介绍了互文性,认为:“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我们将文本定义为一种语言跨越的手段,它重新分配了语言次序,从而把直接交流信息的言语和其他已有或现有的表述联系起来。”“我们当然不能把互文性仅仅归结为起源和影响的问题,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范畴:已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在《文本的意趣》(1973)中则解释说:“我体会着这些套式的无处不在,在溯本求源里,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互文正是如此:在绵延不绝的文本之外,并无生活可言——无论是普鲁斯特的著作,是报刊文本,是电视节目,有书就有了意义,有意义就有了生活。”②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第12、13页。并强调:“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③王瑾:《互文性》,第40页。巴特的《文本理论》一文,对“互文性”理论的介绍最为集中和系统,并且着意凸显出“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的广义互文观。
在互文理论构建的行列里,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 )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在《广义文本导论》(1981)中说:“诗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本,而是广义文本。广义文本无处不在,存在于文本的上下周围,文本只有从这里或那里把自己的经纬与广义文本的网络联结在一起,才能编织起来。”④王瑾:《互文性》,第115页。热奈特相关论文见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热氏“广义互文”的提出,标示着与此前理论的迥异。在《隐迹稿本——二级文学》(1982)中,对“广义文本”又作进一步推演,提出了“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概念,认为:“诗学的对象是跨文本性……跨文本性超越并包括广义文本性,以及其他若干跨文本关系类型。”⑤王瑾:《互文性》,第115页。“跨文本性”概念的创立,巧妙地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进行了分解,构建起异于此前的互文阐释体系。“跨文本性”统摄互文本和超文本;超文本下辖:准文本(指文本的序、跋、标题、副标题、护封等)、元文本(与谈论此文本的评论)、超文本(联结前文本与在前文本基础上构成的次文本间的关系,如自我扩写或修改等文本)、广文本(组成文学领域各种类型的等级体系)。热氏给互文性的定义是:“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⑥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第19页。“切实”一语将互文从笼而统之的混沌中剥离出来。由上可见,在热氏的分类中,“互文性”被严格地限定在一个极窄的范围。因而,《隐迹稿本》也就成了“互文性”概念由广义到狭义的过渡标志。
我们这里对“互文”和“互文性”概念的使用,是沿着祝克懿(2010)的思路下来的。认为“互文”作为一专业术语,有四个义项:a指一种理论体系,类似“隐喻”、“模仿”等理论范畴,“互文”可与之平行,构成更高层次的理论系统;b指语篇形成过程中的行为方式,语篇可用多种方式构成,互文只是一种,借以标示言语行为的功能类型;c指互文动作的结果,所形成的现实语篇实体;d指互文语篇参互各方在形成互文过程中的方式和格局。a、c、d的义项是名词性的,b义项为动词性。在具体行文时,有时特指某一项,有时兼指多项。用于动词性义项时,与传统修辞学中的“互文”、“对照”、“对偶”等方式近似。“互文”可作为组篇的一种行为方式和过程,即在组篇的过程中,表达者为增强语篇在内容上的说服力,引入它文(即使用他人或个人此前的言论)进入当下语篇的行为。下文在使用这组概念时,凡不特加说明,均为同义互用。
(二)我们对“互文性”的理解
我们对“互文性”的理解是:在语篇构组的过程中,表达主体为强化其意念语篇的语势,引入已存历史语篇的过程和结果称为互文性。在这一表述中,互文性有三个核心要素:A.意念语篇;B.历史语篇;C.互文语篇。意念语篇也就是表达主体在言语交际中想要表达的语篇,是表达者在表达前存贮于意念中的语义结构;历史语篇是已存在于历史文库中、先于意念语篇而存在的语篇;互文语篇是意念语篇与历史语篇在互动互构过程中而形成的现实物质化结构。可见,意念语篇是非现实性的语篇,互文语篇则是可把握的现实语篇,其物质化形态是其赖以存在的依据。如梁启超在论及清代学术时,谈到对宋明理学之反动,反动者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遵宪、王夫之和颜元。梁氏认为:
(A)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艰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葛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尝曰:
(B)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竟不必附和雷同也。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9页。(A+B=C)
任公此段言论,可分为三个部分,(A)为梁氏的意念语篇,其意在论述清儒顾、黄、王、颜四子,尤其是颜元与旧学斗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B)为历史语篇,是颜元本人与旧学决裂的誓言,进一步印证颜氏尚实崇真的品格;(C)是语篇(A)与语篇(B)的合成产物——互文语篇。显示任公对与旧学争斗人士的敬仰与赞颂。就这个命题而言,有三个注视点:
一是说明互文性的发生语境,是发生在“语篇构组的过程”中。也就是说互文与语篇构组具有因果联系,一切互文只能凭借特定语篇而存在,离开语篇构组则无所谓互文。颜元此番有关学术是非的议论之所以能被引入,那是因为颜氏作为新派学人,在与旧学的论战中,敢于“明目张胆”地批判程朱陆王宋明理学,而正是这种冲杀精神,博得饮冰室主人感情上、观念上的共鸣,也正是语境适切,故而才有此段互文语篇的发生。所以说互文的生存环境只能在人类的言语活动中。当然任何言语活动的发生,都有先于言语活动的认知活动,在表层语篇结构形成前,互文意识就随着语篇的构思而运动着。如果对此作一理论界定,可称为“前互文”,前互文是非现实性的互文,只是表达者的一种意识结构。互文性作为理论概念是抽象的,而互文却是现实的、具体的,且具有物质上的可掌控特征。
一是互文的主体是表达者,表达者不仅掌控着对互文结果的预设构想,更支配着对引入历史语篇的选择。强化语势是选择历史语篇的唯一标准,如无“强化语势”的需要,则无须互文,充其量只能是言语游戏,非任何意义上的言语活动。既然要选择,就存在与理念语篇的契合度问题。粗而论之,可分为三个层次:完全契合,基本契合和不契合。完全契合即与预想结果一致;基本契合,与预想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但在未觅到更合适的历史语篇情况下,还可以接受;不契合,与理念语篇脱节或分离的历史语篇。契合度由谁来确定,是表达主体,还是接受主体?从互文语篇生成的角度看,表达主体是契合度的主导者。如定义所引入的互文语篇。其主导者是饮冰室主人。梁氏欲从论述清代学术潮流中,概括出“为学问而学问”学者的人格是:耿介、志专。学问之价值在于:善疑、求真、创获。所以梁氏选定颜元及其典型言论来强化语势。可见,互文性中对历史语篇的选择,完全由表达者智能结构的素质所决定。由此足以证明,历史语篇进入互文的过程,是在主体理念主导下的动态行为。
一是“过程和结果”,在语篇构组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过程都有结果,有的只有过程,而无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说语论文者,差不多都有这种无果而收的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出现在“前语篇”的构组时,即使是在运笔属文,或键盘论语,也有废稿满筐和“垃圾”充斥硬盘之虞。因为表达者在构组语篇时,一者可能未搜寻到合适的历史语篇,以强化语势;一者在形成过程中发现理念语篇,已将历史语篇的语义融入其中,这时就可能出现删除显性历史互文的情形,这也叫有过程无结果,然更习见的情况是过程与结果共现。“过程”中,意念语篇与历史语篇的参互方式,固然可以以十计之,但不管何种历史语篇,一旦被选定,都必须受制于意念语篇,按照意念语篇所框定体式,与其一起编织成互文语篇。现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论”,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互文方式参互佐证,用以说明互文的整合功能。梁氏《概论》中所用历史语篇,可以十、百计之,然不管其原来语篇是何种体式,是对话、叙事、坐禅,抑或讲史,都毫无例外地被整合为与意念语篇顺向的议论语篇。而静安《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论”,历史语篇多为诗词摘引,然却都依然被模铸为词话体的议论语篇。可见,互文过程中,引文体式可能繁杂多样,但语篇主体的主导,却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切都必须绝对服从意念语篇的体式。
二、“双值性”是互文的根基
(一)“双值性”的内涵
“对话性”是巴赫金艺术哲学的核心,而“双值性”则是其对话理论的基石。巴氏认为,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任何“表现”都具有双向性,都存在着我和他人,“在这里我是为他人而存在并借助他人而存在”。①巴赫金:《巴赫金全集》(4),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05页。在巴氏的心目中表现者与被表现者共存于同一个生存体中,所以,任何文本“总是在两个意识、两个主体的交界线上展开。”克里斯蒂娃将“双值性”视为其学术的支柱,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中,“双值性”出现了44次,2012年岁末克氏在复旦演讲《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中,该词出现了15次,二文都为“双值性”专立了章节。早期的定义是:“术语‘双值性(ambivalence)’指历史(社会)植入一个文本,文本也植入历史(社会);对于作者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水平轴(主体-读者)和垂直轴(文本-情境)交汇,凸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至少有一个他词语(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在巴赫金的著作中,他称之为对话性(dialogue)与双值性(ambivalence)。”②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和小说》,《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2012年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再次进行了界定:“什么是‘双值性’?就是一个词语、一个段落、一段文字里,交叉重叠了几种不同的话语,也就是几种不同的价值与观念,有时甚至相反。”③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
(二)俗解“双值性”
所谓双值性我们的理解是:指互文语篇在语义解释上所具有的双层语义结构而言,“双”值不是形式是意义,是语篇在意义上历时与共时交汇而出现的语义阐释。共时是语篇作者此时此地的语义表现,历时是语篇作者所用的历时语义(即此前历时文本、传说、文化意象等的历史语义)。双值性就是出现在这个纵横交汇点上。这个“点”平行联系着作者与读者,垂直联系着现实与历史,双值就是在这个“点”上被展开,被读出。就创造主体而言,通常是以历史语篇的语义结构为一值,互文语篇的核心语义结构为另一值。实际上,任何语篇何止双值,都是由多层双值结构所构成,按照对话理论,任何语篇都是对话,既然是对话,就必定有作者的“值”及与之相对应的读者的“值”,这是一层;而任何语篇又都是互文语篇,那么除了读者与作者,就互文的语义结构来说,在任何互文语篇中,都含有语篇共时的“值”和历史语篇的“值”,这又是一层。再上溯,历史语篇本身也含有双值,如此向上追索直达无限;就现实语篇来讲,读者的“值”,也是个无限量的“值”。实际上在中国的古典阐释学中,对“双值”已有多种界定,诸如:“莫衷一是”、“言人人殊”、“乐山乐水”、“言不尽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至“诗无达诂”。明清学人王夫之《船山遗书·诗绎》更有精辟的论述:“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性而自得。”①又见谢榛、王夫之:《四溟诗话 姜斋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39-140页。这种以尊重读者地位为前提的阐释理论,与西方的阐释学、符号学、接受学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论者毫不逊色。
现以唐代张籍的《节妇吟》为例予以说明。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对于此诗的“值”,从诗的语义结构本身看,就是描述一达官贵人对有夫之妇的追求与挑逗。而有夫之妇在“感君缠绵意”的引诱下,心有所动,将双明珠系在贴身的红罗襦里。并声称“知君用心如日月”,当意识到己身已有所属,旋即将放浪之心收回,于是将明珠还回,并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惆怅,收住全文。这一值既是一般读者的“值”,也是文本表层语义结构的值,是对男女情爱的抒发。而张籍写作该诗的本意是:对中唐权势炙手可热的藩镇节度使李师道的应召的回绝。依据历史事实,张籍反对藩镇割据,主张大一统。但慑于对李氏的权势,只好用曲折委婉隐喻,表明“事夫誓拟同生死”的决心。作者张籍的这一值,应该说只有张氏本人最清楚。
这种反差“值”的出现,是作者与读者,历史与现实交叉结果。言外历史值,是文本题下注“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提示所宣,人们沿着“注”,搜索到李、张背景及其招纳与拒纳的往来细节,故能准确地解读出历史值。历史值与文本当下语义值之间的反差,所造成“政治值”与“私情值”迥异如冰炭水火的效果,却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双值性”的哲学命题。之于对《节妇吟》的他解,明末唐汝询,在这首诗后批道:“系珠于襦,心许之矣。以良人贵显而不可背,是以却之。然还珠之际,涕泣流连,悔恨无及,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唐诗解》)同时,贺贻孙在他的《水田居诗筏》中评此诗云:“此诗情辞婉恋,可泣可歌,然既系在红罗襦,则已动心于珠矣,而又还之。既垂泪以还珠矣,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之时。柔情相牵,展转不绝,节妇之节,危矣哉。”这两段对系珠与还珠行为的解读,则完全消解了“节”正值,已涵贬意。明清之际还有徐增、瞿佑、钟惺等均参与对此诗的解读。我们这里引出这些,目的是想说,“双值性”并非纯“双值”,而是多值。
“双值性”提出者的初衷是用于阐释文学现象,其立论依据的文本是小说、诗歌、神话等,后推而广之到广义的文化领域,将其作为哲学概念,用于解释人类言语活动的普遍事实。问题就在“普遍”二字上,它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普遍性?上文我们已经看到有相当多的语篇是多值。那么,反过来说,有没有“单值”?从直接接受者的角度看,在言语生活中,在特定的语境下,存在着“唯一值”,拒绝多值存在。如军令等一切带“令”字语篇,其语义解释的绝对性压倒一切,也就是说此类语篇无“双值”。这仅就军令语篇接受者而言,其解读只能按照成规进行,但离开接受者的特定身份,依然存在着双值,非军令接受者,当得知军令后,自然会按照“各以其性而自得”来解读,因为军令对他们并无律法上的约束力。这就说明,所谓“单值”依然跳不出普遍原则的套子。此例对我们的理论启示是:第一,双值的展示不是按同一个模式显现,而是依语篇的语体类属不同而不同。律令语体与文艺语体可能是处在“双值性”横向链条的两级,两级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值”差。第二,“值”价差的大小,有可能成为鉴别文艺语体品位高低的尺度之一。如文学史上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诗历来为多解的引例,众说纷纭,难以确解。可以说有多少个读者就可能有多少个值。而同是唐人张打油的《咏雪》:
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两相对照,各自所含的值,轩轾斐然。前者作为艺术精品而受到历代赞赏,后者则被讥为“打油诗”,就连作者也被“授予”张打油诨号,史上连个名字都没留下。由此可望,用“值”差来鉴衡语篇,可为语篇的语体属性分辨和艺术品位鉴赏提供一可操作的尺标。
三、主体是互文的中枢
(一)“主体”的义界
“主体是互文的中枢”命题,源于语篇“对话性”特征而生。既然对话是一切语篇基本功能,那么一切对话的必备条件必须有参与者,即表达者和接受者。二者孰主孰次,从语篇发生初始看,先开口者就是有意而发,就有特定旨意和接受者,就掌控着话语权。然而言者和受者身份并非专属,此言彼受,或彼言此受,这种角色转换是言语活动的常规。轮换并不意味着主体角色的消解,判断的标准就是围绕特定话题所展开的话语权由谁控制,控制者就是语篇主体。世上根本不存在无主体的语篇,所谓“无名氏”本题便是有名,是佚名。西方解构主义者的“作者已死”的哲学命题,是为凸显阅读者的地位,所推导出的极端命题。它与“诗无达诂”不同,“诗无达诂”是有特定所指,是以“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性而自得”(王夫之),可见,“诗无达诂”中诗的主体“未死”。而“作者已死”是用于阐释人类文化现象的普遍性命题,它很像一个无底洞,跳进去就很难出得来,从这个角度看,这似乎又像一个“伪命题”。
克里斯蒂娃与巴特不同,40多年来从未放弃对“主体性”的强调,直到2012年她在复旦答问时,还着意指出:“主体性和历史性恐怕是我给结构主义带来的新的向度。”“互文性阅读也需要一个度,不能让读者的想象代替作者想象。”①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的生成是一个主体自主甄选的过程,在互文形成过程中,主体始终在场,对其他文本进行重读、更新、浓缩、易位和深化的有意识活动;巴特则强调互文生成是个无意识、自动生成的过程。我们认为强调读者是为了创造一种哲学理论,而坚守“主体性”,一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一是对人类创造精神的激发。如《节妇吟》的主体张籍,不仅创造了该语篇,而且该语篇的最终语义结构解释权永远是张水部。之于该语篇的解读者,因已转换为解读主体,自可“各以其性而自得”。现代诗僧苏曼殊作有《本事诗》,诗中借入了两个历史互文,一是“恨不相逢未嫁时”,一是“红叶题诗”: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据传,曼殊剃度出家后,曾有一靓丽少女,慕其名而向其索句,曼殊有感于斯,着墨以寄其意。前两句叙事,后两句寄情。情从何来?借自唐人张籍“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名句。张句原意是以婉言曲意回绝权贵之聘,字面虽凄哀婉切,意蕴却气高节坚,貌似有情却无情。玄瑛的“无情泪”,是无可奈何的言辞,反张意而用之,“道是无情却有情”。“恨不相逢未剃时”确是道出了心底之言。这种互文仿拟确乎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本事诗》主人的“恨相见晚”是实情真意,张籍的情是虚情假意。之于红叶题诗亦是玄瑛随手拈来,则更是张诗所无。可见,每转换一次主体,就必定出现一次新的语义阐释。新的语义阐释,既非语境所赐,亦非客体所生,是写作主体的主导所致。
(二)“主体”的类属
互文的主体,按照语义结构可分为:当下主体、历史主体和解读主体。当下主体即现实已存语篇的创造者,不妨称其为原创主体(并非严格意义上)。历史主体系由当下主体所引入的主体,进入当下语篇的历史语篇,既可是一,也可是二、或三、四、五不等。实际上,在言语活动中,进入当下语篇的历史语篇量,一是少数,多数超出二或三。《本事诗》是二,一是“红叶题诗”作者,①《本事》有多个版本,现摘其一:据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十载:“中书舍人卢渥,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独获所退宫人。宫人睹红叶而呈叹久之,曰:‘当时偶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一是《节妇吟》作者。王国维的境界论是三:第一境界来自晏殊的《蝶恋花》,第二境界来自柳永的《凤栖梧》,第三境界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②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静安作为解读主体,将三者选为互文,绝非是“无意识”的行为,而是王氏加意甄选的结果。这种甄选只有静安能为之,且与其为创造“凡治学问者,须广泛涉猎、刻苦研修,不畏艰险,殚精竭虑,方有望达到学问的巅峰”(本文作者解)的语义结构相参互。此时的王国维,已由解读主体转身为新的原创主体,突破了克里斯蒂娃所设解读的“度”,为历史语篇注入了新的灵魂。应该说这种创造是空前绝后的,晏柳辛的历史语篇原义被王氏引为喻义,从语用心理来讲,其认知跨度之大前无古人。正如叶嘉莹所说:“晏殊的‘昨夜西风’三句,不过写秋日之怅望;柳永的‘衣带渐宽’二句,不过写别后之相思;辛弃疾的‘蓦然回首’,不过写乍见之惊喜。这些词句与所谓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其相去之远真如一处北海一处南海,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势。”③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0-451页。确实是“风马牛”与“北海南溟”,然而在静安的笔下,“怅望”、“相思”、“惊喜”三值,令人信服地变幻出“求索”、“苦炼”和“喜获”的语义结构。对此王氏咬定“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正是在“自有境界”主导下才能“借古人之境界”,才能将古人的境界,“为我之境界”。静安的断然声气,作为语篇创造主体的地位昭然。辛弃疾的《贺新郎 送茂嘉十二弟》④辛弃疾:《贺新郎送茂嘉十二弟》:“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1)马上琵琶关塞黑,(2)更长门翠辇辞金阙。(3)看燕燕,送归妾。(4)将军百战身名烈。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5)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这里(1)“马上琵琶关塞黑”,互文汉元帝时昭君出塞事;(2)“长门翠辇辞金阙”,互文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事;(3)“看燕燕,送归妾”,互文春秋时卫庄姜送去国归妾事;(4)“将军百战身名烈”,互文汉李陵别苏武事;(5)“易水萧萧西风冷”,互文荆轲刺秦王事。中的历史语篇有五,稼轩借用史上著名的别离故事,以强化离情别绪之苦。就互文的关联性而言,境界论与晏柳辛词语义上的关联性,几乎是“零”,而辛词与所述五个历史语篇,其相关性则显而易见,二例显示出主体在互文过程中主导作用的力度差异。这就说明主体对互文的主导作用,存在着强弱之分,后者为弱势互文,前者为强势互文。
四、创新是互文的生命
(一)“创新”的能动作用
尽管人们对互文性理解纷纭,客观讲,互文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文化传递中的内在奥秘。这就是“意义”运行的动态性、开放性和无限性。在动态、开放进程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毫无例外地闪烁着创造的晶莹,人类的历史文化就是在互文过程中永无止境地向前涌动着。节点上每一次晶莹的显现,既相似,又迥异,都不是前次互文的重复,而是异于前者的创新。“相似”是因为同一基因所致,相异却是创造、发展、前进。创新是互文的结果,也是互文存在的根据,无创新的互文是无生命力的互文,唯有那些创新度强的互文,才能葆其永恒的活力。互文的创新机制,既显现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演进行程,也体现在个体语篇的生存和发展上。
对于人类文化整体创新的阐释,互文性理论始创者们多有论述,这里仅就个体互文的创新进行例释性说明。例如“西风、渭水、落叶、长安”四个物象,作为自然物并无任何人文色彩,然一旦进入互文网络,就在原创主体的基底上,擢升为“萧索、感伤、别离”的文化符号,自动地进入汉文化的历史流通长河,在连绵不断地传递着其固有信息同时,并不停地萌生新的意义。文化符号“西风、渭水、落叶、长安”的首创者为唐贾岛,出自其《忆江上吴处士》: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圆。
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夕聚会多,当时雷雨寒。
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贾诗借“西风”、“渭水”、“落叶”、“长安”的萧索景象,抒发忆念旧友之情。因贾诗情真意笃,故后世不断地进入互文结构。宋周邦彦的《齐乐天秋思》中有“渭水西风,长安乱叶”思念故人。元白朴的《得胜乐 秋》有“听落叶西风渭水”,《梧桐雨 普乐天》有“西风渭水,落叶长安”追思古往伤心事。金仆散汝弼的《风流子》中有“几度秋风渭水,落叶长安”来哀叹唐明皇杨玉环悲剧。毛泽东则一反美成、仁甫、良弼等对个人间的别绪离情哀叹,用其来嘲讽、鄙视国际反华势力的衰败之象: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满江红》,1963年1月9日)
面对所述各情各景,我们更加敬佩润之互文的巅峰极致,为“创新度”说提供了典型的范例。上述各例虽然都是借贾岛之境,但由于各自内在智能结构的差异,从而造成互文语篇创新度上的轩轾。如果说“西风渭水,落叶长安”是同一个互文在千年历史中单向传递,那么在王蒙笔下《黄杨树根之死》中的互文,却是另一番景象。王氏采用多项文化符号并行推进。如当其写到主人公马文恒为“作家梦”奋斗了几十年,一朝“成功”时的癫狂神态是:
(1)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2)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3)指点江山,激扬文字;(4)哎呀呀,王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白白活了三十五!①(1)为李白的《将进酒》中句,(2)为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句,(3)为毛泽东《沁园春 长沙》中句,(4)为民谚。
王氏将李白、杜甫、毛泽东的高雅诗词和坊间谣谚置于同一平台,将古与今、美与丑、狂欢与痛苦、高雅与低俗平行并置,既是对历史语篇语义结构的颠覆,也令其在毁灭中重生。这种超越平庸,恣意戏谑,类欧陆的“梅尼普式”讽喻体②梅尼普讽喻体,源于苏格拉底对话中的“狂欢场景和反抗结构”,经梅尼普(Ménippe)吸收并改造成为一种以戏谑、谩骂、怪诞、愤世嫉俗为特征的狂欢化的讽喻、调侃言语类型。在公元前一世纪由罗马人瓦罗(Varro)命名为“梅尼普讽刺体”。,抑或是王蒙有意而为之的创新。
(二)创新的能动量
对于互文性的创新功能,李玉平(2006)认为:互文性的价值在于文本之间的异质性与对话性。互文不是被动地去用前文本,更重要的是对前文的超越与创新。③李玉平:《互文性新论》,《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李氏依据创新与否,将互文语篇分为:积极互文和消极互文。认为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是对话式的积极互文,科学中的互文性是独白式的消极互文,并断言“互文性对于科学来说无足轻重”。我们认为,既然互文的机制是不停地在传递人类历史文化,并在传递中派生、分蘖、重构,生产出新的互文语篇。所以,无论是文艺文本或是科学文本都是按照互文网络进行编织,文艺与科学两类文本的差异,既在形式,更在于意义。也就是其各自的语义结构孽生能力的强弱有别而已,绝非有的是“举足轻重”,有的是“无足轻重”;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科技语篇中的实验数据、文献索引作为互文进入互文语篇,绝非是消极的“无足轻重”的赘文琐语,而是作为强势语义,顺向支撑着创新互文的语势。顺向强化语势是科技互文别于文艺互文的本质特征。如下列a、b两例:
a.任何物体在空中自由下落时,其加速度为每秒32平方英尺,换言之,地心引力所产生的加速度为32ft/s2。
b.50岁以上妇女最容易发生髋部骨折,因为绝经期后雌性激素水平下降,骨骼钙流失更加迅速。老年女性中髋部骨折最为常见,几乎60%的病例发生在75岁以上的妇女。
a、b两例均为科技语篇。a例中“换言之”所领引的互文语篇,对自由落体的语义结构是顺向强化。b例中有两层互文,一是“因为”所引,一是“老年女性”所引,二例都是对髋部骨折的顺向互文。如果将其任一互文删掉,语义信息虽然完整,但其语势的力度显然低弱,由此可见互文的强化作用显而易见。而对于文艺语篇的互文,原创者从不留意语势是顺向还是逆向。上述“西风渭水落叶长安”中美成、仁甫、良弼、润之等的互文语篇是顺向,王蒙的《黄杨树根之死》则是逆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与科学之间的空间带上,存在着大量的日常生活、学术和公务等无限量语篇,它们在互文过程中,用“积极”“消极”来鉴定语势的强弱,势必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泥淖。因为在这中间带上语篇,进入互文的自由度与文艺语篇无异。所以,断然说唯有文艺语篇是积极互文,余者皆为消极互文,显然具有极大的武断性。倘从语义入手,以顺向与逆向为标尺来鉴衡互文创新的力度,则可了然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