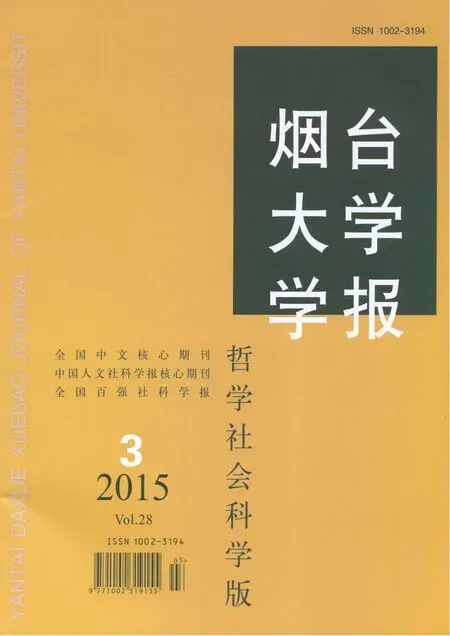从酷吏辈出到大族兴起——汉代河东区域文化的发展历程
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的河东文化繁荣兴盛。闻喜裴氏、解县柳氏、汾阴薛氏三个享誉天下的冠冕大族的存在,即是其显著标志。然而,自魏晋上溯四百余载,河东地区却是酷吏的渊薮。区域文化特质的前后反差何以如此鲜明?通过仔细梳理河东区域文化在两汉时期的发展脉络,或许可以作出尝试性的解答。①有学者认为,西汉时代的河东地域风习以“尚武尚法”为基本特征,东汉时期,“在举国皆兴儒的大环境下,河东之儒教也没有呈现出比西汉时进步的景象”。河东“文教事业发生转变是在东汉末,杜畿任河东守时”。见赵李娜:《西汉河东郡地域风习探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笔者认为,这个说法过于绝对化。实际上,自汉武帝时期社会文化大环境发生改变之后,河东地区绝非一个文化绝缘体,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必然受到文化大环境的深刻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或许有潜移默化与暴风骤雨等形式上、程度上的差别。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东汉末年“河东文教事业发生转变”视为两汉时期河东文教因素长期积累的渐进性结果,或许比长期停滞却一朝转变的文化突变论合理一些。而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探究两汉时期河东文教因素的渐进性生长过程。
一、西汉中期以来河东酷吏的转型
在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作用下,西汉前期的河东地区保留了浓厚的以“刻削”“急法”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册,第238页。为特色的秦代政治风格遗存。随着汉王朝的基本国策由保守转向进取,需要大批酷吏参与政治管理,河东地区因应时势,成为输送这类人才数量最多的一个郡级行政区。①具体论述参见拙作《西汉河东酷吏政治成因再认识》,《晋阳学刊》2014年第2期。
不过,在酷吏最为活跃的汉武帝时代,酷吏群体已经表现出向儒学靠拢的迹象。在司马迁所记录的酷吏当中,占据最大篇幅的是张汤。据记载,由于汉武帝“方向文学”,此人作为汉武帝时代酷吏群体中代表性人物,在处理重大案件的过程中,“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②《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10册,第3139页。亭,《集解》引李奇曰:“平也,均也。”身为酷吏而援引儒术,张汤的做法顺应了西汉政治文化发展的大势,也预示了酷吏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然而,张汤是关中人,与之相比,出身于河东的酷吏在角色转型方面较为滞后。他们或“以鹰击毛挚为治”,或“痛以重法”约束部下,③分别见《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所载义纵、减宣事迹。在汉武帝时代,尚看不到他们援引儒学“古义”以决狱的事迹。
“文学”、儒学在河东人心目中地位的上升,发生于另外一个政治群体身上。汉武帝时期,尽管河东人大多以酷吏身份入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就是以外戚的身份步入政治舞台,卫青、霍去病、霍光莫不如此。“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卫青由此平步青云,官至大将军。④《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9册,第2921页。霍去病之父霍仲孺,“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而卫少儿是卫子夫之姊,霍去病作为卫子夫、卫青的外甥,仕至骠骑将军。霍光虽然与卫子夫、卫青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他与霍去病是同父异母兄弟。其父霍仲孺离开平阳侯家后,回到河东,“娶妇生光”,遂与先前所生的霍去病“绝不相闻”。十多年后,霍去病任骠骑将军击匈奴,路过河东,“乃将光西至长安”,“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⑤《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9册,第2931页。经过数十年的宦海历练,汉武帝临终之际,霍光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汉昭帝时期的首辅大臣。
在河东外戚家族中,卫青、霍去病常在军旅,对学问之事兴趣不大。相比于二人,霍光对学问之事的态度有所不同。《汉书·循吏传》:“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繇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⑥《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11册,第3628页。这段记载表明,霍光在昭帝时期的执政理念与汉武帝时期重用酷吏的做法一致。不过,在昭宣之际,霍光对精于学问之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早逝,霍光援立昌邑王为帝。但他旋即后悔,又与亲信大臣合谋,打算废黜昌邑王。这场政变尚在酝酿之中,却发生了一桩有惊无险的意外。《汉书·夏侯胜传》:
胜少孤,好学,从(夏侯)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蕳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祆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⑦《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第10册,第3155页。
因为自己的废立阴谋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而被成功预知,霍光“益重经术士”,并且认为当政者“宜知经术”。与之前相比,虽然不能说霍光已否定了“以刑罚痛绳群下”的习惯做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执政理念明显因经术之学的渗透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尽管如此,班固在褒扬霍光“拥昭立宣”有“匡国家,安社稷”之功的同时,面对霍氏族灭的历史结局,却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慨叹:“然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①《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9册,第2967页。霍光死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上距他“益重经术士”只有六年。班固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说霍光如果能够早一些认识到经术的重要性,便会懂得保身持家之道,不至于深陷“盈溢之欲”,最终导致“宗族诛夷”的悲惨结局。与霍光本人从服务于“省政”的政治功用角度看待经术相比,班固将经术与提升人生境界联系起来。从河东籍官员尹翁归的事迹来看,班固的看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尹翁归早年受到担任河东太守的酷吏田延年器重,被选入官府,“以为爪牙,诛锄豪强,奸邪不敢发”。②《汉书》卷九○《酷吏传》,第11册,第3665页。可见,他成长为酷吏的潜力很大。后来,尹氏担任东海太守,“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善于“以一警百”,达到“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的治理效果。升任右扶风之后,“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使斫莝,责以员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辄笞督,极者至以鈇自刭而死”,“京师畏其威严”。观其施政风格,与酷吏无异。但《汉书·酷吏传》并没有尹翁归的一席之地,如此编排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在于班固对这个人物持如下看法:“翁归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甚得名誉于朝廷。”③《汉书》卷七六《尹翁归传》,第10册,第3207-3209页。身为酷吏而懂得“清洁自守”、“温良谦退”,这与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及“湛溺盈溢之欲”的霍光相比,堪称河东酷吏实现根本转型的典型代表。
尹翁归并不一定是因为自身直接修习经术而提升了为官做人的层次,他的履历中也找不到研习经术的痕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④见《汉书》卷六《武帝纪》班固赞,第1册,第212页。,如果不是昭帝时期“增博士弟子员”⑤《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596页。,继续重视经术的传承,如果不是宣帝时期“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⑥《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9册,第2821页。,尹氏这样具有复杂人格的酷吏也是很难出现的。可以说,汉武帝以来六经、六艺地位的持续提升,是塑造出以“温良谦退”为人格特征的酷吏所不可缺少的历史背景。
二、西汉末年河东儒学的初兴
河东籍酷吏在汉昭帝、汉宣帝时期的逐渐转型,意味着该时段河东区域文化的法家底色正在趋于淡化。在这一时代大势中,朝廷对河东太守的选拔任用开始发生变化。
数学学科教学往往让学生觉得枯燥无趣,定义、定理和例题都抽象难懂。在实践共同体中每周进行一次集体备课,在集体备课中,各位教师针对学生的基本情况总结了简捷的讲解方法,搜集了实用的材料,还准备了应用型例题,彼此间进行交流共享、取长补短、互相借鉴。这样很好的发挥了集体的作用,不仅让各位教师找到一种归属感,还提高了教师的教学应用能力。
汉宣帝以前见于记载的河东太守有季布、胜屠公、番系、田延年。季布“为气任侠”,重然诺。胜屠公与酷吏周阳由争权,“相告言罪”,“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番系来自于僻远的九江郡,汉武帝时期策划“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欲为朝廷去除漕运过程所面临的“砥柱之限”。田延年更是被班固明确列入酷吏群体。⑦参见《史记》卷一○○《季布栾布列传》,第8册,第2729页;《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10册,第3136页;《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4册,第1410页;《汉书》卷九○《酷吏传》,第11册,第3665-3666页。这四个人均没有“文学”气象。宣帝以后的元帝、成帝、哀帝时期,周堪、甄少公、萧咸曾担任过河东太守。甄少公事迹不详,周堪“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霸为博士。堪译官令,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⑧《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604页。所谓“经为最高”,无疑表明周堪属于很有影响力的大儒。史载“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①《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7册,第1948页。可见儒者周堪对河东的治理颇得民心,这个事实意味着,与西汉中期相比,河东民风已经发生了改变。萧咸其人虽以“能吏”见称,②汉哀帝即位之初,丞相王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用之。”见《汉书》卷八六《王嘉传》,第11册,第3492页。可见,萧咸并不以“儒者”名世。但其父萧望之乃一代“巨儒达学”,③《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颜师古注,第10册,第3271页。“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④《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10册,第3271页。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萧咸的儒学造诣也是可以想见的。这一点,从汉哀帝时期的一件事情上即可看出。
哀帝用人不遵法度,任命年仅二十二岁的董贤为大司马。董贤之父董恭钦慕萧家为名门,欲为另一子董宽信求娶萧咸之女。正逢萧咸的另一个女婿王闳意图结好董贤,他跟岳父萧咸提这门亲事。《汉书·佞幸传》:
咸惶恐不敢当,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闳性有知略,闻咸言,心亦悟。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⑤《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11册,第3738页。
所谓“允执其中”,见于儒家经典《论语·尧曰》,是篇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⑥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35页。萧咸对封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中出现的“允执其中”一语,准确找出了其对应的历史掌故,从而敏锐地觉察到汉哀帝有传位给董贤的念头。⑦“后上置酒麒麟殿,(董)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说,左右皆恐。”见《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11册,第3738页。可见,萧咸对哀帝所谓“允执其中”的政治含义,理解得何等透辟。能把握经典话语的现实语境,这个情节显示,萧咸应当也是一位颇具儒学素养的河东太守。
选拔具有儒学文化背景的长官到河东任职,一方面说明河东地域的治理形势比之前宽松,另一方面,他们的到来,也为河东区域文化的继续成长创造了条件,一个前所未有的表现是,河东当地也出现了以儒学名家的文化人物。
《汉书·儒林传》:“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⑧《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602页。《易》家姚平,此其一。另有《尚书》家杨仲续。《后汉书·杨厚传》:“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袠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此处显示出杨春卿、杨统为父子关系。而《后汉书·杨厚传》李贤注引《益部耆旧传》又曰:“统字仲通。曾祖父仲续举河东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为立祠。乐益部风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学,以《夏侯尚书》相传。”⑨《后汉书》卷三○上《杨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4册,第1047、1048页。由此可知,杨仲续、杨统为曾祖孙关系。那么,杨仲续就是杨春卿的祖父,二者之间有两代人的差距。“汉兵平蜀”在建武十二年(36年),⑩《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1册,第59页。杨春卿死于此时,以代际差距二十年计算,则杨仲续当属西汉成、哀之际的人。关于杨仲续的籍贯的问题,既然他被举荐为“河东方正”,根据汉代察举制度,中央高官、郡太守、王国相都有资格举方正。⑪如汉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汉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诏,“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这里仅举两例,对两汉时期举方正这一求才模式,劳榦先生有十分详尽的梳理。可参看氏著《汉代察举制度考》,收入《汉代政治论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629-680页。不过,从理论上说,无论中央官还是地方官,其所举来自某一郡国的方正都不应该占据其他郡国的名额,因此,杨仲续也应当就是河东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姚平、杨仲续的儒学旨趣皆以政治预言为特色。姚平所学京房《易》本之于焦延寿,焦氏《易》学“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而京房得以步入高层政治舞台,也是因为在特殊时期“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姚平作为弟子,深得京房倚重,师生关系很不一般。京房欲行官吏考课法,推荐姚平作刺史,以辅助自己实现政治抱负。而当京房因政敌倾轧陷入危局时,姚平敢于对其师直言不讳:“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①《汉书》卷七五《京房传》,第10册,第3160、3164页。劝其师顺天应命,从容待死,莫再作无谓的挣扎。这并非姚氏落井下石、欺师灭祖,恰恰说明他深信京房那一路以政治预言为特色的《易》学,通过“涌水已出”等异象,认定其师在政治斗争中必定落败,因而才有这番推心置腹的交流。
三、东汉河东儒学的厚积薄发
汉元帝以来的河东儒学虽然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与传统的齐鲁儒学相比,甚至与三河区域内的河南、河内儒学相比,河东儒学的分量仍是很微弱的。因此,尽管王莽代表着“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他为了夺权,也确实“处心积虑地尊宠、笼络、收买经学与知识分子”,③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07页。但在现存有关王氏执政时期的历史资料中,极少见到河东士人的身影。④王莽曾以“长安国由为讲《易》、平阳唐昌为讲《书》”。见《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12册,第4126-4127页。随后的东汉光武帝时期,河南、河内已有孙堪、郑兴、蔡茂、张玄等经学之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⑤孙堪、张玄分别见于《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郑兴,见《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蔡茂,见《后汉书》卷二六《蔡茂传》。而河东人见于史册者唯有杨茂,其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⑥《后汉书》卷三八《杨璇传》,第5册,第1287页。,不以经术为业。不过,河东儒学发展的低谷是暂时的、相对的,凭借西汉时期儒学发展的点滴积累,因应东汉习经之风甚盛的历史大势,河东文化重新步入上升轨道,也是必然的。
章帝以后,选拔具有经学背景的人士担任河东地方官员的做法比较常见。活动于桓灵之际的政治家陈蕃,是公认的士林领袖,据《后汉书·陈蕃传》,陈蕃的祖父曾为河东太守。①《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第8册,第2159页。逆推两代人四十年的时差,则陈蕃之祖的政治活跃期当在安帝、顺帝时代。考虑到东汉一代有注重家学传承的文化风气,通过陈蕃的历史表现,我们可以逆推,其祖父很可能也有一定的经学素养。桓帝时,中山刘祐、陈留史弼均担任过河东太守,刘祐其人“宗室胤绪,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学《严氏春秋》、《小戴礼》、《古文尚书》”。史弼“少笃学,聚徒数百”。颍川陈寔担任过闻喜长,早年“有志好学,坐立诵读”,还曾“受业太学”。京兆赵岐“少明经,有才艺”,后来任皮氏长,“抑强讨奸,大兴学校”。安定皇甫嵩任临汾令,其人虽出自边地,“习弓马”,然亦“好《诗》《书》”。②刘祐事迹见《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贤注引《谢承书》,第8册,第2199页;史弼事迹见《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第8册,第2108页;陈寔事迹见《后汉书》卷六二《陈寔传》,第7册,第2065、2066页;赵岐事迹见《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及李贤注引《决录》,第8册,第2122页;皇甫嵩事迹见《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第8册,第2299页。灵帝时期,河东太守孔彪乃“孔子十九世之孙”,“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帅礼不爽,好恶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践言。龙德而学,不至于谷。浮游尘埃之外,皭焉汜而不俗。”③《隶释》卷八《博陵太守孔彪碑》,见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97页。灵帝熹平年间,韩仁在调任前夕去世,司隶校尉评价说:“仁前在闻憙,经国以礼,刑政得中”。④《韩仁铭》,见高文:《汉碑集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7、418页。
东汉河东地方官员多有经学背景,无疑与当时整个社会浓郁的习经之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社会文化生态对河东本土人士的文化形象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西汉时期,河东地区没有仕至三公高位者,东汉中期,却有两个河东人位至三公。一是平阳人梁鲔。《后汉书·殇帝纪》:延平元年正月癸卯,“光禄勋梁鲔为司徒”。李贤注引《汉官仪》:“鲔字伯元,河东平阳人也。”⑤《后汉书》卷四《殇帝纪》,第1册,第196页。关于梁氏的文化背景,《续汉书·律历中》:“章帝复发圣思,考之经谶,使左中郎将贾逵问治历者卫承、李崇、太尉属梁鲔、司徒掾严助、太子舍人徐震、巨鹿公乘苏统及訢、梵等十人。”⑥《续汉书·律历中》,《后汉书》,第11册,第3027页。此处的梁鲔官职为太尉属,而此事发生于章帝元和二年(85年),而名为梁鲔者任太尉,事在延光元年(122年)。两者很可能即是一人,因为以近四十年的仕途辗转,由太尉属而至太尉,是合乎情理的。如此,则梁鲔长于天文历法。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在汉代讲究天人感应的思想氛围中,这门学问与儒家的关系甚深。另一个是解县的王卓,《后汉书·顺帝纪》:阳嘉三年十一月,“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李贤注:“王卓字仲辽,河东解人也。”⑦《后汉书》卷六《顺帝纪》,第2册,第264页。对于他的学术背景,由于记载简略,目前难知其详。
桓帝、灵帝时期,河东士人中仕途比较可观者,也有疑似以经学为文化背景的。比如临汾敬谦、安邑凉则。前者为东海傅⑧《礼器碑》,见高文:《汉碑集释》,第186页。,后者为议郎⑨《隶续》卷一二《刘宽碑阴门生名》,见洪适:《隶释·隶续》,第401页。,分别负责“导王以善,礼如师”以及“顾问应对”。⑩分别见《后汉书》第12册,第3627、3577页。从二人的职掌来看,很可能均具备较高经学修养。如果这只是推测的话,那么,桓灵时代河东人对经学大师的顶礼膜拜,则是河东儒学日渐兴盛的确切实证。桓灵时期的碑刻有不少是纪念已故高官兼耆儒的,其中能够看出河东人对此类活动的积极参与。弘农华阴人刘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①《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李贤注引《谢承书》,第4册,第886页。官至太尉。《刘宽碑阴门生名》著录来自三河地区的门生共“九十一人”,而在三河之中,河东籍46人,竟然超过一半。②洪适:《隶释·隶续》,第401-406页。弘农杨氏亦是东汉有名的经学世家,《杨震碑阴》所列门生“可识者百九十余人”,河东籍14人,占比约7%。③洪适:《隶释·隶续》,第137-138页。《杨著碑阴》题名56人,其中19人来自河东,占比近34%。④洪适:《隶释·隶续》,第134页。表面看来,《杨震碑阴》的河东人占比较低,但这是因为杨震的社会影响甚巨,门生的籍贯比较广泛,门生基数也较多。就绝对人数而言,《杨震碑阴》的河东门生数实际上与《杨著碑阴》大体相当。
河东人纷纷自投弘农大儒门下,以这样的地域文化生态为基础,河东儒学逐渐迎来了收获硕果的时刻,而东汉末年的河东大儒乐详正是顺应这样的历史契机而出现的。《魏略》曰:
乐详字文载。少好学,建安初,详闻公车司马令南郡谢该善《左氏传》,乃从南阳步诣许,从该问疑难诸要,今《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详所撰也。所问既了而归乡里,时杜畿为太守,亦甚好学,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至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详学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别受诏与太史典定律历。太和中,转拜骑都尉。详学优能少,故历三世,竟不出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⑤《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2册,第507页。
从这段记载来看,汉魏之间的河东儒者已成为当时经学界的翘楚。不但如此,连河东、弘农儒学地位的对比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曾任命太原令狐邵为弘农太守,“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⑥《三国志》卷一六裴松之注引《魏略》,第2册,第514页。由此可见,原本对河东儒学发生重大影响的弘农地区,为了促进本地的文化发展,也不得不调过头来仰仗河东,河东、弘农两地文化地位发生了逆转。
四、河东大族成立的前奏
文教加速发展,这是河东地域文化在东汉后期演进的显著特征。而在文教加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魏晋河东大族的先世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异动,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魏晋至隋唐的河东存在着三个享誉天下的大族,即闻喜裴氏、解县柳氏、汾阴薛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三大家族并非一时俱起。薛氏在曹魏末年方才随着蜀汉的亡国从蜀地迁至河东,其在河东发展的起步最晚。⑦“(薛)衍生兖州别驾兰,为曹操所杀。子永,字茂长,从蜀先主入蜀,为蜀郡太守。永生齐,字夷甫,巴、蜀二郡太守,蜀亡,率户五千降魏,拜光禄大夫,徙河东汾阴,世号蜀薛。”《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三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0册,第2990页。关于柳氏,《元和姓纂》记载:“周公孙鲁孝公子展,展孙无骇,以王父字为展氏,生禽,食采柳下,遂姓柳氏。鲁灭,仕楚。秦并天下,柳氏遂迁于河东。”但该书所列秦汉时期的柳氏人物,“秦末有柳安,惠裔孙也,始居解县。安曾孙隗,汉齐相。六代孙丰,后[汉]光禄勋。”⑧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095、1096页。柳安、柳隗、柳丰三人均无法得到正史的印证。而汉代见于正史的柳氏人物有西汉柳褒,《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①《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9册,第2821页。又有东汉柳分,桓帝时“中常侍管霸、苏康憎疾海内英哲,与长乐少府刘嚣、太常许詠、尚书柳分、寻穆、史佟、司隶唐珍等,代作唇齿”。②《续汉书·五行一》,《后汉书》,第11册,第3283页。见于碑刻者还有孝廉柳敏。③洪适:《隶释·隶续》,第93页。但遗憾的是,柳褒、柳分二人的籍贯不明,纪念柳敏的碑刻乃在蜀中,三人均未必是河东人。鉴于南北朝时期士人惯于攀附先世、伪冒士籍,世系造假现象较为普遍。④参见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不过,严格说来,《元和姓纂》所载柳氏的汉世祖先似乎并不属于“攀附先世”或“伪冒士籍”。按照仇文的定义,被攀附、伪冒的对象应是客观存在的大族,而笔者担心的重点在于《姓纂》记载的柳氏先祖或许根本就是假造的,无中生有的。笔者借用仇文的两个概念,主要意图在于说明南北朝人在祖先谱系方面的造假动机。在没有直接的文献佐证的情况下,笔者目前只能对《姓纂》的记载存疑。不过,据记载,东汉末年河东人贾逵,“世为著姓,少孤家贫,冬常无袴,过其妻兄柳孚宿,其明无何,著孚袴去,故时人谓之通健。”⑤《三国志》卷一五《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第2册,第480页。柳氏族人柳孚与“世为著姓”的贾氏通婚,由此可知,即便《元和姓纂》所谓柳氏在秦代已著籍河东的记载未可全信,但至东汉末年,柳氏已在河东居留多时,这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经过东汉时期多年的成长,进入曹魏时代,柳氏却寂寂无闻,其可以得到确认的大族之路的时间起点,与薛氏相近,似乎皆在魏晋交代之际。《新唐书》卷七三上:“(柳)丰,后汉光禄勋。六世孙轨,晋吏部尚书。”⑥《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三上》,第9册,第2835页。《晋书·刑法志》:司马昭“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⑦《晋书》卷三○《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册,第927页。柳轨是第一位得到正史印证的参与中枢政治的人物,当时司马昭尚在,正当魏晋禅代之际。比较而言,裴氏早在东汉晚期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已较为深入,并且这一趋势在曹魏时期得到了延续。
《元和姓纂》载:“(裴)陵裔孙盖,汉侍中。九代孙遵,始自云中从汉光武平陇、蜀,徙居河东安邑。安、顺之际,又徙闻喜。”⑧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333页。据此,西汉时代裴氏居云中,至东汉初乃有徙河东者。另据《裴岑纪功碑》的记载:“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⑨《裴岑纪功碑》,见高文:《汉碑集释》,第59页。“永和”是东汉顺帝年号,裴岑乃云中人,可见至东汉中期尚有裴氏生活于云中。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元和姓纂》对汉世裴氏迁徙路径的记载大体可信。一些碑刻、墓葬资料显示,东汉晚期的裴氏的确已经是河东地区的冠冕一族。山西夏县王村壁画墓是东汉桓、灵时期所建,壁画中有一位中年人形象,榜题墨书为“安定大守裴将军”。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地区文化局、夏县文化局博物馆:《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壁画墓》,《文物》1994年第8期。现今夏县与汉代闻喜境壤相接,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2-43页。此裴姓将军很可能即闻喜人氏。东汉京兆郑县有一水利设施,名为殽阬。据《殽阬君神祠碑》,因年久失修,光和四年,县令“河东闻憙君讳字君……乃复浚治殽阬,通利其水”。⑫洪适:《隶释·隶续》,第32页。而据《水经注·渭水》“又东过郑县北”条,“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庙,东南向华岳,庙前有碑,后汉光和四年,郑县令河东裴毕字君先立。”⑬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65页。此记载可补足《殽阬君神祠碑》的缺文,两相比照可知,郑县令裴毕亦是闻喜人。
需要指出的是,裴将军虽贵为太守,但安定郡属边地,安定太守的戎马色彩比较重,其“将军”称谓也表露了这一点。裴毕类似于汉代循吏,文教取向很明显,然而,职位不过县令。对河东裴氏成长为大族的总体进程而言,裴氏族人对士林抗争活动以及中央高层权力的参与,应当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东汉桓、灵时期,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这一政治形势波及河东,对立双方都在争取对河东的控制权。比如刘祐作为士林代表担任河东太守时,就发现河东“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①《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8册,第2199页。而刘祐离任之后,“中常侍左悺兄胜代之”,②《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第8册,第2122页。宦官集团完全把持了河东。对河东籍人士来说,对立双方也在着意笼络。
士大夫与宦官都在积极争取,这势必导致河东士人的分化,裴氏家族有人坚定地站在了士林一边。《后汉书·史弼传》记载,史弼因“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大怒”,遂发生激烈冲突:
命左右引出(诸生),楚捶数百,府丞、掾史十余人皆谏于廷,弼不对。遂付安邑狱,即日考杀之。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渑之间,大言于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选德报国,如其获罪,足以垂名竹帛,愿不忧不惧。”弼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昔人刎颈,九死不恨。”③《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第8册,第211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士大夫与宦官的生死较量中,河东人裴瑜④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八○一:“裴瑜,河东人,察孝廉”。清雍正年间《山西通志》卷六五:“裴瑜,河东人,尚书。”又卷一二三:“裴瑜字雉璜,河东人”。《大清一统志》卷一一七:“裴瑜,字雉璜,河东人。”为了表达对史弼的精神支持,言辞慷慨,壮怀激烈,而这正是“尚名节”、“轻生尚气”的东汉士人的典型特征。⑤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2、104页。通过类似行为,东汉士人往往邀得盛名。裴瑜后来位至尚书,应当与此有关。不仅如此,据记载,裴瑜“聪明敏达,观物无滞。清论所加,必为成器;丑议所指,没齿无怨”,⑥《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李贤注引《先贤行状》,第8册,第2112页。甚至取得了品鉴当世人物的体制外权力。而具有这种隐性权力的人,即便其没有很高的职位,在东汉晚期也可以成为士林仰慕的对象。在裴瑜之前,河东是不曾出现过此类人物的。
比裴瑜稍晚的裴茂,遭逢乱世,但在河东裴氏向魏晋大族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汉献帝初平四年,“遣侍御史裴茂讯诏狱,原轻系。”建安三年,“遣谒者裴茂率中郎将段煨讨李傕,夷三族”。⑦《后汉书》卷九《献帝纪》,第2册,第374、380页。在那段时期,汉王朝名存实亡,汉献帝被李傕、曹操架空,中央机构仅备员而已。然而,裴茂并没有弃汉献帝而去,汉献帝也很重视裴茂。针对“讯诏狱”、“原轻系”,由于“其中有善士为傕所枉者”,李傕劾奏裴茂:“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奸故,宜置于理。”献帝诏曰:“灾异数降,阴雨为害。使者衔命,宣布恩泽,原解轻微,庶合天心,欲解冤结,而复罪之乎?”⑧张烈点校:《后汉纪》,第524页。当时李傕骄横跋扈,汉献帝敢于为裴茂开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裴茂的器重。
在曹操掌权之后,有两大忌讳,对汉献帝小朝廷内部比较亲密的君臣关系很忌讳,对经学世家兼累世公卿的家族很忌讳。袁氏、杨氏遭受严厉的乃至毁灭性的打击,就与此有关。来自河东的裴茂既不是经学世家,先世也没有特别显赫的地位,并非曹操所担心的对象。如果裴茂继续与汉献帝走得很近的话,他仍然可能受到曹操打压。所幸裴茂久历宦海,又值波谲云诡、凶险异常的乱世,深知谨小慎微对于保身持家的极端重要性,其子裴潜“少不修细行,由此为父所不礼”。注重“细行”的家庭环境,对裴潜影响甚大。他“折节仕进,虽多所更历,清省恪然。”“又以父在京师,出入薄軬车;群弟之田庐,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于石奋。”①《三国志》卷二三《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第3册,第672、673页。西汉石奋“恭谨无与比”②《史记》卷一○三《万石张叔列传》,第9册,第2763页。,史家以之比裴氏家族,说明裴氏以严谨家风为特色。如果缺少这个特点,裴氏或许不能平安地度过数十年的汉魏禅代历程,更遑论成为魏晋大族。
从西汉前期酷吏辈出,到东汉末年以至魏晋之际的大族生成,长时段的历史观察表明,河东区域文化在汉代经历了巨变。而这个巨变并不宜简单地被视为文化面貌的突变,必须看到,历时漫长的文教因素的积累,是促成河东文化巨变所不可或缺的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往在晋文化、中古河东文化概念框架内进行的研究,或偏重先秦,或详于魏晋以降,而具有承前启后历史地位的河东区域文化发展的秦汉时段,似乎被遗忘了,即便偶有关注,也以长期的文化停滞视之。类似的研究取向不无偏颇之处,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