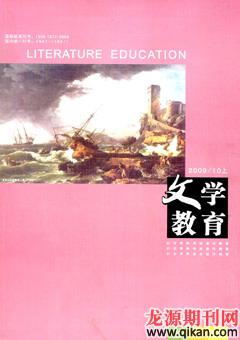论俞平伯探索新诗发展之路
郝栩甲
胡适的《尝试集》以革命者的姿态,宣告了与中国旧诗的诀别,“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无疑使诗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新思想、新方法在新的诗体中得以表现,但从我们今天较成熟的诗歌创作的经验上看,胡适及早期白话诗人的新诗不免缺乏审美价值,而显得幼稚和不成熟。新诗带着尴尬的表情出现在中国新诗史上。这种尴尬一方面是由于白话诗和古典诗词完全决裂,白话诗人失去他们文化积淀的历史源头,失去了可以借鉴的“巧妙的艺术”;另一方面,汉语和西方语言先天的隔阂,使得西方诗歌无力给予白话诗持续发展的能量。
一、完善不“适宜”的工具
俞平伯在他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指出“中国现行的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口哒是对胡适的观点:即。“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的一种理智的修正。俞平伯的意思是“我觉得在现今这样情形下,白话实在是比较最适宜的工具,在寻不到比它更好的工具;但是一方面,我总时时感到用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白话虽然已比文言便利得多,但是缺点也还不少呵,所以实际上虽认现行白话为很适宜的工具,在理想上却很不能满足。”他的理想是指诗歌“确是发抒美感的文学,虽主写实,亦心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因为雕琢是陈腐的,修辞是新鲜的,文辞粗俗,万不能发抒高尚的理想。”俞平伯认识到了白话作为不适宜的工具时,他同时也身体力行地进行着“修复工作”:首先他认为“做白话的诗,不是专说白话”,“用白话做诗,发挥人生的美,虽用不着雕琢,终与开口直说不同。这个是用通俗的话做美术的诗之第一条件。”强调了白话本身仅仅是工具,而不是诗,这也道出了初期创作白话诗歌的一个严重误区。在弄清楚工具和诗之间的区别后,他努力完善着这种工具,逐步减小白话和诗的差距。于是他认为要用新鲜的修辞去改造这种工具,否则就会落人粗俗的泥淖。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胡适的认同,他在《(白话诗的三大条件)跋》中肯定:“俞君这信里我所最佩服的两句话是‘雕琢是陈腐的,修辞是新鲜的”。当然俞平伯唯恐这些不够说明问题,在《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中他还进一步做出了白话做诗的要求即“用字要精当、做句要雅洁、安章要完密。”俞平伯对白话人诗的考虑是周全的,无疑是对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做诗观念的一种冷静的反思。俞平伯通过对白话作为工具的不适宜之处的完善,就从根本上指明了新诗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了,才能将诗与美联系起来。
二、向传统借“砖瓦”
当新诗拒绝了传统的母体时,它同样拒绝了它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料供给站。作为新诗创作者的先锋之一,俞平伯在责难旧诗词的陈腐限制着新诗乃至新文艺的发展日寸,对待传统的诗歌却多出了几分温情;在力求破决旧诗藩篱的同时,又向传统借来那种巧妙的艺术作为“砖瓦”,努力构建起白话诗的大厦。
在俞平伯看来“尽管诗体很拘苦,诗思很腐败,但是他们运用工具的手段,实有长足的进步。”“我们现在对于古诗,觉得不能满意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艺术的巧妙,我们也很惊服的。”我们从俞平伯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对古典诗歌艺术的借鉴,实际已经根植在他的新诗深处,从意象、音律上无不闪耀着古典的光辉,有意或无意地营造了美的诗感。如《冬夜之公园》一诗:“哑!哑!哑!伯队的归鸦,相和相答,淡茫茫的冷月,衬着那翠叠叠的浓林,,越显得枝柯老态如画”,“昏鸦”“冷月”“老树”的意象正式来源于古典诗歌中,在元曲《天净沙·秋思》中就有“枯藤、老树、昏鸦”营造的意境,此诗借用了古典的意象,将那种秋天塞外荒凉之景移植到了冬夜的公园,凸显出与古典情怀相似的凄冷氛围,让此时略显幼稚的白话诗获得了一次成长的洗礼。所以我们可以说俞平伯终于找到白话诗的突破之路,即向传统寻“根”觅“源”,以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认为“俞平伯氏能融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如《凄然》;又能利用旧诗里的情景表现新意,如《小劫》;写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听雨》。《呓语》中有说理浑融之作;《乐谱中之一行》颇作超脱想。《忆》是有趣的尝试,童心的探求,时而一中,教人欢喜赞叹。”
当然俞平伯这种白话诗在艺术上向古典的回归,并不代表着他对新诗的“反叛”,正是他对古典诗词的客观认识和机智的借鉴,才为举步维艰的新诗找到了一条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在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得到过响应,如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平静了现代主义的激情后,最终走向了“新古典主义”,由此形成他特有的诗风。由此可见,俞平伯的这种探寻是值得肯定的。
三、音韵的胶着
俞平伯对新诗音韵的重视,无疑就是为这条修补起来的“裂痕”做最后的胶着。首先他认为“诗歌是一种韵文,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音节务求谐适、却不限句末用韵,……做白话诗的人,固然不必细剖宫商,但对于声气音调顿挫之类,还当考求,万不可轻轻看过,随便动笔。”1924年,他还在《诗底格律》中详细论述了诗为何要有律以及新诗无诗律的缺憾,并且具体列出了制作诗律的五项措施,即“1句中之和当与句末之韵并重,2句法的参差须有一个限度。3诗一面有格律,一面仍能适合语法之自然。4用韵处不可过多,押韵时不可牵强。5造句不可拗涩,不当规定平仄四声。”
俞平伯对新诗音韵的要求即可总结成为自然和谐的音节,不受固定的规则所限制,奉行的是“自然的规则”。他的新诗无论是叠字、衬字,还是对句的出现,都在音韵上完善着白话诗,为此闻一多用“凝练”、“绵密”、“婉细”等词语来形容他的诗的音节特色。朱自清也在《冬夜·序》中说“平伯诗底声律似乎已到了繁与细底地步;所以凝练、幽深、绵密,有‘不可把捉的风韵。……他诗里用韵底处所,多能因其天然,不露痕迹,很少有‘生硬、‘叠响(韵促相逗,叫叠响)、‘单调等弊病。”
当然俞氏对音韵的追求也是多元化的,正如他的高足吴小如所说“而平伯师最后一本新诗集《忆》,走的也正是继承并发展民谣和山歌的道路。”
俞平伯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无疑是有意识地修正了早期白话涛出现的问题,他努力弥补着白话和诗的裂痕。作为新文学的先驱,俞平伯做白话新诗的经验还不丰富,在其诗歌中未能将他的诗歌主张很好的体现出来,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但他的尝试却是让人敬佩的,在那个激情膨胀的年代,他那种冷静的思考必定为新诗的发展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