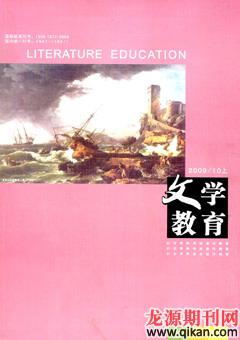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扫描
施战军
让我们打量中国地图的边缘,不妨从西部看起,慢慢转向南、北、东,再延及内陆的山高漠广、人口较少地带,这些地域多为少数民族居住区,经济、科技方面还欠发达,尚存自然和神性的原始气息。这样的地域,也许比内陆蕴藏着更多的文化和文学的丰富性——一个趋于全面现代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的古老文化和城乡格局正在遭受着新经济时代的严重改写,尤其在21世纪,少数民族地域虽然也免不了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但是其相对特异而持久的风俗、风景,以及那种史诗民歌与现实生存并未完全割裂的生活状貌,已成为中国人越来越重要的人文寄托与文学想象的对象。
无论是横空出世的《藏獒》(杨志军)、备受争议的畅销作品《狼图腾》(姜戎),还是在艺术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空山》(阿来)、《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范稳)、《乌尔禾》(红柯)等等,这些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标志性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少数民族文学视界的打开为特色。而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也是前所未有地涌现。新世纪中国小说出现的两大创作与研究的热点,一是“农民工进城”故事,指向现代性的状况与后果;二是对边地生态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审美观照,都指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建构。我们对这两者的基本评述和习惯印象,虽然大致无错,但是相对于丰富而活跃的创作实情来说,却都是不够全面甚至武断的。
纯正的文学对人的处境从来都是慈悲的打量、深切的体恤和贴心的思忖。包括对民族生活的态度,不应该是窥探,也不该总是羡慕、向往,更是对每一个个体的人的生活的感同身受。
在新疆的卢一萍,给我们描绘了塔吉克人夏巴孜的遭遇:
“他知道,初冬的塔合曼草原——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人的古老的冬牧场,正承受着超载的畜群的啃噬,像白云一样的羊群在草原上飘荡,但这些绵羊为了填饱肚子,已经像精怪一样的山羊学会了用嘴拱开、用蹄子刨开泥土啃食草根。……
每家蓝盖力的屋顶上都冒着羊奶一样白的牛粪烟,烤馕的香味、炖羊肉的香味混合着塔合曼草原金色牧草的香味和雪山上冰雪的气息飘过来,让他感觉到了一股暖意。夏巴孜已不止一次发现塔合曼的迷人之处。他从骨子里爱着这个地方,觉得美丽的塔合曼草原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所以才听从了西仁乡长的劝告,答应离开这里,迁徙到大沙漠边缘的、陌生的麦盖提平原上去生活。”
如夏巴孜这样,在醒来的精明人眼里却被讥为“夏巴孜傻瓜”,这里有意味深长的反讽。见过过多世面的人们,以牺牲共同的长远利益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傻。
与内陆文明的对应性,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客观呈现着,专家的评论也多从这样的角度看取民族文学的价值,从而渐渐地,读者对边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接受习惯也就越加强化了这一面。
然而,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形成文化与审美对照的惯性读法,导致在一般的城市读者的想象中,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总是与野生的或者未被充分开发与造访的山水风物、异样的或者新奇的风俗联系更多,对他们的日子本身,反而并不足够地加以细致的体察——更多的读者的兴趣在于外在于内陆文明的神秘的景观和脱俗的传奇,而不是世间内在于伦常、秩序中的人的日常生活。
在这样的情势下,像金仁顺、马金莲这样的作家的重要性更值得我们论说。他们没有把民族文学放在世间世情的对面,而是经由非“异质性”的叙写,不去刻意展示的自然风景、民族风情与习俗,似乎未加思索地将一切都落归于文学的恒常地带:人、生活和岁月。
回族年轻作家马金莲生活在宁夏固原地区的西吉,人们大致知道这里天气干旱少雨,生计贫困艰辛。一般来说,面对这样的地域,作家们去体察苦难和表达同情悲悯,是文学创作的常规,其民族因素的表现方式,往往会借助宗教以及带有宗教色彩的事项并通过性格化的人物来完成。近年的小说《掌灯猴》、《碎媳妇》,句子里总是容纳着最细微的身心反应和照应着人际而生的善意的顾忌。《碎媳妇》是体恤型的,是溶入式的,是身在其中的,而不是观察型的更不是概念式的,这里不可能有我们常见的猎奇性的想象,有的是对生活的忠诚和爱意。雪花自出嫁到生育的经历,面对的是外出打工的憨厚丈夫还有心中有数的婆婆、精明话多的嫂子,但日常的一切都在安然的秩序里,她有平常而聪慧的品质,无论对劳作还是对家族状况,心思里有的是朴素的富足感,这让小说在这著名的干渴土地上微微荡漾着水样流年的波光。
日常生活和岁月里善解人意的民族美德,在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桔梗谣》里有着更生动的表现,长辈之间的爱与怨在晚辈的理解和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中不无起伏地通向化解,家常的对话里性情各自呈显,青春的婚礼上感恩之心春风一样温煦地吹拂。
然而这样并不就等于完全消解了各自民族的特点,《碎媳妇》里娃娃出生前的扫炕换水和给女儿起名字时候缺席的阿訇,《桔梗谣》里的歌声、礼庆服饰和食物,等等,它们以生活的自然存在而不是摆放道具的方式,在悄然和乐的氛围中,把本然的民族生活味道飘洒了出来。
藏族作家阿来的《遥远的温泉》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小说,不求夸大的特有民族标识性的魔幻,也不做刻意的现时代功利性追求与人性矛盾状态的规避,作品不仅分明有凛然的自知和对情境的体认,还有内热的衷肠衷曲。让我们领略到成熟作家的从容,从容到似不经意间将民族的思维与想象方式得以呈现;同时更让读者感知出藏人的宏阔,宏阔到以历史处境、现实命运和文化负载所构成的张力钩沉民族性格的理趣。情景切换的炫彩之中,细部布满恍惚连绵的诱惑,甚至是情绪上的沮丧和失落,但是整体贯通的无疑是硬朗不灭、豪壮苍劲的尊严和作家应有的清朗的人文认知。这和阿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空山》,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将文学写作朝向传世经典的方向的作家,才会有如此透彻远瞩的眼睛,才会找到这样旺盛翻涌的创作泉源。
次仁罗布的《杀手》和龙仁青的《一双泥靴子的婚礼》,都是藏族作家的小说,但是他们的叙事方向却又格外不同。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盛兴一时的“先锋文学”常以藏地为依托,用玄秘的想象来进行叙述结构和叙述语式的新探索,在这一类创作的领军人物中,既有汉族作家马原,也有本地藏族作家扎西达娃,他们现在已经用当年的创造将自己的文学力作牢牢地镶嵌在了当代文学史的长廊。在内陆文学的先锋写作已经余绪飘散的时候,藏区这个先锋文学的渊薮,依然强劲地活跃着从小说叙述本体出发来探照人的心灵世界的“先锋派”作家群,目前,次仁罗布就是其中最为醒目的代表性作家。《杀手》的故事虽然简单,寻找——找到——放弃,这样的故
事模式也并不够新鲜,但是“杀手之谜”让这个小说在心理层面却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波折,一个康巴汉子寻找元凶替夫报仇,凶手的家庭生活情况和自我救赎的诚心使康巴人的复仇未果,复仇者在寻找元凶,而这个与小说作者同名的故事的讲述者在寻找那位复仇者,复仇者没能做成杀手,故事的讲述者却在梦中替康巴人杀了罪魁。幻梦中的暴行丝毫没有影响光天化日下的生活流程,而如何消弭内心的罪与罚,则是这小说里深藏的一个问号,宗教般令人敬畏的“赎”与“恕”的意蕴绵延到了文本之外。
《一双泥靴子的婚礼》,像龙仁青的《奥运消息》等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短篇小说一样,有一种童真的眼光,对世间的新鲜事物尤其是成人世界所拥有的经验充满好奇和向往。这样的小说从另一个意义上带有先锋小说的性质,它以孩子的心唤醒了对万物有灵的敏感,从而获得近于原始思维的想象力和叙述技法,将藏族的民歌、传说、礼俗融人小说。这又与次仁罗布的小说有着很明显的不同,儿童或者少年的视角,让龙仁青的小说不追求冷静的刻画,而是在盎然多趣的活动中,体现一种温暖又有些落寞的情感。温暖而落寞,也许正是人类的乡愁。
东乡族作家了一容的《绿地》,是另一种成人的童话,一位美丽的姑娘,两位追求她的男子,游走之态、俚俗之言甚至是身体的打量中,包藏着对美好的惜爱,男主人公内心之爱的结果是失落的,但是他的割舍里没有怨忿,青草、阳光、美梦、祝福,承载的同样是温暖与落寞的动人乡愁。
在“民族文化”与“发达文明”相遇的时候,不变的自然依存和不可止息的外来因素的渗入,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民族生活方式的取舍。于是,乡愁式的铭感,会形成民族文学深情叙说的内在动力。在红柯写图瓦人生活的《哈纳斯湖》、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金色牧场》里,存在着更为繁富和立体的写照。
《哈纳斯湖》和《金色牧场》都是诗情洋溢的小说,对民族生活充满无限的爱感,同时,又是同样在深情打量和向往安宁的意绪里,贯穿着一种难以道明的担忧。
《哈纳斯湖》把这种担忧在“老师”和“乌鲁木齐那个无法安静的女人”的情事、图瓦人和“水电站人”的对视等诸多层面上铺开,依然不能解决初民的生活境况免遭打扰和神性文化被现代文明演变的问题,于是作品里有一种复杂的心绪,蓝色的基调里又不得不视听杂音。无论是原住民、投身者,还是自我救赎者、闯入开发者,对这四种人,哈纳斯湖的容纳和拒绝都已经不再是安之若素的,伤怀胜过了明澈。这使作品在貌似浪漫主义的语言气质中,有着更为真切的现实主义精神。
相形之下,《金色牧场》更显得单纯饱满,不那么宽泛地延及现代与原始文明的对照和环保等问题。人的生活乃至整个生灵世界,仿佛被传说所附体。像“来时我还看见遍地阳光,可是现在,天空的乌云已经伸出舌头要舔我们的脚后跟了”这样的原始而形象的句子俯拾即是。可爱的语言和可思的描绘不时地一起出现在风物摹写之中,让这部小说更有通灵的动感和人心的明敏。这样的片段有很多,比如小说这样写雨前:
“鲁克勒猛然间站住,它抬头朝前面一片摇动的草丛看着,低低地叫了一声。它像一位见过世面的老人给我提醒呐。我看见了毕力格的枣红马,它四周的草静静伫立,好像做着连绵不绝的美梦。可是那一片草丛却在弥漫的金光里一阵阵地颤抖着,似乎被一股雄浑的漩涡用力地裹卷起来。”
作品中的生病、失恋,是很自然的写实,都不是煞有介事的,但都是带有结构性和关节性的故事内容,不能不说也是带着隐喻功能的构造。对草原气象、生活气息的把握和对人物成长、命运遭遇的呈现,总归要通向变故和平复,即便有来自神的说解,那些良弱的悲伤、认命、顺神,都让心灵的牧歌带着长长的颤音。作者把这些情状隐藏得非常巧妙,或者处理成无意的动静,意味往往就在青草、阳光、风、雨、天空、彩虹里以物景的方式传达出来。越是美好,越是若无其事,就有越深的隐忧和越加难以排遣的感伤。
民族生活中,不仅有空间上相对僻静朴素的情境、时间上相对缓慢悠然的速度,还有野性尚存、野生尚在的人与自然生命共生的生态。是人们在混乱中对宁静的寻觅,匆促中对安稳的皈依。有成长的欢乐与疼痛,有日常的爱恨恩仇。那是类似于宗教感的体验,追求一种本质的、长久的、有所敬畏也有所慰安的生命意义。
常规的城市文学之所以使人倦怠,是因为城市生活和想象缩略到了室内“肥皂剧”一样的小天地里,琐屑的小悲欢、肉体的欣快、精神的空虚,形成欲望的涂抹,黯然破碎的心在无光的文字里得过且过。在多数时间里,生活的常态令人麻木。而在广大的空间中,所有的边地都可能蓄满想象,处处存在应有的奇迹。不啻是信仰之所托和神启之所在。从这一层面上看,还有一些相当出色的短篇小说值得我们细读,比如温亚军的《硬雪》、梅卓的《护法之约》、石舒清的《黄昏》、郭雪波的《穿过你的灵魂之郭尔罗斯》、张存学的《拿枪的桑林》等等。
将生活的历史、生命的际运和民族的特性综合抟糅得最为出色的,是迟子建叙写中国东北端少数民族生活的一系列作品,其中有关鄂伦春地域生活的小说《微风人林》,同样是以呈现“人文魅性”、传达人间体恤为意绪的作品,由于身体因素的介入,使它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显得有些特别。汉族人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教化与挤压,跟鄂伦春山林里丰沛的近于原始的生命激情形成的比照,使得这篇小说始终富于叙事的张力,微风人秫,星月马影,身体的欢爱在这样的情境中不再有偷欢的猥琐,而更像天籁的乐段。
少数民族题材小说里总是流贯着野地上生长的歌声。这歌声无不诉求于天、地、人的和谐。
蒙古族作家白雪林的《霍林河歌谣》,在生存满足的低洼处,人与牛共有的伟大的母性,彼此保有令人动容的相通心灵,善良、坚忍、受难、牺牲……接天连地的长调,催人泪下又决不颓唐,宛若人间情感的安魂曲。这种精神之于生存的力量,正如悠远的史诗里总有的信念——百折不挠、绝处逢生。
许多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长篇史诗,那是他们各自的精神源头,而当今的少数民族文化,在迅疾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无数作家和读者的精神休憩所在,不是想象的余数,几乎是我们心灵的安妥和依靠之地。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民族史诗,往往构成文宗,也是他们后世文学创作相对发达的资源,特别是民族精神活化为人物性格的时候,总是能够从其民族史诗的某一母题里寻绎出某一原型的草蛇灰线。因此,承传也好,变异也罢,我们都能从这些作品里隐隐约约地把捉到来自民族深远血脉的审美律动。而对于普遍的内陆读者而言,这样的作品里何尝不正寄寓着我们人类共同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