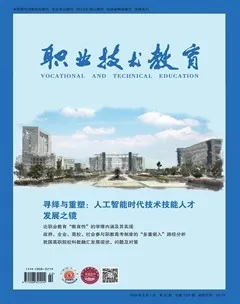职业教育的技术文化复归:内涵表征、现实意蕴和践行路径
摘 要 职业教育技术文化作为产教双主体交互融合而催生的一种新文化,是技术观念文化和技术实践文化的合一,其样态分别表征为工匠精神和产教融合。技术文化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理性表达和实践指引作用,赋予职业教育以价值追求,凸显其作为类型教育的内在性、精神性的独特之处。然而,由于技术文化历史断层与现实错位致使人们对职业教育存在认知偏差,进而出现产教融合适应性疏离等问题,需要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以耦合协同、异质同形的职业教育实践观重塑职业教育技术文化:从内生动力角度主张走向技术实践共同体,增强职业教育双主体适应性;从外生发展角度形塑实体嵌入的工匠精神技术观念文化;从共生同构角度倡导产教“异质同形”的技术实践文化。
关键词 技术文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适应性;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2-0019-06
职业教育作为“跨界”的类型教育。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在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方面存在适应性不强的困囿。本文以技术文化为研究视角,审视职业教育发展样态,追求职业教育文化自觉。回顾职业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脉络,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主体方面,研究局限于从教育的立场谈职业教育适应性,在问题域、发展观和动力源[1]方面均体现职业教育被动适应的文化倾向;二是职业教育双主体在厘清“职业性”与“教育性”的边界性与约束性方面的研究较多,从技术文化角度融合产教双主体的研究较少;三是在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研究内容多是从宏观层面对政策文件等政治话语的诠释,对具体的现实落点缺少有深度的学理分析,严重影响了校企合作在技术传承与技术实践方面有效衔接。鉴于此,需要重塑职业教育技术文化,复归技术文化既是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其价值取向的应有之义。
一、职业教育技术文化的内涵释义及表征形态
技术与文化内在关联。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来看,“技术是一种文化,文化是一种技术”[2]。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wski)视技术为一种文化因素,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技术角度认为文化的本质即为技术展现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具有技术的性质。进言之,文化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3],带有价值性、历史性和地域性的“基因”,是“塑造教育品格的深沉力量”[4]。技术作为一种有形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技术文化以一种无形力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5]。当前,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具有厚重感的文化底蕴来重塑技术文化,技术文化既蕴涵文化之维,又蕴涵践行之径,浸润引领跨界类型教育。
(一)职业教育技术文化的内涵:“性命向善”的观念文化与实践文化的合一
本研究把职业教育技术文化界定为观念文化和实践文化的合一,是产教双主体交互融合催生的一种新型文化。职业教育技术文化赋予职业教育以价值追求,凸显其作为类型教育的内在性、精神性的独特之处。
1.本体论:技术观念文化和技术实践文化的交织融合
在本体论方面,职业教育技术文化的要素结构包括技术观念文化和技术实践文化,二者构成一个内在关联的结构体系。若按照文化的一般结构来看,职业教育技术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结构,可分为技术器物文化、技术制度文化、技术观念文化三个结构层次,其中技术器物文化作为技术实践文化的载体,技术制度文化作为技术实践文化的制度保障,二者归属于技术实践文化。具体而言,技术器物文化属于纯粹实在的“具体世界”范畴,如职业教育实训技术机器设备、基础设施、教师队伍等。技术制度文化是虚实结合的“思想客体世界”,属于内在稳定的“关系世界”范畴,满足于组织内外各种关系调整的需要,是一种契约的、开放的理性文化模式,如现代企业制度、教育制度,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制度等。而技术观念文化属于纯粹的“理念世界”范畴,主导着“向善”的技术价值取向,是“技术文化的内核,是从精神、理性和价值层面对技术的理解和实践”[6],体现导向性与内隐性无形的文化特征。相比于技术实践文化,技术观念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恒久,是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规约,如具有特色的办学理念、校风校训等。可见,技术观念文化与技术实践文化是同构互生的关系,技术观念文化指引技术实践文化朝向深层次发展,技术实践文化又反哺技术观念文化,为其更好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2.认识论:技术观念文化之“道”和技术实践文化之“技”的和谐相通
技术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中国人特有的“关联思维”“综合融通”的信念浸润,重视技术观念文化的“道”与技术实践文化的“技”和谐相通,是“致力于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的统一追求”[7]。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丰厚的伦理实践文化积淀,“对生命内涵的诠释更加深刻、全面、具体,更具内向性和实践性”[8],正如李泽厚所说中国文化是伦理哲学,在思(知)与行、技与道(艺)方面的研究同思同构、和谐相通。
中国技术文化以“道”和“技”之间理实合一的关系为逻辑主线。所谓“道”即附着在形器上的意义及观念系统,突出匠人的技艺层面和匠心的修炼层面,其内蕴着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人的自由,技术技能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9]。此外,技术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遵循“志道、据德、依仁”[10]的根本,注重德技并修、诚信守德,强调“道”对“技”的指导以达到道技融合,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等具有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
换言之,技术观念文化之“道”与技术实践文化之“术”应达到内外和谐的自为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了技术价值论与技术工具论的“道器合一”,目的与手段、理想与条件、形式与实质的关系耦合。职业教育的知能传授应以遵循价值层面的“格心”“立心”考量为前提,将敬业乐业与德艺双馨相结合,培养具有人文气质的技能型人才[11]。概言之,教育性应是一切教育类型的前提,以促进职业教育人才“以主体赋予为载体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12]的丰盈。
3.方法论:在工作实践情境中体认与领悟贯通
职业教育技术文化倡导身心一如的“体知”思维模式,注重整个身心介入的内在体验,在职业教育的工作实践情境中注重内在逻辑和外显规范的体认和领悟。强调“人文化成”的德行过程,通常表现为由外向内转化的融会贯通与豁然省悟。基于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能力禀赋参与的工作情境,在完整的实践过程中探究技术文化的转化和升华,使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实现由与工作过程脱嵌到以身体之、由技术知识的封闭到智慧的敞开、由静态规限到动态生成转变。进言之,技术文化在方法论上,要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从“‘二元对立式’思维转向‘融通创生式’思维”,由依归‘求同’转向尊重‘存异’[13],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对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内在性控制”或“确定性把握”[14]。
(二)技术文化的表征形态
针对近代技术工具理性所造成的人被异化的窘境,若职业教育发展缺乏技术文化指引,技术与人难免会坠入与现实相悖的幻境之中。当下,技术文化在职业教育发展中需要找到其生长点。挖掘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传统经典元素,探索古代与现代技术文化的连接点,如体现工匠精神的技术观念文化和展现产教融合的技术实践文化。
1.技术观念文化表征:工匠精神
职业教育技术文化历经各种社会形态,其始终不变的内核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职业被尊重敬仰的底气,工匠精神内蕴“敬业诚信、精益求精、创新创业”的技术素养和人格品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极大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传统的注重批量生产效率转向现代注重精雕细琢的个性化需求,促使蕴涵工匠精神的技术观念文化得以复归。当下,技术文化关心“能够做什么”,反思“应该做什么”对职业教育发展进行规约,凸显自省意识的技术文化观。
那么,工匠精神是什么?工匠精神作为职业教育技术文化的观念表征,具体表现为注重培养学生的技术伦理意识、主体意识、创新意识、理解交往意识。通过培育工匠精神解蔽技术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异化的风险。具体体现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工作中做到精益求精,注重工作细节,追求技术(产品)的完美和精致极致;对技术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必须细致严谨不取巧;对待技术目标和技术困难需要耐心、专注、坚持;在技术生涯中始终保持技术理性、好奇、热情”[15]。
2.技术实践文化表征:产教融合
职业教育双主体涉及两种生产体制,即学校与企业。按照美国组织社会学家艾滋奥尼(Amitai Etzioni)对组织进行三种类型的分类,即功利性组织、规范性组织和强制性组织,职业教育的企业主体属于功利性组织,学校主体则属于规范性组织。进言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一种典型的“松散联结系统”(loosely coupled system),按照卡尔·韦克(Karl E.Weick)提出的此概念内涵来看,企业作为自由性生产体制,而学校作为协调性生产体制,前者治理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后者治理则更依赖政府的协调作用,以抑制和稳定过度活跃的市场竞争所造成的无序。
职业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由技术器物文化和技术制度文化所构成,具有组织间“松散联结系统”的特点,正如托尼·布什(Tony Bush)对其概括的特点,“组织目标不明确,管理手段和程序不清楚,校企独立,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比较小,强调分权优势,对外部信息的把握不明确,决策过程模糊等”[16]。因此,需要技术实践文化来整合。
二、职业教育技术文化复归的现实意蕴
(一)职业教育与技术文化关注的契合之处
职业教育与技术文化具有内在同构性,二者具有共同关注、共同规约和共同指向的契合之处。因此,不能把两者割裂,职业教育是技术文化的载体,技术文化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1.共同关注:实践性的技术知识与技能
一方面,职业教育和技术文化都关涉主体的匠器禀赋,关注身心一体的技术知识与技能,关照知行合一的中国智慧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从技术知识与技能的类型以及运用领域差异来看,以社会职业为蓝本,以技术活动领域来确定其知识和技能类型,多以程序性默会知识为主。通过对社会职业的岗位进行总体分析确定相关工作任务以及所需的知识、态度和技能。
2.共同指向: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技术实践
技术文化揭示和解释职业教育实践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职业性和应用性上。技术文化的载体是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技术实践操作,职业教育工作过程系统化作为职业场与教育场的桥梁,职业场域随着技术发展岗位能力不断变化,教育场域伴随技术发展教学内容不断更新,教育场域与职业场域分别是实施与开发的平台,分别担负学科知识系统化的解构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重构,强调教育过程与工作过程有效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一致性。
(二)技术文化历史断层与现实错位致使职业教育存在认知偏差
技术文化既是时间概念又是空间概念,技术文化蕴涵了时间上的延续性与空间上的连续性。我国古代技术文化具有独特的内容特色和伦理价值。随着近代工业文化的影响,技术文化发展史断层造成了文化羁绊,从而制约了职业教育技术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技术文化历时态发展的历史断层。我国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受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影响,导致“道技一如”的中国传统技术文化逐渐式微,致使现代技术文化在追求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出现历史缺位,表现为在指导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文化冲突,如产教融合不顺畅、理性的契约合作意识淡薄等。另一方面,技术文化共时态发展的现实错位。现代化工业发展需要大量集中化和专业化的工人通过学习基本的技术技能知识掌握实体性技术。由此,批量的“工人”取代了个性化的“工匠”,工人掌握标准化、规范化技术知识来操纵机器,负责流水线上的某个环节。崇尚技术理性成为工业文明的主导精神。从此,西方认识论体系追求科学的理性精神,“造成人的应然性丧失,被工具理性所支配的人丧失了生命激情”[17],造成“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意事实的人”[18],正如泰勒工作制下流水线作业的技术工人很难践行技术文化精神。进言之,因后发劣势导致职业教育技术文化在中国不同地域呈现前现代、启蒙与经典现代和后现代的时空叠加特点,这种焦虑的追赶心态导致“技以载道”的技术文化精神被忽视和割裂。
其一,把职业教育等同于技术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是专业技能身体训练的过程还是完整成人的培育过程,是职业教育始终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永恒问题[19]。这种源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割裂式思维,身体被边缘,因此,关于身体的技术技能训练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始终处于被鄙视和被贬斥的地位。其二,职业教育的职业性遮蔽了教育性。把人的教育等同于职业的教育、把职业之人的培养目标等同于人之职业的培训,“职业之人”还是“人之职业”?职业围绕着人还是人围绕着职业?这是职业教育技术文化“成事达人”所必须面对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博弈与较量。其三,职业教育办学双主体的良性生态关系错位。从社会层面看,职业教育双主体在参与办学方面各执己见,这一制度执行所需要消耗的交易成本是导致产教融合困难的关键原因,目前双方难以建立起积极且长久的办学意愿。我国职业教育属于典型的高等系科,所谓“高等系科是指与政府和社会关系密切,甚至由政府和社会决定其学科内容,或是否批准其相应学说[21]。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政策文本还需进一步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度,特别是涉及办学双主体深层次的产权、所有制等问题,还需保障相关制度的落地力度。此外,从职业教育的内部生态来看,职业教育“是教育”与“为职业”之间的关系一直未得到优化处理。
三、职业教育技术文化复归的践行路径
职业教育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生态。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以耦合协同、异质同形的职业教育实践观重塑职业教育技术文化,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培养高素质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一)内生动力:走向技术实践共同体,增强职业教育双主体适应性
实践共同体是诸多个体的集合,这些个体长时间地共享共同确定的实践、信念和理解,追求一个共同的事业[22]。技术实践共同体是相互异质性的个体能够相互理解和认同,为共同利益而相互包容形成的亲密伙伴关系。职业教育双主体应着力建构主体间性的共生关系,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彼此封闭关系。
首先,建构多元异质和相互包容的技术共同体文化。重塑“技术—文化—生活”间的内在关系,让人回归有生命力的学习场域[23],关注技术文化品性,回到职业教育的生活世界。其次,多元主体助推、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声望,以巩固和优化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地位和特色。从制度学派的理论逻辑思路来看,组织间的行为必须建立在社会承认的基础上,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所接受[24]。需要具备符合和满足职业声望等级制度的条件,组织的声望必须符合社会承认的逻辑,如具有专业性的技术技能知识。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越强,所拥有的资源就越多,职业教育的话语权越大。再次,促进学生养成具有主体性的职业综合素养,具备适应社会变化的职业行动能力。智能化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面临学历高移、综合职业素养提高的要求。因此,技术文化应着眼于内在与外在的“主体性”构建,关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内在生命体验[25],达到自我实现。此外,技术文化观照的技术人文取向着眼于民族的长远未来发展,技术文化应注重塑造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价值规范与伦理准则,这样才能由外在的“技术人”“职业人”转向内在的“完满人”。
(二)外生发展:形塑实体嵌入的工匠精神技术观念文化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肩负着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质量观念提升的价值使命。用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嵌入性”视角来形塑以工匠精神为内核的技术观念文化,职业教育工匠精神的制度化与社会过程关系密切,职业教育外生发展的适应性要融于实体嵌入的社会结构环境之中,如政治经济环境、文化制度环境等。实体嵌入形塑的工匠精神技术观念文化具有“崇尚创造、注重实效、鼓励多元、宽容失败、精准可控、团结协作的技术精神”[26]。有助于实现由边缘性参与者向深度嵌入的主体性参与者的转变。因此,本文试图以此作为突破路径,即以工匠精神技术观念文化缝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适应性的裂痕。
一方面,建立实体嵌入的组织内科层关系[27],由组织间相互独立关系转化为组织内相互依赖关系。职业教育遵循不同的组织文化。实体嵌入的工匠精神技术观念文化需要跨文化适应。产业界是自由性生产体制之下典型的组织间市场关系,企业遵从市场经济运作逻辑,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其生存逻辑是追求利益与效率。换言之,职业教育双主体理想稳定的组织关系应是实体嵌入性的组织内科层关系,即产业和学校为了实现共赢的目的合二为一,有助于培育稳定的职业态度以保证工作品质,体现在设计上追求独具匠心,质量上追求精益求精,技艺上追求尽善尽美的工匠精神[28]。应鼓励多方面、多角度探索异质性组织间的技术观念文化,塑造引领时代风尚的技能观与择业观,多渠道营造崇尚技能的校园文化氛围和社会文化风气。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尊重普通劳动者、重视技术技能、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技术观念文化。
另一方面,创造性转换、接续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发掘中国传统的独特话语体系与潜在认识论基因[29],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工匠精神养成的社会土壤,主动挖掘和吸收地域与企业优秀文化。培育德技并修的工匠精神的逻辑前提是建立工匠精神养成的技术观念文化体系,建立校企文化交流平台,使学生了解企业文化以适应企业工作。我国文化传统为塑造工匠精神提供内在基础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性命向善的和谐观,中国古代工匠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形成了“精益求精、德艺兼求、至善至美、大巧若拙”[30]的精神特质,有助于产教双主体优势转化、相辅相成,以达到工匠精神的最高境界。在职业教育实体嵌入的组织内科层关系中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乎“善”的精神,如将“止于至善”“众善奉行”等规则准则融入到工匠精神之中,建立互信和利益机制,通过共守合作协议的互信机制和互利互惠的利益分享机制,多渠道、多形式实现企业参与合作利益最大化,如企业文化进校园,但不是企业的市场逻辑取代学校的教育逻辑。此外,推崇“工必尚巧”,强调工匠在制造过程中发挥开发万物的技巧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警惕机械的形式主义倾向。
(三)共生同构:倡导产教“异质同形”的技术实践文化
产教融合体现了产业文化与教育文化之间的博弈与适应,如果说产业文化致力于开拓职业的外部世界,那么学校文化则致力于塑造人的内在世界,外显与内隐形态体现了职业教育外部统摄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支配的理念逻辑。可见,产业界与教育界遵循“异质性”的发展逻辑。但在职业教育场域,两者需要在技术实践文化指引下达成同形同构。技术制度文化作为技术实践文化的外显形式,从新制度主义视角来看,技术制度文化强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合法性”机制,维系和促进职业教育产教双边关系,为其作为类型教育寻找影响“信号”。新制度主义学派提出的新制度主义同形理论,致力于在耦合共生中走向共赢共益。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先进的技术制度文化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引导与规范作用。
一方面,搭建职业教育产教“异质同形”技术制度文化的现实载体。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产教融合围绕的核心问题是交易成本问题,异质性的组织间交往,组织内的协调成本要低于组织间的协调成本。按照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组织具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人们行为的投机性倾向[31]。若组织间关系合并为组织内关系,可以更容易依靠行政命令来解决供求关系。首先,产业学院作为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新载体,是产教融合的新型组织形态,真正契合行业产业需求,有效解决产教人才供需对接失衡问题。其次,建立和发展现代学徒制专业,引教入企和引企入教,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再次,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基础理论协同创新研究平台,这是对产业界和教育界进行融合的“同形”要求,这要求技术制度文化在引领职业教育办学双主体时做到:在宏观层面上,产业界与教育界所关注的物质增长与精神成长相适应;在中观层面上,学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与生产经营、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适应;在微观层面上,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适应。可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校办厂”一体化关系,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和产业学院等复杂的松散联结组织结构,这些抓手成为形塑职业教育技术制度文化的现实落点,以弥合校企关系疏离、“校热企不热”的不适应现象。
另一方面,纾解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张力矛盾。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适应环境而生存,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认识组织行为、解释组织现象,组织环境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于职业教育双主体来说,企业更关注技术环境,而学校更注重制度文化环境。前者注重效率最大化原则,而后者是组织为了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需要组织耗费资金去满足其“合法性”地位,服从“合法性”机制。一定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双主体适应性发展效果欠佳,是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的矛盾问题,之前的解决方案总是着眼于技术环境的改善,轻视制度文化环境,鉴于此,应在职业教育双主体的组织内与组织间建立激励制度等组织决策制度。
总之,职业教育技术文化既是技术观念文化与技术实践文化的交织,又是技术经验文化与技术伦理文化的融合。其负载多元多维的价值诉求,着眼于“完满职业人”人才培养目标的整体生成,建构起“人”与“工作世界”的有机联系,有利于学生了解、走入职业世界,实现整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李政.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理论循证、时代内涵和实践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33-143.
[2]吴虑.职业教育学习空间重塑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20:136.
[3]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
[4]高伟.论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现代教育价值[J].高等教育研究,2021(2):14-23.
[5][30]梅红霞,王屹,唐锡海.中国古代学徒制的文化考察[J].职教论坛,2017(10):90-97.
[6]郑新娟.文化再造职业教育——基于技术变迁的视角[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33.
[7]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79.
[8]王嘉毅,鲁子萧.规避伦理风险:智能时代教育回归原点的中国智慧[J].教育研究,2020(2):47-60.
[9]吴国胜.技术与人文[J].北京社会科学,2001(2):90-97.
[10]叶浩生.具身认知的原理与应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71.
[11]王洋,顾建军.智能职业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新路向[J].现代远距离教育,2022(1):83-91.
[12]满忠坤.论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学[J].教育发展研究,2017(23):70-77.
[13]李政涛.教育的唤醒:探寻实践哲学的教育方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144.
[14]徐平利.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67.
[15]程宜康.技术文化——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文化育人论[J].职教论坛,2016(24):14-19.
[16]托尼·布什.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M].强海燕,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8-177.
[17]鲁洁.实然与应然两重性:教育学的一种人性假设[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98(4):1-8.
[18]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30.
[19][20]李政涛.教育与永恒[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16-117.123.
[21]伊曼努尔·康德.论教育性[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2.
[22]戴维·乔纳森.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郑太年,任友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6.
[23]罗生全,杨柳.深度学习的发生学原理及实践路向[J].教育科学,2020(6):21-27.
[2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82.72.
[25]康永久.教育学原理五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460.
[26]王伯鲁.技术与文化互动问题剖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6-21.
[27]郝天聪,石伟平.从松散联结到实体嵌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困境及其突破[J].教育研究,2019(7):102-110.
[28]张健.职业教育质量治理的价值追问与提升方略[J].当代职业教育,2022(1):4-9.
[29]孙彩平.中国德育研究的认识论困境及突围路向[J].齐鲁学刊,2022(1):78-87.
[31]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ome Elementary Consideration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2).
The Return of Technical Cultur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Representatio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Shang Jing
Abstract" The technical cul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new culture spawn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ical concept culture and technical practice culture, and its pattern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raftsman spiri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echnical culture plays a rational expression and practical guiding role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ndows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value pursuit, and highlights its inherent and spiritual uniqueness as a type of educ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historical fault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nd the dislocation of reality, people have cognitive bias towa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n problems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alienation of adaptability appear. It is necessary to restore the technical cul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ith the coupled, coordinated and heterogeneous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view, and the practice paths of its restoration should be advoc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to the community of technical practice: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dual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hous motivation; form the craftsman spirit and technology concept culture embedded in the 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ogenous development; advocate the technology practice culture of producing and teaching “heterogeneous and homomorphic”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isomorphism.
Key words" technical cultur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daptability; new institutionalism
Author" Shang Jing, lecturer of College of Marxism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Ph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Qvfu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作者简介
尚晶(1986- ),女,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昆明,650031)
基金项目
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研究”(BJA210105),主持人:李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