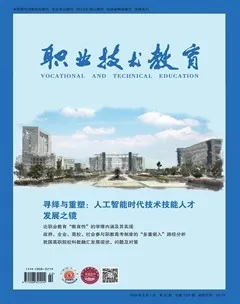论职业教育“教育性”的学理内涵及其实现

摘 要 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加快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迫切性。当前,职业教育还未能摆脱“技能教育”“低技能人才的教育”和“差生教育”的社会认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关键在于认识其教育属性。基于对杜威思想的分析,职业应是教育的手段,而非目的。教育通过职业活动来建立与工作世界的联系,激发个体的职业兴趣来获得自我成长。当社会生产活动深化了职业内容,技能人才需要的职业教育内涵亦随之深化。其表现为三个方面,即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要转向更为完善的人格培养,教学内容要转向“知其所以然”,教学过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基于此,职业教育要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生涯指导,强化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知识性,加强学生在学习实践中的经验体验。
关键词 职业教育;“教育性”;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2-0006-06
当前,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印发是职业教育从“分等”走向“分类”的转折点。理性来看,短时间内要将职业教育从一种为在普通教育赛道竞争失败的学生提供的“次要教育”,转变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的类型教育,还并不能令人信服。过度强调职业教育的独立性不仅会使职业教育陷入窄化、固步自封的困境,还会危及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原有地位。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职业教育既是基于现代化工业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基于民生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转变大众对职业教育的消极认知,还需要在社会层面加深对职业教育“教育性”的理解,在理论层面赋予职业教育新的价值内涵,探索职业教育“教育性”的价值逻辑与实现路径。
一、问题提出
工业化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其与职业教育的联系更加紧密。当前,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与社会缺乏高技能人才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与科技的进步使产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工作场域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的增量同步上升,而职业教育的育人方式还未完全发生改变,职业教育发展还存在一系列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职业教育是否只是“技能教育”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职业教育与技能教育在概念上是等同的,其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交织。技能教育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工业化时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催生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大批具备实际操作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劳动者支撑工业发展,该时期职业学校是实施技能教育的重要载体,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授服务机械化设备生产的操作技能和实用技能,因此,工业化生产初期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技能教育。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职业教育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单纯的技能训练已不能满足现代化工业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的目标开始转向更加综合的方向发展,除了传授实用的操作技能外,也开始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沟通能力、道德素养等符合未来就业市场需求的能力培养。这种转变的背后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和职业需求的变化,尽管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一定的重叠,但是它们的定位和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所不同。简单地将职业教育理解为“技能教育”的观念深刻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并造成了职业教育在育人模式上的局限性。
(二)职业教育被误认为是培养“低技能人才的教育”
在传统观念中,职业教育是培养从事技术工人、操作员等基础性职业的教育,培养的学生被认为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或低技能的职业,故社会期望不高。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被限制在“低技能教育”的育人框架下,导致其提供的技能学习内容很难突破和提升,如有研究者发现大部分职校生在校期间习得的技能只是专业技能的“皮毛”[1]。职业院校对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低端化定位会造成学生就业起点不高以及就业机会受限等,若学校课程过于注重具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在未来职场中难以胜任更高级别的职位;“低技能”的学习目标不仅不能激发学生对技能学习的兴趣,反而会导致他们缺乏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并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产生怀疑。目前,年轻人对职业的追求已不再是一份工作,而是向往更高的工作平台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职业教育应为职校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转变育人思路,摆脱“低技能教育”的人才培养标签。
(三)职业教育被误认为是“差生教育”
由于缺乏对职业教育的正面宣传与价值引导,致使一些社会群体仍对职业教育存在刻板印象。职业教育往往被视为次等教育,即认为只有无法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功的学生才会选择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的生源绝大多数来源于普通教育升学失败的学生。从中职的录取分数线来看,各地职业学校录取分数线都没有明确的最低标准,这导致职业教育的入学门槛很低;职业学校的学习风气也常常被诟病,社会偏见依然存在。此外,“差生教育”的观点也反映了职业教育文化课程较弱、知识性教学不强等现象。弱化知识内容会影响学生进阶课程的学习,尤其高等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思维能力。因此,要摆脱“差生教育”的标签,职业教育还需要加强知识性内容的教学。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教学生获得技能,更是促使其成长成才。当前社会关于职业教育的“教育性”内涵还缺乏实质性的理解,仍然是从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性”上来认识职业教育,这种观念不仅限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还会加深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裂痕,理性认识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是建设现代教育体系绕不开的话题。
二、职业教育“教育性”内涵的时代争议
职业教育的“教育性”问题,最初来源于“理论”和“实践”的二元对立。自由教育发展伊始就将职业教育排除在外,“学校”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语的“闲暇”,它是指接受教育的学生必须是“有闲”的,而不是“劳动”的。职业教育的教育性并非内生,它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后衍生出的新的价值内涵。
(一)民主主义与职业主义的分论
20世纪初,以普洛瑟为代表的职业主义阵营和以杜威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阵营对美国究竟应实行何种教育体制展开了争论。杜威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坚持“单轨制”教育,他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两类教育,教育的分轨会加剧阶层的分化,不符合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要求。杜威认为,民主社会的问题应在于消除教育上的二元论,要尽可能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这两种教育的结果彼此重叠[2]。与杜威主张不同,普洛瑟等人从社会效率的角度出发坚持“双轨制”教育,即认为职业教育要与普通教育分离,他认为教育的分化更有利于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和社会效率的提升[3],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主要目的具有本质的不同,其在教育方法和手段上也必然会存在分歧[4]。从二者比较来看,杜威希望教育能培养未来社会的改造者,教育的作用就是促进个体经验的不断改造,通过变革当前工业系统来促进形成新的工业社会,见表1。但是,他认为现有工业标准对人的发展具有局限性,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是通过间接的活动来发现受教育者真正的能力倾向,而不是让受教育者直接获得关于确定的、完全的职业准备[5]。普洛瑟等人认为,教育的过程就是为了职业,通过在学校里教授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为学生提供专门的职业活动和仿真的特殊训练,让学生毕业后能适应社会,并成为未来社会高效的生产者。
表1 民主主义与职业主义的职业教育观比较
观点内容 民主主义 职业主义
哲学基础 教育一元论 教育二元论
心理学基础 建构主义 行为主义
教育目标 培养社会改造者 适应社会发展者
教学组织 游戏、主动的作业 尽可能仿真的特殊训练
教育内容 广泛的活动 专门的职业活动
教育体制 单轨 分轨
职业与教育的关系 职业活动是教育过程的载体 通过教育获得职业
基于杜威的观点,他反对职业教育作为独立的教育存在,本质是在反对将职业教育视为技能训练。他指出,“过于注重机械化训练可能会导致个体丧失一些关键的认知和计划能力,从而在职业发展中失去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理智上的益处”[6]。他认为个体要改造社会,而不是顺应社会,教育不是“原封不动地永远延续社会现有工业秩序的工具”,而是“改革这种工业秩序的手段”[7]。职业训练将人限制在某一个固定岗位的做法限制了人的发展,同时也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僵化,不利于社会进步。
(二)杜威:教育要从分离走向整合
在民主主义思想诞生之前,教育内部一直存在着二元分割,如精神和物质的对立、理论和实践的分离、知识和行动的对立等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阶级分化严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教育属于上层阶级的特权,我国教育对象的平民化得益于孔子创设的“有教无类”思想,但教育的阶级性依然存在;在同时期的古希腊,教育也是奴隶主、贵族专有的特权,社会分工使得闲暇阶级的奴隶主可以在物质上无忧,这时的教育是一种身份象征,它与生产劳动脱离。劳动和技艺被看作是低贱的活动[8],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技师和劳动的人是无法践行美德的”[9]。
中世纪时期,职业的分化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内部的分离。伴随着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学校开始出现,这类学校专门培养手工业和商业所需要的职业人才,高深学问的研究逐渐转移到了大学,教育内部依据智力活动程度进行分化,此时的职业教育并不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除职业学校以外,这时的职业教育主要是以家庭作坊的“学徒模式”为主,并以师带徒的形式进行着技能学习和技艺传承。
现代社会的职业教育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决定力量。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客观外在条件[10]。在规模化的工业集团下,工人被当作机器的一部分,劳动过程被机器分解为一系列的简单步骤,工人只需要按照规则操作即可,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特点表现为适应性和服从性。但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与改进,工厂对技能人才的要求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对技能的精益化和对个人意识的创造性要求。
杜威意识到教育的割裂并不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教育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坚持育人的统一性。杜威将职业作为教育过程中的一种活动中介,他认为职业是一种兴趣,兴趣在教育中极其重要,如果儿童没有学习兴趣,则不可能激发儿童在这一工作上的潜力和积极性。他进一步指出,“现在的工业已经不再是习惯传下来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比较粗糙的程序了。工业方面的职业有了比过去更多的理智内容和文化修养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一种教育,使工人们了解他们职业的科学和社会基础,以及他们职业的意义”[11]。不然,工人会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基于此,杜威认为“社会效率的取得不是通过消极地限制个人的天赋能力,而是通过积极地利用个人的天赋能力,去做具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民主的准则要求我们发展学生的能力,使他们能选择自己的职业,在事业上发迹”[12]。美国的职业教育课程更具开放性,其课程设计是以人为中心,而非以产业为中心,他们注重个体选择职业的能力和注重发展教育在职业选择上的引导性功能,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要更具有包容性和迁移性。当前的职业教育不应只将固定的具体职业岗位作为人未来发展的方向,过度强调职业教育为职业做准备会忽视人的个性化发展。
三、职业教育“教育性”的价值逻辑与学理内涵
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社会的改造者而非顺应者,这一观点对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惯性具有很大的冲击力。职业教育不是简单地进行肢体训练的活动,而是需要学生去解决实际问题以及能够对新问题的出现提供解决策略。如果要按照这一思路探讨职业教育,则需要重新理解职业与教育的关系。
(一)职业与教育的逻辑关系
杜威非常重视职业和教育的关联性,他认为要“通过职业而教育”,职业和教育的关系是活动与过程的关系,职业是开展教育时所依赖的活动要素,职业活动是学校教育过程的载体,是课程的设计依据;而教育是职业活动的发生过程,教育通过职业活动来建立与工作世界的联系。职业教育要将课程教学内容转化为学生可以用于未来工作的直接或间接经验,教育的过程即经验获得的过程,而经验的形成依赖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依赖于个体实践的反思,学校要建立这样一种学习环境。
职业和教育亦是方向和结果的关系。职业作为人生活所遵循的方向,其不仅是为了生计这一目的,更长远的目标在于个人的成长发展,职业应当被视为引导学生规划未来发展、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因素。社会进步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发展的外部环境,在理想的社会环境下,职业教育的发展将更加关注人的“教育性”问题,并且关注培养具备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的技能人才。杜威认为,只学习特定的职业能力会使人缺乏社会的适应性[13],职业教育若将获得的职业能力看作目的本身,就会失去教育原本的目的。就像杜威认为的教育不是“为了未来生活做准备”,而是通过接触职业活动激发职业兴趣并获得自我成长的过程。职业教育不应当局限于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职业教育,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需求,发展自身能力,并在实践中实现个人价值。
(二)“教育性”的价值来源是基于生产模式演变中的技能人才需求变革
职业教育是否是一种狭隘的工具性教育?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已经发生了转变。产业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机器运作从一种遵从程序化的操作转移到一种脱离人为控制的主动工作模式,产品终端操作逐渐简单化,但是工业开发和产品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却在无限增加[14]。职业教育的“教育性”转向是由生产模式演变产生的技能人才需求变革。
技术创新是职业教育变革的动力因素。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活动中,生产方式主要以小规模的单件生产为主,工人主要通过技巧和经验的积累进行工艺制作,也不需要接受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只要通过师徒传授、做中学的方式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在传统粗放型的社会生产模式中,工厂对工人的要求是数量的要求而非技术的要求,工人工作任务的技术含量不高,只需要进行简单的程序操作即可,故企业非常关注工人是否遵循了生产过程的流程化和规范化,这也导致社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期望并不高,因为该时期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操作型技能人才。随着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精细化的生产作业对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的要求逐渐提高,人工智能改变了生产作业模式,人与机器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依存关系,而是一种交互式的合作关系,尤其智能化工业生产模式对人所需要的职业能力逐渐综合化和复杂化,生产的产品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技术工人需要具备灵活应变的能力,以便服务现代化、个性化、多样化的社会生产方式。在这一情境下,产品设计和产品生产环节开始从分离走向整合,工人不仅是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是产品设计的参与者,如技术工人也需要为产品的升级完善提供策略建议。因此,技术工人必须能从事多种专业化的工作,并在工作中不断深化职业技能。
(三)职业教育“教育性”的内涵探索
职业教育的传统定义认为“职业教育是传授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知识技能的教育”[15],这一定义的使用较为宽泛,但并未解释职业教育“教育性”的内涵。杜威指出,“理想的民主主义国家应当充分发展人的才能,来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16]。所谓“教育性”,就是要使人的天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并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改造社会。从这个意义来说,“教育性”应包含三个维度。
1.职业教育育人目标要转向更为完善的人格培养
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要落实到人的发展,要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依据学生的能力和学习规律组织教学活动。当前,职业教育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职业学校学生缺乏基本的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如学生对所从事的职业缺乏兴趣、不了解自己的特长优势、对未来职业发展规划迷茫等,很多学生的职业选择都是父母决定的,他们自己并不清楚学习该专业以后能做什么,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对社会、个体和组织应承担怎样的责任,缺乏职业认同感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目标感低、学习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对未来工作的自信心和坚定事业的决心不足。基于此,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要转向更为完善的人格培养,如加强对学生职业认同和职业责任意识的培养,要让学生意识到职业对自我发展的重要性,明晰自己的职业规划路径并意识到所从事职业的价值意义,以此才能让学生做到认可职业、热爱职业、忠于职业。
2.职业教育教学内容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理论知识
知识论视角认为职业教育有其独特的知识属性和价值,职业教育的知识内容并非完全是职业的和实践的,其也涉及高深的技术理论内容,职业教育类型化的前提就是要提升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让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转向更高层次的技术理论研究,培养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实践、运用实践,然而,理论和实践内容未能有效融合,导致理论类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对于技术实践活动而言,尽管抽象思维能力并不是技术实践活动本身的主要构成要素,但它是辅助学生理解技术活动操作原理的主要因素。尤其对复杂情境的问题而言,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知识内容不仅包括技术实践,还包括技术理论,技术理论知识是组成个人经验判断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此,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要使学生能够“知其所以然”,还必须要重视对技能理论知识的教学。
3.职业教育教学过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
实践与反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个体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经验需要通过反思这一思维活动的加工与改造。反思关注的是意义的重构[17],即个体通过回顾在实践活动中的行动表现来重构对事物的意义理解,反思的过程是重新赋予实践活动意义的过程,它能使个体挖掘出更多的深层次信息,以此重构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和理解,并将已有的经验与新的认知相结合,以完成新知识的内化。实践学习是一个不断建构、反思、重构经验知识的过程,实践和反思的结合能够培养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等。然而,职业教育教学在促进学生反思能力的形成上表现不佳,不少用人单位指出,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只能从事指令性的工作,他们有较强的执行力,但是在解决新问题的表现以及创新性上不如普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的教学应加强对学生实践反思能力的培养,通过反思性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建构反思思维。
四、职业教育“教育性”的实现路径
从“教育性”的意义而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都是为了充分发展人的才能、使人更好地享受生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大的区别并非在于智力和能力差别,而是类型差别,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培养的是不同类型的人才,无论是职业技术人才,还是科学研究者,其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教育的作用是充分发展人的才能,使每一个人都能有所成就并实现个人价值。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三条实现路径。
(一)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生涯指导
杜威指出,“理想的教育就是提供各种手段,满足这些独立的分门别类的兴趣”[18]。职业教育一直致力于帮助不适合智力赛道的学生构建一条职业发展路径,但这条路径应该面向多个就业选择,而不是限制学生的发展空间。职业学校的学生对职业的认知要远早于普通学校的学生,但是他们在职业认同和职业情感方面却没有较大进步,缺乏职业认同和职业热情会影响他们在未来工作中的态度、表现和工作回报。职业教育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职业生涯指导,这些指导应该涵盖学生个人身心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指导其对职业认知、职业责任感、职业认同感、职业道德等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加深个人与职业的关系与联系。第一,学校可以通过开设职业规划课程、职业测评指导等,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职业选择。第二,学校可以通过开展社团兴趣活动让学生与他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提升职业责任感。第三,要突出学生在参与校企合作项目中的主体性,增强学生在实习、实践学习活动中的参与感,让学生深入了解自己的职业选择,增强职业认同感。第四,学校要引导学生认识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如通过榜样宣传的方式增强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知。
(二)强化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知识性
基于当前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职业教育要培养具备解决问题能力、创造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从这一层面出发,职业教育必然要加强课程教学的知识性。然而这一想法的落实并非易事,因为大多数职业学校的文化基础普遍薄弱,学生对文化课程和理论课程的学习兴趣不强,若要提升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知识性,则必须对职业教育教学的知识内容进行重构。第一,专业理论课程的知识内容要重新设计,对于原理和概念性的抽象知识要结合具体的工作实践知识进行解释,同时中职与高职的专业理论课程要有区分度和衔接性。第二,公共基础课程的知识内容要适当精简和调整,尤其是数学课程的知识难度不宜过高,要考虑到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丰富语文、历史、政治等人文课程的知识内容,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此外,强化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知识性还需要借力职教高考,通过提升职教高考考试内容的知识性来迫使学生主动进行知识性的课程学习。
(三)加强学生在学习实践中的经验体验
加强学生在学习实践中的经验体验有助于学生反思能力的形成,职业学校要为学生提供能够获得经验的场所。杜威认为,教育的意义不在于为一个行业培训工人,而在于利用儿童的整个环境,给他们的学习提供动机和意义[19]。就实践学习的场所而言,职业学校应积极与企业合作搭建真实的工作场所和学习平台,关注学生在工作实践中的学习过程和结果,为学生提供实践经验的直接体验;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学会借助“经验”这个中间要素来构建知识在行动中的意义,如通过设计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考察、实验操作、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其中;另外,职业教育的课堂更应该是生成性的,波兰尼指出,“行家绝技也只能通过示范而不能通过技术规则来交流”[20]。因此,教师、学生与学习资源的互动尤为重要,个体职业能力的获得产生于其与环境互动的过程,教师要通过示范、引导、组织学生完成项目任务,让他们在项目中探索、合作和解决问题。
参 考 文 献
[1]杜连森.“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22-130.
[2][5][6][7][11][12][13][16][18]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68.329-330.329.335.332.132.153.11.131.264.
[3]DAVID F. LABAREE. How dewey lost: the victory of david snedden and social efficiency in the reform of American education[D].Stanford University, 2008:163.
[4]路宝利.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6(3):60-61.
[8]RUSSELL B.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M]. Simon and Schuster, 1946: 110.
[9]MOKYR J. The Lever of Riche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20.
[10]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74.
[14]乌尔里希·森德勒.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M].李现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22.
[15]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简编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613.
[17]RAELIN J A. A model of work-based learning[J].Organization Science, 1997(6):563-578.
[19]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M].何克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66.
[20]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81.
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al”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A Reflection Based on Dewey’s Ideas on Democracy Education
Yu Yun, Xu Guoqing
Abstrac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has put forward a higher dem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ccelerated the urgenc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t pres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not yet gotten rid of the social cognition of “skills education”“education of low-skilled talents” and “education of poor students”. As a type of education, the key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lies in understanding its educational attributes. Based on Dewey’s analysis, occupation should be a means of education, not an end. Education builds connections to the world of work through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nd stimulates an individual’s career interest for self-growth. When soc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deepen the contents of occup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quired by skilled talents also deepens. It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that is,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shifted to a more perfect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the teaching contents should be shifted to “know why it is true”,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reflection ability. Based on this,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wider range of career guidance, strengthen the knowledg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rse contents,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experience in learning and practice.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Dewey; Democratic ideology of education
Author" Yu Yun, PhD candidate of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 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Xu Guoqing, professor of the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in 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作者简介
余韵(1994- ),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上海,200062);徐国庆(1971- ),男,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职业教育教材管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我国职教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BJA210104),主持人: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