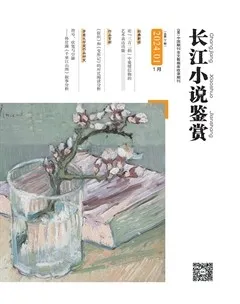《促织》和《变形记》的对比阅读分析
张兰
[摘 要] 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都叙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通过对比阅读分析,可加深对文本意蕴的理解,从叙事学的角度可看出两者在视角聚焦上的区别,不同的视角使文本各有侧重;从文本的具体细节入手,可分析出两者荒诞外壳下逻辑上的合情合理,人化为虫的情节具有荒诞色彩,但异化后的人物保留着原有性格,继续以人的思想开展故事,从逻辑上看完全合乎人性。结合时代背景与作者经历,两篇文本的人物命运都展示出高度重压下的绝望状态,《促织》表现了封建制度下皇权对普通民众的压迫,具有时代特征;《变形记》展示了传统家庭关系中父权的压迫,与卡夫卡本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具有个人色彩。
[关键词] 《促织》 《变形记》 对比阅读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1-0036-04
本文将《促织》与《变形记》进行对比阅读分析,通过文本细读探讨两篇文本的叙事视角、文本逻辑和主题意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为第三人称客观叙事,《促织》采用非聚焦型视角类型,着重于情节叙写,而《变形记》采用内聚焦型视角类型,通过主人公的见闻和思想,强调人物心理;披着“人化虫”的荒诞物质外壳,两篇文本中人物的行为逻辑都合情合理;《促织》中成名之子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异化究其根源都是权势压迫,前者是皇权,后者是父权,一喜一忧的不同结局从正反两面深刻展示出重压下的绝望个人。
一、客观叙事下的聚焦侧重
根据叙事文本中视野的限制程度,可将视角分为三大类型: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外聚焦型。《促织》和《变形记》都是在第三人称下展开的叙事,虽同为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但叙事视角有所不同。
《促织》采取的是无所不知的传统非聚集型视角类型。叙述者可以从所有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并且可以任意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叙述者知道的比任何一个人物都多。《促织》中,叙述者承担着旁观者的角色,将故事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交代得全面详细,并不在人物叙述上做出主观干预,这体现在文本的人物心理描写缺失而更侧重情节叙说上。
《促织》中,关于“变形”的描述一笔带过,仅用一句“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1]插入“人化为虫”的故事情节,文本对虫身人魂的变化缘由和过程只字未提,读者只能通过作者的客观描述来窥探和猜测文本的“空白部分”,即化为促织的人的行为逻辑和心理状态。
《促织》一文情节跌宕、起伏有致。围绕“促织”可梳理出故事情节,分别是:宫中崇尚促织、官吏征收促织、成名不敢敛户口且捕捉不到强壮的促织、驼背巫师画促织蛤蟆图、成名按图捉一善斗促织、成名之子无意放出促织后成濒死状态、成名复得促织、促织大战虫鸡、成名将促织进贡后喜得嘉赏。情节层层相扣,遵循因果,但并不俗套,轉折和悬念为故事增强趣味性。情节中大转折和小波澜相得益彰,处理得恰到好处。情节的转折大致体现在促织的得失。成名“早出暮归”地四处寻找促织,甚至“靡计不施”,费尽心力却只能找到劣弱之物,受罚之后成名“惟思自尽”,这时巫师的帮助令成名寻找到俊健的促织,极其爱护之时,又被成名之子无意放生,丢失促织的成名一家绝望之际又偶遇另一善斗促织,正是这一只促织令一家人命运发生逆转,让他们由危转安,由贫变贵。除此之外,悬念的设置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一是驼背巫师的占卜画,占卜带有奇幻色彩,看起来荒诞无稽,画中所示“青麻头伏于小山怪石下”[1]的景象是否真实可靠,这引起读者猜度,但紧接着成名便由此找寻到促织,此情节的设置为故事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二是看似“短小”“蠢若母鸡”[1]的促织却能战胜小虫、躲避鸡啄。好事者之虫与成名之促织的比斗是故事情节的高潮,无论从体型还是经验上,战无不胜的蟹壳青都比小而劣的促织更有胜利的可能性,但在少年的撩拨下,促织竟奋起反击,战胜了对手,大喜之际遭遇鸡啄,促织已在鸡爪之下,这时又来一反转,促织竟出现在鸡冠上。情节上处处有转折,这不仅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更增强了可读性与故事性。
内聚焦视角使得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叙述者虽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讲故事,但采用的却是故事中某个人物的视角,并将这一特定的视角范围贯穿作品始终。《变形记》整个叙事结构都围绕主人公格里高尔的感受与思想展开,故文本着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格里高尔变形后一直处于身心矛盾、内外交困的痛苦状态。虫形的身体使格里高尔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自由,他继续坚守着变形前供养家庭的职责,但并未意识到一只甲虫不可能去工作的客观事实,显然身心失调。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一直活在无助与孤独之中,工作上的常年疲劳给心理造成重压,家人的逐渐抛弃使得格里高尔在绝望中死去。从外部而言,格里高尔与社会的连接薄弱到只剩一扇窗户,家人对他的照料逐渐烦躁和敷衍,格里高尔的生存空间被打扰、被侵占;从内而言,格里高尔首先失去对自身生存基础即食物的兴趣,然后逐渐对家人的状态产生无所谓的心理,在情感上无所依托,这是一种无希望状态下的自我放弃。
运用内聚焦的第三人称叙事文在视野范围上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故事一经叙述者传达,则存在着两个主体,既有人物的感觉,又有叙述者的编排。正因讲述者的立足点不同,我们会对人物命运产生不同的感受。《变形记》中,卡夫卡通过对格里高尔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一个普通家庭里承担供养职责的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意在引起读者对其产生同情、怜爱等情绪。《变形记》里的视角聚焦在主人公格里高尔身上,但格里高尔死后,叙述并没有中断,这离不开叙事视角的扩充和叙述者的干预。小说以主人公死亡后家人的生活状态作结,叙述者即作者将视角跳出具体人物之外,客观地展示人物消亡后的场景,注入一种带讽刺意味的、不为聚焦人物所知的画外音。家庭曾经的供养者死后,他的家人却如释重负般怀着“新的梦想和良好意愿”[2]继续生活,这样的结局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或许是悲惨的,但对格里高尔来说却是美好的,他在家庭秩序中是职责的承担者,他对家人的关爱远超于对自我的关注,他死前“对家人怀着温情脉脉的回忆和爱意”,面对死亡他绝望却平静。
二、荒诞外壳下的合情合理
人幻化为动物这一现象显然是荒诞不经的,但化为动物的人的行为逻辑却合乎情理,两篇文本都为异化后的主人公保留了“人”的思想,使故事走向合乎人性,同时具备神秘感和真实性。
《促织》中,化为促织的是主人公之子,作者虽于文末才道明真相,但读者可从该促织的基本行为猜测其端倪。9岁孩童具有天真无邪、活泼贪玩的性格特征,自然地与文中成名所得促织的勇猛灵巧相互映照,成名之子化为促织后仍保留着孩童特征。首先,该促织“短小”,符合尚不成熟的年龄特征;其次,该促织在与好事者的虫比斗时灵活勇猛,更能机智地躲避鸡的啄食,在宫中也能击败蝴蝶、螳螂等身形比自己大许多的动物,不仅是因为促织有孩童的好动和人类的智慧,更因为成名子心怀帮助父亲的愿望,才能在比斗中屡屡获胜。“每闻琴瑟之声,则应声而舞”是奇异之事,一般虫物不能听懂音乐,更无法与之共鸣而舞,但将孩童灵魂代入之后便有了合理解释。由人而化的促织不仅保留着成名之子作为孩童的生理特征,更具有人化虫的一般心理过程,这从促织与蟹壳青的比斗中可以看出。在斗盆中的促织先是“伏不动,蠢若木鸡”[1],在少年大笑并撩拨虫须后“仍不动”,直到少年屡次笑而撩之后才“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1]。促织由呆到灵的行为转变,是人身蜕化虫身后由迷茫到适应的渐变过程,面对陌生的身体和危险的比斗,一个9岁的孩童先是茫然无措的,在被挑逗之后带着人类的愤怒奋而反击,并意识到了自身的处境,怀着救赎家人的愿望圆满完成以促织之身赢得统治阶级喜爱的任务。
《变形记》描述人物变形后的感受则更加细致真实。格里高尔变形后,生理上的各种感官都迅速发生变化:背“坚硬得像铁甲”,“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2],“细得可怜”的“许多条腿”,这样的变化使得格里高尔无法离开床,在尝试失败后,面对家人与秘书主任的询问,格里高尔说话的声音也发生变异,那是一种别人丝毫听不懂的“畜牲的声音”,他的味觉也发生变异,對新鲜的食物反感,而喜欢“不新鲜的、半腐烂的蔬菜”和“已经变成稠板结的白色调味汁”[2]。在生理结构上,格里高尔逐渐变成一只甲虫,脱离人类的基本生理特征,同时丧失语言能力,与其他人无法正常沟通与交流,在人际交往上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依靠听觉和视觉去感知外物。然而格里高尔的心理处境却无法与虫身的生理结构相适应,与化为促织的成名之子善斗以自救的行为完全不同,格里高尔对身体的变异是一种忽视、被迫接受的态度,面对自己忽然变形为一只动物的现象毫不关心,只想起床赶上火车以免延误工作,这符合一个被上司压榨并常年奔波劳累的人的心理,承担着养家职责的格里高尔变形后对即将失去工作的担忧、对甲虫身体的逐渐适应、对家庭前途的担忧,都是一个家庭伦理中承担供养责任的人的真实写照,作者关注个人的内心感受,着墨于化为虫后的格里高尔的所思所想,刻画了一个普通人消亡于家庭责任的普遍命运。
对于变形这一带有魔幻色彩的行为,卡夫卡没有交代缘由和过程,只用一句“一天清晨,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2]作为小说开端,直接交代格里高尔变形为甲壳虫这一事件,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保留着人的思想,但外形变异带来的处境和心理却真实可靠。“变形”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贯穿始终,它指涉的是人的一种特定状态:社会化功能的丢失。如果将变形这一动作置换为人的瘫痪,小说的逻辑仍然顺畅。
三、权势压迫下的绝望个人
《促织》和《变形记》都依托“人化为虫”的故事外壳,塑造了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典型人物,成名一家是封建制度下被皇权压迫的普通人,格里高尔是父权家庭关系中的牺牲品,两者的结局虽完全不同,但都导向了无法逃脱的个人命运,究其变形根源,都是高度的权势压迫下的产物,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存在,《促织》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变形记》具有独特的个人色彩。
《促织》的异化背景是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皇权不可违抗,个人的命运在封建政治制度的统治下完全被动,文本批判性地展现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的残酷现实。“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2],所言非虚。王世贞《王弇州史料》中收录了明宣宗朱瞻基给况钟的一道密诏:“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数少,多细小不堪,已敕他末后自运要一千个。敕至,你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可见皇帝喜促织而向地方官府施压。吕毖在《明朝小史》中载有一事:“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遴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比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自缢焉。”该粮长便是现实版的成名,没有蒲松龄的神话加工,在丢失促织后只得绝望自尽,这是普通人的命运。
《促织》故事的缘起与中心思想用作者的话讲便是“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在等级森严、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天子的一言一行必会由上而下地向官吏、百姓层层施加影响,用现代眼光回看当时,便知个人命运的卑微与绝望,蒲松龄对此进行了辛辣讽刺。促织是天子玩物,是皇权缩影,它能左右官场,分量更比人命重。成名一家的性命安危与官场前途无法依靠自身的学识与品德,只能无奈寄托于一只玩物身上,一只促织与一家人命紧紧关联,深刻反映了封建制度压迫下个人身处困境时的绝望与对命运的无奈。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同样承担着父权下伦理亲情的重压。传统的家庭关系中父亲的地位最高,父亲具有绝对的话语权,父亲的性格特征直接影响家庭关系。《变形记》中,父亲这一角色的暴戾便是压力的来源,他的每次出现都给格里高尔以重创。当变形后的格里高尔第一次出现在家人面前时,母亲在惊吓之中手慌脚乱,父亲却跺着脚拿着手杖驱赶格里高尔回房间,在父亲的猛力一推下,格里高尔“顿时满身鲜血淋漓”[2]。在母亲为格里高尔清扫房间时,发现画像上趴着的格里高尔后因晕倒而导致了一系列混乱,此时父亲却“认定格里高尔干了某种粗暴行为”[2],于是拿苹果扔向格里高尔,格里高尔被重重地击中、疼痛不已,在母亲的哀求下才勉强从父亲手中逃脱。面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母亲心怀疼惜,妹妹给予帮助,而父亲却以暴力相待,态度强势。客观来看,父亲是导致格里高尔重伤死亡的直接原因。
格里高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卡夫卡本人的映射。格里高尔是家庭的牺牲品,卡夫卡也一直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这在卡夫卡写给父亲的超级长信里得到验证。在这封写给“最亲爱的父亲”的长信中,卡夫卡对其父的性格特征、教育方式与对自己的不良影响做了种种说明。父亲易怒、严肃、自负,教育孩子时完全做不到言传身教,暴君似的父亲在卡夫卡身上用过的“语言手段”有“斥骂、威胁、讥讽、冷笑与奇怪的自责”,这使得卡夫卡从小就活在父亲巨大的阴影之中,对父亲敬爱而畏惧,在没有尊严、没有信心、没有关爱的世界里长大的卡夫卡软弱自卑。父亲身体上的强壮与精神上的统治权威使孱弱的卡夫卡习惯性地服从,父亲不断压制着卡夫卡的个性与思想,使得卡夫卡永远活在“奴隶”的世界里,既不能真正理解且亲近父親,不能摆脱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不良影响,也无法与不受限制而自由的外界相连接,这种孤独无助的处境和情绪与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如出一辙。
卡夫卡在《变形记》中以变形为媒介构想出一种心灵解脱的可能,他以变成甲虫的方式试图停止目前痛苦而矛盾的现实生活,可扭曲的家庭关系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格里高尔,他跟卡夫卡一样自卑、沉默、不满却习惯性地服从,服从着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劳苦生活,想要彻底改变这种关系显然是徒劳的,格里高尔最终的死去暗示着卡夫卡的结局,这一场自我斗争最后以保持原状告终。
《促织》和《变形记》虽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蕴,但都通过非现实的幻化变形展示现实的个人处境,蒲松龄笔下那个好玩物而轻人命的君主并非个例,而为家庭奔波牺牲的格里高尔更是现代社会的典型形象。中西文化虽各有侧重,但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个人内心的探索并无国别之差,两篇文本都为我们留下一个永恒的主题,即个人的存在与拯救。
参考文献
[1]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选[M].叶廷芳,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3] 卢今.聊斋志异名篇赏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4]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 刘畅.浅谈卡夫卡的“父亲情结”[J].文学教育,2018(13).
(特约编辑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