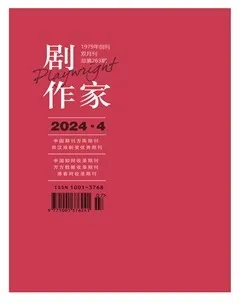爱尔兰文化身份的重构: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玛丽·琼斯戏剧《他口袋里的石头》初探
摘 要:北爱尔兰当代剧作家玛丽·琼斯的《他口袋里的石头》是一部表现文化帝国主义对爱尔兰文化入侵的戏剧作品,讲述了几名爱尔兰演员面对好莱坞电影制作对其语言、文化和身份的入侵进行反抗,最终实现身份重构的故事,反映了爱尔兰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民族身份的深入思考。本文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视角,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对爱尔兰的他者化建构造成的文化身份迷失,主角查理和杰克如何进行边缘化的逆袭,最终进行爱尔兰文化身份的重构。本研究呼吁对文化多样性、社会正义和本土知识的关注与尊重。
关键词:《他口袋里的石头》;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身份重构
引言
玛丽·琼斯是爱尔兰当代屡获殊荣的剧作家,先后获得贝尔法斯特艺术大奖评审团特别奖、2002年大英帝国勋章、晚间标准戏剧奖最佳西区喜剧奖。她还创立了一家女性戏剧公司“游览车剧院”(Charabanc Theatre Company),旨在解决女性缺乏演出角色的问题。她因作品中坚持的盎格鲁—爱尔兰文学悠久传统而被称为“爱尔兰人民的剧作家”。玛丽·琼斯的代表作有《他口袋里的石头》(Stones in His Pockets)、《十一月之夜》(A Night in November)、《盲人小提琴手》(The Blind Fiddler)等。《他口袋里的石头》是一部表现爱尔兰人在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所遭遇的身份重构问题,自1999年首演以来,一直广受好评,已在三十多个国家改编并上演。该作品曾获得《爱尔兰时报》剧院奖最佳剧作奖、奥利弗最佳新喜剧奖并荣获托尼奖三项提名。该剧以轻松诙谐的方式叙述了两名爱尔兰临时演员面对好莱坞电影制作入侵其村庄和文化的故事,深入探索了个体和社区在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压力时的复杂心理和行动策略。本文以后殖民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试图探讨文化身份、全球化霸权及个人与集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挣扎与重塑。
该剧的主角和叙述者查理·科隆和杰克·奎因是两名来自凯里郡的临时演员,他们被一部名为《寂静谷》(Quiet Valley)的好莱坞电影聘用,拍摄关于爱尔兰乡村爱情故事的场景。查理和杰克为能够参与这样一部大型电影项目感到兴奋不已,他们以为这一经历将成为人生中的转折点。然而,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两人逐渐意识到好莱坞团队对爱尔兰文化的浅薄理解和刻板印象。电影团队将爱尔兰乡村及其居民描绘成充满异国情调的背景,忽略了当地社区的真实生活和文化复杂性。这种文化的误读和曲解让查理和杰克感到不安,并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和参与这部电影的意义。而后,当地青年肖恩·哈金因为剧组成员的羞辱和误解而自杀,这一悲剧事件震撼了整个社区,也让查理和杰克深受触动,开始怀疑并质疑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方式及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在经历了一系列内心的挣扎和思考后,杰克和查理一起创作了剧本《他口袋里的石头》,用一个更真实、更尊重爱尔兰文化的视角重新讲述电影拍摄期间的故事。
一、“他者”的构建——爱尔兰文化身份的迷失
20世纪,英国结束了对爱尔兰长达四百年的统治,但在英语世界的主流舞台上,爱尔兰人已经被描绘成叛逆不驯、滑稽荒唐、没有文化等娱乐性十足的丑角形象。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以‘东方’与‘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1]P58。但实际上,东方主义者本质上忽略了东西方不同社会的复杂性,错误地将西方当作进步的缩影,而构成东方的,是人为塑造出的与西方相比所缺乏的特性,并非东方所具有的特性,进而构建了“东方”这一从属的“他者”。这种构建是权力和霸权的体现,有利于宣传有关东方的理念和知识,也便于殖民和帝国统治。在《他口袋里的石头》中,好莱坞制作团队的入侵体现了这种文化霸权的实践,尤其在语言、故事、土地及尊严的控制和践踏这四个方面。
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维持统治阶级权力的机制[2]P12。语言是文化身份最直接的标志之一,在其建构和维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剧中,杰克·奎因的爱尔兰口音不仅构建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也成了被他者化的工具。制作团队将这种口音视为一种异国情调的特色,仅在这种特色能为电影增添“地道性”时才予以欣赏。然而,这种欣赏是肤浅的,没有赋予其平等的尊重或价值的认识。饰演女主角的美国明星卡洛琳·乔瓦尼屡次向杰克抛出橄榄枝,仅仅是为了学习他的口音,以便于丰富自己的演出,来满足对爱尔兰的刻板印象,显现出对语言多样性和文化重要性的无视。除此之外,所有的临时演员都被要求表现得“更爱尔兰一些”[3]P28,只能听从剧组的安排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被迫按照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等级制度行事,在这个制度中,操英美口音的人处于上层,而操爱尔兰口音的人则处于底层。对语言的操控反映出文化帝国主义是如何利用文化工具来传播和强化统治文化,同时通过改变和压制当地声音来维护其叙事的主导地位的[2]P11。
查理·科隆的剧本惨遭拒绝,则体现了文化帝国主义控制别国叙事话语权的另一面。查理多次尝试将自己的剧本拿给导演看,却因剧本讲述的故事“不够吸引人,不是一个爱情故事”[3]P57而惨遭拒绝。好莱坞电影工业忽视本土历史和故事的做法,是文化霸权的直接体现,也是东方主义中“他者”叙事的延续。它将全球市场化置于真实表现之上,以牺牲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代价,延续着单一、简单化的文化形象。正如萨义德所阐述的,西方对东方的叙事控制不仅是对知识的掌控,也是权力的行使[1]P61。查理的故事被驳回,意味着代表爱尔兰声音的沉默,同时也强化了一种文化模式,即只有当地方故事迎合主流(西方)观众的期望和刻板印象时,它们才被允许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叙事权力的斗争不仅体现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谈判,也揭示了美国所主导的文化霸权如何通过控制话语权来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上的统治和侵略。
好莱坞电影摄制组不仅剥夺爱尔兰人的话语权,还征用爱尔兰的土地以演绎他们的故事,正如杰克所说“他们想要的不是我们,而是这片土地”[3]P15。在片场,临时演员们扮演着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在铲草皮;但在片场外,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土地归还到他们手中。70岁的米奇自认为是电影中唯一一个固定的临时演员,对于查理和杰克一开始“不敬业”的表现,以主人翁的姿态予以批评,但在他醉后闯入拍摄现场时,遭到了导演助理西蒙的恶语相向,威胁要将他赶出去,对此米奇无措道:“你们现在站着的土地曾属于我的曾祖父,现在却告诉我,我必须从这片土地上离开。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3]P54这一段关于文化身份和所有权的发问,展现了个体的精神困惑和差异化的内心挣扎,以及后殖民世界中复杂的文化互动。土地占有是文化入侵和身份消解的象征,好莱坞以其全球影响力,无视当地的文化和社会需求,单方面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爱尔兰,哪些部分值得被展示,爱尔兰的乡村被描绘成一个充满诗意和未经触碰的自然景观,好像是时间停滞的空间,只为等待好莱坞的镜头来赋予它意义。土地是爱尔兰人的寄托,是爱尔兰人所共同热爱的东西。爱尔兰人的土地被电影拍摄者所征用,却未能反映出爱尔兰人对土地的情感价值和文化意义。这种剥夺不仅是物理上的,更是一种文化场所的重构。通过这种方式,土地不再属于爱尔兰人,而是变成了全球文化消费的一部分。米奇的无助代表了爱尔兰农民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无力感和被边缘化的状态,他们的土地和传统被外来力量轻易地取走和改造。在这种外来压力下,土地不再只是生活的场所,而成为了文化抵抗和身份认同的战场。
这种对语言、故事和土地的掠夺使如米奇这样的老一辈爱尔兰人和像肖恩这样的年轻一代爱尔兰人感觉失去了尊严,并最终选择以死亡来进行无声和无奈的抗争。作为一名年轻的临时演员,肖恩小时候的梦想是拥有这片土地上最好的牛群“牛要比人有用多了,我想要变成一头牛,这样就不会被杀掉了。”[3]P41在失去土地出后,肖恩的生活没有了指望,面对临时演员一天40英镑报酬的诱惑,他终日想着去美国闯荡,失掉了对自己家乡的希望。他在电影制作过程中遭受了极大的心理打击,与女主角卡洛琳的搭话也使他被安保人员扔到街上,这令他感到羞辱万分,最终只能选择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和绝望——他把口袋里装满石头,走进水中自我沉没。肖恩试图通过这一行为在文化和个人层面上重申他的存在感,这是个体在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压力时的极端孤立和绝望。就像他幼时所喜爱的牛为了寻找更好的农场而迁徙,现实世界里的大批爱尔兰人越过大西洋,寻找所谓的应许之地,却发现“寂静谷”只是电影的一部分,是一场幻觉罢了。这些石头在他的行动中承载了超越物理重量的意义,变成了对被剥夺的土地和被忽视的文化身份的一种象征性抗议。
“身份认同”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4]P38。剧中失去了语言、故事、土地和尊严的爱尔兰人成为了“他者”——在文化帝国主义构建的叙事中被忽视和边缘化。随着经济的不断衰弱,他国价值观的入侵不断干扰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无法归依的窘迫和亟待恢复的焦虑心态。他们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自豪,却又明白自己在电影中并不重要,只是被当作道具来使用。他们在这样割裂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独有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的被剥夺和失去又令他们感到迷茫和痛苦。肖恩只能通过自杀这种方式,无声地表达对被侵占和重塑的文化领土的坚持和哀悼。
二、边缘化的逆袭——文化抵抗的双重路径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通过主流文化符号所书写的。在殖民统治时期,他们的民族记忆里始终存在“他者”的影子。因此,在后殖民的语境中,主流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认同并不为殖民主体所接受,这些地区的人民开始寻求自我民族身份。二战后的美国逐渐稳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政治文化、商业规范、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20世纪60年代的爱尔兰,在经历内战、独立、北爱冲突后,民族身份呈现出复杂多样化的趋势。政府尝试将国家经济由贸易保护转向自由开放,以期改变战后的经济停滞状态。然而,开放的背后是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在爱尔兰的长驱直入,在崇尚民主自治、社会契约和权力平衡且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美国,不少爱尔兰人在政治上取得了用武之地[5]P42。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则是人口的大量流失,在美国强大的吸引力之下,本该留在爱尔兰建设祖国的青年进退两难——留,心里始终难以割舍美国梦的吸引;走,则面临与民族文化身份的割裂。美国的这种“文化外交”政策作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式,影响着许多爱尔兰青年的未来选择。在剧中,占主导地位的好莱坞电影制作团队将其世界观和文化理解强加给当地民众,在这一场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中,促使像杰克和查理这样的个体通过不同的策略来维护和弘扬本土文化,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蚀。
杰克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在与查理讨论由于电影拍摄所造成的当地经济和社会混乱等现象时,他直言“外来者进来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我不喜欢这样”[3]P12。由于传播与控制信息的工具空前发展,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得以迅速扩张,深刻影响着全球文化景观。杰克对这种单向文化流动的敏锐认识和抵制行为,捍卫了真实的文化表现形式,还指出了娱乐商品化对当地传统的破坏。在与电影明星卡洛琳的首次独处中,他引用了谢默斯·希尼的诗歌《暴露》(Exposure),以表达自己对外来文化影响下个人身份的失落与文化同化的不满。作为一位在北爱尔兰长大的诗人,希尼的作品深受英爱两国文化冲突的影响。《暴露》这首诗主要指出了艺术家在文化危机中从事艺术创作的困难[6]P226。“错失了一生只有一次的凶兆,彗星那搏动的玫瑰”[3]P25这句诗象征了对未抓住机会的遗憾,也是杰克在美国创业失败,回到受好莱坞文化侵略的家乡的注解,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如何面对并抵抗外部对其文化身份的简化和剥夺。当他发现卡洛琳接近他只是为了模仿他的爱尔兰口音时,杰克感到被侮辱和利用,他拒绝了与卡洛琳的进一步接触。在电影制作人西蒙要求他去教授卡洛琳爱尔兰口音时,杰克的拒绝不仅是对个别要求的抗拒,而且是对整个好莱坞系统化的文化简化和商业化利用的挑战。杰克的拒绝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抗性阅读”[7]P151。在这种阅读中,他不接受外部强加的文化表达方式,而是坚持本土文化的独立性和复杂性。杰克的反抗根植于对社区和文化完整性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展示了他作为文化守护者的角色,以机智和深刻的地方认同感挑战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袭。杰克不仅是在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更是在挑战那些试图定义什么是“正宗”爱尔兰文化的外来力量。他的行为和选择是从边缘文化向中心发出的声音,反抗文化同化和文化霸权,是对外部力量剥削本地资源和劳动力的批判,也展现了他忠于社区及其传统的深情厚意。
而作为乐观主义者的查理,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在全球资本的排挤下,他赖以生存的小音像店被迫关门,他也随之失去其立身之所。查理这一经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叹,也是全球化经济和文化入侵影响当地爱尔兰社区的缩影。在这种情况下,查理选择成为电影的群众演员,试图在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过程中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面对好莱坞明星刻板化塑造爱尔兰角色的荒谬行为,查理的批评尖锐而直接:“呵呵……这里一半的美国人都在扮演爱尔兰人,而他们却说我是局外人。”[3]P13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全球文化流通中存在不平等,通常是西方传播和巩固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并将其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借此支配其他文化[7]P206。出于对爱尔兰故事和人物被外国演员及行业操纵的不满,查理一直积极推销着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让真实的爱尔兰故事得到展现,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来影响叙事。这实际上是在尝试打破这种不平等的文化流动,防止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他不断表达剧组对浅薄描绘爱尔兰生活的批评,讽刺道:“无所谓……有那么多电影明星扮演爱尔兰人,大家都以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么说话的。”[3]P14他认为,当地人只是被当作装饰品,而不是他们自己故事的讲述者。当殖民主体的话语权被剥夺,而被殖民地的人民应该有权利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故事,以反抗殖民主体的控制。后殖民时代的文学通过重新审视历史,并从被殖民者的视角重新解释故事,来挑战殖民时代的权力结构。查理质疑导演将他的悲剧故事改编为快乐结局的做法:“你怎么能指望一个溺水身亡的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呢?”[3]P57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扩张常常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商业化和标准化[8]P125,导演希望查理改变这个真实的故事以符合好莱坞的商业期望,但这样做就会削弱爱尔兰本土文化故事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查理的抗拒说明他不满足于作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是想积极地成为文化的生产者,塑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他的这一努力不仅保护了爱尔兰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也促使观众进行思考:故事的讲述者是谁?这些故事如何塑造大众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故事应该由谁来讲?
三、身份的重构——爱尔兰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作为美国电影工业象征的好莱坞,生产特效、科技、美国超级英雄并且贩卖美国梦,借此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诱导人们认为美国社会是理想社会,他们还自诩远离政治,追求娱乐至上,但实际上其中很多电影并未远离政治,甚至主动向政治靠拢,被称为“铁盒里的大使”[9]P47,而电影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文化全球化的无休止传播,也使爱尔兰文化身份的寻找和重构变得更加复杂而艰难。如果两个文化存在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那么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帝国主义,或是殖民主义,此时的载体不再是政治或者军事,而是文化[8]P123。
琼斯将故事设定在凯里郡,这是爱尔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岛,相对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保留了爱尔兰语和传统的爱尔兰音乐、歌曲和舞蹈。然而这样文化遗产丰富的地区,也已经被好莱坞、旅游业和全球化所破坏。琼斯严厉批评了这种文化威胁,她质疑和颠覆好莱坞传统工业模式和商业电影的套路,来寻求文化身份的重构之路。在剧本的一开始,查理和杰克是受到压迫的弱者,他们代表了爱尔兰历史上所经历的殖民统治和经济落后等现象,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社会排斥和失业问题的影响。相比之下,好莱坞电影剧组则拥有权力、财富和文化优势,可以随意地操纵和控制电影制作的过程。这种文化帝国主义代表的霸权地位和落后的乡村形象是两种对立的状态,二元对立的身份划分只会加剧不同社会之间的矛盾。在殖民话语中,身份的建构总牵涉到与自我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在重新创造这种“他者”。自我或“他者”的身份认同远非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知识的和政治的过程[10]P34。随着剧组的漠视和肖恩的离世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当地人不得不在遭受来自主流文化叙事的排斥和困境之间做出选择:是随波逐流以顺应维持这种窘境、生活在困惑中,抑或是勇敢地站起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为保护本土文化传统而进行积极的反抗。
杰克鼓励查理将自己剧本的主角由电影明星转为临时演员,以《他口袋里的石头》为题重新讲述这个故事。而爱尔兰身份的重构也通过语言、故事、土地和尊严这四个方面展开,展现了对外来文化的抵抗与对本土文化的维护。首先,语言是身份认同和文化抵抗的关键工具。好莱坞剧组试图让当地的群众演员说出更符合国际观众期待的“爱尔兰口音”,查理和杰克却利用这一机会反思和重申自己的语言真实性。他们都并未因好莱坞对爱尔兰口音的刻板印象而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而是更加坚定地强调真实的爱尔兰口音和表达方式。通过维护语言的纯正性来重构爱尔兰的文化身份,拒绝让其被外来文化标准化或简化。其次,故事的重构是爱尔兰人重夺叙事权的体现。在新的剧本中,焦点从好莱坞的光鲜亮丽转移到肖恩的真实生活经历上——一个充满挑战和困境的爱尔兰农村青年的故事。剧本开场描述了好莱坞制作组来到这片土地上,征求肖恩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电影拍摄的许可。这一转变不仅重构了故事的叙事焦点,还赋予了肖恩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尊严,改变了爱尔兰故事被外来文化主导的局面。这种叙事主体的转变,体现了以杰克和查理为代表的村民们重新获得消解殖民话语的勇气,借助好莱坞模式拍摄一部反好莱坞模式的电影,进而挑战和颠覆其固有的权威性。因此,拍摄行为从被动的、强加的任务转变为主动的、充满力量的自我身份和文化完整性的宣示。再次,土地在剧中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代表了爱尔兰人的文化归属感。杰克和查理通过重新讲述故事,强调土地和农业在爱尔兰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在他们的新剧本中,奶牛和农场作为重要的文化元素贯穿始终,剧本的开头和结尾,肖恩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草地上惬意生活的奶牛身上。因此,奶牛和土地不再是简单的观念符号,而是爱尔兰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是对于本土情感和传统的回归和拯救,展现了爱尔兰人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自信和坚定态度。最后,爱尔兰人通过主动掌握对自己故事和文化的控制权而获得尊严。查理也曾一度陷入绝望,考虑过自杀,但最终他选择了和杰克一起重写自己的剧本,以此表达对文化侵蚀的反抗和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肯定。在肖恩的葬礼上,杰克对前来吊唁、以此作秀宣传的卡洛琳发出尖锐的抨击,指责她的行为导致了肖恩的死亡。他愤怒地说道:“你甚至不认识他……就把他像垃圾一样扔出了酒吧!”[3]P48杰克的愤怒不仅揭示了外来文化的压迫对本土个体的毁灭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对抗,他从一个对明星顺从的角色转变为敢于直面质问入侵者的抗争者,体现了他身份的重构和对尊严的捍卫。他们拒绝好莱坞的模式,选择以真实的爱尔兰生活为题材,这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和对外部压迫的直接回应。通过这些努力,爱尔兰村民的身份也被重构为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主体,他们的生活、信仰和传统也被描绘为独特而美丽的,这与好莱坞对爱尔兰文化的肤浅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口袋里的石头》从根本上反思了爱尔兰当代社会面临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化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强调了文化的自主性和多样性。玛丽·琼斯的创作不仅是为了点明爱尔兰的现实挑战,也不单单是一场简单的文化反抗,更是在呼唤着对于一个民族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义。这种身份的重构不仅是对文化自信的回应,更是对社会正义和文化多样性的探索和呼吁。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认同的建构不应止步于表面的抗争,更要从内心深处找到自我,通过遵循平等、包容的文明观,优化叙事逻辑,创新叙事策略,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叙事体系,展现爱尔兰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达到文明共融、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
结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外来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社区和个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和挑战。而文化帝国主义无处不在,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社会,为当地居民带来新的困惑和身份危机。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自身身份迷失的困境,凯里郡的村民们对文化认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而当个体和社区在面对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化挑战时,以杰克和查理为首的主角选择通过维护爱尔兰文化和讲述本土故事来进行抵抗和反击,在重新审视历史、传统和价值观,以及积极参与文化生产来实现文化认同的自我觉醒和探索。如玛丽·琼斯自己所言,《他口袋里的石头》讲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两个普通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却抵制了好莱坞电影团队的强势输出,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故事。该剧不仅是一个爱尔兰人讲爱尔兰故事的故事,也是在一个全球化影响日益加深的世界中为保护和尊重本土文化而斗争的一个缩影。琼斯以其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创作,为爱尔兰及其他类似文化身份的重构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范例,即在面对外部文化冲击时,不是盲目地拒绝与排斥,而是要通过建构自身的叙事体系,坚持本土文化特色,实现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目标。当今世界存在文化帝国主义等隐含的殖民主义,只有当不同社会的身份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各国才能平等享有国际规则话语权,才能共同构筑和谐的多元文化。
参考文献:
[1]高曦:《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2]李永虎:《语言、历史与霸权: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建构》,《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Marie Jones. Stones in His Pockets amp; A Night in November: Two Plays, London: Nick Hern Books, 2000
[4]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5]王寅:《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崛起与融合》,《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
[6]谢默斯·希尼著,黄灿然译:《开垦地:诗选 1966—1969》,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7]约翰·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8]张小平:《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及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9]郑东超:《好莱坞电影与美国意识形态输出》,《国际传播》,2018年第13期
[10]李盛:《重审萨义德后殖民批评:再现“真实”与表征身份》,2023年第3期
(本研究系2023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山西地方戏曲对外译介及传播路径探究——以《赵氏孤儿》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3SJ093。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责任编辑 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