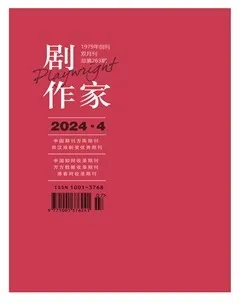新世纪经典剧目改编创作的再讨论
摘" 要:经典剧目的改编创作不只依托外在的人脉、优势和最高最好的展示平台,更应沉心静气多考虑原作品的时代背景,改编创作时应充分赋予原作品中人物角色以当时的历史阶级属性和时代特点,同时结合当前时代和新要求,借助前沿科学技术手段辅助呈现,使之焕发新的艺术魅力,让更多观众喜欢。
关键词:经典剧目、改编创作、时代特性、科技手段
经典剧目包括老戏、历史剧和其他艺术样式的改编创作,笔者认为大概有三种:一是整理旧时残缺不全的传统戏、历史剧。所谓“残缺不全”指因各种不详原因或外在的、内在的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剧目载体形式(如手稿、誊写本、记录簿、油印册和近当代音视频摄录、口述的存储介质等)客观上在流传中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内容遗失、毁损的情况,或受限于原作者精力不足、知识面窄,当初只创作了原作品部分内容,主观上存在先天性的内容欠缺,需要再补充创作完整。二是传统戏、历史剧情节陈旧,反映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当前时代不符合,或结构松散,或矛盾冲突设置凌乱,在全剧的谋篇布局上需要再梳理。三是有的传统戏、历史剧在舞台呈现时情节繁冗、内容庞大,表演时间拖沓过长,例如能演十天半月的连台本《火烧连营》《目连救母》等,需要改编缩减成两个小时左右的剧目;还有其他艺术样式在剧情进展和角色设置上,整体的铺垫时间漫长,例如产生一定市场影响力和有口碑、受追捧的电视连续剧、姊妹篇章的电影、动漫剧、网络游戏等,需要改编为适合舞台呈现的戏剧、戏曲。
概而言之,关于经典剧目、历史剧和其他艺术样式,如果要改编创作为适合新时代舞台呈现的戏剧、戏曲,那么剧作者动笔前就要充分考虑舞台演出的特点和当前时代的要求,力求在保持原作品风格的前提下重新架构、整合,再展开艺术创作,尤其强调恰如其分地赋予原作品一种新的主旨和价值影响力,自始至终要贯彻承上启下式的原则,以实现提升原作品精神内涵和审美意蕴的目的。
其实不论经典剧目,还是老戏的改编创作、现代戏新编,抑或其他艺术样式的电视剧、电影、动漫剧、网络游戏改编为舞台剧目,都属于舞台剧繁荣发展的措施范畴。早在1960年4月份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期间,关于舞台剧的繁荣发展,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就提出了“中央三并举”,“我们要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和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1]P13-15 。
时至今日,舞台剧的开拓创新和繁荣发展仍然是严峻不可回避的话题,全国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下辖的各院团在剧目生产上群策群力,在中央部委关于促进和推动舞台剧发展出台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的指导下,也都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做着相关的事情。例如从内容上注入新颖主题和表现形式的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改为全本剧《英台上坟》(京剧)、全本剧《梁祝哀史》(越剧)、全本剧《梁祝》(台湾新黄梅调)、全本剧《梁祝》(话剧),或改为折子戏《化蝶》《十八相送》;也有《窦娥冤》改为全本剧《六月雪》(粤剧)、同名剧《窦娥冤》(河北梆子、蒲剧),或改为折子戏《羊肚》《探监》《斩娥》;还有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改为同名全本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北京曲剧、黄梅戏、广东潮剧)、全本剧《皮秀英四告》(淮海戏),或改为折子戏《四告》(淮海戏);昆曲《十五贯》改为同名全本剧《十五贯》(秦腔、上党梆子),或改为折子戏《测字》等。甚至有的是不改内容,只截取精彩部份,这种样式在戏曲表现特色上突出单一性,有的以唱功为亮点,如淮海戏《四告》、京剧《打神告庙》,有的突出身段功法,如黄梅戏、粤剧《春草闯堂》,苗剧《挂画》,蒲仙戏《烤火》,京剧《三叉口》等。
除了上述三种方式和手段,实际上还有一种方式,主要以京剧为主。例如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这项文化工程在电视台比较常见,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经常推出这类作品。或是以新生代导演配以新颖前沿的视角进行改编创作,再辅以高科技手法搬上舞台,例如通过多媒体电脑制作全息影像,同时结合使用声光电等有效手段再现原作品内容。
无论经典剧目,老戏、历史剧目改编创作,还是其他艺术样式,终究都是为了推动戏剧艺术的繁荣发展,都是让原作品能够与时俱进焕发新的魅力,并借助前沿科技手段进行舞台呈现,使之让新生代的观众喜欢。这当中有的剧目就做得很成功,有的就只是哗众取宠,仅仅是期望值高,实则没有吃透原作品,仅仅依仗大牌的影响力炒作炫了一把……
例如中央广播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播出的大型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第九期是根据经典电视剧《渴望》改编的小话剧,成功之处,可谓亮点多多,不一而足。
原作品《渴望》在20世纪90年代初(1990年底)播出,讲述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青年人的爱情,反映了他们对爱情和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田沁鑫导演利用三个舞台和多重空间将人物故事穿插、交织在一起(即影视化手段处理环境切换),向大家重现了那个年代街头里弄普通生活中的不平凡,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揭示了人们即使面临生活的困境,也会渴望美好的人生。
这个小话剧创作之初,先天就具备了多个方面的成功要素:1.有很好的表现平台央视一套;2.演员是名流大咖,老戏骨;3.导演也是一流的导演;4.因为观众基本是中青年以上的,他们容易从这个作品中找到共鸣;5.改编的作品是曾经万人空巷的经典电视剧《渴望》。尤其开场时,那首悠扬动听的主题曲《渴望》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入到那个时代、那个情境中……就算是八零后乃至九零后和六零七零后坐在一起观赏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很容易进入到那种共鸣中,也许这就是当下所说的台上台下一起产生的“沉浸时体验”吧。
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由于上文说到改编创作前的优点太多,所以导演结合自身条件,同时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先天的优势,在重新架构这出浓缩版的小话剧时就存在一定的短板……
全剧开场由宋大成在路边为刘慧芳买一碗酸梅汤开始。一碗酸梅汤,寓意着人生的冷暖和酸甜苦辣咸,该剧内容表现的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戏,婚前宋大成对刘慧芳一见钟情,这种情感一直贯穿到宋大成和刘慧芳各自婚后,进而渲染放大了刘慧芳那种女性的外在柔弱和内心的强大。
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有喜怒哀乐,都充满着酸甜苦辣咸。原作品背景是60年代,而这个小话剧缺失那个时期的原生态滋味。
例如角色王沪生的发展轨迹没有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一种质感。我们知道,戏剧创作人物的特性是“人物内心要表现人物”,这里在王沪生的内心塑造上就有些不自然,好像他一生下来就是可怜巴巴的,其实最好在剧情中稍微补充一下人物背景。王沪生的父亲被抓坐牢,妈妈又重病卧床最终离世……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不顺心和打击,所以他本人才萎靡不振,更导致了以后的人生不完美、不幸福。后来的剧情走向也印证了这个处境——师父刘慧芳因为同情他的遭遇和他结婚了,但他仍然没有变得幸福,甚至发生了意料当中的婚后出轨,和自己婚前的女友肖竹心好上了。
我们知道旧情复燃在婚前仍属恋爱,是一种合理的爱的回归。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男女双方的婚后,或是任何一方的婚后,那就突破了伦理,变成了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突破了一般的广泛的认知尺度。这个王沪生倒好,行为暴露后,还明目张胆地和肖竹心继续有情有意地在一起,合作写论文的事,简直丢尽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
什么叫爱情?因为那个特殊年代,王沪生父亲被抓坐牢,母亲重病卧床不久又去世——刘慧芳就决定和王沪生走到一起。这个不叫爱情,应该称为刘慧芳对王沪生的一种同情,这种感情完全属于一种怜悯。拒绝美好的爱情,牺牲自身救赎对人生感到悲观绝望的王沪生,选择与其携手一辈子。若是放在过去来评判,像刘慧芳这样的女人是伟大的、高尚的。较之当今男女青年的择偶标准“高富帅、白富丽”而言,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傻”,因为刘慧芳没有选择从小到大一直对她好的那个宋大成。那个才叫真正的爱情,那种表现方式就是发生在现在这个新时代也不过时,仍然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爱情。
在小话剧中,刘慧芳因为要以自身去救赎悲痛不能自拔的王沪生就没有接受青梅竹马的爱情——以此来阐述善良,并放大善良这个主题,我认为是不太合适的,似乎以揭示一个可爱女人的遭遇更合适。
小话剧在舞台呈现上相对于原电视剧而言,许多情节都采用口述讲故事的方式来交代,没有进一步深入挖掘,只是简单的点到即止。这种表现人物角色感情的方式和现代舞台演出的方式手段雷同,当然由于时间短,可能局限于不能细致地交代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和那个时代的人对于婚姻和感情的表现方式,但是这些又是必须要考虑的,毕竟艺术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而不是脱离生活。这里的“生活”是指该作品塑造当时的人物必须要反映该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例如“70年代前后走,80年代手牵手,90年代搂着走”。为什么“70年代前后走”,那是很小心谨慎的,不会有现在这个时代的浪漫和直白的表达方式,不可能因为随便一句脱口而出的“我喜欢你”就接受了求婚,就表示两个人可以处对象,可以领证结婚。那个时代结婚,对男女双方的审查非常严格,如阶级成分、政治表现、祖宗三代背景调查等,男女双方如果有单位就要打报告,找领导批准,先开具介绍信,再去领取结婚申请书后才能办理结婚。没有单位的则要向生产大队、街道打报告,经领导同意走完这一切程序才能办理结婚证。那个时代如果自己喜欢某个人就随口而出表白的话,人家姑娘会骂你不正经,耍流氓,弄不好男方会刑拘的。
不容置否,刘慧芳是善良人物的代表,但是善良不等于软弱,不能说这种软弱就是可以被欺负的。小话剧在展开剧情时,用浓墨重彩围绕刘慧芳这个女性角色的外柔内刚来展开剧情——以这个角度叙述剧情,变成了善良是被欺负的解释。例如王沪生容不下那个弃婴(小芳)就和刘慧芳离婚,刘慧芳则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接受这个结果,于是自己默默地扛起了一个家,抚养弃婴和照顾公公……
我们常说创作剧本,尤其是改编创作,提倡充分尊重原作品风格和历史阶段属性,这不是嘴上唱的说的,无论怎么改编创作或是运用其他任何艺术样式,都不能剥离原作品中人物角色及发生矛盾的时代烙印和阶级属性特色。这种烙印和特色不仅是外在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同时还要反映在人物喜怒哀乐的内心性情上。
参考文献:
[1]傅谨:《新时代戏曲需要“新三并举”》,《中国京剧》,2023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姜艺艺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