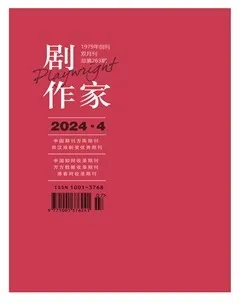《俄瑞斯忒亚》人物形象在当代欧洲的重塑
摘 要:《俄瑞斯忒亚》三部曲是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代表作,讲述的是一组发生在家族内部的连环凶杀。这一经典母题在后世被剧作家们不断改写。由于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两千多年后的当代剧作家们在改写时往往会对人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本文将以希腊剧作家卡班奈里斯的《晚餐》三部曲、波兰导演瓦里科夫斯基为主创的《阿波隆尼亚》和丹麦剧作家德拉戈尔的《美国的厄勒克特拉》三部作品为例,从英雄角色、女性角色和神明角色三方面探讨《俄瑞斯忒亚》中传统人物形象在当代欧洲的重塑。
关键词:俄瑞斯忒亚;改写;晚餐三部曲;阿波隆尼亚;美国的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亚》(Oresteia)是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代表作,也是现存最早的完整“三部曲”戏剧,其中包含《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复仇女神》①三部前后相互接续的作品,讲述了一组发生在阿特柔斯②家族内部的连环凶杀:在英雄时代,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亚十年后终于胜利归来,然而当晚就被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杀死,为当初被他献祭给神的长女伊菲革涅亚报仇;多年后他们的儿子俄瑞斯忒亚重回家乡,次女厄勒克特拉鼓动他杀死了母亲和母亲的情人埃癸斯托斯,以此为父报仇;俄瑞斯忒亚因此遭到了复仇女神的日夜纠缠,不得安宁,阿波罗指点他前往雅典娜神庙接受保护与审判。在雅典娜的主持下,法庭最终判他无罪,复仇女神也被说服,放下了仇怨,才最终给这场冤冤相报的家族悲剧画上了句点。
我们能够从该剧的结局安排中窥见埃斯库罗斯所秉承的观念。一方面,他使俄瑞斯忒亚最终被判无罪,说明他认为俄瑞斯忒亚杀母为父亲报仇比起克吕泰墨斯特拉杀夫为女儿报仇有着更高的正当性,父权应当高于母权,且俄瑞斯忒亚是一位英雄;另一方面,剧中的神明对人起着引领的作用,神意是不可违抗的,这又体现出埃斯库罗斯对“神圣正义”的虔敬。这些观念也融进了他对人物的刻画当中。
而到了两千多年后的当代,在全新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已然拥有了全新的思想。传统的英雄形象不再受到剧作家们青睐,埃斯库罗斯的父权思想与对众神的虔敬于当代人而言也已经显得陈旧。本文将以希腊剧作家卡班奈里斯的《晚餐》三部曲、波兰导演瓦里科夫斯基主创的《阿波隆尼亚》及丹麦剧作家德拉戈尔的《美国的厄勒克特拉》这三部改写剧作为例,结合原剧内容,从英雄角色、女性角色和神明角色三个方面探讨当代欧洲剧作家们对《俄瑞斯忒亚》中传统人物形象的重塑。
一、从英雄到“反英雄”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们不是神与人结合生下的后代,就是人类中的贵族,高贵的血统赋予了他们超凡的勇气和意志力,使他们能够完成常人做不到的事。他们代表着人类对于自身力量与道德的美好理想。古希腊悲剧多以英雄们对抗命运或权威定下的教条为主题,虽然结局通常是失败和死亡,但观众却能够被他们无所畏惧的崇高精神和意志所深深震撼。
《俄瑞斯忒亚》原剧中的俄瑞斯忒亚清楚地知道弑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不仅会遭到复仇女神的追逐——“疯狂和夜里出现的无端的恐惧会驱策我,困扰我”[1]P54,还会因为杀人者的不洁身份被城邦的一切公私事务排斥在外,无处可去——“不得参加调酒会饮,不得参加那保证友谊的灌奠……谁也不得接待我,谁也不得和我同住;最后,在我死去的时候,不受人尊重,无亲无友,遭受毁灭,凄惨地枯萎而死”[1]P54。但他最终还是选择顺应神的命令和自己所秉承的道德伦理观念复了仇。在后续的审判中,面对复仇女神的迫害他也能应对自如。显然,埃斯库罗斯是以塑造英雄的方式来塑造俄瑞斯忒亚的,古希腊时的观众会被这一角色的坚强意志所打动。
但随着时间来到20世纪、21世纪,资本主义和战争对人类的异化使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渐渐丧失了对人类文明的信心,文艺作品中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们越来越少,“反英雄”角色却越来越多。“反英雄”并不等同于“反派角色”。根据《西方文论关键词》中对“反英雄”的解释,“反英雄”是“‘英雄’的反面……是对传统理想中‘英雄人物’的解构,或者说是这些理想概念的破碎和丧失”[2]P103。在《俄瑞斯忒亚》的当代改写作品中,原剧中的英雄也大多变成了“反英雄”。
首先是“从虚幻中惊醒的人们”[2]P105,这类“反英雄”在最开始曾有着坚定的理想或价值观念,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们发现自己苦苦追求的东西是错误的、没有价值的,便经历了严重的崩溃。他们虽然得以惊醒,却往往因此陷入另一种恍惚的、行尸走肉般的状态。
原剧中的俄瑞斯忒亚在受到复仇女神追逐时仍能保持相对清醒,在法庭上还能积极为自己抗辩。而在卡班奈里斯的《晚餐》中,他是茫然无措的。他在弑母之后才看到了母亲写给自己的解释一切的信,这才知道母亲多年来忍受着怎样的痛苦,意识到他们对她的误解和仇恨是多么不公平。他的精神不堪重负,被往日记忆所压垮,时常无意识地念叨着信中的字句。该剧中没有明确的复仇女神的角色,折磨他的是他自己的心魔,而他无法战胜它。他也不再坚定相信自己没有罪,所以再也没有从这种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
《晚餐》中的厄勒克特拉也与俄瑞斯忒亚相似。虽然知道了真相,但母亲已死,自己手上所沾染的谋杀至亲的血也再难洗清,她将一直处于痛苦当中。姐弟二人最后死于多年后重回故乡的伊菲革涅亚③在酒中下的毒,她不忍看他们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随后她自己也服毒而亡。
《美国的厄勒克特拉》中的乔治·约翰逊也属于这一类反英雄。他对应《俄瑞斯忒亚》中的阿伽门农,但与原剧中为了战争不惜献祭亲生女儿的阿伽门农不同,乔治是一个秉承理想主义的外交官。他曾积极地尝试调解冲突,不顾妻子的阻拦前往巴格达去“创建和平”[3]P57,他希望奥德瑞(伊菲革涅亚)跟着他去伊拉克也只是因为希望有家人在身边支持他。
但奥德瑞在巴格达街头被试图复仇的愤怒平民射杀,这件事彻底击垮了他,“和解的努力不再有任何意味”“他被悲哀窒息了”,他的理想就像后来约翰·汤普森(埃癸斯托斯)讽刺他说的那样,“用和平和宽容建出的漂亮精美的空气宫殿”[3]P76因为一颗子弹而分崩离析。他最终在近似瘫痪的状态中被妻子乔安娜(克吕泰墨斯特拉)与约翰合谋杀死,并被假传是自杀。
当代剧作家们常用《俄瑞斯忒亚》原剧中相互杀戮的至亲来隐喻当今世界仍不断相互争斗、杀伐并且因此受苦的人们,但在《晚餐》中,卡班奈里斯没能为俄瑞斯忒亚与厄勒克特拉找到比死亡更好的结局;在《美国的厄勒克特拉》中,尽管德拉戈尔猛烈地抨击了借口挑起战争的美国,外交官乔治·汤普森的崩溃也意味着以外交达成和平的天真美好的愿景的破灭。从剧作家们各自对结局的安排来看,他们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态度是迷惘而悲观的。
另一类“反英雄”甚至比前一类坠得更深,他们的理想早就幻灭,已经不再相信积极的东西,他们“生活在不可理喻的世界上”,显得“卑微可笑”[2]P110。这类人物已然完全没有理性可言,他们在《西方文论关键词》的“反英雄”词条中被称作“荒原人”。
《阿波隆尼亚》中的俄瑞斯忒亚上场时,涂着紫红色的唇彩,戴着白色的假发,手指勾着发梢,言行都在模仿少女,给人强烈的怪诞感和不协调感。他向母亲揭露身份之后,跟随她走入内室,在挥刀刺向她时爆发出一阵阵儿童玩弄舌头般的怪声。在沙发上,他用大腿压住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身体,喘着粗气,透露着病态恋母的意味。母亲死后,他又将她装扮成妓女的样子,令她的尸体端坐在马桶上,自己则脱得只剩一条内裤,做着奇怪的直播。
这一位俄瑞斯忒亚在经历母杀父,而后自己又杀母的震荡之后,形象和精神都彻底扭曲了,在心灵遭到极端打击之后,他除了自毁之外很难再有出路。“反英雄”至此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阿波隆尼亚》开头时,伊菲革涅亚曾以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选择了自我牺牲,由此换取军队的顺利出航。但显然,这并没能导致任何好的结果——母亲杀死了父亲,而弟弟变得疯癫,又杀死了母亲。瓦里科夫斯基在原剧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样的牺牲是否有意义?该剧中另两条主线也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他没有在剧中给出答案,或者说他也处于困惑之中,因此无法给出答案。
《西方文论关键词》在“反英雄”词条的最后写道:“如在这样的荒诞后面还有余意的话,那只能是‘拯救’,由此相伴而来的则是‘价值’的重现和‘英雄’的再生。”[2]P111《阿波隆尼亚》中的俄瑞斯忒亚到了最后似乎在思维混乱中尚留存有一丝清醒,他向人们发问:“会有美好的东西在此次灾难过后留存下来吗?”[4]P75并以一把火终结了这病态的现实,或许结束这荒诞的一切也是一种勇气。而另一方面,未来改写《俄瑞斯忒亚》的剧作中是否会出现具有更新意义的当代“英雄”来回答人们如今的困惑。
二、从“坏女人”/“好女人”到立体的女性形象
在埃斯库罗斯生活的时代,古希腊人认可父权社会带来的“稳定”与“繁荣”,所以杀死丈夫、“颠覆”这一秩序的克吕泰墨斯特拉自然被认为是罪大恶极。对于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坏女人”,埃斯库罗斯在剧中对她进行了多番贬斥。
首先,城邦长老们不信任克吕泰墨斯特拉作为阿尔戈斯临时摄政者的能力。当她将希腊军队得胜的消息转告他们时,他们首先表现出怀疑,对她进行了多次的反问与确认,而这种不信任的根本原因竟然只是她是个女人。
而当克吕泰墨斯特拉表现出“超越女人”的地方来时,他们又将她称为“一个有男人气魄、盼望胜利的女人”[5]P209、“像个聪明又谨慎的男人”[5]P216。但这不是对她的恭维或者认可,而是在暗暗指责她的所作所为超过了女人被允许有的本分,僭越到了男人的领地当中。对她“男化”的形容都是在暗示她是一个“非正常”的人。
《俄瑞斯忒亚》中还充斥着对克吕泰墨斯特拉表现出的母性的不信任,作者总是暗示她在说谎欺骗。克吕泰墨斯特拉曾多次强调,她杀阿伽门农是为了给长女伊菲革涅亚报仇,但却被认为是借口;她担心阿伽门农出征在外时城邦发生叛乱,故而决定将俄瑞斯忒亚送去城邦盟友家中躲避,这一举动不被众人认为是对儿子的保护;她在得知俄瑞斯忒亚假传的“死讯”时为他哀叹,保姆也认为她的悲伤不过是假装的。
即使是在同为女性的角色那里,克吕泰墨斯特拉也没有得到正面的评价。卡珊德拉是被阿伽门农掳掠回阿尔戈斯做侍妾的,但她却仇恨地将克吕泰墨斯特拉形容为“一条两头蛇,或是一个住在石洞里的斯库拉(怪兽)”[5]P237、“两只脚的母狮子”[5]P238,即使克吕泰墨斯特拉如此珍爱她的长女,她仍被称作是“一个狂暴、恶魔似的母亲”[5]P237。
这些情节在当代观众眼中无疑是漏洞百出、倍显荒谬的。当代改写剧作家们在性别观念上选择与时俱进,他们重新审视原剧中存在的陈旧父权思想,对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厄勒克特拉都进行了更多的共情,最终赋予她们更丰富、更立体的形象。
对于卡班奈里斯而言,“克吕泰墨斯特拉是一个被误解、受冤屈的人”[6]P6。在他笔下,克吕泰墨斯特拉是温柔、坚忍的,甚至是博爱的。虽然和原剧中一样被旁人误解和污名化,但她始终都爱着自己的儿女,即使女儿对她充满仇恨,也会出言维护,她甚至能够主动同情丈夫的侍妾卡珊德拉的悲惨身世。她多年来都忍受着阿伽门农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暴力,因此她会爱上另一个更智慧、文雅的人就再正常不过了。像是为了回应原剧中保姆对她“虚假悲伤”的指控,卡班奈里斯还写到她记得孩子们小时候发生过的点点滴滴。
《阿波隆尼亚》中的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形象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在由瓦里科夫斯基导演的演出版本中,在伊菲革涅亚被献祭前,她一身无袖裙装,留着干练的黑色短发,是一位端庄优雅的王后,然而话语间充满对阿伽门农的不满和对女儿的不舍和悲痛。
而随着伊菲革涅亚被揪住头发拖下舞台,克吕泰墨斯特拉当着观众的面由工作人员脱下衣服,换上一顶柔顺的黑长假发,随后她掏出口红用力涂着,好几处都涂出了边界,显得更加狼狈不堪。此时她面容苍白,红唇如血,宛如一个被操纵的诡异人偶。她以这样一个顺从的形象迎接阿伽门农归国,就像是在父权压迫下失去了自我。在杀死丈夫之后,她终于歇斯底里地大喊出声,随后癫狂乱舞,与先前的隐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爆发式的宣泄非但不会让观众产生厌恶,反而拥有极强的感染力,能够唤起深深的同情。
到俄瑞斯忒亚上场时,克吕泰墨斯特拉没有再戴假发,露出了自己原有的金发,并改穿一身绿色裙装,先前夸张的口红也已经被擦掉,整体形象就像一位疲惫的苍老的母亲。俄瑞斯忒亚递给她一本安徒生的童话书,并假传了他自己的“死讯”。那一刻,克吕泰墨斯特身体略向前倾,凝滞了片刻。随后她翻开书,读起开篇的一则《母亲的故事》。俄瑞斯忒亚或许意在用故事里的慈母来讽刺她,但观众能感受到她的淡然的语调和平静的眼神之下是竭力压抑着的沉痛。
尽管《阿波隆尼亚》中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台词几乎都直接来源于埃斯库罗斯,但从为她设计的三种造型与表演方式来看,主创们对她也充满了同情与理解。
不过,当代改写剧作中的克吕泰墨斯特拉也不都是正面的。《美国的厄勒克特拉》中的乔安娜·约翰逊在爱女奥德瑞死后无法继续忍耐,于是与约翰·汤普森(埃奎斯托斯)合谋杀死了崩溃的丈夫。剧中的家庭晚宴上,乔安娜一直坚称是约翰主导了谋杀,直到最后约翰被艾丽莎(厄勒克特拉)冲动射杀,她才终于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撒了谎,其实是她给乔治的心脏注射了致命的一针。
而这样的角色形象之所以被当代观众所接受,是因为她并不刻板,她确实是自私的,但在说谎与谋杀的污点之外,她也有脆弱的一面。她深爱奥德瑞,也的确深爱过乔治,她怀念过去的美好生活,甚至最终还愿意为女儿顶罪。她的人物逻辑是通顺的,形象是丰满立体的。
对于厄勒克特拉,埃斯库罗斯在《俄瑞斯忒亚》原剧中几乎是比照着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反面来刻画的,克吕泰墨斯特拉是母亲,厄勒克特拉便不顾一切地拥护父权;克吕泰墨斯特拉作为摄政者,“僭越”到了男性的社会领域中,厄勒克特拉就在男主角俄瑞斯忒亚开始实施复仇后及时退出舞台,从而不违反古希腊人对女性不能在家庭和祭祀之外的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要求;克吕泰墨斯特拉是“坏女人”,厄勒克特拉就是“好女人”。作者通过这种对立,使得她自豪地宣称:“我的心比母亲的更纯洁,我的手也更虔敬。”[1]P50
而与原剧相反的是,改写剧作家会在剧中更强调二人的相似,并且根据这一点使她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深刻。
在卡班奈里斯的《晚餐》中,厄勒克特拉对弟妹们说“认识她的人,都说我很像她,说我有着她的特点!”曾经她是那么仇恨母亲,但在母亲死后,她反而需要透过自己的样貌来找寻母亲的痕迹。“我自己照着镜子就可以发现……我的眼睛变成了她的眼睛,我的嘴变成了她的嘴……”[7]P140使观众感到痛惜。
在原剧中,厄勒克特拉这一角色所思所想只有复仇,充满了工具属性。而当代剧作家在改写作品中丰富了她在筹谋复仇之外的生活,为她带来更立体的形象,使她不再只是刻板的“复仇之女”。
在《晚餐》中,卡班奈里斯也合理化了她如此狂热地崇拜父亲却仇恨母亲的原因,她不是父亲所期待的儿子,因此遭到冷落,但父亲却偏偏又对她说:“真是可惜啊,你若是男子,我便可以将迈锡尼留给你替我管理。”[7]P108于是她才那样怨恨母亲没有把自己生作男子,并且拼命地想要向父亲证明自己的价值。虽然与弟弟合谋杀母的行为极不理智,但她的过往遭遇是非常让人同情的。
当代剧作家们在对原剧的改写中使得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厄勒克特拉不再只是刻板扁平的“坏女人”或“好女人”,并且赋予她们更为丰富立体的形象,标志着当代人性别观念的进步。
三、从威严莫测到走下神坛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波战争中,希腊人战胜了强大的波斯侵略者,埃斯库罗斯因此笃信“神圣正义”——相信众神能够明辨善恶,他们会为正义的一方助阵,而对不义的一方实施严厉的惩罚。
这一概念在他的几乎所有戏剧中都有所体现,《俄瑞斯忒亚》三部曲更是其中典型。剧中有一句极富概括性的台词:“不义的行为才会产生更多的不义。”[5]P225为了惩罚在宴会上拐走主人妻子的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宙斯促成了特洛亚的毁灭;阿伽门农献祭女儿,复仇女神就协助克吕泰墨斯特拉完成了复仇④;克吕泰墨斯特拉和情夫谋害丈夫,阿波罗便发出命令要求俄瑞斯忒亚复仇——每一桩案件都能追溯到根源,体现着世界运行的准则。只要所行不义,就终有一天会遭到“神圣正义”的制裁。而如若遵循神所认定的“正义”行事,便会得到神的庇佑,比如俄瑞斯忒亚遵照指示完成复仇,他便得到了阿波罗和雅典娜两位神明的庇护,从而免于遭难。
在原剧中,以阿波罗和雅典娜为代表的众神作为超脱世俗世界的存在拥有着相当崇高的地位,他们在冥冥之中观察着人间的一切;为了不惹怒众神,导致灾难降诸己身,人类必须对神虔敬,谨言慎行。众神与“神圣正义”能从宗教层面震慑住当时的人,也敦促他们恪守伦理道德,起到了积极的指引作用。
然而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早已不再信仰古希腊多神教,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观念也不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众神随之逐渐跌落神坛,失去指引的力量。
在瓦里科夫斯基的《阿波隆尼亚》中,阿波罗与雅典娜被怪异化,他们画着极浓的妆容,举止浮夸,阿波罗几乎脱到全裸,雅典娜的穿着也是非常暴露性感,反倒是克吕泰墨斯特拉的阴魂显得心平气和,严肃庄重。
本身阿波罗所言“母亲只是新播种的胚胎的养育者,父亲是播种的一方;她只是保存着这苗裔”[1]P104以及雅典娜“我没有母亲”“除婚姻以外的所有事,男人都得我心;我完全属于我的父亲”[1]P107的论调在当代观众视角来看本就已经足够荒谬,当他们又以这样怪异的形象聚在线上会议室中对俄瑞斯忒亚的案件进行审判,就显得更加不可信了。瓦里科夫斯基等主创用荒诞的方式消解了神的崇高,表现出对埃斯库罗斯原剧中传统价值的怀疑和反思。
更进一步的是卡班奈里斯的《晚餐》中虽然有着亡者鬼魂与活人同席的超自然情节,但已不再有神的角色;德拉戈尔的《美国的厄勒克特拉》中也没有神出现。
当代改写剧作中古希腊天神信仰的衰减其实暗喻了现实中许多人对上帝信仰的怀疑乃至崩溃。当原本信仰的神不再可靠,人们发现世界并不遵循“善恶有报”的规律,也不再有一个会为人类指明方向的强大存在,此时人类便需要应对“神圣正义”缺失的问题。
卡班奈里斯为剧中人们寻求了另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指引,它强调爱和宽恕,带有东正教色彩。《晚餐》的舞台提示中写道:“外边悠悠传来圣诗班的歌声,听起来像是拜占庭教堂的音乐。”[7]P120圣歌前两次在剧中出现时,人物们都试图在回忆中重新面对自己一直回避并且不敢面对的往事的梦魇,最后一次出现则是死亡为他们解脱了痛苦。三次圣歌就好像灵魂的净化仪式,使这个家族的基调由血腥和杀戮归于宽恕与和解。
《阿波隆尼亚》中虽然还有神明角色,但如前文所述,他们的形象都变得怪异浮夸,他们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遭到质疑和反思,人们已经不会再信这种“神圣正义”能够继续指引前路。在下半场中,主创们更是通过丰富的拼贴素材提出了大屠杀中旁观者的麻木、人对动物的残忍、为了保住更多人的性命而捂死一个孩子是否能够原谅等许许多多有关人性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人”发出,也唯有人自己才能解答。主创们没有在剧中给出答案,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的自问,也是向观众的发问。
在德拉戈尔的《美国的厄勒克特拉》中,神的角色完全消失了,除了女主角乔安娜的噩梦之外剧中不曾出现任何能与超自然搭上边的元素,舞台上从头到尾都只有人,人是全然孤立无援的。剧中几位男性角色的名字都取自《圣经》,但他们也都被残酷的现实所摧毁。虽然这部戏的规定情境是夏天,但结局中母女二人却如冰雕般久久站立在窗边,深陷在对未来的惶恐不安与茫然无措中。这种不安与无措来自于作者,这一结局也是他向世界发出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无声之问。
在后两部剧中,剧作家们都没有对“神圣正义”消减后人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再给出明确的答案,战争这样有关人类整体的问题及造成的后果似乎无法仅靠宣扬爱与和解就能解决,他们更多地展现出失去向导后的思索与迷茫。
当代剧作家们积极地将《俄瑞斯忒亚》与全新的当代语境结合,对原剧中的传统人物形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颠覆,并摒除了其中如今已丧失意义的糟粕。此举不仅是在与古希腊传统进行“对话”,也是在源源不断地为这一古老母题注入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虽然对于女性角色的重塑体现出当代人性别观念的进步,但对于原本的英雄角色、神明角色的重塑,则更多反映出了当代欧洲剧作家们对于人类命运的迷惘与悲观。人类到底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或许不只是剧作家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一直思考下去。
注释:
① 罗念生所译古希腊戏剧选集中将这一部译为《报仇神》,但其中的“报仇神”角色现在一般被称为“复仇女神”,为了本文前后连贯,故一律改称“复仇女神”。
② 阿特柔斯为阿伽门农与墨涅拉俄斯之父,古希腊戏剧和相关文献一般都以“阿特柔斯家族”来指代阿伽门农、墨涅拉俄斯及他们的妻子与儿女们。
③ 《晚餐》延续了欧里庇得斯为《俄瑞斯忒亚》续写的情节:伊菲革涅亚被献祭时,阿尔忒弥斯女神于心不忍,便将她救下,让她成为陶里斯岛的祭司,多年后她被俄瑞斯忒亚找到并带回了故乡。
④ 《阿伽门农》第1504行前后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台词:“是那个古老的凶恶报冤鬼,为了向阿特柔斯,那残忍的宴客者报仇,假装这死人的妻子,把他这个大人杀来祭献,叫他赔偿孩子们的性命。”
参考文献:
[1]埃斯库罗斯、索福勒克斯等著,罗念生译;《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一种·古希腊碑铭体诗歌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4年
[2]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德拉戈尔等著,京不特译:《丹麦当代戏剧选》,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年
[4]姚佳南:《后现代语境下的戏剧文本拼贴——以〈阿波隆尼亚〉为例》,上海戏剧学院,2021年
[5]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著,罗念生译:《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勒克斯悲剧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艾琳·蒙特拉基著,熊之莺译:《当代希腊剧作法:现代剧场寻根与古代神话新生》,《戏剧艺术》,2019年第2期
[7]卡班奈里斯著,罗彤译:《奇迹大院:希腊剧戏剧家卡班奈里斯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20年
责任编辑 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