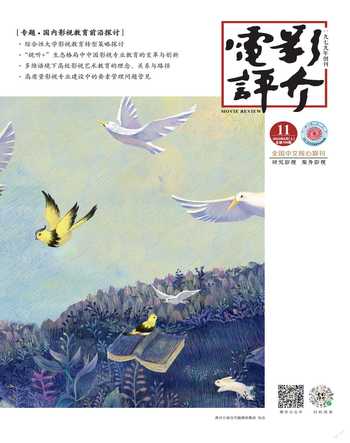《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从任侠到任侠电影
姜滨
“武士道”,是日本掌握七百年武家社会主导权的武士在战争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些习俗、惯例和常规,从镰仓时期始一直是日本武家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也一直是对日本民族精神及战斗道德的“统一”称谓,这种统一感源自新渡户稻造对其概念的西方化解析、本土性阐释始。而事实上,从江户时期开始,与武士道这种主流阶层道德、精神有了一种独立的平民伦理在逐渐形成、完善,那便是“任侠道”。秉持任侠道者虽历经数次身份变容,但被通称为“任侠”(通“仁侠”),他们是游离在体制之外的被疏离者、更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叛逆者。
任侠群体作为日本民间的暴力集团,虽有着苛刻的集团伦理,但毕竟赌徒、流氓等身份者杂其中,善行恶举皆存。这是真正的任侠团体存续样态,也使任侠道无法与作为主流伦理的武士道一较高下。二战后,武士道式微,任侠组织即黑道组织参与到社会秩序重建,黑道组织所秉持的任侠道开始受到瞩目并与契约社会的现代伦理相融合渗透。20世纪六十年代,任侠电影热潮席卷而来,为战败后失去精神家园的日本人构建了一个新的“理想乡”,将任侠道的义理与人情规则更仪式化、行为化:任侠电影中的侠客们抱持武士缺乏的肆意与人情,重恩守诺,“义”大于天。其内核的底层抗争意识唤起了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民众意志,甚至有替代武士道成為与现代社会秩序更自然共生的日本国民精神的趋向。
日本学者在对任侠、任侠道伦理及任侠电影进行溯源、关联研究时发现,日本任侠的“大发展”在江户时期,恰正值中国《水浒传》传入并盛行之时。从《水浒传》文本传入日本始,叛逆者们开始逐渐集团化,虽有反体制性质却期待拥有“正统”身份,强化平辈之间的兄弟之“义”,江户时期开始流行的牡丹、龙等“定番”刺青与水浒人物鲁智深、史进密切关联等细节表征也呈现出《水浒传》的现实映射。而任侠电影,则将这种纠葛具象化为侠客们悲怆的执念,以其反现代、反欧化的时代感呈现大众诉求。从文本到影像,中国的《水浒传》在日本形成了独特的传播脉络与接受样态。
一、文本传播:集团化与伦理建构
(一)从“梁山好汉”到日本的“叛逆者”
《水浒传》在江户时期传入日本。自汉文原本在1624年传入日本后,随着各版日文译本发行,传播范围开始扩大。冈岛冠山①于1757年翻译的《通俗忠义水浒传》是第一部《水浒传》日译本,拉开了《水浒传》在日本文坛与平民间的传播序幕。而江户时代中期开始,日本本土作家根据《水浒传》题材、风格、表现技巧,进行的日本本国历史故事“嫁接”的翻改作品也纷至沓来,如《本朝水浒传》《日本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后主要的翻译版本有曲亭马琴、高井兰山编译本,葛饰北斋插图本以及歌川国芳所绘《通俗水浒传》等。
“一部《水浒传》,不但使下层百姓爱不释手,广为流播,而且从中还寄托了他们全部的希望。他们对梁山伯好汉津津乐道,对绿林豪杰百般仰慕,他们也只有在侠客之书中才能求得心理平衡。”[1]面对独占暴力特权的武士阶层,水浒英雄们快意恩仇的行为、反抗强权渴望正统的诉求,无一不对日本下层百姓形成吸引与指喻。可以说,《水浒传》的传播以更生动的形式引发了与武士阶级矛盾激化的日本平民的“共鸣”,同时,也如同梁山好汉们所呈现的时代性一般,“其所反映的还是根植于百姓中的信仰性的思想意识。”[2]似乎,在梁山好汉的伦理秩序中,某种与下层百姓身份相去甚远的武士道德相悖的信仰力量正在衍生。“总体上讲,水浒思想是反体制的,最明显的就是对于儒教的无视。全书很早就出场的知识分子——落第秀才王伦,被林冲骂作‘笑里藏刀、言清行浊的人。这并非是王伦一人,而是普遍对于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3]。而这种对于知识阶层的藐视便恰恰是下层百姓内心杂糅着抗争与自卑等诸多情绪的体现。
随着《水浒传》在平民百姓中的广泛传播,江户市井帮派的组织化特征愈发明显,朝不保夕的下级武士、侠客们集结成群,在与幕府的对抗与妥协中逐渐壮大了力量。由室町时代至战国末期战乱中滋生的下级武士群的统领者“歌舞伎者”①,承续发展出了具有强大集团化力量的民间帮派组织“町奴”②,与武家治下的“旗本奴”③相对立,重义信诺、扶弱济贫。著名的日本大侠客幡随院长兵卫即为当时町奴的领袖,其为平民利益而谋划、隐忍乃至付出生命的故事广为流传。日本经典时代剧作品《大江户五人男》(1951)就生动刻画出这样的人物像。江户时代中后期,町奴在被利用与剿杀中消亡,具有一定社会服务性质的平民“町火消”④形成规模,在救火职能背后,是叛逆者们自町奴传承的保护弱者的道义、反体制基因以及对于集团化发展的生存认知。“从江户时代以来被大众尊崇的任侠,最鲜明的特征是集结起来反抗强权、讲义气、锄强扶弱。”[4]而《水浒传》则是一本生动的现实“教科书”,“水浒传的英雄们是用暴力抗争秩序的虚妄、揭掉制度遮羞布的神人”[5]。
《水浒传》与《游侠列传》、唐传奇一脉相承。但本质性的不同在于“秘密结社”,以及其作为集团组织鲜明的反体制性质。唐传奇的侠客一般是隐于山林,具有鲜明的个体性。而《水浒传》的集体性、组织性给予江户时代的日本平民领袖们以启示:集结起来才有更强大的力量,才能获取更多的生存砝码及利益,甚至可能具有跻身权力阶层的资格。当然,结社还需要维系其稳固发展的内部伦理,且需要与权力阶层道德的武士道形成明确的区分。
(二)从武士道的“忠”到任侠道的“义”
武士道精神源自于中国的儒家精神。儒家精神推崇仁义为先,而武士道则强调以“忠”为核心的“战斗者的道德”,形成了对中国儒家精神的本土继承与发展。汤重南先生曾对武士道有如下表述:“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6]“忠”一直是武士道中的重要德目,是维系武家封建社会主从关系的道德基础。从幕府早期以君恩换武士献身的实践道德,到江户时代,主君要求武士绝对无条件尽忠的单方面道德规范,其道德行为与观念发生本质的变化,同时也形成了武士道最鲜明的伦理特质。
武士道不仅是日本武家权力阶层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的秩序伦理束约,也影响着日本的平民。而《水浒传》的传入,为有着叛逆精神的平民领袖们开启了一种新的集团化建构和伦理建构的可能性:他们大多有过犯罪“前科”,是社会的疏离者,显然没有为主家尽忠的“资格”,所谓武士道对于他们而言可望而不可即。而《水浒传》中宋江们所组建的兄弟联盟是志同道合者齐聚,“哥弟相称、不分贵贱”,这种平辈之间的关系显然更适配于当时的平民领袖们,水浒英雄们所秉持的“义”也契合新集团伦理建构的根本需求。虽然宋江的“就职”誓词表达出“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忠义不“分家”的主旨,但对于宋江之外的绝大多数好汉而言,他们早已没有了效忠的目标。“义”才应是维系彼此及组织架构的最强纽带,“义”与“忠”不是排序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的彻底置换。“秘密结社的成员,从主流社会的角度去看,都是失败者。但从其团体的角度看,被选择的成员都是精英。梁山集团也被描写成了类似秘密结社的组织。支撑这个集团的便是一个‘义字。众好汉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而是因义结盟的异姓兄弟。……在义字面前,一切世俗的价值观都是无效的。”[7]
这样的价值观同样源自于儒家教义,但因及其先后关系而暧昧地产生本土“父子”般的衍生关联,既表现出了日本平民對于武士阶层的复杂情感,又以新的“战斗者的道德”来进行反体制者们的束约。这种新的侠客集团伦理被称为“任侠道”。以平辈之间的“义”来对抗武士道下对上的“忠”,而维系自身利益的方式则是同样的行使暴力。
另一方面,《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人结成兄弟联盟,在日本传播时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本土认同典型,其排序前四的人是“无良”(不良)僧侣鲁智深、浪荡公子史进、憨直“阿呆”(傻)李逵、坚忍教头林冲。[8]从四人的性格塑造可以看出其代表性:排名第一的鲁智深是彻底的反抗者,兼具侠客的仁义勇武,又有僧侣的达观朗旷,看透世事与人性;史进从不务正业的浪荡少年到驰骋沙场的战士,是典型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叛逆者代表;李逵是心粗胆大却率直忠诚,憨直若愚的农民形象;而林冲本在“体制内”,一直委屈求全百般忍耐,最终被逼上梁山。这四人是不同身份与阶层的代表,契合了当时日本人的情感与道德审美,推动了《水浒传》在日本的多维度传播。江户侠客也被认为是后世日本侠客的原点:“他们(水浒英雄)在故事中张扬的反权力性精神,强烈的认同诉求,应该就是我国任侠性格形成的原点。”[9]而鲁智深、史进、燕青、张顺等人标志性的刺青更代表了一种“无赖”的“风流”被当时的侠客所推崇。牡丹、龙等刺青自此流行,后来又增加了唐狮子、虎、豹、鹰、鲤鱼等中国鸟兽图案,呈现出《水浒传》乃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江户侠客之间密切的影响性关联。
二、影像接受:叛逆者的“野望”与悲情
(一)“野望”:任侠道崛起,理想的家国
日语中有“野望”一词,表述的是某种野心与欲望并存的情绪、心理状态。以此来指喻二战后的“任侠”①,较为简洁精辟。
二战前,武士道作为武士的伦理道德、尚武精神甚至代表了日本民族的优秀精神。而事实上,“武士道”一词虽在江户时代已经出现,但仅为表示武士道德说法中的一种。旅顺大屠杀②事件发酵后,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撰《武士道》(1899)一书,利用“武士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行径辩护,并认为“武士道”与西方的“骑士精神”相似,杀人的行为只是履行了他们的最高道德。后来日本政府的御用文人井上哲次郎则大力推动武士道的传播,使其更好地为军国主义服务。“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在力求摆脱外来民族危机的同时,采取了‘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对外政策,走上了侵略亚洲邻国的军国主义道路。为此,在国内积极推行‘全民皆兵制度和‘忠君爱国教育”。[10]由此可获悉,武士道作为日本最高道德、精神,是被面向国外的“包装”及以侵略为目的的国内推行所形成的复合性结果。
二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所接受的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国民教育遭受了本质性的质疑,这个时期的日本人,需要有新的、能够收拾动荡人心的精神家园。任侠精神,即任侠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强调其江户时代特质为核心进行传播,而宣扬它的媒介,是电影。
任侠电影兴起前日本以武士、旅人的影片都属于时代剧范畴,二战败战后美国统治期间被限额制作,到了50年代后才开始逐渐恢复。任侠电影这一特定类型的确立始于东映电影公司③的《人生剧场飞车角》(沢岛忠,1963),讲述的虽然是现代黑道故事,呈现的却是日本侠客们与代表西方以及屈从于西方的本国恶势力之间的“战争”,在暴力与暴力的对决与侠客们的悲情胜利中,盛赞了护卫传统、反强权、弱者救济的江户侠义精神。之后的近十年,以东映为首的六大电影公司纷纷投入“量产化”制作,不仅迅速替代了以武士故事为主的时代剧,更促成了日本电影史上一个奇迹的发生:任侠电影这一类型片的隆盛,延续了上一个十年的黑泽明、沟口健二等大师级电影创作的辉煌,将日本电影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又延长了十年。
在任侠电影建构的虚拟世界中,日本人仿佛又回到了江户那个“伟大”时代,有一批侠客们为护卫传统的规则与秩序而战,这种规则与秩序即“任侠道”。相较于被质疑乃至于被否定的武士道,任侠道所秉持的义理与人情,更贴近现实与人心;在尴尬的战后时代,重新架设起现代与传统、当下与历史的桥梁。日本人也需要这样的“沉浸”:电影中侠客们充满仪式感的兄弟结义的排序与诺言,刺青的忍耐力试炼①,以命相偿的恩情义理以及过失惩罚的切指、破门②等,复现出了一个有着强大精神信仰的理想家国,而这样的理想家国背后,是江户豪侠们所书写的传奇,是梁山好汉们的光影浮掠。
(二)悲情:叛逆者之殇,“侠”的宿命
二战前,日本的任侠组织与时代、社会的关联度并未有多凸显,一直与体制秩序之间有着隐约的分界线、保持着行为的克制以及距离的安全,在“普通与跳脱之间的境界线反映着时代的道德性。”[11]换而言之,任侠道的存在并未撼动武士道作为国家思想的主体地位,但二战后的时势造就了任侠电影兴行的条件与环境,也以媒介之力促成了大众对任侠道的广泛认知。
任侠电影以现代黑道的传统与西化的对立表现为中心,正如电影评论家四方田犬彦所表述的“以已经丧失殆尽的江湖义气为前提,寻找对传统共同体的归属感,这种意识将为人们带来无上的乌托邦快意。这种对前现代的怀旧不可能出现在战前或战后,只有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60年代,它才作为一种倒错的情感被诱发出来。”[12]电影中塑造的是日本“失乐园”中与现代契约制度抗争的传统英雄形象,他们与西方所代表的伦理秩序格格不入,他们如同《水浒传》中大篇幅呈现的鲁智深、林冲、武松、杨雄等英雄的故事一般,忍无可忍后在反抗中爆发;他们的作风更像江户时代的侠客,如鹤田浩二所诠释的幡随院长兵卫般的“儒侠”,与强权者斗争,救济弱者;他们是正义的游历“侍”者,如高仓健所演绎的孤高“一匹狼”,那是国定忠治、清水次郎长,在旅途中快意恩仇。[13]同时,也正是高仓健、鹤田浩二、岚宽寿郎、若山富三郎、藤纯子等这些自身便带有“复古”气质的演员们,以《日本侠客传》《昭和残侠传》《绯牡丹博徒》等系列作品诠释出了符合传统侠客审美、为所坚守的价值观而战的成功形象,使任侠电影有了重要的标志性系谱并得以类型化发展。
任侠电影盛行的时期,也许是日本政治与日常最为密切、大众自我意识也较为高扬的时代。战争创伤似乎被高速发展的经济“疗愈”,恢复为正常国家的民众意志越来越强烈。文字、绘画、影像等诸多的传播媒介充满了抗争的热情,抗争所针对的实体,是战败后被操控的日本政府,是其背后代表着“现代”的西方力量。日本人对于传统服饰、文化乃至于任何二战前拥有的本土特质的眷顾,无一不是在传达这种意志。“反体制”成为时代的流行语,自江户时代一直为体制所不容的任侠组织,在所谓民主社会的旗帜下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而其自身所承传的反动特质,反而形成了一种时尚的风向。任侠电影正是反映了现实中这些无法理清的因果。“体制=恶”“反体制=善”等的关系构图与江户时代的水浒英雄效仿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对权力的反抗,对暴力的肯定以及刚勇男子之间的结义情谊更直接将任侠组织作为黑社会组织的本质掩盖,最后与体制博弈败北的结末更凸显出“侠”的非主流悲情。
可以说,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任侠组织一直所重复的现实命运,以及影像中建构起“理想乡”复又破灭的虚构故事,都如同水浒英雄般难逃宿命的安排。这种悲情,最为触动日本人,而且是全民性的。在任侠电影近乎苛刻的规则与仪式中,英雄人物所迎接的终章往往是身陷囹圄、乃至于死亡;侵略战争的最后败北,及被美国统治数年的过往,在任侠电影最终人物平静地将双手伸向镣铐的情节设定中,共情便产生了。而以电影为媒介达成被人们盛赞结果的任侠道,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对自称任侠的黑道组织统一定位为“暴力团”后,逐渐消弭在日本和平社会的文化包装中。但任侠道的种种集团仪式与伦理,却通过任侠电影的影像叙事与现代日本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秩序形成了潜移默化的融合,曾经的兄弟之间的“义”,已经形成了广泛意义上的道理与礼仪,甚至简化为“借”与“偿还”这样带着责任、诺言同时又兼具距离、顾虑的人间情感。
结语
江户时代是日本积极消化中国文化并进行本土文化建构的重要时期,由上至下对于汉学的重视、商贾往来积极传入中国的“时尚”文作、艺作、手作等,都形成了对当时的社会风尚、文化观、价值观等的重要影响。《水浒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江户的叛逆者们提供了风流豪气、重义信诺男子的“模版”,并辅以集团化发展、伦理建构等的醍醐“指示”,使江户侠客成为后续日本任侠及任侠组织的原点。这是现实中的《水浒传》传播形态。
而二战后的任侠电影,其主角是尊崇任侠道的叛逆者及其组织,充满了理想色彩,封建王朝的“忠”与“义”二者的矛盾在虚构的影像中得到纾解。以道德置换政治,以向善、守诺等形成对任侠精神的易辨析行为解读。不仅融入日本社会的政治变革、文化博弈乃至于经济转型的社会动态,更于内在勾勒出日本人的现代集团伦理与国民精神,映射出动荡的时代与人心。这是任侠电影的策略,期许任侠道在武士道式微背景下能够树立起普通人皆可效仿的秩序与伦理,也是于虚构影像中《水浒传》风流美学的接受与延展。
当然,日本的侠客作为叛逆者逐渐趋向集团化发展,建构起模仿武士道的内部伦理,以及后续任侠电影的量产,不能完全归功于《水浒传》这一本作品。而是在传入后因其特定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与精神内涵所形成的本土“水浒”题材融合与延展,又呼应了日本封建制度下不甘心被奴役、被统治的平民的强烈诉求,才形成从文本到影像,从现实到虚幻的数百年的特质传播与接受脉络。《水浒传》早已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参考文献:
[1]陈宝良.无籍之徒[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569.
[2][3][7][日]宫崎市定.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M].赵力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113,116.
[4][日]青山栄,斯波司.やくざ映画とその時代[M].东京:筑摩书房,1998:27.
[5][日]松田修.刺青·性·死―逆光の日本美[M].東京:平凡社,1972:55.
[6]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庞杂的精神糟粕[ J ].日本学刊,2005(04):7-19.
[8][9][日]中本征利.任侠のエトス[M].东京:劲草书房,1987:166,170.
[10]王志,王晓峰.近代日本武士道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163.
[11][13][以]Jacob Raz.ヤクザの文化人類学[M].高井宏子,译.东京:岩波书店,2002:55,56-57.
[12][日]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110年[M].王众一,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202.
①名明敬,又名璞,字玉成,又字援之,号冠山,通称弥太夫,长左卫门和喜兵卫,是日本著名的汉语翻译家。
【作者简介】 姜 滨,女,辽宁鞍山人,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电影文化、电影制作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从任侠道到任侠电影:《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编号:XW22104)阶段性成果。
①又称“倾奇者”,意为极端的异样行动及风格倾向的人。其与传统艺能的歌舞伎虽联系紧密,但具有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而根据历史学者北岛正元的定义,歌舞伎者是江户时代前期以江户及其他都市为舞台展开反体制行动的武士及奉公人等。
②“奴”字的意义并非奴隶,而是指从武家的奴仆转型而成的“具有侠气与血气的勇武者”。
③旗本是一万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高级武士。而旗本奴是在旗本(体制)中存在的无赖集团、不良武士的徒党等。学者猪野健治将其称为“御用暴力团”。
④江户城火灾频发,幕府痛感火灾对“木造”国度的巨大威胁,开始确立消防制度并组成了具有一定编制的灭火队,即消防队。当时有两种性质的消防队:被称为“定火消”的武家(体制内)消防队及被称为“町火消”的平民消防队。“町火消”资金来源于民间筹措,与武家“定火消”有着官与民的区别。因关系到存亡问题,“町火消”在执行任务时更勇武,也更得民众信任。
①随着现代社会秩序的建立,“任侠”这一称谓沦为自称,“暴力团”与其画上了等号。
②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军于1894年11月21日攻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死难者不能精确计数,最高可能达2万人。
③1947年4月,黑川涉三为社长,以牧野光雄等伪满洲“满映”电影人为核心,于京都成立东横电影公司。后于1951年3月31日与东京映画配给、大泉映画合并成为“东映”,日本自此进入东映、松竹、东宝、大映、新东宝“五社体制”时代。
①传统刺青的纹法不用麻药,施术时极其疼痛:骨或木制的刺具尖端有无数细小的针头,特别刺到背、胸等敏感部位时疼痛感更为显著。且刺青需长时间精细作业,如整个后背的刺青图案就需一百小时左右方可完成。因此,刺青是黑道试验成员忍耐力高低的方式。
②對于破坏组织规矩成员的惩罚方式。切指,是最普遍的一种惩罚及谢罪的仪式。一般切断小指的第一关节。切指者需将切下的手指用干净的布包好,庄严地跪呈组长表示悔过诚意。破门,即驱逐出组织,也是最严重的惩罚。破门意味着个体被其所依托的集体所抛弃,对于集团性极强的组织成员而言,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无誉”结果,甚至比死亡更感到羞辱。
——读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