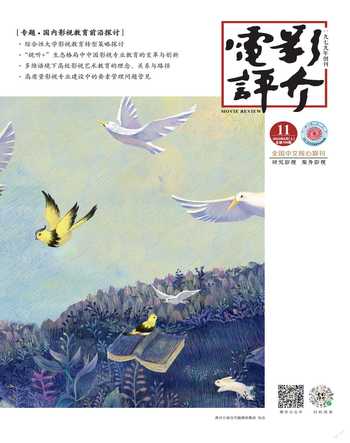21世纪少数民族儿童电影新变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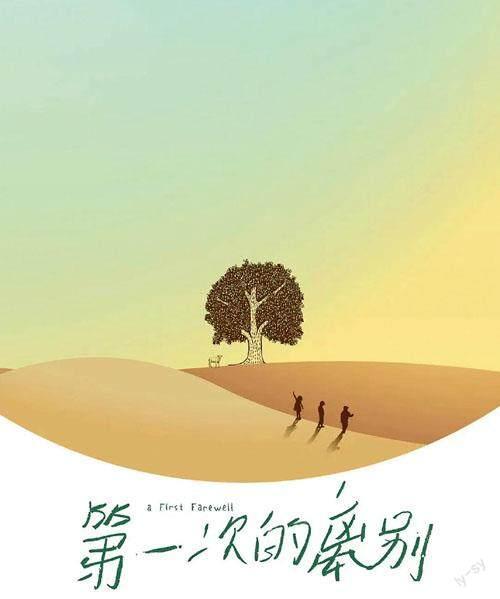
从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五彩路》问世,少数民族儿童电影在中国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所谓儿童电影,虽然学界尚无统一标准进行表述,但一般意指为少年儿童拍摄的并适合他们观看的、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角色、以表现少年儿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影片。[1]换言之,在儿童电影中,少年儿童是影片重点关注的对象,甚至影片就是以少年儿童的视角拍摄而成的。在中国的儿童电影中,少数民族儿童电影是独特的一种类型,它既有儿童电影的性质,也带有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承担着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借儿童之名对现实进行观照,并非是以天真烂漫的局部凝视修饰现实,相反,它是构成时代复述历史和现实实践的一个部分。
一、建国以来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的发展脉络
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经过60多年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这一脉络一直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是以中国为本位、为主体、为目的的国家叙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五彩路》讲述的是三位藏族孩子听说解放军在山的另一端修筑一条五彩之路,于是结伴去寻找这条五彩路的故事。故事的开端源于儿童的美好想象——有“一条路五光十色闪闪发亮”,为此,藏区恶劣的自然环境都不为孩子们所畏惧。孩子的纯真心思侧面烘托出彼时藏区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他们要寻找的五彩路是指引他们获得民主与解放的路。这也正是五彩路的真实寓意。富有政治意味的能指借助孩子的目光,变得更为具象,可感可信,也更容易为其立意进行宣传,带有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意味。《五彩路》上映之后直到1978年,中国陆续拍摄了三部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电影,它们分别是《阿夏河的秘密》《萨里玛珂》和《火娃》。这三部影片都带有浓烈的时代特点:均为不同民族的少年儿童为集体战斗与奉献的故事。尽管以后设的目光来看,故事中的革命小英雄大无畏地投身阶级斗争显得过于坚强果敢,不像一个孩子,反而更像一个成熟的高大全革命英雄缩小版[2],但这类银幕小英雄的出现一方面在于特定的时代背景,革命英雄(不论年纪大小)是国家意志在时代的具象化注脚;另一方面,儿童作为社会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真实问题未必就比成年人少,甚至可能更难解决。于是困境中的儿童形象更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获得共情。所以尽管这时期的儿童电影有刻板性与局限性,但也并非毫无感染力。
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电影生产采用“政府拨款拍片”模式,每年12部儿童电影生产指标由政府下达到当时的几大国营电影制片厂。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成立,八家单位合并成立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儿童电影生产开始由集团下属的第三制片公司承担。儿童电影生产开始慢慢从“计划”朝“市场”迈进。除了体制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开端这二十年间,儿童电影制作的内容也一改从前革命与政治结合的单一格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维度开始进入电影创作,题材开始多元。有塑造儿童与动物间深厚情感的《红象》(1982)、《熊猫历险记》(1983)、《走进象群》(1989)、《小象西娜》(1996)、《会唱歌的土豆》(1999)等;有塑造儿童间情谊的《应声阿哥》(1982)、《小客人》(1987),甚至还有已经关注到城市发展的《广州来了新疆娃》(1994)等。有学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少数民族电影的题材扩展,突出表现在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上。[3]电影作为对现实的艺术观照,多元题材、新颖立意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变化。新时期的中国,语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社会剧变必然影响着这片大地上人们的生活。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改善,人们也发现了物质与精神、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等二元对立的端倪。像《走近象群》中古董贩子费尽心思,想从女孩莎贝爷爷的遗言中了解到远古宝藏的线索;《小象西娜》中兄妹二人悉心救护了一头受伤的野生小象,但小象又被利欲熏心的盗贼一伙偷走;《广州来了新疆娃》直接呈现了繁华城市中物质诱惑对人的异化。这些远不同于革命阶级话语的规训意味,而是带着更多揭示、呈现与沉思的余韵。儿童相对于成人,无疑是柔弱的,一个柔弱的身躯被放置到社会宏大议题中,往往只能以本能、天性招架龃龉,让观众对时代缝隙中的困境获得直观的体验。总体而言,这个阶段不管是一般的儿童电影还是少数民族题材儿童电影,局限性都较明显:“创作意识陈旧,缺乏市场意识,缺乏儿童视角和对儿童生活的真实体验,这是中国儿童电影最大的硬伤。”[4]
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电影又有了一些新变化。影片关注的议题愈发多元,无论是儿童之间、儿童的代际关系,还是儿童与社会,甚至儿童与自然的关系都有所涉猎。与此同时,儿童电影开始尝试回归儿童本位视角,以儿童视角观察生活与讲述故事。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儿童电影或许可以变为一个承载更丰富意涵的容器,一个带着时代褶皱的特殊空间。其间有成长的烦恼、代际的龃龉及远方的吸引,同时这个情感世界又与外界紧密相连,它指向现代性裹挟下的现实变化,既有城乡二元矛盾,也有传统与现代的更迭。
二、社会性痛感的表达与治愈
不管儿童还是成人,在生活中均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背后有其复杂的动机。尤其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现,不仅带有社会交往的意味,而且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一旦这种自我实现受挫,容易产生“社会性痛感”(Social Pain)。社会性痛感是情感性疼痛的一种重要形式,特指个体觉察到自己所渴望的社會联结(Social Connection)面临威胁或社会关系贬损时,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情绪情感反应。这一社会认知领域中的新概念属于情感性疼痛的范畴。[5]像亲密关系建立/维护受挫、亲友离世、目睹他人受难等都会诱发这类痛感生成。儿童处于急速成长的阶段,对世界的认知无固定观念进行统摄,如果对社会性痛感的体认与理解没有得到正面积极的引导,容易造成认知偏差,影响自身积极成长。21世纪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中,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亲密关系与成长历程中产生的社会性痛感问题并不鲜见。
儿童成长历程中最为亲密的关系,一是来自家庭内部,二是来自共同成长的同伴。家庭内部的代际差异带来对问题的认知差异,甚至造成家庭代际成员的冲突。这种龃龉指涉的“不仅是不同代之间在公共物品和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权力冲突,同时也意味着支撑这些利益背后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偏好上的差异和分裂”[6]。像影片《布尔塔拉》(2007)《寻找那达慕》(2009)中都讲述了网瘾少年与家中父辈、爷辈的冲突。染上网瘾是戏剧冲突得以展开的导火索,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背后引人深思的是:少年儿童为何会染上网瘾、家长对此是否有了全面的认知、是否站在对孩子理解与关爱的基础上采取纠偏措施。这些问题关涉“儿童个体—家庭—社会”三个面向的复杂关系,也是电影在讲故事时应深度思考与提示的内容。尤其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儿童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带来的海量信息,很难简单地判断一个现代儿童的实际认知与真实年龄之间的差距。正因如此,如果没有站在儿童的视角探索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帮助、引导其正确探索与理解社会,而只是简单粗暴地进行“正面说教”,那就难以产生说服力与感染力。像《小黑鸟》(2011)中沉迷网络游戏的13岁少年巴尔斯,父亲一气之下砸了他心爱的电脑,不但未能纠正孩子的坏习惯,还导致父子关系的进一步僵化。
除了代际问题,同伴之间的陪伴及共同成长也是儿童电影中的话题焦点。这个同伴包括是儿童之间、儿童与动物之间。像《巴图快跑》(2013)中男孩托雷希望获得赛马比赛冠军,成为草原的英雄,为了实现小主人的心愿,陪伴他成长的牧羊马巴雷不顾伤病努力备赛比赛,最终倒在终点前。托雷因失去好伙伴巴雷伤心欲绝,但也从牧羊马身上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影片《我和神马查干》《乌珠穆沁的孩子》也都讲述人类与动物间的深情厚谊。另外像《扬起你的笑脸》《天籁梦想》(2017)、《米花之味》(2017)、《第一次的离别》(2019)、《石榴娃》(2020)这类儿童电影则主要描述儿童之间的深厚友谊。同伴情谊是儿童成长道路上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小伙伴还是小动物,彼此间的情感互动能形成一种积极的共生依赖。一旦失去了这种共生情感,儿童会感觉失去了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产生“失落”“沮丧”“悲伤”等负面情绪。如何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或者说在“社会性痛感”袭来之时,儿童要如何应对,并最终收获了什么样的感悟与成长——是此类儿童影片的立意所在。
可以说,与社会性痛感相关联的负面情绪是儿童电影中人与家庭、社会关系的一个侧面。克服这类情绪,获得正面成长的办法主要来自“社会—家庭”各方的“爱”与“关怀”。像影片《蔚蓝色的杭盖》(2006)讲述了女孩与非亲生的“父亲”之间,从冷漠隔阂到彼此难分离的深情;《格桑梅朵》(2011)讲述因玉树地震创伤失语的小女孩格桑梅朵,在社会多方帮助下,克服障碍再度开口说话的故事。这些影片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孩子从负面创伤中走出来,离不开“社会—家庭”的关爱。而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与一般儿童电影相比,还有一些特殊之处。一方面是影片中民族文化元素的引入,不仅拓展了影片的审美空间,而且丰富了影片的民族文化底蕴。例如,电影《布尔塔拉》中的小主人公朝克泰沉迷电子游戏,父亲将他送回了蒙古草原上的爷爷家。爷爷是个驯马高手,朝克泰在与爷爷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体味到草原上的马与人命运的一体。同样塑造了一个网瘾儿童巴尔斯的影片《小黑鸟》,巴尔斯同样是被父亲送回了住在天山的爷爷家。草原雪山、悠扬的民歌,还有熟能生巧的冬不拉——这些哈萨克族传统的文化元素让小主人公对自我与生活产生了的不一样思考。影片结局没有讲明巴尔斯是否已经戒断网瘾,但爷爷冒着风雪为他买来电脑,使得巴尔斯开始隐约地读懂了父辈的心,曾经的代际矛盾在此获得和解;另一方面则是其它文化元素的加入,强化了信仰对人的救赎意义。像《阿拉姜色》讲述了藏族小男孩为完成母亲遗愿,与非亲生的父亲一路历尽艰辛到拉萨朝圣的故事。这部影片没有刻意展示藏区独特的风光地貌与人文风俗,而是将这一切当做故事的发生背景放在这对继父子的朝圣之路上。不管是煨擦赛的习俗、一步一叩的跪拜,还是父子之间的只字片语、彼此抚慰,都让观众看到藏族人民关于家庭、亲情、爱情和信仰的智慧,这是治愈社会性痛感带来的负面情绪的另一种有效性途径。
三、儿童本真视角的呈现与保持
中国儿童电影在建国早期通常作为家国同构的表征,其中角色的塑造主要为阶级斗争叙事服务。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文艺界思想解放与人本主义的强调,儿童电影作为一种视角独特的电影,应该遵循儿童成长的独特性的观点愈发被肯定和强调。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道路上一个独特的阶段,此阶段的儿童对世界、社会的认知有明显的率真性与直接性,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是基于自己的认知做出的直接反应。藏族导演拉华加的处女作《旺扎的雨靴》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主要讲述小男孩旺扎非常渴望拥有一双雨靴,待到他真的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雨靴时,却一直等不到下雨的故事。故事以雨靴为线索,从旺扎的视角展开。起初旺扎由于没有雨靴被同学嘲笑,为此他显得不自信,甚至觉得父母不重视他;邻居小姐姐把自己的雨靴借给他穿,旺扎穿着雨靴在河水里玩得尤其开心;待到母亲真的为他换来一双雨靴,天却放晴了,旺扎又十分渴望下雨,甚至想阻挠村里的“挡雨”祭祀。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但通过儿童的反差心理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塑造,呈现出童稚本真视角下的独特审美趣味。《旺扎的雨靴》同时保留了对现实难题的刻画。因为父亲不同意购买雨靴,旺扎最开始对雨靴求而不得——这是故事的第一层冲突,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家庭生活的拮据;而临近收成季节,为保住一年收成,全村人都担心下雨,甚至要去寺庙作法“挡雨”——这又与渴望降雨以穿上雨靴的旺扎心愿形成第二层冲突,这背后是父与子、人与自然,甚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可见旺扎的生活并非充满童趣的牧歌,同时也是缓慢追逐现代性的藏区牧民的生活寫实,其中有诸多无法一举解决的难题。影片对此没有刻意回避,也没简单地作先进/落后这样的二元区分,而仍是以童真的方式进行回应。其中最独特的一幕就是旺扎和拉姆想吃供奉在佛龛前的糖,拉姆说小孩要吃糖就要对佛说“我们不是抢,不是偷,是跟您要的”,说完再磕三个头才能拿走一颗糖。最后还不忘强调,不能贪心,糖只能拿一颗。简单的稚子之言与藏区人民生活、文化传承相关的内容一并被呈现在影片中,使“叙事主体拥有了更复杂的童年生活背景,以及真实细腻的儿童形象,体现出儿童的共性和中国儿童的个性,具有了广阔的社会意义”[7]。
相较于《旺扎的雨靴》的唯美清新风格,保持儿童视角又凸显现实语境的《第一次的离别》则显得舒缓沉静。影片围绕新疆小男孩艾萨的日常生活展开:艾萨的父亲常年从事沉重的农事劳作、哥哥学业繁重,家中失智母亲则只能由他日常照料。艾萨竭尽所能地照顾母亲,在梳头、喂水、洗脸等一系列熟练的动作间,可以看到他对母亲的依恋与爱意。艾萨的好朋友凯丽是个乐观开朗的小女孩,她与弟弟是艾萨最好的朋友,三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嬉戏,但凯丽也有她的生活苦恼——她总说不好普通话,母亲为了让她与弟弟接受更好的教育,准备举家迁徙到县城。凯丽哀伤地询问母亲自己能否带上小伙伴一起离开,母亲告诉她,每个人都要面对离别。于是,在这个洋溢着新疆地区独特风味的故事里,在胡杨林、沙漠、棉花田里成长起来的艾萨与凯丽则开始面对生命中一场又一场的离别:艾萨的父亲决定将妻子送去养老院,艾萨不得不与母亲离别;艾萨的哥哥决定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艾萨不得不与哥哥离别;而凯丽举家搬迁,艾萨与凯丽也终将分别。每一场离别的背后都是成人世界里的诸多考量,也是远超儿童之力所能控制的选择。但影片中所塑造的离别哀而不伤,有更深的寓意:离别是人生常态,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在影片的最后,艾萨与凯丽同养的小羊走失,艾萨在风雪里出发寻找小羊——这个情节与开篇艾萨母亲走失后,他的惊慌失措不同,此时的艾萨沉着镇定地走进风雪里。小羊的走失,是童年的告别,但已经经历与母亲、兄长和好友离别后的艾萨已经开始明白,离别纵然使人惆怅,但生活还要继续。他要继续在村子里学习与生活,闲下来的时候去养老院探望母亲,以及等着远在他乡的哥哥寄来的信……一切似乎没有太多变化,但又都通通变了。影片通过配乐、构图、用色,民俗与意象将沙雅地区的生活进行了艺术还原。童年与乡愁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出现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中,但镜头语言没有过分拔高孩童的精神成长高度,也没有刻意煽情与说教,而是以孩童的视角完成对故土的审视,显得真实质朴,给人以悠长的回味。正是因为这份真实的独特,《第一次的离别》先后在东京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First青年电影展等国内外影展斩获优秀评价,被认为是“完美地展示了电影之迷人,在现实中唤起了诗性”[8]。
新时代中国电影在与时俱进中平衡着艺术审美与市场票房的关系,儿童电影也不例外。要拍出具有鲜活生命力与感染力,同时能接受票房市场考验的儿童影片,需要尊重儿童的本真与天然。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以儿童视角讲述儿童故事,是中国儿童电影获得长足发展的基本要义。
四、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中的命运共同体建构
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作为影像载体,具有讲述民族文化传承和变迁的重要功能。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在电影里不再是纯然的客观景象,它更多地指涉一种历史性的审美与文化旨趣,在镜头前呈现为一种文化意象。景观呈现也从自然景观、人类生活场景延伸出“地方”“空间”等“社会—文化”内涵,最后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建构。[9]
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中,雪山、草原、高原等自然风景经常作为经典符号贯穿于整个影像叙事空间。在美国视觉研究专家米切尔(Mitchell)看来:“风景意味着空间,风景被想当然地看成是空间和地方的现实特征的美学框架。”[10]自然风景这一符号的使用,最重要的是能够突出独特的地域特征,催生观众对民族地区的专有想象和对异域风景的独特情感体验。像《天上草原》《巴图快跑》《布尔塔拉》中广袤的草原;《伊宁不眠夜》《第一次的离别》中新疆地区独有的沙漠、胡杨林、棉花地;《梅里雪山》《静静的尼玛石》《格桑梅朵》中藏区的雪山高原,都是能唤起观众对特定区域的专有想象。除了自然景觀外,人文景观同样作为特殊符号呈现在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中,如建筑、服饰、手工艺、宗教、民俗等都是影片中的重要构成内容。像《寻找那达慕》中蒙古族的赛马大会、《俄玛之子》中的哈尼族歌舞、《小黑鸟》中哈萨克族的乐器冬不拉、《少年吉美》中藏族僧侣的日常生活等,都不再是单一的图像集合,还是一种话语体系的建构,在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中构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体系。这份独特性在少数民族题材故事片、纪录片中都能看到,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的重要标识,是凸显自身文化认同的符号载体。但也有学者指出,为了避免成为奇观化的表达,少数民族影片需要“注意处理猎奇和艺术之间的关系”[11]。关于民族性的表述,不应只有刻板的景观符号,而应该是多元与开放的。民族不是单一、纯粹的存在,基于中国特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在长久的发展历程中,必然会发生地区与地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融与杂糅,生活、文化、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互相产生影响。[12]在这个基础上,各族人民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伦理与政治的“连带”关系。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在非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样出现,是共性议题,造就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影片《少年吉美》作为一部纪录片,观察的是一个藏族少年吉美对于生活意义的思考:究竟是出家还是还俗才能抵达生活的本真。小众的僧侣生活话题背后是有关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与传承问题。传统的传承,其中有传统与人,乃至社会各层关系的复杂缠绕。21世纪以来的诸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通过对传统文化传承现实的难题思考,具有明确的共通性表达,富有建构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影片正是通过人的内外处境连接社会、反映时代,并产生信服力与感染力。对生活本真的呈现与思考不局限于某一地某一身份,且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正如《少年吉美》的影片结尾,一个吉美在山区里骑车的远景镜头,他的身影单薄渺小,没有人知道他将要去向哪里。
正是基于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境遇,在诸多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族别文化的独特性不再被重点强调,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背景,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也不例外。像《旺扎的雨靴》中对宗教文化和民俗景观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呈现,导演松太加在采访中表明他希望表现一个“更通俗化、大众化的故事,一个全国甚至全世界观众都能看明白的故事,而非具有强烈地域性和宗教性的故事”[13]。这样的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电影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少年儿童是祖国、是世界发展的未来,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少年儿童题材电影呈现出的问题或许不仅是儿童面对,可能成人也需要面对;不仅民族地区在面对,可能全球也在面对。像《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天籁梦想》中的弱势群体问题等都反映出创作者通过儿童的视角,“立足当代关照现实,以更积极的态度回应宏阔的社会变迁的努力”[14];也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多重角力中落实儿童电影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和个体追梦成长,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结语
多民族文化景观自古存在于中华大地,影像作为记录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化共融与发展的一个路径,是进入当代中国的有效切入点。21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儿童电影承担着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折射了巨变时代儿童与成人的斑驳心影和历史发展中个体的微观情感结构。人们能在这个特殊的影片类型上看到儿童电影开始尝试回归儿童本位视角讲述故事的努力,其中既有对社会性痛感的表达与治愈,也有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藉此来观照当代中国发展褶皱里的幽微内容,才有可能真正触及历史深处的脉动,缔造开放性的、对话性的共同体叙事,并反作用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甚至启示出替代性的现代性方案。
参考文献:
[1]周晓波.儿童电影艺术与欣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48.
[2]罗娇,毛攀云.十七年儿童电影人民性文艺观的实践与审美[ J ].电影文学,2019(21):10-12.
[3]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M].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198.
[4]高卉佳.儿童电影:不能只给儿童看[N].中国电影报,2005-01-27(02).
[5]舒敏,刘盼,吴艳红.社会性疼痛的存在:来源于生理性疼痛的证据[ 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06):
1025-1031.
[6]吴小英.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 J ].青年研究,2006(08):1-8.
[7]张晗.“儿童本位”意识下国产儿童电影叙事特色[ J ].电影文学,2020(13):41-44.
[8]杨碧薇.《第一次的离别》:类型跨越中的诗性营造[ J ].电影评介,2019(07):53-57.
[9][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9.
[10][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
[11]冯小强.试析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J ].当代电視,2012(03):79,82.
[12]汪荣.跨民族连带:作为比较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 J ].民族文学研究,2015(03):84-95.
[13]曹娟.儿童电影《旺扎的雨靴》的改编策略和文化身份[ J ].电影文学,2019(15):103-105.
[14]林琳.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自觉[ J ].当代文坛,2022(01):132-138.
【作者简介】 林 琳,女,广东湛江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主要从
事影视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与‘中国故事表述研究1949-2018”
(编号:19CZW05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