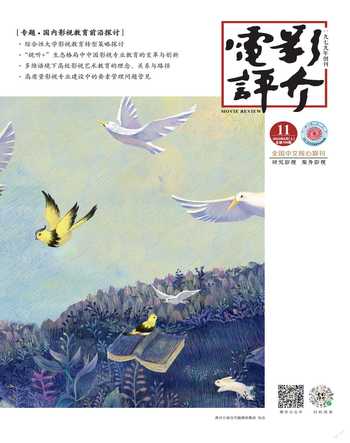复合审美与审美的复合性:新时期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多维美学体系建构与思考
钟菁

随着短兵相接的大规模战争时代的结束,现代军队的职能、现代战争的形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平与战争的边界不再泾渭分明,各国围绕军事题材所创作的游戏、电视剧、电影等正在媒介战场上以另一种隐蔽的方式博弈。美国学者提姆·莱诺(Tim Lenoir)和卢克·卡德韦尔(Luke Caldwell)提出“军事—娱乐复合体”概念,给全媒体时代下的军事题材电影赋予了独特的双重身份。[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事—娱乐复合体”的提出,代表着当代学者对于军事电影功能性由单一走向复合的一种反思,反映出新时期军事题材电影的审美范式、审美观念出现了复合性倾向。
一、“规训”与“娱乐”:军事电影审美功能的复合性
(一)政治美学的“规训”耦合
美学是先验范畴与感性经验的双面耦合,这种双面性使得军事题材电影中充盈着“美”与“丑”的对立思辨,这种思辨同时影响了美学的历史嬗变、审美意识、审美范畴及审美理念等多重维度的美学辩证体系。军事电影的美学体系转向具备政治美学的范式体征,而政治意义的美丑判断则与权力概念的泛化“规训”不谋而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说道:“它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2]军事与政治的天然胶着决定了战争美学必然受到政治体制的规范化引导,纯艺术领域的美学理论难以切实涉及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电影的美学逻辑。尤其对于军事题材电影而言,涉及有关根本的生死观、是非观、正义观及合法性的问题判断时,国家意志总是倾向于将评判的权力潜移默化地予以控制,借助美学的共识性将战争审美与道德伦理相挂钩。
从艺术发生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美学思潮的产生及衰退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类文明变革息息相关。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美学演进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轨迹紧密契合,同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刻影响。譬如,传统中国军事题材电影普遍习惯通过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来表现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通过演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历程来见证和书写国家历史。“十七年”电影、主旋律电影、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皆被主流意识形态赋予了超越电影本身的社会功能。饱含爱国意识、忧患意识、救亡图存愿景的中国电影人,将军事电影的创作与激励民族团结一心、弘扬正义道德理念、鼓舞军民战斗士气、启蒙和解放思想等合目的性的现实使命结合在一起。“功利主义美学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艺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政治功能的学说,融含着儒家传统思想中‘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等观念。”[3]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年代,功利主义美学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党性意识、典型性方法论等形式体现于具体的电影创作中,以政治美学的显性姿态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观众,使其通过观看军事电影,接受崇高精神的洗礼,感受革命史诗的雄浑壮阔。进入和平年代,随着社会现实和艺术环境的转变,功利主义美学的政治功能性显示出局限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毕竟不能用于直接实现阶级立场和国家意志的巩固,在面对审美多样化、个体化、差异化的当代电影观众时,政治“规训”开始寻求通过间接的、可能的道德伦理,以一个个或悲壮、或崇高、或浪漫的革命故事,打破刻板的“神化英雄”形象和“无冲突论”思维,传播军事美与人性美,以期获得大众的共情和审美体验。
正如康德所言:“美是道德观念的象征,把审美范畴的崇高对象定位于客体的无形式”[4];“美感不是用知识和推理的方法去寻求客观事物的知识,而是用想象力去感受客观事物得到的趣味”[5]。至此,军事题材电影的美学体系逾越了纯电影艺术的美学范畴,而与政治美学指导下的伦理叙事相结合,不断阐释着德性伦理、道德传统叙事的正义神话,旨在从稳定的民族心理层面取得一定的叙事认同和情感共鸣。美学的转向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经验的空间拓展,一种从浅表感知层面上的本能体验向具备理性思考、逻辑思辨的深层审美活动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合规律性、从善从美的审美惯性的逾越。
(二)暴力美学的娱乐表达
军事电影,尤其是战争片,与暴力的胶着关系是天然存在的。战争以暴力的形式展现,而暴力程度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战争规模的大小。从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论来看,人类对于生本能与死本能(暴力)的渴求是本能欲望的体现。[6]暴力在电影中被视为非理性的原始冲动、教唆青少年犯罪、荼毒社会的洪水猛兽,即便真实战场上的军事活动也处处充斥着极度震撼的暴力,电影中也不能如实呈現三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美学诉求导致过去的军事电影,无论在叙事亦或是剪辑上都着力于塑造观念和书写意义,甚少将注意力集中在通过暴力表达操控观众的情感体验、追求各种感官刺激的兴奋强度上。
电影对于暴力表达的欠缺在当代大众引领的泛娱乐化大潮中迅速反弹,由于“性元素”的呈现始终是国家严格把控的高压线,暴力成为军事电影追求娱乐强度和审美体验最好的途径。越来越多充满血腥的屠杀场面被毫不避讳地呈上银幕,枪战的特效场面甚至比真实战场上更为激烈凶残。有关军事题材的影像制品向着现代战争的仿真复刻方向不断靠近,追求真实战场上紧张刺激的暴力体验,叙事剪辑风格迅速而凌乱,模拟第一人称视角的战斗画面呈现出失控的抖动和逼仄的局限感,观看时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类似《使命召唤》《美国陆军》《反恐精英》等战争游戏。新时期军事题材电影的画面普遍是直接的、震撼的,大众对于电影审美的认知也变得无意识和条件反射,“这种认知由感官体验带来的无意识的副现象——情感、激励、刺激和抑制、愉悦和痛苦、震惊和适应等组成。电影跨越了一般认知的门槛而成了一种新型的认知,它要么低于人类的认知水平,要么高于人类的认知水平。它是具体的,与生俱来带有前反思性,但缺乏深度和内化”[7]。现代军事题材电影对于暴力美学的直白追求不仅体现在诸如《军情五处》《24小时》《勇者行动》等国外影视作品中,同时在近年的国内军事题材电影如《战狼》《红海行动》《八佰》《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等作品中也得到了佐证。在2021年票房冠军电影《长津湖》中,表现作战场面的镜头绝大多数都采用手持跟拍,并且画面伴随着美军战机的炮弹轰炸而产生强烈震颤摇晃,仿佛将观众视野代入一个身陷炮火的士兵身上,大量运动镜头的快速组接使观众的视听感官在短时间内受到的刺激程度大大提升,对于战争暴力的审美方式也变得感性而直接。
同时,科技主义的蓬勃兴起也为战争影像的暴力书写增添了无限仿真现实的可能性。仅《长津湖之水门桥》一部影片中,多家公司参与战场特效制作,从宏大的全景展现到微观的作战武器、交火场面表现上,影视特效的大量植入都强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军事电影的美学观念产生了革新。暴力美学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电影中意识形态叙事的份额,压缩了观众思考战争的空间,同时平衡了传统军事电影过分追求“意义”和“主义”的倾向,使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在内容与形式层面上都产生了复合式的互动发展。
二、“结构”与“范畴”:军事电影复合审美的双重维度
(一)电影美学:悲剧美感与伦理救赎
战争是无情的,是丑陋的,一切战争对于生命个体来说都是悲剧。暴力摧残生命,战争美学的审美同时是一种审丑。残缺的肢体、破碎的家庭、悲鸣无力的哀嚎及飞溅的鲜血“都表现了人生内容的欠缺性和不安定性,所以它们与美的本质相对立,都意味着丑恶的东西”[8]。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在论述悲剧的本质时说:“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悲剧是人的苦难或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足够完全使我们充满恐怖和同情。无论人的苦难和死亡的原因是偶然还是必然,苦难和死亡反正总是可怕的。”[9]
但在战争中,“丑”的东西处在特定历史境遇下也会与美相转化、相融合,成为一种异相之美。猥琐、卑鄙、意志力薄弱的敌人在遭受暴力时不堪一击、毫无抵抗之力,从而衬托出正义方的强大与力量。弱小无助的平民在炮火中成长,犹如冲破厚土、顽强破壳而出的嫩芽富含勃勃生机,最终获得反抗压迫的力量,这也是一种充实生命力和体现,具有厚积薄发的美感。马克思(Marx)在论述悲剧的本质时指出:“新的社会力量虽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是面对着强大的传统的力量,却显得弱小,因此在斗争中必然会有牺牲和失败,在实践中逐渐壮大自己。这种力量对比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形成悲剧的客观现实基础。”[10]新生力量在壮大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与创伤是悲剧产生的源泉,也是战争产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军事战争电影塑造了无数为了正义牺牲的悲剧英雄,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为了保护大部队转移死守在棋盘峰抵抗日军3500人,最后抱着对共产主义信念跳崖牺牲的5位八路军战士,还是《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野战军为了抵抗敌军的猛烈进攻,与国民党交战中全部牺牲的我軍一个营的指战员,都具备了浓厚的悲剧感染力。如果仅从客观力量对抗结果的比较上,牺牲的一方自然是在体能上弱小的,在战斗力上低下的,但是何以在悲剧中重生,使得人的力量在毁灭中重生,使得肉体的弱小显现出精神的崇高,便是依靠意志美、精神美及人性美得以升华。此时,战争叙事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成为使广大观众对于战争电影中的悲剧赏析从单纯的恐惧转化为敬仰,从审丑转为审美的重要工具。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1]所谓有价值的东西,是指那些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体现群体道德的高标准、代表全人类利益和进步要求的东西;而“毁灭”是指人类共同的道德象征,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伦理道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隐形准绳。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即便是最坚硬的道德准则也会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军事电影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在所有电影之中,它将必须最坚定地遵守一切道德上的、伦理上的、法律法规上的游戏规则,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他电影的表率与榜样。诚然,从生命的尊严角度而言,每个战争中被炮火剥夺的个体都是悲剧,但却并不是每个消失的生命都具有审美价值。只有代表正义理想,符合道德伦理的牺牲才具有悲壮美。
道德伦理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意志精神和人性本质,它是赋予军事电影以审美价值的关键。“不是所有带着悲剧意味的英勇豪壮的军事行为,苦难、顽强与牺牲,都是军事悲壮美。只有那些脚踏苦难、征服苦难,在苦难中奋起,以生命推翻暴政、用热血祭奠真理、以暴力换来和平与安宁的军事行为和战争行为,才是军事悲壮美。”[12]悲剧英雄的普遍共性体现在伦理道德上,他们是自觉的真理捍卫者及斗争者,他们的牺牲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肉体在巨大的战争苦难中被无情地粉碎碾压,但他们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无畏与激情,使得死亡行为本身成为微弱的真理之光,最终照亮黑暗的希望,成为新世界取代旧世界的转折点。
(二)战争美学:军事智慧的美感与韵律
战争不仅是体力的正面对抗,而且是头脑的激烈博弈。“美的基本含义,在古希腊哲人那里有二:一是智慧;二是技巧。军事美的基本含义,就是军事智慧和技巧。军事艺术美,是军事智慧和技巧美的集中表现。”[13]战争的智慧美,是指战争本身作为一门艺术所展现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之美。不论是军事知识、治军思想、战争伦理或是战斗方式、战役指挥都彰显着人在战争中所绽放的不同于野兽搏斗的理性智慧之美。战争智慧在影视作品中的展现使得战争脱离了纯粹蛮荒的厮杀与毁灭,使战争影像表达脱离了单纯血腥刺激的技巧,而上升到了一种充盈着人性力量的生存博弈。
近几年,军事题材电影对于战争场面的刻画,以及对战术、战略的还原更为谨慎求实。《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等影片中大篇幅表现了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志愿军开展的冷枪冷炮运动。在敌我装备武器水平及作战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大批志愿军特等射手、狙击手(实际由于志愿军所配发的武器落后,根本没有真正的狙击枪和光学瞄准镜,严格意义上他们只能被称作“步枪手”)、游动炮兵穿插迂回于前线战场,配合主力部队进攻,破坏封锁阵地内的交通,把火力对战的焦点推向阵地的前沿。在电影《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志愿军第七穿插连的多次进攻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战争智慧和钢铁般的战斗意志。该连使用的装备主要有驳壳枪、三八大盖、布朗式轻机枪和M2型60毫米轻型迫击炮,以及少量从敌军处缴获的卡宾枪、巴祖卡火箭筒等。而美军出现的装备有大八粒M1加兰德、M3式冲锋枪、M2式勃朗宁大口径重机枪等。美军的火力压制强,射程远,后勤粮草弹药补给充足第七连战士缺衣少食,后勤补给线被美军轰炸机多次炸断,作战武器简陋匮乏,战场传递信息只能靠吹口哨和喊话进行。即便如此,穿插连战士依旧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利用一切优势,从侧面或缝隙中迂回包抄,阻击敌人后撤,扰乱敌方进攻。美军士兵尽管战斗实力十分强悍,对重型武器的操作炉火纯青,但一旦脱离了空军和重型火力的配合,很容易就会失控崩溃。打穿插对于执行任务的部队来说困难极大,穿插的过程中,要长时间暴露在敌人的火力封锁线上,而一旦穿插成功,到达敌人身边,又会陷入被前后夹击的围攻中,几乎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性。能打穿插的队伍都是士兵里精英中的精英,但即便如此,仍会首当其冲受到最凶猛的进攻,死伤最为惨烈。《长津湖》中小战士伍万里的编号是第677号,也就意味着在他之前,这支连队已经在过去的战斗中阵亡了好几轮战士了。
相较于《长津湖》史诗般的全景战场刻画,2022年上映的《狙击手》则更侧重于以小见大,以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次小规模战役为表现对象,细致刻画了敌我双方八次你来我往的战斗过程。片中有一幕对战的场景,生动诠释了志愿军“赶鸭子上架”战术的神机妙算:一片寂静的雪地中,美军狙击手藏在战壕死角,易守难攻。五班班长刘文武和小战士大永为了引诱敌人主动暴露,双人配合,一人一枪拉开距离,埋伏两侧,并在两人间的雪地上悄悄平均间隔开来,放置了另两把上好膛的备用枪。战斗开始,刘文武首先对着敌人战壕开了第一枪,趁敌人寻找开枪方位时,原地发射第二枚子弹。此时,敌方狙击手躲在战壕中,锁定了目标,开枪还击。刘文武迅速滚到第一把备用枪处,换枪打出第三发子弹,随后滚到第二把备用枪处,换枪打出第四发子弹,然后带着第二把备用枪滚到大永身边,打出第五发子弹。紧接着,大永用自己的枪开出第六枪,敌军被一枪毙命。对于不大熟知军事的观众来说,这一幕战斗场景可能不容易理解。刘文武和大永之所以要如此布局进攻,是因为在这场战役中,敌方狙击手使用的是M1941狙击步枪和M1C半自动狙击步枪,而且皆配备了当时最高端的八倍光学瞄准镜;而中方战士使用的枪支是1944式莫辛纳甘短枪管步枪,没有瞄准镜,仅能靠肉眼瞄准,有效射程短。这款俄罗斯研发的旋转后拉式步枪为整体式弹仓,打一枪要上一次膛,而且弹仓只能容纳五发子弹。敌军狙击手深知这点,因此在刘文武开前四枪时,敌人尽管立刻都予以了还击,但仍死死躲在战壕中,不暴露位置。直到刘文武滚到大永身边,开出第五枪后,敌人误以为我方只有一人一枪,五发子弹已经全部用完,必须要重新给弹仓填充弹药,因此想趁着这个停火空隙伸出头来,好彻底看清战场局势,一枪解决我方狙击手。却没成想,前五发子弹都是用来迷惑他的烟雾弹,而大永在五发子弹结束后也终于看到了探出战壕的敌人,果断瞄准目标开出第六枪,赢得了最终胜利。
战争智慧并不單纯是一种对于战争技巧的赞扬。万韦岗战役、平型关战役、黄土岭战役,以及众多的游击战、运动战可以运用智慧巧胜,而孟良崮战役、上甘岭战役、淮海战役等更多的大型战役却只能强攻。面对强敌,有坚强的意志与毅力抓住时机,同样是战争智慧美的表现。“军事艺术美实际上是军事主体辩证心理过程的流动的美。它是随客观实际的变化而采取自由灵活的方法,来处理复杂多变的军事与战争问题,克敌制胜的军事手段和技巧的美。”[14]战争思维、技巧、观念、信仰都属于战争智慧之美的表现形式。技精而成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革命斗争史中领导着中华民族创造了一场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神话。这些战争神话中所蕴含的智慧之美为军事电影的美学观念维度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为电影的美感创造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结语
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美学体系是一个涵盖广阔的集合体,它不仅涉及军事学、战争学、电影学、叙事学、美学等有关于艺术本体的学科,而且与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诸多有关艺术语境的学科相联系。复合审美范式和审美的复合性倾向形成,既是一种历史维度的发生历程,也是一种观念维度的感知融合。尽管新时期军事题材电影在当代泛娱乐化的浪潮中愈发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了国家主流意识的“规训”意味,隐藏了社会功利主义的审美诉求,弱化了过去电影中那种简单直接的政治立场表达和高昂饱满、无往不胜的战斗姿态展示,且从宣传工具向消费艺术品的身份上不断转化,朝着电影的娱乐本性不断发展,但它终究是以表现军事战争、表现与军事紧密相连的意识思想的一种电影形态。政治美学、电影美学、道德美学的多维互动融合,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军事电影美学理论发展的指导方向和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美]提姆·莱诺,卢克·卡德韦尔.军事——娱乐复合体[M].陈学军,译.北京:后浪出版公司,2021:2.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41.
[3]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2:52.
[4][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5,172.
[6][奥]弗洛依德.精神分析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1997:57.
[7][美]Steven Shaviro.The Cinematic Body[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26-27.
[8][日]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M].魏常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33.
[9][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M].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02.
[10]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美学与美学史论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10.
[1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78.
[12]田立延,刘晋生,亦村.军事美学[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49.
[13][14]方振东,宋海英,李学明.军事美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5.338.
【作者简介】 钟 菁,女,陕西西安人,成都大学影视与动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