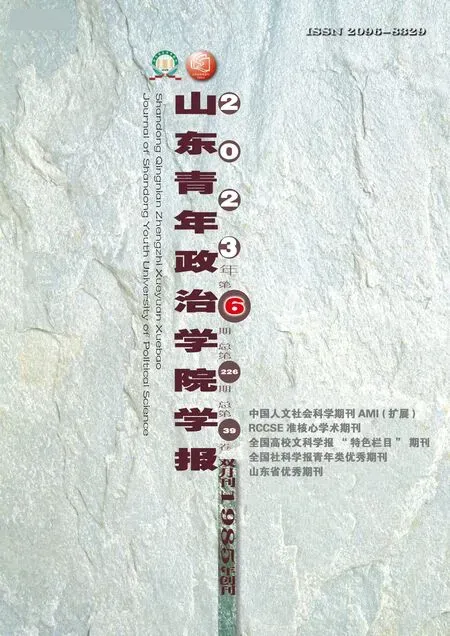性·神·电:康有为人性论新解
能星辉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
康有为的人性论,徘徊于“自然人性论”与“性善论”之间,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文本支持。对于前者,康有为在论“性”时都要提及“性”为“生之质”,这几乎贯穿了他全部的文本,但后者也并非无迹可寻。在《孟子微》中,康有为就直言“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发之于外,即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无此不忍人之心,圣人以无此种,即无从生一切仁政。”[1]有仁政才能实现大同,有不忍人之心才有仁政,既然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谓人性本善,康有为这里所主,不能不说是“性善论”。
其实,学界对康有为人性论的理解,也应乎“徘徊”二字。如李泽厚先生称康有为的“自然人性论”闪烁着近代资产阶级的新的光芒,但也指出他在注经(如《中庸注》《孟子微》等)时期又回到了程朱性善论的传统窠臼。[2]萧公权先生认为康有为虽整体上贵告子伦理中立之说,但并非一直保持不变,一时兴起时,又飘向浪漫的孟子观点。[3]其实,这正说明,康有为的人性论不能单一地视为“自然人性论”或“性善论”,而应当认识到中间或者经历了某些变化,或者代表了某种张力。
本文于此所要论述的“性·神·电”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反映了这种变化或者张力:一者,对于康有为人性论的变化,学者鲜有阐述,而“神”这一概念恰是康有为从自然人性论向性善论的转向中提出的,要阐明“神”的内涵,不得不认识到这种变化;二者,康有为以“电”论“神”的思想,目前未有详论。康有为借助科学的、物质性的“电”论述哲学的、精神性的“神”,并以“神”为“德性”之“精”来搭建出一条通往“性善论”的理论构建,显露出其别具时代特色与自身风格的人性论诠释。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康有为最终借助性善论的囊括力,与自然人性论作了一融合,这同样与他的所处时代和自身性格息息相关。
一、从自然人性论到性善论的转向
萧公权认为,康有为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幼年始到大约1883年,康有为从古典转治汉学,大致顺从传统;第二阶段约始于1888年,他从古文经转至今文经,并以《春秋》公羊学为研究焦点;第三阶段约始于1892年,止于1902年,他以《春秋》三世之说及《礼运》大同之旨为基础建立其社会哲学,并对儒学经典展开了全面的研治。[4]康有为论述人性论的文本集中分布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整体上,康有为在第二阶段持自然人性论,且这一自然人性论内在也有一发展,而随着整体思想的转向,到第三阶段时,康有为便偏爱起性善论。
从《康子内外篇》(1886)和《长兴学记》(1891)的文本来看,康有为最初持“自然人性论”无疑。他以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为宗,认为“今之所谓仁义者,积人事为之,差近于习,而非所谓性也。若夫性,则仁义爱恶无别也。善者,非天理也,人事之宜也。故以仁义为善,而别于爱恶之有恶者,非性也,习也。”[5]又称“言相近者,谓出于禽虫之外,凡为人者必相近也,不称善恶。至于习于善、习于恶,则人为之矣,故相远也。”[6]即是康有为认为孔子所说的“性相近”是言人性本身无善无恶,“习相远”则指善恶皆是后天学来。
对于“性”,康有为认为“夫性者,气质所发,犹一子也,但于气质中别名之耳,安所谓不备哉?譬如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气质之为之也。”[7]又称“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8]世界万物皆有其“性”,乃受于“天命之自然”,由气质所发,而于人之上的“性”,即是自身气质带来的自然属性,推开来说,就是“视听运动”“食色”等人的生物本能和生理欲望。
在此基础上,康有为认为,自孔子之后,“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扬子言善恶混,韩子强为之说曰三品,程、朱则以为性本善,其恶者情也”,均属“不知性情者也”。[9]他还以义理出于气质批判一些宋儒:“程子、张子、朱子分性为二,有气质,有义理,研辨较精。仍分为二者,盖附会孟子。实则性全是气质,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也。”[10]“性”只是“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即“善”,是从属于气质的后天习得。而在众多关于人性的讨论中,康有为认为只有告子一说“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11]。
其实,康有为虽以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为宗,倡告子“生之谓性”一说,对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诸宋儒的人性论加以非议,但他不止于此种批评,而是有意调和众人的观点。若不调和还罢,此一调和恰使得康有为完成了自然人性论的内在发展,并愈发地靠近性善论。
在《春秋董氏学》(1893-1897)中,康有为就认为:“性善性恶、无善无恶、有善有恶之说,皆粗。若言天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与《白虎通》同,可谓精微之论也。”[12]在《万木草堂口说》(1896)中,康有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尝试调和孟子、荀子、董仲舒之间的差异:
孟子传孔子之学粗,荀子传孔子之学精。孟子言扩充,大指要直指本心。荀子则条理多,孟子主以魂言,荀子主以魄言。二者皆未备,《白虎通》所说更精。[13]
荀子言性以魄言之,孟子言性以魂言之,皆不能备。[14]
《白虎通》言之甚精,学者能以魂制魄,君子也。若以魄夺魂,小人也。[15]
《白虎通》分性、情、欲,此说从孔门传出,遍证诸家,莫能及此。[16]
董子微言大义,过于孟、荀。[17]
董仲舒言:“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18]而《白虎通》承接董仲舒的思想,自然也就延续了他这一论“性情”的框架:“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故《钩命决》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19]其中“性”便是“五性”:仁、义、礼、智、信;“情”为“六情”,即喜、怒、哀、乐、爱、恶。康有为赞许董仲舒,也并非就是主张“性善情恶”,在《万木草堂口说》中,他还是一再强调“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20],“性只有质,无善恶”[21]。这并不矛盾,反而是康有为顺承经学视角在自然人性论完成的一步推进。从气质言性,是说“此自然而本然之质中并无仁义之道德性”[22],故无有善恶之分。而言有贪有仁的性善情恶,则是在说气性有向善恶发展的倾向,仁之气性落于具体即是善,贪之气性落于具体即是情欲,其实,皆是谈气性。如果说康有为在写《康子内外篇》和《长兴学记》时持的是“性无善恶”论,那么这一时期,他对董仲舒和《白虎通》的赞赏表明他已“进一步就其差别分化而言其气质之善恶之倾向”[23],“性”本身未有善恶,但有“善质”,有“恶质”,人之所成的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即“伪”,也无怪乎康有为此时对荀子也有所推崇:
总之,“性是天生,善是人为”,二句最的。其善伪也,伪字从人,为声,非诈伪之伪,谓善是人为之也。[24]
总之,天下人有善有恶,然性恶多而善少,则荀子之言长而孟子短也,然皆有为而言也。[25]
从荀子说,则天下无善人。从孟子说,则天下无恶人。荀子说似较长。[26]
康有为借助对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的调和,从生之谓性的性无善恶发展到了性无善恶却可言善质恶质,这一发展仍是在自然人性论的范畴里,前者是普遍地说气质的根底,后者是具体地说散开的征象。然而,这一肯定善质为后来康有为对性善论的偏向奠下理论基石,同时,康有为也不自觉地开始意识到性善的价值所在。孟子以魂言性,荀子以魄言性,二者所说皆不完备,《白虎通》言之甚精。但《白虎通·性情篇》所言“魂”“魄”是以魄主性,以魂主情:“魂犹伝伝也,行不休也。少阳之气,故动不息,于人为外,主于情也。魄者,犹迫然著人也。此少阴之气,象金石著人不移,主于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秽;魄者,白也,性以治内。”[27]康有为则认为“以魄夺魂”是小人,“以魂制魄”方为君子,这明显是以魂主性,以魄主情。又认为荀子多言魄,孟子多言魂,从这里来看,若想成为君子,反倒是要寻孟子之学了。
不过,《万木草堂口说》的体例毕竟特殊,其中言论皆是单独成句,康有为在书中对孟子、荀子、董仲舒的调和尚且疏浅,而这一工作的进一步完成则是要到下一阶段。《万木草堂口说》成书于1896年,也许是戊戌变法(1898)的失败,促使康有为将思想重心从“改制”转移到了“三世”与“大同”之上。“三世”观点的确立让康有为的学术视野焕然一新,1901年到1902年之间,康有为完成了五部经书的注疏:《中庸注》(1901)、《孟子微》(1901)、《礼运注》(1901-1902)、《大学注》(1902)以及《论语注》(1902)。王玉彬认为,在此思想转变之中,他对性善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28]魏义霞亦言:“在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对荀子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对孟、荀的评价也随之相去甚远。此时,孟子依然被康有为奉为孔门之龙树、保罗,荀子却被边缘化,甚至成为孔学内部的异端。”[29]“神”与“电”正是这一时期提出的,二者撑起了康有为一条走向性善的理论进路。
二、神:性之精
中国文化对“神”的讨论并不少见,康有为也讲“神”,但是相当特殊的是,康有为并没有单独解释它的内涵,而是把它等同于很多其他概念:“夫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30]
仅此一句话中,康有为就将“神”与很多概念相对等。其中,“知气”出自《礼记·礼运篇》“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魂知”概是“魂”的流变,不指向某一具体出处。“精爽”出自《左传·昭公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灵明”应该特指王阳明的思想:“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31]“明德”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对等概念的互释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出,“神”应该能指代人的知觉、精神、道德意识,同时也有点精神本体的意味。但是这句话还远远不能充分地说明“神”的内涵。
康有为还更多讲“神明”。其实“神明”就是“神”,康有为曾言:“是有精爽,至于神明,神也。”[32]另一方面,康有为也把“神明”与诸多概念等同起来,他说:“性有质性,有德性。德性者,天生我明德之性,附气质之中,而昭灵不昧者也。粗者为知气,精者为神明。古称明德,后世称为义理之性。或言灵魂,或言性识。诸说之名不同,其发明此实则一也。”[33]“神明”与“明德”“昭灵不昧”“知气”与“灵魂”等有内在的相通性,而这些词同样与“神”相通,只是异名而同实,所以“神明”即是“神”。同时,从这一句话中,我们也能断言,康有为是在人性论的范畴下讨论“神”,前述所说的诸多概念以及这句话中的“义理之性”“灵魂”“性识”等在康有为看来都是“性”二分为“质性”与“德性”中的“德性”。既然“德性”可以等同于“义理之性”,那么“质性”也应当是“气质之性”的简称。之所以选用“德性”,也有一定的调和意味。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说》中曾言:“‘明’字为一大道理,孟子言性善,不如《大学》言明德。”[34]此时他尚贬低孟子,故有“不如”一说,但这一时期他将“德性”与“义理之性”等同,显然就没有这种倾向了。
“德性”之中仍有粗与精的划分,“神”“神明”为“德性”之精,“知气”为“德性”之粗,这一想法康有为多次强调,“性者,人之灵明,禀受于天,有所自来,有所自去。……精言之谓‘神明’,粗言之曰‘魂灵’”[35],“知气者,灵魂也。……尤为灵明者,则为精气,为神明,亦曰明德,其义一也”[36]。虽然康有为常常称“德性”的粗精为一回事,但通过分析会发现,二者仍有根本性的差别。知气、魂气、灵魂、魂灵等为粗(以下统称之为“知气”),神明、灵明等为精(以下统称之为“神明”)。“德性”之粗等词围绕着“魂”,皆与身体性的“魄”相对立,关乎人的高层次的精神意识和认知①,而神明、灵明等词虽同具人之精神义,却在这一层面上与知气拉开了不小的差距。从灵明言,人自可充塞天地,主宰天地鬼神。因此,虽知气、神明都可指代人的精神意识,然知气或是在人禽之别上谈人有知觉思想,神明则进一步言人之道德主体精神,此精神昭昭其明,至精至灵,能够使人达到一种赞天地之化育而可以与天地参的深邃高远境界。
同时,“神明”又不止于一种境界或是能达此境界的能力,即德性之粗精又有第二层含义:知气似夹杂理与气,而神明则升至纯理。宋儒谈“义理之性”,又称之为“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依此性扩充,便可得天德良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虚灵不昧”,“昭灵不昧”亦有此意,朱熹认为“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37],王阳明称“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38],明德者当是具本然的仁心善性,湛然虚明,感通万理。即使不以同等概念相论,康有为也曾直言:“人之灵明,包含万有,山河大地,全显现于法身,世界微尘,皆生灭于性海,广大无量,圆融无碍,作圣作神,生天生地。”[39]即是人之“神明”又上升为万物存在的根源,其“虚灵不昧”“昭灵不昧”,为人之“明德”以及作为能力与境界的“神明”作一本体层面的保障。
研辨至精,还可以说,康有为在使用“德性”一词时,注重的是“神明”而非“知气”,不然也就无有必要称之为“义理之性”“虚灵不昧”“昭灵不昧”,更罔乎言佛教的阿赖耶识,基督教的灵魂了。康有为虽然认为自灵魂言,“则诸教无不同者。……耶所谓灵魂,佛所谓阿赖耶,识深之则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者也。”[40]但佛教谈阿赖耶识,识深之“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是见诸法空相,证真如心体,“修炼精神,以至成佛”[41]。基督教论及灵魂,其典型代表如托马斯·阿奎纳认为灵魂是人一切生命现象和精神活动的唯一根源,具有某种永恒性或超越于人的普遍性,或与外在于人的某种宇宙理智相同一[42],直与上帝相关。以此所论“德性”,不论是从第一含义还是第二含义,都当指“神明”而非“知气”。
统合上述,能够看出,原本简单地以“魂-魄”二元结构调和人性论的思想,到这里便复杂了起来。一者,“魂”与“魄”的结构被转化为“德性”与“质性”,汉儒之语被宋儒之语替换,而且德性不止在孟子、荀子和董仲舒上谈,而是遍及儒释耶;二者,相比于曾经的重董仲舒、荀子而轻孟子,这一时期康有为重德性轻质性,知气神明虽有差别,然总的来说都属人性之高层次面,而气质体魄作为赘物则被轻蔑地抛弃了。于是在人性论上,康有为对“质性”无有多谈,而专以“德性”及其“神明”内涵论述:
孟子探原于天,尊其魂而贱其魄,以人性之灵明皆善,此出于天生,而非禀于父母者。厚待于人,舍其恶而称其善,以人性之质点可为善,则可谓性为善,推之青云之上,而人不可甘隳于尘土也。盖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故可以全世界皆善,恺梯慈祥,和平中正,无险诐之心,无愁欲之气。建德之国,妙音之天,盖太平大同世之人如此。[43]
性者,天赋之知气神明……人为天生,性为天命,收摄保任其心,无使为物诱所化,则退藏于密,清明在躬。培养扩充其性,无使为习俗所熏,则光明刚大,参赞化育矣。[44]
性是人之“神明”,“天下人与物都在我性内,都是我心性精神所化生”,便有“形而上本体的意义”[45],“神明”也即成纯善之性体,此性善由神明而具有客观性。性与神明“受之于天”,仁为“天性之元德”[46],故此性善又具有超越性。康有为此时以人之“神明”谈性善与早期所论的“善质”已有本质的不同,此性善是在人生性自然之中插入一直贯于天道的道德性本身,乃定然之善,不再是就气之分解而谈其善恶倾向,所以若因康有为“元气”概念更为基础而将其归为自然人性论,恐并非十分合适。善性人人皆有,是人平等自立的根源,若人能扩充,便参天地赞化育,人类社会也能渐渐步入大同,因此,康有为此时所持人性论当称之为“性善论”。
三、电:神之乘
神与电在中国文化中本就有着极深的渊源,二者或都源于“申”。《说文解字》在解释申一字时说:“申,神也。”[47]解释“虹”也说:“虹,籀文虹从申。申,电也。”[48]“申”字之甲骨文象空中电光霹雳卷曲之形,而天之异象变化,古人不知其故,或敬或惧,又以此为神,因此申、神、电三者或同为一源,申为电和神的初文,这一观点也受到近代许多学者的认同②。康有为也认识到了“神”和“电”的相似,但他尚无意探讨三者在字形字义上有何渊源,而是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
在康有为(1858-1927)生活的时代,西方的电器以及物理学已传入中国,康有为敏锐地发现:“今为物质之世界,精于物质者强。电尤物质之至精新者,精于电者尤强。”[49]尽管康有为并不识电之原理,也不知物理学上的电子电荷为何物,但他深受当时传入的电灯、电车、电报等物品的震撼,也粗略地了解到“凡物之动皆由于电”[50]“乾隆时美人弗蓝格林考出物质体内皆有电气”[51]等知识,于是从中抽象出“电”之概念。同时,康有为还认为电无所不通,甚为神妙,“今夫电一杪时则三十万里,人之电力可上达于诸星、诸无量天”[52]。
康有为说:“明德乃天所生,人人有之,能相视以目,相听以耳,如电灯焉。吾已作一书,名《电通》,电一发,即到十二万里。行而上者谓之神,行而下者谓之电。”[53]其中化用《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把“行”理解为“行动”,这句话应当是人之“神”支配人的行动,人之“电”实施人的具体动作,考虑到康有为使用“神”“电”来论述“明德”,则此处兼以“形而上”“形而下”来理解更佳。朱熹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54]朱熹以理气解释人性,人之“义理之性”“天地之性”即是理,它纯粹至善,而人之“气质之性”则受到气禀所限,它遮蔽本性,是恶的根源。在康有为看来,“神”是人之“德性”之精,同于“义理之性”,康有为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55]可以说,“神”就是“理”的一种转化。但“电”字,也说“电气”,康有为不曾论述。《说文解字》言:“电,阴阳激耀也。”[56]古人认为电的产生是阴气阳气激荡产生的,另一方面,电的通达也与气的广泛流通很相似,所以“电”也可以看成“气”的一种转化。“神”,同于“理”,保障人之性善。但是“电”,却不能说完全等于“气”,应该说是“气”中尤为特殊的一种。在理学论域下,气是人之形体的构成,它有清浊偏正之分,对人性构成限制,而康有为则更注重电的通达,电器的实现比中国传统哲学中“气”的不可见来得更加明显,上至宇宙“诸天”,下至物质人体,万物皆由电而可实现通达。
康有为说:“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神气即电气也,……,而神尤为电气之主”[57],此“神气”是《礼记》所言,康有为认为这种“神气”实质是“电气”,并且“神”是“电气”之主宰,故电之通达根源于神,神乘电而有妙能。康有为从无线电中得到灵感,认为人既有“神”,那么体内也当有类似无线电台的东西,可以为人之性善明德提供条件。它不可见,却既能主动地接收外在事物与人发出的电,“国家之兴亡,灾祥皆应”[58]。还可以将自身之电传递出去,影响他人,孔子曾言“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康有为说:“明德,电之为也,无不相吸。故有德者,必有类从,德愈明则党愈多。”[59]有德者修电至强,使得其电发扬出去,相感应者无不相吸,德愈明则朋友愈多。《中庸》言:“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康有为同样认为,此积善一说,并非偶然,而是有德者修电吸引所致,佛教谈因果报应也顺乎此理。甚至于古文中一些不可解的事迹,如曾母啮指而曾子心痛,杞妇哭而崩城,孟宗哭竹生笋,阮孝绪母病而自归,尹敏母思子而尹敏亦心痛而自归等等,在康有为看来也都是人体中电的通达所导致的。
“神明”善性人人皆有,电亦人人皆有,关键在于是否自修,若能内在地接收电,保存电,“修电之点而为电团,务令聚而不散,则长明不昧,长存不散”[60],便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及至最高境界,康有为说:“明之至则超凡人圣、造化同游,其理同于电矣。……知电通之理,则人世之富贵贫贱不足介意,而地球之微渺不足婴吾念虑矣。”[61]可谓纯体透亮,光大无穷,无不烛照。历来保持人性本善,不随物欲所隔绝的求善工夫,康有为也都以电来解释,孔子之“克己”,《周易》“斋戒以神明其德”,《大学》“明德”,《中庸》之“诚”、“慎独”,乃至于老子之道,佛教、基督教之修炼等等,凡是与“神明”相关的工夫,都不过此修电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有时又认为“知气”就是“电气”,“知气者,灵魂也,略同电气,物皆有之”[62],甚至还将“不忍人之心”等同于“电”、“以太”,“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63]。在这种情况下,神与电似乎又不再有形上形下的差别,“精神、意识与物质的‘电’等同起来”了[64],神就是电,电就是神,物质性的电直接就被赋予了精神属性,有了价值蕴意。
四、结语
“神”与“电”构建出康有为思想中一条通向性善论的理论进路,“神”与心性天通而为一,是在人气质之中竖贯一道德性本身,并非就气质横向之分解而言“善质”,此为义一。“神”同“理”,是人性善的根源,“电”似“气”,但并不隔绝人之性善,反而当修电以致善,此为义二。本文所论康有为之性善论,即是就这两义而说明。
康有为晚年时,曾于1923年在《开封演讲辞》中说:“盖性有德性,有气质之性。董子所谓性有阴阳,阳者德性也,阴者气质之性也。二性皆天与人,不可少者。”[65]似是又重新回到了自然人性论。不过也不尽然,康有为称朱子“性即理”一说“不能该人之性,即不能尽人之道也”[66],还言:“《礼纬》、《孝经纬》、荀子、董子,皆谓性者生之质也。有质则内之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固为性也。即外之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身之安逸,亦性也。”[67]因此康有为或是想囊括“生之谓性”与“性善”。从“生之谓性”谈,虽可尽“人之道”,却失去了通向天地和大同的效力;从“性善”谈,虽可尽“天之道”,却忽视了人的欲望追求。他在“生之谓性”与“性善”的选择之间还是存在一定模糊性。
从这个角度看,康有为在人性论上的几经变化,或许正是因为他对思想“外在领域”的重视选超其“内在领域”,“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重视远过对德性问题的注重”。[68]康有为在早期认肯“生之谓性”,是在政治改良的视角下肯定人之欲望以求发展,所以闪烁着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的光芒。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将目光投注到更遥远、更广阔的大同之下,此时,“性善”由于其更强的解释效力、更广的理论空间和更远的理想追求,便重新被康有为所重用。因此,康有为虽一度偏爱起性善论,然最终也未能在人性论这一范畴上形成一套严谨的体系。
同样地,这一不严谨也充斥着康有为的其他思想。就本文来说,虽然康有为在“德性”领域提出的“神”有着形而上本体的高度,但这是通过分析与“神”相等价的概念得来的,康有为对此少有正面的论述。神与电的关系同样不能说明确,有时神与电可区分开来谈,神为形而上,电为形而下,有时神与电又等同起来,跟仁、心、性同处一个层面。
这一现象或许与康有为的经历和性格有很大关系。康有为所处之时代,外有西方入侵,思潮涌进;内有政治衰败,文化消逝,而他本人也多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还接连流亡海外,“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他少有作哲学静思的时间”[69]。同时,康有为本人“武断与教条性的倾向,难以导致哲学上的丰收。他经常显示不愿考虑不同的见解以及不喜欢的事实”[70],因此,他的思想系统并不精致,纰漏和抵牾时常相随。
然而,这并不阻碍康有为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建立哲学系统的思想家,第一个试图用西学来扩大与充实中国哲学的思想家。康有为的思想系统虽深受历史和时代的条件所限,内在上有所不足,但有着崭新的风貌。在人性论上,不论是自然人性论的改制,还是性善论的大同,都是为救亡图存所发;“神电”并举,虽有附会近代科学之嫌,却同样也是传统思想现代化诠释与中西思想聚结融合的开路先锋。此等积极进取之象,对后世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无‘尽精微’之力,却有‘致广大’之功”[71],以此来总结康有为的人性论乃至全部思想,可谓极致之辞。
注释:
①匡钊总结了先秦关于“魂”和“魄”的思想,认为“魄”关乎人的形躯,决定了人生来具有的一些经验层面的感识和运动,而“魂”则决定了人高层的精神意识和认知(《心灵与魂魄——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观念的形而上学共性》,《文史哲》2017年第5期);《中国哲学大辞典》认为“知气”、“魂知”被康有为指代人的知觉精神(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46页“知气”词条和第688-689页“魂知”词条)。
②高田忠周,马叙伦,杨树达,田倩君,张日升等人皆持此种观点,参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3-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