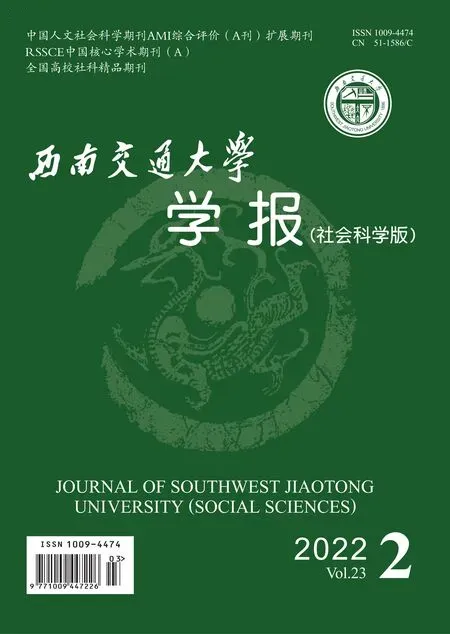严复翻译实践中语言认同之审视
丁如伟,王 毅
一、引言
在学术界的研究中,“认同”并非一个新兴的概念。廖炳惠编写的《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中有对“identity 认同”〔1〕条目的简要溯源:从古希腊柏拉图开始,“同一”(identity)与“差异”(difference)就开始成为哲学家们探讨的对立范畴,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在关注多元文化身份的同时,“认同”与“身份”的问题也备受关注,认同研究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都有涉及,其对象也具有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如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的、性别的等等,多学科多维度的相关研究赋予了“认同”丰富的内涵,也使围绕“认同”而展开的研究更具吸引力。以往的研究常常把语言认同视为族群和文化的身份标识,强调种族、阶层和性别等社会结构对语言认同的塑造作用,将语言认同简单化为一种社会识别的结果〔2〕。这种仅将语言认同作为族群和文化身份标识的认识观具有单向性,忽视了语言的反作用力。其实,语言认同是在历史、文化、权力等因素作用下由个人和群体在语言实践中持续不断建构而成。语言既表达了认同,也在建构着认同〔2〕。只要个体从事语言实践活动,社会组织和语言结构对个体身份的塑造就处于动态变化中。而这种塑造效果取决于个体是否积极地参与到语言实践中来,进而促发语言认同的建构机制。语言认同通常包含认同主体和语言主体两个方面,一个人所呈现的语言身份是在对语言认同的过程中两个主体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在翻译层面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是不可忽视的认同主体,而译者具有双重语言认同的体认——对籍属语言的认同和对翻译源语的认同,这使得翻译实践中语言认同的主体间性作用更为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结构等权力关系也很繁杂,这些都使语言认同的建构更具复杂性。
晚清时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高潮期,这一时期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成果最引人瞩目,他们二人的成就得到了其同时代人士的认可,如孙宝瑄在其1902年的日记中写道:“今人长于译学者有二人:一严又陵,一林琴南”〔3〕。其中,严复的“八大名译”在近代史上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同时代孙宝瑄对严复积极肯定之外,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对他西学中学的精通程度也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民国的胡适也称其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徜徉在中西文化之间,在其翻译实践中,无论是在务求翻译文笔渊雅方面,还是在文言书写的选择上,抑或是贯穿于文本之中的“文以载道”思想,都极好地诠释了语言认同建构的复杂性。本文拟探讨和分析严复译作中的渊雅文笔、文言书写以及译书传“道”三方面的内容,以探求严复的语言认同对翻译文本的影响以及翻译文本的语言对读者认同的建构作用。
二、语言求雅
晚清时期,翻译语言的文体选择有四种:骈文、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白话文〔4〕。那时的士人多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重视文辞讲究文笔,文辞雅驯的译文容易吸引当时的知识分子阅读,进而促进他们探求西学新知。严复以古文译书,译文文辞考究、文笔雅致,其文言书写受到晚清民国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高度称赞:“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5〕。民国时期蔡元培认为严复的译文虽给今人以陈旧过时之感,但是就严复时代而言,当时的学者们对这些文言译文还是颇为认可的,而且蔡元培对严复的译书在选材、翻译方法等方面也进行了赞赏〔4〕。无论是译书文本的选材、语言文体的选择还是翻译方法策略的选取,都遵循着译者文化认同的理性逻辑,而译者的文化认同又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按照福柯的权力关系的概念,社会中所有相互作用关系均隶属于权力关系的范畴。社会主体文化和主流价值等因素促成了严复的语言选择,在翻译实践中也体现出了文化结构、历史背景等多重因素对他的影响。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译者的语言认同起到了建构作用。
严复与晚清桐城派有着密切复杂的关系,至于是否可以将他划归于桐城派这里不做赘言(1)相关研究可参见潘务正《严复与桐城派——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不收严复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见《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1-4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翻译语言效仿了桐城古文。他与桐城派吴汝纶的交往甚密,二人常有书信往来。《严复集》收编的严吴之间的书信共有11封(其中吴汝纶的信札8封,严复的信札3封),这些书信除吴汝纶的第7封信内容与翻译无关外,其他10封书信都有对严复西书翻译工作的讨论或内容,这足以证明吴汝纶对严复的翻译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吴汝纶在给严复的一封回信中表达了用文言翻译西书的意见:“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所称叙记、典至二门,似为得体……欧洲记述名人,失之过详,此宜以迁、固史法裁之。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6〕吴汝纶认为翻译应求雅洁,应当以司马迁、班固的史书写作手法为参照标准进行翻译,以便为译文行之久远做些思虑。吴汝纶在《天演论》序言中也同样表达了关于翻译文体的看法:“凡吾圣贤之教,上着,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5〕这一句道出了“文”与“道”的关系,文统之传承是桐城派文论的精神支撑,而文统延续又与道统相表里〔7〕,正是“文以载道”思想的反映。从严复的翻译实践来看,吴汝纶这些有关翻译的思想对他有着一定的影响,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8〕。由此可见他极为认同吴汝纶的观点。
另外,严复在与梁启超的通信中阐述了他的语言美学观:“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9〕这段文字印证了严复对吴汝纶“雅洁论”的认同,他赞赏司马迁、韩愈的语体风格,并以二人文章为书写典范。吴汝纶建议严复“此宜以迁、固史法”来削减欧洲名人传记,可见严复与吴汝纶都对司马迁的书写风格极为认同和推崇,二人论见彰显出典型的桐城派“雅洁”文体论说的特征。“雅洁论”自桐城派开创之初就已现雏形,桐城派初祖方苞认为《史记》的书写最为完备的言说示范了“雅洁”义法,并示人以法度,“雅洁论”对桐城派文体语言风格的形成影响深远〔10〕。吴汝纶作为桐城派的主要代表,他的语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严复,后者又将桐城派理论付诸翻译实践中,从中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胡适直称严复是桐城派的嫡系了〔11〕。不过从严复对籍属文化的认同方面来说,与其说他的翻译实践源自对桐城派语言观的认同,还不如说是在古今新旧文化的较量之中、在文言白话相争的语境之下他对于文言书写、古言古体有更高的认同度。
三、文言书写
严复认同文言,但又不是绝对地肯定它,他对中国文言文体的含混性和模糊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严复在《政治讲义》中对文言的弊端批判道:“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12〕他认为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最大阻力是中国文字,他批评中国文言逻辑不清晰,要精准地言说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很大困难:“其一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难;二是思理层析,准确表达难”〔12〕。这体现了他对自身语言文化身份的焦虑,但面对文言的这种缺陷严复又显得束手无策,他表示这样的语言只能将就对付使用,除了修正改良、谨慎使用之外别无他法。严复在翻译实践中极为重视遣词造句的准确性、明晰性以及行文写作的层次性、逻辑性,这得益于他对西方的逻辑学的研究。他翻译的《穆勒名学》对其思想有深远的影响,就如史华兹所言:“严复的译著《穆勒名学》(Logic)是严复综合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13〕。1900年到1902年间,严复翻译完成了《穆勒名学》上半部,并于1905年首版发行。1905年严复接受上海青年会邀请讲演西方政治学,演讲稿题目是《政治讲义》,这次演讲中他所表达的一些观点显然受到了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严复习惯于从逻辑学的角度去审视古文的语言组织、文章脉络,以“异域之眼”对文章逻辑进行考辨。严复在点评《古文辞类纂》时说将苏轼的《始皇论》收录在内并不妥当,他在文中批注道:“此篇实不必选,目下第以二圈尤非”〔14〕。他给出不该选择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其不符合逻辑,“此篇立论最不合名学而有纠缠之处”〔12〕。可见严复对文章是否应当入选的判断依据是逻辑学。我们可以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来解释他的这种做法:严复具有双重文化体认,他自身的文化体认有时处于与籍属文化相异的一个位置点,他站在文化“他者”逻辑学的位置点上对籍属文化不符逻辑的地方是不予以认同的。而且严复对“自我”文化的认识和定位也绝非单单缘于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同,他对语言逻辑表达精准性的要求是与他本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对他治学影响最大的应是他自幼所浸淫的籍属文化,他的私塾先生黄少岩对其治学的影响非常大。在黄先生“汉宋并重”〔15〕思想的教导下,严复年少时便秉承了宋元明儒的学术作风,又颇受重考据实学、治学严谨的清代“汉学”的熏陶,追求对系统知识的掌握。史华兹也认为:严复所表现的治学态度可能来自他早年受到的“汉学”家治学方法的训练〔13〕。对于严复这种受到中西文化双重影响的情况,可以借用霍尔的文化认同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有两个同时发生的轴心或向量“建构”人们的身份认同: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其实质是阐释文化认同的同一性和差异性问题〔16〕。可见严复对语言的认同是中西文化的“同一”和“差异”互动的结果。
严复深知用文言翻译西书,无论在文体表达方面还是在逻辑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困难,他之所以选择用文言翻译,一是因为他认同“雅洁说”,在翻译中要达到“雅洁”的行文要求;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心中有预设的译书读者群体,这类读者诵读古书、吟诵文言,对文言语体更为认同。严复的这种想法可在他给梁启超的回信中得到印证:“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9〕他在回信中还说明翻译的目的“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9〕,他深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9〕这一众口难调的道理,他期望的目标读者并非市井乡僻的大众之人,也不奢望普通民众会对他的书感兴趣,他意在呼吁读古书、熟古言的知识分子通过阅读他翻译的西书能够对社会有所警醒,因此他投其所好地选用了这类人群更易接受的语言。吴汝纶与严复的通信中也有关于译本的预设读者的探讨,吴汝纶认为:“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6〕。他们的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舞文弄墨的士绅们往往对俗言鄙语不屑一顾,再加上严复的翻译文本极其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只有当时的知识分子才可能有阅读的兴趣,引介西学、传播新知及开阔思想也只能最先从精英阶层进行思想启蒙,进而再自上而下影响到普通民众。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取向以及权力结构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严复对文言有更高的认同度,因而去追求贵族化的文言书写。胡适也对严复选择古文译书予以理解,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正是由于严复的文言书写才使得他的译书身价得以提高〔11〕。可以说严复的文言书写是使译本在士人阶层流行开来的一块敲门砖,而且历史表明他的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严复的翻译文本备受士绅群体以及智识分子的青睐,他的翻译作品在晚清风行二十年之久,很多人都从严译引介的西方思想中开拓了国际视野。由此可见,严复深谙国人不同阶层人士对籍属文化的认同之道,认识到传统对一个人的语言认同的影响和塑造的力量。传统可以连接“语言和思想,过去的知识和当前的认识,社会群体中个体间的差异”〔17〕,在将中西文化置于同一个时空当中时,读者对籍属语言的习惯性认同使得异域“他者”的差异性更为凸显,而异于“自我”的“他者”文化容易激起读者心中的排他性情感,严复为了避免这种情感的产生,依照预设读者的喜好,兼顾读者的身份,将异域的“他者”改装换面,变成他们可以接受的身份,促进了思想的传播,使得读者在无意识之中重塑或建构了自身认同。
四、译书传“道”
严复所译文本并非辞藻华丽、空洞无物的古文,它们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胡适对其文本形式和内容就有较高的评价:“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11〕严复能取得这些译书成就不仅仅是源于他扎实的古文功底和渊博的西学知识,更在于他具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译匠精神。中国清朝时期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西学术思想更是少有交流,在学习西方最新文化思想时,中国语言中很少有对等的词句来表达,严复在文章中就有所论及:“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8〕。当时各种新的理论纷至沓来,名目各异种类繁多,在中文中很少能找到对应词,即使勉强可以对上,还是多少有差别,让人感觉勉强,也只能靠译者自己斟酌揣摩了,所以严复在翻译西学时在语言文字选择方面非常用心。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说道:“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申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18〕从对英文字词的追古溯源、广罗涵义,再到从中文中摘寻相似表达,无不显示出严复务实求真的翻译态度。在给张元济的信中他也提到:“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踯躅,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19〕可见严复在选词酌句上的严肃认真,在用汉语传达西学内容上的一丝不苟,避免了梁启超在《论译书》中所说的“徇华文而失西义”以及“徇西文而梗华读”〔20〕二弊的出现,以求做到翻译文本的词切意合,努力使文本达到尽善尽美的效果。严复这种认真翻译的态度是因为认同“文以载道”的主张,熟知语言是思想的外在形式,并服务于思想的传达,他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达情感之音声也”〔9〕。他的翻译思想实则是与人生抱负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想借翻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严复的翻译活动始于《天演论》,其长子严璩在《严先生年谱》〔6〕中交代了该书的翻译背景,明确说明了严复正是在甲午战争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刺激之下开始致力于翻译著述的。其时泱泱中华败给东瀛小国,使得国人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这一时期的人们在对待中国文化上也表现出了复杂的感情。籍属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碰撞,人们文化身份的纯粹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对于精通中西文化的严复而言,他认为“西人所孜孜勤求”的大事是“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21〕,而国内的当务之急是“鼓民力”、“开民智”及“新民德”,于是寄希望于西学思想以达成所愿。他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提到,面对“民智不开”,朝廷之中“守旧”与“维新”两种模式都无法达成的现实状况,为了之后能够让士人群体以及普通民众更多地了解、辨明中西实情,以求扭转乾坤、力挽狂澜,他选择“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22〕。他很乐观地认为西学具有启迪民智的功用,将愈愚救亡的抱负同西方思想密切地关联了起来,借此期待中华民族的复苏,并在《原强》中提出了国家富强复兴的战略步骤和构想。严复认为要首先在民力、民智、民德这些方面下功夫,寄希望于西方的达尔文、斯宾塞的思想,以求物类繁衍、保种救国,而寻求富强则是其后要做的事情。严复认识到寻求富强并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定的践行步骤,“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23〕。因此,在严复思想体系中,强国之路要从保种图存开始,然后呼吁实行能够使人们自治、自由、自利的利民之政,最终达到富强的目的,他的这种富强要有渐序渐进步骤的思想从他八大译作的主题选择的先后顺序中可以得到佐证。严复竭其所能地对译本精心编排、精雕细琢,只为西方思想能够在国人中有更高的认同度。他以译文载西学之道,宣传西学,启蒙国人,很好地阐释了语言对认同的建构作用。
五、结语
严复在翻译中务求语言渊雅,“与其伤洁,毋宁失真”〔6〕体现了当时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因素对其语言认同的影响,而且严复深受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在西方的生活经历和获取的西学知识又对其语言认同有所塑造,他以“异域之眼”对本土语言进行反思,对文言文体逻辑不清晰的弊端予以批判。尽管如此,严复不放弃以文言书写来吸引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以精益求精的译匠精神追求中西文本尽善尽美的对应效果,他的这种努力也促使译本在晚清士人群体有了较好认同度,在有形无形之中通过语言建构了国人的认同感。严复译书,正如他在《天演论》〔25〕结尾引用诗人丁尼孙的诗那样践行着“载理想之羽翼、达情感之音声”的文以载道思想,通过译书实现了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及“愈愚”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