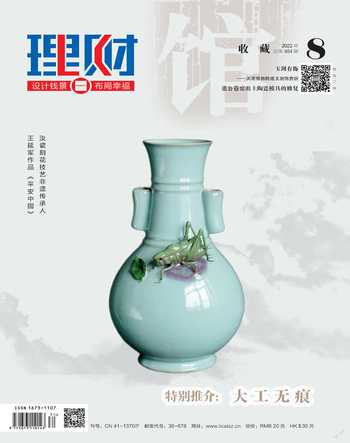唐代仿制品浅议
贾中宝

唐代是中国封建制国家的顶峰,国力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朝又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疆域空前扩大,规模空前统一,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唐代的仿制品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
唐代仿制品产生的背景
人们往往通过交往和商品了解到外部世界,同时激发出对未知事物的渴求。唐代无论是基于贸易、猎奇、宗教还是其他原因而来的外国人,都给繁荣昌盛的帝国带来了生机。城内专门设置了接待胡商的邸店,定居的外国人也开办了酒馆、店铺,双方都在实现自己目的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融合着异样的文化。
唐代仿制品产生的原因及外来文化在文物和遗址中的反映
以南北朝民族融合和外来文化渗透为基础形成的唐文化,展示出了多元性和包容性。各国文化,甚至相互冲突的信仰在唐代得到容纳,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之间和睦相处在世界史上也属罕见。唐代佛教兴盛达到高峰,长安城内包括玄奘主持翻译印度佛经的慈恩寺大雁塔等遗迹至今犹存,敦煌、龙门等地遗留下的石窟造像更多。西安西郊土门村发现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祅教徒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志文汉文和中古波斯文合璧,说明晚唐时仍有懂得中古波斯文的人。长安西市南大街中部街南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附有加工作坊的珍宝商行遗址,反映当时跋涉兴贩的“胡客”店铺的真实存在。乾县章怀太子墓有两幅“客使图”壁画,每幅绘六个人,其中服饰相同、举止稳重的三人是迎接外国来宾的外交官,另外着装各异、面目有别的是客使,分别表现着东罗马、高丽、高昌、吐蕃、大食等各国的使者,更进一步证实了对外交往的兴盛。
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出土遗物中得到生动体现。文献中记载波斯马球运动在长安风靡一时,对应的遗物有唐章怀太子墓打马球的壁画场景,而打马球的陶俑更在墓葬随葬品中多次发现,长安城禁苑遗址中还出土方形奠基石碑一块,上刻“含光殿及球场”。大量的陶俑和壁画人物盛行胡服也明显地反映与西方世界的交往。
唐代仿制品的特点
1.唐代仿制品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当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和现实时,风格突变、创新的器物就会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粟特银器的传入,使唐代产生出一批新颖的器类。何家村出土的人物纹金带把、乐伎纹银带把杯,就是与粟特银器最为接近的器物。突出的特征是杯把部分做得很精致,环形把的上面带宽指垫,下面有指鋬,连粟特带把杯指垫上的胡人头像,甚至两个相背的胡人头像的做法,均精细地表现出来。环形把的外侧还做出连珠装饰。这种由大连珠装饰的环形把曾是中亚各民族较普遍采用的做法。但是唐代的金银带把杯有的采用中国传统铸造方法制作。这些器物如不是粟特工匠在唐朝的制品,至少也是唐朝工匠直接的仿造。同类的带把杯在形制上模仿粟特银器的同时,纹样却是中国特色的缠枝、花鸟等。唐代的手工业者仍属工乐杂户,大都是被动应役,少有创作自由,如果不是供求双方的认可,不会出现大量仿制品。仿制行为不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终结,通过模仿在工艺技巧和艺术形式上获得启示,伴随着输入品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器物。唐代陶瓷器中大量的被称为胡瓶的带把壶,就是直接借鉴西方而成为唐朝流行器物的。但似乎唐朝人仍把胡瓶看作是外来器物,因此在与人物和某些场景相结合出现时,总与胡人、商旅有关,壁画和塑像上的胡人执胡瓶、骆驼背上悬挂胡瓶是唐代常见的形象。
2.唐代仿制品取材广泛,材料丰富
唐代仿造的器物取材于各個不同地区。唐代器物中一些称为洗、盏、碟、盘、船形杯、花口形杯等,显然是源于萨珊的器物,特点是器身为长方形多曲,杯体较浅,对称的曲瓣使器内凸棱,外表为凹线,有椭圆形矮圈足。由于长杯的数量较多,可以按时代早晚将之依次排列发现渐变的过程。唐代前期的长杯,形制上忠实地模仿萨珊多曲长杯的造型,两侧曲瓣不及底,为横向分层式,几乎是萨珊式器物的翻版。但由于信仰和审美的原因,萨珊长杯上与信奉拜火教有关的阿那希塔裸体或半裸体女神、圣树和水中鱼怪等题材,遭到唐代工匠们的摒弃,而代之以唐代繁缛细密的植物纹样。
唐代高足杯曾一度成为当时器物作品的典范,金、银、铜、锡、石、玻璃、陶瓷的材质都用来制造。这些器物大都处于墓葬之中,年代比较明确,证明外来样式的仿制高足杯流行的时代是在唐代前期。由于中、小型墓葬和瓷窑遗址都出土较多的高足杯,说明源于西方的高足杯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成为较常见的日常生活器皿。
3.唐代仿制品先重美观艺术再重实用性
唐代仿制的萨珊多曲长杯宛如开放花朵式的造型给人以美感,却因分曲形成凸起的条棱使内部失去光滑。如果只是追求艺术效果而不关心实用性,这样的仿造很难坚持长久,因此要寻求解决两者之间矛盾的办法,就是进行改造调整。唐代后期这类器物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曲瓣从口到底成为纵向式,分曲减少并趋于平滑;还有一种是基本保持着横向分层式的多曲,却淡化了凸鼓的曲瓣,加深了杯体,增高了圈足。这一演变表明唐后期萨珊特征只能说是一种痕迹,实际上已经与其母体分道扬镳,异域风格服从了实用安排,外来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进行了重新搭配组合,最终演变为创新器物。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符合大众的共同喜好并有实用性的器物,就会具有流行于社会的生命力。萨珊多曲长杯对中国器物造型的影响,不仅局限在金银器上,滑石、白瓷、玉、玻璃器物也普遍出现,越是精心模仿的,一般时代越早而且可能是非实用性器物。宁夏固原唐总章二年(669年)史诃丹墓和西安唐总章元年李爽墓出土的多曲玻璃杯,无法准确肯定产地,可能是在对西方玻璃造型、装饰和原料都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的仿制品。日本正仓院藏有一件十二曲玻璃长杯,底部没有足,成圆底,采用吹制手法成型,器物外壁刻花草和动物,造型与日本自身的容器毫无关系,原料成分中含铅极高,达55%,与中亚、西亚玻璃不同,却与中国制造的玻璃成分相类,被推测为中国仿西亚器物的制品。
高足杯不是中国传统器形,呼和浩特毕克齐镇和西安城郊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银高足杯,已基本肯定是西方输入的产品。这种器物上部为圆形或多曲形的杯体,下部是器足,足的顶部较细,中部一般有算盘珠式节,下部向外撇呈喇叭状。陶瓷高足杯的出现可上溯到东晋,但数量极少,大都出土于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西地区。这一特别现象似乎与跟东罗马的交往有关。中国通过南海与罗马—拜占庭交往的历史悠久。隋唐时陆路交通兴起,《隋书·裴矩传》记载了通往东罗马的三条商路中,“北道从伊吾,经过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佛菻シ国,达于西海”。此路须绕道黑海,这一区域正是高足杯流行的地区。唐代是一个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时代,高足杯这种西方特征的器物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许多仿制品,但与仿制萨珊多曲长杯一样,纹样采用唐代的缠枝花卉、狩猎、各种动物。唐代后期高足杯的形制也逐渐变化,形成粗筒状的喇叭圈足,杯身流行花口浅瓣式,整体已改造成为一种新的器物,并流行到宋代以后。
对外来装饰纹样的吸收融合是唐代的普遍现象。金银器、石刻、丝织品中的周围环绕圆框的“徽章式纹样”,本是萨珊艺术特征,却在唐代得到广泛的应用。但这些意趣相同的构图细部中并不相同,萨珊纹饰中环绕圆框连珠圈内的野猪头、口衔垂珠项链的立鸟被卧鹿、立鸟取代,丝织品上又发展出单鹿、对鹿、对马、对孔雀以及天马骑士等纹样。那些朱雀、凤凰口衔丝带的纹饰还出现在铜镜上,称为鸾鸟衔胜等。纹样通常反映一定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由于观念上的差异,人们不完全了解外来的纹样含义,感兴趣的只是艺术形式。在改造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产地的大多数特征,兼收并蓄之后,出现了别具一格的纹样。“徽章式纹样”圆框多是连珠纹,突然兴盛在北朝至唐代前期并非偶然,敦煌壁画的边饰、彩塑服饰以及石刻和木质家具等遗物上常常见到。尽管如此,人们心目中仍把这类纹样看作是异域风格。在传世的《步辇图》上,晋见唐太宗的吐蕃使节禄东赞,身着连珠纹样的窄袖胡服为异域标识。唐代前期一度涌现的葡萄纹也与西方艺术的影响有关,最为明显的是唐代极富特色葡萄纹铜镜大量涌现,它们绝大多数出土于7世纪中叶到8世纪前半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葬中。较早的葡萄纹铜镜内外区之间和边缘饰锯齿纹和突出瑞兽,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做法,这些纹饰与葡萄纹相结合,是葡萄纹铜镜产生初期的特点。但葡萄纹很快变为铜镜的主体而兴盛起来,有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葡萄纹柔长的枝条、舒展的花叶、丰硕的果实与生动的瑞兽、活泼的飞禽构成了新颖的图案,十分符合盛唐时期追求华丽的审美取向。在古代世界堪稱精湛独特的中国瓷器,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启迪,主要不是体现在瓷器工艺上,而是在造型和纹样方面。
崇尚外来事物在唐朝前期成为潮流,甚至引发起居生活方式的变化。唐代灭突厥后,大批突厥人入居内地,带来了新的生活与文化方式,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行为举止有礼仪制度约束的太子李承潜,日常生活也极力模仿突厥语言、服饰并喜欢居住帐篷,欣赏其习俗。说明唐朝对异种文化的接纳并不受多少限制。大诗人白居易也喜欢住毡帐,并写了大量毡帐诗。对外来物品的使用也反映在考古发现的遗物上。陕西房陵公主墓壁画表现的进食场景中,侍女手持高足杯、带把执壶等是外来器物的样式,甚至连用手指掐住杯足那种不自然的执壶方式也模仿着异域情调。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兽首玛瑙角杯是流行在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器类,与中国生活习俗无关,却在西安、洛阳、湖北唐墓出土的唐三彩仿制品中出现,体现了置传统而不顾、对器物实用性要求远不如追求新奇奢华重要的时代风尚。
结 语
唐代仿制品之所以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与唐朝是中国封建国家发展的高峰阶段,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融合、多民族统一和谐发展密切相关。唐代仿制品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从开始对极个别器物的仿造,到大量的多个器物的仿造,从生搬硬套到结合本国的国情,融合本国的传统习惯和观念,在外来器物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仿造出适合本国人民使用的大量生活器物。正因为有如此多的仿制,生产出大批量的生产、生活器物,现在我们才可以从墓葬、遗址、传世品等文物和遗迹中看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