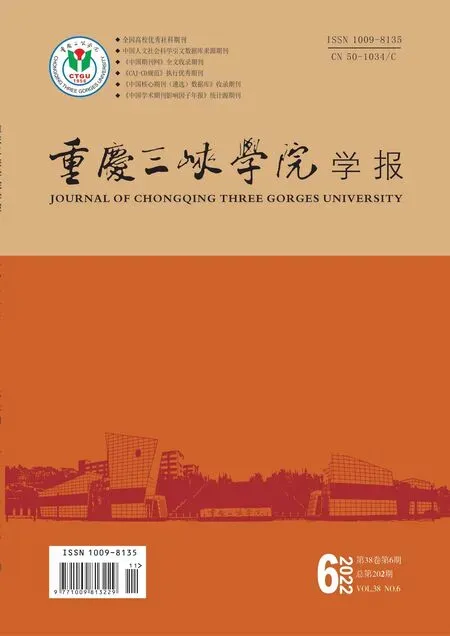周作人的小诗翻译与创作观念溯源
王金黄
周作人的小诗翻译与创作观念溯源
王金黄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在新诗发展史上,周作人的小诗探索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一方面,他通过对日本俳句、短歌、俗歌、童谣以及希腊古诗等作品的大量翻译,为小诗运动的发生和兴起提供了可资借鉴且丰富多元的外来资源。另一方面,在译介的基础上汲取日本和古希腊小诗的精髓,提出简洁含蓄的形式主张与人间本位主义的小诗观念,在日常情感的表达与世俗欲望的书写中品味人生。同时,以审慎“即兴”的方式进行小诗创作,彰显出新文学为人生的底蕴。从翻译实践到观念建构,再到创作尝试,周作人的小诗探索都离不开欧日渊源施加的双重影响,并在小诗运动的助推下汇入新诗发展的血脉当中。
周作人;小诗创作观念;人间本位主义;欧日渊源;审慎即兴
对中国新诗史的考察与研究,首先要解决新诗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周作人始终是一位无法回避且无法绕开的重要探索者与开拓者。日本学者小川利康认为,他在“五四”诗体改革运动中做出了两大突出贡献,一是“发表《小河》尝试散文诗”,二是“译介日本俳句短歌尝试小诗”[1]。这个评价颇为中肯。如果说《小河》的写作是为新诗的长足发展揭开了序幕,那么周作人对于小诗的集中译介、创作尝试以及长期关注,则积极响应并有力地推进了诗界革命的进程。
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初期阶段的标志之一,小诗运动大抵从1919年开端,在1921年至1924年达到顶峰,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诗歌创作潮流,迅速风靡整个20年代,持续近10年之久[2]。相比之下,周作人对小诗的关注则明显早了许多。1916年6月,他发表在《叒社丛刊》第3期上的杂录五则,就包含了一篇《日本之俳句》(署名启明),这可以视为开端;而作为下限,直到1959年上半年还在翻译石川啄木的短歌集,表明即使在小诗运动已衰落式微的50年代,周作人也不曾忘记小诗这一诗体对中国新诗建构的独特意义与价值。可见,周作人对小诗的关注是持续的、动态的而非间歇的、平面的,是有建设性目的而非偶然性随感的,这种瞩目的限度已经超出了小诗运动的创作藩篱,而与“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整体风貌以及发展走向有着密切的连接。周作人与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的关系,历来是学界研讨的重点,从他对小诗关注的起止也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诗歌对小诗运动的直接影响。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源头?周作人的小诗翻译、小诗观念及其创作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如何从新诗发生的角度看待和评价周作人对小诗的情感态度与精神寄托?这些都是值得重新思考和反复审视的问题,也是厘清周作人对新诗贡献的解题关键。
一、周作人小诗翻译的多向维度
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并行不悖、交织渗透,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历程的一大独特景观,这与新文学力求摆脱旧文学影响的诉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翻译的发生必然离不开异质文化的输入与接触,由此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潮。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周作人早年旅日留学(1906—1911)的经历,为他投入文学翻译事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条件。然而,在中日关系逆转下的日本经验又具备双重性,“它既是抒情个体栖居异国的见闻、感知、情绪与思想的聚合,也包含着对日本文学乃至间接对西方文学的接受与体味状态”[3]。作为东西方文化传播与接受的中转站,周作人在日本并没有为故国传统文学的没落黯然神伤,也没有拘囿于日本一国之文学,而是博采众长,广泛吸纳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优秀文学资源加以译介。仅小诗的翻译,就涉及希腊古诗、法国俳谐诗以及日本的俳句、短歌、俗歌、儿歌、童谣等,除泰戈尔之外几乎涵盖了从古至今东西方小诗体裁的代表性创作。
首先是对日本小诗的大力引介与翻译。就俳句而言,周作人重点选择诗人小林一茶,在《一茶的诗》(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1期)一文中进行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解读。开篇即指出了日本俳句的两大特征,即描写情景的“简洁含蓄”与“意在言外”的暗示,同时点明小林一茶“几乎是空前而且绝后”的风格特征,“冷笑里含着热泪”“乖张而且慈悲”[4]540,这也可以看出选译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及其流传背后的文化深意。值得注意的是,他不纯然是对小林一茶50首俳句的翻译,而是将其分阶段、分层次地镶嵌在整篇译介的行文中,便于读者深入三昧地进行品读和回味。这种译介方式同样运用在《日本的小诗》(载《诗》1923年第2卷第1期)一文中,不过这一篇原本就是他在清华大学的讲演稿,因而不可能只是诗歌的译本。周作人此文较系统地回顾了俳句历史沿革的起承转合,列举松永贞德、西山宗因、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正冈子规等四个时期的杰出俳人,译出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共20首,由此大体构成了周作人俳句翻译的经纬。就短歌而言,翻译的主要作品有武者小路实笃的《劳动的歌六首》第1~3首(载1920年12月26日上海《批评》第五号),《石川啄木的短歌》21首(载《诗》1922年第1卷第5期),《杂译日本诗三十首》中的近10首(载《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4期)等。除了以上这些近现代以来的日本诗人诗作之外,短歌的翻译还应包括那些分散在日本古代经典中的大量作品,诸如《古事记》中神语的歌、天皇作的歌、夷曲、战歌、对答歌、行旅歌、酒乐歌、婚丧歌、宫人调、天田调、读歌、召幸歌、伴舞歌、狩猎歌等,《枕草子》中的酬唱歌与各地方短曲,甚至在《平家物语》以及《狂言选》里也有许多短歌和唱曲。周作人翻译时,有意保留短歌的形式,从整体勾勒出小诗这一形态的发展变迁史。就俗歌而言,不少篇章都以小诗的面目呈现,收录在《日本俗歌六十首》中(前40首载《诗》1922年第1卷第2期,后20首载《努力周报》1922年第20期,署名仲密)。它包含了“日本民间合乐或徒歌的歌词”,种类繁多,“如形式上的端呗与都都逸等,性质上的盆踊歌插秧歌以及‘花柳社会’的歌;现在不加分别,只统称俗歌”;其特色仍是言简意赅,“能在寥寥两三句话里,包括一个人生的悲喜剧”[5]。儿歌和童谣,主要译有柳泽健元的《儿童的世界(论童谣)》(载《诗》1922年第1卷第1期)、小林章子的《星的小孩》(载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署名仲密)以及北原白秋的《儿歌里的萤火》(载《歌谣》1936年第2卷第29期,署名知堂)等,共计27首。
其次是对欧洲小诗的翻译。大体包括《杂译希腊古诗二十一首》(前18首译于1924年5—6月,未发表;后3首从《希腊讽刺小诗》中选取,载《语丝》1924年第2期,署名开明)、《法国的俳谐诗二十七首》(载《诗》1922年第1卷第3期)以及分散在《论小诗》(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第6卷第29期)等文章中的古希腊诗铭零星译作。虽然周作人把波德莱尔的诗作称为“散文小诗”,但不论是形式还是旨趣都应属于散文诗的范畴,所以不算在内。从严格意义上讲,27首法国俳谐诗绝非欧洲本土的产物,完全是仿效日本俳句的舶来品,而且周作人直接译自日语而非法语或英语。1921年11月,与谢野宽在《明星》第一期上进行译介,第二年3月就翻译过来,基本上与日本的接受同步。可以说,法国的俳谐诗在创作地域上属于欧洲,但其文化基因却与日本俳句同宗同源。
归纳起来,周作人的小诗翻译主要有两大源头:一是日本小诗,二是希腊古诗,基本上都收录在《陀螺》(北京:新潮社出版,1925年)这本集子里。对于小诗翻译的方法和态度,他以直译法来自白,“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6]424。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直译法既不是死译,也不是胡译,而是一种融合了意译的直观译法,富于变化却又不逾矩,能够兼顾诗形的定式与诗意的传达。在他的翻译下,即使是同一题材或同一类型的小诗,也能够显示出不同的风味和迥异的境况(比如日本各地儿歌里的萤火、小林一茶人生各阶段创作的俳句等等),从而让小诗对于日常生活及心境流动的多维凝聚和映射功能得以保存。另外,小诗翻译的多向维度还体现在多国文学史的架构上,确切地说,周作人是在古希腊文学史、法国文学史以及日本文学史的框架整合下从事翻译的。以日本小诗为例,他的翻译既囊括了俳句、短歌、俗歌、儿歌、童谣等多种类型,也从历史的维度呈现了上古、中古、近代乃至现代的诸种小诗形态,而且涉及官方—民间、大人—孩童、男性—女性等多重诗歌场域,构筑起一个庞大宽广的小诗世界,而这个小诗世界又是整个日本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子集,为他的小诗观念生发与创作试验提供了体系化的多维视野,并奠定了丰盈而充实的生态基础。
二、周作人小诗观念的欧日渊源
相比于成果集中且数目繁多的翻译作品,周作人没有关于小诗的专门性论著,只有几篇散见于报刊书籍的文章,比如《论小诗》《〈陀螺〉序》等,有的是大学讲座的演讲稿,有的是译诗集的序言或译作前的简要说明,有的则是对某位日本诗人诗作的译介评析。整体而言,周作人的小诗理论是不成完备体系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认识和看法在当时的确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与引领性,指引并概括了小诗创作乃至小诗运动的发展及走向。不妨把这些散布的真知灼见称为小诗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就从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来,因此也拥有两个共同的源头——古希腊和日本。实际上,中国历代诗歌都不乏小诗这一形体,从先秦《诗经》到唐代绝句,从宋词小令到民间的子夜歌、懊侬歌等等,然而这些传统的“小诗体”或是受到严格的韵律限制,或者离不开文言的表达方式,得不到自由发展而最终没落,即使仍有作品不断问世但已无法跳出窠臼,失去了诗歌原有的活力和血肉。周作人借国外小诗的译介来涤荡中国传统小诗的行将就木,以期脱胎换骨为新诗的本色,此为他的小诗观念探寻之缘起。
“所谓小诗,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7]73,这几乎成为小诗外在形式的定论;而日本的31音短歌、17音俳句(其中不包括17音的讽刺诗川柳)以及26音的民间小呗则成为小诗内在形式的渊源,虽然“这几种的区别,短歌大抵是长于抒情,俳句是即景寄情,小呗也以写情为主而更为质朴;至于简洁含蓄则为一切的共同点”[7]75。但事实并非完全绝对,在周作人的论述中似乎存在一些出入,甚至是抵牾的地方。在外在形式上,“《诗经》里有许多篇用叠句式的,每章改换几个字,重复咏叹,也就是小诗的一种变体”[7]73。可见小诗不一定必须限制在四行之内,行数仍可作为一个标准与非标准的分水岭,四行及四行以内为典型的小诗,因用了叠句或重复咏叹而超过了四行、但又在八行以内则为变体的小诗。在简洁含蓄这一内在形式上,周作人有另一种看法:“因为这样小诗颇适于抒写刹那的印象,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至于影响只是及于形式,不必定有闲寂的精神,更不必固执十七字及其他的规则,那是可以不必说的了。”[8]85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论断,是因为“俳句十七字太重压缩,又其语势适于咏叹沉思,所以造成了他独特的历史,以后尽有发展,也未必能超逸这个范围”[8]87。他还认为:“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确是日本诗歌的特色,为别国所不能及的。”[9]不难看出,对于简洁含蓄的认识与运用是存有矛盾的,而这种不完全接受的态度恰恰体现出周作人的清醒与客观,以及秉持的辩证发展理念,这与他对日本文化与文学的独特性把握相一致,在借鉴他者时无需模仿而是要“创造的模拟”,因为“模拟与模仿不同,模拟可能外表与被模拟的像,而内在却并非一致”[10]。也就是说,中国小诗的创作不必全部照搬日本短歌或俳句的字数规则,更不必刻意去模仿日本俳谐精神,而且这些方面绝非学习、挪用所能获取;相反,简洁含蓄这一内在形式特征应置于中国文化语境内加以理解,使之呈现本土诗歌的特色。
在诗作内容上,他主张人间本位主义,在人生的游戏和生活的享乐中追寻艺术的境界。从早期译诗集《陀螺》的命名中,可以窥见周作人对于小诗所表现的内容及其旨归的定位。他貌似漫不经心地选取一件街头巷尾、普普通通的幼儿玩具作为书名,甚至戏谑地称“这一册小集子实在是我的一种玩意儿,所以这名字很是适合”,但又立即正色,这种玩味不是“不诚实的风雅”,也不是“故意的玩笑”,而是“一切的愉快就在这里”的“一无所得”[6]423;里面蕴含着“游戏的三昧”与“艺术的化境”,寄托着一种混杂了忘我造作、享受愉悦以及宗教意味的“道”之理想。这里的“道”尽管也受到小林一茶、石川啄木等日本诗人的影响,但并非日本小诗纤巧诙诡、闲寂幽玄、隐退洒脱或者写生细描等风格的移植栽培。小林一茶的诗不拘泥于一隅而是随心千变万化,或庄严或滑稽,“以万物为人,一切都是亲友的意思”,“以森罗万象为友,一切以人类待遇他们”[4]544,“即使说着阳气的事,底里也含着深的悲哀”[4]547。对此周作人颇以为意,认为这种悲哀值得玩味,因为在悲哀里浸透了浓厚且温存的人世情愫。而石川啄木首倡的“可以吃的诗”则更具人间烟火味,无疑对他的小诗观念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可以吃的啤酒”到“可以吃的诗”,这是一种“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像我们日常吃的小菜一样,对我们是‘必要’的那种诗”[11]207-208。在这里,小诗成为直面生活的产物与真实心绪的照相,回避或蒙混都是对自身的不负责。诗人可以通过小诗这一介质,使每一个情感个体都得到应有的正视,每一种来自生活的刹那情绪和微妙官感都被凝练地记录下来,从而让诗歌承载起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以及对生命本真的敬畏与热切。
不过,日本小诗终究沾染了物哀的底色,周作人便以古希腊的世俗享乐加以冲和。1922年6月13日,他为燕京大学做演讲时曾谈道:“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他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与日本,在思想上是冥想与享乐。”[7]75在此之前,他不曾翻译过印度文学,更未谈论过印度文学对自己的影响,这里所指的“冥想”应是对冰心等其他小诗诗人而言。那么,来源于日本的“享乐”潮流又是什么情形呢?遗憾的是,此次演讲并未展开论述。
两年后,他相继翻译了《杂译希腊古诗二十一首》,这些来自古希腊的小诗打破了东方渊源的单一格局,周作人开始将世俗的种种欲望纳入小诗的摹写范畴中,如第八首和第九首:“蔷薇花盛开只是暂时,过后去寻访,不见蔷薇只有刺了。”(无名氏作)“美如会老,那么及时分享了罢;如若永存,又为甚怕给予那存留的东西呢?”(斯忒拉多作)[12]这两首古希腊小诗都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事物之美,表面上叹息美的转瞬即逝,实际是肯定美在当下的永恒意义,宣扬及时行乐的哲思。与日本小诗表露出来的隐忍、克己的“享乐”相比,希腊古诗明显更具有光明正大、恣意奔放的“享乐”模样。而且更关注和突出世俗个体的官能体验与生活欲求,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与读者直接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小诗的表现空间与主题向度。
三、周作人小诗创作的审慎“即兴”观念
在周作人的诗歌作品序列里,古体诗占据了极大部分,包括五绝、七绝、杂事诗、打油诗、排律、集句、联等体裁,其创作基本上贯穿了他的一生。而新诗只有《过去的生命》(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这一部诗集以及16首未被收录的作品,大多数创作于民国时期,尤其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小诗所占的比例更少,如果把变体的小诗也算在内,大概有20余首,包括:《过去的生命》诗集里的《山居杂诗》《小孩》《花》等;发表在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的《中央公园即目一首》以及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刊》上的《仁慈的小野蛮》;2018年《鲁迅研究月刊》第7期上的《周作人的六首未曾发表过的白话小诗》等。按照周作人的说法:“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13]
这段话有三处值得关注:其一,他认为自己创作的这些散文句法的诗歌当不得“真正的诗”,会让人失望。这既是周作人谦逊的体现,更与他对自己的散文小品创作定位有关,也为他日后处理新诗作品的方式埋下了伏笔。他不注重编辑整理新诗集,导致作品散佚甚至许多未曾面世。因此,他到底创作了多少首新诗、多少首小诗,难以预估。其二,这些新诗被冠以“过去的生命”,可见小诗创作时间之短暂。其三,把这些新诗等同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看似贬抑,实际上是褒扬其诗作的价值和意义。
不难看出,周作人对于诗乃至新诗的创作态度都是极为审慎的,这与两大文学渊源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一边是日本文化和文学传统对情感的极度抑制,一边是古希腊文学对原欲的极度推崇和放纵,他试图在二者之间选择一条不偏不倚的中正道路。在具体创作中,审慎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表现真实的极致要求,二是对表现日常生活口语的凝练。石川啄木曾提出“诗的革命三问”,其中何谓诗人与诗的面目问题,指向了诗的真实这一命题。他认为诗的真实取决于诗人的真实,要“将自己心里所起的时时刻刻的变化,既不粉饰也不歪曲,极其坦白正直地记录下来,加以报导”,因此“诗必须是人类感情生活的变化的严密的报告,老实的日记。因此不能不是断片的——也不可能是总结的”[11]210-211。然而这种诚恳认真的态度以及记录真实的一丝不苟,并不等同于审慎。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做出了进一步的限定,“所谓真实并不单是非虚伪,还须有切迫的情思才行,否则只是谈话而非诗歌了”;“倘若是很平凡浮浅的思想,外面披上诗歌形式的衣裳,那是没有实质的东西,别无足取”[7]77。可见,他的真实须有迫切之情与哲理之思,方可下笔成为小诗。比如《小孩》2首与《中央公园即目一首》均为周作人的“急就章”,前者为他所见孩童的未来幸福而担忧,后者即景抒发愤慨之情,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倡言开路。诗人在对客观现实的体察中,折射出审度时局、谨为民生的忧世情怀。关于小诗的语言,石川啄木认为应“从现代的日常的言词中选取用语”[11]205,特别是“明治四十年代以后的诗非用明治四十年代以后的语言来写不可,这已经不是把口语当作诗的语言合适不合适,容易不容易表达的问题了,而是新诗的精神,也就是时代的精神,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11]209。对于中国的小诗创作而言,只有使用现代白话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鲜活口语,才能摆脱旧体诗词的规则束缚,彰显“五四”时代精神,这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诗坛诉求颇为相似。周作人对此深以为然,《啄木的短歌》一文就是明证。
与之相比,希腊古诗在语言的表达上更加自由多变,也存在较多口语化的痕迹,以至于翻译时增添了不少困难。在简洁含蓄的观念引领下,周作人对小诗语言的选择与洗练都是慎重而非随性的。近年来发现的6首小诗在语言上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露水的人生呀,然而露的光阴,原是在他的夜里。”(《露》)“我有这样一首诗藏在我的心里,我轻轻捉一支笔,我的诗又不在笔里,然而我的诗却无所不在,它像一面镜子似的。”(《镜》)[14]第一首的叹词“呀”与第二首多次出现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看似可有可无或重复啰嗦,实则具有自身的表意功能及其独特的句法价值,这种语言现象在周作人翻译的希腊古诗中较为常见。总体而言,两首小诗都运用了通俗易懂且生活意味浓郁的白话口语,表达流畅清晰,几无多余之字,更无臃肿之句。虽算不上字字珠玑,但可以看出诗人对于语言的把握是精细而周密的。
如果说审慎是周作人小诗创作完成的充分条件,那么,“即兴”则是其创作发生的必要前提。他明确指出:“我有这一种脾气,也就成为一种主张,便是创作以及译述应是为自己的‘即兴’而非为别人的‘应教’。”[15]此处的“即兴”,饱含着“满足自己感性的要求”的况味。因此,他的小诗纵然有赠答之作,也绝无应制敷衍或报刊约稿之流,一切从自我的真情实感出发,是对人间本位主义观念的践行。以《山居杂诗》7首为例,这组小诗写于1921年西山避暑期间,每一首都源于山中生活的日常见闻,或是藤萝缠柏、石榴开花、不知名的果子生长,或是小虫鸣歌、百蛤飞过、黄蜂绕窗、苍蝇黏纸,全是微不足道、每日乃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自然小事。但在那一时一地,诗人敏锐的感官与这些小事物相遇,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正如周作人所言,“做诗的人只要有一种强烈的感兴,觉得不能不说出来,而且有恰好的句调,可以尽量的表现这种心情”,“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7]78。这种属于自己的情思可以帮助诗人摒弃那些属于非我的异质之物,将个体的人生与人类的生活发生链接,从而达到小诗所特有的艺术境界。它既不同于旧体诗词汲汲建构的伦理世界,也不同于儿歌童谣表现的纯粹自然的世界,而是介于“生出在儿童的世界与大人的世界的那边的‘第三之世界’”[16]。这一概念原本由日本学者柳泽健原提出,但他并未作详细的说明和阐释。周作人将其拿来用于建设小诗“即兴”的意境,相比于“大人”功利化的世界,具有更多的人情味;与不沾染世俗的童稚世界相比,它又包含一丝成熟后的思索与哲理。然而,创生于电光石火之间的“第三之世界”,尽管与新诗的自由主义精神相契合,但终因其刹那性和个人化的特点,与社会启蒙及批判的时代主题相背离,为其消隐和没落埋下了伏笔。
四、结语
就在小诗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文坛和学界的各方非议。对此现状,周作人借助为小诗集《农家的草紫》写序的时机,从两个方面给予回应。一是小诗的创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让其发展、成熟,并且也要容许其试错,“期望每年出十个诗人,每月出百篇佳作,不但太性急,也不免望太奢了”,“现在一时的消沉是不足介意的,只须更向前走去,自然可以走到别一个新的境地”[17]651。可见此时的周作人,对于小诗以及小诗运动是充满信心的,且寄予厚望。二是小诗本身所追求的自由精神决定了它的变化万端,需要足够开阔的批评空间来接纳它的存在。“至于小诗的是非,本没有千古不易的定理”,“要论好坏,只能以艺术的优劣,或趣味的同异为准,我不能说小诗都是好的,但也不相信小诗这件东西在根本上便要不得,所以那世俗的笼统的诟病只是一种流行的话,不足凭信”[17]652。但就在10年后,周作人却坦言:“俳句之于中国的诗,虽稍有影响之处,可是诗的改革运动并未成功。”“所谓‘小诗’运动也曾有过,结局是失败了。”[18]纵观小诗探索的历程,从选择作品到具体翻译,从译介评论到提出观念,从创作尝试到结集出版,可以说周作人为其倾注了大量心血。因此,当他宣告小诗运动失败的时候,不免流露出萧索冷瑟之意;但这不能成为否认他为新诗发展做出了实际贡献的缘由或借口,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总的来说,周作人对小诗的探索是“五四”时期新诗发生与成长的一个侧面,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有直接的关联。如果说石川啄木呼吁诗的革命,是源于一位诗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那么,周作人对小诗的关注和推崇,则更多的是从中国文学发展所面对的种种现代困境出发来考量的。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邻国日本和古希腊,通过翻译、观念建构、创作三重方式审慎地吸取精髓,并注入小诗当中。同时,周作人的小诗探索更多地受到文学研究会所号召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影响。作为新时代的文学家和生活家以及“偶像破坏者”,小诗诗人理应“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创作“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19]。这种新文学必然属于那些具有人性的个体,表现的也应是这些个体的人性,而非种族或国家层面的神性。因此,小诗所彰显的人间本位主义,既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至上,也非纯然功利的伦理说教,而是一种从属于人性的个人主义,它所表现的情感与世界是对正当的、善的、美的人性之肯定。在小诗运动的推波助澜下,随之注入了人们对于新诗的理解和期许当中,也为新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确立了一种思维范式。
[1] 小川利康.周作人与小诗运动[J].现代中文学刊,2016(4):60.
[2] 黄雪敏.20世纪20年代“小诗”运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91-96.
[3] 罗振亚.中国新诗与日本关系的发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97-103.
[4] 周作人.一茶的诗[M]//周作人译文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 周作人.日本俗歌六十首[M]//周作人译文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76-577.
[6] 周作人.《陀螺》序[M]//周作人译文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24.
[7] 周作人.论小诗[M]//周作人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8] 周作人.日本的小诗[M]//周作人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9] 周作人.啄木的短歌[M]//周作人译文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52.
[10] 陈融.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06-111.
[11] 石川啄木.可以吃的诗[M]//周作人译文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2] 美勒亚格罗思,等.杂译希腊古诗二十一首[M]//周作人译文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63.
[13]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序[M]//王仲三.周作人诗全编笺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371.
[14] 张菊香.周作人的六首未曾发表过的白话小诗[J].鲁迅研究月刊,2018(7):44-45.
[15] 斯威夫特.育婴刍议[M]//周作人译文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99.
[16] 柳泽健原.儿童的世界(论童谣)[M]//周作人译文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80.
[17] 周作人.《农家的草紫》序[M]//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18] 周作人.闲话日本文学[M]//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393.
[19]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M]//止庵.周作人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27.
On the Origin of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Concept of Small Poetry from Zhou Zuoren
WANG Jinhuang
Zhou Zuoren’s exploration of small poetry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r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oetry. On the one hand, he provided diverse foreign resources for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poetry movement in China,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translations of poetries from ancient Greek and Japan. For example, Japanese haiku, short songs, folk songs, nursery rhymes, etc. On the other hand, Zhou puts forward succinct and implicit formal propositions and concept of humanistic of the poetry, by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hi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and ancient Greek poems, tastes the life while expressing daily emotions and write worldly desires. At the same time, he creates small poems in a prudent "improvisational" way, which shows that the new litera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life. From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to concept construction, then to his attempting of create, Zhou Zuoren’s exploration of small poem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ual influence of European and Japanese origins,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small poetry movement, it has merged into the blo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oetry.
Zhou Zuoren; the creation concept of small poetry; departmentalism with human life as the core; the origin of Europe and Japan; prudence and improvisation
王金黄(1990—),男,河南平顶山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中西诗歌比较与欧美文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16ZDA240)。
I206
A
1009-8135(2022)06-0074-10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