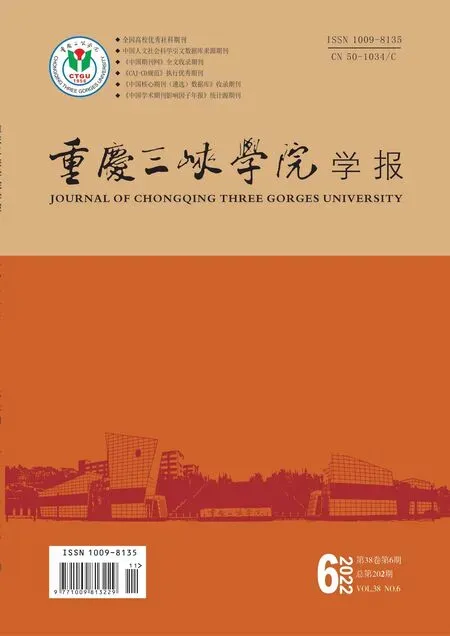“战争”烟尘中的独特视角与意识——抗战前后徐訏“战争”小说研究
张露
“战争”烟尘中的独特视角与意识——抗战前后徐訏“战争”小说研究
张露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学界对徐訏与抗战有关的作品持忽视或误读态度,甚至将其放入浪漫主义范畴中进行审视,忽视其抗战爱国意识与家国情怀。徐訏在描摹战争时,刻意远离正面战场,将抗日战争与世俗生活相结合,将战争残酷性寓于日常性描写中,通过战争反映千百年来国民性和人性之积弊,借此展示人性,反思战争。他提倡“文艺大众化”的同时,将启蒙性与战争结合起来,以寻求爱国意识与启蒙意识的表达。
徐訏;战争;日常性;家国意识
抗战时期徐訏曾创作了不少与战争有关的作品,但这些作品自产生之日起,多数时候被排斥在“战争文学”或“抗战文学”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訏的文学价值和贡献虽被重估,但学界对其评价依旧未摆脱“浪漫”与“雅俗”的怪圈,其文学价值评判依旧桎梏在“爱情叙事”的框架与标准中。对其“抗战”题材小说的品评,依旧是在“爱情”与“人性”的传统标准中进行,甚至有人仍旧延续80年代的定论。徐訏抗战题材小说的价值被低估,他的抗战意识和爱国意识一直被忽视,值得重新审视。
一、徐訏“抗战”题材小说研究述评
徐訏有《一家》《春》《旧地》《痴心井》《风萧萧》《灯》《江湖行》等与抗战相关的小说,大部分创作于抗战时期,是作者对抗战及战争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真实生态的反映。这些作品从产生至今,徐訏的战争观念、抗战叙事模式以及爱国意识与家国情怀,一直处于被忽视状态。陈封雄回忆徐訏时,曾总结20世纪40年代大陆文坛对徐訏的评价:“有人说他是‘洋鸳鸯蝴蝶派’,说他是‘黄色小说家’,说他‘毒害了青年’‘教唆青年走向颓废’。甚至于说他‘破坏了抗战的士气’‘帮了敌人的忙’。”[1]这些说法一直延续到90年代,甚至有人现今仍对其该类题材作品存在些许偏见。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评价徐訏抗战时期的作品(《鬼恋》①《鬼恋》一直被公认为“写于抗战时期,且此文‘与抗战无关’”。笔者《徐訏〈鬼恋〉写作时间与地点辨正》做过考证,《鬼恋》写于1936年6月11日抗战正式爆发前之上海,不应再以“与抗战无关”为由对徐訏的抗日爱国意识和文学创作理念进行抨击。《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不仅与抗战无关,而且于抗战有害,“对于我们的抗战大业多少是起了消极的作用的”[2]。同时期,香港文学批评家司马长风却高度评价徐訏的文学成就,认为是“全才作家”,并以赞许的态度评论了徐訏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风萧萧》和《江湖行》。司马长风详细分析了《风萧萧》的情节、主题、人物设置以及哲理意蕴,认为该作在人物设置等方面均超越了《子夜》《科尔沁旗草原》和同时期的《四世同堂》等作品。司马长风高度肯定《风萧萧》等作品的价值,同时也认为徐訏专注于“内倾化”视角,“对外在世界向来缺乏兴致的”。
在大陆评论界,杨义详细分析了徐訏前期小说,将徐訏定义为“主观想象型作家”,在异域情调与浪漫爱情烘托下,以“心理剖析”为主要方法,实质上是向“哲学沉思”的回归。杨义虽不否认徐訏小说爱情叙事的主题,但他以《一家》《风萧萧》等作品为例,比较客观地剖析了徐訏小说的现实性和战时作家的个人沉思与家国情怀,“也许不能说他的作品是出世的,因为他不无认真地思考着民族文化的积垢和人类理想的蓝图”[4]430-431。在分析《风萧萧》主题时,杨义说:“应该承认,作品是不乏民族意识的,而且它把这种意识渗透在人物的憎、爱、怨、悔之中,不时迸发出清词隽语的哲理火花。”[4]436可以说,杨义基本上超越了“浪漫爱情”定论对徐訏研究的禁锢,比较客观地分析徐訏小说,正确认识徐訏战争题材小说的艺术价值,对于日后徐訏研究和文学史中徐訏部分的书写,定下了比较公正的基调。
杨义将徐訏评论引入文学史后,其他史家与评论家开始关注徐訏,并写入所编文学史,但无一例外,还是定义为“浪漫主义作家”。严家炎甚至说:“他终身是个浪漫主义作家。”[5]尽管多数评论家聚焦于徐訏前期作品《风萧萧》,但评判视角依旧是浪漫、爱情与哲理,鲜有人将其归入“战争文学”范畴去审视,所以徐訏在上海、重庆和香港时期创作的与“抗战”有关的小说容易被忽视。
与文学史评论几乎相似,20世纪90年代有关徐訏的文学论文呈雨后春笋之势,徐訏逐步进入评论界视野。但对其“抗战文学”的评述,相对说来确实有些少,且不系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体作品品评以及“浪漫文学”之定论
对徐訏与“抗战”小说的评论,主要表现为《风萧萧》解读。《风萧萧》作为徐訏代表作,首先进入评论界视野,本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众多论者从“浪漫爱情”与“通俗文学”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而忽视其“战争文学”的属性。老白在《论洋场才子的“唯美”恋爱观——评徐訏的〈风萧萧〉》一文中,彻底否定徐訏本人和《风萧萧》的文学艺术价值,“徐訏所写的是空虚的心境,奇怪的女间谍,‘美好的’矫揉造作,以及徐訏先生自己的‘企慕’‘热情’‘理想与梦’”[6],正是由于徐訏生活在“荒淫的虚伪的阶级里”,才导致《风萧萧》中充斥着“庸俗”的生活状态。禹玲也认为,《风萧萧》消解了战争题材的“庄重性”,将“抗日叙事”与“间谍”和“多角恋”相纠缠,令原本“宏大的主题”融进了“畅销小说”之中。妥佳宁《“孤岛”时期徐訏小说创作中的彼岸追寻》肯定徐訏抗战时期特别是“孤岛”时期小说的文学价值,但论述基点还是“浪漫”与“爱”,这种“信仰与爱”也是基于对浪漫爱情的探索。陈旋波认为,徐訏40年代的作品(包括战争题材作品)基本上还是在“现代玄学爱情”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与哲学思考和生命体验的展现。众多论者都是从“浪漫文学与爱情”角度审视徐訏大部分作品,兹不赘述。
吴义勤论述徐訏创作风格时,提出了新观点,即从“民间性”与“个人性”角度出发,重评徐訏作品的“个性”、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他在提及《风萧萧》《江湖行》等作品时,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角度进行论述,虽未着重强调此类作品的文学和艺术价值,但这种观点也为重新认识与研究徐訏及其作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二)“雅俗文学”视域下的徐訏研究
徐訏前期作品多数将爱情作为审视社会与人生的着眼点,伴随爱情叙事的是传奇、浪漫、丰富想象力以及浓重的故事性,故多数论者认为这种“浪漫叙事格调”是徐訏前期甚至一生文学创作的风格形态,因此徐訏所作与“抗战”有关的小说,自然而然被纳入“通俗文学”的范畴。徐訏曾将自己文学风格归入“雅俗融合”之行列,导致后人以此作为评价其作品的一个统一标准。实则不然,“雅俗融合”的背后,隐藏着对“纯文学”与“雅文学”的艺术追求。程亦骐等虽未否认徐訏小说“雅”的一面,但他们认为徐訏作品带有“海派文学”色彩,无论是“奇幻”“异域”,还是对“真善美”的追求,都是徐訏用来吸引读者“眼球”的一种手段,是扩大读者群,并以此赚取丰厚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而已。耿传明在谈及徐訏和无名氏时认为:二者的成功,得自“精英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即雅俗融合。他重点强调徐訏等人作品的“俗”与“庸俗”和“媚俗”还是很不同的,在谈到徐訏与抗战有关作品时,仍置于“浪漫”与“爱”的框架之下观照。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当下,不少论者在“浪漫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下,也确实无法看到徐訏对战争的文学架构和表达。同时,众多论者已将“雅俗”作为解读徐訏小说的标准,而徐訏的战争观念和爱国意识也一直被误读,所以,对于战争与社会、日常生活和人性表达的标准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对徐訏抗战题材小说的初步肯定
部分论者在谈及《风萧萧》时,将徐訏的创作意图放置在抗战背景下考察,从爱国文人的家国意识去审视该类作品,虽不能完全摒弃传统定论,但能认识到徐訏抗战题材作品的价值,客观探查其爱国思想和家国情怀,也是难能可贵的。尹康庄在《真善美的别样探寻——论徐訏移港前的小说》中,虽谈及“间谍”与“人性”,但没忽视徐訏对于家国的思考,在他看来,徐訏正是将故事置于国家与民族——“大我”的环境中,将国破家亡紧急关头的时代环境作为审视国人爱国意识的对象,才令作品拥有了“较为鲜明的历史感现实性”[7]。闫海田认为,徐訏“抗战悲风”中弥漫着“空气”与“场面”,这样制造浪漫“气氛”也是徐訏惯用的表达方式。闫海田对徐訏战争题材作品是比较重视的,他将这些作品进行分类,但未深入探究,或者也认为它们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二、日常叙事中的“战争”表达与反思
尽管徐訏创作过不少反映社会底层的作品,但1937年前后创作风格基本固定,将爱情叙事与哲学、社会、人生、家国相结合,但也不能简单地将其作品认定为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小说。徐訏大多从知识分子视角出发,将爱情作为折射社会的一个窗口,无论是成名作《鬼恋》,还是《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等,爱情与婚姻既是诱发作者思考的楔子,也是作者进一步展现社会百态和人生哲理的角斗场。徐訏前期创作的不少与战争有关的作品,大部分虽也可放入其前期的创作模式中去考量,但也有其自身独特价值。
徐訏创作于抗战期间或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与抗战有关的作品,突出特点就是忽略对正面战场的描写。该系列作品除《江湖行》《风萧萧》《灯》涉及“游击战”以及与日本人搏斗等场面外,其他作品均难觅正面战场的身影,这也是他一直被误解乃至被忽视的直接原因。《风萧萧》在《扫荡报(重庆)》连载结束后,《四世同堂》即被该报选中,虽同在此报发表,但二者命运和评价截然不同。徐訏对正面战场的游离,肯定与其经历、思想和写作风格有关,但是否描写正面战场,不应该成为评价战争题材作品价值和作者思想倾向的唯一标准,而应突破传统评价标准和定论,从内涵角度去全面分析作品中反映的战争意识、家国观念和文学理想。
徐訏将战争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突破战争场面描写,在战争背景下,将人性探寻放在首位。无论是日常生活描写,还是爱情叙事,突出的是人性,但故事的底色都是战争。他的关注点也正是战争背景下,“国将不国”情势下,家国意识与人性如何纠结、扭打的过程。而徐訏此类文学创作的特色,则是在战争不断发酵过程中,将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不堪与丑陋的人性展示出来,“文学的本质还是人的本性,文学要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情感或感觉”[8]85。描写战争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思考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家与民族遭遇困难的原因的过程。中篇小说《一家》被誉为“徐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以抗战为背景,描述杭州危急时刻林氏家族逃难的过程,重点不是展示国破家亡关头难民的遭遇,而是将这个家庭对战争的认识与人性的展示作为剖析对象。抗战时期,南京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沪杭危急,但对于是否“逃难”,家族成员曾广泛讨论。而是否支持“逃难”,每个人却都基于自身私利来考量:林老太太不赞成逃难,在她看来,自己没做啥亏心事,祖宗也没造啥孽,日本人是拿她没有办法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舍不得她的经堂;而二少奶奶等主张逃难,原因是怕“奸淫掳掠”……随着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家族成员都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纷纷支持“逃难”。当所有成员克服重重困难,迁居上海之后,在短暂和平生活中,人性的自私与丑陋暴露无遗,因而也忘记了战争,仿佛之前对战争的恐惧全然消失了。
无论是《一家》,还是《痴心井》《春》《江湖行》等作品,抗战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已。从表面上看,作品讲述的故事似乎与战争无关,这也是徐訏战争题材作品一再被误解或者批判的原因。很多人因此认为徐訏此类题材作品“与战争无关”,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徐訏不是因为对战争不了解而逃避战争描写,而是将战争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将战争的残酷性世俗化,同时也在思考战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除了《旧地》直接展现日本侵略者给枫木村带来的伤害外,其他作品都是侧面呈现战争的残酷与无情,甚至有的小说中,战争就是一种背景,但又让读者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战争就在身边。《一家》里林氏家族逃往上海后,小说就没有再出现与战争有关的信息,林家人又陷入了日常庸俗、享乐和自私自利的生活中,但无论是对于家乡田产被日军掠夺的惋惜,还是上海租金的增长与来沪人员的增多,都暗示着战争并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发展。《痴心井》讲述几代人不断上演的爱情悲剧与人性宿命,除了开篇介绍过故事发生地——被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后的余道文家老宅外,没再介绍与战争有关的故事,但杭州余家老宅的破败、漪光楼遭破坏后的荒凉、日军杀人场景带来的恐惧以及家族轮回性的爱情故事,无不为故事的发生营造了一种悲凉气氛。同时,虽然《痴心井》以讲述爱情故事为主,但凄惨的爱情轮回、人性的批判与探究以及悲剧性命运的展示,无不昭示着日本侵华战争给杭州城带来的灾难。徐訏将战争的残酷性与人物命运的悲剧性结合起来,看似写爱情,实则在思考战争,这也是其一系列作品惯用的思考模式与写作模式。
尽管徐訏讲述的一个个故事看似与战争关系不紧密,甚至有人认为这些小说是“与抗战无关”的通俗作品,如果深入到每个故事中就会发现,徐訏其实在思考一些问题:这些悲剧性故事与战争的关系;国民性弱点与战争爆发和持续的关系;家与国的观念在世俗生活中的体现与演变;什么原因导致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溃败等。正如徐訏所言:“这些文艺上的表现只是多方面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现实的表现,这也正是人间的,而不是非人间的。最想逃避现实的思想与情感,正是对现实最有反应的思想与情感。”[9]“战争”在徐訏叙事过程中,不仅仅充当了“背景”的角色,同时也是促进故事行进的暗线。而徐訏又将战争与历史、国家民族、世俗和人性结合起来,在历史中考察国民性演变。同时,战争也为爱国意识和世俗人性的展示提供平台,在极端情况下,将国家、民族、人性与爱国意识中最真实的画面展现出来。徐訏规避了正面战场的描写,而战争性与日常性的结合,也为其反思战争与国民性提供了一个空间。
《风萧萧》与《四世同堂》先后被《扫荡报(重庆)》刊载,二者均以抗战为背景,描绘了抗战期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风萧萧》刊出时,据说每天长江江轮上几乎人手一份,却为何后世对二者评价不同呢?为何以《风萧萧》为代表的徐訏作品,一度受到误解甚至批判呢?其实,通过将《风萧萧》与《四世同堂》对比就可以发现,徐訏以“谍战”与“爱情”作为切入点,而《四世同堂》则将战争“日常性”与“人性”“国民性”相结合。无论是“战争题材”作品,还是其中后期小说,大部分都涉及“爱情”,且将爱情与“谍战”“浪漫”“传奇”相结合,这也为其作品被纳入“通俗文学”提供了借口,因而徐訏曾说:“在我与艺术界朋友往还久了以后,我发觉大多数的艺术家都有一种自信,他们因此有派系的偏执,因而往往对别人的作品或表现有不客观的批评。”[10]其实,徐訏小说无论是爱情描写的深度,还是展现爱情的方式,与“通俗文学”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抗战小说”将“战争”与“爱情”和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写作模式,确实为战争残酷性增添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徐訏的这种战争描写模式,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与庄严性,是为其“浪漫”和“传奇”创作风格的表达服务的,但描写方式和文学的最终追求有时是不完全一致的,这也为透过写作方式,窥视徐訏的抗战意识和家国意识,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徐訏文学创作的最终归宿是探讨人性,这也是一种创作观念的不同。正如《〈一家〉后记》所言:“我的目的不是将一群我训练过白耗子对读者演我的所编成的戏,我只是指出它们日常的生活。你也许觉得可怜,也许觉得可笑,也许觉得人生的阴暗与渺小,也许觉得家庭组织的凄惨与时代的残酷;我不希望有人爱其中一个人或恨其中一个人,因为他们活着,我们也活着,人世上的确有这样的生存,有时会需要这样的生存。”[11]这正是徐訏一直探讨的问题,文学究竟应该反映什么?抗战期间,文学始终存在是否应该“成为战争附庸”的讨论。在徐訏看来,文学可以反映战争,也可以为抗战服务,但文学也不能逃避反映人性的“宿命”。他认为文学就应揭示生活中的种种形态,将其展示出来,无论是战时还是日常。徐訏对于抗战时期人性的展示深入骨髓,对战争背景下人性的揭示,也是对战争的深沉反思。无论是中美间谍的抗日行为,沦陷区人民对侵略者的痛恨,还是战争状态中日常生活的呈现,人性的种种弊病展露无遗,就像《〈一家〉后记》所言,徐訏只是让大家看看不同人的真实生活(包括内心生活),而“国将不国”的形势下,对于自私人性的展示和批判,也是对战争与家国意识的另一种思考。
抗战时期,徐訏对“抗战八股”是不太喜欢的,在他看来,“抗战八股”之外的一系列“客观主义作品”,过滤了战争初期的激昂与乐观,比较客观地“静观与反思”战争。他批判这两类作品,将“抗战八股”定义为“原始的浪漫主义”,将“客观主义作品”归为“原始的现实主义”。这二者都是以“口号”或“预设的政治观念”作为表达的方式,缺乏“艺术生命”。徐訏将战争日常化叙事的同时,用一种“近乎冷漠”的态度展示人性的罪恶与自私,这种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叙事,为战争书写带来了一种“冷漠”的感觉。徐訏采取不同于前两种“战争文学”的叙事方式,冷静地将战时的人性客观解剖,在近乎“自然主义”的叙事中,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感到主人公言行所传达的意图。作者几乎不发表任何议论,任由主人公静静地展示,尽管《旧地》喊出了一些抗日口号,但大部分作品还是客观地呈现战时日常生活的状态,看似没有表达对战争的看法,可战时的混乱、人性的扭曲、生活的无着,则是作者对于侵略者无声的控诉,对古老中国人性阴暗面的深切反思,这也是徐訏的爱国意识和家国情怀一直被忽略的原因吧。
三、“文艺大众化”与抗战爱国意识表达
徐訏20世纪40—60年代创作的战争题材作品,之所以一直不被主流战争文学所认可,主要基于其描述战争的视角。在徐訏看来,国破家亡背景下,战争文学已成为一种政治话语的表达形式,而在“抗战八股”之外,应该有更多表达战争的方式。他认为,在展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同时,将战争文学与“文艺大众化”结合起来,将灾难展示与战争思考结合起来。
这种表达“战争”的方式,也是徐訏“个性化”展示的一部分,在有关“鲁迅风”以及“文艺大众化”论争中,徐訏明确反对“抗战八股”与“宣传文学”,其创作过程中也没有践行“抗战八股”对“战争文学”的规定与要求,但这并不代表他反对抗战、反对“文艺大众化”。他认为“抗战八股”在表现战争、激发抗日爱国情绪上是有功的,但从文学角度看,其表达方式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抗战八股”不应成为战争观念与爱国意识表达的唯一方式,“文化大众化”在展现战争的同时,应站在大众利益的立场上。这也是徐訏能得到年轻人“所一致拥护的”原因。徐訏并不反对抗战文学,但他认为抗战文艺应创作“有生命的作品”,而“抗战八股”为了宣传既定观念,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公式化,损失了艺术表现力和文化内涵,“所谓客观主义的作品是拼凑材料根据预定的政治概念来编写的,也即是没有生命的概念化的作品”[16]113。在徐訏看来,无论是直接描写正面战场的作品,还是展示战争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真实生活场景的文学,都应属于抗战文学的一部分。徐訏并没有完全否认之前“抗战文艺”的作用和价值,但在抗战时期,从民族利益出发,文学可以为抗战服务,也应从客观实际出发,正确对待战争,“原来作家们像抗战初期所有的热情与乐观的态度已经消失,了解抗战的现实绝不是短时期可结束,在艰难的生活下,对战争作了静观与反省,因此产生了这类作品”[12]112。
徐訏认为,在主流话语之外,寻求展现战争的方式,甚至写一点无关抗战的作品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不能反对抗战。徐訏对大众文学的提倡,是基于他对“抗战八股”所引发的关于话语权威的思考,他在反对文学成为“宣传工具”的同时,承认文学的“宣传”特性,“宣传可以就是传达,人类有‘语言’,语言可以说就是为宣传而用,文字是语言的记录,自然在空间上可以传得广,时间可以传得久,所以自然是一种宣传,而且是比语言更有效的宣传”[12]88-89。徐訏眼中的“宣传”,更多等同于“传达”,“传达则是成了一个要求别人了解的一种清楚的形象”[12]90,文学应言之有物,传达作家的“真感”,反映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我说艺术的大众化,是说艺术不考查任何人的身份、财富、教养与学识,谁都可以去接近它,谁越接近它谁就越获得它”[14]23。这种“文艺大众化”的观点,并不违背抗日救国的宗旨,战争状态下生活性与日常性的描写,既贴近了世俗生活,又在“接近”的过程中实现了战时启蒙的任务。
徐訏反对“抗战八股”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抗战背景下战争与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从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世俗性角度反映战争,既不违背他一贯对人性和国民性探索的诉求,也将战争残酷性、生活繁琐性与人性复杂性相结合。战争的日常化书写,不仅展现了持续性战争中民众的麻木性和惰性,也从生活角度暗示了人民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抗。徐訏从日常生活角度书写民众日常生活,无论是战争、爱情、家庭、人性,还是抗战,他让大家在品读作品时,不仅重温了自己的生活,更是让大家深切体味战争给生活带来的苦难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战争。这也是其战争文学日常性的用意所在吧!
战争日常化叙事并未将徐訏的抗日爱国意识遮掩,评价其抗战系列作品时,应客观审视他的思想、态度和战争观念,如果不因袭以往对于徐訏“浪漫小说家”的评价,评论界是不会将“黄色作家”和“特务作家”等称号赠予徐訏的。纵观目前有关抗战文学的相关资料,只有少数编者收录了徐訏个别作品,大部分还是秉持原有观念,忽视他对抗战文学的贡献。
徐訏作品中一直潜藏着抗敌爱国意识,无论是《风萧萧》对中美反法西斯同盟的描述,还是《旧地》《春》等作品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他一直没有忽视战争对中国人的影响。正是因为战争来临,林家才舍弃几代人积累的家财,冒险逃往上海;“我”儿时的乐园——枫木村,在日本人的烧杀抢掠下,已无回忆中的温暖与美好,物是人非,只剩下无尽的残破与荒凉;董大嫂一家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抗战爆发后,儿子参军,随着儿子的牺牲,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徐訏虽未直接描写正面战场的残酷,但其将重心放在战争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上,将小家与国家相结合,从日常情感角度让读者感知战争的残酷,相比于一些“口号”与“宣传”来说,虽不直接,但对于读者情感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徐訏虽变换了叙述方式,但其爱国抗战意识和个人节操,应该是不容置喙的,正如《旧地》描述的那样:“杀尽奸杀我们父母姊妹的日本鬼子!”“抗战到底!”徐訏该类作品反映的家国意识和抗战精神不容置疑,他之所以被后世误解,乃至批判与污蔑,主要是因为其创作方式对于主流话语的背离。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放弃了法国的学业,“抗战军兴,学未竟而回国,舞笔上阵,在抗敌和反奸上觉得也是国民的义务”[13]。徐訏曾被学界归入“论语派”,但纵览其所谓“论语派”同仁,有不少曾在抗战时期丧失民族气节,如周作人、陶亢德等,徐訏曾在《从“金性尧的席上”谈起》中提及陶亢德等人失节前的反常表现。徐訏的一位朋友也曾代表日本人邀请他出山主持上海“文艺运动”,以“每天跳舞赌博,哪有心机去做什么文艺运动”[18]为借口婉拒,不久即舍弃心爱的藏书,只身逃离上海,前往重庆。所以,摒除过往成见,透过“黄色作家”“特务作家”的定论,可见徐訏对国家、民族与人民的赤诚忠心。
徐訏所作抗战相关作品,虽与当时主流战争文学创作方式存在差别,但应从“战争”与“文学”相结合的视角,重新审视其战争理解与反思,对战时日常生活中人性的展示与暴露,对“国将不国”甚至近代以来中国动乱原因的挖掘与揭示,以及在批判与反思中展现的家国意识、爱国情怀,这对重新审视过往徐訏定论、徐訏“战争文学”及其思想变化,大有裨益。
[1] 陈封雄.忆徐訏[G]//徐訏纪念文集.香港: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学会,1981:105-106.
[2] 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M].香港:香港东亚书局,1978:270.
[3]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97.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0-431.
[5]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308.
[6] 老白.论洋场才子的“唯美”恋爱观——评徐訏的《风萧萧》[N].大公报(天津),1948-01-27.
[7] 尹康庄.真善美的别样探寻——论徐訏移港前的小说[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56-62.
[8] 徐訏.牢骚文学与宣传文学[M]//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9] 徐訏.三边文学序[M]//场边文学.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71:III.
[10] 徐訏.《乐于艺》序[J].明报月刊,1969(38):22-23.
[11] 徐訏.《一家》后记[G]//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1937—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71.
[12] 徐訏.服务于抗战的文艺[G]//中国现代文学过眼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
[13] 徐訏.《徐訏全集》后记[M]//徐訏全集:第1卷.台北:正中书局,1966:597.
[14] 徐訏.从“金性尧的席上”谈起[J].笔端,1968(5):5-8.
The Unique Perspective and Awareness in the Smoke and Dust of “War”:A Study on Xu Xu’s Novels Around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Zhang Lu
The academic circle tends to neglect Xu Xu’s works related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or even to examine these works under the category of romanticism, ignoring Xu Xu’s patriotic awareness and his strong attachment to home and land. When Xu Xu depicted the war, he deliberately moved away from the frontline battlefield but combined the Anti-Japanese War with daily life. By embodying the cruelty of war in day-to-day descriptions, he displayed the evil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of nationality, in order to reveal humanity and reflect incisively on the war. While advocating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Xu Xu combined the enlightenment and war in his works to express patriotism and to promote enlightenment ideology.
Xu Xu; war; everydayness; patriotism
张露(1987—),男,河北任丘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徐訏文学编辑活动及相关史料整理与研究”(2020BS28);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抗战时期徐訏‘新闻’活动及史料整理与研究”(21SKGH201)。
I206.6
A
1009-8135(2022)06-0084-10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