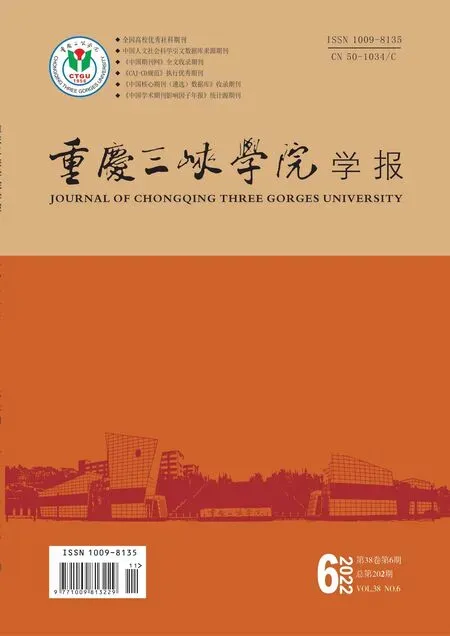胡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与主要原则
李耀威
胡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与主要原则
李耀威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胡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鄂东地方文化中的精英与圣贤人格意识为思想背景,以鲁迅思想、五四精神为人生向导,以日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思想为精神养料,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精神指南。胡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主要包括三条原则:生活真实构成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来源,进步思想促成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视野,历史原则增加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深度。上述两大方面内容共同组成胡风文艺思想的基本框架。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判是上述三原则的一次深入实践,它证明这些原则既是逻辑自洽的,又具有准确而鲜明的现实指向性。
胡风;现实主义;生活真实;进步思想;历史原则
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领域的众多名家中,胡风(1902—1985)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鲜明的理论体系、昂扬的主观战斗精神取得突出成就。学界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理论内涵、形成原因、意义价值已有众多研究成果,过分捧高或贬低都不属于公正评价,唯有结合历史、地域等因素加以考察,方能理解胡风的文艺理论。
一、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
胡风文艺理论与批评有两个现实指向:一方面,研究文艺理论、创作方法、文学遗产等问题,评介青年作家与外国作家作品,从内部深化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胡风以文艺理论与批评为武器,将其与时事评论紧密结合,配合编辑、翻译等活动,积极参与进步社会活动,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胡风文艺思想成熟较早,其批评论著在当时就产生较大影响,部分作品被翻译成俄语介绍到苏联。胡风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以下几个方面思想因素相关:鄂东地方文化中的精英与圣贤意识、鲁迅思想与五四精神、日本与苏联的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以鄂东地方文化中的精英与圣贤人格意识为思想背景
明朝中后期,鄂东文化教育盛极一时。晚清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鄂东地方文化复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胡风生长于这样的环境中,少年时期接受传统私塾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怀疑这种一成不变的古典教育,又逐渐反感地主少爷们喜爱的法政专门科,感觉世界上应该存在“更明亮的地方”[1]268,所以果断地离开家乡,前往武昌求学。后来回忆这段青年时代的经历时,胡风感慨说那时的自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1]267。如果从地方文化视角来看,胡风朦胧地对现状不满,自发地追求更高境界,这是晚清近代以来鄂东地方文化中的“豪杰型和圣贤型”[2]107人格的具体例证。类似的名家还有熊十力(1885—1968)、闻一多(1899—1946)、徐复观(1903—1982)、殷海光(1919—1969)等。这两种带有浓厚地方文化色彩的人格因素,是胡风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一生的经历和著述中产生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胡风始终以鲁迅为榜样,坚持启蒙立场,以决绝姿态投入复杂生活,都是上述因素影响的结果。
(二)以鲁迅思想、五四精神为人生向导
鲁迅在思想、人格、文风等多个层面深刻地影响了胡风,坚定的启蒙立场更成为胡风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柱,并终生引领他不断建构、完善文艺理论体系。与家乡及青少年时期自发追求更高境界的经历不同,胡风深入研读鲁迅著作,撰写多篇纪念、分析、阐释文章,如《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等。胡风不仅深刻地认识到鲁迅的重要意义,还继承了鲁迅深刻的怀疑精神,即在面对复杂生活时,始终保持清醒,既要歌颂也要批判,更要理性分辨真实的生活与被粉饰的生活;在生活快速向前发展时,还要敏锐察觉并果断跟进。胡风清醒地认识到,作家思想、作品内容、生活真实三者之间是存在裂隙的,这是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无法避免的现象。因此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如鲁迅,对生活真实始终保持热情又不断怀疑。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看进现实生活的深处,因而禁不住唱出了他的沉痛的哀歌”[1]592《过客》小释。在抗日战争期间,胡风指出文艺创作要面对的真实状况是“二十多年来的新的文学底传统”,另一方面是“民族战争所创造的生活环境以及它所拥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远景”[1]604今天,我们的中心的问题是什么。解放战争期间,胡风强调,“在内容上,凡是在应有的思想真实上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内容的,都好”,“要反对思想内容上的歪曲和创作态度上的虚伪”[3]426以《狂人日记》为起点。胡风之所以不断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真实,并反复向作家、批评家强调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真正指向,就是因为他深刻感受到时代纷乱,单凭个人视野及判断力难以达到洞穿迷雾、把握脉搏的目的。这不仅说明胡风发现了鲁迅的价值,还说明他自觉继承鲁迅思想,勇于扛起启蒙大旗。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是形塑胡风精神世界,推动他走向现实主义、走向人民大众的重要事件。他在不同历史、现实环境中,不断向人们阐释这一事件的宝贵价值,既是为了鼓励乱世困境中的人们继续抗击侵略者,也是为了推动现代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向更加深广的方向发展。胡风对鲁迅思想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阐发与推崇,不仅使他在文艺理论领域取得卓然成就,也使他的人格与精神令人敬仰。
(三)以日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思想为精神养料
自青年时代起,胡风在当时复杂的社会思潮中逐步接触、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通过日译本阅读到一些阐发性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了解,并加入日共。回国后积极从事无产阶级文献翻译及思想传播工作,在文艺批评中自觉运用无产阶级理论和视角,以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及批评标准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展开深入分析。特别是在“左联”任职期间,胡风因工作关系主持编辑多种“左联”刊物,接触到较多来自苏联的文论译文,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左翼文艺理论水平。他还发挥日语特长,从日文转译相关文献,如将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的日译本翻译成中文,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四期(1934年12月16日)。1935年,胡风在讨论文学遗产问题时,引用了“佛列德里克所提出的要和‘思想的深’及‘历史的内容’完全融合的‘莎士比亚的泼辣’”,反对“席勒的方法”[1]91关于文学遗产。在讨论典型问题时,引用马克思“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106什么是“典型”和“类型”这一观点。在与周扬争论现实主义问题时,引用并分析了恩格斯《致敏·考茨基》中的重要观点,并指出周扬对这封信理解错误之处[1]369现实主义的一“修正”。
苏联文艺观念及俄苏文学作品也是胡风的重要思想资源。一方面,胡风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直接来源于苏联。他推崇苏联文学创作技巧,专门撰写《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关于创作经验》等文章,向青年介绍这些创作理论。另一方面,胡风高度重视俄苏文学作品,在总结《译文》杂志第一卷、第二卷的总体情况时,胡风列举了《译文》介绍过的俄苏作家:普式庚、果戈理、奈克拉索夫、莱蒙托夫、杜斯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卢那察尔斯基、柯洛连科、普列波衣、蒲留梭夫等,特别向读者提示应注意这些作家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胡风接受、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是曲折的。由于时代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手稿尚未充分整理及准确翻译,使中国人接受并实践马克思主义遇到障碍。苏联不断推行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艺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左翼文艺发展方向。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审查,导致胡风无法更多、更直接地在论著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也依然是胡风最重要的精神养料,对他文艺思想的核心观点、理论形态、现实指向均产生决定性影响。
(四)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精神指南
自青年时代起,胡风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通过写作、演讲、编辑刊物、筹集经费、传递情报等多种方式为党工作。1923年在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胡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3年7月至1934年10月,胡风在“左联”担任领导职务时不领取报酬;1935年,担任中共中央特科“机要通讯员”,完成了很多党交办的秘密任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胡风与党的联系更加紧密,更自觉、主动地配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在著述中吸收《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的核心思想,以之完善自己的文艺理论。1949年,他参加了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并着手创作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此后,他深入基层,采访各领域先进人物,完成多篇特写和报告文学作品。可见,胡风虽然一生都没有正式入党,但他始终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南。
要之,鄂东地方文化中的精英与圣贤意识、鲁迅思想与五四精神、日本与苏联的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四方面共同构成胡风性格与思想的基底,决定了胡风文艺理论的中心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他后期的命运。
二、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三原则
现实主义是胡风文艺理论思想的主体,是他评价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的首要标准。同时,胡风还致力于宣传以俄苏文学为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与当时各种类型的“现实主义”展开正面斗争,从而使他的文艺理论显示出鲜明的中国化、时代化特点:关注现实,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反抗国民党势力压迫;关注情感,为人民疾苦呼号。
在此过程中,与周扬的多次论争,很大程度上形塑出胡风文艺理论多方面的具体形态。胡风与周扬的首次交锋发生在1935年至1936年,论争焦点是如何准确阐释恩格斯相关信件中的“典型”概念。胡风认为“典型”是特定群体共有的、不带有偶然性的特征;周扬则更多强调“典型”的个性化特征。双方观点都受到时代局限,存在明显缺陷。第二次交锋发生在1936年,论争的焦点是两个口号“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孰优孰劣。前一口号系周扬从苏联译介而来,但其内涵宽泛,立场模糊,现实指向性不强,虽然符合统一战线要求,但实际的宣传、鼓动作用有限。针对这一问题,鲁迅等人提出后一口号,由胡风撰成《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并发表。此后,在鲁迅的建议下,胡风没有再发文参与此次论争。这足以见出鲁迅对胡风的信任以及胡风对鲁迅的敬仰之情。第三次交锋发生在1938年至1940年,论争的焦点是“民族形式”的内涵及其建设方式。胡风坚持启蒙立场,认为洋形式、土形式、旧形式都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更不应直接拿来当做“民族形式”,应当建设现实主义的、以启蒙为核心的全新“民族形式”。周扬此时身处延安,以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强调应建设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民族形式”。第四次交锋发生在1942年之后,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理解现实主义,如何创作现实主义作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以工农兵为中心的全新阶段。胡风在论著中对“讲话”表达了有限认同,他依然坚持鲁迅思想和启蒙精神,强调作家应当以主观战斗精神突入现实生活,反对作家从属于政治,反对左翼内部出现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周扬此时已经成为阐发“讲话”精神的主力军。经过几次论争,胡风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鲁迅亲密合作、在时代大势中深入思考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与价值等方面收获颇丰。不可否认的是,胡风现实主义思想是有时代局限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阅读与理解不够全面、准确;受苏联政治及文艺思想影响较深。但是,既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胡风文艺理论,也不宜过分拔高其历史价值,应当予以全面客观评价。
(一)生活真实构成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来源
“真实”与“生活”均是胡风文艺论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表征着胡风文艺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内核,也表征着胡风在情感上始终与当时的中国现实、苦难中的人民紧密相连。
胡风认同新文化运动主将提出的“八不”“文学革命”等口号,赞扬这些观点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他对远离现实、脱离人民的贵族的、山林的文学始终持激烈的否定与批判态度。胡风强调,到处都有生活,作家只有主动地、积极地走出自己熟悉的、感到舒适甚至麻木的小天地,走出复古高蹈的精神世界,走进复杂、火热的现实生活,才能获取真正有价值的创作素材。然而,新文化运动逐渐退潮后,一部分作家转向“性灵”,追求“闲适”,部分青年作家受此影响,也逐渐远离现实,开始模仿对世界进行“明净的观照”。胡风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对中国人民苦难悲惨生活的有意漠视,对群众挣脱命运枷锁呼声的刻意忽视。有鉴于此,胡风指出,作家应当清醒地认识大环境与小环境——所谓大环境,就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状态并没有太大改变,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次政治、军事、文化事件共同构成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人民依然遭受来自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压迫;所谓小环境,是指百姓的真实日常以及某一事件的发生现场,最能反映出生活的原始、残酷面貌。
胡风对赛珍珠《大地》的否定性评价能够很好地说明,在文学作品中做到清醒地认识大环境与小环境实非易事。赛珍珠是美国人,婴儿时由传教士父母带到中国,在华生活约40年。她以中国生活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面对这样一部受到西方赞誉的作品,胡风于1935年7月撰写《〈大地〉里的中国》,彼时《大地》已获普利策奖,尚未获得诺贝尔奖。胡风肯定赛珍珠这部作品展现了底层中国民众的生活与命运,以及作者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同时强调其缺点也非常明显:作者始终是站在西方文化和宗教立场,以猎奇的心态观察并展开叙述,赛珍珠不仅不了解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还将19世纪西方小说(例如《简爱》《远大前程》《基督山伯爵》)常见的继承遗产、发现宝藏等俗套植入其中,强行造成主人公命运的转折;更重要的是,该作品刻意忽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展开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等事实。胡风认为,生活在中国并写出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意味着真正了解中国;观察过中国人民的生活,体验过中国人民的疾苦,并不意味着能在文学作品中将这一切都感人至深地表达出来;相反,还可能会暴露作家在阶级、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傲慢、盲视与偏见。
所以,胡风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是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同时又在某些方面高于生活。在今日看来,上述观点已经是常识。但在胡风时代,上述观点需经详细论证才能成立①胡风就这一问题在《文学与生活》第一至第三章展开详细论证。。因为鲁迅《幸福的家庭》中描绘的臆想式创作方法在当时并不少见。胡风以普式庚和新文学运动为例,从横向角度说明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以儿童游戏和原始人为例,从纵向角度说明文学艺术根源于劳动。这就论证了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观点。胡风以古希腊《情歌》、印度妇女唱的收成歌和求雨歌、法国果尔蒙创作的反映农业社会的诗歌《毛发》、英国反映商业活动的古歌《格林维志的老人》为例,论证了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并跟随社会发展而发展这一观点。接着,胡风以列宁的文艺反映论为基础,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学艺术简单记录现实生活事件和场景。他认为,记录生活只是文学艺术的基础内容,作家还应深入思考如何将纷乱繁杂的生活现象选择、组合,如何从中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部分,如何将“生活的脉搏”[1]315-316即生活发展的真正大方向表现出来。这些才是值得作家真正应当深思的问题,也是胡风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首要原则。
(二)进步思想促成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视野
“进步”在胡风文艺批评中,指称那些始终坚持民族与人民立场,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始终与不断涌现的反人民、反民族、消沉隐逸、妥协退让的势力展开斗争的思想与作家,备受胡风的热情赞颂和大力弘扬,在青年作家评介文章中尤为明显。
胡风称赞艾芜在南洋漫游期间体验到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统治以及那里的大众所遭受的苦难,随后完成小说集《南国之夜》。他赞扬欧阳山没有在熟悉的生活中变得麻木,反而不断观察其变化,并善于捕捉新奇之处;更重要的是,欧阳山“用自己的具体和心灵把握到了真实”[1]176,从而创作出小说集《七年忌》。他称许萧红《生死场》表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面对生活时的麻木和应对命运时的无助,小说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作品的质朴性令读者凄怆动容。他肯定端木蕻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