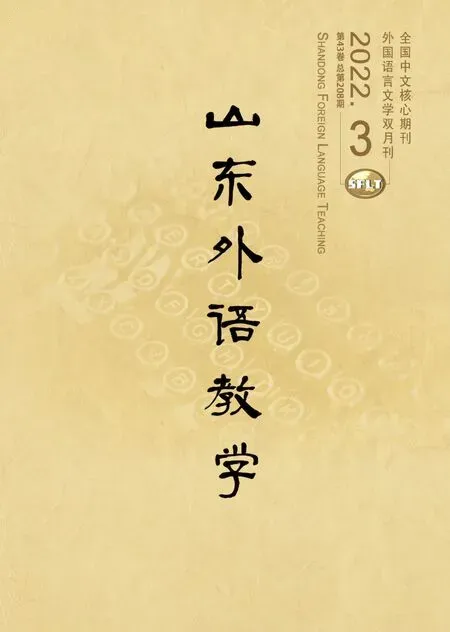清代翻译科缘起考
——顺治八年还是雍正元年
宋以丰
(湖南理工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1.引言
古代科举取士分“文”“武”两类,其中文举兴于隋,武举始于唐,二者在公为求人才,在私为求入仕,此后虽经历宋、元、明、清等朝,仍相沿不替。清代的科举制度因袭明制,虽在细节上与后者存在不同,但整体上仍以正途为重,而以异途为轻,并与明朝一样,仍以“养士”“取士”并重,成为国家任贤取士与成就治道的重要途径。清代之科举取士不但袭用前朝旧制,使旗人、汉人同场竞技,而且另辟蹊径,创制满洲特色之翻译科,为旗人入仕、进身提供专途。清代的翻译科举制度是清代翻译政策的重要形态,是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无疑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它对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时空条件有着强烈的依附性。翻译就其整体而言,主要不是译者的个体行为,而是有条件、有组织、有指向、有作用的集体行为,乃至国家意志行为。固然,翻译是文化更新与演进的重要途径,有助于促进宿语文化的新陈代谢,但文化作用显然不是翻译功能的全部(袁帅亚,2020:124)。以清代翻译科为例,它的创制便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因与意涵。清代翻译科的创制缘起于雍正年间,这一点毋庸置疑。雍正帝即位伊始,即对传统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不仅调整了考官的选派,也调整了考试的重点与内容,放宽了考生的资格审查。同时,出于对翻译事业的重视,雍正即位之初便在传统八旗科举考试中增设翻译科目,将其从前者中单列出来,形成自行独立的制度形式,即今之所谓“翻译科”。雍正帝创设的翻译科含满洲、蒙古二科,分童试、乡试、会试三级,由八旗满洲、蒙古根据相关规定报名应试。翻译科自雍正元年(1723年)始设,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与文科举一并废止,历时凡一百八十二年。作为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制度,翻译科为清廷拔擢了大量翻译人才,也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提供了进身之阶,其存在尽管有着自身缺陷,却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门阀制度的不足,也为清代政治与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
2.翻译科的制度雏形:清初八旗科考中的翻译考试
翻译科乃清代特设之科目,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其渊源可远溯至太宗皇太极时期。天聪三年,太宗诏令更易明例,以考试分别优劣,振兴文治。八年,太宗命礼部“考取通过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范文程等,1985:73)。崇德三年和六年,朝廷遵太宗圣谕再次办理考试,分举人、生员进行取用,授以官职。上述举措的推出使清初的考试任官得以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崇德八年,太宗猝崩,世祖继位,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为吸纳汉族士子,多尔衮于顺治元年十月颁布诏谕,循明制开科考。至顺治八年,世祖亲政,谕礼部研议八旗科举则例,并首开八旗科举,分乡试与会试两种,满洲、蒙古和汉军皆可参加,一时令旗人崇文之风盛行。然而,由于清廷担心旗人汉语能力不及汉人,故在考试中对应试者进行区分,要求识汉字者翻译汉文,不识汉字者则作清字文(鄂尔泰等,1985:457)。在考试中加入翻译内容,并将取中情况分榜公布,此举未见于太宗时期,实为八旗科目之肇始(福格,1997:187)。本次始设的翻译考试继承了金朝女直进士科的传统,并在后者基础上对考试的程序和体制进行改革,旨在选取通晓满、蒙、汉语的八旗翻译人才。
然而,旗人崇尚文学,并经考试“即得陞用”,此举易致其怠于武事。故而,顺治十四年,世祖敕谕礼部、吏部和兵部,宣布停止八旗科举(鄂尔泰等,1985:832)。可是,停止旗人考试,使汉人独占科举仕途,又会造成八旗士子失去进身之阶。于是,康熙二年,圣祖谕令八旗乡试复行,并应御史徐诰武奏请,拟于康熙六年起,令满洲、蒙古、汉军与汉人一体参加会试(马齐等,1985:328)。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起,为避免旗人专心习文,致使武备松懈,朝廷遵圣谕决定效法世祖旧例,自康熙十五年起停办科举,直至康熙二十六年,期间停办时间虽然不长,影响却较为深远。世宗即位后,对康熙后期以来的八旗弊政进行反思,其中也包括旗人的清语学习。由于当时的旗人普遍不谙清语,每遇翻译、说写之时,“字句偶有失落,语音或有不正”的情况比比皆是,世宗为此多次晓谕八旗,令八旗兵丁务必以学习清语为要(张玉书等,1983:8)。雍正初年,世宗降旨总理王大臣,命其会同礼部、兵部研议翻译科之事,目的在于激励旗人勤习国语,专精骑射。
毫无疑问,顺治年间增设的翻译考试系清初以来科举取士的接续与发展,它既是统治者因应时势的积极创举,也是长期以来铨选翻译考试传统的自然产物。事实上,通过铨选翻译考试选拔官吏,并非始于满清。如蒙元时期,朝廷便已有蒙古学考试,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翻译。《元典章》卷 31《礼部卷之四·学校一》中说,元世祖至元八月之际,朝廷在京师开设蒙古国子学,要求包括诸王在内的相关官员参与学习,并以《通鉴节要》的蒙语译本为教本,从习学生员中“选择俊秀,出策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为中选,约量授以官职”(陈高华等,2011:1081—1082)。顺治年间的翻译考试继承了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基本特点,以及铨选翻译考试的任官传统,正所谓“兼备金元之制而加盛焉”(汪师韩,1996:473)。
作为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清政权的政治特点之一便是语种林立,文化与习俗各不相同。出于统治需要,清初以来便在各级政府衙门设置专司文书的翻译和撰拟。其中,除最具代表性的笔帖式之外,内阁侍读、中书以及各部院主事等职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担当翻译之责。同时,汉文典籍的翻译,以及满、蒙文字史籍的撰述也需要大量翻译人才。所有这些人员的铨选、考核和派充等,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翻译考试,择优录用。虽然这样的铨选翻译考试并不具备翻译科的性质,取中者往往不能获得科名,但翻译考试的结果仍是官员晋升、罢黜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为嗣后创制翻译科提供了制度雏形。
3.《雍正会典》等关于顺治八年翻译科的误记
关于清代翻译科的创设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雍正元年,另一种则认为是顺治八年。雍正元年世宗诏谕举办满洲翻译乡试,而顺治八年出现了翻译进士麻勒吉与麻祐,两种说法各自有文献依据,互不能说服对方。如《清史稿》卷273《麻勒吉传》中,明确提及麻勒吉曾经参加翻译乡试,并于会试中取中第一(赵尔巽等,1976:10038)。《清史稿》关于此事的记注源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后者在卷十五中也指出麻勒吉“以翻译取中举人” (周俊富,1986:767)。虽然上述两处记载中,均没有出现“翻译会试”字样,而只是说“以翻译举人举会试第一”,以及“明年会试第一名”,但支持者仍以顺治年间为翻译科的起始时间。将顺治八年的翻译考试视作清代翻译科的缘起,这种观点主要见诸于商衍鎏(2014:231)、王庆云(2001:34)和张杰(2007:193-194)等。在这些研究中,商衍鎏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商衍鎏乃清代末科八旗会试探花,先后授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以及实录馆总校官等,其看法具有代表性。《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商衍鎏对清代翻译科的阐述并不详实,仅论及翻译科的三个层次,即翻译童试、乡试与会试,但明确提及翻译科创设于顺治八年,指出这一年“定考试满洲、蒙古翻译”,而雍正时只是“复行考试” (商衍鎏,2014:231)。与商衍鎏等人不同,更多的人则是将翻译科之缘起归于雍正年间,如石桥崇雄(1988:5)、村上信明(2002:307)、屈六生(1993:229)、叶高树(2013:51)和邹长清(2013:145)等。另外,也有少数将翻译铨选考试视作翻译科缘起者。如康熙二十四年,清廷曾组织翰林院侍讲的考选,由圣祖仁皇帝钦试。此次考试的对象以各部院衙门中的无品笔帖式,以及旗人中的革职、闲散人员为主,含八旗满洲、蒙古及汉军,应试者必须通汉文,善翻译。由于清代政书中对于此类考试并无统一命名,故多称之为“铨选”,即“选才授官”之意。简单来说,所谓“铨选”即指各部院衙门通过考试翻译,从应试考生中选取成绩优异者,授官或派充至各部衙门,负责行政文书的翻译和撰拟,其主要的形式包括笔帖式、内阁侍读与侍讲、中书、通事、监贡等。正是由于铨选翻译考试的自身特点,有人便将其与翻译科考等而视之,不加区分。
那么,清代翻译科是否滥觞于顺治八年?或者说,顺治八年出现的翻译考试是否具备翻译科的正式形态?欲回答此问题,务必先对《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一段记载进行摘引与分析,其中写道:
顺治八年六月壬申,礼部议:八旗科举例,凡遇应考年分,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学政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各衙门无顶带笔帖式亦准应试,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各衙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俱准应试,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二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报可。(鄂尔泰等,1985:457)
上文中,礼部所奏涉及八旗乡、会试的额数与形式等。由于八旗官学中向来有习清书、习汉书之分的传统,礼部遂奏请采用不同方式,对应试者分别考试翻译或清字文,无论乡试、会试,皆是如此,而区别只在于会试时针对应试者学习语言的不同背景,各自增加了一道题量,即习汉字者除了考试汉字文翻译,另考试文章一篇,习清文者则在乡试的基础上,增试清字文一篇。这一规定既针对八旗满洲,也针对八旗蒙古,但不针对八旗汉军,后者的考试内容与普通汉族士子相同。同时,礼部也奏请对笔帖式和他赤哈哈番、哈番(即“笔帖式哈番”)参加乡、会试进行规定,其中前者参加乡试,后二者参加会试。
上文引用的内容也出现在《雍正会典》(又称《(雍正)大清会典》),以及两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光绪)中,三者都明确提到停止(八旗)考试的具体时间,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而且三者中都加有“按语”,进一步说明此事。其中,《雍正会典》中的说法是“此后复行考试,与汉人一体。停止翻译”,《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说法则是“康熙二年(1663)谕:满洲、蒙古、汉军生员俱准乡试。此后惟翻译未经举行”(昆冈等,1963:657;允禄等,1995:4619-4620)。从《雍正会典》的记载及其“按语”看,至少可以推导出两点:其一,八旗科举考试始于顺治十四年前,但十四年即停办;其二,顺治十四年前,翻译科便已存在。顺治十四年以后,八旗科举考试得以恢复,但翻译科举仍被停止。《雍正会典》中的这一记载与两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说法如出一辙,后二者也将顺治八年的八旗科举考试视作翻译科的第一事例。而且,三种文献均提到了停办翻译科的事,即“停止翻译”和“此后惟翻译未经举行”。
固然,无论是天聪八年的八旗乡试,还是顺治八年礼部研议的八旗科举,二者皆与翻译考试有关,但就性质与意义而言,二者皆非翻译科之缘起。《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和《八旗通志·初集》中,均将顺治八年的旗人考试称为“八旗科举”或“八旗考试”,而没有将其称作“翻译科举”或“翻译考试”,由此可知二者之区别。《钦定八旗通志》中,虽然用了“翻译考试”或“考试翻译”等字眼描述顺治时期的八旗科举,并将其视作翻译科举之源,且《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中也有康熙二年“复行满洲、蒙古、汉军翻译乡试”的记载,但上述记录实为误记的可能性较大,不排除系实录馆馆臣或编纂者依据雍正年间的情形误植所致(叶高树,2013:52)。有清一代,以“翻译”之名选拔八旗士子的科目很多,如庶吉士、翻译庶吉士、笔帖式等,但这些考试属于各部院衙门自行选用人才的方式,均未形成独立建制,与文科举并行。所谓顺治时期八旗考试中的“翻译考试”或“考试翻译”,也只是一种考试的内容或形式,并非是一种科考制度。
4.《八旗通志》等关于翻译科创建时间的订正
如前所述,天聪八年的八旗考试虽然有着不同类型之分,如满洲习满书、满洲习汉书等,本质上却是“语文测验”,而非翻译科考。同理,顺治八年的八旗科举虽然包含翻译考试的项目,但所谓翻译考试也只是八旗文科举的附设环节,尚未独立成科。凡此二者,皆与雍正元年研拟并于翌年首次开科,且具有独立、自主的制度设计的翻译科明显不同。
《雍正会典》与两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关于翻译科创设的说法不仅与《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冲突,也与《八旗通志》等存在较大出入。《八旗通志》和《钦定八旗通志》中,也将顺治八年、十一年两榜满、蒙举人和进士,归于“文举人”和“文进士”之列,而不是“翻译举人”和“翻译进士”之列,并把首科翻译举人归为雍正二年甲辰科,而将首科翻译进士归为乾隆四年己未科(鄂尔泰等,1985:3393-3396、3419-3422;铁保等,1968:811-813、828-830)。显然,在《八旗通志》和《钦定八旗通志》的编纂者看来,顺治八年、十一年的两科举人与进士均不是出自翻译科举,而是出自八旗文科举。
从清代进士题名碑的情况看,也可知翻译科并非始设于顺治年间。例如,在由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写出版的《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90)一书中,收录了顺治九年、十二年两榜进士的题名碑,但题名碑的书写与文进士题名碑并无不同,碑头和碑文中都没有出现“翻译”字样。而同书在处理乾隆年间的四科翻译会试(即乾隆四年己未科、十年乙丑科、十三年戊辰科,以及十六年辛未科)时,碑头和碑文中却明确标注“翻译进士”或“翻译会试”字样(北京图书馆金石组,1990:52、169;24、146)。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本书中关于顺治期间两榜进士(九年壬辰科、十二年乙未科)的称呼也只是“满洲进士”,而不是“翻译进士”,而且该书收录的题名中皆为文进士,未见有翻译进士。由此可知,《雍正会典》和两部《会典事例》将顺治八年看作翻译科之起点确系误记。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大清会典》中,并没有录入“翻译科”的条目,这一点表明编纂者或许已对翻译科有了重新认识。《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中说,顺治十四年正月,世祖降旨吏、礼、兵三部,要求“今后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俱着停止,各部院衙门取用人员不必分别满汉文学”,但此处诏令停办的乡、会试同样只是八旗科举文试,而不是翻译考试(鄂尔泰等,1985:831-832)。事实上,早在顺治朝以前,也曾有开科取士的情况,如天聪八年太宗皇太极命刚林、恩国泰等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崇德三年、六年又取中两榜举人,但上述三科同样并非翻译科(铁保等,1968:780-781)。
毫无疑问,顺治时期的八旗科举和雍正元年初设的翻译科考之间有着渊源关系。首先,顺治朝的八旗科举与翻译科考一样,都有为旗人开设专科的倾向,只不过在前者中满洲和蒙古合为一榜,汉军与汉人合为另一榜,而翻译科考则容括了汉军。其次,就考试内容而言,顺治年间的翻译考试只针对识汉字者,翻译并非考试的全部内容,而翻译科考则主要考察应试者的翻译能力,以实现满、蒙、汉等多种语言融通。雍正朝以后,虽然历代统治者对翻译科考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调整与改革,但翻译科考的制度雏形却在顺治朝时已然形成。可以认为,顺治朝时期的翻译考试为雍正帝创设翻译科考,以及日后各朝的修订与完善,打下了良好基础。
5.《钦定国子监志》对于翻译科缘起的补正
与《八旗通志》《钦定八旗通志》和《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等不同,清代历史文献中,也有将顺治八年、十一年两榜举人与进士称作翻译举人与翻译进士的情况。例如,在沈廷芳辑注的《馆选录》和朱汝珍辑注的《词林辑略》中,顺治年间识汉字且通过考试翻译中式举人和进士者,往往被称为翻译举人、翻译进士。如满洲正白旗人达哈塔于顺治九年壬辰科中进士,被称为翻译进士,并分派至内院学习,正白旗人玛尔汉,则被称作“顺治甲午翻译举人”(邹长清,2011:357)。然而,据前文关于顺治年间八旗科举考试的分析可知,这样的称呼与事实不符。顺治年间的八旗士子,无论习清语,还是习汉语,都是一体考试。只不过,对于识汉字者而言,考试中增加了翻译的环节(内容),但考试本身仍归属文科举范畴。然而,由于编纂者的误解或误记,致使讹错流传。如《国子监志》卷四八《金石三》中,便将顺治九年、十二年两科及第者俱称“翻译进士”:
九年壬辰科,赐邹忠倚等三百九十七名及第出身题名碑,又赐翻译进士麻勒吉等五十名及第出身题名碑。以上五碑在大成门外之东南向。十二年乙未科,赐史大成等三百九十七名及第出身题名碑,又赐翻译进士图尔宸等五十名及第出身题名碑。以上五碑在大成门外之东南向(梁国治,1986:527)。
《国子监志》由乾隆十三年进士梁国治奉敕纂辑,全书共62卷,分圣谕和御制诗文等,后者依类分载于各“志”。按照上述记载,麻勒吉、图尔宸等都被称作翻译进士,由皇帝赐及第出身题名碑。顺治九年,朝廷决定以满、汉分科的形式开科取士,麻勒吉于同年壬辰科考取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一,一甲其余二人为折库纳与巴海,俱赐进士及第出身。然而,尽管麻勒吉后来授封教习庶吉士,但其本人并非翻译进士,这一点从《题名碑录》《进士题名碑录》以及《八旗通志》等文献中均可得到应证。《国子监志》于乾隆四十三年奉敕纂辑,并被收入《四库全书》之后,又于道光年间经监臣李宗昉等奏请,开馆增辑刊印。道光十四年,文庆等完成增辑,共82卷,取名《钦定国子监志》。然而,与梁国治版《国子监志》不同,《钦定国子监志》中,并没有将麻勒吉和图尔宸等人称作翻译进士,这一点也许是文庆等编纂者基于历史事实而做出的修正。与此同时,该书在乾隆四年翻译进士题名碑之后,也增加“按语”如下,可作为考证麻勒吉、图尔宸等人翻译进士身份的重要线索:
翻译乡会试,自雍正元年,定于子、午、卯、酉年二月乡试,辰、戌、丑、未年八月会试。嗣后或举或停,或止准乡试而停会试。至乾隆四年八月,复举行会试。题名之有碑刻,自是科始。二十二年,仍议停止会试。四十四年,照旧举行,并奏准赐进士出身。停其殿试。又奏准停止建立碑记。今翻译进士题名,故仅止四碑。详识于此(文庆等,2000:1106)。
据上文所载,至少可以明确以下四点:首先,翻译乡会试始于雍正年间。雍正朝期间,原定举办四科翻译乡试,即四年(午)、七年(酉)、十年(子)、十三年(卯),四科翻译会试,即二年(辰)、五年(未)、八年(戌)、十一年(丑),但期间时停时举,或仅举办翻译乡试而停办翻译会试,并不规律。其次,乾隆四年八年办理乙未科时,回复办理翻译会试,中式者赐进士出身,有碑刻。再次,乾隆二十二年,停办翻译会试,四十四年恢复,中式者仍赐进士出身。最后,翻译殿试一直处于停办状态。因而,翻译进士题名碑仅有四科,分别是乾隆四年己未科、十年乙丑科、十三年戊辰科,以及十六年辛未科。如果《钦定国子监志》中的上述记载属实,则可知《国子监志》中将麻勒吉、图尔宸等称作翻译进士,并由此认定顺治八年即为翻译科之起始年的观点并不可取。事实上,《国子监志》不仅误记了顺治九年、十二年两榜进士(满洲、蒙古)题名碑,而且在乾隆年间的两科翻译进士题名碑问题上,也发生了讹错与遗漏。具体而言便是,《国子监志》中仅记载了两碑乾隆年间的翻译进士,分别是乾隆十三年的戊辰科和十六年的辛未科,颁赐对象分别是武进、武立等42人。至于乾隆四年己未科和十年乙丑科,其中未见有记录,此事令《国子监志》的可信度受损(梁国治,1986:530)。
6.结语
翻译科的创设始于雍正年间,而非顺治年间,这一点毋庸置疑。顺治时期,八旗科举考试中虽然已有了翻译考试的内容,但此时的翻译考试并非独立建制,而是隶属于八旗文科举,为后者考试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为其考试内容的一个部分。雍正年间,世宗为整饬八旗“废弛陋习”,奖励清语学习,因而创制翻译科,将其视作方法与工具,鼓舞八旗满洲与蒙古奋勉向学,以图进取。翻译科的创设带有明确、强烈的政治、文化意涵,是为了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根本,以及满族文化特征。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满洲祖制,避免满族固有文化被汉族同化,另一方面则是想通过传承自身文化,实现全国政权的长远统治。毫无疑问,作为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的重要成分,翻译科的创设自有其积极意义,它不仅使旗人获得了进身机会,缓解了八旗生计的困难,而且也为朝廷遴选了大量翻译专才,促进了国家治理。然而,翻译科自身也有缺陷与不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首崇满洲”的基本原则上,它是维护满洲特权与旗人利益的集中体现。即便如此,系统考察清代翻译科之缘起,及其利弊得失,对当下研究清代政治、文化发展与变化,以及有清一代的民族关系与政策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