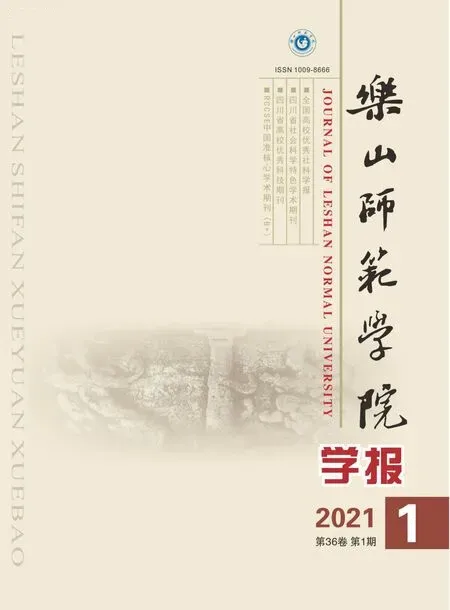元好问: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读者”
孙雅洁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二十》:“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诗下自注:“柳子厚,宋之谢灵运。”[1]72又《其四》注云:“柳子厚,唐之谢灵运。”这开以柳继谢之先河,是继苏轼后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又一大发明。将苏轼作为柳诗的“第一读者”,前辈学者多有著述,已成定论。陈文忠先生一文《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论及苏轼对柳诗的评价时,首先引入了“第一读者”的概念,此后学人如尚永亮先生、杨再喜先生等也对这个论点进行了继承和再阐释。而纵观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历程,元好问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亦是重要一环,丰富了接受内涵、改变了接受方向,足当之“第二读者”①。
前辈学人如叶嘉莹先生、尚永亮先生等,对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谢客风容映古今》一首,都从“风容”之美与“寂寞”之心两个角度切入进行深入细致的诠释,指出了谢灵运与柳宗元在这两方面的共通之处。并站在传播接受的立场上,进一步指出,元好问“以柳、谢之间深刻相似性的新发现,突破了苏轼之后柳诗接受中韦、柳近陶的主流思路,开启了后世柳诗学谢还是近陶的争议,从而使柳诗风格在接受的拓宽和深化中逐渐得以丰富。全面地展现”[2]592。本文试图梳理接受史上“谢柳”同流观点的发展细脉,单独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置“谢柳”于一脉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意义
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经历了较长历程。唐人对其诗缺乏关注,往往就其文“韩、柳”(韩愈、柳宗元)并称、就其政治活动“刘柳”(刘禹锡、柳宗元)并称,至宋代苏东坡、严沧浪发明其义后,逐渐有诗歌风格上的“陶柳”(陶渊明、柳宗元)、“韦柳”(韦应物、柳宗元)并论;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继而又将“谢柳”(谢灵运、柳宗元)并举,给柳宗元诗歌接受赋予了新的意义层。
在元遗山此论前,宋人就有将谢灵运与柳宗元放在一起作比较的,但着眼点仅在创作的山水诗:
柳子厚诗云:“鹤鸣楚山静”,又云:“隐忧倦永夜”,东坡曰:“子厚此诗,远在灵运上。”[3]2704(宋·苏轼《东坡题跋》)
则岂先生好奇,如谢康乐伐木开径,穷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数耶?[4]218(宋·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
谢灵运和柳宗元的山水之作皆名于世,故将二人诗作从此切入作比较,是最易于开掘的角度。苏轼和汪藻彼处持论,都认为柳宗元有过于谢灵运处。苏轼举出的两句诗,一出于《与崔策登西山》,一出于《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这两首诗都是柳宗元山水诗作的代表,笔触细腻,描摹如画。结合这两首诗,再以此处拈举的两句综合来看,仿佛恰好能够突出柳山水诗不同于谢的特点:山水诗中每见其积郁不平之气。汪藻的评说也意指柳宗元的诗歌不似谢诗仅穷山水之趣,谢诗相对来说较为浮于表层。
承续以谢柳山水诗为批评视角的,有清人宋长白、沈德潜、吴汝纶、朱庭珍之辈。他们同时也对上述宋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宽或修正:
康乐、柳州搜奇抉险,尽翻山水窠臼者,不欲以浅易近人,一览而尽耳。[5](清·宋长白《柳亭诗话》)
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永嘉山水明秀,谢康乐诗肖之;夔州山水主险绝,杜少陵诗肖之;永州山水幽峭,柳仪曹诗肖之:彼专于其地故也。[6]1526(清·沈德潜《艿庄诗序》)
古今好山水者众矣,而谢康乐、柳柳州名独著,岂非以文采照烂,足与山水相发哉。[7]167(清·吴汝纶《龙泉园志跋》)
山水诗,以大谢、老杜为宗,参以柳州,可尽其变矣。……夫文贵有内心,诗家亦然,而于山水诗尤要。盖有内心,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作山水诗者,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康乐、工部二公以后,《广陵散》绝已久,柳州望门而未深入,不足嗣音。[8]2344(清·朱庭珍《莜园诗话》卷一)
谢柳二人皆以山水名世,但纵观批评史发展历程,评论家们又自抒其妙。宋长白及吴汝纶所论,不过是在众多山水诗人中拔高和推举谢柳二人。而沈德潜和朱庭珍之言可相互参看,谢柳二人描山摹水,潜心悟会,各得山水精神:灵运诗明秀肖永嘉,宗元诗幽峭肖永州。继以筱园持论,柳宗元游处山水时因不能忘“我”,有损其神。不同于宋人着重于物外之意,清人更倾向于观物忘意。谢康乐游山历水,穷山开径,自得于山水妙趣;柳柳州出贬僻远,每怀苦忧,发言为诗自有积郁。虽然持论立场不同,苏轼与朱庭珍二人所得结论亦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上述无论清人或宋人,皆不脱对谢柳这两个山水名家诗作进行优劣比较的视角局促。
依上所见,元好问“谢、柳”并举之论并非平地而起,实是有宋人将二人山水诗作比的基石。其开辟性贡献,在于并不祖述优劣,而是创立起一种传继论。即与上述批评视角的本质分别,在非为谢、柳诗作区别,反着眼于发其同。在元好问之前,宋代也有一例以将谢灵运与柳宗元置于一处谈论的:“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9]669蔡绦将柳子厚诗置于稍让于陶、谢二人的位置上,“雄深”侧重于文辞的雄浑深沉,“简淡”侧重于风格的简朴淡泊。这显然受到了“第一读者”苏轼的影响,苏子评韩柳诗时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10]苏轼将陶渊明与柳子厚置于同一诗歌风格体系之中,突出其淡而有味的共性特征。蔡绦显然受此启发,但更进一步以诗风为衡量维度,将谢灵运融入进来。值得注意的是,他虽兼论陶、谢、柳三人,但往往偏重于陶、谢二人为一体,三者之间亲疏关系不同。批评史中亦能发现其他例子来佐证:
尝谓古人之诗,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乐天,得其冲淡。[11](金·赵秉文《答李天英书》)
则李、杜之古乐府,陶、谢、韩、柳之工而淡,可到也。[12](元·方回《跋周君日起诗册》)
子厚诗在唐与王摩诘、韦应物相上下,颇有陶、谢风气。[13]191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柳子厚,斟酌陶谢之中,用意极工,造语极深。[14]1322(元·陈绎曾《文筌》)
康乐诗,记室赞许尤矣。至其制题,正复妙绝今古……柳州五言刻意陶、谢,兼学康乐制题,如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江口潭岛深回斜对香零山等题,皆极用意。[15]71②(清·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六)
上所列举,都同涉陶渊明、谢灵运、柳宗元三人。可每一则里,陶、谢二人都是连带出现的。柳宗元则与他们在论述中距离较远,都间隔有他人或他语。梳理一下接受史发展的细脉,这里其实存在着两条接受线索的交融:一是上文提及的苏轼论及的“陶柳”关系,二是唐代就有的“陶谢”并称③[16]320的传统。虽然在一则评说中同时出现了陶、谢、柳三人,但若单独拈举出谢与柳两人,并没有直接的深层关联。
同涉陶、谢、柳,或更与其他诗人放在一处谈论,仅限于一种诗歌风格上的归类。以陶渊明为中介,既开掘了柳、陶、谢诗风的相似处,但同时也对相异处进行了遮蔽。元好问本人在《<东坡诗雅>引》的一段中,也同时提到了陶谢柳,“五言以来,六朝之唐,谢、陶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更进而点出了他对“第一读者”苏轼观点的直接接受:“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17]但他并没有将三人混同一谈,而是极力将陶渊明剥离开,单独提举出谢柳二人深层源流上的承继关系。《论诗三十首·其四》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这一首乃是评说靖节诗,诗下小注“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1]60。按说这首诗评说靖节,单言后一句陶、白关系即可,前句又突然提及谢灵运与柳宗元,正是要努力破除在“陶谢”“陶柳”关系线影响下将“陶、谢、柳”混谈一处的现象。
元好问另一首“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将柳宗元置于谢灵运一脉,认为二人有直接的源流承继关系。此首小注“柳子厚,宋之谢灵运”与其四小注“柳子厚,唐之谢灵运”是同一个意思。结合起来看意指,唐朝的柳子厚就是南朝宋的谢灵运,进一步明确和重申自己的论断。而他立论的关键,在于《其二十》后两句“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中的“寂寞”二字。遗山此论见地特出,后世评论者如翁方纲“柳诗继谢之注,至此发之”[18]1499、查慎行“以柳州接康乐,千古特识”[19]72,都予以了认可和推重。
二、谢、柳二人诗歌“寂寞”之意旨
谢、柳二人都因政治上受挫败,在山水间寄寓此身,这也是他们创作的高峰时期。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都作于永嘉、会稽,寂寞之情又自庐陵王义真死后尤甚;柳宗元的诗文在被贬后愈加淘砺精思,“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20]252,又“子厚遭贬谪后,文格较前进数倍”[21]8。
但二人被贬后的心态是不同的:谢灵运出身高门士族,承蒙族荫,被贬后仍可以山水适志;柳宗元虽也出身累世官宦的河东著姓,但至他一代已经渐趋衰败,退保无力。又加以主流思想引导,南朝推崇玄学自然无为,唐朝盛行儒学经世致用。二人同样创作于贬后的山水诗,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22]352(清·沈德潜《说诗晬语》)造语灵秀与幽峭,不应局限于客观自然环境特点的影响,更应是主体心理态势发诸文辞的外在呈现。谢灵运笔下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23]165(《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23]269(《石门岩上宿》),是含有乡怀温情的。与柳宗元“桂岭瘴来云似墨”[24]336(《别舍弟宗一》)、“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24]357(《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这样峭硬幽拔的笔触,截然不类。风格之别固与江浙、荆湘山不同的山水颜色有关,但更有主观心理的投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元好问前,评论者会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作缺少柳诗那种深刻感痛的情绪。
在元好问前论及谢诗,“清”是对其诗风的主流看法:“谢诗如芙蓉出水”[25]160(钟嵘《诗品》);“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26]44(韩愈《荐士》);“公独思康乐,临流诵句清”[27]182(梅尧臣《许昌晚晴陪从过西湖因咏谢希深苹风诗怆然有怀》)……谢灵运谈玄论道,在族荫之下纵情山水,后人对其诗内在情绪的认知有一个历程。元好问没有因袭前人成见,而是透过表层话语的遮蔽,点出他诗中潜藏的“寂寞”之味。这也是他将柳归于谢之一脉,而非陶渊明一路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只他一人切入了谢柳二人山水历游表层动作之下,遥相契合的寂寞心境。
寂寞的情绪从二人诗歌文辞本身着眼,随处可见:
谢灵运: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登池上楼》)
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东山望海》)
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结念属霄汉,孤景莫与谖。(《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濑,修竹茂林》)
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登石门最高顶》)
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23]
柳宗元:
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构法华寺西亭》)
孤赏诚所悼,暂欣良足褒。(《尤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读书》》)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入黄溪闻猿》)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况我万里为孤囚。(《放鹧鸪词》)
屏居负山郭,岁暮惊离索。(《郊居岁暮》)[24]
“寂寞”“孤”这样的字眼反复出现,透露出他们身处山水地之时,内心孤独感亦最为浓烈。创作于被贬之时,是上文所举诗作的一个共性特征。统计谢、柳二人诗作,“寂寞”及“孤”字眼在谢诗中共出现8次,柳诗中共出现17次,创作于被贬时期的分别占100%及94%。用词频率实际反映的是一种心理态势,是主观潜意识的客观投映。因此可以说“寂寞”之情直接导源于贬官经历,无论是谢灵运还是柳宗元,由京都至地方,都非自己主动选择。地理上由朝廷至山水,心理上由进取趋于寂寞。据史料对二者贬谪经历略加梳理,以观察这种打击对他们寂寞心境的直接作用:
谢灵运,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刘裕即皇帝位,因换代依例由康乐公降为县侯,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少帝即位,为司徒徐羡之等患,由太子左卫率出为永嘉太守,在永嘉前后一年辞官归始宁;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帝唯以文义见接,意不平,由秘书监之职赐假东归;同年,复因游娱宴集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归始宁南山;元嘉八年,任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为有司所纠,又兴兵抗收,徙付广州,元嘉十年受弃市刑。
柳宗元,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永贞革新失败,贬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为永州司马,废锢十年;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因武元衡等排挤,复出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卒于贬所。
谢、柳二人山水诗呈现出的整体风格虽有差异,但屡遭贬弃后投寄山水的内心寂寞之情则一,发言于诗,俱为可哀。何三本《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言:“比较灵运与宗元生平,论家世门第,宗元自远逊灵运;然夙负才名,好功嗜进,而卒不得志,放情山水,则与灵运类。二人同写山水诗,诗中俱呈现寂寞不遇之心情,正由于此种类似之遭遇使然也”[28],虽门第有异,但精神相类、际遇相仿,情志为一。寂寞,从词源上讲是无人声的意思,未必无人相伴,但是无人相惜。谢、柳都在遇与不遇间挣扎,但他们的政治悲剧是注定的。谢灵运表面是富贵士族,但有着皇权与士权斗争漩涡下的士族之悲。他一面带着家族的荣光自矜门第、恃才傲物,一面又要努力争取权位维系家族地位,这两点都深为王权忌惮。虽有庐陵王相知,但刘义真实则也站在皇族的利益立场,仅将谢灵运视作一般文人之流游处。柳宗元的悲剧命运亦是自身性格和政治环境决定的。他自幼目睹社会黑暗,与一批同志之人得到顺宗赏识,急切地欲有所作为。但刚激的举措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他们对革新党人多加曲解诬蔑之辞,使柳宗元等陷入了“名益恶,势益险”[29]490的境地。谢灵运和柳宗元都是怀有才情和政治理想抱负的,但个性与大环境的冲突使他们受到排挤,从政治中心被迫退身山水。无论家世背景与时代背景如何,谢、柳落寞的心境无异。
他们二人亦文才甚高,《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30]15将悲懑发诸笔端在柳诗中显然能见,但就谢诗而言,则难从山水描绘与哲理叙说中得到直接观感。元好问敏锐地觉察到了旁人未及之处,叶嘉莹先生在《从元遗山论诗绝句谈谢灵运与柳宗元的诗与人》一文中给予了更为具象的阐发:
反而正是这种缺少直接的体验与感动的叙写,才正是谢氏真实的心境的表现。因为谢氏的遨游山水与述说哲理,原来都只是他自己在寂寞烦乱的心情中,想要从外在获得慰解的一种追求而已。而事实上谢氏对于山水之追求,既未能使精神与大自然泯合为一,达到忘我的境界;对于哲理的追求,也未能使之与生活相结合,做到修养的实践。因此他的诗乃极力刻划山水的形貌,又重复申述哲理的空言,便正因为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他在烦乱寂寞之心情中,想要自求慰解的一种徒然的努力而已。[31]40-41
谢灵运在山水之间看似平静乐处,但在表层略显枯燥的文辞之下,翻涌着对苦痛的努力压抑和对自求慰解的希冀。谢灵运自矜自傲的性格注定,他不会把情绪泣血而出。而克制隐忍之下被掩盖和遮蔽的心境,至元好问被一语点破。
“第二读者”元好问在接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从后人以柳州宗灵运的论调中予以印证。他立论的核心“寂寞”二字,也因后人的进一步申发而更为明晰:
“一语天然万古新,……未害渊明是晋人。”此章论陶诗也。而注先以柳继谢者,后章“谢客风容”一诗具其义矣。盖陶、谢体格,并高出六朝。而以天然闲适者归之陶,以蕴酿神秀者归之谢,此所以为“初日芙蓉”,他家莫及也。
其不以柳与陶并言,而言其继谢,不以陶与韦并言,而言其似白者,盖陶与白皆萧散闲适之品,谢与柳皆蕴酿神秀之品也。[32]1504(清·翁方纲《石洲诗话》)
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33]2429(清·刘熙载《诗概》)
苏长公、严沧浪皆谓柳子厚五古胜韦左司。渔洋论诗云:“柳州那得并苏州。”不知柳州宗大谢,苏州宗靖节,门径自殊,未易优劣。[34]715(清·施山《望云诗话》)
元好问穿透接受传统中陶、谢、柳平淡诗风相似性的遮蔽,将陶渊明与谢、柳二人区分开。清人翁方纲阐释得更加清晰:陶与谢、柳,一为“天然闲适”,一为“蕴酿神秀”。“天然闲适”指文辞上的不加修饰和性情上的悠游自在,陶渊明和白居易可以称之,放在谢灵运和柳宗元身上显然不合适。他们二人的“蕴酿神秀”,乃是经时间和生命的砥砺淘洗,方脱胎换骨、神采秀发。刘熙载点出谢、柳“性”之近,心性的相近导源于相同的“寂寞”之心。
三、结语
《论诗三十首》呈现的诗美观念,尚建安慷慨豪强的风云之气,亦尚陶柳的平淡自然之风,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言:“元好问论诗虽尚豪迈,但于陶、柳之诗亦深致推许。此与苏轼诗风虽才气奔放,近于一泻无余,而其论诗则重在‘天成’‘超然’之意相近。苏轼‘南迁二友’乃是陶、柳二集,元氏论诗推崇陶、柳,亦是此意。”[1]72元好问继承了苏轼豪气奔泻与天成超然这两种诗风并加推许的传统,而又在风格表征之下更进一步,提出潜藏之“心”,即诗人的表层文辞之下的真实话语。元好问对“心”的开掘和关注,几乎出乎本能,也是他独开一面之处。除了本文论及的指出谢柳“寂寞心”外,又有“老阮不狂谁会得”(其五),点出阮籍外狂非真狂,实出自内心的悲凉郁愤之情;“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1]62(其六),跳脱出潘岳自我塑造的诗文形象,指出其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的表里不一……元好问的追求是真心,是“心声传心”。以“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35]予以佐证,他认为唐诗的高绝处,正在以诚为本。遗山自身的诗歌实践亦是立足于诚心、本心,闻名于世的丧乱诗,就是经离乱而作的诗。
赵翼《题遗山诗》评说元好问诗“赋到沧桑句便工”[36]772,“工”之一境的到达必经“沧桑”的淘洗磨砺。这组论诗诗创作于兴定元年,此时的元好问已深有感于现实。虽年仅二十八,但他已历经三次科举失利,且在蒙古军进逼中多年辗转逃避,对国家危亡坎坷和自身政治前途有深刻的体悟和忧虑。论诗诗的精到与他对人生痛感的独到体验密不可分,故能直击其它诗人心灵深处,从文平淡辞中见出命运的砥砺低徊。也只有怀抱同理心的读者,才能够切中肯綮地理解诗歌文字下的内蕴。所以他读谢柳诗,除却肯定浅层的“风容”之美、“遗音”千古,更点明内里从未明说“寂寞”之心。并据此改变了“第一读者”苏轼以柳继陶的接受方向,将柳宗元诗转到了谢灵运一路中去。《论诗三十首》大致是以朝代顺序评论历代诗人之诗,其八至其二十基本是评述唐人。《其二十(谢客风容映古今)》一诗,虽谢柳二人兼论,但按此推测当更偏重于论柳。元好问编纂的《中州集》,收录了周昂一首《读柳诗》:“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37]184柳宗元诗歌中低徊的情感特色,乃出自忠而被黜的经历磨洗,元好问对此是认可的。又在自己的诗论评价体系中将柳诗上溯起源至谢灵运,推动柳诗与谢诗形成跨越时代的交鸣。至清代文人翁方纲,直接承继遗山此论并进一步阐发,对元遗山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地位加以确认。
通过以上论述,观照元好问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地位。首先他继承了“第一读者”苏轼“陶柳”并举的论述,也受到了苏轼之后“陶、谢、柳”以诗风并论观点的影响。但他敏锐地体察到谢、柳二人与陶渊明内在情性的相异,将谢灵运与柳宗元建立起直接联系。通过发掘谢、柳不平的人生际遇和凋敝的内心世界,将柳宗元以“寂寞”之心为共通点转换入谢灵运一源中,改变了苏轼“陶柳”同流的接受方向。概而论之,作为“第二读者”的元好问进行了三步努力,即承继、融合和开立。在“第一读者”苏轼给予的期待视野基础上重新挑战,建立起自己的诗学批评体系,并影响了许多清代学人。
注 释:
①德国文艺理论家姚斯提出:“第一位读者的理解,将在代代相传的接受链上保存、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这样得以确定,其审美价值也得以证明。”“第一读者”的理解及阐释,给予后世读者一种先验性的审美期待,同时对接受活动也形成制约。尚永亮先生在《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一书导论中,开创性地从“第一读者”的概念中引申出“第二读者”,指“那些能突破‘第一读者’诠释之约束、转换接受角度,并同样可以引导接收方向的读者”。本文中认为的“第二读者”,首先继承了“第一读者”造就的期待视野,其次又进行修正或拓宽,以此创造了新的接受方向,形成了新的接受期待。
②这则材料提供了柳宗元学谢灵运的另一接受视角,即从制题出发。因与文旨关联不大,此处仅略表一二。对历朝诗题的关注,清代乔亿《剑溪说诗》卷下就有云:“论诗当论题。魏晋以前,先有诗,后有题,为情造文也。宋齐以后,先有题,后有诗,为文造情也。诗之真伪,并见于此。谢康乐制题辄多佳境。唐人制题简净。”乔亿认为魏晋诗题为情造文,宋齐以后为文造情,而又特拈举出谢灵运制题,可见其制题当是情文并茂。不同于唐人诗题的简净,谢灵运的诗题呈现的突出特点是凝练地写入人物、地点、行为这些要素中的几个,其中又尤以交代地点要素为主要特色。陈衍此处所举柳宗元诗题,不同于《江雪》《读书》这类简洁的诗题,着重点明写作地点,此类与谢灵运相类。
③如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焉得思如陶谢手。”见文献[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