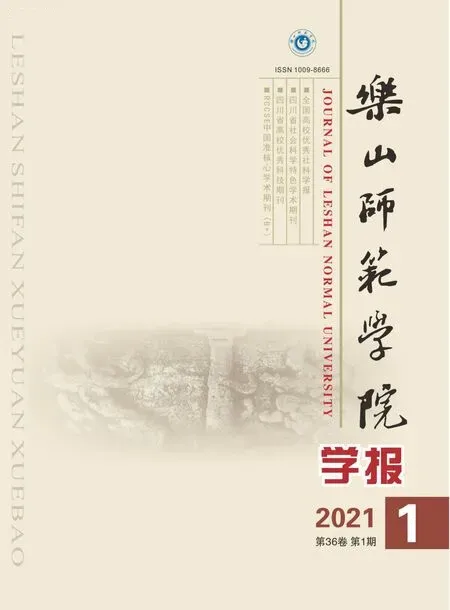圣人作教论
——以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窥探
李前梅
(武汉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430061)
魏晋南朝的《论语》诠释著作,所幸还能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下称《义疏》)中一窥其貌。这个时代喜欢品藻人物,尤其热衷讨论何为圣人、何为贤人等话题,孔子在这一时代被视为圣人,然而在这个公认的称呼下,内涵却并不一样。我们从曹魏时代王弼的《论语释疑》来看,孔子之为圣人在于“体无”,“穷神研几”,“举本统末”等,“立言垂教”只是末节而已①。而东晋以来的学者,诸如东晋的李充、梁朝的顾欢、太史叔明、皇侃等人却在对《论语》的解释中直称孔子为圣师②,并且皇侃对圣人的定义也是“见其作教正物而曰圣人”[1]432。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孔子为圣人乃在于他为圣师,在于他的“作教”。这种对王弼眼中“末节”极为重视的《论语》诠释,是值得我们留意并加以探讨的。
一、圣人作教说在六朝《论语》诠释中的兴起与发展
在魏晋南朝的漫长时期中,《论语》注疏之学可谓异常繁荣,仅据《隋书经籍志》,这一时期对《论语》作“集注”(或集解)的就多达七家,《义疏》类著作也有七家。而流传至今的,却只有何晏的《论语集解》与皇侃对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义疏》,《集解》所集为汉魏诸家《论语》注解,《义疏》所集虽也涉及汉魏,主要部分则是魏晋南朝学者的《论语》诠释。
我们要研究六朝《论语》诠释中的“圣人作教”思想,《义疏》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本。通过对《义疏》的仔细爬梳,我们可以发现《论语》诠释中有关“圣人作教”的思想是在东晋兴起的,发展到梁朝的皇侃而逐渐完善,我们从王弼梳理起,一步一步展现其中的发展轨迹:
例如对于圣人为教多方的总结,王弼之时只是对《论语》中常常出现“同问而异答”的情况予以释疑。见《子夏问孝章》疏引王弼曰:“问同而答异者:或攻其短,或矫其时失,或成其志,或说其行。”[1]31王弼只是根据具体的语境,或者历史背景作出的判断。比如问“弟子孰为好学”,季康子和哀公都有问,但孔子对哀公的答语更为繁复,不仅说颜回好学,还对他说颜回不迁怒贰过之事。学者们则用春秋笔法,对于这个细微的差异予以解释,有人说孔子因为哀公有迁怒贰过的毛病,故而含有劝谏之义,这即是王弼说的“或攻其短,或矫其时失”之类;又有人说季康子是臣,故略相酬答,则是根据历史中人物的身份为依据。如果说上述之例,只是后来学者的臆测,而《论语》“闻斯行诸”之问,则有孔子自己的解说作为证据,子路、冉求同问“闻斯行诸”,而孔子的回答相反,孔子给出了解释,子路喜欢兼人,故而答之有父兄在,不能即行,冉求性退,则答以进之,这就是王弼总结的“或成其志”之类。我们可见,王弼的总结,已经含有孔子为教方法多样性的意思在内,但是王弼却并未把它与孔子行教联系起来,没有把它上升到作为圣人行教的一部分。
而东晋的江熙,和王弼解释着同样的一段文本,却与行教联系到一起了。《子夏问孝章》,皇疏又引江熙称或曰:
夫子答异者,或随疾与药,或寄人弘教。孟懿子、孟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1]31
后人在王弼“或攻其短”的总结上,又添上个“寄人弘教”,这或许是因为子游、子夏列于孔门四科,故而解释者赋予他们更高的地位,这类说法在东晋与南朝的《论语》诠释中十分普遍,也是圣人作教思想的组成部分。
再到梁朝的皇侃,则有更为精炼完整的概括了。《行有馀力》疏云:“教体多方,不可以一例责。”又《义疏叙》云:“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同凡。”
又例如魏晋南朝学者皆普遍认同“圣人生知”的说法,但是《论语》中又常常出现孔子言己学之语,学者则以隐圣同凡来解释,将之看成是圣人行教的一种策略。然而从郭象到皇侃,在看似相同的话语解释中,却有着不一样的侧重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玄化的圣人与圣师之间是有差异的。
《不食不寝以思章》疏引郭象说:
圣人无诡教,而云不寝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后通,习而后能者,百姓皆然也。圣人无事而不与百姓同事,事同则形同,是以见形以为己异,故谓圣人亦必勤思而力学,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则圣人之教因彼以教。[1]410
郭象虽然也是用圣人之教来解释“圣人生知”与“圣人亦必勤思而力学”的矛盾的,但他只是为了阐明圣人因顺万物之情而已,这与他在《庄子注》中,对于圣人的定位是一致的。其实这样的解释反倒是在取消圣人的教化功能,因为在郭象看来,每个个体都是性各自足、无待乎外的,那么个体并不需要“学”,反倒是“学弥得而性弥失”了,因此也就更不需要圣人的“教”了。汤用彤先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一文中,对于魏晋学人之所谓学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其中说到,“不自足乃有所谓学,然王弼曰物皆得一以成,则群有均不离道;郭象曰物皆适性为逍遥,则万物本不假外求。然则众生本皆自足,人皆可圣,亦不须学”。[2]108-109另外,王葆玹先生曾辨析与比较过向秀与郭象的《庄子注》,在对向、郭二人笔下的“圣人”与“至人”进行分析时,敏锐的发现向秀对圣人的肯定多些,说他只反对过时的圣人,不反对当时的圣人,而郭象所发挥出来的见解却更近于《庄子》,认为圣人从根本上来说更利于桀、跖,因为愈重圣人便愈使桀、跖受益。同样,在有待与无待的问题上,向秀那里,万物的生存变化是有待的,唯有圣人与至人是无待的,至人可顺有待者,使万物所待不失,郭象则断定万物原是无待的,至人的作用不过是使万物不失本性,不待乎外。[3]515,535由此我们才说,郭象讲“圣人之教因彼以教”,反而表达了他对圣人之“教”的 摒弃,这与东晋以来的李充、孙绰、皇侃等人崇尚圣人之教是不同的。我们且看《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疏引李充说:
圣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接世轨物者,曷尝不诱之以形器乎?黜独化之迹,同盈虚之质,勉夫童蒙而志乎学。学十五载,功可与立,自志学迄于从心,善始令终,责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约之以礼,为教之例,其在兹矣。[1]25
李充在郭象独化说流行的影响下,以“黜独化之迹”“隐圣同凡”的思维方式,将圣人的行为重心拉到了行教上来,他认为此章就很好地体现了孔子的汲引之教,“责不逾法,示之易行,而约之以礼”,堪称为教典范。同时,他把《孺悲欲见孔子章》也解释成是圣人在设教,还称叹其为教“不显物短,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绝。”[1]464又在《叩其两端而竭焉章》,李充略带抒情的说:“日月照临,不为愚智易光,圣人善诱,不为贤鄙异教,虽复鄙夫寡识,而率其疑诚,咨疑于圣,必示之以善恶之两端,己竭心以诲之。”[1]214将圣人为教的竭诚之心描述得十分恳切。恰巧的是,我们梳理《义疏》中保存的对于孔子“圣师”的称呼,发现也是自李充开始的,可见李充及其所处的东晋时代是我们分析圣人作教论兴起的一个重要线索。
我们继续延着圣人行教说在李充之后的发展路线,可以看到孙绰将孔子的崇教、勉学思想表达得愈加明白。《十室之邑,不如丘之好学章》疏引孙绰说:“今云十室之学不逮于己,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而求耳,此皆深崇于教,以尽汲引之道也。”[1]123又在解释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孙绰比附《系辞》大衍之数五十说:“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穷学尽数,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学之至言也。”[1]26但是发展到比较完整,并且将其定为《论语》主旨思想的做法,却是直到皇侃这里,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章》疏,皇侃用科段的方法,将圣人行教的全过程,并用《论语》中的事例描述了出来:
“云毋意者”一也,此谓圣人心也……圣人无心,泛若不系舟,谿寂同道,故无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谓圣人行化时也。物求则赴应,无所抑必,故互乡进而与之是也。无所抑必由无意,故能为化无必也。“云毋固者”三也,此圣人已应物行化故也。……圣虽已应物,物若不能得行,则圣亦不追固执之,不反三隅则不复是也,亦有无意故能无固。“云毋我者”四也,此圣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迹也。圣人晦迹,功遂身退,恒不自异,故无我也。亦由无意故能无我也。[1]208-209
科段既是皇侃《义疏》的特色[4],段中也没有引用他人的解释,也没有顺延何晏《集解》之说,足见此段疏文将“子绝四”用圣人行教(化)串联起来,是皇侃的特有说法。而他认为只有做到“毋意”,才能实现后三者的思想,也表明了作教的圣人是玄学化的圣人,与李充是一致的,故而本文说圣人作教论的兴起,仍是在玄学主题的“崇本”之下,对于“统末”深蕴的发挥。
二、东晋兴起之因探析:以李充为例
我们通过对王弼到皇侃的《论语》诠释进行分析,已经知道东晋的李充是孔子称谓从“圣人”向“圣师”的转变、以及圣人作教说兴起的一个关键人物。并且我们也已说明,“圣人作教”仍然是玄学发展下的一个命题,只是向“末”的延伸,那么为什么是在东晋时,方强调“圣人作教”的一面呢?这就需要我们考察玄学的发展趋势与东晋的时代背景。
首先,从玄学的理论发展来说,学者都认同,玄学经王弼到郭象,在理论的深度上已经发展到极致,王弼在“以无为本”的层面,与郭象在“无为”“自生”“自化”“独化”等方面建构的理论体系都很精致了,并且他们对《论语》都有训释,但是诠释的《论语》仍然是围绕着上述主题展开的,我们由此可以说玄学在王弼讲的“本”的方面,已经发展到鼎峰了③,而玄学理论若是再进一步的发展,从本的层面向末的发挥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了。同时,从名教与自然这个玄学的主题来看,竹林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受挫之后,从中朝到东晋,特别是经过了郭象“独化说”的理论糅合,以及乐广“名教中自有乐地”的倡导,名教与自然的合一,基本上已经形成稳定的看法,而“无心”与“以礼约之”的圣人行教思想,也正是合一的表现。
再就东晋的时代而论,历经西晋的短祚,除了玄学自发展伊始就有被斥为虚浮的批判之声,玄学家自身也在国破家亡之感中,对玄学发展兴盛之下的放诞之风有所反思。罗宗强先生在他的著作《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将东晋时期的士人对玄风的反思分析得很详细,按照他的举例,大致可划分为这几类:一是以左思、葛洪为代表,对于玄学的反思带着冷眼旁观的性质,虽然对玄风不满,但不是因身受其害而对玄风痛心疾首;二是以王衍、刘琨为例,二人都曾在玄风之中,待到身临斧钺,才悟出虚誕之误国,他们的反思,都是着眼在玄风带来的不婴世务的人生态度的为害上,并且作者认为从这一角度对玄风进行反思是东晋初的一种普遍共识;三是渡江之后,如卫阶与周顗,只因山河异目之感而引起的一时感伤,却把玄风的一整套生活方式与情趣都搬到江左去了。[5]211-226李充做过王导掾属,史书说他深抑虚浮之士,曾作《学箴》,他也自述作学箴的目的是惧后进“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见义教之杀而不观其隆”,他说的“义教”无疑是指礼治教化的儒教,这也就反映了为什么他要在《论语》训释中着力发挥孔子为圣师以作教的思想。但是人们根据他的“老庄明其本,圣教救其末,本末之途殊而为教一”之语,常用来说明他仍是玄学的思维,比如唐长孺先生在《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中就说:“李充还是个南方经学家,但他的深抑虚浮,却是用玄学家的说法。”[6]323这个说法大体不差,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从当时玄学发展正炽,李充反对放诞之风来看,李充这时候说“圣教救其末”“本末殊途而为教一”,反而不是对以老庄为依托的玄学的推崇,这更像是说,据当时之世,应该是圣教救其末的时候了,而不是大畅玄风之时。
《学箴》中对于圣人是这样描述的:
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载之遗风,则非圣不立。然则圣人之在世,吐言则为训辞,莅事则为物轨,运通则与时隆,理丧则与世弊矣。是以大为之论以标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责于圣人而遗累乎陈迹也。故化之以绝圣弃智,镇之以无名之朴。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途殊而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见形者众,及道者尟,不睹千仞之门而逐适物之迹,逐迹愈笃,离本愈远,遂使华端与薄俗俱兴,妙绪与淳风并绝,所以圣人长潜而迹未尝灭矣。[7]2389
他解释了圣人的作用在革制垂训,以为物轨,故而是以“为”来标其旨,但是仅寄责于圣人,又会累乎迹,故而需以老庄“无为”之旨化之。这也就是他说的,老子讲“绝仁弃义,家复孝慈”,并不是说仁义绝而孝慈乃生,只是“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多”,故而他说“老庄明无为之益,在于塞争欲之门。”[7]238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者“为教则一”,而世之虚浮放诞者,却只是在形迹上做功夫,并不懂老庄之道的本意,反而使社会兴起薄俗虚华之风。所以在《学箴》的最后,他对儒家的仁义与礼都持有肯定的态度:“礼不可以千载制,亦不可以当年止,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7]2390换句话说,在他眼里,老庄也是在“去其害仁义者而已”。其实玄学家是不反对仁义的,他们注重的是否是发自人们内在的自然情感,就这点学者已有辨析④。比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王弼解释说:“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1]6还有《林放问礼之本章》、《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章》,王弼重视“礼之本”“礼以敬为主”,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王弼与李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王弼追寻仁、礼的自然情感,是带有不满意现存的名教社会,而追求一种合乎自然的名教社会的理想在里面;[8]258而李充则是针对当时的“放欲越礼”之风,从而主张仁礼不能弃,要发挥其教化与约束功能。我们还可以从李充的《论语》解释中以探究竟:在《管仲之器小哉章》,对于孔子曾称管仲为仁,又说他匡齐不用兵车,而如今又言其器小的问题,皇疏是用魏晋以来流行的才性论来调和,说“管仲中人,宁得圆足”,而李充则列举管仲之功与管仲之行,赞他是“不洁己以求名”,认为他是君子行道忘其身者,这种“漏细行而全令图”的做法,唯大德才堪之,而说“管仲之器小”,只是因为“季末奢淫违礼,则圣人明经常之训,不得不贬为小。”[1]76可见他对仁功的热烈赞赏,对“洁己求名”的不以为然。又在《公冶长》章,孔子评价崔子清矣,而不是仁。李充说:“违乱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无可……洁身而不济世,未可谓仁矣。”[1]117他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与他“穷猨投林,岂暇择木”汲汲追求仕途也具有一致性。
三、圣人作教论的一部分:贤人助教说及其意义
“圣人为教,须贤启发”,这是皇侃对《论语·先进篇》孔子所说“回也非助我者,于吾言无所不说”一语的解释,这一解释所蕴含的思维范式,大有为孔门弟子正名之风,是东晋南朝学者的《论语》诠释之中颇有特色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学者们是通过“助圣人为教”的思想对孔门弟子看似有些违经叛道之语,进行了正面化的解释。有关宰我的例子是最明显的。
在《哀公问社于宰我章》,宰我答“周人以栗,使民战栗”。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云:“宰我不知道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为之说。”[1]71郑玄注文也说宰我“媚耳”[9]21,然而无论是妄说,还是谄媚,总之都是不好的形象。而皇疏却是这样解释的“宰我见哀公失德,民不畏服,无战栗悚敬之心,今欲微讽哀公,使改德修业。”[1]71继而,孔子闻宰我之答所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三语,人多以为是斥宰我,皇疏则以“遂事不谏”是指哀公,意思就是孔子知道宰我的讽谏哀公之心。皇疏又引李充之说,认为这三语看似是在讥宰我,实际上是在感慨道衰。又于《宰我问三年之丧章》,皇疏引缪播的解释:“尔时礼坏乐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惧其往,以为圣人无微旨以戒将来,故假时人之谓,咎愤于夫子,义在屈己以明道。”[1]468又引李充之说,“宰我冠言语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发违情犯礼之问乎?将以丧礼渐衰,孝道弥薄,故起斯问,以法其责,则所益者弘多。”[1]469又在《宰我昼寝章》,皇疏记载了当时的两种说法:一是说宰我是中人,难免有失。一说宰我是与孔子为教,讬迹受责,珊林公、范宁都持此意见。可见在魏晋南朝学者的笔下,宰我的形象被全方位的洗刷了,那个谄媚、不守礼、上课睡觉的学生,变成了针砭时义、屈己以助圣人为教的孔门弟子。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章》以及《樊迟问稼章》等。
当然这种解释的背后,既有情理上的推测,也与《论语》中本就有所展现的一些弟子启发孔子的事例有关。然而这却足以让六朝人感到自负,认为这是自己对《论语》精微之义的挖掘。《季氏将伐颛臾章》疏,引蔡谟曰:
冉有子路并以王佐之资……岂有不谏季孙以成其恶,所以同其谋者,将有以也。量己揆势,不能制其悖心于外,顺其意以告夫子,实欲致大圣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发明大义,以酬来感,弘举治体,自救时难。……斯乃圣贤同符,相为表里者也。然守文者众,达微者寡也,暏其见軓而昧其玄致,但释其辞,不释所以辞。惧二子之见幽,将长沦于腐学,是以正之以莅来旨也[1]424
冉有本就有为季氏聚敛之失,而蔡谟却在此为冉有辩护,赞美他与孔子是圣贤相契互为表里,认为他是要助发圣人之言以拯弊,而孔子则因之以发明大义。蔡谟又斥责那些守文解句者为腐学,声称他们不能识得其中的精微玄妙,而使二人见幽,故正其旨。这种以为自己义理深微、己说即圣人之意的自负,是魏晋南朝时人相较汉儒的特有自信,他们不满意仅停留在显而易见而无深意的层面,如《有教无类章》疏引缪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谅深。生生之类,同禀一极,虽下愚不移,然化之所迁者,其万倍也。若生而闻道,长而见教,处之以仁道,养之义德,与道终始,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论之也。”[1]415故而我们可以说,孔门弟子助教说,也是魏晋南朝的《论语》诠释追求深刻义理的表现。
孔门弟子助教说的普遍化,构成了圣人作教说的一个部分,这使人产生了一种印象,即他们似乎是在为把孔门构成一个完整的教派而努力,这不由得让人联系到东晋以来,在佛、道教的发展盛况下,学者们这样的解释,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儒教的自我标识。特别是佛教作为外来宗教,随着它的传入,与儒教成为鼎立之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相互融合与影响,又互相加以区别,孔门弟子助教说在东晋南朝的流行,或许也有受佛教讲经方法的影响。而这种特意的区别,在皇侃的《义疏》中,也可见其痕迹。例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章》皇疏说:“外教无三世之义,见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未来。”[1]273问“事鬼神”,是问过去,“敢问死”,是问未来,这是皇侃站在佛教的立场,而称佛教之外者为外教。
其实,我们若将《义疏》中所载的贤圣关系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贤人助教说有个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意义,就是这其中寄托了学者对自身的安置。我们知道,贤圣是魏晋以来的人们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话题,其中涉及到对人物的品鉴,将人分出等级,这些分法有很多标准,比如在《论语》中,就有按照所长划分的孔门四科,又有根据“学”的类型,分成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等,还有圣人、君子、大人、善人之别,以及上智与下愚的区分。不过最为细致的要算刘劭《人物志》,其中不仅有诸如“兼材”“偏材”的大类型,还有“九偏”“七似”等对于细微之处的把握。而最简略普遍的还是“辨三等”,就是上中下,分别对应圣、贤、愚,我们在《义疏》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字眼,而其中圣贤分却是讨论的最热烈的,《义疏》中以孔子为圣自不必说,贤人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颜渊为代表的孔门弟子;二是隐士。我们看《义疏》所集诸家对于孔子与颜渊、隐士之间的描述,便可以窥得六朝圣贤关系之大体了。
首先,从孔、颜之间来看,即使颜回被目为仅次于孔子的上贤,但是与圣人之间仍有不可度越之处,用《义疏》说法就是“圣贤道绝”。《子罕篇》,颜回说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皇疏解释说:“孔子至圣,颜生上贤,贤圣道绝,故颜致叹也。”东晋孙绰也说:“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兴立,卓然出视听之表,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从之将何由也,此颜孔所绝处也。”[1]217具体来说,可以分四点来论:一是学者根据《周易·系辞》“见几者,其唯圣人乎”、“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的说法,认为颜回不能照几,故不能无过。(《言寡尤章》疏)二是从“学”上,圣人“生而知之”,颜回即使是“好学分满”(《不迁怒不贰过章》疏),也不能及圣人。三是从“无”与“有”上看,圣人能出入于无有之间,而贤人所体只在有形之域。(《吾与回言终日章》疏)。四是或受佛教中观学派的影响,以为圣人能“全空”“忘忘”,而贤人不能。(《回也其庶乎,屡空章》,梁朝顾欢与太史叔明之说)不过圣、贤有所绝处,是魏晋以来学者的普遍共识,人们也普遍认为圣人是不可学至的,他们一般不敢称圣,最多也只是以贤自诩,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贤”在他们心目中就有特别不一样的地位。比如在魏晋学者那里,孔子是圣人,老、庄则为贤人,然而老庄却成为他们的思想底色。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重视《义疏》中还有对圣贤相成一面的论述:《述而篇》“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疏引江熙说:“圣人作则贤人佐,天地闭则贤人隐,用则行,舍则藏也,唯我许尔有是分者,非圣无以尽贤也。”[1]159
江熙用“天地闭则贤人隐”的说法,更像是在议论士人仕进出处,即是说君主需要贤臣辅佐,而唯有圣主方能用贤臣之意。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之君与臣,都喜欢称道尧舜庭有八凯八元、以及武王“予有乱(治)臣十人”之故。正如刘孝标的《辩命论》说:“夫虎啸风驰,龙兴云属。故重华立而元、凯升,辛受生而飞廉进。然则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而馨犹不同器,鸟鸾不接翼。是使浑沌、梼杌,踵武云台之上;仲容,庭坚耕于岩石之下。”[10]705浑屯、梼杌、仲容、庭坚都是八元八凯里的人物,刘孝标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没有遇到舜这样的贤主(舜其实是在为尧臣的时候举荐他们的),而是生活在暗主之世,也就都没有什么作为了,故而他认为那种废兴在我不在天的说法,是不知命的表现。这就是非圣无以尽贤的思想,或许这也是八元、八凯在六朝特受人们关注的一个原因。与江熙相比较,庾翼的议论,则更似针对孔子作为行教的圣人而发,《子在,回何敢死章》庾翼解释说:“贤不遭圣,运否则必隐,圣不值贤,微言不显。”[1]285这是说圣人的微言大义要靠贤人来显明的,皇侃则把这个思想向前更推进了一步。《先进篇》“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皇疏云:
夫圣人出世,必须贤辅,如天将降雨,必先山泽出云,渊未死,则孔道犹可冀,纵不为君,则亦得为教化,今渊死,是孔道亦亡,故云天丧我也。刘歆曰:颜是亚圣,人之偶然。则颜孔自然之对物,一气之别形,玄妙所以藏寄,道旨所由讃明,叙颜渊死,则夫子体缺。[1]271
《子在,回何敢死章》,皇侃又重申了这个思想:“夫圣贤影响,如天降时雨,山泽必先为出云。孔子既在世,颜回理不得死,死则孔道便绝”。[1]285这是说,没有贤人,圣道就绝了,故而我们更加可以体会到“贤”有一特重要之地位。如果我们考虑到皇侃作为一个经学家,而经学家则正是传播圣人之道,显明圣人微言大义的,那么他这样极力强调“贤助圣教”“贤死则道绝”的思想,是很有为学者自身寻出人生价值的意味的。
对于隐者作为贤人与圣人之分,在《义疏》中也是用类似的思维方式解释的:一是以隐者为中贤,不达圣人教旨。如《宪问篇》:“孔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競兢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皇疏解释孔子之语说:“我道之深远,彼是中人,岂能知我,若就彼中人求无讥者,则为难矣。”[1]385这看起来孔子作为圣人与作为隐者的贤人似有高下之分,但是皇疏又强调说“玄风之攸在贤圣相与……苟各修本,奚其泥也,同自然之异也”,可见他主张的是二者相与,而不是互论优劣。相同的意思还有《微子篇》,长阻桀溺奚落孔子,而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皇疏引沈居士说:“世乱,贤者宜隐而全生,圣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伦。彼实中贤,无道宜隐,不达教旨者也。我则至德,宜理大伦,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无违,无非可相非。”[1]484虽然意思都指向于圣人、隐者无可相非,不过沈居士的立脚点,却是从乱世出发,乱世贤人隐则自无可责处。二是认为隐者与圣人之教相资,相为内外,此则有相资以为教之意。如《微子篇》,孔子对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虞仲、夷逸等隐者有个评价,说自己是“无可无不可”,皇疏于此引江熙说:
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资。若数子者,事既不同而我亦有以异也。然圣贤致训,相为内外,彼协契于往载,我拯溺于此世。不以我异而抑物,不以彼异而通滞,此无所谓无可无不可者耳,岂以此自目己之所以异哉。我迹之异,盖著于当时,彼数子者,亦不宜各滞于所执矣,故举其往行而存其会通,将以导夫方类所挹抑乎?[1]489
人们多以为孔子讲“无可无不可”,是孔子自异于隐士之语,在境界上有高于隐士的意味,而江熙则认为,圣人之迹与贤人隐士之迹相互发明,相互致训,资以为教,是完全将二者以平等地位相待。由此可见,总体而论,六朝《论语》诠释大多主张孔教与隐士之间不执此以攻彼,但是对于圣教拯弊救末却都怀有一种悲怆感。
四、结语
皇侃在《子击磬于卫章》还有一段疏,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六朝圣人作教思想:“圣人作而万物都暏,非圣人则无以应万方之求,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之所缘,动悔之类,则焚书坑儒之祸起;革命之弊,则王莽赵高之釁成。不挌击其迹,则无振希声之极致。”[1]385这是说天下须圣人作教拯弊,但是弊之所起,又缘于有迹。通过这段话,我们就更能理解学者们在《论语》训释中为什么要声称“无心”“黜独化之迹”的圣人,而又将着眼点放在圣人作教的方面。
因为是对《论语》的训释,作教的圣人指孔子,但是正如皇侃所说:“圣人行教,既须德位兼并,若不为人主,则必为佐相。”[1]155-156而孔子则佐相都不是,由此我们不能忽视圣人对理想天子的喻指。从偏安的东晋南朝士人来说,对于一位起而救天下之弊的圣人天子,一定是充满了热切的渴求,但是造成这种偏安的因素,却又是人人都想角逐天下而称帝,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就是一个现实的导因,他们着力描述一个“无心”圣人,行教化于天下,功成而身退,也正是这种现实矛盾所激发出来的幻想。
注 释:
①《天何言哉章》疏引王弼曰:“子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耳行化。”(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64页。)
②分别参见《叶公问孔子于子路章》疏、《子谓子贡,汝与回也孰愈章》疏、《长阻、桀溺耦而耕章》疏、《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章》疏。(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分别见第168、107、480、110页。)
③学者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看,王弼属于本体论,而郭象则接近存在论。我们这里只是用王弼的“本末”思想来看,郭象讲的“无为”“无心”“独化”等仍是属于本的层面的,故而说王弼、郭象在本的层面已经讲的很完备了。
④王葆玹先生在谈论何晏的“性情说”时,对这个问题有过特别说明。他说“所谓仁孝礼义是一些伦理方面的准则,这些准则得到名教的认可,但却不限于名教的规定范围。”(王葆玹:《玄学通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第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