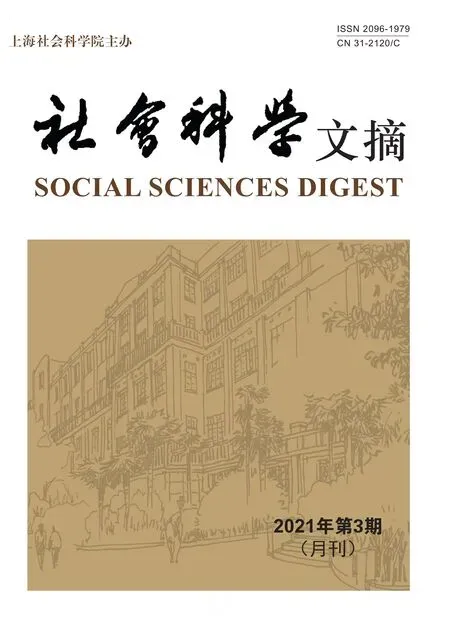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再辨析
“内圣外王”乃儒家表达立教宗旨的理论模型:“内圣”表达人格理想,“外王”表达社会理想,二者有“体”“用”之内在关联。“内圣”指内在的“圣贤工夫”,即以“成德”为目标、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道德修养。“内圣之学”亦称“成德之教”,即教导人在有限生命中取得无限而圆满意义,以成就圣贤人格的学问。“内圣”具有永恒意义,内容和目标持久不易,不会随时代而变化。更为重要者在于,“外王”可由“内圣”推衍以解决。“外王”指外在的“事功”,即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施行礼乐教化德治之“王道”。就内容讲,“外王”即《尚书》之“利用”“厚生”“惟和”、孔子之“安人”“安百姓”、《大学》之“亲民”“止于至善”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现代,由于现代化要求这一时代主题的出现,“施行王道”的“旧外王”已不适应时代需要,故有推进一步的必要,变为“科学和民主”的“新外王”。即,现代化语境下的“外王”已经不再是传统泛泛的“事功”,而变化为“科学”“民主”的具体内容。因为“新外王”的出现,使“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型出现了张力,给“内圣外王”的立教宗旨提出了挑战——在前现代,“内圣”可以直接推出“外王”;在现代,“内圣”未能开出“新外王”。
面对这种挑战,牟宗三对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深入探究。在他看来,既然传统“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而“内圣”又具有永恒意义,内容和目标均持久不易,那么,是否可以在“内圣”之内容和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对其功能进行调节,将“旧内圣”转为“新内圣”,从而开出“新外王”呢? 这个课题便是“新内圣开出新外王”。
在牟宗三看来,“道德理性”“实距理性”亦即“良知”,目的在于指导人的行为,故凡“真”“善”“美”皆“良知”所意欲者,因为它们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真”“美”分别源于狭义的“知性”“感性”,而此“知性”“感性”实即广义“知性”亦即“认知心”的两种功能,故,“真”“美”实源于“认知心”即广义的“知性”。但事实是,“良知”并不“直接具有”“认知心”,而须经由“良知自我坎陷”,使“良知”“曲通”开出“知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良知自我坎陷”可能吗?
“良知”与“知性”是否“兼容”乃前提性问题,否则谈论“良知自我坎陷”便失去了意义。对此,牟宗三的答案不仅是肯定的,而且认为“知性”可以呈显或充实“良知”。基于此,他借助康德“现象”和“物自身”概念,对三个“我”之关系进行了分析:“良知”即“知体明觉”亦即“真我”或“物自身的我”,它以“智的直觉”应之。“真我”之于人呈现为“现象我”即“假我”,它以“感性直觉”应之。“真我”“坎陷”为“认知我”即“统觉的我”;相对于“真我”之“实质的有”,“认知我”仅是一“凸起”,为“形式的有”,故而能由“感性直觉”来认知,当然亦不能由“智的直觉”来认知,只能由“纯粹直觉”即“形式直觉”应之。再次,在牟宗三,仅仅证明“良知自我坎陷”开出“认知心”还不足以开出“新外王”,因为“新外王”与“新内圣”一样,均需要一套形上学的“存有论”为基础。因此,他基于“良知自我坎陷”、依“一心开二门”理论模型建构起“两层存有论”——“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
牟宗三的上述理论建构不仅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而且较圆满地完成了形上建构。对此,学界涌现出大量论著对其进行诠释、传播和弘扬,同时,亦有诸多论著依“体”“相”“用”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批评。所谓“体”,指对“良知自我坎陷”内涵本身进行的批评;所谓“相”,指对“良知自我坎陷”外在特征的批评;所谓“用”,指对“良知自我坎陷”实际效用的批评。
对“体”层面批评的辨析
批评者认为,“良知自我坎陷”在“体”的层面存在若干关键性的理论缺陷。其一,“良知”作为“道德理性”,为伦理学范畴,而不是存在论范畴,故不能作为“本体”。或者说,“良知”至多可为道德本体,而不可为存在本体。即,存在论意义下的“本体”必须是“绝对”,而不能是“相对”,而“自我坎陷”的“良知”却有“知性”与其相对,故不足以“充任”“本体”。质言之,“良知”与“知性”一样,均为“相对性”的概念,为“绝对性”的“本体”之下一个层次的概念,故不可为存在本体。既然不为存在本体,那么所谓“良知自我坎陷”便为“无源之水”,为无根据之论。其二,“良知”与“道德”的区分不明,故所谓“良知坎陷”并不准确。所谓“良知坎陷”就存在理论漏洞,存在“小马拉大车之虞”,故“坎陷”的主词不应是“良知”,而应是“道德”,故须将“良知坎陷”改为“道德坎陷”。质言之,“良知坎陷”不应是两层,只开出“知性”,还要涉及“感性”即“欲性”,而应展开为三层。其三,“道德理性”与“知性”“了无牵涉”,故以“良知”开“知性”乃“无法说明的问题”。其四,“良知只可呈现而不可坎陷”。即,现代人类的“病痛”在于“良知障蔽”,人心陷溺于私欲、物欲。要对治这种“病痛”,方法不是“坎陷良知”,而是“呈现良知”。如果“良知”可以“让开一步”,便意味着可以“永远让开”,而“良知”一旦“永远让开”,“知性”便会乘机“作主”,私欲、物欲会更加泛滥。其五,“认知心”虽可由“良知坎陷”而确立,但此说只是基于“时代必要性”而言,而未能说明“坎陷”的理论必然性,故难以“稳住”“认知心”。
关于上述批评,笔者逐一对应地辨析如下。其一,就儒学史来看,“良知”已经超越道德范畴,而成为存在范畴。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我”即“良知”,亦即“心”,可以与“天”贯通;故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很显然,孟子之“良知”已不仅是道德范畴。在王阳明,“良知”不仅是造化的“精灵”,而且是知之是非和德之善恶的“试金石”,其为存在本体的表述更为彰明。牟宗三继承了此种意义的“良知”,并进行了深入论证。一方面,“良知”既具“创造性”又具“无限性”,故为存在本体。即,人虽在现实上为“有限存在”,却以“超越者”为体,而“超越者”既具“创造性”又具“无限性”,故“良知”亦具“创造性”和“无限性”。这“超越者”不是“上帝”,而是“天道”;“天道”与“上帝”一样,亦为“创造性本身”。另一方面,“智”为“良知”所包含者,即便“智”经由“开出”而为“知性”,亦“隶属”于“良知”;它不是客体而是主体,是“良知的影子”,而不是与“良知”平列相对者;与“知性”平列相对者为“物”,而不是“良知”。可见,“良知”“知性”均非本体之下一个层次的概念,故“良知自我坎陷”为“有源之水”,为有根据之论。其二,“良知”虽然是道德本体,但与“道德心”并无实质之不同:前者强调的是“本体”义,后者强调的是“总体”义。而且,“良知”作为“仁体”包含“智”于内,尽管这种“智”为“圆智”而非“方智”。可见,“良知坎陷”不是“仁性”和“知性”两层,而乃已然展开为“仁性”“知性”“感性”三层。其三,“良知”对应“实距理性”,“知性”对应“理论理性”,二者为同一理性之两种功能,而非两类不同的理性,故不可以说二者没有关联。其四,此批评实际上乃未完全理解“良知自我坎陷”内涵而产生的担心。如前所述,“自我坎陷”的“良知”虽“归藏于密”,作用通过“认知心”呈显,但它仍然发挥统驭作用,不存在“良知”“永远让开”的情形,亦不会发生“知性”乘机“作主”的情形。这正是牟宗三讲“良知”虽“坎陷”但并非“真执持自己”、“认知心”不过是“良知的影子”之意旨。因此,“良知坎陷”不会导致私欲、物欲泛滥,“良知”也不会“为情识陷溺所困”。其五,实际上,所谓“必然性”,不仅可指逻辑的必然性,亦可指实距的必然性,即牟宗三所谓“客观地必要”之义。“良知自我坎陷”开出“认知心”,乃为实距必然性的开展,而非逻辑必然性的开展。既然有必然性,“认知心”便可以“稳住”。
对“相”层面批评的辨析
批评者认为,“良知自我坎陷”在“相”的层面有“主体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其一,“良知自我坎陷”体现出明显“主体主义”倾向,甚至表现出“专制性”“咒术性”或“良知的傲慢”。其二,“良知自我坎陷”有“泛道德主义”的问题。所谓“泛道德主义”,亦称“道德至上主义”,指把人生和社会的一切都“道德化”,以道德代替一切、“侵占一切”;人生和社会其他领域都不再有独立地位,甚至沦为道德的“奴婢”,故而无法实现独立、健康的发展。
关于上述批评,笔者分别辨析如下。其一,关于“主体主义”问题。实际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是人和社会的问题,包括社会政治等的“外在事务”,归根结底都发端于“人自身”,而“人自身”的核心和根本非“性命”“心性”莫属。由此来讲,要解决人和社会的问题,均须从“性命”“心性”去寻求化解之道,故可言“极端内在化”并不为错的路径。就“实距理性”之地位和功能讲,它必然需要具有一定的“专制性”,否则无法宰制“理论理性”,避免人类实距失去方向。所谓“咒术性”实指“辩证地开出”,而“辩证地开出”是就“实距的必然性”而非就“逻辑的必然性”来讲;“实距的必然性”相对于“逻辑的必然性”可能体现出“咒术性”,故“咒术性”亦为不可否定者。其二,关于“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应该说,对儒学的“泛道德主义”的批评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传统儒学作为“道德主义”确实有“泛化”的问题存在,即未能合理地解决“外王”问题,“圣而王”的理想往往“异化”为“王而圣”的现实。不过,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些问题,牟宗三才提出“良知自我坎陷”理论,通过调节“旧内圣”以开出“新外王”,从而解决“泛道德主义”所带来的弊端。质言之,“良知自我坎陷”理论恰是应对现代化的时代主题需求、出于对传统儒学“泛道德主义”的“反拨”而进行的理论建构。
对“用”层面批评的辨析
批评者认为,“良知自我坎陷”在“用”的层面实距意义不具足。其一,西方的民主传统与其说源于自由主义,不如说源于自由主义对于种种“黑暗势力”之正视和省悟的“幽暗意识”;儒家虽然对人性弱点有所洞察,但始终未能超越基于“性善论”的“乐感文化”和道德理想主义。因此,包括通过“良知坎陷”开出“知性”进而开出“新外王”都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情。其二,传统儒家有“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种理路,分别对应“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心性儒学”只可解决“个体生命”的安立问题,“政治儒学”能够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故要解决社会政治现实问题,必须依靠“政治儒学”而开展。而且,所谓“新外王”乃来自西方,并不适合儒家文化传统。其三,以“良知自我坎陷”为核心的“开出说”的确具有理论意义,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远远不够。牟宗三的“开出说”只是与人间社会完全隔绝的纯粹形上学,它虽然完成了“形而上的保存”,却并没有真正实现“实距的开启”,至多只是“实距的开启”的“预取”。
关于上述批评,笔者逐一辨析如下。其一,以自由主义之“幽暗意识”来解释西方民主政治传统固有其事实依据,但并不能将其作为开出“新外王”的唯一依据。准确地讲,“新外王”得以开出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幽暗意识”,而是“理性的架构表现”即“知性”。因此,需要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知性”,进而实现“新外王”。不过,同时还须“摄智归仁”,因为“知性”同时涉及是非、善恶,而它自身无能力解决之,故须由“摄智归仁”通过“良知”来解决。显而易见,这样一种理论恰恰反映的是“幽暗意识”,即对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进而,既然理论上是可能的,实距上便有了依据;有了理论依据,实距也就有了可能。质言之,基于“性善论”的“乐感文化”和“道德理想主义”之开出“新外王”,是可能而且现实的。其二,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并非要直接解决政治问题,而是“哲学地”解释“新外王”之可能的理论问题,即通过“心性儒学”的探讨以解决“政治儒学”的基础问题,因为“心性儒学”是“政治儒学”的理论基础,二者乃“体”“用”关系。不仅不能将“政治儒学”“心性儒学”视为“离则两美,合则两伤”的对立关系,而应将其视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贯通关系。而且,以为“新外王”来自西方就拒绝,显然这是20世纪初叶保守主义的“复活”。实际上,与科学没有国界一样,“民主”乃天下之“共法”,而非专指西方民主。仿照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讲,各国的民主模式其实并无绝对的同质,所谓“民主”乃由不同“成员”构成的“家族相似”。因此,纵使可以拒绝西方民主,但不可拒绝作为“共法”的“民主”。其三,哲学作为一门超越地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超越性”而不是“经验性”是其根本特征,“形而上的保存”是哲学这门学问的“职责”和“使命”。如果由此而否定之,实际上是否定了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就此来讲,“良知自我坎陷”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只要能够说明在中国“新外王”是可能的,哲学家就已尽了职责,而在现实层面完成“新外王”事业则属于科学家、政治家的责任。
结语
总而言之,为了应对现代化要求这个时代主题,牟宗三以开出“新外王”为目标进行了形上的、思辨的严密论证,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理论——“良知”经过“自我坎陷”开出“知性”,由“理性的运用表现”开出“理性的架构表现”,进而基于“无执”到“执”的转折,依“一心开二门”的理论模型,建构起“无执的存有论”“执的存有论”之“两层存有论”。对于这样一套理论建构,牟宗三是以“内圣外王”为理论模型开展的——在稳住“旧内圣”内容和目标的前提下对其功能进行调节,实际上是将“旧内圣”转为“新内圣”,从而解决了开出“新外王”的可能性,即哲学地证明在中国开出科学和民主的可能性。很显然,相对于传统“内圣外王”讲,牟宗三不仅明确“旧外王”应转变为“新外王”,而且调节“旧内圣”的功能为“新内圣”,即对“内圣”“外王”进行了双向调节。牟宗三的理路不是“旧内圣”开“新外王”,而实为“新内圣”开“新外王”;在现代语境下,“新内圣”与“新外王”实现了双向互动。对于这样一种“新内圣”与“新外王”双向调节的理解,应以应对现代化要求这个时代主题而进行哲学理论建构为语境,否则可能会对此理论产生不同理解,前述的很多批评即多源于不同语境。因此,这些批评可谓“人病”而非“法病”,而此“人病”源于语境的变换。当然,亦不可完全否定前述“体”“相”“用”三个层面批评的价值,因为它们在改换后的自身语境下亦有其价值。总之,肯定牟宗三关于“内圣”“外王”之双向调节理论,不仅意味着对“良知自我坎陷”的理解,亦意味着对儒学自身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