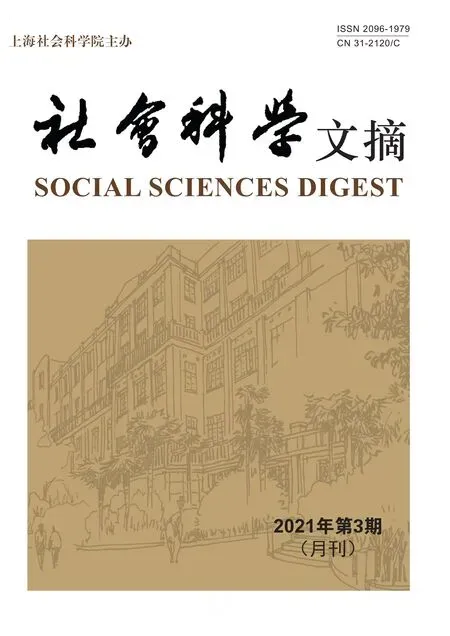论秦汉都城空间的演进与京都赋的形成
《两都赋》《二京赋》是以长安、洛阳两都(二京)分篇行文的方式写作,设置的人物对话也是相互辩驳式的两都优劣论。班固、张衡的这一结构设置只是文本呈现的表层结构,他们的主观目的也许有展现长安、洛阳优劣的一面,但更在于强调洛阳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都城,即比较两都只是方式、手段,目的则在于赞颂“洛邑之美”。为了实现这一创作目的,班固、张衡固然根据的是现实中的长安、洛阳,但侧重的内容无疑是经过筛选、加工甚至夸饰而成的。因此,班固、张衡笔下的长安、洛阳,是文学作品塑造的都城。《两都赋》《二京赋》的这一创作方式提醒着我们:东西二都的优劣之争只是文本的表层结构,而他们的目的在于赞颂理想的都城。
京都赋作家笔下的“洛邑之美”尽管呈现出理想化的色彩,但无疑又具有都城实体的支撑,如宫殿布局、郊祀之礼、三雍建筑等都可以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然而,“有制”“法度”之下的东都并非一蹴而就的,即“洛邑之美”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持久而长期的历史进程,而它一旦形成便促使、激励着班固、傅毅等人创作京都赋,以呈现它的“完美”与成熟。
东都洛阳的空间建设与“元始故事”
从京都赋的内容来看,“京洛之有制”的典型表现并不在于都城的朝向、宫室的结构化、中轴线的明晰等,而在于都城礼制空间的完善。这就是班固、傅毅等人屡屡提到的“三雍”,即明堂、辟雍、灵台。为了突显这些礼制建筑的重要性,班固甚至觉得只在正文描绘还不足以呈现它们的价值,所以在结尾处又以“颂诗”的形式单独对其加以赞颂,以此东都主人也彻底折服了西都宾,后者更真诚地赞叹,并作出了终生的承诺。班固在描述西都宾叹服之时,也点明了自己作品与司马相如、扬雄之作的区别。其中“义正”“事实”,应蕴含着对洛阳帝都气象的强调:与司马相如、扬雄笔下的长安事物相比,东都洛阳的特质是“义正”“事实”,而“义正”“事实”落脚于实体建筑无疑正是“三雍”。通过这样的行文安排,班固显然是在强调完美的礼制建筑是帝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空间,它是“京洛之有制”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度”的核心代表。
同都城的整体空间一样,洛阳礼制建筑的完善也呈现出秦汉礼制空间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京都赋作家引以为豪的“三雍”于中元元年(56年)动工,永平二年(59年完工),时间跨越光武、明帝两朝,三雍之礼的制定和实施也由汉明帝承担。“三雍”建成当年,汉明帝“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同时“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这是制定并实施明堂祭祀、灵台望气、辟雍养老等礼仪。与“三雍之礼”相配合的是五郊迎气之礼,即“是岁,始迎气于五郊”。汉明帝制定和实施的“三雍之礼”“五郊迎气之礼”,标志着东汉国家的郊祀开始形成体系。然而,无论是三雍礼制空间的建设,还是汉明帝制定和实施的相关礼仪都存在着曾经在西都长安讨论、实施的历史踪迹。
对于东汉士人而言,“三雍之制”往往被追溯至西周乃至更早的远古帝王,但对于汉帝国而言,在京都建设“三雍”,最早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即位之初与“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但最终“未就”;后来,汉武帝又建“汶上明堂”,这座明堂显然远离于帝都长安。王莽奏建“三雍”的时间是在平帝元始年间,除了“三雍”的建设,此时还制定了一系列郊祀礼仪,这就是光武帝、汉明帝举行祀典时所经常言说的“采元始中故事”。也就是说,东汉时期成体系的国家祭祀礼典应直接来源于“元始中故事”。与之前相比,王莽所制定的“元始仪”提升了帝都长安的地位,“元始故事”似乎使长安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和神圣中心。然而,王莽的作为和努力在东汉统治者以及京都赋作家那里并未得到认可。
京都赋对王莽的否定与“帝德”的确立
对于东汉统治者而言,“元始故事”“元始仪”虽然为帝国的礼制建设提供了依据或参照,但它的主持者王莽却最终谋篡了大汉的天下,这一点也许正是东汉统治者只乐意提及“元始中故事”而不愿意提及王莽的原因所在。
同时,京都赋作家在作品中对新莽一朝的鄙夷与批判显得更加直接,如杜笃云“逮及亡新,时汉之衰,偷忍渊囿,篡器慢违,徒以埶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诛自京师”,班固言“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张衡曰“巨猾间衅,窃弄神器。历载三六,偷安天位”等。既然是“篡器”“作逆”“窃弄”,班固、张衡等人显然不愿意将洛阳之“法度”“有制”追溯于王莽治下的长安。从《两都赋》《二京赋》的内容来看,西都宾、凭虚公子对长安的描述限定在王莽之前,因此举行“元始仪”时期的长安是被京都赋作家有意忽略的阶段。班固、张衡的这一做法,符合东汉知识界的惯例,如东汉王朝在使用“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说”时,也有意忽略了王莽“新朝为土德”的阶段,而直接采用了“汉承尧运”“协于火德”之说,即《东都赋》所云“系唐统,接汉绪”。
客观来看,元始礼制的确有助于提升帝都长安的地位,是都城文化空间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新莽祚短、天下汹汹,郊祀的威严与神圣不但没有巩固、持续,反而被一再的亵渎和破坏。因此,长安也就没有真正成为天下士人心中的理想之所,帝都的神圣与权威更没有真正地建设成功。
王莽新朝的国策多变,固由多种原因所致,迁都之事虽然最终搁浅,但从王莽迁都心意的坚定性来看,帝都长安显然不是新朝中心的理想所在。经过“元始改制”,作为天下中心的帝都长安本应成为时人心中的“首善之区”,然而王莽迁都的计划足以说明事实远非如此。因此,王莽主持下的建三雍、定郊祀流于形式和表面,根本没有真正完成帝都神圣与权威的文化建设,而这一点则要延续至东汉光武帝、明帝时期加以完成。
光武、明帝两朝都城文化建设可依靠的知识资源是包括“元始故事”在内的“汉家故事”。以都城的文化空间建设而论,东汉古典国制的建立同样蕴含着洛阳作为帝都文化建设基本完成的意义。
相对于王莽新朝礼制的空洞、无力,汉明帝制定并实施的“三雍之礼”“五郊迎气之礼”显得真实而强劲,更带有正统而神圣的色彩。也许东汉王朝的礼制体系还需明帝之后的章帝、和帝继续完善,但经过光武、明帝的努力,都城的文化空间建设显然已经走向了成熟:帝都洛阳成为集皇权与神圣于一体的天下中心,“处乎土中”“图书之渊”连同礼制之美、神雀宝鼎之瑞,一起见证着帝都的完美和首善。于此,王莽心仪而未能实现的“定帝德,国雒阳”,此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东汉朝廷而言,“帝德”显然就是“汉德”,即班固所言的“目中夏而布德”“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述叙汉德”,张衡所云的“汉帝之德,侯其褘而”“大汉之德馨,咸在于此”。“帝德”的确立与明晰,昭示着帝都文化建设的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帝都”一词得以独立,“义尚光大”的京都赋也得以形成。
帝都神圣性的建构与附会
迁都之论是京都赋所呈现的表层结构,但是否迁都显然不是班固、崔骃、傅毅、张衡等人所能决定的,他们以赋的体式言说迁都之争也许主观目的各有不同,但由此塑造的理想都城显然是洛阳而非长安。那么,京都赋作家心中的洛阳无疑是完美的帝都,它强调“法度”、“有制”、仁义道德,更是“大汉之德馨”的象征;与此同时,它又是圣主“体神武之圣姿,握天人之契赞”“寻历代之规兆”的结果,它的明堂、辟雍、灵台使得“上帝宴飨,五位时序”、“三光宣精,五行布序”、宝鼎神雀之瑞频现天地。将这两方面相结合便可以看出,班固等人的京都赋为我们呈现出一座十分完美的“统和天人”之帝都,这也正是一座集皇权与神权于一体的帝都。
京都赋作家的这一塑造并非个例,同时期的大臣王景有感于迁都之论,“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可见,王景在写作《金人论》之时与《两都赋》一样通过“神雀诸瑞”强调“洛邑之美”在于“天人之符”。与盲目、过度、无节制的神灵信仰相比,班固、张衡描述的神圣帝都显然是有序的、礼制化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受到天神的护佑并降下诸般祥瑞。所以,帝都的神权是以德性为基础和前提的,这也是班固、张衡等人一直强调“汉德”的原因所在。
与此相比,在班固之前的杜笃不但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更缺乏对帝都神权根据的描绘,虽然他也使用了“天人之符”,但他强调的不是帝都,也非立都,而是限定于光武帝“受命立号”,即所谓“于时圣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获助于灵只。立号高邑,搴旗四麾”。在杜笃眼中,帝都是“守国之利器”,与神权无关、与仁义无关,所以他的结论是“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杜笃的结论并非无据,而是来源久远,直承于西汉初年的刘敬、张良等人的定都之言。在刘敬言说定都关中之时已经明言并非“与周室比隆”,也不是“务以德致人”,而是以关中“阻险”“入关而都”,以形成“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刘敬之言,又被留侯张良认可,进而刘邦定都长安。
因此,杜笃与刘敬、张良等人的观点一脉相承:二者在强调关中之“阻险”“守国利器”的同时,也排除了“仁义”“有德”之于帝都的意义。与班固、傅毅等人相比,杜笃的论调显得陈旧,他既没有注意到东西汉建国初期客观形势的不同,也没有考虑大汉帝国经武宣元成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更没有探及都城文化空间的建设和积淀。
与之相反,班固等人不但在强调帝都的德性,更在尽力展示帝都的神圣。当然,神权笼罩下的帝都并非从班固等人开始建设的,在此之前可追溯至秦始皇“作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建阿房宫“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古今学者多认为这是“象天设都”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史记》的记载来看,秦朝的咸阳城还谈不上“象天设都”,因为秦始皇关注的是个体宫殿的“象天”,而非都城的整体布局,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象天设宫”。
秦朝的“象天设宫”观念是否直接影响了长安城宫殿的建设,我们很难从《史记》《汉书》中找到切实的证据。魏晋时期出现的《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城上应南斗、北斗的天象,因此被称之为“斗城”。这一描述关注的是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因此常被当作“象天设都”观念的主要论据。但是自从元朝开始,这一说法广受质疑,结合相关考古成果,“斗城”之说的城墙曲线都是因地形所致。显然,“斗城”之长安是《三辅黄图》的一种附会。
京都赋的重塑与都城实体的互动
然而,《三辅黄图》对长安城的附会也并非完全没有踪影。以现存的文献来看,言说长安城的建筑上应天象的内容不见于史书,而见于《两都赋》《二京赋》,且都是指向宫室、池沼建筑,如《西都赋》言“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昆明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西京赋》云“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等。以秦朝的“象天设宫”而论,班固、张衡的描述应该具有真实性。这在验证长安宫殿延续秦朝观念的同时,也展现出《两都赋》《二京赋》的价值:它们以文学的手法为后人呈现了帝都长安城建设中的“象天设宫”。更为重要的是,班固、张衡的这些描绘成为《三辅黄图》进一步演绎的基础,并最终提出长安为“斗城”之论,由此中国古代的“象天设都”观念也正式形成。
由“象天设宫”走向“象天设都”,即由都城的局部走向都城的整体,京都赋是这一衍生过程的关键阶段。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张衡的《西京赋》:“及帝图时,意亦有虑乎神祇,宜其可定以为天邑。岂伊不虔思于天衢?岂伊不怀归于枌榆?天命不滔,畴敢以渝!”这是言说刘邦定都长安的过程,与杜笃明显不同,张衡虽然把西京长安置于东京洛阳的反面,但并没有刻意回避长安作为帝都的“神性”:他使用“神祇”“天命”来表述选都的过程、使用“天邑”来称谓长安,也许“天邑”在张衡的本意中是指“天子之邑”,如同《尚书》之“天邑商”,但在其他人看来,又完全可以理解为“象天之邑”。再结合其中“天衢,洛阳也”,“象天之邑”的理解显得更为合理、有据,于此西京长安在整体上拥有的“象天”之神意呼之即出。因此,京都赋对长安神性的描述,直接启发了魏晋时人看待长安城的视野,进而形成长安为“斗城”的结论,“象天设都”的观念也正式提出。
《东都赋》《东京赋》对洛阳城礼制和法度的描绘,也同样启发着《三辅黄图》对长安城的塑造。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三辅黄图》对三雍礼制建筑的“重塑”:长安“三雍”的建造晚至平帝时期,但《三辅黄图》却将明堂、辟雍的建设追溯至汉武帝时期。这一看似无意的“重塑”显然增强了帝都长安的礼制性格,以至“隋宇文恺议立明堂,王元规议上帝后土坛”皆以《三辅黄图》的记载为论据。所以,《三辅黄图》对帝都建筑、形制的重塑,一方面承继于京都赋的描绘,另一方面又启发着后世帝都建造者的设计和构想。这是由京都赋经都城文献(《三辅黄图》)再至都城建设的路途,如果以此来说明京都赋对都城实体的影响还显曲折的话,那么隋唐长安城的建造者宇文恺对《东京赋》“三雍”内容的引用,则能够证明京都赋对于后世帝都建设的直接影响。
明堂、三雍、圆丘等还仅仅局限于都城单体建筑,至于都城整体的形制和布局,宇文恺更是实距、落实着由京都赋到《三辅黄图》的知识衍生,这就是隋唐长安城的“象天设都”。隋唐长安城在“有制”“法度”之中又有上天星象的象征,是真正“统和天人”的完美代表,更是“天邑”的完美呈现,由此“象天设都”的观念也得到完美的落实。
从两汉时期长安、洛阳的实体建筑到京都赋的描绘和增饰,再经过《三辅黄图》的演绎和重塑,以至隋唐长安城的设计和建造,可以呈现出都城实体、都城文学、都城文献乃至都城文化之间的多维互动:两汉时期的都城实体反映于京都赋,京都赋的铺陈与夸饰又被都城文献(《三辅黄图》)加以延伸和推进,进而又影响隋唐时期都城建筑的设计和整体布局。都城文学、都城文化乃至都城实体也正是在这一多维互动之中逐渐走向丰富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