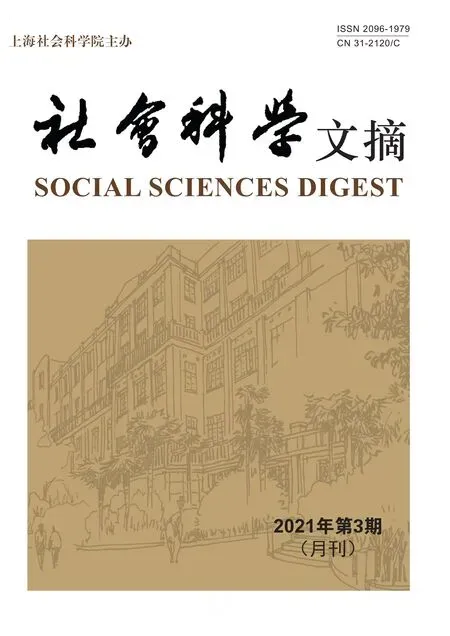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特性
面对全球数字化这一不可逆转的浪潮,数字命运共同体因其包涵的全面解放社会生产力和全面解放人的巨大潜力,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路径和判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指数的重要标准。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数字命运共同体
随着数字化浪潮在人类的生活、交流、工作和存在中不可逆转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理应也会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一方面来讲,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内容;从另一方面来看,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也是衡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指标。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四大理念(全人类性、未来性、共有性、共同性),数字命运共同体已经实现了高度重合。数字命运共同体主要有三大新特性,能够让其担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这三大属性分别是: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
数字命运共同体的连通性
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第一大新特性是数字连通性。数字连通性是“超数字时代”人类信息交流与互换、形成交流与互通共同体的新属性,构成了区别于人类现代文明时期最初的交流互通的本质属性。
数字连通是数字时代人类交往主体打破国界限制、进行全球化跨境联通交流的新形式。数字人类的数字连通性,将促成全世界在数字平台上实现跨境交流。“跨文化交际”进行“数字转向”的内在属性,要求连接进入“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各方从文化政策和技术支持方面扩展出跨国文化交流的多种渠道,开发更多的跨文化交流网站、手机app软件,最大程度地开放与共享更多的数字化资源,让跨境交际人群更容易、更快捷、更廉价地获取和处置更多的数字信息与多媒体资源。“数字跨文化”可以运用前所未有的廉价、便捷、高速、多元的方式,让更多人无需跨出国境就能切实加入跨国跨文化交流的“大朋友圈”。
在数字全球化的时代,数字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数字化浪潮有利于世界各国交流实体以数字化的全新形式打破国界,构建基于全球化跨境连通交流新形式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各国数字化的不均衡,甚至基于数字技术优势而产生的新的“数字鸿沟”或“数字天堑”也可能让世界各国之间产生新的“数字垄断”和“数字霸权”,阻断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协同发展,甚至因为数据泄露、黑客攻击等重大数字事件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动乱。数字全球化像经济全球化一样,都是数字全球化和数字本土化的辩证性统一,数字命运共同体能够超越地域因素对跨文化交流的物理性限制,但不会完全祛除人类跨文化交流进程中的地域特征,从而形成多元共生的“数字全球本土化”。
作为承载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平台,互联网不但是一个国际交流工具,而且是通过本土交流实现本土化过程的方式。接入互联网的各个国家与国民并不是语言不通、无法理解、互相敌对的文化社群,而是以一种高度的文化多元性形态,努力探索着不同于面对面和实质性接触的、跨文化交流的全新的民族文化“数字大熔炉”模式。这个熔炉无意移民,却能够随意迁移。它不愿殖民,却能够跨越国境长驱直入。它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并不是实体存在,却又无处不在。具体而言,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在互联世界的同时形成了连通性的新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数字连通性开拓出了文化畅通性;第二,数字连通性保留了文化差异性;第三,数字连通性塑造出了文化新形式。数字连通性这三个新特征,也让数字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互联世界的平台,其通过范围更广、方式更多、程度更深、关系更密的立体形态把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总之,从未来世界格局的宏观新形态来看,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及其第一大特性——数字连通性——极有可能会塑造出一个全新的数字文化疆域,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万国连通及其“全球国家数字联合体”:其尊重各国数字文化疆域主权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共享联合体内各国的数字信息与数字权利,言说与书写着共同的数字编码语言,发行与流通着共同的数字货币。“全球国家数字联合体”这一新形式或许可以成为符合马克思所预言的,一个人类文明主导下的,以数字科技推动人类生产和生命解放、实现人类组织形式的新型“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最终能够完成“历史任务”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互惠性
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第二大新特性是数字互惠性。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互惠性,是先前任何历史阶段所不曾拥有的。
从全球的人类历史来看,地域之间的大连接,也即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征服、掠夺和剥削,相应而来的是一方的特权和另一方的被夺权,一方的压迫与另一方的被奴役。到了数字时代,也就是数字全球化的时代,数字化连通的方式,很有可能会成为规避殖民主义掠夺的新模式。当然,殖民主义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展开,比如说强国的互联网黑客通过窃取弱国数据或操纵弱国舆情的方式,实现影响他国甚至颠覆他国的政治目的。但是,技术是中性的,面对数字化连通加以拒绝否定或是进行封锁封闭并不是一项明智的选择。规避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使用技术的主体是否能够坚持秉承一种“互惠性”理念。
对此,数字命运共同体内在的“互惠性”理念,将有机会革新这一“开拓—殖民—压迫—反抗”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受难的“此增彼减”二元对立方式,代之以“先进带动落后,发展惠普各方”的新合作理念。互惠性是数字命运共同体连接性的第一步升华性体现,也是基于统筹性理念生发出来的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密切连接性。立足于统筹性的互惠性,是数字命运共同体能够肩负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任的重要特征。所谓统筹性,即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种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的信息化机制建设。如此言之,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就是顺应数字全球化而生、能够在数字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大发展的人类数字共享交流机制。
数字命运共同体将以一种平等、互动、开放、共享的理念,打造成为一个范围更大、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互惠更多的机制平台,来支持世界的数字全球化新形式和数字社会新形态,支持世界跨境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创新。
笔者提出了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所包含的几层内涵:
(1)一种跨国信息传播的实体化基础设施建设或虚拟媒介,或实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与虚拟媒介的结合体。(2)一种区别于经济全球化,但又同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全球化呈现方式。(3)一种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世界信息共享和国际合作的有效平台机制。(4)一种以数字化方式推动世界大同思想以社区形式实现的世界主义理念。(5)一种推动数字化基础与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家工信业现代化行为。(6)一种互联网时代世界文化自由无碍地跨境传播与互融并存的文化形态。(7)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参照指数与阶段标准。(8)互联网时代人类的一种交流和生存的媒介与方式。
面向未来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可能出现的最大特征就是参与各方没有输家、都是赢家,参与各方可能赢的大小不一,但都会赢。可能纳入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各方在短时间内没有实现绝对的平等主义,但其宗旨和最终目标必然是公平、正义、机会均等、各方平等的机制性建构。
在“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联合体”的理论指导下,我们更应该加强以互惠性为基本理念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从而让互联互惠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连通性将给全球化交际的人类主体赋予一种新的“共同语言”,以解码—编码的数字语言形式,编织起数字命运共同体运行的软件和所需要支持的技术性硬件。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能够在连通中互惠、因互惠而连通,进而形成整体上的良性循环,不会因霸权主义和单向剥削而不可持续。
数字命运共同体的调试性
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第三大新特性是数字调试性。数字命运共同体中的“数字调试性”概念,是指连接到数字命运共同体、达成互惠的各方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的共存形态特征。这种“数字调试性”将是“数字连通性”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巩固和推动“数字互惠性”的重要保障。“数字调试性”的内在本质,要求连接进入数字命运共同体内的世界各国破除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片面单向维度,而从全球视野的立体面多维度考虑问题。未来世界不可避免的数字全球化将进一步从更深层次推动政治方面国家利益的全球布局协调、经济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开拓、文化方面创新发展的国际交流共享、社会方面人类组织形式的海外散居,进而逐步发展成“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多元混杂形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数字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沦为“唯数字技术马首是瞻的技术奴隶”和“数字商品拜物教教徒”,被无限泛滥的数字信息所吞没,在“娱乐不至死但玩物已丧志”的数字命运歧路口迷失。
数字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这种“数字调试性”特征,能够帮助全人类不脱离根本的民族—国家爱国理念,同时又超越较为狭隘的民族—国家唯我中心观,以一种数字时代普遍适用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从更为理性谨慎、全球整体的宏观角度来制定和执行国际国内的各种决策。在数字命运共同体“共存并立”的平台机制中,出现发动世界大战的战争狂人或者胆敢按下核按钮毁灭地球的疯子的几率变得微乎其微,各国领导者与广大人民将能更加深切地领会到“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历史经验,各国政府也将会以更审慎的理性态度来处理分歧,共同享有人类科技文明发展成果带来的巨大福利,共同应对重大疫情灾害、恐怖主义、跨国腐败、毒品交易等威胁全人类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从而将各方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从国际关系来看,数字命运共同体中的“数字调试性”反对一成不变的固化思维方式,倡导多元对话框架内的相互协商、相互适应,并以此作为数字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国之间展开跨文化对话的精神基础,进而有力地遏制单边主义行动,有针对性地切实减少国际冲突。
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数字调试性”特征将塑造出具有如下三个素养特征的未来国际性领导人才。
第一点,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数字调试性将塑造出新数字一代国际事务管理者的“数字领导力”。不同于人类古代权斗历史上靠足智多谋、攻心驭人式的心理战型领导,未来领导者不但需要自身具有强大的数字信息搜集检索、筛选、分析的能力,以及在充分保障信息安全的情况下运用数字媒介进行信息沟通和舆情处置的能力,而且需要站在数字时代前沿的眼力、能力与魄力,在国际层面积极地实质性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文化机构的完善与发展,给予数字技术发展所需的政策支持,制定出台数字技术相关的管理文件与政策,管理好数字技术支持的虚拟或实体社区。这种数字领导力素养,也许有朝一日会与外文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并重,成为遴选国际领导人才的重要衡量标准。
第二点,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数字调试性将塑造出数字新一代国际事务管理者的“世界领导力”。具有世界领导力的数字新一代国际事务管理者将不同于为帝国进行海外探宝和海外殖民的哥伦布与麦哲伦式的探险入侵者角色,不会运用自身掌握的先进数字技术来进行数字垄断、布局数字操纵、制造数字鸿沟、施以数字殖民和数字剥削,而会因其所具有的、超越国界的世界性数字人文主义情怀,致力于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平等度更大、共享度更高、信息更透明、社会更和谐的国际秩序。这种新型国际事务管理者的思维出发点,不同于以往历史上基于民族国家或者地区领导所持有的、以片面维护一方或者多方利益而损害其他更多或者世界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观,而是能够在基于全球人本主义关怀所需的调试性和灵活性框架内进行去偏见化和去本位中心观的政策制定,全力做到既不损害国家利益也不损害世界利益,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巧妙的平衡点,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世界使命。
第三点,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数字调试性将塑造出新数字一代国际事务管理者的“调试性领导力”。数字命运共同体中的“调试性领导力”将符合三点要求:第一点,充分获取数据材料,包括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采集分析的方式,形成基于数据而又超越数据的宏大系统观;第二点,基于调试性,形成既能够稳定地立足于本国利益的本位,同时又充分考虑他国感受的知己知彼、换位思考的多元视角;第三点,从数字调试性出发,落足到统筹观,能够在兼顾平衡中开发出话语合作的无限可能性与现实模式。总之,数字命运共同体更注重避免主观争论的歧见和偏见,让沉默的数据说话,以充分的“调试性领导力”整合国别资源,跨越国家差异,超越国别文化,在系统平衡和优化中探索最佳效能且切实可行的多方合作方案。
综上所言,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对未来国家跨文化交流的管理领导人才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将打造出一批具有数字领导力、世界领导力和调试性领导力三大能力,同时兼备数字世界主义人文关怀和为数字人类谋福祉两大素养的新型国际化人才。与之相似,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推进也将为全新的调试性数字化人才提供培育的土壤和发展的平台,让精通国际业务的数字精英型人才在数字化时代居要位、显大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共同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形态,塑造数字命运的新未来。
小结
数字命运共同体对未来人类文明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数字科技时代人的全面解放和人类文明的重塑提供了可行的思想基础和实距平台。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出现,将促成一种“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在“数字世界主义”思想理念的指引下,人类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归属感可能会被数字命运共同体重新塑造出一种全新的、超越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以及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数字人类的数字文化多元性也会在“数字世界主义”的重新融合与散播中,重构出新的兼具通行性和独特性的话语体系,最终通过“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放射性路径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圣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