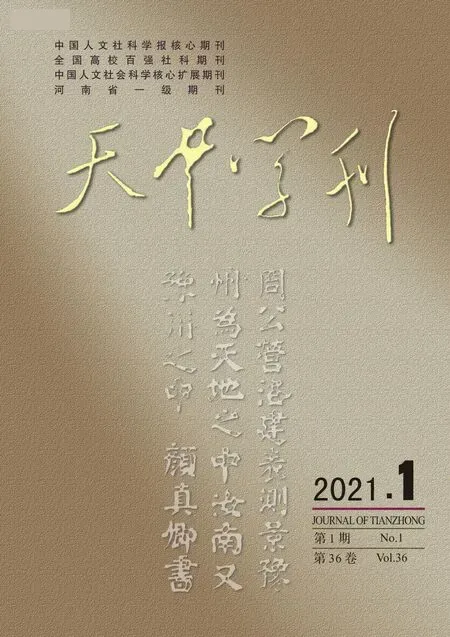论“神道设教”思想的理性旨归
闵明
论“神道设教”思想的理性旨归
闵明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神道设教”之表述始于《周易》。关于“神道设教”的意蕴,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神道设教”是神秘主义外衣下的封建统治方式,是一种愚民手段,“设教”的理性目的被“神道”的迷雾笼罩乃至消解。事实上,在殷周政权更迭之间,神鬼之祭在慢慢褪去宗教神秘色彩,儒家从中看到“神道”在民众教化上的超约束力,并以“神道设教”作为社会治理的模式,进而将神道思想与礼义教化结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序发展探索出一条生生不息之路。探讨“神道”意蕴和“神道设教”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有助于揭示“神道设教”所蕴含的圣贤治世之理性趋向和社会教化之意义旨归。
神道设教;儒家;意义信仰
《周易》所描绘的天下是圆融而生生不息的,要达到这种理想之境,需要一定的依托。在人世教化上,圣贤看到“神道”思想中超验约束与理性精神的结合,故而选择以“神道设教”推行社会教化。学界在“神道设教”的目的指向上还存在争辩。钱钟书认为“神道设教”是“愚民以治民之一道”[1]。史继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神道设教”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是一种统治之术,且认为这一套政策统治者本身是不信的[2]。当然,必须承认在某些历史时期存在统治者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愚民统治。但是,从《周易》元典精神出发,上述观点可谓只见“神道”手段,而未见“设教”旨归。在理解“神道”内涵上,如不能见其全貌,而将这种制度模式仅仅理解为“愚民政策”是不可取的。本文将从《周易》元典精神出发,重新解读“神道设教”意蕴所指,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何为“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最早见于《周易》,“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彖传》)。圣贤设观卦之旨在于,由“观”所见自然四时的运转而知天道流行不易,以“上观俯察”达到对天地万物的体认感悟而明天道、神道,并以此教化万民,观卦正是说明圣人借天道以教化生民之旨。
(一)“神道”意指
何为“神道”?对这一概念如何阐释,直接影响对“神道设教”的理解。易学界主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以高亨为代表,认为“神道”是超越的神明之道,“圣人因而以神道设教,教人信神,信神能赏善而罚恶,信神掌握人之富贵贫贱,则不敢越礼为奸,犯上作乱”[3];另一种观点以黄寿祺为代表,认为“神道”是自然之道,“神道,犹言‘神妙的自然规律’”[4]。对于“神道”如何理解,《周易》中早有表述,《周易·系辞上》有:“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依据《周易》的诠释,“神道”可理解为“阴阳不测之道”。这里所说的阴阳不测,并非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不可预测之意,而在于强调天地万物消长、生灭之间的往复与变化。《周易》中的“神道”指向的是自然运转之道,如此“设教”内涵亦可明晰,即为“教化”之意。
(二)自然之道与人世教化
既然“神道”如此精深,那么如何才能借“神道”以实现“设教”之功,或者释为“神道”与人世教化之间的通道如何形成?《周易·系辞上》说:“是故阖户未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周易》认为乾坤阴阳的变化之道,在百姓日用中就已显明,而这种变化之道的高明处就在于,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是极其推崇这种神妙之用的,“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系辞下》)。孔颖达疏亦有:“‘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而四时之节气见矣。岂见天之所为,不知从何而来邪?盖四时流行,不有差忒,故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5]134孔颖达以极具理性的态度提出,“神道”显现为天地之间“四时流行”的自然运转,他于《周易》看到了天地之间规则秩序的无处不在,天地规则自然生发,天道四时流转而不易,圣人能效法天地,故能以此“神道”教化民众。“神道”之用早于民众生活中的自然生发,当然,圣贤取法天道而对民众施行教化还需一定载体,这有待下文进一步讨论。
(三)以“神道”致“设教”
《周易》中所说之“神道”即自然之道,效法自然之道而行,以“神道”致“设教”,它以神明之道为其表征,内含的是对自然运行规律的把握。在理解儒家的“神道设教”时,首先就当避免以神秘主义看待“神道”之全部内涵,“上古时代‘神道设教’,非为愚民,而多在于注重传统的承继……并非统治者为愚民而特设,而应当是民众自发的教育形式,当然这其中也有统治者的参与和支持”[6]。摒弃以“愚民政策”理解“设教”的意义指向,如此方可进一步讨论这一教化之方,如果只看到“神道”的宗教仪式,而不见“设教”目的,那么就不能见出儒学的高明所在。结合《周易》所述,“神道设教”当有如下的含义:其一,以祭祀仪式为其手段与表征;其二,以效法天地法则为内在精神;其三,以促进社会和谐为根本目的。
二、“神道”的目的转向
殷周交替之际,伴随着政权的更迭,“神道”思想也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转向。“神道”思想最早与天帝鬼神之说关系密切,自三代以来,鬼神观念在社会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殷商重鬼神祭祀,他们往往会以丰盛的祭品,表达对神鬼祖先的敬畏,其祭祀活动亦未脱自然崇拜的特点,“上帝”在殷人心中是至高无上、喜怒难测的,人只能匍匐在神力之下。
(一)宗教神秘性的退场
周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虽然祭祀活动亦颇为隆重,保留有前朝祭祀的形式,“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但在意义上此时已然不同于商朝。与殷人相比,周已经有所变化,周人看到了前朝只求于神灵而亡国的教训,他们并未在神明的超越力量的幻象中迷失自我,而是更趋于理性。虽然周人心中所奉的祖先神、帝仍旧具有至高地位,“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尚书·多士》),且周人希望在祭祀活动中借助天道的超越性来证明君王权力的合法性,“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大雅·文王》),但同殷商不同之处在于,周人在这些仪式中更多地看到了所处世界的真实性,看到了其中的规律性,新的“神道”观念渐渐形成,“神道”背后的价值意义更为凸显,宗教神秘色彩逐渐退场,“神道”的目的落在了“敬德”“保民”处。所以,周人也会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二)“神道设教”的社会治理价值
基于殷周文明发展的特殊阶段,于民智初起之际,绵延普通民众心中的原始信仰具有巨大的约束力,是圣贤借以推行政治治理的最有效途径。殷周之时,鬼神信仰极为普遍,而鬼神的超约束力,在某些时候要高于法律、道德的约束。所以,在古代精英统治阶层中,借助“神道设教”治理社会,成为广泛的共识,其根本目的是以“神道”的教化之力确保万民合天道运行之意志,以使民风醇而天下治。由此,“神道”之力便显现出来。所以,“神道”思想中潜藏着巨大的理性精神。我们应当看到圣贤在组织社会的过程中使用“神道”手段的意义,圣人以祭天、敬神为实施教化的手段,而实质是要达到对社会的治理。当然,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以“神道”的理性内核为手段而施行教化,与纯粹的“愚民”思想之间存有巨大区别,虽然两者都指向社会治理,但“神道设教”之目的不是单纯的政权统治,它是圣贤对自然运行之道的“模写”。
(三)儒家的天道观
上述神道思想上的变化,影响了儒家对治世之道的思考,他们从祭祀仪式中看到了鬼神信仰在社会教化上的意义。在儒家看来,“神道”的仪式皆为教化的手段,儒家一再明言不信鬼神之事,比如:孔子曾说“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荀子的看法更为直接,“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荀子·解弊》),荀子直接认为鬼神之说是人在精神恍惚间做出的判断。但是,在对社会治理的设想中,儒家却于此用功最多。儒家学者对“神道设教”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孔子说:“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礼记·祭义》)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荀子也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是虔敬地对待鬼神;二是还要以此教化民众:然教必以祭祀为主者,以神道设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观之,则圣人制为祭祀之礼者,非但以致吾之诚、报神之德而已也。而实因之以设民之教,使咸安其分,尽其职以报乎上焉。”(《大学衍义补·卷五十五》)由此可见,儒家的学者们早已看到了“神道设教”在社会治理、民众教化上的独有优势,通过仪式感极强的祭祀之礼,能使民众德性醇厚。由此可见,自周孔开始,“神道设教”逐渐抛却了原有的神秘色彩,慢慢走向了人文教化的目的。“儒家的祭祀,原来只是道德的延续,而不是宗教的祈求。一般宗教的祈祷,都是为了求福,而儒家的祭祀,则完全为了报恩。祭天是为了报本反始,祭祖是为了追养继孝,祭百神是为了崇德报功。”[7]祭祀活动在民间传统中所体现的意义大多是“伦理性”的,而非全是宗教意义,我们祭祀神鬼,实际是祭祀祖先的魂魄。
周朝持“神道”制度,所要表明的不仅是其政权合法性,它更是民众教化目标的实现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由重“神性”转向“人性”,在这个过程中,以“神道”形式施行教化的模式亦随之确立,在随时代变迁中“神道”依旧保有其独特的教化作用。对“神道”这一思想的转变认识,孔颖达的注疏最明:“‘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者,此明圣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观’设教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为而成,圣人法则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故云‘天下服矣’。”[5]134–135圣人所以能以“神道”教化生民,在于能效法自然之道,进而将这种自然之道运用在社会治理之上。所以,天下便能够有规律地运转发展下去,此为圣贤以“观”而知社会治理之规律;同时,只有圣贤自身显现出“贞正”之德,才可为天下生民所见,也因为这种“自行善”,才可为万民效法,此即圣贤以自明之德使天下“观”而治之理。
三、以礼“设教”与意义信仰的生成
随着文明进程向前,以“神道”而致“设教”的最终目的指向发生转变,“设教”目的终于成为主动力,而“神道”作为手段随之留下的只有“仪式”,“礼”之内涵也逐渐丰富,“古时人的公私生活,从政治、法律、军事、外交,到养生送死之一切,既多半离不开宗教,所以它首在把古宗教转化为礼,更把宗教所未及者,亦无不礼乐化之”[8]。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礼”的作用范围是更广于宗教的,“礼”之功用伴随我国古代文明发展而行,宗教信仰所依靠的原初动力是以“神圣”外力教化人,而“礼”是靠内化的道德修养使人远离“野蛮”。于是我们看到,要通向“神道设教”的教化目的,终究还需“礼”的贯彻。
何为“礼”?许慎解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说文解字·示部》)“礼”强调践履而行,它的本义是敬神以求福,礼的甲骨文为“豊”,根据字形可会意为以玉置于器皿中,表示敬奉神明之意。“礼”的形成本于祭祀活动,“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礼”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意义重大,儒者认为知礼堪称教化之本,“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经解》)。“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强国》)。“礼仪”的设计在于秩序建构,《礼记·祭义》明确表达出这一点:“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崇拜神、敬畏神的阶段,而“礼”就成为连通天人之际的必要桥梁。
由“神道”致“设教”的制度模式中,“礼”的内容亦随之扩展,“礼”不再单纯是祭祀中的“礼节仪式”,而从祭祀仪式进入政治教化中进一步体现为“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与这一改变相伴的是,传统“祭祀”之意义逐渐发生改变,“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荀子·天论》)。可以说“神道设教”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已经完全是出于理性的结果。唐代柳宗元指出祭祀“非于神也,盖于人也”(《柳河东集·䄍说》),直截了当地说明祭祀目的是为了人,而非为了神。王夫之亦说:“圣人以神道设教,阴以鬼来,我以神往,设之不妄,教之不勤,功无俄顷而萌消积害,圣人固不得已而用之。”(《船山遗书·周易外传·观卦》)
随着理性文明的生发、壮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亦随之深入,“神道设教”的背后,是宗教信仰模式向意义信仰的转向。《中国经学思想史》一书将信仰体系区分为两种:“一种信仰体系指向彼岸世界,此即宗教信仰;一种信仰体系指向此岸世界,此即意义的信仰。”[9]两种信仰最终是两条不同的路向,这也使意义信仰与宗教信仰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神道设教”所关涉的就是宗教信仰走向意义信仰,“意义信仰”借助“礼”教化万民,同时采用“宗教”的祭祀形式开展教化,这是因为祭祀仪式庄严肃穆,能使参与者身心沉浸其中,在特定时期往往能让人更好地接受教化。人的理性思维逐步生发,由宗教信仰走向意义信仰,是整个社会理性进步的结果,从原始的鬼神敬畏,到对其存而不论,儒家希望将社会关注的视线转移到人事之上,鬼神信仰被用作道德教化的手段,意义信仰所关注的此岸世界凸显出来。而以“神道”致“设教”更是社会理性发展之必然,殷周之际正值“神道”目的转向,而人文理性之力日益彰显,在“神道”的祭祀仪式之下,当看到圣贤在组织、治理社会过程中的理性旨归。
[1]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
[2] 史继忠,三白.历代治黔方略:民族·宗教卷[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3:166.
[3]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214.
[4]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8.
[5] 周易注疏[M].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陆德明,音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6] 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
[7] 唐端正.儒家的天道鬼神观[J].孔子研究,1986(2):102–108.
[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08.
[9] 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44.
On the Rationality of Superstation-converted-Confucianism
MIN M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Superstation-converted-Confucianism” (ShenDaoSheJiao) was first appeared in.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view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at it is a kind of feudal governance under the cover of mysticism and a means of fooling the people. The rational purpose behind it is ignored. In fact, during the regimes of Yin and Zhou dynasties, the sacrificial activities of gods and ghosts gradually lost its theological and mysterious color. The rulers saw the super-binding effect of superstation and converted it a form of social governance.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superst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and practicality of “Superstation- converted-Confucianism” will find its rational tendency of govern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social education.
Superstation-converted-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faith
B2
A
1006–5261(2021)01–0012–05
2020-05-22
闵明(1990―),男,江苏淮安人,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叶厚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