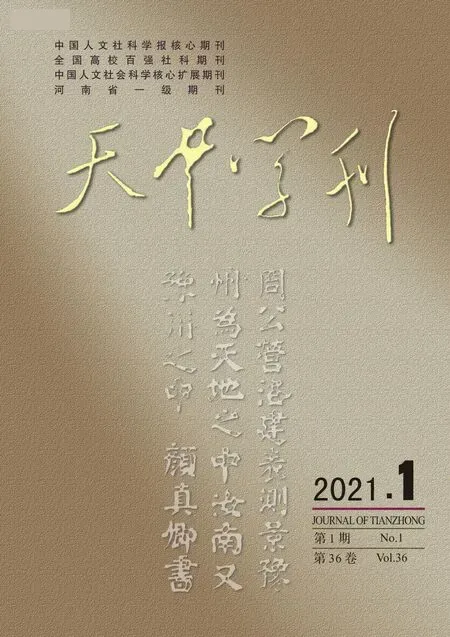王氏家族与新室代汉——基于家族史视角的考察
张楠
王氏家族与新室代汉——基于家族史视角的考察
张楠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元城王氏家族的崛起和内部调整对新室代汉有着重要影响。王氏的“四父五侯”通过干预皇室、清除异己使王氏控制了政权,实现了由外戚向权臣的转型。王氏中衰复起后,王莽以此为契机排除叔父势力,安排子女命运,提拔亲己成员,重组家族结构,使自己摆脱了叔父蒙荫,树立了自己在王氏家族内的领导地位,为实现代汉迈出了关键一步。新朝建立后,王氏成员经历了家族中混杂着阴谋与忠诚的一系列风波,对王朝的兴亡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氏家族;王莽;新室代汉;家族史视角
新室代汉是秦汉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该事件的主要人物王莽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王莽与新室代汉的问题,学界从外戚专权、儒生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切入的研究甚多,但从家族史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缺乏,仍有一定的探讨空间①。本文拟从家族史的视角对王氏家族与新室代汉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元城王氏家族在其中的变迁历程,以期有益于新莽研究。
一、“四父五侯”对政局的控制
西汉自宣帝起,“外戚由帝舅身份而封侯开始形成制度”[1]151,这为王氏家族控制政局提供了便捷之门。元、成交接,王政君晋升为太后。与此同时,和王政君同辈的王氏家族男性成员依旧例封侯辅政,尤以王凤为贵。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王氏一门五人同日封侯,震动朝野。自此,“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2]4018。王氏家族的势力充斥内、外两朝,皇权受到节制,外戚专权的局面初步形成。王氏的权力来自其外戚身份,外戚自吕、霍之乱后成为朝臣厌恶同时又畏惧的存在,因此朝中有许多人对王氏不满。为了巩固家族地位,王氏家族必须压服朝臣,左右皇帝,成为真正的权臣。具体而言,王氏家族“四父五侯”从两个方面采取了行动。
首先,干预皇室内部事务。对于外戚出身的王氏家族而言,其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与刘姓皇室的姻亲关系。因此,如何干预甚至控制刘姓皇室的事务是王氏家族考虑的重点。由此牵出了两个事件,即许皇后事件和定陶王事件。许皇后是汉成帝的第一任皇后,早年深受皇帝宠爱,但其子嗣皆早夭。成帝时期一度连年发生日食现象,朝中“言事者颇归咎于凤”[2]3982,指责王凤是引发日食异象的罪魁祸首。王氏家族为了转移矛盾,由谷永等人出面将指责的矛头指向许皇后。许皇后开始感觉到王氏家族对自己的敌意,“自知为凤所不佑”[2]3982。清代学者王先谦在此处认为:“凤死于阳朔三年,后废在鸿嘉三年,去凤死四年矣,言此者,以见后之废,由王氏肇端也。”[3]5974许皇后确实由此开启了失宠之路,后被牵连于诅咒之事,终遭废黜。在王凤等人与许皇后的关系中,汉成帝的态度至关重要。成帝没有听从许皇后的辩解,而是听信了依附王氏家族的谷永之言,如此一来王氏家族成功嫁祸于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看作王凤等人对皇帝的一次试探。自成帝继位以来,王凤一直把持朝政,“威权尤盛”[2]3982。在关乎帝后的重大问题上,汉成帝倒向了王氏家族。对王氏而言,这是对控制皇帝效果的一次检验,结果显然“可喜”。同样,在定陶王事件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王氏家族对皇帝的控制效果。汉成帝无子,欲转位于定陶王刘康,于是利用刘康来朝的机会将其留在京城。刘康的受宠引起了王凤的不满,王凤假托日食现象,认为“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2]4019。汉成帝虽有万分不愿,但被迫与刘康痛哭而别。
其次,清除异己。这里主要针对的是朝臣和其他外戚家族。王氏家族的专权引起了王商、王章等人的反对。王商为宣帝旧戚,对王凤深有不满,于是在诸多事情上与王凤针锋相对。如在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天的京师大水谣言事件中,王商力排众议,冷静地戳破了谣言,使得听信谣言的王凤大为羞愧忿恨。王商逐渐成为王凤的敌人,后在王氏集团的打压下最终免官而死。王章向来刚直,在定陶王事件和王商之死中都对王凤的专权提出了直接的挑战,甚至还建议让“先帝时历二卿,忠信质直,知谋有馀”[2]4021的冯野王代替王凤辅政,结果王章一家遭到了王氏的残害。这些事件使朝野上下对王氏家族充满恐惧,而王氏“四父五侯”则利用已有的权势继续排除异己,震慑群臣。冯野王因王章事“惧不自安,遂病”[2]3303,最终在王凤的运作下免官回乡。张禹最初与王凤并领尚书事时便畏惧王凤,后又因肥牛亭土地一事得罪了曲阳侯王根,但当吏民指责王根时,张禹为避难,又被迫上书为王根开脱。成都侯王商素来与陈汤不和,在其掌权后将陈汤“下有司案验,遂免汤,徙敦煌”[2]3418。
通过上述手段,王氏家族的“四父五侯”全盘控制了西汉政权20多年。他们上持天子,下御群臣,成功完成了由内侍外戚向内外权臣的转型,这为后来王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汉成帝也曾经一度想将王凤、王根、王立等人治罪,但考虑王氏家族内为外戚而不忍、外为权臣而不便,最终不了了之。
二、王氏家族的中衰与重组
汉成帝末年,王氏家族“四父五侯”中仅剩王根、王立二人。汉哀帝即位后,对王氏家族进行了清理。哀帝先是在司隶校尉解光的倡议下剪除了王根、王况的势力,接着又培植自己的外家势力,“封拜丁、傅,夺王氏权”[2]3503,最后将王莽贬回封地。通过哀帝一系列的运作,“成帝外家王氏衰废,唯平阿侯谭子去疾,哀帝为太子时为庶子得幸,及即位,为侍中骑都尉”[2]3738。可以说,在朝廷层面上,除了孤悬于上的王太后外,王氏已无权高在位者。这对苦心经营二十余年、成功控制朝政的王氏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然而哀帝早逝,随着哀帝的去世和平帝的继位,王氏家族卷土重来。虽然哀帝对王氏家族造成了沉重打击,但也正是这次打击给了二次掌权的王莽重组家族结构的机会。王莽重新掌握权力后,外压群臣,内整家族,就其对家族的整合与重组而言,他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王莽在汉哀帝打击“四父五侯”残余势力的基础上继续清理叔父的遗留势力,同时消除同辈中的威胁。到汉平帝时代,王氏家族的“四父五侯”中仅剩下红阳侯王立。在五侯的继任者中,有威望的是平阿侯王仁、成都侯王邑、安阳侯王舜等人。其中王邑、王舜是王莽的心腹,而王立、王仁的存在令王莽感到不安。红阳侯王立在五侯中的影响力虽不如王凤、王根等人,但他也不是安分守己之人。早在成帝在位时期,王立就曾多次利用权势贪赃枉法,成帝就曾因“红阳侯立父子臧匿奸滑亡命,宾客为群盗”[2]4025而大发雷霆。鸿嘉年间,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2]3258,被孙宝劾奏,从而失去了继任大司马的机会。王立不思悔改,反而怀疑淳于长陷害自己,视之若仇敌,后又因私人利益为淳于长言事,引起成帝的怀疑。王立因逃避案验,竟令自己的儿子王融“自杀以灭口”[2]3732,自己则被贬回封地。对王莽而言,存在这样一个曾经在朝廷中上下其手的叔父,显然不利于自己,即所谓王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2]4045。更令王莽担心的是,王立在南阳封地期间“与诸刘结恩”[2]4035。众所周知,平帝即位后,王莽代汉已日见明显。在此时前后,却有王氏家族成员与刘氏宗亲往来甚密,这显然与王莽的计划背道而驰。综合以上考虑,王立必除。于是王莽先以旧罪令王立归国,又在元始三年(3年)借王宇事件派使者令王立自杀。至此,王立的势力基本被摧毁。与王立的贪赃枉法不同,王仁则属于另一种情况。史书称王仁“素刚直”[2]4030,这样的性格为王莽代汉所不容。此外,王仁和王莽同为王氏家族新一代的才俊人物,汉哀帝曾令王莽和王仁回到京城共同侍奉王太后。不难想象,这样的经历自然使王仁在家族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因此也招来了王莽的担忧。于是,王莽动了杀心。在王立自杀的同一年,王仁也因王宇事件而被迫自杀。除掉二人后,王莽叔父辈的势力基本被清除,同辈中具有威胁的主要人物也被消灭。可以说,以王立、王仁的死为标志,王莽在家族内终于一人独大,成为王氏家族的实际领导者,这为王莽发动新室代汉打下了又一个基础。
其次,在子女问题上,杀子嫁女,客观上巩固威信,重新缔结外戚姻亲。王莽有嫡子四人,三人横死,其中王获、王宇在王莽代汉之前去世。王获死于王莽蛰居新都时期,原因是王获杀死了自家的奴仆,王莽令其自杀以谢罪。这个事件争议颇大,但其客观结果显而易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2]4043,王莽也因此重新被征召回京。王宇之死与王获有所不同,如果说王获之死是王莽的“小题大做”,那王宇之死则引发了一场血雨腥风。众所周知,王宇死于“血门事件”,起因是王宇坚持要王莽将卫太后留在京城。这与王莽“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2]4065的策略相背,由此引发了父子二人的矛盾。王宇之死无论是王莽出于排除异己的考虑,还是王莽出于“诛杀管蔡”的大义,这些历来自有评说,本文不再多言。但必须要承认的是,王宇和几百人的鲜血确实在客观上震慑了天下的反莽者。同时,连续诛杀两位嫡子的行为更是震慑了王氏家族,进一步强化了王莽在家族中的领导地位。与对待儿子的严厉不同,王莽在对待女儿的问题上则表现得柔和许多。其在嫁女一事中表现更多的是欲擒故纵的委婉策略。王莽欲将女儿配与平帝,在选后的问题上以退为进。他先下令排除王氏之女,以谦退的姿态换来吏民“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2]4052的呼声。尔后,再以谦虚之言来推辞,引出陈崇、张竦的赞美之词。又经过王宇之死事件对反对者的无情镇压,天下所闻尽是对王莽的欢呼颂扬之声,王莽嫁女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王莽之女成为皇后后,皇室与王氏家族重新缔结的外戚关系,在制度和情感上确保了王氏家族权力的合理性。同时,这次对家族的调整使得王莽成了皇帝的岳父,为其代汉提供了便利。
最后,提拔忠于自己的家族成员,拉拢家族内的亲己势力。在清除叔父残余势力、打压家族同辈势力、安排子女命运的同时,王莽也没有忘记提拔忠于自己的家族成员。在王氏家族中,最为王莽所重也最忠诚于王莽的成员当数王舜和王邑,即所谓的“王舜、王邑为腹心”[2]4045。王舜为王音之子,是王莽的堂弟,为王太后所信爱,与王莽私交甚好。哀帝无子而亡,“莽白以舜为车骑将军,使迎中山王奉成帝陵”[2]4044,因此王舜有拥立之功。元始元年(1年),群臣以益州塞外蛮夷献白雉为契机要求加封王莽。王莽不敢一人贪功,因此上书加封与其共谋迎立之事的诸多党羽。王舜因拥立之功受到嘉奖,“益封万户,以舜为太保”[2]4047,成为四辅之一。其后王舜在王莽通向帝位的道路上尽心辅佐,并在代汉的诸多重要环节上发挥了作用。元始四年(4年),王舜首先提议进一步封赏王莽,给予王莽“殷之伊尹,周之周公”[2]4066的待遇,由此引发王莽加封宰衡。之后,王舜进一步为王莽造势,要将王莽“化行海内”的功德报告天下。元始五年(5年)十二月汉平帝去世,该月发生了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的事件。王舜看似十分为难地以“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2]4079为理由奏请王莽摄行皇帝事,使王莽成为“代理”皇帝。此时的王莽已逼近代汉的临界点。王莽面对忠诚得力的王舜自然也是投桃报李。居摄元年(6年)三月,王莽立孺子婴为皇太子,“以王舜为太傅左辅”[2]4082,之后又将王舜的两个儿子封侯。在槐里赵明、霍鸿起义时,王莽为保障皇宫安全,让王舜和甄丰在殿中昼夜巡逻,足见王莽对王舜的器重与信任。如果说王舜是以文辅佐王莽,那么另一位心腹王邑则是以武著称。王邑是成都侯王商之子,居摄初期任光禄勋,负责王莽及皇宫的安全卫护工作。居摄二年(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一时间关东大乱,王莽以王邑为虎牙将军与其他七将率兵东征,于同年年底诛杀翟义。居摄三年(8年)正月,“王邑等自关东还,便引兵西”[2]3438,马不停蹄地进攻关中地区的赵明起义军,并于同年二月取得胜利。这一东一西两场战争的胜利为王莽稳定政局、巩固代汉的预备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王邑也因其突出表现在稍后的新室代汉中跻身新朝高位。
在成帝年间的王氏家族结构中,“四父五侯”是当之无愧的家族核心。不过,王太后虽被“四父五侯”左右,但终究还拥有一定的权力,对“四父五侯”的权力还有一定的节制作用。“四父五侯”与王太后处于合作的状态,即使成帝末年王莽上位,其依旧受到王太后的节制。然而王莽二次掌权后,形势却逐渐发生了变化。王莽借助清理叔父势力、安排子女命运和提拔亲己成员的方式重新组合了王室家族的权力结构,使得自己彻底摆脱了叔父辈的蒙荫,在家族中树立了足够的威信,建立了忠于自己的可靠集团。在这个新的家族结构中,太皇太后王政君处于孤悬遥尊的状态。她名义上是家族的领袖,但实际上的领导权早已被架空。真正的核心人物是王莽,他通过诛杀异己与拉拢亲己,权势早已超越了一切家族成员。王舜向太皇太后索要玉玺时说的“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2]4032一语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这句话在这里不仅仅指王莽控制了朝廷,也指王莽控制了王氏家族,他已经成为实际的家族长。至此,整个王氏家族已经成为王莽的囊中之物,这也为新室代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王氏成员与新室的兴衰
在做足了准备工作后,王莽成功代汉立新,建立了新朝。王氏家族成员在新朝转变为皇室宗亲,参与了新朝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的王氏家族有几点现象值得注意,它们展现了王氏家族在新朝复杂曲折的生存轨迹。
首先,王氏成员加官封爵,构建起新朝统治的基础。王莽设立四辅、三公、四将制度,其中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王邑为大司空,封隆新公。二人皆是王莽重臣,在代汉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此番占据要职,也在情理之中。他又策命群司,以“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2]4101,“司空典致图物,考度以绳,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众殖鸟兽,蕃茂草木”[2]4102。可见,太师之职与天文历法有关,司空之职则与建设生产有关。颜师古引晋灼注说“春秋分立表以正东西,东,日之始也,故考景以晷属焉”[2]4102,说明太师负责春、秋日影观测。众所周知,春、秋二季为农忙时节,此举与农事有紧密关系。司空的职责范围还拓展到保护和开发自然环境,也与农业有莫大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农业生产是国家的基础命脉,王莽将两个与农业有关的职位交于二人,进一步巩固了二人在朝廷及家族内的地位。其他王氏成员在新朝也有被授予要职者,如王邑之弟王奇担任“五威左关将,函谷批难,掌威于左”[2]4117,王邑之兄王况担任虎贲将军领兵征伐匈奴,王舜次子王匡担任太师将军等。此外,王氏没有官职的成员也一并被封赏。王莽统一“封王氏齐缞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男以‘睦’、女以‘隆’为号焉,皆授印韨,令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韨”[2]4104。由此形成了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王氏宗室阶层,构建起新朝基本的权力格局。
其次,在太皇太后和皇室子女的问题上,王莽有着比较复杂的情感。太皇太后自王莽索要玉玺时就对王莽不满,王莽代汉后尊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但这并没有换来王太后的欢喜。尔后不久,王莽又在孝元庙的问题上惹恼了太皇太后,使得太皇太后对其更加不满。太皇太后不遵王莽更著黄貂、改汉正朔的规定,仍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食”[2]4035,以此对王莽表示抗议。王莽面对这样的太皇太后讨好不得,强硬不得,也是无可奈何。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王莽对太皇太后的情感相当复杂。一方面,太皇太后是自己的长辈,也是家族名义上的领袖;另一方面,抗议的举动使太后成为王莽的“政敌”。面对这个无奈的局面,在亲情与政治的斗争中,王莽只得选择等待,等待太皇太后去世。王莽长女原为汉平帝皇后,王莽代汉后更号定安公太后。但王女对父亲的行为深怀不满,“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2]4011,刻意与父亲保持距离。王莽对此有所察觉,自知亏欠女儿,于是“敬惮伤哀,欲嫁之,乃更号为黄皇室主”[2]4011,并令孙建的儿子前去相亲,结果惹得王女大怒,王莽无可奈何,只得打消嫁女的念头。从王莽的态度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王莽对女儿的情感也相当复杂。作为父亲,王莽一方面爱自己的女儿,但另一方面却亲手葬送了女婿的王朝,使自己的女儿处于不仁不义的境地,这成为王氏父女至死也不能弥补的情感隔阂。新朝建立时,王莽的嫡子只剩下王安、王临。王安因病少见于史书,王临则在代汉之初被立为太子。但地皇元年(20年)七月,王莽又因迷信符命将王临改为统义阳王,使太子之位空出。尔后,王临在地黄二年(21年)正月因原碧通奸案而自杀,随后王安病死,王莽至此已无嫡子。王莽听从王安遗言,对庶子王兴、王匡进行加封,但并没有再立太子,也未有立储之说。直到地皇四年(23年)新军兵败昆阳后,王莽为安抚战败的王邑才有“我年老毋嫡子,欲传邑以天下”[2]4186一言。王莽严厉地对待嫡子,但当嫡子全部去世后,王莽又陷入了痛苦与无奈之中。一方面是没有继承人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出于莫名的原因不愿立嫡孙、庶子为储,这样的矛盾显示出王莽在皇子问题上有着复杂的情感与心理。
最后,王氏成员在新朝末路时期的背叛与忠诚。新朝自天凤年间陷入动荡,到地皇末期已是狼烟四起。新军于昆阳战败后,起义军逐步向关中挺进,都城危在旦夕。这时,新朝统治内部却发生了刘歆谋反事件,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王涉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王涉因道士西门君惠的建议而寻求刘歆一同反莽,但刘歆最初并未有所回应。后王涉反复劝说,刘歆终于同意,二人遂与大司马董忠结为同谋。在这个过程中,王涉的两个理由打动了刘歆:一是王涉认为“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2]4184。王涉为王莽从兄,时年已值古稀,为反莽竟说出如此“秘密”,可见其对王莽毫无感情。赵国华据此认为,“从这次谋反事件来看,王涉无疑是最初发起者”[4]。此语的毒辣之处在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王莽与王氏家族的关系,继而动摇了新朝的合法性,这增加了刘歆谋反的底气。二是王涉认为董忠“主中军精兵,涉领宫卫,伊休侯主殿中”[2]4184,大家掌控内外,如果行动则很可能会成功,这增加了刘歆谋反的信心。然而刘、王、董三人最终因策略问题导致谋反失败,王涉自杀。王氏家族本是王莽统治的基础,出自家族内部的叛乱对王莽震动极大。加之动乱的局势,王莽陷入了“忧满不能食”[2]4186的狼狈境地。与王涉相反,以王邑为代表的另一部分王氏成员则决定用生命保卫王莽,与之同命运。地皇四年(23年)十月戊申朔,起义军攻入都城,王邑等人“分将兵距击北阙下”[2]4190,与起义军展开殊死搏斗。三日庚戌,宫城战斗失利,起义军已突入宫中,王莽移驾渐台,试图凭借池水阻挡起义军。此时的王邑及士兵经过3个昼夜不间断的战斗,已经疲惫至极,王邑之子王睦想趁机逃跑,但被王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2]4191。最终王邑父子和一干忠于王莽的臣子全部死于渐台,王莽身死国灭。在新朝最后的时刻,王邑等人展现出了惊人的忠诚。这不仅是对王莽的忠诚,也是对王氏家族最后的忠诚。
新朝灭亡后,更始帝刘玄“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2]4193。于是,王氏家族的余脉得以保存,然而元城王氏的辉煌终成历史。纵观整个历程,新室代汉诚然是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王氏家族的自身崛起和内部调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氏“四父五侯”通过干预皇室、清除异己使王氏控制了政权,实现了由外戚向权臣的转型。经历了哀帝时代的中衰后,王氏重新崛起,此时的王莽成为家族的核心人物。他以家族中衰和二度崛起为契机,排除叔父势力,提拔亲己成员,重新组织了家族的权力结构,使自己彻底摆脱了叔父蒙荫,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极高的威信,树立了自己在王氏家族内的领导地位。此时的王莽不仅控制了朝廷,更控制了王氏家族,这为实现代汉迈出了关键一步。新朝建立后,王室成员成为国家的统治阶层,他们经历了国家和家族的一系列风波,其间混杂着阴谋、杀戮、无奈以及忠诚等诸多复杂因素,这些都对王朝的兴亡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一部王氏家族史就是一部新室代汉史。以往学界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出现了对王莽“翻案成风”“无限拔高”[5]的做法。事实上,我们理应回归基本材料,从对细节的梳理中更为真切地认知王莽及整个王氏家族。
① 近代以来,国内外关于王氏外戚和王莽的研究颇多。杨倩如在《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综述及理论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这些研究多侧重皇权、官制、后宫、谶纬、改制、军事、民族、人格、儒生政治等方面,尤其热衷于争论是否应为王莽代汉正名。但在王氏家族与新室代汉关系的问题上,学界大多只是笼统地归纳为外戚专权。就王氏家族的历史而言,在一些有关王莽的传记中有所提及,如孟祥才的《王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葛承雍的《王莽新传》(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元的《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但这些研究多聚焦于王莽,对王氏家族其他成员的涉猎有限,对王氏家族内部变化的观察也有所欠缺。
[1] 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 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J].史学月刊,2016(5):13–20.
[5] 杨倩如.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综述及理论思考[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1):5–13.
K234
A
1006–5261(2021)01–0129–06
2020-06-19
张楠(1993―),男,天津人,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