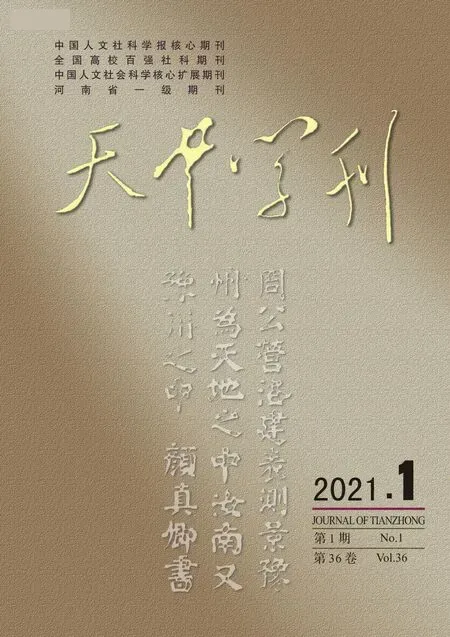紫砂陶艺的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李健
紫砂陶艺的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李健
(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近代以来,紫砂陶艺开始进入一个由多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促成的转型期。对于紫砂陶艺现代转型的认识,首先需要立足于相对宏观的历史语境,理解其作为手工技术、造型艺术和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属性;其次需要立足于紫砂陶艺的近现代发展史,对其清末革新、民国初建、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转型,进行必要的梳理和说明;最后则需要立足于当代文化实践,对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遇与挑战给予揭示和展望。
紫砂陶艺;现代转型;文化遗产
自鸦片战争以降,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图谋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思路逐层递进,最终深入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与之相辅相成,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深刻的现代转型阶段。所谓现代转型,参照卡林内斯库对现代性的讨论,可以被理解为“成为现代”[1]的观念变迁与社会实践过程。就现代中国而言,它集中体现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理论与现实”等一系列张力关系所构成的图新求变意识和实践上。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紫砂陶艺发展的阶段,都以整个时代的发展状况为依据,开始从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中前期的繁盛阶段,进入一个由多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促成的转型期。宽泛地看,紫砂陶艺的转型过程,自晚清初现端倪,经清末革新、民国初建、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转捩点,一直没有停止过。时至今日,伴随着社会文化形态以及人们日常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紫砂陶艺更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尤其需要予以重点关注。
一、紫砂陶艺的社会文化属性
众所周知,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尽管其后清政权又苦苦支撑了数十载,但中国社会以此为起点,开始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时期。此后出现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皆因之而起。西方文明强势入侵反衬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在器物、制度乃至文化层面的全面落后。紫砂陶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手工艺,既涉及器物层面的制作工艺、制度层面的组织形式等诸多因素,更关乎文化层面的审美积淀和观念革新等一系列问题。要想深入理解其在近现代进入转型期的前因后果,有必要对其社会文化属性作简要梳理。
首先是手工技术属性。紫砂陶艺属于陶瓷生产中的一个特定类属,尽管明中叶之后才真正兴起,但仍然需要我们通过中国古代手工业系统的整体结构来认识和理解。确切地说,紫砂陶艺在本质上首先应归属于这一系统中因特定社会需求而产生的手工技术及生产部门。中国手工制业自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等制作技术开始出现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前行的步伐,逐步形成了分工细致、规模庞大的手工业系统。尽管这一系统长期依附于农耕文明,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却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必不可少的重要社会构件之一。陶器作为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日用器具,很早便有独立的生产部门,制作技术和经营形态更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改进和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规范及制作工艺的《考工记》就描述了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抟埴等六大类30个手工业工种,其中“抟埴”即指制陶手工业[3]。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更详尽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具体形态,陶瓷同样属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
具体到紫砂陶艺,它得以兴起的动因,既缘起于社会性的日常生活需要,也得益于制陶技术的经验积累和不断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紫砂陶艺的陶瓷史地位是与其工艺制作方式和水平直接相关的。历史地看,完整成熟的工艺体系的最终形成,是紫砂陶艺进入繁盛期的重要标志。其中,明万历年间以时大彬为代表的一批制陶大师,对紫砂陶艺的制作工艺进行了至关重要的技术革新和定型,使得它具有了区别于其他陶瓷制品工艺的独创性。可以说,离开手工技术属性层面的独创性,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紫砂陶艺的兴盛和历史发展轨迹的。因此,无论紫砂陶艺现代转型蕴含多么复杂的社会文化面向,都必须回溯至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的一般规律中予以探讨。
其次是造型艺术属性。这意味着紫砂陶艺不仅是一种手工技术,还是一种可以进入艺术史书写视野的艺术类别。以艺术类别观之,紫砂陶艺与诸多其他类型的陶瓷工艺一样,属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艺术史视野之下,它无疑又可以归入造型艺术这一常见美术类别当中。纵观中国古代美术史,除了绘画、雕塑之外,工艺美术同样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典时期尚未严格区分纯艺术与实用艺术,即便是绘画和雕塑也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一种工匠性的活动。比如雕塑这种在中国古代明显缺乏独立地位的造型艺术种类,长时间是作为一种手工技艺被看待的。至于陶瓷、玉器、青铜器这类具有实用性的工艺美术,更是无法与现实功用脱离干系。但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又都是构成造型艺术历史叙事逻辑的重要内容。再比如李霖灿的《中国美术史讲座》一书专章讨论了画像石、雕塑、玉器、青铜器、陶瓷等艺术。在“陶瓷王国·华夏之光”一章中,他曾指出:“古代的中国人先发展了陶器,又由陶器发展出了瓷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特色,所以我们称之为陶瓷王国,华夏之光。”[4]69陶瓷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代表性,由此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透过陶瓷工艺,中国古人借助造型艺术所反映出的审美情趣和品位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审美需求,都得到了必要的说明。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由“有意味的形式”议题入手,对原始社会的陶器纹饰进行了观念史意义上的美学分析[5],深刻揭示了陶器所蕴含的丰富审美意味及其背后的社会观念。因此,对紫砂陶艺现代转型的考察,需要我们将其置于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历史逻辑中,从美学的角度予以必要的剖析。
最后是文化遗产属性。在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下,紫砂陶艺又可以被看作中国古代社会留存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所谓文化遗产,在宽泛意义上可以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有留存至今的“历史流传物”涵盖在内。在存在形态上,它又可以分为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紫砂陶艺一方面自明代中叶以来为后世积淀了大量具有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的实物器具;另一方面则作为仍具有文化活力的手工艺技能,成为世代相承的非物质性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可以说,无论作为手工业系统中的某种技术能力,还是美术史中的特定艺术形态,紫砂陶艺都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在紫砂陶艺那里所反映出来的工艺精神、审美追求和文化底蕴,不仅闪耀着历史的光晕,也令其足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遗产,在当今时代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保护。尤其是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文化语境下,对紫砂陶艺的传承和保护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并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无疑也是当代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强,包括紫砂陶艺在内的很多传统手工艺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作为仍具有时代活力的文化遗产,紫砂陶艺的当代传承和建设意义重大,但同时又面临着各种现实困境。所有这些问题都理应围绕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得到充分的考量。紫砂陶艺在现时代所呈现的转型特征,与此息息相关,后文仍将就此做进一步说明和阐释。
二、近现代转型期的紫砂陶艺
具体到紫砂陶艺的近现代发展历程,晚清的紫砂陶艺仍保有较为庞大的行业规模,也涌现出一批工艺精湛的制陶名家,但在总体上它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阶段。立足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语境,此一阶段紫砂陶艺所经历的一系列变迁,不是可以用手工制业的衰落来简单概括的。正如紫砂陶艺的兴盛与制陶工艺、茶饮文化、文人参与等多重因素息息相关,其晚清以来的诸多变化同样是时代变迁综合效应的必然结果。
首先,这种转型表现在经营模式、行业形态的变化方面。清末以降,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各种张力关系交织,紫砂陶艺亦不能独善其身。其中一个较为直观的变化,便是带有商品经济特征的新兴手工业工场的出现和发展。随着制陶手工业工场的发展,不仅其内部的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而且营销模式和路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去开设陶瓷商店。”[6]138
毫无疑问,这种变化与西方现代经营理念的引入密切相关。事实上,在紫砂陶艺发展历程中,中西文化的交互视野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有确切的资料显示,在17世纪60年代,英国贵族开始使用宜兴的紫砂壶。在17世纪末,越来越多贵族家庭的记账簿上出现茶叶和紫砂壶”[7]。更重要的一个历史现象,则是“几乎所有欧洲的重要博物馆陶瓷收藏中都有宜兴紫砂,有时并不因为是其器物本身的精美典雅,而是因为其在启迪欧洲瓷器发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8]。的确,西方近代的炻器制作史,并不缺乏紫砂陶器的“影响因子”。当然仅以中西交汇来说,晚清以降无疑是更需要重点考察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伴随着由清末至民国的一系列器物、制度以及文化层面的改革乃至革命,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既离不开对传统的批判性继承还面临着民族危亡的现实困境,同时也是在西方文化这一挥之不去的参照系中体现出来的。而紫砂陶艺的转型期正是以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状况为基本背景的。
民国时期,紫砂陶艺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在总体上,民国初期的紫砂陶艺在前人的基础上仍有较为显著的发展,不仅分工更为细密和专业化,而且工艺也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比如,利用现代工业化工技术丰富泥色,开发挂釉、吹釉、印花等紫砂器加彩技法,为适应商业需求对紫砂器进行金刚砂抛光处理等。另外,造型及品类方面亦新品迭出。这一阶段,紫砂陶器仍广受青睐,不仅国内市场颇具规模,还远销海外。更重要的是,与这一时期实业救国思想相互印证,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经营紫砂陶器的私营公司应运而生,并成立了同业公会。其中声誉较盛、经营形成规模的有葛德和陶器公司、利用(利永)陶业公司、吴德盛陶器行、陈鼎和陶器厂等。同时,还出现了像江苏省立陶器工厂这样带有国营色彩的制陶企业。这些陶业公司大多都有一套较为完整成熟的运营机制,不仅聘请名家制坯、陶刻,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往往还在上海、杭州、青岛等外埠开设店面。比如,成立于1860年的葛德和陶器公司很早就在上海开设了陶器店,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聘有陶工达300余人,形成了产、供、销完整的营销链。立足于社会转型语境,紫砂陶艺也有了更多走出国门展示自己的途径和机会。其中最为常见的方式便是参加各种形式的国际博览会。紫砂陶艺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工艺,在这些博览会上屡获大奖,也令紫砂之名愈发享誉世界。至20世纪30年代中叶,紫砂陶业依托新兴的现代经营模式以及仍旧庞大的社会需求,达到了鼎盛期。
其次,民国时期在紫砂陶艺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亦有明显区别于过去的变化。一方面,新兴的陶业公司为培养紫砂陶器制作人才,开始尝试不同于单一师徒传承方式的陶艺培训班。比如利用(利永)陶业公司1921年曾开办过“陶工传习所”,由程寿珍、范大生、俞国良等当时的制陶名家任教,并培养出冯桂林这样位列“民国五大家”的制陶高手。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教育系统的逐步完善,与陶瓷有关的学校教育也开始陆续出现。从最早创办于1905年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开始,陶瓷及相关专业的职业学校教育便一直没有间断过。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江苏省宜兴初级陶瓷职业学校,便是一种明显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紫砂陶艺人才培养学校。
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子承父业、师徒相授的紫砂陶艺传承方式仍较为普遍。所有这些都为民国时期紫砂陶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储备。就制陶艺人来说,这一时期亦不乏名家,“民国五大家”即为其中的佼佼者。其中,程寿珍师承养父——清末紫砂名家邵友廷,尤擅长掇球、仿鼓、汉扁三种紫砂壶式的制作,特别是掇球壶最负盛名,他曾以此参加国际博览会并获大奖。范大生师从清末紫砂名家范鼎甫,所制紫砂器颇具审美意趣,名重一时,曾受聘于利用(利永)陶业公司、吴德盛陶器行等多家陶器公司。冯桂林作为这一时期紫砂艺人的杰出代表,非常具有创新意识,作品往往构思精巧,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紫砂陶艺奇才。另外,裴石民、王寅春亦多有才情,技艺精湛。他们与任淦庭、朱可心等制陶名家以及这一时期尚显稚嫩的顾景舟、蒋蓉等人一起,成为新中国紫砂陶艺得以继续传承、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紫砂陶艺的当代转型特征
民国紫砂陶业发展至抗日战争爆发阶段,开始进入一个急剧衰退时期,并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仅以从业者的数量来看,“曾经有过六、七百人的紫砂从业队伍,到1949年解放前夕只剩下三十余人”[6]142,凋敝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状况随着政权更迭得到了彻底的改观。20世纪50年代,紫砂陶业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逐渐恢复了生机,并形成了新的组织形式——紫砂工艺合作社,其后又发展成为紫砂工艺厂。紫砂工艺厂既承担着紫砂陶器的生产及设计工作,也负责紫砂工艺水平和技术的提升,同时还是重要的培养紫砂制作人才的组织机构。即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紫砂陶器的生产也没有中断。尽管此时的紫砂器绝大多数仅有“中国宜兴”钤印,但却往往因为材质优良、制作精到而颇受认可。仅就制作工艺和水准而言,紫砂陶艺并未由于时局动荡而停滞不前。这也为其以改革开放为起点重新走向正轨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此为背景,紫砂陶艺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转型阶段。其转型特征主要体现在泛商品化和博物馆化两个方面。
首先,就泛商品化而言,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紫砂陶艺的生产销售状况与此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观。以港台地区为主的外来资本介入所引发的紫砂收藏与投资热潮,更是在客观上推动了紫砂陶艺的商业化进程。紫砂陶器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具有投资潜力的商品,紫砂市场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挖掘。特别是紫砂陶艺史上的名家制品,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不仅如此,当代紫砂制陶名家的作品同样备受青睐,30余年间价格一路攀升。顾景舟、蒋蓉、吕尧臣、汪寅仙、徐汉棠等一大批当代紫砂制陶名家,在继承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锐意进取,创作出大量工艺水准精湛的紫砂陶器,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肯定。紫砂陶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商品,收藏与投资价值由此可以得到充分的显现。这种收藏与投资价值,无疑成为推动紫砂陶业不断发展的重要社会动因。但在对名家茗壶的追捧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动因需要考量,即紫砂陶器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现实功用。众所周知,进入当代社会,那些促使紫砂陶艺在明清两代走向繁盛的诸多因素都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紫砂陶器的现实功用较之繁盛期已大大降低,当它主要被作为一种可供收藏的投资性商品看待时,其商品属性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是紫砂陶艺所面临的客观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民间工艺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最能够反映这种困境的,无疑是这些民间工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我们需要刻意保护的文化遗产。
其次,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紫砂陶艺在当代社会还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商品化的特性,即博物馆化的倾向。所谓博物馆化,反映了紫砂陶艺与日常生活的“剥离感”,它更多需要借助某种历史叙事方式来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事实上,紫砂陶器成为一种投资性商品本身便是最好的说明。由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大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保有原先的茶饮习惯,知识阶层也缺乏借由紫砂器具来传达某种文化品位或审美意趣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在日常生活层面,紫砂陶艺如果不能被有效地加以保护,其社会现实需求在客观上会变得越来越有限。正是出于对各种具有显著文化价值的口头或无形遗产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制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于2006年生效。紫砂陶艺不仅符合这一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而且其“非物质性”的文化价值蕴含在整个紫砂陶艺史及其制作工艺过程中。就此而言,紫砂器具本身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核心的部分。正如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点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9]。
时至今日,紫砂陶艺越来越被视作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为人们所关注。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通过,“宜兴紫砂陶艺制作技艺”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一种,正式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紫砂陶艺进入转型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它反映的是随着时代状况的变迁,紫砂陶艺的传承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紫砂制陶技艺进行保护,无疑是有益和积极的,但如此优秀的工艺传统成为‘文化遗产’,只停留在保护阶段是远远不够的。手工艺的困境并不完全是自身导致的,也并非手工的生产模式不合理、不科学,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环境中人文意识逐渐淡薄,真正需要加强的,并不仅仅是‘保护’,而是提高整体的思想认识水平。我们需要完整、系统地对其深入研究,进而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11]很显然,这样一种超越技艺层面并进入文化语境的传承与保护策略,在操作层面存在太多需要审慎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李霖灿在谈及中国陶瓷艺术时,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只要从史前的简陋陶器想起,一路上沿着彩陶、黑陶、白陶、带釉陶器,然后青瓷、白瓷、釉下彩、青花、珐琅彩的顺序欣赏下来,不由自主的就会使人惊喜不止,一方面我们感谢古人的无限创造之力,一杯一盘,如今我们所日常使用的,都当思其来之不易;另一方面继往开来,我们系出名门之后裔,如何对陶瓷艺术再去发扬光大创新又新,那就是我们后来者的责任了。”[4]81紫砂陶艺同样应当作如是观。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紫砂无疑仍具非凡的魅力和活力,并保持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它在新的时代状况下又面临着各种现实困境。紫砂陶艺无论商业化还是博物馆化倾向,都既有其积极意义,又不乏负面效应。一言以蔽之,紫砂陶艺的传承与发展,实可谓任重而道远。
[1]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37.
[2]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G]//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149.
[3] 戴吾三.考工记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4] 李霖灿.中国美术史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 李泽厚.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50.
[6] 蒋赞初,杨振亚,贺盘发,等.宜兴紫砂的历史及现状[M]//史俊棠,盛畔松.紫砂春秋.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
[7] 熊微,黄巍锋.明清输欧宜兴紫砂壶的文化情境及造物特征研究[J].创意与设计,2015(4):90–96.
[8] 黄健亮.宜兴紫砂器在欧洲的文化历程[J].东南文化,2016(3):87–92.
[9]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7.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EB/OL].(2006-06-20)[2020-04-10].http://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
[11] 杨子帆.紫砂的意蕴:宜兴紫砂工艺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4:8–9.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Boccaro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 Jia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Boccaro art has entered a transition period caused by multipl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we should understand its features as cultural heritage and handicraft in the macro historical context, its social change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expect th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modern times.
boccaro; modern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heritage
TS938
A
1006–5261(2021)01–0144–06
2020-04-1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ZX117)
李健(1972―),男,安徽舒城人,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