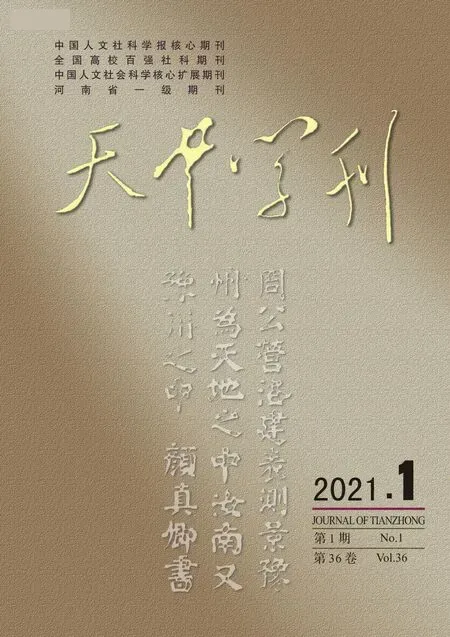奇气、理趣、巧思——《竹山词》新论
路成文
奇气、理趣、巧思——《竹山词》新论
路成文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蒋捷《竹山词》转益多师,其词基于宋元易代特定时势和蒋捷自身之精神气质、禀性学养等,从而形成一定的特色和风格。其中一部分作品秉承稼轩风调,慷慨激昂,富于豪宕之气;很多作品融历史、社会、人生经验与思考,从而富于理趣;大多数作品在立意构思、谋篇布局、运笔铸词等方面,颇异常轨。奇气、理趣和巧思,堪称《竹山词》异于同时代词人的重要特征。
蒋捷;《竹山词》;奇气;理趣;巧思
蒋捷为南宋遗民词人之翘楚,在词史上与周密、张炎、王沂孙并称“宋末四大家”[1]1。蒋捷所撰《竹山词》,取径颇广,博采众长,转益多师,风格多样,有“长短句长城”之誉[2]3695。南宋后期词坛或宗尚姜、吴,形成极重格律、声韵、字面、句法,追求典雅清美词风的一派,或推重稼轩,形成以词为陶写之具,逞才使气,议论纵横,慷慨悲壮乃至粗豪叫嚣的一派。前者以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后者以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为代表。相较于以上词人,蒋捷词的风格跨度要大得多,一部分作品秉承稼轩风调,慷慨激昂,富于豪宕之气;一部分作品师法周、吴,颇具典丽沉厚之风。蒋捷词之所以能在当时词坛风气下卓然特立,自树一帜,不仅与其开放的词学观念、宽广的师法取径有关,更与其自身禀性学养,以及特定时代的时势风会有关。基于上述因素所形成的“奇气”“理趣”和“巧思”,是《竹山词》异于并世词人的鲜明特征。
一、《竹山词》之“奇气”
所谓“奇气”或豪宕奇崛之气,是蒋捷人格精神在其词作中的自然流露。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3]王国维对于词的体性特征的经典概括,多少带有“本色”论的意味,不能囊括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诗化之词、豪放之词。苏、辛词的重要特征,是“以诗为词”,以词为“陶写之具”,甚至“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苏、辛之所以能示人以诗化之词、豪放之词,其根柢在各有其“气”,或清刚超旷,或豪迈奔放,故胡寅《题酒边词》云:“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4]169刘克庄云:“公(稼轩)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4]200皆就其人其词之“气”而言。苏、辛以其惊人的创造力,向以“婉约为宗”的词领域注入超迈强劲之“气”,从而使词得以与言志之诗与议论风发之文相提并论。
刘永济《词论》尝云:“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5]苏、辛其人其词之“气”,正关“风会”,不待详论。蒋捷生活的时代,南宋国势倾危,进而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生活于其中的杰特之士,不能不具悲痛欲绝、刻骨铭心的经历与感触,发而为词,固当异乎寻常。
不过,同属宋元易代时期的词人,与并世词人周密、张炎、王沂孙等相比,蒋捷对于时代风会的反应,却迥然有别。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词学宗尚姜、吴。他们在创作上讲求音律字句的驯雅、格调的清空骚雅。宋亡前,他们陶然于临安的烟柳画桥,在词中罕有表达大厦将倾的时势危机;宋亡后,他们大多沉湎于亡国的哀思,无力亦无意作坚定的抗争,虽偶有凭吊故宫、暗伤亡国之词,但格调低沉,辞气啴缓,词情凄婉,有以泪洗面之哀,无振衰起懦之力。甚至向来与蒋捷并称的刘辰翁,也多“辞情”“悲苦”之词,而罕有辞气豪迈之作。这种情意表达总体趋于凄婉悲苦的风尚,虽然笼罩宋元易代时期的词坛,但也有少数例外,如文天祥、邓剡、王弈、陈著等,多有借词以一吐胸中磊块之作,辞气豪迈,令人感奋。尤其是蒋捷,在时代风会的激荡下,创作了一大批辞气激越豪宕、词情沉郁奇崛的优秀词作。试看二例:
结算平生,风流债负,请一笔句。盖攻性之兵,花围锦阵;毒身之鸩,笑齿歌喉。岂识吾儒,道中乐地,绝胜珠帘十里楼。迷因底,叹晴干不去,待雨淋头。 休休。著甚来由。硬铁汉从来气食牛。但只有千篇,好诗好曲,都无半点,闲闷闲愁。自古娇波,溺人多矣,试问还能溺我不。高抬眼,看牵丝傀儡,谁弄谁收。(《沁园春·次强云卿韵》)[1]27
甚矣君狂矣。想胸中、些儿磊块,酒浇不去。据我看来何所似,一似韩家五鬼,又一似、杨家风子。怪鸟啾啾鸣未了,被天公、捉在樊笼里。这一错,铁难铸。 濯溪雨涨荆溪水。送君归、斩蛟桥外,水光清处。世上恨无百尺楼,装着许多俊气。做弄得、栖栖如此。临别赠言朋友事,有殷勤、六字君听取。节饮食,慎言语。(《贺新郎·甚矣君狂矣》)[1]269
这两首词皆以抒摅情志为主,词情激切郁愤,与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词之啴缓哀吟者迥不相侔。前一首是次韵之作,强云卿其人已不可考,据蒋捷所次之韵,可大致推断此人与蒋捷同属宋亡后遁迹不仕的“宋季高节”。此词因大段阐理而被认为“词旨鄙俚”,读来“令人绝倒”,然词人之性情和词人心中奇崛郁勃之气,皆充溢于词中,尤其词的下片“硬铁汉从来气食牛”等句,有气冲牛斗之势,在气势上完全压倒词人所蔑视的“牵丝傀儡”(溺于欲、为名利所拘牵者)。后一首是赠行词,“乡士以狂得罪”,被拘遭遣,作品先在开篇拈出一个“狂”字,然后连用三喻来塑造这位疏狂放诞、不合时宜的狂士形象。下片写送别,因行经斩蛟桥而念及晋代宜兴狂士周处之斩蛟除害,实有以周处为譬的意味;“世上恨无百尺楼,装着许多俊气。做弄得、栖栖如此”,是作者有感于狂士遭遇而直抒胸中愤懑,表达对抑扼贤士世道的强烈抨击。通读全词不难发现,蒋捷显然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在为乡贤狂士大鸣不平的同时,抒发满腔郁愤不平之气。
此二首外,《水龙吟·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亦称杰构:
醉兮琼瀣浮觞些。招兮遣巫阳些。君毋去此,飓风将起,天微黄些。野马尘埃,污君楚楚,白霓裳些。驾空兮云浪,茫洋东下,流君往,他方些。 月满兮西厢些。叫云兮、笛凄凉些。归来为我,重倚蛟背,寒鳞苍些。俯视春红,浩然一笑,吐山香些。翠禽兮弄晓,招君未至,我心伤些。[1]72
此词近承稼轩《水龙吟·用些语再赋瓢泉》之体式和风格,远祖屈原《离骚》之骚怨精神。全词为落梅招魂(咏落梅),词情沉郁哀断,词境缥缈峻极。一方面,词人感叹梅花之贞姿素质以及落梅之随风随水而逝;另一方面,又想象并期望梅花之魂能重返枝头,先春怒放,傲雪凌霜。通读全词,我们可鲜明感受到词人心头有一股郁勃不平之气,既惋叹梅花之落,更彰扬梅花之贞。
他的另一首词《尾犯·寒夜》描写自己客夜不眠苦况。开首两句“夜倚读书床,敲碎唾壶”,用东晋王敦咏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6]的典故,表达此时内心郁勃愤懑之情;“人共语、温温芋火,雁孤飞、萧萧桧雪”两句,写与友人扺掌论世的激越孤愤情绪;下片前四句,以不能如祖逖刘琨般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为憾,以如杜甫般凄苦漂泊为恨,将豪杰之气、郁勃之愤扼抑在万般无奈之中。结尾两句“浩然心在,我逢着梅花便说”,与前一首《水龙吟·用些语再赋瓢泉》形成呼应,作者向梅花表明心志,以梅花之贞姿素质相砥砺。两首词中分别出现“浩然一笑”与“浩然心在”,可以见出蒋捷对孟子“浩然之气”精神传统的确认与继承。
以上作品除《贺新郎·甚矣君狂矣》可能作于宋亡之前,大都作于宋元易代以后。正是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使我们认识到蒋捷不同于其他并世词人的个性特征。盖同代之周密、张炎、王沂孙等,宋亡前流连于吴越一带的湖山胜境,陶然于风雅词人的文酒诗会,以词相高,以词为乐,较少留意于南宋江山之大厦将倾,对潜藏的危机视而不见;宋亡之后,虽时时沉浸于亡国破家的深悲巨恸,但以风流才士之怯弱,不敢作丝毫抗争,而依然沉浸于调丝弄管、审音度律、字雕句琢的风雅词人生活,个别人还于出处大节有亏,在元初严峻形势下左摇右摆,不能立定脚跟。
蒋捷则不然。虽然蒋捷曾多次追忆“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表明其在宋亡前也曾有过歌酒风流的才子生涯,但他并非仅仅陶然于此,当“乡士以狂得罪”之时,他义愤填膺地写下那首《贺新郎》相赠,表达对触犯时忌者的同情与勉励,以及对万马齐喑、志士遭抑的愤懑。宋亡之后,蒋捷的家乡直接受到元蒙铁蹄摧残践踏,其本人则在烽火连天的战乱中“影厮伴、东奔西走”,过了相当长时间“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漂泊生涯。等到元蒙政权完全取代南宋,战火渐息之后,蒋捷回到故乡,卜居太湖之滨的竹山,“大德间参政燕公某政礼请见,不赴。宪使臧公梦解、陆公垕交章荐辟,亦辞不就”[1]347,与同样隐居太湖之滨的二三友人以诗酒自娱,以节义相砥砺。“余遭丧乱,摈处湖滨,既与公同壤,公之孙祖儒者,好文墨,工于词,时相过从,共抱黍离之悲。”[1]347守节不移,义不仕元,被《松筠录》推举为“宋季高节”①。与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相比,蒋捷选择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乱世之中,在易代之际,立定了脚跟,保持了志节。
蒋捷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显然与其所禀受的学养根柢有关。蒋捷“出宜兴巨族”,先祖中多有以正身立朝者,“平生著述,一以义理为主”,“学者以其家竹山,称为竹山先生”[1]348。从前人的研究和评价,不难看出,蒋捷主要是以“学者”而非“词人”立身处世的。蒋捷自己也在词中屡称“岂识吾儒,道中乐地,绝胜珠帘十里楼”,其以“儒者”自视的主体意识是相当明确而坚决的。从前引诸词中“鼓双楫,浩歌去”“俯视春红,浩然一笑,吐山香些”“浩然心在,我逢着梅花便说”等句,不难看出蒋捷对孟子“浩然之气”说深所服膺。除此之外,蒋捷对稼轩词的心摹手追,亦处处显示出他与并世词人所不同的精神气度。前面所引述的这些词,大多充溢着或强烈激越喷薄宣泄,或喑呜低沉抑扼难平的豪宕奇崛、深沉郁勃之气。这种奇崛郁勃之气是蒋捷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也是使其词超越同辈的重要特质。
二、《竹山词》之“理趣”
《竹山词》之理趣,乃是作者学养根柢与特定时势相结合在其词中的表达。
词本言情,但在宋代崇儒尚学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特立之士作词并不排斥“理趣”。比如晏殊、欧阳修偶尔在小词中流露对人生、世事的理性思索,苏轼、辛弃疾更“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在一些词作中表达深沉的哲思理路,诠述立身处世的根本和道理。比较典型的词如: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欧阳修《玉楼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苏轼《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稼轩《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鹧鸪天》“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野荠花”。至稼轩《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则通篇说理矣。这些词作或通篇阐理,或以一二俊语蕴理,或写景言情而理在其中,成为《全宋词》中比较耐人玩味的优秀篇章。蒋捷《竹山词》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从而使其词与并世词人相较多了几分“理趣”。
《竹山词》中以理见胜者着实不少,前节所引《沁园春·次强云卿韵》以及《念奴娇·寿薛稼堂》《解连环·岳园牡丹》《梅花引·荆溪阻雪》《虞美人·听雨》等5篇,或通篇阐说道理,或借咏物以反思历史,或写景抒情而理寓其中,颇具代表性。
稼翁居士,有几多抱负,几多声价。玉立绣衣霄汉表,曾览八州风化。进退行藏,此时正要,一著高天下。黄埃扑面,不成也控羸马。 人道云出无心,才离山后,岂是无心者。自古达官酣富贵,往往遭人描画。只有青门,种瓜闲客,千载传佳话。稼翁一笑,吾今亦爱吾稼。(《念奴娇·寿薛稼堂》)[1]126
妒花风恶,吹青阴涨却,乱红池阁。驻媚景、别有仙葩,遍琼甃小台,翠油疏箔。旧日天香,记曾绕、玉奴弦索。自长安路远,腻紫肥黄,但谱东洛。 天津霁虹似昨。听鹃声度月,春又寥寞。散艳魄、飞入江南,转湖渺山茫,梦境难托。万叠花愁,正困倚、勾栏斜角。待携尊、醉歌醉舞,劝花自乐。(《解连环·岳园牡丹》)[1]47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吹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梅花引·荆溪阻雪》)[1]154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虞美人·听雨》)[1]224
《念奴娇·寿薛稼堂》是一首祝寿之词。与一般寿词偏重于祝福颂谀不同,这首寿词通篇出之以规讽劝谏,不啻一篇劝隐辞。薛稼堂生平无考,考稽蒋捷生平,结合此词风调,大致可以推断薛稼堂是蒋捷隐居太湖之滨竹山时期所相过从的二三友人之一。词的前五句是对薛稼堂称赏之辞,据此可知薛稼堂襟抱甚高,名声甚著,见识甚广,应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乡贤高士。“进退行藏”三句,暗示薛稼堂此时正面临某种重大人生选择。宋元易代之后,元蒙政府出于政府治理的需要,多次征召和诱赏前朝士人出仕为官,蒋捷同年进士臧梦解在元军南下之际,即从其乡郡宋将内附仕元,大德中,臧梦解尝与陆垕向朝廷交章举荐蒋捷,但蒋捷“辞不就”②。从这几句词来看,薛稼堂也许正在面临这样的选择,何去何处,是仕是隐,或许颇有些矛盾和焦虑。“黄埃扑面,不成也控羸马”,以反诘语气试探薛稼堂究竟欲作何选择。对于蒋捷的试探,薛稼堂大约借陶渊明的进退出处作了回应,如何回应不得而知,但据词的下片可猜其约略,即先出山看看再说,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蒋捷紧逼一步,替薛稼堂分析利弊,“人道云出无心,才离山后,岂是无心者”,是说即使主观上不想出仕为官,但只要迈出了第一步,便淄染红尘,失却节操。“自古达官酣富贵,往往遭人描画。只有青门,种瓜闲客,千载传佳话”,用一正一反两种选择、两种结局进一步劝谏薛稼堂。结二句“稼翁一笑,吾今亦爱吾稼”,显示薛氏接受蒋捷劝谕,坚定了隐居不仕的决心。
《解连环·岳园牡丹》咏岳家园之牡丹。据杨景龙考证,宋亡后蒋捷隐居太湖竹山,所与游者之岳君举、岳君选,为岳飞后裔[1]7。此岳园当即常州岳氏花园。此词题咏牡丹,实则借牡丹以反思由唐而宋数百年历史兴亡:“旧日天香,记曾绕、玉奴弦索”,记盛唐唐玄宗、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之事;“自长安路远,腻紫肥黄,但谱东洛”,记北宋洛阳牡丹之盛;“天津霁虹似昨。听鹃声度月,春又寥寞”,记北宋之衰亡,京洛(中原)之沦陷;“散艳魄、飞入江南,转湖渺山茫,梦境难托”,记宋室之南渡以及南宋之覆亡。南宋牡丹诗词颇多,蒋捷这首词堪称借牡丹以反思历史兴亡的最经典之作,体现蒋捷思致之深。
《梅花引·荆溪阻雪》从字面上看是纪行之作,但细绎词旨,却俨然词人心路历程的一次形象抒写。词的开篇借白鸥之口发问:“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舟行遇雪,阻滞水滨,本属寻常之事,然如许琐事,能激发词人内心波澜,似非偶然。这几句从字面上看,似乎是白鸥与作者的一番晤谈,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则这首词倒不失轻松、欢快与幽默。然而根据词的下片“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可知词人心境绝非轻松、欢快、幽默,或一般意义上的阻雪而不得已,而是别有一番愁情。这是一番什么愁情呢?词中有交代:“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几句以递进的笔法一气呵成:引起愁情者,不过是旅次寂寞冷清而思旧游,此第一层;“旧游旧游今在否?”是针对“忆旧游”而发起追问,此第二层;“花外楼,柳下舟”,回答“旧游”之所在,是第三层;“旧游”今日尚可得见否?是由“花外楼,柳下舟”所引发的进一层的潜藏在字面下的追问,此第四层;“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对前所隐藏的一番追问做出了极其决绝的否定回答:昔日之“花外楼,柳下舟”,如今连做梦都不可得见,则今昔时间、空间距离之辽远可知,此是第五层;如果我们再结合蒋捷特殊身世遭际,则里面更潜藏着一层深层的痛楚,那便是南宋江山的覆灭,使曾经拥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连在梦里也无可追寻。短短几句词,包含六个层次的层深结构,显示出词人思致之深切、愁情之浓烈。回到本文所讨论的话题,这首词借现实生活中的“阻雪”,联类而及今与昔、此与彼的时空阻隔,故严迪昌先生认为此词抒写的是一种“无法逾越难以寻觅的阻隔感”[7],确实是中肯之论。但这种“无法逾越难以寻觅的阻隔感”不仅包含前所言及的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阻隔,更包含词人主体身与心的“阻隔感”。这是一个亘古常新的富于哲理思索意味的话题。“身”的不得已,与“心”的不可能,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矛盾,在白鸥的发问中集中爆发,又以“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做出没有答案的回答。面对这种窘境,除了痛心疾首地抒泄愁情之外,也确实是无可如何了。这首词虽然只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作者内心的思索、矛盾与煎熬却鲜明可感,从而使整首词具有了哲理思索的意味。
《虞美人·听雨》是蒋捷最脍炙人口的名篇,该词以蒙太奇的艺术手法,通过三个相似而不全同的场景叠加,以极浓缩的笔法概括人一生的遭遇和经历。这种表现手法本身是极富哲理意味的,它在三个片段的变与不变中,反思人生的价值,追问存在的意义,进而获得对人生真谛的感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正是对这种反思、追问的精确而凄美的回答。《沁园春·次强云卿韵》基于特定的时势和交流语境,阐述“道”与“欲”的问题,进而以气冲牛斗的语势,表明立场和观点,言论看似迂阔,实则极具针对性,是同道之人的相互砥砺,既富于理趣,又饱含激情,令人激赏。
除以上作品外,《竹山词》中多有以一、二俊语传达哲思和理趣的词句,如《大圣乐·陶成之生日》之“富贵云浮、荣华风过,淡处还他滋味多”[1]43,《高阳台·闰元宵》之“人情终似娥儿舞,到嚬翻宿粉,怎比初描”[1]117,《满江红·秋本无愁》之“万误曾因疏处起,一闲且向贫中觅”[1]147,《探芳信·菊》之“酒休赊,醒眼看花正好”[1]151,《一剪梅·舟过吴江》之“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1]185,《小重山》之“劝花休苦恨天天,从来道,薄命是朱颜”[1]211,《步蟾宫·中秋》之“天公元不负中秋,我自把、中秋误了”[1]253,《步蟾宫·木犀》之“人间富贵总腥膻,且和露、攀花三嗅”[1]233,《玉楼春·桃花湾马迹》之“桃花湾内岂无花,吕政马来拦不住”[1]239,《浪淘沙·重九》之“前事渺茫中,烟水孤鸿”[1]247,《贺新郎·乡士以狂得罪,赋此饯行》之“临别赠言朋友事,有殷勤、六字君听取。节饮食,慎言语”[1]270,《少年游·枫林红透晚烟青》之“春风未了秋风到,老去万缘轻”[1]334等。这些词句频频表达对历史、现实或人生的感悟、感慨、反思与追问,有的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有的抚今追昔,感慨无限,有的则寓理趣于情景,令人思索回味。
蒋捷以“儒者”自视,“平生著述,一以义理为主”,这使得他与并世之风雅词人“道”不相同,故在宋元易代之世,蒋捷选择了一条甚为艰辛的人生道路,并在此艰苦卓绝的历程中,不断观照现实,反思历史,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断以“儒者”的姿态和理论来砥砺志节和操守。正因如此,蒋捷在搦管为词之时,便不是单纯地把某一时期人生所遭际的苦难和深悲巨恸以一往情深的笔法和啴缓悲怨的语调婉转传达出来,而是把历史、现实和人生作为一个对象来观照、思索和追问。《竹山词》之所以富于理趣,其本质和根柢即在于此。
三、《竹山词》之“巧思”
所谓“巧思”,乃是作者求新求奇、转益多师的词学追求和宗尚在词中的具体体现。《竹山词》风格多元,豪放者上跻苏、辛门墙,婉约者平视周、姜、吴、王,集两种反差甚大的风格于一身,并行不悖,甚而至于泾渭分明,亦词史上一奇观也。前人基于不同词学宗尚,对《竹山词》的评论,出入辛、姜,褒贬失据,毁誉逾常,也堪称词学批评史上一大奇观。郑海涛《试论前人对竹山词的毁誉及其原因》对此已有评述[8],此不赘言。
尽管前人对《竹山词》毁誉不一,但似乎都注意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竹山词》的立意、构思或运笔,颇异常轨,沈雄云:“蒋捷……其词章之刻入纤艳,非游戏余力为之者,乃有时故作狡狯耳。”[9]周济云“竹山薄有才情,未窥雅操”[10],又云“竹山有俗骨,然思力沉透处,可以起懦”[11]。刘熙载云:“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炼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2]3695谢章铤云:“蒋竹山《声声慢·秋声》、《虞美人·听雨》,历数诸景,挥洒而出,比之稼轩《贺新郎·绿树听鹈》《贺新凉》‘绿树听啼鴂’阕,尽集许多恨事,同一机杼,而用笔尤为崭新。”[12]张德瀛云:“神不全,轧之以思,竹山是已。”[13]唐圭璋云:“竹山小词,极富风趣,诗中之杨诚斋也。”[14]以上评论中,所谓“狡狯”“才情”“思力”“机杼”“用笔”“理法气度”“风趣”等,讨论的正是蒋捷词的立意、构思或运笔问题。这些评论虽然或褒或贬,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蒋捷词立意、构思或运笔颇与众不同。
蒋捷存词90余首,尽管风格差异极大,但在立意、运思和用笔方面却多所留意,别具匠心,不落窠臼,因而创获颇多。
第一,竹山寿词,罕作门面语,而多有深意在焉。
自唐五代以来,词本花间尊前之薄伎,具娱宾遣兴之效,故颂圣祝寿之词,所在多有。作为一种目的明确的应酬性文字,极易流于门面套语。有鉴于此,沈义父《乐府指迷》“寿词须打破旧曲规模”条云:“寿词最难作,切宜戒寿酒、寿香、老人星、千春百岁之类。须打破旧曲规模,只形容当人事业才能,隐然有祝颂之意方好。”[15]蒋捷寿词甚多,虽偶亦有“寿仙”“婺星”等寿词习语,但主体内容和作品意旨往往高远、典型,远非一般应酬敷衍者可比。比如《大圣乐·陶成之生日》,上片铺写寿筵之排场甚大,是应景文字;但主人公陶成之的出场则非同寻常,“主翁楼上披鹤氅,展一笑、微微红透涡”,有仙风道骨,超然尘俗之致。下片用陶姓远祖故事以致祝颂之意,是惯常思路,陶侃、陶潜分别代表两种不同人生境界:“千年鼻祖事业,记曾趁雷声飞快梭”,是陶侃趁时而起的“事业”;“但也曾三径,抚松采菊,随分吟哦”,是渊明辞官归隐、潇洒田园的境界。虽均属陶氏,而竹山却明显属意于后者,“富贵云浮,荣华风过,淡处还他滋味多”,是对富贵荣华的一笔扫空和对陶潜境界的确认,“休辞饮,有碧荷贮酒,深似金荷”,切回现场,对寿翁表示劝勉和期待。
立意近似的寿词还有《珍珠帘·寿岳君选》《沁园春·寿岳君举》《念奴娇·寿薛稼堂》等。其中《珍珠帘·寿岳君选》“突出寿主不贪声色之乐,酷嗜读书的性格特点”,“充分地表现了寿主岳君选‘芸边事切,花中情浅’的性格本质”,“字里行间透着书卷的清气,给人以雅美的享受和品位的提升”[1]107–109。《沁园春·寿岳君举》,由寿主岳君举与唐代中兴名相裴度的“前后同年”但“逸劳异趣”,“突出一个‘逸’字”,赞赏和艳羡岳君举隐居南塘“做散仙人”的境界。《念奴娇·寿薛稼堂》如前所析,不仅标举高隐之致,更寓劝诫薛稼堂守节不移之意。
蒋捷另有四首同寿“东轩”的词,写法与前四首稍异,即较少直接描写或咏赞寿主品行、性格和特点,较多着意于时序、景物、居处环境以及东轩生日“神仙之会”时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瑞鹤仙·寿东轩立冬前一日》从“立冬前一日”这一时间点着眼,通篇围绕这一特定时序娓娓下笔,闲淡而家常,在寿词中别具一格。《糖多令·寿东轩》虽仍提及其生日在“重九后,小春前”,但写法上则变为对东轩所居进行精彩的描写:“秋碧泻晴湾。楼台云影闲。记仙家、元在蓬山。飞到雁峰尘更少,三万顷,玉无边。”这里波光云影,楼台掩映,更远处雁峰出尘、琉璃万顷,宛如仙境。主人的仙风道骨和出尘之致,借此流露。《摸鱼子·寿东轩》和《玉漏迟·寿东轩》两首,重点呈现自己是否与会的感受和心理:前一首写自己曾数度参与庆祝东轩生日的“神仙之会”,但这一年却因客居外地而无法与会,只能寄意于梦中;后一首写自己曾经因客游异地而无法参与庆祝东轩生日的“神仙之会”,但今年却因恰好归来而得与此会。一正一反,别具匠心。这组寿词,笔势上以闲淡为主,不似前几首激切,但透过这些描写,我们能感受到主人陶醉于远离尘俗、恍如神仙境界的高隐生活环境和状态的惬意,感受到蒋捷与东轩相得相契的深厚情谊。二三友人隐处湖山守节不移的相同志趣,不言而意在其中。从这个层面来看,蒋捷的寿词不仅在构思、运笔方面自出机杼,别具匠心,而且在立意方面也有一以贯之的深意,那就是有通过寿词与一群高隐湖山、义不仕元的“宋季高节”们相互砥砺之意。
第二,竹山咏物,刻意雕琢;构思、运笔,出人意表。
宋词咏物之盛,莫盛于南宋;南宋咏物之盛,莫盛于宋元易代时期。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周密、张炎、王沂孙等南宋遗民词人拈题分韵、唱和创作《乐府补题》五题37首。蒋捷作为同时代词人,大约与“补题”诸人少相过从,故不与其事。从咏物词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乐府补题》诸人尤其是王沂孙的词作,无疑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必须指出,他们的咏物词仍然着力于音律、字面、用典等方面,尽管许多作品不乏寄托,甚至有的还刻意于寄托,但在构思、运笔方面,则显得比较拘束。
蒋捷则不然。他的咏物词比较好地继承了“体物写志”的咏物传统,比较注重构思、运笔、达意,因而往往能做到立意高远,大开大阖,出人意表。先看其咏物奇作《声声慢·秋声》:
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锁更声。故人远,问谁摇玉佩,檐底铃声。 彩角声吹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笳声。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知他诉愁到晓,碎哝哝、多少蛩声。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1]135
此词体式奇特,通篇以“声”字为韵,是一首“福唐独木桥体”词。不仅如此,此词以“秋声”为赋咏对象,虽然受到欧阳修《秋声赋》的影响,但构思奇特,组织精密,立意深远,较《秋声赋》犹有过之,王沂孙等人同题词作远非其俦。欧阳修《秋声赋》先写夜读闻声:“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16]体物堪称精妙,但全文主旨乃在借“秋声”以发议论、抒感慨。王沂孙《扫花游·秋声》从构思角度来看,受欧公影响更多,与《秋声赋》相比词意显豁,创意无多。蒋捷则不同,他几乎调动了最敏感的听觉细胞,将特定时势节候下的“秋声”统统纳入感受范围:黄花红叶飘坠之声、秋夜雨声、风声、丽谯门更声、檐底铃声、鼓角声、战马声、胡笳声、捣衣的砧声、碎哝哝的蛩声、凄厉的大雁声,一齐涌向词人的耳鼓。仅从字面上看,这首《声声慢·秋声》已超越《秋声赋》和王沂孙《扫花游·秋声》。更令人称奇的是,蒋捷字面上似乎并不打算抒写夜闻“秋声”的感慨,只是一层层、一项项地罗列各种各样的“秋声”,但透过字面,却不难感受到隐藏其中的词人心声。首先,词人的敏锐听觉源于因某种焦虑感所导致的彻夜难眠。各种悠远的、细微的、寻常的、不寻常的“秋声”,是一般人极易忽略掉的,但却被词人敏锐感受到了,这本身是不寻常的。其次,细绎各种“秋声”,不难感受到其中所蕴蓄的宋元易代之际风雨如晦、战火纷飞、形势严峻的时势和氛围,以及战乱时代抒情主人公孤身漂泊的孤苦伶仃和敏感焦虑。也就是说,这首词在看似冷静客观的铺陈描写中,向读者展示了整体时代氛围和个体不幸命运,从而把“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妙谛演绎到了极致。
蒋捷真是用心思写词的人,他的另外15首咏物词依然能证明这一点。如他的两首《木兰花慢·冰》,同调同题,一般人能完成一篇已属难能,蒋捷却通过变换抒情主人公(一首以闺中女性的视角写,一首以秉笔之士的视角写)巧妙地演绎出两首情致迥异的佳作。他的《昼锦堂·荷花》,借鉴曹植《洛神赋》的笔法来写,《高阳台·芙蓉》通过演绎苏轼《芙蓉城》中的神仙之事来写,《燕归梁·风莲》借鉴《霓裳羽衣曲》及《长恨歌》的若干笔法来写,《水龙吟·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用《招魂》的思致来写,《翠羽吟·绀露浓》通过檃栝赵师雄遇罗浮梅神事来写,都取得了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③。同时,这些咏物词又或隐或显地有着共同的主题,即易代之际词人对个体命运和时势变迁的深沉感慨。这使得其咏物词在立意、构思和运笔的层面,超越了同时代其他词人。
第三,竹山节序词,多用赋体,运笔朴拙,发语沉痛。
节序词是宋词中比较习见的题材,蒋捷同时代的张炎《词源》有专论:
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耳……(周邦彦《解语花·赋元夕》、史达祖《东风第一枝·赋立春》、《喜迁莺·赋元夕》)如此等妙词颇多,不独措辞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至如李易安〔永遇乐〕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17]
张炎的这些意见,如附之歌喉的节序词“类是率俗”、多为“应时纳祜之声”等,大体符合事实,他所激赏的周邦彦、史达祖诸词,“不独措辞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足见其颇具眼光。但对于易安《永遇乐》,张炎虽未予恶评,但似乎不甚以为然。同时,他认为花前月下、良辰美景之际,唱俚俗的节序之词,如“击缶韶外”,不够雅驯。基于这样的主张,张炎及其同好如周密、王沂孙等,皆不甚喜作节序词。同时代的刘辰翁虽然喜作节序词,但似乎正堕张炎所批评“类是率俗”的境地,唯《永遇乐·璧月初晴》《兰陵王·丙子送春》等几首,抒发国破家亡背景下一己之悲苦情愫,与易安《永遇乐》同调。
与张炎等人相比,蒋捷并不排斥节序词,其所存90余首词作中,节序词即有16首。与刘辰翁等人相比,蒋捷的节序词取径明显不同,他并不过分把个体命运遭际作为节序词抒写的主题,反而更接近张炎所主张的“不独措辞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只不过因生当宋元易代,所谓“节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已不复存,故蒋捷节序词反过来着眼于“节序风物”之衰与“人家宴乐”之异了。试看下面两首元夕词:
蕙花香也。雪晴池馆如画。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而今灯漫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蛾儿争耍。 江城人悄初更打。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剔残红灺。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吴笺银粉砑。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笑绿鬟邻女,倚窗犹唱,夕阳西下。(《女冠子·元夕》)[1]32
翠幰夜游车。不到山边与水涯。随分纸灯三四盏,邻家,便做元宵好景夸。 谁解倚梅花。思想灯毬坠绛纱。旧说梦华犹未了,堪嗟。才百余年又梦华。(《南乡子·塘门元宵》)[1]230
这两首元宵词从题序及词中若干字面,可知都作于南宋灭亡之后。两首词共同的关注点,就是元宵节晚上的花灯。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的记载,无论是北宋都城汴京,还是南宋都城临安,都极重元宵节,是夜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繁华无比。可惜如许繁华与热闹,终被元蒙铁蹄踏碎,“而今灯漫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随分纸灯三四盏,邻家,便做元宵好景夸”,如今的元宵佳节,竟是如此的凄清与冷落!作者并不刻意于一己悲苦情绪之抒发,而是通过元宵灯夕今昔之铺陈对比,沉痛地怅叹和追问两宋败亡的冷酷历史事实,从而表达出深沉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
他的另两首中秋、重九词,主题虽不及前面两首元夕词重大,但也体现出类似的特点:
去年云掩冰轮皎。喜今岁、微阴俱扫。乾坤一片玉琉璃,怎算得、清光多少。 无歌无酒痴顽老。对愁影、翻嫌分晓。天公元不负中秋,我自把、中秋误了。(《步蟾宫·中秋》)[1]252
明露浴疏桐。秋满帘栊。掩琴无语意忡忡。掐破东窗窥皓月,早上芙蓉。 前事渺茫中。烟水孤鸿。一尊重九又成空。不解吹愁吹帽落,恨杀西风。(《浪淘沙·重九》)[1]247
这两首词都作于行旅漂泊途中,上片重在铺陈描写节物风光,下片重在抒发客中漂泊情怀。值得注意的是,两词都擅长以乐景衬哀情。《步蟾宫·中秋》上片描写今岁中秋无云遮月的空明澄澈之景,着一“喜”字,似乎作者被无边无际的“清光”所感染而心情大好,但下片以“无歌无酒痴顽老”一转,词情顿趋沉重,“天公元不负中秋,我自把、中秋误了”,以重笔写情,蕴含无限痛悔与怅惘。《浪淘沙·重九》上片描写重九秋光,色泽明丽,尤其“早上芙蓉”四字,颇带几许亮色,但下片以“前事渺茫中”一转,将对重九嘉会的期待一笔扫空,总体特点正是运笔朴拙,而发语沉痛。
其他如《女冠子·竞渡》,用近乎史传的笔法,借鉴《离骚》《九歌》的字面来铺写屈原行吟泽畔及自沉汨罗事;《解佩令·春》《最高楼·催春》用近乎一唱三叹的民歌语调铺写春事之来去,笔法朴拙,词风却甚轻灵。透过这些迥异常调的节序词,我们不难看出蒋捷在立意、构思、运笔方面的独特个性。
第四,竹山感怀、纪行诸作,大都情动于中,一往情深而思致精巧细密。
《竹山词》中,数量最多最富有感染力的是那些易代之后的纪行、感怀之作。这些作品皆情动于中,因情生文,在构思、运笔、遣词造句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前文所引《梅花引·荆溪阻雪》《虞美人·听雨》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梅花引·荆溪阻雪》开篇通过白鸥与抒情主人公的对话逗引出本词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旨:抒发一种“无法逾越难以寻觅的阻隔感”,而不是黏滞于题面来铺陈描写阻碍舟行之雪;《虞美人·听雨》并不着墨于“听雨”本身,而是以近乎蒙太奇的手法,将人生三个不同阶段“听雨”的片段和场景组接在一起,通过强烈的对比,突显出“悲欢离合总无情”这一沉重的主题。这两首词在构思、运笔方面的巧妙思致,是显而易见的。
再看以下几首词。
渺渺啼鸦了。亘鱼天、寒生峭屿,五湖秋晓。竹几一灯人做梦,嘶马谁行古道。起搔首、窥星多少。月有微黄篱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 愁痕倚赖西风扫。被西风、翻催鬓鬒,与秋俱老。旧院隔霜帘不卷,金粉屏边醉倒。计无此、中年怀抱。万里江南吹箫恨,恨参差、白雁横天杪。烟未敛,楚山杳。(《贺新郎·秋晓》)[1]1
这是一首感怀之作,写家国之恨郁积心底的“万里江南吹箫恨”。词的上片通过描写所居之地太湖之滨秋天拂晓的景色,营造出一副凄清黯淡的情感氛围,“竹几一灯人做梦,嘶马谁行古道”,表明抒情主人公心怀隐忧彻夜难眠,特别是“嘶马谁行古道”六字,突出刻画抒情主人公对漂泊生涯的极度敏感。合观上片,已臻情境融汇的妙境。词的下片集中抒情,极吞吐哽咽之致:“愁痕倚赖西风扫。被西风、翻催鬓鬒,与秋俱老”,即景借用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诗意,是一吞吐;“旧院隔霜帘不卷,金粉屏边醉倒。计无此、中年怀抱”,反用谢安“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之意,谓欲效谢安中年以后溺于声色,既不能,亦不可得,亦是一吞吐。通篇感怀,感情细腻敏锐,运笔吞吐哽咽,颇见巧思。
小巧楼台眼界宽。朝卷帘看。暮卷帘看。故乡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 天不教人客梦安。昨夜春寒。今夜春寒。梨花月底两眉攒。敲遍栏干。拍遍栏干。(《一剪梅·宿龙游朱氏楼》)[1]181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剪梅·舟过吴江》)[1]185
与长调之吞吐哽咽相比,蒋捷短章小令多运思精巧,一往情深,一唱三叹,这两首行旅途中所作《一剪梅》堪称典型。第一首作于浙江金华附近,因借宿朱氏小楼,故因楼发兴。词从小楼形势写起,眼界宽者,楼所处之地势甚高也;朝看、暮看,一望一心酸者,思乡之切也;故乡何在?云水迷漫,故乡渺不可见也。客梦难安者,故乡不可归去也;昨寒、今寒,两眉紧攒者,乡愁深且长也;“敲遍栏干”“拍遍栏干”者,愁无可解,痛彻心扉也。第二首作于舟行吴江之时,因舟行所见,有感而作。开篇直揭心绪:“春愁”。何以解愁?唯有酒!一个“待”字,则明言无酒。“江上舟摇”者,行旅之中也;“楼上帘招”者,舟行所见也;秋娘渡、泰娘桥,所经之地也;风飘、雨萧者,天气不甚佳也;着两“又”字,心中甚烦甚恼也。“何日归家洗客袍”者,归心之切与归家之难也;“银字笙调,心字香烧”,家中温馨之至,令人无比期待也;“流光容易把人抛”者,岁月流易,年华渐老,而仍未归家也;“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匆匆春又去也。两首词主题一致,但情怀略异,前一首表达留滞中的急迫感,后一首表达“近乡情更怯”的焦虑感,思致细密,运笔灵活,语势流转,一往情深,一唱三叹。
蒋捷作为宋元易代之际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位词人,秉持“义不仕元”之气节,以词为其精神、情怀抒泄之载体。其词之奇气(或豪宕奇崛之气),是其人格精神在词中的自然流露。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对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与若干友人砥砺志行,形诸于词,使其作品富有理趣和历史反思意识;其词之理趣,乃是其学养根柢与特定时势相结合的特殊表达。其开放的词学观念和转益多师的学词态度,以及刻意求精求奇的思致,使其词富于巧思,常能摆脱常轨,取得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大约因其面目多元,故前人对蒋捷《竹山词》多有误解或偏颇之论。本文从以上三个层面对蒋捷及其词予以重新衡论,或可弥合歧见,达成相对完善的共识。
① 参见沈雄《古今词话》“宋季高节”条,见王弈清、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5页。
② 参见《元史》卷177《列传》第64卷“臧梦解、陆垕传”。
③ 参见拙撰《文学经典的跨界影响与继承创新:以〈竹山词〉为个案》(载《词学》2015年第2期第61―79页)。
[1] 杨景龙.蒋捷词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刘熙载.词概[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王国维.人间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4258.
[4] 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 刘永济.宋词声律探源大纲;词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9.
[6] 余嘉锡,等.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97.
[7] 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325.
[8] 郑海涛.试论前人对竹山词的毁誉及其原因[J].船山学刊,2004(4).
[9] 沈雄.古今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012.
[10]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634.
[11]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644.
[12]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3379.
[13] 张德瀛.词征[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4162.
[14] 唐圭璋.词学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48.
[15] 沈义父.乐府指迷[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282.
[16] 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77.
[17] 张炎.词源[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263.
I207.23
A
1006–5261(2021)01–0111–11
2020-03-3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4BZW053)
路成文(1973―),男,湖北仙桃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