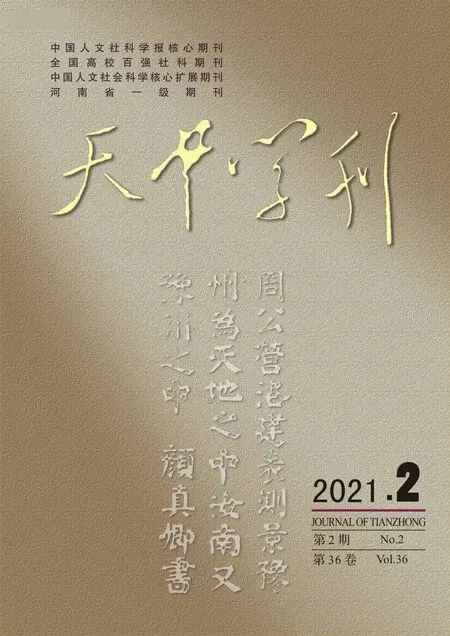日本神道的《易经》视野
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神道(しんとう)是日本的本土宗教,《易经》是中国儒学经典。《易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中国大陆学者把对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阐释的部分叫作《易经》,即狭义的《易经》,把对《易经》部分进行阐释的象、彖、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叫作《易传》,进而把《易经》与《易传》统称为《周易》;而中国的港台地区以及日本的大多数学者把中国大陆学者说的《易经》《易传》都统称为《易经》,即广义的《易经》。本文所探讨日本神道与《易经》关系中的《易经》,使用的是广义的《易经》概念。中国的《易经》对日本神道的影响不可忽视,无论是日本神道的名称,还是神道的内容都借鉴了《易经》,并且日本学者在神道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利用《易经》解读神道,可以说《易经》在日本神道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易经》在日本神道中的渗透
(一)神道的名称来源于《易经》
日本神道的名称来源于《易经》的观点,也被大多数日本儒学家、神道家所认可。被誉为日本精神文化传道师的小阪达也说:“其实‘神道’和《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神道’这个词是从《易经》中引用的。……原本,在日本连‘神道’这个词都没有,人们认为在自然中有‘神灵’寄宿,一边感谢自然的恩惠,一边进行祭祀,而佛教传入的时候,觉得应该给日本自己的这个祭祀取个名字比较好,于是引用了《易经》中的‘神道’这个词。”[1]7
日本神道,是以保护由地缘、血缘等结合起来的共同体(部族、村庄等)为目的而被信仰的。神道以传统的民俗信仰、自然信仰、祖灵信仰为基础,建立人与神之间的相通,人和神连接的具体礼仪是祭祀,进行祭祀的地方是神社。关于神道的产生时间,学界众说不一。也有学者认为神道开始于有史以前的古代,日本人的信仰融合了山、火等自然神以及土著民族的神和外来神共计“八百万神”,这些被称为原始神道(古神道),但最初日本没有神道的概念,也没有“圣典”、确定的教祖和创始人。也就是说,古代日本信仰的原型,原本是对自然和当地神灵的朴素信仰,以求祈祷共同体的安泰,山、树、场所等都是神体。那个时代还没有神社,只是有祭祀时立着神降临的“神篱”,祭祀结束后就把其拆除。之后,日本人又建造叫作“社”的临时小屋,即后来的神社原型。神道原本是古代日本自然产生的自然信仰,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种解释和意义也被结合进来,其原始的模糊定义被覆盖或追加。可以说,神道在现代日本人的心中形成了多重构造,其存在形式大致分为作为民族风俗的神道、添加了思想解释的神道和添加了用于政治统治思想的神道三种。这样的神道没有基督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那样正式规定的“正典”,也没有像其他宗教那样有具体的教义,只是后来人把《古事记》《日本书纪》《古语拾遗》《前代旧事本纪》等古典当作神道的圣经。神道是基于神话、八百万神、自然现象等祖灵崇拜的民族宗教,属于多神教,其祖灵崇拜性很强。在日本的上古和中世时代,神道基本属于泛神论,设有神社,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神学思想和宗教制度。在奈良时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神道与佛教信仰混淆,并作为一种宗教体系被重新构成,即神佛习合。直到明治时代,日本的思想家们为了谋求以天皇为中心的国民统一,把所有的神社都进行了神佛分离,使神道和佛教有了区别:神道信仰强调以保护由地缘、血缘等结合起来的共同体(部族、村庄等)为目的;佛教信仰则以人们的安心立命、灵魂的救济、国家的安抚为目的。与其他宗教相比,神道显示出现世主义的特征。日本远古意义的神道,以祖先神、氏族神、国祖神的崇拜为中心。到了日本近代,神道一度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国家神道),而且神道中的“神”也包含了天皇家族的祖先灵神和镇守地方的诸神。在明治十四年(1881年),神道各派展开了祭神的争论,在明治天皇的裁决下,伊势神道派取得胜利,天照大神获得了最高的神格。明治以后,神社被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形成了以伊势神宫为顶点的国家神道,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政府颁布的《神道指令》,日本的国家神道解体了。
神道的定义众多,学术界也各执一词。一般学者把神道定义为日本固有的民俗宗教,也有学者认为神道即“神圣的尊神之道”[1]1。日本的神道分为诸多流派,主要有皇室神道、民俗神道、神社神道、古神道、国家神道、三轮流神道、云伝神道、橘家神道、山王神道、儒家神道、吉川神道、伊势神道、垂加神道、吉田神道、复古神道等。日本大正至昭和时代前期的神道学者补永茂助曾指出:“现代神道有两个主流:一是神社神道(以神社为中心)——非宗教;一是教派神道(以教会为中心)——宗教。”[1]11日本对神道的理解、解读各异,故而形成了神道的诸多派别。尽管日本神道派别林立各异,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神道的名称出于《易经》。“神道”一词,在日本的文字记载中,最初见于8世纪的《日本书纪》中“用明天皇”纪中的“天皇,信仰佛法,崇尚神道”,但《日本书纪》的写作时间在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之后。5世纪,中国儒学经典《论语》传入日本,而后儒学经典《易经》也传入了日本。日本学者吉野裕子考证说:“日本自古以来神社祭神的起源是作为祖灵的蛇神。6~7世纪,从中国传来的《易》五行的新诸神。”[2]757年,《易经》作为日本古代国子监的教材被推崇。由于《日本书纪》借鉴了《易经》的许多思想,我国以及日本的诸多学者都认为日本神道之名借用了《易经》中的“神道”概念。我国学者吴伟明指出:“日本……‘神道’一词源出《易经》。”[3]73日本学者小阪达也认为:“我学习《易经》,是因为‘神道’和《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神道’这个词是从《易经》引用的……那么,‘神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原本,在日本连‘神道’这个词都没有,认为各种各样的神寄宿在自然中,人们一边感谢自然的恩惠,一边进行祭祀。然而佛教传入的时候,认为日本的这个祭祀最好加上什么名字,中国的《易经》有‘神道’这个词,就被借用了。”[4]神道学者补永茂助认为:“神道之文字,最初见于我国古典《日本书纪 · 用明天皇纪》中‘天皇信佛法、尊神道’,中国‘神道’之词最早见于《易》的十翼,其‘神道’还具有其他意义……关键是要弄明白‘神’指的什么?‘道’所阐释的是什么?”[1]7“神”字也是日本借鉴中国的汉字,日语的发音为“かみ”,指已经去世的人之亡灵或值得崇拜的树木、山川、动物、植物之灵。“日本的信仰,从古代开始就以太阳的运行为基础,把神的来去设想在东西轴上。但是到了白凤期,作为信仰的中国阴阳五行传入日本后,对神的信仰就变成了南北轴。”[5]由此可知,《易经》的“五行”观念,影响了日本对“神”的认识。
由上可以推断,“神道”一词在日本的出现晚于《易经》传入的时间,而且日本神道之名借鉴了《易经》的“神道”。《易经》中的《彖传上 · 观》说:“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山鹿素行对此句进行了阐释:“上古之神道,而乃圣人之道,《易》所谓‘天之神道……圣人以神道设教……’。愚谓:《易》所谓神道者,天地之妙阴阳不测之神道也。圣人观之法天地,以立此教,是于《观卦》所以言观神道也。”[6]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易经》中所讲的神道与日本神道词汇的意义是相同的。江户时代的阳明学家熊泽番山曾说:“理无二。中华圣人之道亦为天地之神道。我国之神皇亦为天地之神道。《易经》亦为天地之神道。”[3]75
(二)《易经》对神道理论基础典籍的渗透
在日本,人们解读神道,都离不开《古事记》《日本书纪》,尤其重视以《日本书纪》为基础阐释日本神道。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是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681年至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采用汉文编年体写成,是日本成书最早的正史。《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都记载了很多神话。虽然日本的神道没有明确指定教典,但是日本历代对神道的阐释,大都以《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经典为理论基础,而《古事记》《日本书纪》都渗透了中国儒学,特别是《易经》的思想。《古事记》上卷开篇就有:“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7]其中的“乾”“坤”“阴”“阳”即汲取了《易经》的相关概念。《日本书纪》也借鉴了《易经》中“阴阳”及“五行”说,比附日本的七代天神(见图1)。

图1 日本七代天神图
总之,日本神道的各种派别对神道的阐释,一般都会采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对神代史的阐述,而这些阐释又渗透了《易经》的思想。
二、儒学者和神道家借助《易经》阐释神道
日本江户时代,神道受佛教和儒学的影响很大。当时,禅僧企图把神道纳入佛教,却遭到日本儒学者和神道家的一致反对。日本儒学者与神道家组成了联盟,极力采用儒学丰富神道的内涵。日本儒学者和神道家都提倡借助《易经》的思想阐释神道,反对佛教。只不过,前者极力用儒学阐释神道,后者则极力把神道纳入儒学体系。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神道家主张神道和儒教一样都是王道。当时日本著名的朱子学派儒学者、近代儒学神道先驱林罗山在参悟朱熹研究《易经》所著《周易本义》《太极图说解》后如获至宝,认为神道、王道、儒道、人道的本质是相同的,“神”以“理”来说明神道。林罗山在日本被誉为近代儒学神道的先驱,他指出:“王道一变至于神道,神道一变至于道。道,吾所谓儒道也,非所谓外道。外道也者,佛道也。”[8]林罗山借助朱熹的理学和易学思想阐释日本的神道,提出了“儒神一致论”。他以朱熹的太极论、理气论为依据,认为万物由“理”和“气”构成,“天”(理气未分的太极)内化为自然的一切事物,“太极”又借助“气”而创造万象,以“理”主持万象,正是“太极”的作用,而且人应接受“天理”,通过学问贯彻宇宙,通过修养消除情欲。林罗山提出作为宇宙原理的“理”,在人际关系中以身份等级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上下定分可使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正当化,从而构成幕藩体制基础的身份秩序绝对化理论。林罗山还认为,“五行”即“阴阳”,“阴阳”即“太极”,“太极”即本源性的“神”,本源性的“神”即“国常立尊”。他在采用朱熹“无形而有理”的“太极”观点说明“国常立尊”时,认为“一而无形、虚而有灵”。我们对其认真分析的话,可以发现林罗山说的“无形”与朱熹说的“无形”的意思是不同的。朱熹“太极”的“无形”是指没有任何“气”要素的“无形”,由“无形”形成了“形”是“理”所当然的表现。林罗山认为的“国常立尊”是“无形”的“混沌”,即“神”。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最初形态的地方有这个“神”,从这个“神”那里生出众神,尽管这个“神”没有“形”,而这个“神”是构造论中世界的根源,是“太极”,即“国常立尊”。由此可见,林罗山把朱熹的“太极”置换成了根源性的“神”,他依据朱熹“太极即理”的理论,借助《易经》的“太极”阐释了神道的“神”。
林罗山的思想总体上以儒教的现世主义、道德主义和合理主义为特征。他否定了当时主流的神国佛国论,提倡日本神国论,即主张“神道即王道”的“神儒合一”王道论。在批判佛教和基督教的同时,他借助《易经》阐释神道的理论,说明世界的“普遍”原理,并引用《易经》的“神明之德”论证“谓以具明道理于人心之中为神道也,故在微妙而成清明”[9]。他在批判佛教站在“彼岸主义”的立场上避免现世人类社会中的问题时,认为佛教的“来世”陈述的是虚妄,追寻“虚妄的彼岸”是无视道德。在否定佛教的再生之说时,他说:“再生之说,浮屠之所言也,非吾儒之所专言也……人物之生也,皆天地阴阳之所感,生者自息,死者自消。比如逝川而不舍昼夜,更无一息之间断也。今天之春,非去年之春,树头之花,非复根之花,《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由是观之,无死而再生之义,虽然聚散迟速,如火之初灭,而烟气仍犹郁乎,故有鬼神之感格,有属灵之来出,有精爽之依托,有魂魄之流行,而其终由大虚,无‘所’不‘之’,何踪迹之遗有哉。况其人死又脱胎乎?”[10]万物是由阴阳之气产生的,死后就消失了。林罗山的这一番论述,正是借鉴了《易经》的“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思想。林罗山还说:“人所以生,精气聚也……夫聚散者,气也。若理,则只泊在气上,初不是凝结自为一物……然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11]由此可知,林罗山借助《易经》,依据朱子学的理论,论证了儒学神道一致性,即“神儒合一”性,从而排斥了用佛教解读日本神道的路径。他强调只有通过《易经》与《日本书纪》,才能深刻地理解神道,阐释日本的神代史。
江户时代的儒学家、神学家山崎暗斋,最初是禅僧,25岁时还俗学习儒学,成为儒者。从佛教转向朱子学和“神儒兼学”,他潜心钻研了朱熹的《周易本义》,热衷于神道的神儒合一说,提倡神儒一致说,并创立了垂加神道。垂加神道是山崎暗斋吸收朱子学、阴阳学、易学,集大成而完成的神道。他把朱熹关于《易经》“太极”“阴阳”“五行”的阐释,当作垂加神道的理论基础,认为神道中的“道”是“阴阳”两个“神”所生的“天照大神”之道,并且附会地解释日本古代的传说。采用朱熹的“理气”“阴阳”“五行”理论,诠释《日本书纪》之神代卷中的神代神话,也就是将《易经》与《日本书纪》中有关的内容结合,阐释日本神道。但是山崎暗斋认为,儒教和神道不是主从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的对等关系。他一方面把《易经》奉为“中国神代之卷”,认为《易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另一方面,他把日本的《日本书纪》尊奉为“日本的易经”,认为《日本书纪》是日本古代最重要的经典。山崎暗斋也与林罗山等人一样,把《易经》和《日本书纪》结合起来去理解、阐释神道。比如,在日本的神话中,伊奘诺尊是接受天神的命令开天辟地的神祇。山崎暗斋认为自日本天地初开,伊奘诺、伊奘冉随天神好卜筮,从“阴阳”而设教化,天地之理也。他采用《易经》的“阴阳”之说,认为伊奘诺是“阳”神,伊奘冉是“阴”神,并赋予“阴阳二神”以“五行”秀气。山崎暗斋还采用《易经》中的“阴阳”“五行”阐释日本神代的七代神祇,他指出:“天神第一代者,天地一气之神,自第二代到六代,是水、火、木、金、土之神,第七代者,则是阴阳之神。”[12]山崎暗斋对《易经》的阐释,与朱熹等哲学家对《易经》的阐释还是有差异的。朱熹是按照“太极—两仪(阴阳)—五行(水、火、木、金、土)”的顺序阐释,而山崎暗斋把五行(水、火、木、金、土)放在了两仪(阴阳)的前面。他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并不是阴阳和五行在太极之后产生的,而是太极在阴阳和五行中的意思。太极是无极的,只是有理而无形。所谓太极,不过是二气五行的道理……也就是说,以理之言,则之不可谓有,以物之言,则之不可谓无。”[13]在这里,他认为“太极”是阴阳五行之理,并不是阴阳五行之外有“太极”,“太极”是阴阳五行的“太极”,阴阳五行没有“太极”就不存在。山崎暗斋认为《易经》的神道与日本的神道都遵守自然规律,两者的目的都是构建人伦以及等级秩序。他借助《易经》论述“儒神一致”论,认为儒教、神道同出一源,但他晚年更倾向神道,并借助《易经》阐释他的神道论。
此外,著名儒学者熊泽番山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儒学家荻生徂徕,也都借助《易经》《日本书纪》阐释神道。他们认为不论是《易经》之道,还是神道之道,都是“圣人设教”的圣人之道,目的是治理国家。
江户时代的日本神道家主张儒学、神道具有一致性。“神道学家也学习《易经》……他们经常用易理去解释神道。虽然他们也强调神道与儒学有不少共通之处,但是跟同时代儒者不同,他们不认同神道是圣人之道之一。”[3]77神道家度会延佳著有《阳复记》,其书的名字就是采用了《易经》中复卦“一阳来复”的含义。“最能体现度会延佳神道论的,是他在庆安四年著的《阳复记》……从专门以佛阐释神道的路径中解脱出来,度会延佳依据《周易》的原理,以神道为主,阐释了《易》说与神道的一致性。”[14]《阳复记》的内容显然是采用《易经》阐释神道,否定神道对佛教的依附,从而排斥佛教,使得神道、佛教习合为中心的中世纪神道改变了方向。度会延佳说:“何故我国上古传来之事多与《易》相合?盖撰神书之人附会《易》也。何故日本神圣之迹与唐圣人立书相合者?天地自然之道于此国彼邦无疑。神道应如是也。”[15]《阳复记》从伊势神道和神儒一致的立场出发,以日本固有的神道、惟神道为经,以阴阳五行、易的思想为纬,用问答体的方式来叙述神道。神学家、吉川神道的创始者吉川惟足认为神道中夹杂着《易经》的阴阳五行说和宋儒的理气说,其开创的神道,也被称为理学神道。
江户时代也有学者排斥儒学与神道的一致论,甚至将《易经》神道化。室鸠巢虽然也是日本主要研究朱子学的著名儒学家,但是他认为《易经》之神道与日本神道意义不同。儒学者太宰春台反对用《易经》解读神道,他认为《易经》的神道,是圣人之道,而日本用《易经》比附历史上不存在的神代史,就把日本神道演绎成了一种巫祝。由此,太宰春台只是推崇儒学,而排斥儒学与神道的一致性。当然,也有日本学者基于对《易经》的漠视而排斥儒学与神道合一论。比如,本居宣长认为日本的神道与中国的《易经》无关,极力排斥儒学,推崇复古神道。和泉真国虽然是本居宣长的弟子,但是他的观点与本居宣长有所不同。和泉真国用《易经》去阐释神道,但试图使《易经》神道化。他认为神道是立于《易经》之外的独立体系,神道才是自然之道,只不过《易经》的某些思想与日本神道恰巧相符。被誉为复古神道领袖的平田笃胤以日本的《日本书纪》为主阐释神道,认为“主宰一切宇宙万物”的唯一主宰神是天御中主神,《易经》的神道没有真实的神道观,只有日本的神道才是“神”之道。并且,他也反对用《易经》的五行观去比附日本的神代史。到了晚年,平田笃胤积极研读《易经》,并且写了两部关于《易经》的著作,即《三易由来记》《太昊古易传》。然而,他并没有用《易经》去阐释日本神道,而是认为《易经》出于日本神祇之手,倾向于将《易经》神道化。
三、日本解读神道的《易经》视野
(一)利用《易经》的“太极”“两仪”“五行”阐释神道的视野
日本学者或者通过《易经》将儒教、神道一致化,以此与佛教对抗;或者将《易经》神道化,试图与中国儒学脱离,从而强调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然而,即使日本排斥儒学的派别,也始终摆脱不了儒学对他们的影响。因为,儒学早已与日本的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他们在反对儒学时往往借助儒学的构思与词语去排斥儒学,所以他们对神道的阐释,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易经》的视野。可以说,《易经》是各个学派论证自己观点的工具。
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大都依据《朱子全书》的太极图阐释神道。其实该太极图是朱熹对《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阐释。中国儒学中的朱子学深受日本幕府的青睐。由于德川家族对朱子学的推崇,朱子学一度成为反映日本官方意识形态的官学。日本儒学者、神道家不仅研究朱熹的《朱子语类》,还研究朱熹的《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太极图解说》等著作。由于朱熹的《太极图解说》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解说,故而他们对《太极图说》也比较重视。他们一方面对朱子学《太极图解说》中的“无极而太极”进行解读;另一方面,用朱熹的“太极”“理”比附神道中至上的“神”。“神道的宗旨是治国之道,而不是祭祀和行法。并且神道,非常重视朱子学中的核心概念‘太极’。‘太极’是天地未分之前的万物元始,是万物生成之根源,总而言之,‘太极’是万物内在的本质,‘太极’与《日本书纪》开篇出现的‘国常立尊’结合在一起开展说明,并且‘太极’是人的内在之心,其‘心’是‘天照大神’的显现,从而论述神与人的合一。”[16]在日本学者那里,他们通常把《易经》的“太极”与《日本书纪》的“国常立尊”联系在一起,阐释神道。还有日本儒学家、神道家将《易经》的五行相生相克比附于日本众神的相生相克,阐释日本的神代史。
(二)利用《易经》的“五行”与儒学“五常”阐释神道的视野
日本学者在利用《易经》与《日本书纪》解读神道时,往往把《易经》的阴阳五行与儒学的“仁、义、礼、智、信”融合在一起阐释神道,并借助《易经》阐释日本的等级制度。小阪达也将《易经》的“五行”与日本“仁、礼、信、义、智”德目序列结合进行了比附,认为儒家的“五常”德目“仁、义、礼、智、信”在日本发生了序列变化,成了“仁、礼、信、义、智”的顺序。《日本书纪》记载:“十二月,戊辰朔壬申,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并十二阶,并以当色缝之……十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始赐冠位于诸臣。各有差。”[17]冠位十二阶是日本远古时代即飞鸟时代圣德太子(574―621年)确立的一种表示官场地位不同等级的冠位制度。冠位十二阶制度始于603年,它将侍奉朝廷的臣下分为12个等级,依照等级的不同,分别授予他们不同颜色的冠。另外,冠位十二阶之所以把“智”放在了“五常”德目的最后,是认为如果有智慧而没有正义只不过是掠夺。
(三)将《易经》的神道与日本神道进行比较的视野
日本历代学者在阐释神道时都会借助《易经》理解《日本书纪》,再由《日本书纪》阐释神道。可以说,无论是日本的儒学家,还是日本神道的派别,在论证《易经》中的神道与日本神道的异同时,或试图将《易经》神道化时,都绕不开将《易经》中的神道与日本神道相比较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