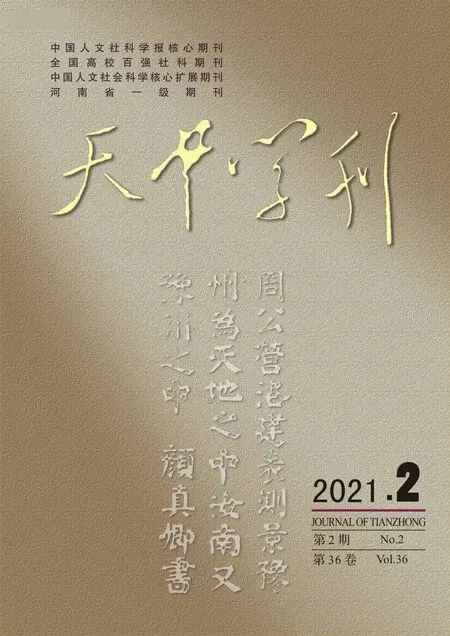关于北宋“庆历新政”的另一种思考
——以欧阳修《朋党论》为中心
陈冬根
(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朋党问题,可以说是漫长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的大问题。至于朋党起于何时,一直以来说法不一,有起于周朝之说,有起于汉朝之说,有起于唐朝之说,等等。宋代欧阳修等人甚至认为朋党在尧舜时代就已有了。不过,学界一般认为,朋党问题始于东汉的党锢之祸。范晔《后汉书》专列了“党锢列传”一卷,写道:“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下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1]据这段文字可知,朋党问题应该起于汉桓帝时,始作俑者是甘陵人周福和同郡人房植及其宾客。在范晔看来,朋党之始,是持不同观点的士大夫群体之间以对立姿态出现的。后来,这种群体间的对立也会表现在政治观点或利益的不同方面。但不管如何,朋党之间只要存在对立,就必然存在所谓的斗争形态。
一、北宋皇帝对朋党问题的态度
朋党问题历代皆有,甚至在某些时候还特别严重,如延续了整个唐代中后期的牛李党争即是典型,其不仅斗争惨烈,而且严重动摇了唐帝国的统治基础。鉴于唐代党争现象的可怕性,宋代统治者一直很重视或者说敏感于朋党问题。不过有意思的是,北宋统治者一方面特别害怕大臣结党成群,影响君权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又有故意在大臣之间制造派别的嫌疑,以使大臣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从而削弱其对抗君权的能量。宋朝皇帝长期摇摆在这种矛盾态度之中,这几乎成了宋朝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北宋朋党问题,特别是庆历以来的朋党之争,都与皇帝这种骑墙态度有关联。反过来,不同党派群体也会利用皇帝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为自己谋利益。这种情态一直延续到南宋,直至宋亡。
二、欧阳修撰写《朋党论》的背景
(一)蓝元震、夏竦等人造“朋党论”
庆历年间的朋党斗争,其核心点在范仲淹提出的改革主张。所谓庆历朋党,不外乎就是两大群体:一是支持范仲淹改革的士大夫群体,如杜衍、富弼、韩琦、欧阳修、余靖、石介、蔡襄、苏舜钦等;二是反对范仲淹变革的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派,如夏竦、贾昌朝、王拱辰、章得象、陈执中、晏殊、胥偃等。此外,两派之间还有一个摇摆的力量,那就是宋仁宗及其身边的宦官群体,我们可以谓之中间力量。朋党之间的斗争手段,不过是一方争取或联合中间力量,以打击或压倒对方。比如,夏竦等人摘取欧阳修等人批评宦官的一些言论,刺激宦官群体加恨于范、欧等人,从而拉拢宦官势力,使之站在自己这边。果然,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内侍蓝元震上疏抨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党造乱,危害社稷。他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有察知?”[2]蓝氏的这封奏疏措辞激烈,帽子也扣得非常大,几乎陷改革派于死地。当然,仁宗还算是英明皇帝,并没有完全听信蓝元震等人的话。但是,两派的这段斗争却在皇帝心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年十一月的“进奏院事件”及其处理结果即是明证①。
(二)范仲淹等人的行为
庆历党争实质是景祐年间政治斗争的延续,“始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3]。庆历四年前后夏竦和蓝元震等人的弹劾,不过是二派之间矛盾斗争的一次激烈显现而已。其实,范仲淹与吕夷简等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景祐年间即已爆发过一次。斗争结果是“大臣不堪,遂以党目之,仲淹于是有鄱阳之行”[4]442。不过,在这次斗争中,范仲淹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在道义上赢得了喝彩,获得了一大批士大夫的力挺。史书记载:“……是行也,李纮、王质载酒往饯,而欲附党以为幸。欧阳修、余靖、尹洙抗疏力争,而愿同贬以为荣。仲淹何慊哉?以至韩琦救蔡襄之诗、程琳议党人之谤、若谷明君子之类,此皆营救仲淹也。惜夷简之党胜。仲淹之党不胜,至使受知荐主方尔从坐,同年进士又相继出,诸贤皆以朋党逐矣。”[4]442可见,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很自然地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也就是所谓的朋党。
斗争延续到庆历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范仲淹在政治上获得了优势,不仅极力将景祐年间支持自己的人提拔或推荐到重要位置,同时对吕党一派如夏竦、贾昌朝等进行排挤、压制。夏竦等人不会坐以待毙,必然奋起反抗,寻找一切机会攻击对方,以期扳倒对方。宋史记载:“至仲淹陕西召还,稍惬公议,日夜谋画,图报主知。然按察之令严,磨勘之法密,未有惬侥幸者之意,小人不悦,再以党论之,仲淹于是复为陕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国,谗者益甚。贾昌朝主王拱辰而逐益柔,益柔,仲淹所荐也。钱明逸希得象而去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陈执中固孙甫而去杜衍,杜衍,尝为仲淹言也。邸狱之起,朋党作仇,一纲之打,私徒相庆。”[4]442-443此事的直接起因,是范仲淹等人以杜衍代替了夏竦的枢密使之职,夏竦由此心生嫉恨,与其党共造舆论,言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妨碍公行,危害国家。这招非常狠,刺激了皇帝内心那层不能与人“分享”的隐秘。于是,范仲淹改革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石介等人所谓庆历君子颂歌
庆历三年以来,范仲淹获得了仁宗皇帝的空前支持,开始着手朝政的全面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一时间全国呈现出百废待兴、百舸争流的欣欣向荣局面。其中,兴学校、改科举、用谏官等改革措施,更是获得了人们特别是士大夫群体的欢迎和肯定。一大批科举士子认为这是文人梦寐以求的春天来了,情不自禁为之欢呼呐喊。比如,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中旬,任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的石介赋《庆历圣德颂》,对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等人大加肯定、充分颂扬,视之为正人君子之党,将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夏竦等人视为邪恶一派,予以猛力挞伐。实际上,在石介稍前,蔡襄就曾写诗歌颂欧阳修、余靖、王素等人获除谏官之职,为改革派鼓吹。对此,司马光说:“庆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谏官,君谟以诗贺曰:‘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谟猷裨帝力,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三人以其诗荐于上,寻亦除谏官。”[5]71
石介等人的作品从表面上看是在称颂仁宗英明,能够亲贤人,远佞臣,实则是为范仲淹一党在政权上的胜利欢呼。可见,石介赋诗的行为是轻率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必将刺激另外一方的反抗,并引发皇帝的不快和警觉,对朋党加以戒备。在某种意义上说,石介等人的做法如同党争的助燃剂,大大加剧了北宋仁宗朝以来日益突出的朋党之争。石介的朋友孙复在听闻其诗作后惊呼:“子祸始于此矣!”[6]507。果然,“新政”实施不到一年,即在夏竦、王拱辰等一党的猛烈反攻下迅速落败,范仲淹一党贬谪四方。石介本人更是悲惨,于庆历五年去世后甚至还被诬为诈死,险遭开棺验尸之辱。
三、欧阳修《朋党论》的创作及影响
《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庆历四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欧阳修与石介是同年好友,在政治上也基本属于同一派,至少是同一阵营。令人惊讶的是,欧阳修于庆历四年所作的《朋党论》一文与石介于庆历三年所作的《庆历圣德颂》一诗存在同样的问题,都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庆历党争问题。也就是说,欧氏此文也必然加剧庆历党争的严重情态。二者略有差别的是,石介诗作于范仲淹庆历新政伊始时,是主动唱赞歌;欧阳修的这篇奏论作于新政实施近一年而开始遭遇反对派猛烈攻击之时,是改革一派的被迫反击或一种政治辩解。具体来说,《朋党论》之作,是在蓝元震、夏竦等人试图以“朋党”之罪对范仲淹一党进行毁灭性打击之时的抗辩,是欧阳修对已经生疑的宋仁宗进行的释疑。不妨先抄录欧氏原文,以便后文解析。其文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位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7]
作为一篇政论散文,《朋党论》较为明显地贯穿了欧阳修的文风和政治观点,似乎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故被看作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不过,笔者以为,抛开散文写作艺术,仅从作为奏折的政论文角度剖析,《朋党论》是有问题的。
首先是其立论基础有问题。《朋党论》的主要立论观点是:自古以来,君子有党,小人无党。这颠覆了士大夫群体传统的观点,即承认自古就存在君子、小人之党。尽管欧阳修立论很新,但基础却有问题。因为自古有朋党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从来没有明确的所谓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之分。欧阳修强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理由非常牵强,而其斥责所谓小人之党为伪党,即没有党,此说则更难以站住脚。一般而言,人们比而为朋,聚而成党。只要一群政治人物因某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出于共同政治目的或者某种利益支持或反对某些人、事,从而影响国家政策和决策,就可以说是朋党。利于国家者是朋党,不利于国家者亦是朋党,不存在什么伪党之说。欧氏的这个假设观点,立论基础明显是不稳的。我们据史可知,欧氏此论乃是针对蓝元震的弹劾奏章所发[8],目的是要驳斥对方言论,以释仁宗皇帝心中之疑,所以其情急之下所发之论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其次,欧阳修《朋党论》的逻辑有问题。欧阳修“朋党论”立论理由是君子以道义聚合,为真党;小人以钱财、禄位相邀,有之则成团聚,无之则鸟兽散,是伪党。平心而论,欧阳修这种论述逻辑是有问题的,是缺乏说服力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欧阳修此文等于是间接承认了蓝元震对范、欧等人结党行为的指控,这是致命的漏洞。如前文所论,宋朝皇帝对大臣结党行为是非常忌讳的,不管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对皇帝来说,都是让人无法安枕的危险存在。一旦承认了范、欧一派存在结党现象,也就等于承认了蓝元震等人的指控。那么,无论他再怎么强调范仲淹一党是君子之党,是因道义结合在一起,一切都是为了朝廷的,都没有用了。因为大宋皇帝考虑问题的第一出发点,就是其统治权威的问题。可以说,在这里欧阳修犯了政治大忌。另一方面,欧阳修此文等于给其政治对手提供了一件有力的斗争武器。因为任何党派都会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同时也会指斥对手是结党营私的,是非正义的,是危害国家社会的。反过来说,任何党派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小人之党,是以利益相聚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欧阳修可以说范仲淹一党是大公无私的,是真君子之党,那夏竦、贾昌朝等又何尝不可以说自己是大公无私的,是真君子之党呢?因为当时并没有一条绝对的标准,来界定谁算君子,谁属于小人。君子、小人之辨是一个具有很强主观色彩的概念。客观来讲,北宋景祐至庆历时期的党争,主要还是政见分歧所致,争斗双方开始还是从国家角度出发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对的,是为了国家朝廷。正如《宋史全文》编写者在编写仁宗本纪时所言的那样:“吾而以贤自处,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以夔、契自许,孰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褒,孰肯以邪曲自毁哉?如必过为别白,私自尊尚,则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为君子之祸?”[4]443欧阳修这种辩解几乎没有说服力,夏竦等人完全可以套用这种说法,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欧阳修这种论述逻辑是有漏洞的,因为你无法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君子他方是小人,而对方可以轻松找到你的破绽,抓住你的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种逻辑常识此时被欧阳修所忽略了。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欧阳修《朋党论》的负面影响很大。欧阳修这篇申辩奏折,在当时影响很大,但严格来说,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此文出来后不久,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宣告失败了,范氏一党人物多被贬谪放逐,如石介之辈更是可怜,连死都不得安宁(政敌污蔑其诈死,开棺验尸)。对于这种结果,我们当然不能全部归罪于欧阳修这篇奏论,它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如对手的狡猾以及强势反攻、皇帝的动摇、“新政”执行问题和庆历新党成员自身缺陷等,但我们不能否认,从政治革新所需要的理论辩护角度评论,欧阳修这篇《朋党论》在这次朋党斗争之中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最直接的影响,是加速了“新政”的失败进程。正如有学者曾这样总结道:
邸狱之起,朋党作仇,一纲之打,私徒相庆。虽欧阳公以去国之身怀不自已,抗疏力言,至谓“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未尝不忠于国者,而大势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为夷简党目之所斥,诸贤尚有左袒。及仲淹再为夏竦党论之所贬,诸贤皆为倒戈。盖夏竦用心惨于夷简,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复希执中也。然尝反覆史传,窃谓党祸之作,固小人之罪,而希天子之风,附君子之名,不得尽辞其责。故尝妄为之说曰:“党论之始倡,蔡襄‘贤不肖’之诗激之也。党论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诗激之也。其后诸贤相继斥逐,又欧阳公邪正之论激之也。”何者?负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尔。[4]
显然,在修史者看来,“庆历新政”的迅速失败,与蔡襄、石介等人的无端鼓吹和颂扬有关系,同样也与欧阳修《朋党论》这种立论基础不牢、分析逻辑不严密的抗辩有密切关系。
总而言之,欧阳修《朋党论》一文的出现,不仅没有解除宋仁宗对朝堂革新派大臣结党的忧惧,反而使得皇帝倒向了夏竦等保守派一边,从而加剧了北宋党争的斗争激烈程度,最终使得范仲淹、韩琦等人领导的“庆历新政”很快走向了失败。这种遗憾的结局,让我们后世读者在赞叹欧公的论说文笔畅达、优美的同时,不能不去反思《朋党论》之类的文章作为政论文的社会效用和历史意义。
注释:
① 庆历四年(1044年)秋天,监进奏院苏舜钦命人变卖院部废纸,并用所得银钱,招妓买酒,邀请王洙、王益柔、梅尧臣等12位官员一同宴饮。负责纠察官员的御史王拱辰得知此事,认为苏舜钦等人是公款吃喝,影响恶劣,上章弹劾。结果,苏舜钦与刘巽削职为民,其他参与宴会的王洙、王益柔、章岷、吕溱等十余人被悉数贬官,逐出开封城;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也受到牵连而被迫辞去相职。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此即进奏院事件。可参看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卷第448―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