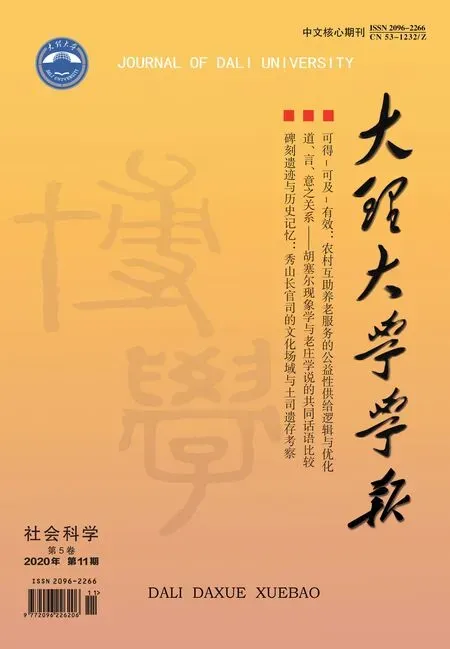道、言、意之关系
——胡塞尔现象学与老庄学说的共同话语比较
佘国秀
(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成都 610106)
中西方诗学“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1〕,在共同诗心或文心的基础上,呈现出源自不同文化的诗学品质。兴起于一战后的西方现象学,试图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给予分崩离析的西方文明以绝对的确定性,从而解决20世纪欧洲社会的文化信仰危机。现象学直观及其对意识的意向性特征的强调,正是为了达成绝对的确定性,使实证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哲学思潮混乱分野的局面,在新的哲学范畴的规划下走向统一。同时,将欧洲文明从深重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中国的老子、庄子均处于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社会激荡期,同样面对利益纷争背后的精神乱象。作为退避乱世而自保的知识分子,他们力图在纷乱的世事中寻找确定性,即“载营魄抱一”〔2〕26与“和之以天倪”〔3〕26。从这个角度看,现象学与老庄学说的学术追求目标是一致的。在视野融合中,笔者着意探讨二者在道(绝对确定性)、言、意关系理解上的融合与差异,以期在中西文论的互证、互识、互见中观照二者的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
一、绝对确定性与道:对最高真理的探求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现象学中追求经世致用的绝对确定性是通过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以及伴同发生的“类型”抽象(“eidetic”abstraction)而获得的。“它是要回到具体之上,回到坚实的根据之上,正如它的著名口号‘回到事物本身’!”〔4〕54胡塞尔的现象学坚持了实在论,通过意识的意向性将主体与客体关联起来,意识在意向性压力下寻求和获得的意义是本质的、不变的东西,是纯粹的现象。“现象学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还原为它们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表象,并且所有表象都是某种为意识而存在的东西。譬如,我当下正在感知的这棵树被还原为我的意识的纯粹现象,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点,我把这棵树的存在放入括号之中。此时所剩下的只有相对于我的表象,这种表象不仅是感性表象而且是理智表象。这种被还原为向我显现的东西叫做现象。”〔5〕64“纯粹现象是种种普遍本质(essences)所组成的一个系统,因为现象学在想象中改变每一对象,直到发现什么是这个对象的不变成分。”〔4〕54由此可知,胡塞尔的绝对确定性就是纯粹现象,是意识将事物对象化后获得的意义,是物的意义化。这一获得确定性的过程将超出直接经验的一切内容取消,使得物世界展现在意识中,并由无法认识的自在状态变为具有意义、秩序的自为状态。胡塞尔哲学中追求的确定性的本质和老庄学说中的道是一致的。道也是确定性,并且是终极确定性。二者都与理性、规律相关,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108,“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66。庄 子 提 出“ 万 物 一 府 ,死 生 同 状 ”〔3〕114,“ 道 通 为一”〔3〕17,这都是对终极意义的探求。而这一探求过程,正是涤除杂念、圆照玄览,主体通过对意义的探求将意识与物世界联结起来,从而参透宇宙万物永恒的规律,即绝对确定性。胡塞尔在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中,偏重主体,取消了真实客体,将重心集中在主体意向性活动本身,也就是主体认知客体的行为上。同样,在老子对道的体悟中,也体现出对主体的重视,“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2〕66,“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66。这使得胡塞尔的确定性与老庄的道同样具有了人本主义色彩,老子强调修身与悟道的关系,“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2〕42,这事实上也是对人的认知行为的强调。
胡塞尔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绝对确定性的挑战,使二人分道扬镳。海德格尔主张意义的历史性,一反胡塞尔的本质主义立场,从人的存在不可压缩的“给定性”即“此在”出发,阐明其存在主义立场,他关注的核心乃人的存在问题。这一问题与20 世纪西方社会的文明危机紧密相连。海德格尔在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中,偏重于客体,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聆听,即“听与沉默”。这与老子所言“道法自然”即强调人对道的遵从与敬畏,以及庄子的齐物论和齐同物论有相近之处。
胡塞尔的绝对确定性与老庄的道都关涉到对本质意义的探寻和对本质意义恒定性的认可。海德格尔将意义的确定性变为意义的历史性,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绝对本质,仍然与规律、理性相关。总之,现象学从逻各斯中心的实在论出发,寻求绝对确定性,与老庄从天地万物变化中探求道一样,均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但二者在原生点上存在分歧。现象学从实在论出发,即生发于“有”,而老庄的道则从“无”出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2〕2,“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103。伴同“类型”抽象的现象学还原所获得的绝对确定性(本质意义)是可以言说和阐释分析的,这直接影响了20 世纪西方阐释学理论的发展。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著名论断。而老庄的道则是无法言说的,只能体悟、意会,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2〕2。庄子也指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3〕223,“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3〕222。尽管胡塞尔坚持绝对确定性(本质意义),海德格尔坚持意义的历史性,使二者产生分歧,但主体在意向性活动中对终极意义或真理的探寻又将二者限定在现象学的大范围之内。二者对确定性的探求,与老庄学说对道的探求在本质意义这一节点上是同一的。正是意义,将现象学与老庄哲学中的主客体以相同的方式联结起来。
二、意义的先在性与意在言外:对言意关系的讨论
在语言与意义的关系上,现象学与老庄学说有明显的契合之处。语言被二者当作是次于意义的活动,“对胡塞尔来说,意义先于语言:语言不过是为我不知怎么就已经占有了的种种意义命名的次要活动”〔4〕58。语言是胡塞尔所说的表达式(书面的或口头的),表达式的意义部分和物质部分被混合或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意识使之然。“这种统一体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这两个部分不仅完全不同,而且还相互独立;然而,通过意识它们能够组成统一体。”〔5〕32-33语言只是为意义服务的工具或能指,是交流和表达意义的手段。而海德格尔则指出:“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话语”“现身在世的可理解性作为话语道出自身。可理解性的含义整体达乎言辞。言词吸取含义而生长,而非先有言词物,然后配上含义。”〔6〕188“话语通常要说出来,而且总已经是[有人]说出过的。话语即语言。”〔6〕195海德格尔并未坚持胡塞尔的语言工具论,他所说的“话语”即意义,他将语言和意义看做“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即意义与语言伴同发生。海德格尔的这一看法与结构主义理论颇为相似。胡塞尔将语言作为表达手段,是意义产生的次要活动,语言与意义相对独立。他对言意关系的理解与老庄学说的言意论十分接近。需要说明的是,“‘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一般来说,它和人的主观情志是相一致的,如《说文》训为‘志也’……对庄子来说,‘意’可以指作品的主旨,这是与他的哲学范畴不可分的,庄子认为宇宙的本体是道,那么万物都是道的派生物,这些派生物又以展示道为其自在之目的,故‘意’还不是道,但已是接近道本身了,如《易传》中‘立象以尽意’之‘意’则和庄子所指是相同的……”〔7〕。因此,庄子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意在言外、言不尽意、意外有道。胡塞尔现象学理论关于言意关系的认识恰好与此相合。
其一,意在言外。庄子指出:“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3〕289,“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3〕216。在庄子的论说中,意义与语言相对独立,语言是携带意义的符号文本。庄子所说的“筌”“蹄”“言”是获得“鱼”“兔”“意”的工具和载体。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竹笱、兔罝、语言都是携带意义的感知,即符号,当符号完成了向接收者传达意义的使命后,便滑向物,而主体意向性活动直接推动了从符号到物的滑动过程。因为主体意识要获得的是符号携带的意义,而非符号本身,但这一获意过程必须借助符号完成。庄子对言意相对独立性,以及在主体认知过程中言意不同地位的认识,与胡塞尔所主张的意义先在性与语言是次于意义的活动是一致的。从符号学视角来看,二者关于言意关系的认识全然符合意义获得过程中从符号到物的滑动,即意义实现后,语言便成为自在的存在,即物。
其二,言不尽意。庄子还提出著名的寓言、重言、卮言“三言说”,并指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3〕290。庄子的“三言说”充分表达了语言作为意义载体的局限性。齐同的事理与分辨事理的言论无法齐同,语言不能穷尽意义,作为携带意义的符号,语言表意总是片面的,符号接收者通过统觉共现和想象,从在场的片面意义获得不在场的整体意义。严羽在论及诗歌时曾指出:“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8〕“言有尽而意无穷”、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正是接收者面对符号文本进行的意义阐释,这种阐释开启了无限衍义的可能。“这样一来,符号过程,定义上不可能终结,因为解释符号的符号依然需要另一个符号来解释。”〔9〕因此,语言符号像其他符号一样,使接收者在接收意义最低完整度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无限衍义,虽然这种衍义会由于需要而暂时终止,获得临时的解释边界,但无限衍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提出的“尺水兴波”,从这个角度看与轮扁斫轮相同,都是对言不尽意的生动写照。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将语言作为意向性活动的次要因素或二手货,重视的是为经验提供意义的活动本身。
确实,“对胡塞尔来说,意义是‘意向性’的客体(intentional object)。他用这个词说明意义既不能被归结为说者或听者的心理活动,也并非完全独立于这些心理过程。意义并不在一张扶手椅是客观性的这一意义上是客体性的,但它也并不单单是主体性的。就其能够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被表达而始终保持为同一意义而言,意义是一种‘理想的’(ideal)客体”〔4〕65。同样,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认识活动所接收的是符号文本携带的意义,而不是符号本身。在整个符号过程中,符号在场,意义不在场。当接收者获得意义时,符号即刻不在场。胡塞尔把符号活动的核心因素——意义牢牢把握住是无可厚非的。他进一步指出,意义“能够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被表达而始终保持为同一意义”。在这里,“不同方式”与“同一意义”实际上成为后来美国阐释学家赫希(E.D.Hirsch Jr.)文本阐释理论的出发点。在赫希的理论中,“同一意义”即作者的心灵,或称为意义(meaning),“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即读者的会解(significance)。文本的意义是不变的,而读者的会解却是多样的,读者会解只要在作者意义允许的范围内即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其实,早在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就提出了著名的“诗无达诂”之权变说,在时间上远远早于西方。胡塞尔先于赫希将作者意义和读者会解区分开来,并且指出二者合一的向度。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庄子提出无限衍义的可能性,胡塞尔则在无限衍义中洞见了平行衍义与分岔衍义的合一性。因此,在言不尽意方面,庄子与胡塞尔建立了超越时空的融通与对话。
其三,意外有道。老子、庄子都提出言所不能论、意所不能察的道,且道在言、意之外。“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5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65。老子提出,道不可言,不可名,混沌天成。庄子则直接继承了老子的道,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3〕158。庄子指出,可以用语言谈论的是“物之粗”,只能意致的是“物之精”,言、意所不能达到的是“不期精粗”的道。意所追随的是无法言传的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3〕139。他明确指出意外有道,非意所能穷尽。因此,在中国文论的三种典型话语模式(孔语、庄语、禅语)中,庄语呈现出言→意→道的层控结构,意不能穷尽道,意不断接近道,与道“符合”。在老庄学说中,道这一形而上、不证自明的终极真理相当于现象学还原和“类型”抽象所把握的本质性和不变性,也就是胡塞尔在危机重重的一战后寻找的绝对确定性。
通过现象学批评方法来把握任意现象的本质,就是接近确定性;再通过范畴,使杂多的对象归于统一,这便是实现绝对确定性。胡塞尔的绝对确定性存在于“意”之外,“言”已经被其认为是二手的东西,因此,与绝对确定性的距离更远,无需多论。“意”不断接近绝对确定性,符合绝对确定性的要求。绝对确定性与道一样,是自我澄明的先验的范畴。即使海德格尔坚持存在主义立场,以时间的历史性与胡塞尔的本质主义分道扬镳,但他仍然宣称:“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是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6〕13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意义”与胡塞尔的绝对确定性都是对终极真理的叩问。胡塞尔将有关现象的知识理解为绝对确定的,而并非绝对确定性;海德格尔则将这种绝对确定性定义为向死而生,“连常人本身也一向已经被规定为向死存在了;即便它没有明确地活动在一种‘想到死’的状态中也是这样”〔6〕292。尽管他将存在主义导向了虚无主义,但这正是面对20 世纪欧洲社会深重文化危机的反应,向死而生使信仰、价值观无所适从的欧洲人在焦虑和痛苦中得到反常的安慰。与此种悲观主义相比,老庄的道则具有身居乱世而豁达、从容的超越品格。“意”外之“道”循环往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103。有无就像玄妙的太极图一般生生不息,人的生命来不可御,去不可止,“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其生若浮,其死若休”〔3〕151。只有息心宽容,才能心平气和、恬淡无为,持守静一而不变,生与万物齐同,死与万物化同。庄子的“刻意”正是磨砺心志、修养身心的超脱之法。老庄的道与胡塞尔、海德格尔追求的绝对确定性都是存在于“意”之外不证自明的真理,即主体意向性活动追求的终极真理。
三、本质直观与目击道存:意义获得的方式
现象学著名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中,“惟一绝对真实的事物是作为材料而显现出来的东西,某种给予我的意识的东西”〔5〕57。事物即意识中的表象,也就是现象。现象学通过将研究视角转入意识领域,通过本质直观而获得意义。胡塞尔将本质称为“艾多斯”,本质直观的对象是一种纯粹本质。“……本质直观是对某物、对某一对象的意识,这个某物是直观目光所朝向的,而且是在直观中‘自身所与的’;然而它是也可在其它行为中被‘表象的’、被模糊地或清楚地思考的某种东西,可成为真假述谓的主词——正像在形式逻辑中必然最广意义上的任何‘对象’一样。任何可能的对象,从逻辑上说‘真述谓判断的任何可能的主词’,在一切述谓思想之先,正好具有它的与表象和直观的目光交遇的方式,这个目光或许在其‘机体的自性中’达到它和‘把握’它……它就是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这个直观在其‘机体的’的自性中把握着本质。”〔10〕52在此,胡塞尔论及的核心问题是本质直观。在本质直观中,强调的是直接经验,因为现象学家只接受直接给予他意识的东西,而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对象化的事物是主客体共同完成的。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与“类型”抽象共同完成对纯粹现象的把握。纯粹现象有三个特质:第一,本质性与不变性;第二,悬置或取消了直接经验以外的东西;第三,在主客体交融中呈现确定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个特质中的“确定性”相当于“言外有意”的“意”,而非绝对确定性所对应的“意外有道”的“道”。
如何获得确定性?如何获“意”?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意义既不存在于主体中,也不存在于客体中,而是存在于主客体交融之中,正是意义将物世界与意识世界、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确定性即本质意义。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与庄子的“目击而道存”“心斋”“坐忘”颇为相似。笔者将从本质直观过程中的直接经验和主客交融两个层面分析中西文论在遥远时空的共振。
首先看“目击而道存”与直接经验。庄子在《田子方》中写仲尼见温伯雪子,见之而不言,子路询问原由,仲尼回答:“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3〕20“目击而道存”即眼睛看见就知道大道存于其身,也就自然不容许语言来表达。“目击”是直接经验,是直观的目光交遇,其对象是温伯雪子,在直接经验中获得的本质就是大道。“目击而道存”可理解为在本质直观过程中,仲尼的主体意识在意向性压力下将原初给予的温伯雪子对象化,并在意义最低形式完整度的基础上,通过意识的经验累积功能而使经验与意义世界相关联。这就是所谓的由直接经验而悟道的过程,或者说寻求确定性的过程。在通过直接经验获得意义的层面上,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与庄子的“目击而道存”几乎是一致的。特别是二者在字面上呈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胡塞尔的“目光交遇”与庄子的“目击”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对视觉感官的重视和提喻性修辞。当然,“目击而道存”也涉及了主客体交融过程中的悟性、禀赋,但更多的还是强调直接经验。
其次看直接经验过程中的主客交融与“心斋”“坐忘”。庄子借仲尼之口指出“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齐(斋)也”〔3〕37。空明的虚境即“心斋”,是道的聚汇所在。不用感官感知外物,不用心符合外物,摆脱外物的牵累,用气,即一种主宰万物和心志的道体形式容纳外物,渐入“呆若木鸡”的状态。如果将其用在具体的文艺创作中,“简而言之,文艺创作主体在感知事物的过程中由耳→心→气→虚的经验观照就是‘心斋’”〔11〕。在经验观照的过程中,主客交融,收视反听,物我两忘,由意识的意向性压力推动获得意义。庄子借颜回之口,道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3〕78。“坐忘”就是摆脱形、智,即身心欲求,超越外物和内心欲望的牵累,用空明的虚境与道融为一体。正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3〕4。这实为胡塞尔所主张的现象学还原时悬置“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将经验之外的东西取消,专注于意识领域对象化的过程,通过一种绝对自足的精神科学,获得绝对确定性。“我们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我们将该设定的一切存在性方面都置入括号:因此将这整个自然世界置入括号中,这个自然世界持续地‘对我们存在’,‘在身边’存在,而且它将作为被意识的‘现实’永远存在着,即使我们愿意将其置入括号之中。”〔10〕97“如果我可尽情随意地这么做,那么我并非像是一个诡辩论者似的在否定这个‘世界’,我并非像是一个怀疑论者似的怀疑它的事实性存在;但我在实行‘现象学的’悬置,后者使我完全隔绝于任何关于时空事实性存在的判断。”〔10〕97-98因此,收视反听,圆照玄览,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均怀胸中。
胡塞尔在本质直观中对直接经验的强调与庄子关于悟道的论说,呈现出异质同构的特征。胡塞尔用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的分析话语揭示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庄子则用天人合一的诗性话语,体悟主客体交融中的意向性活动。二者都归向了绝对的确定性,这种绝对确定性就是意义。与胡塞尔相比,庄子天人合一、法天象地的诗性阐发更胜一筹。“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为物化”〔3〕29-30,这一物我两忘,消弭物我、人我差别,与万物化同的境界正是胡塞尔追求的现象学直观中的主体意向性活动。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附说九]的《心与境》中对此有相应论说:“要须流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观;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12〕沟通中西文论的王国维用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来表现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的精神自由境界,其“境界说”正是超越现实、物我交融的典型体现,景物与情感的辩证统一与高度融合形成的境界,与庄子的“心斋”“坐忘”“梦蝶”是同一的。
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与庄子的“目击道存”“心斋”“坐忘”都强调意义获得过程中的直接经验,试图在直接经验中把握纯粹的现象。而纯粹现象所负载的意义既不存在于审美艺术主体的意识中,也不存在于对象化的事物中,而是存在于二者之间,并将二者以交融的方式联结起来。这既是意义的生成与存在方式,也是世界的生成与存在方式。
胡塞尔的现象学与老庄学说都源于在价值、信仰纷乱离析的现世中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二者都强调直接经验和主客体交融。从哲学符号学的角度看,绝对确定性即终极意义,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和企图在意义追求中重构社会精神或实现精神再生性,是胡塞尔与老庄共同的诗心,也是20 世纪现象学理论与公元前4 世纪至公元前3 世纪老庄哲学通约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与中国古典诗性话语,在对意义世界的探寻目标与理解方式上走向合一。同时,因为二者都依赖了人类经验的累加功能,通过想象力,使不在场的意义在场化,所以无论是科学的分析,还是诗性的体悟,最终殊途同归。当然,在看到二者通约性的同时,还应当注重二者存在的差异,除了逻各斯与道这一原生点的分歧外,还存在终极意义的清晰与混沌、理解方式的分析与体悟、言说话语的科学与诗性等,前文中均已论及到。用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照亮老庄学说,用老庄学说参透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在鉴照洞明中,观览差异性外表下的同一性,这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融通的价值所在。
——论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时间观的继承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