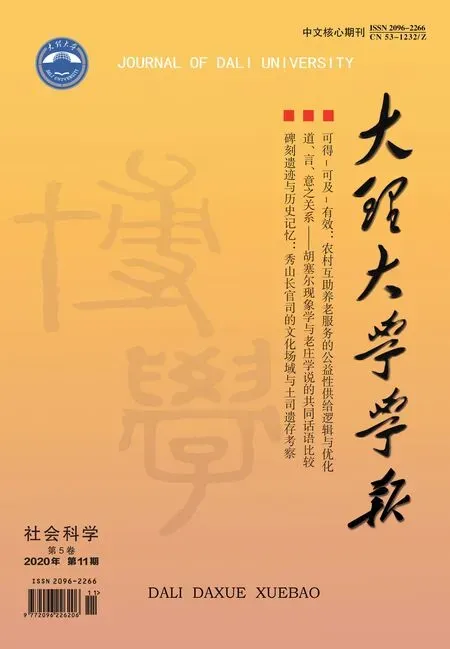保罗·奥斯特《玻璃之城》互文性分析
栗 霞,王 蓉,郭 萌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80)
一、探索语言意义:《玻璃之城》与其互文性
“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当代法国符号学家、女性主义批评家 Julia Kristeva 在其 Semeiotikè〔1〕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①Jonathan,Culler:“once we think of a text as intelligible and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other texts which it absorbs and transforms,then‘à la place de la notion d’intersubjectivité s’installe celle d’intertextualité.’”in Presupposition and Intertextualit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1382.后来,互文性又被Philippe Sollers 重新定义:“每一个文本都联系着若干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2〕Paul Auster 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者和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被视为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其代表作《纽约三部曲》中的《玻璃之城》〔3〕是一部非典型性侦探小说,具有浓厚的后现代特点〔4〕。Auster 通过营造哥特式的紧张气氛,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诱使读者与之一起踏上追寻身份和存在意义的心灵之旅。他运用大量互文,将多个作品交汇于一起,进行对语言意义的探索,使其作品包含多重内蕴。
《玻璃之城》中的互文性通过与多个作品搭建关系实现,从《圣经》到小说,体裁各异,但都与语言及其表达这一主题意义相呼应。语言原本是用于交流的工具,人类用语言实现了沟通、了解世界、记录历史。但在这部小说中,Auster 通过搭建与《马可·波罗游记》〔5〕《堂吉诃德》〔6〕《失乐园》〔7〕《圣经》的互文关系,探究在后现代背景下,由于能指与所指的割裂,造成语言表达的不可靠性以及不同语言背景下人类之间的隔阂和误解的结果。
二、能指与所指的割裂
关于语言的本质,不同时期的语言学家给出的定义各异。Sapir②参见戴炜栋,何兆熊《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Language is a purely human and non-instinctive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ideas,emotions and desires by means of voluntarily produced symbols.(Sapir,192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认为:“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表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之后,Hall③参见戴炜栋,何兆熊《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Language is the institution whereby humans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by means of habitually used oral-auditory arbitrary symbols.(Hall,196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将语言定义为:“语言是一种惯例,凭靠这种惯例,人类用习惯上使用的,口耳相传的,任意制定的信号来交流和互相影响。”二者对语言的阐释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他们对语言的定义揭示了语言的若干本质特征: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出于交际需要而设计的一种符号系统,这也是自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结构主义创始人之一Saussure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家对语言所持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语言是用声音表达思想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声响,一切符号都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音响形象即“能指”,其指代的概念则是“所指”〔8〕。在《玻璃之城》中,Auster 对于语言符号和本质无必然联系这个理念与Saussure的学说相契合,他指出,因为符号和意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所以产生出语言不能表达本质,带来误解的想法。小说中有许多能指与所指割裂的例子,如名字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特性,Peter Stillman 给自己起了许多名字,冬天是Mr. White,夏天又名Mr. Green。另如Virginia Stillman,虽然她的名字在现实中是Peter Stillman 的妻子,但本质上却不是。再如语言原本是用于交流的,可在小说中,人物的每次对话都会产生更多误解,对话双方不能了解彼此的想法。这是由于人类操纵语言去误导欺骗对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故事主人公Daniel Quinn 以侦探Paul Auster 的身份去体验人生,而他虽接受了Virginia Stillman的委托,却不能真正了解她的意图等等。
(一)不可靠的语言记录
《玻璃之城》与《马可·波罗游记》《堂吉诃德》的互文性大体体现在Auster对作品的直接引用上。小说与这两部作品的互文力图强调语言记录的不可靠性,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幻象的问题。《马可·波罗游记》与《堂吉诃德》这两部作品的真实性都有待考证,Auster 通过互文展现了能指与所指的割裂。Marco Polo 是否去过中国,至今无任何材料可考。《堂吉诃德》也是一部显而易见的虚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跨越真实和虚构的边界。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Marco Polo 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其真实性却有待商榷:首先,Marco Polo 是否真的去过中国,如今仍是一个谜。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学术界并没有人能证明他的真实行踪。其次,《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许多夸张、疏失与错乱的内容,在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的 Marco Polo 研究专家Colonel Sir Henry Yule 在其书《马可·波罗游记——导言》〔9〕中提到《马可·波罗游记》里有很多遗漏之处,如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文字、其他奇技巧术、怪异风俗等。此外还有多处纰漏和瑕疵,如地名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多误、攻陷襄阳城一节等。对于如此有东方特色的中国文字和印刷术他却没有注意到,实属怪事。所以,Marco Polo 所著游记的真实性不足以让人信服,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偏见。小说本身即是虚构的,但人们往往把虚构小说当成历史来看。过去西方人就是通过《马可·波罗游记》认识东方世界的,而现在仍有许多人误以为如今的东方即是小说里所谓的“东方”。小说中历史与叙事是相同的,但其实二者相去甚远。
《玻璃之城》与《马可·波罗游记》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Auster 对作品的直接引用。在故事开头描述了主人公Daniel Quinn 的生活,他几乎不需要与人打交道:父母离世,妻儿双亡,卖文为生。在他手边,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Quinn 将自己代入,在反复阅读中幻想自己到过东方城市:“奎因拿起那本《马可·波罗游记》,又从第一页开始看起。所以吾人之所征引,所见者著明所见,所闻者著明所闻,庶使本书确实,毫无虚伪,有聆是书或读是书者,应信其真。”〔3〕12《马可·波罗游记》展现了Marco Polo 主观的眼光和态度,他描述的东方世界的景象看似真实,实则荒诞的捏造。Auster 通过互文性这一技巧的使用,体现了能指与所指的割裂和语言的不可靠性,表现出玻璃之城是一个陷阱,城市中的人常常迷失自己。并深入地摹写了20 世纪中后期以纽约为代表的城市虚无精神,现代资本主义蕴含的理性逻辑已经侵蚀了私人生活的最深处,最终阐发了现实与虚无二者的区别已经消失的主题意义。《玻璃之城》契合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语言观——能指的滑动,即能指尚未指明其所指的意义已经滑向了其他所指,失去了其本身含义。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的《堂吉诃德》与《马可·波罗游记》类似,小说的叙述者不像传统小说中的模式,不再自信和从容,也无法确定故事的真实性。首先,Cervantes 极力地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以增强其作品的可靠性,却一直把读者置身于故事之外。从文章开始到第八章,Cervantes 一直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者,可到了Don Quixote 和Sancho Panza 第二次游侠,和比斯开人发生争斗,故事到了最高潮,叙述却戛然而止。“事情真是糟糕透顶,正是在故事的高潮时,小说的作者没有进一步把厮杀的场面进行更加完整的描述,作者给予的公开理由是,堂吉诃德的事迹和平生,仅有上述这些记载”〔10〕。此时,“我”也不再具有权威性。之后出现了第二作者 Cid Hamate Benengeli,Benengel 游走于多重身份,增加了其作品的不可靠性。其次,从小说的来源看,前面部分是由某个作家查阅资料所记录的,后面部分是由阿拉伯历史学家Benengeli讲述的,素材来源与小说的内容不一致使作品更加失真。因此,Cervantes的《堂吉诃德》也不具有真实性。
《玻璃之城》与《堂吉诃德》的互文性也主要体现在Auster 对作品的直接引用。在Quinn 与真正的Paul Auster的对话中,二人这样讨论道:“塞万提斯,如果你还记得,他用了不少篇幅想让读者相信他不是作者。他说,这本书是一个叫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阿拉伯人写的。塞万提斯描述了自己某一天是如何在托莱多的市场上偶尔发现这本书的手稿的。他雇用了一个人给他翻译成西班牙文,过后他称自己只不过是这个译本的编辑。事实上,他甚至都不能保证翻译本身是否准确”〔3〕111-112。“……还有,我总是怀疑塞万提斯对旧时那些传说故事特别着迷。除非那里边有你喜欢的东西,否则你不可能如此强烈地憎恨它……”〔3〕112。《堂吉诃德》这一故事无论是从素材来源,还是从情节的不确定性来看,都表明小说的虚构性。Auster通过互文性这一技巧的使用,体现了能指与所指的割裂与语言的不可靠性,让人不禁想到主人公Don Quixote,通过阅读他知道自己正在被写作和被阅读,他既是读者也是被读者。在这一点上,Quinn与Don Quixote 相差无几。通过使用互文,Auster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幻象的界限。他描摹了玻璃之城依然繁荣但其内部充满了混沌、人已经处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并行将消失的景象。旨在诘问在现实与虚无的模糊世界里,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而他们的避居之处又在何方?作者的这一写作意图扣合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反客观,反先验。后现代小说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出现了断裂,而语言就是能指的延续,小说的意义仅靠读者自己来解读。
(二)语言造成人类隔阂
将《失乐园》和《圣经》相联系的枢纽也是语言,Auster 通过互文进一步展现了能指与所指的割裂。起初,无论是在伊甸园之中,还是在巴别塔之中,都只有一种语言。后来由于贪婪与罪恶,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单一语言消解为各种各样的语言。巴别塔的故事是为《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 章所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他们说不同的语言使其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失乐园》则以《圣经·旧约》中人类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为基础,以史诗般磅礴的气势展现人类对自己信仰探索的历程。这两个故事均以《圣经》作为本源,将信仰与语言联系起来。
《玻璃之城》与《失乐园》《圣经》中巴别塔寓言故事的互文性并非体现在Auster 对作品的直接引用,而是将Old Stillman 所著的《伊甸园与巴别塔:新大陆的早期意象》和为John Milton 当过秘书的Henry Dark 的《新巴别塔》结合。Old Stillman 研究了《圣经·创世纪》中的两种寓言式形象与新大陆的关系。其一,从Cristoforo Colimbo 发现美洲大陆开始,许多欧洲人把新大陆看成“伊甸园”或“人间天堂”,这不仅是对完美生活的想象,而且也是一种带有乌托邦理想的寓言式渴望。伊甸园的寓言强调,人被上帝所照管和控制,才能达到一种无暇和圣洁的状态。而Auster认为“人类堕落后,名称从事物那里分离出来;词语退化为一串随机符号;语言也已与上帝分离。所以,伊甸园的故事,记录的不仅是人类的堕落,也是语言的堕落”〔3〕51。倘若人类能够回归本真,学习并使用最纯真无邪的原始语言,就能重新从内心获得真理,他们将不再堕落。所以,Old Stillman 把自己的儿子囚禁起来,企图让他说出最原始纯朴的语言;他还在纽约城每天收集样本,为他们命名;他行走的路线图正是《失乐园》里找寻巴别塔的地图。可见,Auster 借《失乐园》及Old Stillman 表达其内心对语言现状的顾虑——能指与所指的割裂。他想要找到人类语言的同一性,通过“扭转语言的堕落,努力呈现伊甸园里的语言,就可以逆转其影响,消除人类的堕落”〔3〕54。其二,Old Stillman 认为《圣经》中的巴别塔寓言也与新大陆有着密切的关系。故事中,人类渴望塔顶通天,拥有和上帝一样的力量,而上帝通过混乱人类的语言,粉碎了人类协作挑战上帝的妄想。故事巴别塔的语言强调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制造高塔,使自己上升到与上帝相同的位置来主宰世界。与Henry Dark 所写的《新巴别塔》结合,Old Stillman 认为,人类都说同一种语言,象征着人类精神的复苏。“建造巴别塔的障碍——人必须遍满地面——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又有可能变得都一样了。如果这一刻到来,天堂也就不会太远了”〔3〕55。而人类也将“呈现出新人之相,说着上帝的语言,准备在第二个永恒的天堂定居”〔3〕56。另外,从Quinn 和 Peter Stillman、Old Stillman 的对话不难看出,Peter Stillman 的“演讲”混乱,随意变换名称,说出了几段高度下流的陈述。他是巴别塔寓言中说着普遍语言的人,这种语言能够制造快感(例如性快乐,获得金钱的快乐……),这种快感把现代城市中无数形单影只的个体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快感共同体。而Old Stillman 则将语言本身和快感结合,他与Quinn的对话就是一种彻底的语言游戏。由此可见,语言本身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却成了人与人之间制造障碍的工具。Auster借《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及Old Stillman 表达重拾语言的渴望,当人类开始堕落以后,能指与所指割裂,他们不能够正常交流,最终造成了一个问题——彼此之间不能够了解,从而产生隔阂。
Auster 通过在《失乐园》和《圣经》中互文的使用,体现了语言只是一堆无意义符号的结合。能指与所指的割裂使得言语造成人类的隔阂这一主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和现代语言的现状:人可以不接触社会直接领悟巴别塔倒塌之前的语言,这样容易造成误解。所以,Auster 渴望真正稳固又坚实的语言,希望人类能够回到本真。此外,他还向人们展示出纽约是一个硕大而又冷漠的玻璃之城,人的身份像玻璃一样破碎。人与人之间如隔了层玻璃,他们彼此关联却又互相利用,失去了正常爱的情感,唯有疏远、冷漠和欺骗,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危机〔11〕。这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相符合:语言犹如梦幻一般,充满了反传统、意识流、支离破碎的特征,成为了恣心纵欲的符号系统。
三、对言语意义的批判:语言及其表达的悲剧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Paul Auster通过《玻璃之城》与四个体裁各异作品(《马可·波罗游记》《堂吉诃德》《失乐园》《圣经》)的互文性探究了每个文本在语言及其表达这一核心意义下暗含的不同层次的主题意义:《马可·波罗游记》《堂吉诃德》表现出能指与所指的割裂和语言的不可靠性,《失乐园》《圣经》体现的是能指与所指的割裂带来了言语造成人类隔阂的问题。总之,在纽约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里,现实与虚幻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个人所能享受的仅是孤独和空虚;人和人之间永远隔着一堵像玻璃一样的墙,看似透明,实则无法跨越,最终留下的也只是疏远、冷漠和欺骗。语言的本体性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相契合,能指的滑动致使能指与所指之间出现了断裂,充满了强烈的后现代性,形成一个予求予取的符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