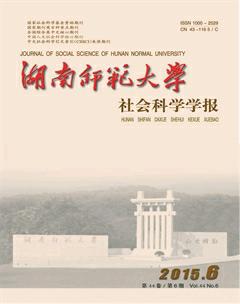语言与文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之四
摘 要:语音有物质与心理两个层面,语音的心理层面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但在语音的两个层面中,物质层面是主要的,心理层面是从属的,是物质层面在人的心理中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语音才能与语言符号的能指划等号。索绪尔将文字看作是外在于语言系统的另一符号系统的主要理由有三个,但这三个理由并不充分,无法论证文字是另一符号系统。语音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在共时的层面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所表征的意义或者说所指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文字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语言符号能指的两种表征方式之一,研究语言和文学可以通过文字进行。
关键词:语言;语音;文字;能指;所指
语言的能指有语音和文字两种表征方式,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固定的联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的学者根据这种差异,认为语言与文字分属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讨论文字不等于讨论语言,研究文字与图像的关系不等于研究语言与图像的关系{1}。这就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语言与文字不属于同一符号系统,那么二者之间就存在转换的问题,而任何转换都会造成一定的偏离与损失,那么,文字在表达语言的时候是否与语言完全一致?如果是完全一致的,如何能够说文字是语言之外的另一符号系统?如不一致,文字又如何能够表现语言?另外,在语言与图像的关系之外是否还存在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探讨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是从语言入手还是从文字入手?文字既是另一个系统,它能否准确地表达语言?将口头文学用文字记录下来时是否存在变形?研究文学能否通过研究文字进行?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需先探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由于索绪尔是强调语言和文字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国内持两个系统论的学者也常常从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寻找根据,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了解他的真正看法并作出自己的分析。
一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从未将文字与语言的能指联系起来,他将能指与语音等同。他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物质的,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跟联想的另一个要素,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这个实体的一面是概念,另一面是音响形象。“这两个要素是紧密相连而且彼此呼应的。”“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2}索绪尔的意思十分明显:语言的所指是概念,能指是音响形象。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从符号学的角度讨论语言时,索绪尔一般倾向于使用能指与所指这两个术语,而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语言时,则一般倾向于使用音响形象和概念这两个术语。由此可见,在索绪尔那里,能指与音响形象实际上是等同的,是同一事物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的叫法。
然而,问题也就在这里。按照索绪尔的说法,音响形象是“声音的心理印迹”,具有心理性质,而能指则是指的语言符号的声音方面。他说,“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全部语言事实,即语言,设想为一系列相连接的小区分,同时画在模模糊糊的观念的无限平面和声音的同样不确定的平面上面。”“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一个声音就变成了一个观念的符号。”“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这一点只有经过一种抽象工作才能做到,其结果就是成了纯粹心理学或纯粹音位学。”{3}在这些论述中索绪尔讲的“声音”,肯定不是声音在人的心理上的印迹,而是实际的物理的声音,也即他所说的“声音物质”。如果指的心理印迹,我们就无法理解如何对声音进行切割,声音与思想为什么不能分离。因为索绪尔已经说明,从纯粹心理学或纯粹音位学的角度,是可以让思想与声音分离的,不能分离的肯定是物质的声音和它所表达的思想。这样,音响形象便无法与能指划等号。
因此,如何理解“音响形象”便成为理解索绪尔相关思想的关键。应该承认,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音响形象”这一术语有其含混之处,索绪尔的论述也有含混之处,这影响了国内学界对于音响形象的理解。目前国内学界对于“音响形象”的理解大致有三种,一种认为音响形象就是能指,一种回避音响形象,认为语言的能指就是语音,一种认为“‘音响形象是语音的‘心理印迹……是和语音勾连在一起、被语音所唤起的语象”{4}。究竟哪一种看法更准确,更符合索绪尔的原意呢?
笔者以为,索绪尔对音响形象的界定是十分明确的,它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不过,索绪尔强调音响形象并没有否定语音的物质性。他说音响形象“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就隐含了语音既是物质的又是心理的意思。另一方面,心理印迹必然要有引起这印迹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从逻辑上说,必然先有一定的声音,然后才有相应的心理印迹。声音与心理印迹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就像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一样,实际上也是不能分割的。
索绪尔之所以强调音响形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认识到,音响形象与说话者的实际发音是有区别的。“重要的是不要把词语形象和声音本身混为一谈,它和跟它联结在一起的概念都是心理现象。”{5}索绪尔将词分为物理(声波)、生理(发音和听音)和心理(词语形象和概念)三个部分,并强调要将三者区别开来,这是有道理也是必要的。因为一种声音可以用人的发音器官发出,也可以用其他的发声体发出,只要两者发出的声波是一致的,两者发出的就是同一种声音。另一方面,索绪尔曾反复强调,“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说话者在使各个声音仍能互相区别的限度内享有发音上的自由。例如法语的r按一般习惯是一个小舌音,但并不妨碍有许多人把它发成舌尖颤音,语言并不因此而受到扰乱。语言只要求有区别,而不像大家所设想的那样要求声音有不变的素质。我甚至可以把法语的r发成德语Bach‘小河,doch‘但是等词中的ch。可是说德语的时候,我却不能用r当作ch,因为这种语言承认有这两个要素,必须把它们区别开来。”{6}也就是说,一个词的声音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段,这个音段的两端以这个声音与同一语言中的其他音段的区别为界限。在这个音段内,发音者发出的声音可以有“不同的素质”,换句话说,只要是在这个音段的范围内,发音者不管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都还是这个词的声音。索绪尔说的音响形象实际上就是这个音段在人的心理上的印迹,它与具体的人所发出的实际声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索绪尔要求把音响形象与实际的发音区别开来,这是重要原因和理由之一。
那么,如何理解音响形象与实际发音之间的区别?笔者以为,索绪尔的相关论述实际上存在一个误区。他在论证音响形象的时候,指的是公众对于语音的心理印迹,而在谈声音的时候,则是指个体的实际发音。个体的实际发音当然与公众的心理印迹有差异。实际上,如果将心理印迹落实到每个个体,每个个体对语音的心理印迹也是不同的。如“牛”这个词,普通话念niú,南方很多人念liú。对于南方人来说,你念liú他能听懂你说的是“牛”;而对于北方人,他则不一定知道你说的是牛。可见在同一种语言内部,不同的人对于语音的心理印迹也是不同的。如果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语音的心理印迹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其一,个人对某个词的发音,形成了这个词的发音在他心中的印迹的核心;其二,他所听到的其他人对这个词的发音,丰富了这个词的心理印迹的内容,这使他能够听懂发音与他不同的人所说的话;其三,语言的心理印迹是可以变化的。一些边远地区的乡民可能听不懂普通话,因为他不说普通话,他也从未听过别人说普通话。但他如果走出家乡,来到城市,听到了别人说普通话,渐渐地,他也就能够听懂普通话了。这说明,语言的心理印迹在他心中已经得到改变。如果从群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语言的心理印迹则有四个方面需要考虑:其一,群体的心理印迹的确与个体的发音有区别;其二,群体的心理印迹与群体的发音是符合的,群体对于某个词的心理印迹是群体中各个成员对这个词的主流发音在群体心理中的反映;其三,群体的心理印迹规范、制约着个体的发音;其四,群体的心理印迹是随着群体的实际发音的变化而变化的。汉语古时有不少入声词,在现代,这些入声词都没有了,不是说这些词本身消失了,而是说它们都不发入声了。因此,现代中国人对于汉语语音的心理印迹,也就没有了入声。群体语音的心理印迹也就没有了入声的内容。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个体看,人们的语音的心理印迹是与实际的语音相符并由实际的语音所决定的。
从历时的角度看,心理印迹是随着实际语音的变化而变化的。索绪尔认为,语音的变化“是无限的,不可估量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预见它们将止于何处”{7}。但“不是任何的言语的创新都能同样成功,只要它们还是个人的,我们就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语言。只有等到它们为集体所接受,才进入了我们的观察范围”。“在一个演化事实之前,总是在言语的范围内先有一个或毋宁说许多个类似的事实。这丝毫无损于上面确立的区别,甚至反而证实这种区别。因为在任何创新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时期:(1)出现于个人的时期;(2)外表虽然相同,但已为集体所采纳,变成了语言的时期。”{8}语言的各个要素特别是语音总是在发生异动。这些异动开始是偶然的、局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异动(大多数)没有得到社会共同体的承认,自然消失了,有些异动得到社会共同体的承认,被保留下来,并取代原来的语音,成为新的标准音。而随着新标准音的形成、推广,人们关于这个音的心理印迹也会随着改变。比如“癌症”的“癌”字,才从日本传入的时候,读作“yán”,但在实际运用中,常与“炎症”的“炎”的读音(yán)相混,造成了很多不方便。比如说“胃yán”,从读音上就很难区分是“胃炎”还是“胃癌”,因此有专家建议将“癌”的读音改为“ái”,此读音得到大家的认同,于是“癌”的读音慢慢从“yán”变成了“ái ”,人们对这个字的心理印迹也产生了改变,再说“胃yán”,就没有人认为是“胃癌”了。而至今仍有很多方言地区将“吃饭”的“吃”(chī)念成“qiá”,但这个读音没有为整个汉语共同体接受,因此还只能在部分地区流行,并在书写上用另一文字“呷”表示。
索绪尔强调音响形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并不是所有人类的声音都是语音。语言是一种以“音响印象在心理上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9}。只有与这些音响印象相符的声音才是语音。因此,他强调语音的心理性质。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指出的,只有先有了语音,然后才可能有这语音的心理印迹。至于为什么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所发出的某些声音成为了语音,另一些声音没有成为语音,则只能从社会实践的层面,从索绪尔的约定俗成、任意性的角度加以理解。换句话说,音响形象只能从语音的角度来解释,语音则不能从音响形象的角度来解释。语音的心理性质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语音只是对人而言才是语音,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体系的人才能分辨出声音与语音。对于其他物体比如动物而言,语音也就是人类发出的声音而已。在训练狗的时候,人们可以发出“站住”、“坐下”、“卧倒”等指令,让狗做出相应的动作;但经过训练,人们也完全可以用“嗨”、“嗬”、“哈”或其他完全不属于语音范围的声音让狗做出同样的动作。对于狗来说,你发出的声音是语音还是音响并无什么不同,人们用语音(语言)来指挥狗不是为了方便狗,而是为了方便自己。其二,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只有符合某一群体与语言相关的心理图式才能成为语音。对于讲汉语的人群来说,当你说“rénmín shì wěidà de”(人民是伟大的)的时候,他们知道你发出的是语音,当你说“de de de de de”或者因痛苦而发出呼叫时,他们则不会认为你发出的是语音。而对于不懂汉语的人来说,即使你发出的是汉语的语音,他们也不一定认为你发出的是语音。当然,当你发声的时候,他们一般认为你是在讲话,也就是说会认为你发出的是语音,但这只是情理上的推测,而不是理性与知识的判定。因为你完全可以糊弄他,发出一连串没有任何意义的声音,而他则无法肯定你发出的是语音还是声响。而决定着人对语音和声响的判断的则是他所掌握的与语言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储存在他的头脑之中,使他能够对语音或声响作出迅速的判断。其三,音响形象与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而就主体的角度看,概念无疑属于心理层面,是人的知识与思想的组成部分。音响形象与概念联系在一起,自然也就带上了心理的性质。但这些都只能说明音响形象为什么是心理的,无法否定语音的物质性,也不能用音响形象代替语音。
笔者以为,语音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根据任意性的原则通过约定俗成纳入语言系统的人类的声音,音响形象是这声音在人们心理上的印迹。声音是语音的物质层面,音响形象是语音的心理层面。宽泛地说,语音是这两者的统一。严格地说,语音只能是前者,即纳入语言系统的人类声音。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意义上的语音和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的能指是同一的,没有矛盾。索绪尔强调语音的心理性质,是为了说明语音的人为性和内在系统性,而不是为了否定语音的物质性,或者认为语音的物质层面无关紧要。从根本上说,语音的两个层面中,物质层面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先有了语音的物质层面然后才有心理层面即音响形象,心理层面是随着物质层面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索绪尔一方面强调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一方面又将音响形象等同于能指。这里的关键仍然还是不同的语境。在论述语言的内部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区分时,索绪尔强调语音的心理方面即音响形象;在论述符号结构时,他又侧重语音(能指)的物质性的一面。考虑到这一点,索绪尔用能指来代替音响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避免误解,笔者以为,在一般性地论述语言时,使用语音这个术语比使用音响形象更能准确地表述语言的声音层面,也更能与符号意义上的能指相适应。
二
厘清了语音内部声音和音响形象之间的关系,再来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就有了基础。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曾几次提到,语言与文字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以把它们译成固定的视觉形象”。“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仪式、军用信号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在另一个符号系统——文字——里也可以看到”{10}。由于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从不将文字纳入语言系统内进行讨论,在语言的能指中也将文字排除在外。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受索绪尔思想的影响,一般也认为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本身并不属于语言系统。如张巨龄认为,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是工具的工具”{11}叶蜚声、徐通锵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的”{12}。
对于索绪尔抬语音贬文字的观点,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进行过分析与批评,如德里达。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强调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表现语言,是语言这种声音符号的代表,因而低于语言,只是语言的替代品的观点是典型的“语音中心主义”,与西方数千年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相信有某种存在于语言之外的本源、本质、绝对真理,而这是一切思想、语言和经验的基础,语言仅仅是表达这一终极之“道”的工具或者通道。语音中心主义认为,在与思想的关系中,语言是直接的、透明的,与讲话者的当下思想具有同一性,因而是在场的、第一位的;而文字仅仅是语言的视觉符号,是一种言语的替代品,与讲话者的当下思想没有同一性,在说话者和言语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存在,因而是不在场的、第二位的。德里达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按照索绪尔自己的说法,符号的能指具有随意性。一定的能指能够指代一定的所指完全依靠它与其他能指之间的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如“树”这个能指之所以能够表达“树”的意思,是因为它与“花”、“草”、“藤”这些能指等有差异,但肯定也是因为它与“钢”、“铁”、“铜”等能指有差异,与“屋”、“楼”、“宇”等有差异。这种差异可无限地列举出来。在这一无限延伸的网络之中,任何符号都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都必须依赖其它几乎所有的符号才有意义,有位置。这样,任一符号的能指与它的所指的关系就很难说是固定的。符号并没有一个超验的意义或中心,它只是一堆差异的组合。而另一方面,所指也是由差异来区分的,“树”的概念(所指)之所以能指示现实中的树,是因为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也是可以无限地延伸的,这样,“树”这一所指也就很难固定在现实中的“树”这一事物之上。这样,“树”的能指不一定能够准确地指向“树”的所指,而“树”的所指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指向现实生活中的树。语音与思想的关系,并不比文字与思想的关系更为密切。语言的相对于文字的优越性(直接、透明、与思想的同一性)也就不存在了,它并不高于文字{13}。
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语音中心主义,而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对于语言和文字的看法。
索绪尔将语言和文字看作两个不同的系统,其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
其一,文字只是表现语言的手段,是依附语言而存在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象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14}。文字只是声音的书写形式,表现语言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既不与语言的内部系统发生关系,也不对语言的内部系统产生影响。所谓语言的内部系统,其核心是声音与思想各自的差异系统,和两者之间的划分与结合。这种差异、划分与结合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与文字没有关系。不仅如此,文字还“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15}。比如汉语中的一些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但在发展的过程,有些词的声音发生了变化,而相应的文字却没有发生变化,表声的声旁指示的却是错误的读音,文字掩盖了语言的本来面貌。因此,索绪尔强调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不能将它们混同起来。
其二,语言无需文字也能存在。索绪尔认为,“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很稳固的,不过书写形式的威望使我们看不见罢了”。“没有文字,决不会损害语言的保存的。立陶宛语今天在东普鲁士和俄国的一部分还有人说,它是从1540年起才有书面文献的;但是就在这很晚的时期,它的面貌总的说来却跟公元前三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忠实地反映出印欧语的情况。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16}。有些民族如我国的土族、裕固族的语言至今都没有文字,但并没影响这些语言的日常运用。苖、壮、布依、哈尼、傈僳、侗、佤、黎、摩梭、布朗、赫哲以及白、独龙、土家、羌、基诺等民族现在使用的文字都是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组织专家为他们制订的{17}。在这之前,他们语言都没有相应的文字,但都保存、流传下来了。语言的独立性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在有文字的语言中,有部分语言资料并没有写成文字,而是通过民间口耳相传的形式保存、流传下来的。这些事实从某种角度说明语言不依靠文字也是可以保存、流传与发展的。
其三,从历时的角度看,语音先于文字而产生。索绪尔认为,“有些原始的文字是标记音节单位的,到后来才有字母的体系”{18}。也就是说,文字至少是部分文字的产生是由于标记语音的需要。文字系统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可能只是单个的文字或文字的片断,后来才慢慢地发展、组合成文字的系统。语音先于文字而产生,文字是为语音服务的,因而它只能是一个外在于语言的系统。
索绪尔的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十分雄辩。
首先,文字与语言(更准确地说,是语音)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的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因此,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而是指的这一颇为神秘的事实,即‘思想—声音就隐含着区分,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19}。语言通过差异将声音流分成一个个互相区别的音段,将思想流分成一个个互相区别的概念,然后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将这些音段和概念相互搭配起来,由此形成一个个的词语。语言形成的关键是“差异”。但是在语言中,存在很多不同的概念用同一语音来表征的现象。如在汉语中,发“shī”这个音的,仅在《新华字典》中就有尸、鸤、失、师、狮等15个词,换句话说,就是“shī”这个声音段表达了15个不同的词。双音节词也是如此,“gōngshì”这两个音节,可以表示“工事”、“公式”、“公事”、“公示”、“攻势”、“宫室”等不同的词。《新华字典》只有400来个音节,加上声调也不过1 000多个音段,但却表征了8 000多个汉字。如果只靠语音,即使加上不同的语境,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差异,使这些不同的词得到明晰的表达{20}。而“任何观念上的差异,只要被人们感到,就会找出不同的能指表达出来;如果有两个观念,人们已经感到没有什么区别,也会在一个能指里混同起来”{21}。汉语的音段“shī”、“gōngshì”表示了那样多的概念,其之所以没有继续分化,是因为它们与不同的文字联系了起来,因而能够提供足够的区分不同的所指的手段。如果没有文字,分化就必须继续下去,直至它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差异,能够更好地区分并指示所指,否则,它就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比较容易把握的思想。而这两种结果,都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按索绪尔的观点,“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22}。文字至少参与了语言的差异系统,使语言系统的差异更加精细。这样,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的系统之外,就缺乏说服力。
其次,语言无需文字固然也能存在、流传甚至发展,这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很难发展成为成熟、复杂、精细的语言。只有高度成熟的语言,才能适应文明发展的需要。运用没有文字的语言,构建不出莎士比亚的剧本、曹雪芹的《红楼梦》、黑格尔的《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精美、复杂、精深、丰富的艺术、思想大厦{23}。索绪尔认为:“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24}。换句话说,语言与思想是无法分离的,因为思想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语言建构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想。高度成熟的思想必然要求高度成熟的语言。而只有在文字的参与之下,语言才能更好地留存、积累、展开,并在留存、积累、展开的基础上发展,精细、准确、复杂、优美,直至高度成熟。语音作为语言听觉形态的能指,诉诸于人的听觉,并且只能直线展开,随着时间而消失,即使用录音的方式保存下来,由于听觉的性质,听者也很难充分地把握。而作为语言的视觉形态的能指的文字则不同,它诉诸于人的视觉,可以在平面上展开,可以在时间中停留,读者容易充分地把握。另一方面,人们在听的时候是被动的,必须被动地适应声音的速度,而在看的时候是主动的,可以主动调整阅读的速度。而且声音随时而逝,即使将它录制下来,其效果也仍然受到限制。而文字则可保存下来,作为思想的物质载体,供人们反复探讨。正是文字的这些表征上的优势,使语言的复杂、精细、优美、准确成为可能。难怪索绪尔虽然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的系统之外,但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25}。可见,运用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这一事实来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再次,从日常生活现象看,的确是语音先于文字。如婴儿生下来,首先学会的是说话,要到上幼儿园甚至是上小学时才会学习文字。许多处于原始或不发达状态的民族也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但这只说明了相对于文字,语音是一种更自然的表征形式。语音诉诸于人的口耳,文字诉诸于眼睛。因此,在把握语言的过程中,人们一般是从把握语音开始。但这只能说明,在语言能指的两种表征形式中,相对而言,语音更具自然性,而文字则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毫无疑问,通过一定的培训,人肯定能够先掌握文字然后再掌握语音,或者只掌握文字而不掌握语音,就像天生的聋哑人学习语言那样。因此,人们把握语言是先把握语音再把握文字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语音一定先于文字而产生。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低级到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裘锡圭指出:“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曾经用画图画和作图解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通常把这种图画和图解称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26}。周有光认为,“文字画(文字性的图画)使图画开始走向原始文字。图画字(图画性的文字)是最初表达信息的符号系列。从单幅的文字画到连环画式的图画字,书面符号和声音符号逐步接近了”。至于表音文字,周有光认为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人为了经商记帐的需要,“模仿丁头字和圣书字中的表音符号,任意地创造了好多种后世所谓的‘字母”{27}这一观点李梵表述得更为明晰:“源于象形文字的表音文字,是将原来的文字图形演变成有限的数十个字母,用这些字母去表示语言中的音位、音节,通过各种组合方式去拼写语言中的语词,因而也称之为拼音文字”{28}。人类的文字经历了从图画到文字画到图画字再到象形文字的过程,拼音文字再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地知道早期语言的语音与文字结合的方式,但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些方式是多样的。最早的文字和语音可能存在各自独立的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才被人们固定搭配在一起的情况。搭配的方式有可能是文字依附语音,但肯定也不能排除语音依附文字的情况。换句话说,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先有语音,再创造一个书面符号,或将一个已有的书面符号与之相配,或者先有书面符号,再赋予它一个声音,两种情况都是无法排除的。假设一个幼儿,他看见一把椅子,发出“哒”的声音。他的长辈告诉他,这是椅子,久而久之,他便以“yizi”这个声音表征他所看见的椅子。但如果他的长辈不纠正他,也跟着他将椅子叫作“哒”,或者,这个幼儿天生听力有障碍,无法听到别人的声音,他就很有可能一直将椅子叫作“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先有了物,再给它赋予声音。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人造的符号上。既然幼儿语言中存在这种现象,我们自然很难排除在原始语言的形成中,不存在先有实物或符号,再赋予其声音的情况。由此可见,索绪尔从拼音文字出发,认为文字是附属语音而产生,为表达语音服务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
自然,作为两种不同的表征方式,语音与文字也有各自的内部组织与运作规律,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必然的。比如,两者都是根据差异原则组织的,但差异的依据却是不同的。语音依据的是声音上的差异,文字依据的则是视觉形式,更明确地说是线条形式的差异。汉语的“王”字,在上面加一点,成为“主”字,在右下加一点,成为“玉”字,但如果在上面加两点,或者在左下加一点,则什么字都不是。再如,由于各有自己的内部组织与运作规律,二者的变化不一定完全一致。作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语音的变化是最快的,文字的变化则相对滞后,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甚至远远地滞后,由此形成书面语言与日常语言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如我国古代汉语共同体中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的言文分离现象。一般地说,在有文字的语言中,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书面语言与日常语言分离的现象;没有文字的语言则不存在这种现象,由于没有文字留存过去的语言系统,他们的语言永远处于现在时。这与语言的能指中,存在语音和文字两种表征形式是分不开的。第三,语音与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使用范围也是不同的。在日常生活、普通的一般交流的场合,人们使用语言时更喜欢用语音来表征;而在重要表达、严肃交流和特殊场合,人们使用语言则更倾向于用文字来表征。第四,语言能指虽然有语音和文字两种表征形式,但不排除部分人由于某种原因只能把握其中某一种表征形式的情况。如文盲,就只能把握语音而无法把握文字;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也不排除某些人只能把握文字而不能把握语音的情况;某些语音已经失传的古文字,经过研究,学者能够把握或者部分把握它们的意义,但却无法恢复它们的语音。在一些俗称“哑巴外语”的学习者中,也存在着把握了文字和它的意义却不知它的语音的情况。
这些都说明语音和文字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语音和文字都可以独自表达所指,因此也可以说语言以语音表征的时候和以文字表征的时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这些差异,而在这些差异是存在于共时层面还是存在于历时层面。索绪尔十分重视这两个层面的区分。他认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了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29}。
共时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其他三个是任意、系统、变化。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中没有时间和空间无法改变的永恒的特征。“任何特征都不是理应永远不变的,它只是出于偶然才保存下来。”{30}语言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但是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语言的历时变化,而是研究共时展开中的语言,研究决定着言语活动的系统和规则。“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对语言学家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他置身于历时的展望,那么他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系列改变语言的事件。”研究语言的历时变化对于研究语言的共时状态并无多大助益。因为“语言状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我们认识共时的状态,不是由于研究了物体,即历时的事件,正如我们不是因为研究了,甚至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不同种类的物体,就会对投影几何获得一个概念一样”{31}。而从共时的角度看,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声音与思想通过差异而区分为一个一个的单位,再在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是任意的,没有理由,无需理由,也找不到理由。“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2}而且,不仅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能指与所指本身也是任意的。人的发音器官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有些音段成为语音,有些则没有成为,根本无原因可寻。另一方面,思想未被划分之前,也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33},语言通过差异将它划分为一个个的单位,成为所指。这些所指为什么要这样划分,一个特定的所指中为什么要包涵这些意义而不包含那些含义,也是无原因可寻的。“如果词的任务是在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那么,不管在哪种语言里,每个词都会有完全相对等的意义;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34}比如,中文的“人”,《新华字典》给出四个义项:(1)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2)别人;(3)指人的品质、性情;(4)指人的身体。基本上围绕人的本意展开。英文中对应的词“man”则除了人的本意之外,还有人类、男子汉、士兵、老兄、伙计等意思。“be man”,并不是说“是人”,而是说“像个男子汉”,“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概”。至于中文的人和英文的man所包含的内容为什么不同,是没有理由可说的。因为“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选择什么音段表示什么观念也是完全任意的”{35}。即使是一般人认为可以解释的象形文字,也是任意的。一个像马的能指,也可以说像驴,用它来表示马而不是驴的意思,仍然是任意的,说不出理由。在索绪尔看来,“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36}。索绪尔的相关论述给我们许多启示:
其一,语音与文字的关系不应从历时的层面而应从共时的层面考量。在语言中,变化是永恒的。在历时的层面,语音与文字的关系的确有许多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但是从历时的层面看,语音和其表征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变化的。“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别的人文制度——习惯、法律等等——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以事物的自然关系为基础的;它们在所采用的手段和所追求的目的之间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适应。甚至服装的样式也不是完全任意的:人们不能过分离开身材所规定的条件。相反,语言在选择它的手段方面却不受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们把任何一个观念和任何一连串声音联结起来。”{37}在时间的长河中,语音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固定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共时的角度把它们作为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应因语音和文字关系中的一些历时因素而将它们割裂开来。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实体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的,如果只保持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这一实体就将化为乌有”{38}。那么,在语言的能指中,能将语音和文字分开并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的系统之外吗?
其二,语音与文字的关系不应从外部而应从内部来考量。索绪尔认为,“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39}。所谓内部的,就是处于系统之中,并能直接对系统产生影响的。反之,则是外部的。作为语言能指的两种不同的表征方式,文字和语音是可以分开单独使用的,这可能造成日常语言和书面语言一定程度的脱离,不同的时间、地点、使用者对两者不同的侧重等现象,但这都是外部的,不会对语言系统产生影响。比如人们经常谈到的言文分离现象。准确地说,言文分离并不是语音与文字的分离,而是日常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分离。但“日常语言”也有文字,可以用书面表达出来,“书面语言”也有语音,可以诵读出来。因此更准确地说,也不是日常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分离,而是日常语言和某种“文献语言”的分离。由于文字与语音的变化并不完全同一,文字以及由文字构成的文献将一定时期的语音、语法与词汇等固定下来,使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未能随着日常语言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形成建立在一定的文献的基础上的“文献语言”。但是这只是语言的历时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共时层面的问题。在共时层面上,日常语言是一个语音、文字和意义的有机组合而形成的完整的系统,其意义体系既可通过语音(口头)也可通过文字(书面)表征出来。而文献语言也是一个由语音、文字和意义的有机组合而形成的完整的系统,它的意义体系也可既通过语音(口头)又通过文字(书面)表征出来。在各有自己的系统这一点上,一种语言中的日常语言和文献语言同两种不同的语言比如汉语和英语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日常语言和文献语言是同源语言,它们是同一种语言中两个不同的子系统,严格地说,它们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当下形态和保存在文献中的这种语言的历史形态{40}。因此,不能将日常语言和文献语言中的语音和文字进行对比,这会造成语音和文字分离的错觉。如杜牧的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在唐宋时念“xia”,现在普通话念“xie”。从共时的角度看,唐宋时的“斜”与“xia”是一个统一体,现在的“斜”与“xie”是一个统一体。如果拿唐宋时的读音与现在读音进行对比,我们就觉得“斜”字的读音变了,文字却没有改变,从而得出文字和语音是可以分离的结论。其实这只是一个错觉,因为在共时的层面上,“斜”这个词的语音和文字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其所表达的意义也都是一样的,即“不正,跟平面或直线即不平行也不垂直的”。
其三,语言是任意的,这不仅是说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是任意的,它们的联结是任意的,也意味着能指的两种表征形式,语音和文字的联结也是任意的。索绪尔说,“字母t和它所表示的声音之间没有任何关系”{41},同样的道理,中文字“树”与它所表示的声音“shu”之间也没有任何自然的或逻辑的联系,它们之所以联结在一起,组成“树”这个词的能指,完全是任意的,是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固定的。而从共时的角度看,既然文字与语音是一个结构的统一体,那么它所表征的所指与语音所表征的所指也就必然是一致的。索绪尔认为,“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42}。文字与语音的联结,它们的结构共同体也即能指与所指的联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慢慢地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上,它们之间的联结却是固定的、不可分割的、完全对等的。这实际上是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基本思想之一,只是他把文字排除在外。而我们认为,这种排除是没有道理的。文字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语言符号能指的另一种表征形式。听觉形式的语音和视觉形式的文字共同构成语言的能指,同时共同表征着语言的所指。在共时的层面上,它们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看法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语言实践中得到验证。在日常生活与阅读实践中,语音与文字这两种能指的表征形式,我们只要把握了其中一种,也就同时把握了另外一种,以及与它们联系的所指。
索绪尔虽然否定文字和语言是同一个系统,但实际上他并未否认在共时的层面上,语音和文字的一体两面的关系。他说,“每个音响形象也不过是若干为数有限的要素或音位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号把它们唤起。正是这种把有关语言的事实固定下来的可能性使得一本词典和语法能够成为语言的忠实代表;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43}。文字能把有关语言的事实固定下来,成为语言的忠实代表,只有在它和语音完全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做到。
我们可以设想现在的一部文学作品,比如莫言的《蛙》。这是一部用文字写下来的书面文学作品。从历时的角度看,它的以文字为载体所表征出来的语言肯定与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以前的汉语不同,也可能与几百年后的汉语不同,但是我们能说它与现在的汉语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将构成这部作品的语言用文字写出来或用语音读出来会有什么不同吗?显然没有。《蛙》的语言不管是用文字表征出来还是用语音表征出来都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互相包含、不可分割的。当然,“看文字”和“听语音”的感受和对作品的把握会有所不同,但那是由听觉系统和视觉系统的差异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语音和文字之间存在什么差异或结构上的缝隙。
由此可见,语言的能指有语音和文字两种表征方式,由于表征方式的不同,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无法改变两者之间的联系的任意性,也无法破坏两者在共时层面的有机统一性。因此,文字不是外在于语言的另一个系统,它就在语言之中。研究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可以通过研究文字与图像的关系进行,研究文学也可通过研究文字进行。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现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科学主义始终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追问真相的冲动也常常是人文学科进展的主要动力”{44}。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对中国文艺理论特别是语言论文论有着重要影响{45}。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语言能指中语音与文字两大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是理解文学并进而理解文学和艺术关系的基础。因为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弄清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才能弄清将文学用文字表达出来与用语音表达出来之间的区别,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讨论文学与艺术的关系。这是否也是一种对“真相”的追问呢?在这方面,本文愿做引玉之砖,期待专家与读者更深入的探讨。
注 释:
{1}赵敬鹏:《再论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6-158页。
{2}{3}{5}{6}{7}{8}{9}{10}{14}{15}{16}{18}{19}{21}{22}{24}{25}{29}{30}{31}{32}{33}{34}{35}{36}{37}{38}{39}{41}{42}{4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1页,102页,第157页,158页,第33-34页,第164页,165-166页,第212页,第141-142页,第60页,第37页,166页,第48页,第56页,第49页,48页,第81页,第157-158页,第168页,第46页,第158页,第47页,第131页,第319页,第127页,第102页,第157页,第162页,第166页,158页,第103页,第113页,第146页,第46页,第166页,第108页,第37页。
{4}赵敬鹏:《再论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8页,注2。
{11}张巨龄:《研究汉字不能搞独尊》,《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日第5版。
{12}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
{13}参见德里达:《论文字学》第一部分第二章,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17}其中为苖、壮、布依、哈尼、僳僳、侗、佤、黎、摩梭、布朗、赫哲等民族制定的是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为白、独龙、土家、羌、基诺等民族制定的是拼音文字方案。
{20}《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收有一则赵元任先生用几乎同音的许多字编出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持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光靠语音,根本无法使意思得到明晰的表达。
{23}语言的成熟与否并不意味与语言相联的文化或文学的高低。《贝奥武甫》产生时代的英语肯定没有莎士比亚创作时期的英语成熟,但这并不意味史诗《贝奥武甫》一定低于莎士比亚的剧本。因为衡量二者的标准不同。语言的成熟与否取决于它能否准确、细微、明晰、复杂地表达思想,而文学的优秀与否则取决于它能否生动、深刻地表现出它所产生的时代,能否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表达出真实、新颖的思想与情感。文学与生活范式紧密相连,某种生活范式消失,与这种生活范式紧密相连的文学类型也就不会再产生,但这种类型的文学并不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魅力。参看赵炎秋:《生活范式与文学类型——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原因再探》,《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8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
{26}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页。
{27}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页,第8页。
{28}李梵编著:《汉字简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第4页。
{40}自然,文献语言与日常语言并不是隔绝的,它与日常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日常语言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日常语言,但它语言系统是过去某一或某些时期的,是建立在过去存留下来的文献的基础之上的。
{44}李春青、袁晶:《“形式”的意义:近年来中国学界形式主义文论研究之反思》,《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
{45}肖翠云:《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形成与确立》,《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
Language and Characters:The Fourth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of Language
and Image from the Angle of Arts
——Reread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ZHAO Yan-qiu
Abstract: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matter and psychology in speech sound. The psychology aspect of speech sound is the“image of sound”. But in the two aspects of speech sound,the matter is main aspect,and the psychology is subordinate which is the reflection of matter aspect in the humane psychology. Only in this sense,can speech sound equate to signifier of sign.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that Saussure thought characters is another system of sign out of the language,but the three seasons are not enough to prove the characters is another system. The relation of speech sound and character is arbitrary. They are a organic unity,and the sense or the signified that they express is completely in line. Therefore characters is an organic integrant of language,one of the two expressing form of signifier of language sign,study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n be done through studying characters.
Key words:language;speech sound;characters;signifier;signified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