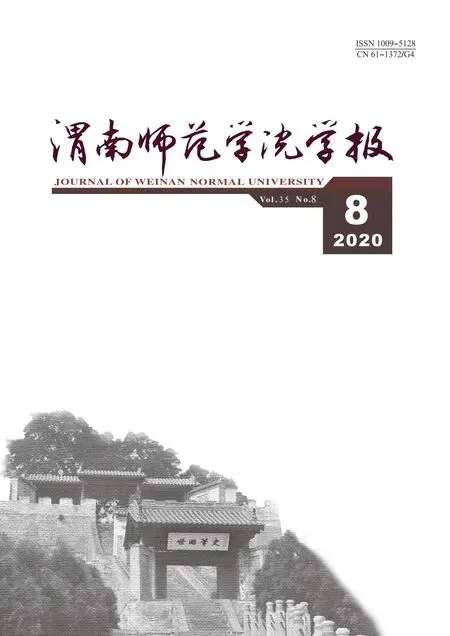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对比研究
——以《废都》两英译本为例
仵 雨 萌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近年来,随着文化的转向,翻译不仅仅涉及语言问题,更多地涉及文化问题。翻译不再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而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移植其最终目的是文化交流。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成功的译者除了要掌握两种不同的语言外,还必须具备理解两种不同文化的能力,即所谓的双语能力和双文化能力。至于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翻译中最严重的错误往往不是由于文字表达不当,而是由于错误的文化假设。”[1]56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是本土文学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多以描写陕西的风土人情为主。其长篇小说《废都》的第一个英译版本TheRuinedCity由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并于2016年在美国出版。葛浩文是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第一人,他的英译帮助诸多中国当代作家提升了海外影响力和知名度,由他翻译的贾平凹小说《浮躁》获得了美孚飞马文学奖。[2]84另一位翻译家是陕西翻译协会会长胡宗锋教授,由他带领的翻译团队已经翻译并出版了贾平凹的多部作品。目前,由其翻译的《废都》英译版本TheAbandonedCapital已经完成并即将出版,笔者将以其最新的手稿为例进行研究。
一、文化图式
文化图式理论是由图式理论延伸出来的一种比较新的理论。“图式”源于希腊语。1781年,德国哲学家康德首次提出了这个哲学概念,强调了现有知识对信息传递的重要性。他指出,当新的信息和思想与个人的已知信息相关联时,它们将是有意义的。[3]7文化图式理论解释了文化是如何呈现的,并让人们了解如何使用头脑中已有的文化知识概念。在研究文化图式时,语言学家尤尔提出文化图式是指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对特定事件形成的认知结构。[4]15作为图式理论的一个分支,文化图式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应用较为广泛,尤其是在翻译领域。自1998年彭开明首次将“图式”引入翻译研究以来,该理论在国内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刘明东教授在2003年对文化图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文化图式是人脑记忆中的文化知识结构,它可以通过现有的知识结构来理解和认识,并形成新的文化认知模式[5]30。它允许并帮助个体记忆、更新和存储文化知识,同时利用存储的知识结构对正在经历或未来将经历的事件进行解释、分析和表达。
语言与文化相互交织,紧密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体现了文化的内涵,文化又影响制约着语言。因此,对于译者,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无疑是难点。[6]13由于语言承载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在文化翻译中要遵循以下原则:在准确传递文化信息时,要尽量保留源语中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在目的语读者明显不能接受的情况下,译者应采用灵活的表达方式,根据源语的主题和英语版本的目的和功能,调整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7]26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是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和比较研究,这就要求译者在考虑语言意义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语言的文化意义。
(一)解码
刘明东教授提出了翻译是对文化图式的翻译的概念,并解释说图式翻译的过程包括对原文本的图式进行解码和对目标文本的模式进行重新编码。[5]31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根据自己已有的模式储备对原文进行解码,然后对目标文本的模式进行重新编码,最后生成功能相当的目标文本。并且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解码和再编码通常并不明显地相互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文化图式对译者解码原文本起着重要作用。学界普遍认为,在翻译文化图式的过程中,首先要了解源语图式,将其输入并保存到大脑记忆中,然后进行信息处理。因此,对于译者来说,加强对文化图式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翻译就是文本与译者之间的交流。对于译者来说,翻译的核心任务是构建“图式文本”,即对原文本进行准确解码。所以如果没有正确的图式,译者将无法准确解码文本。
(二)再编码
对目标文本进行适当的再编码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译者对文化图式的重新编码是否有效,取决于目标文本能否帮助目的语读者获得源语文化的知识和信息。为了减少再编码失败案例的数量,译者必须在译文中提供尽可能多的线索以激活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这与翻译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刘明东教授认为,文化图式是可以翻译的,并且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有效翻译,即A-A、A-B和A-Zero方法。[5]30前两种方法是利用目的语读者已有的文化图式,使目的语读者可以立即接受新的文化图式;第三种方法是丰富和发展目的语的文化图式,使目的语读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接受新的文化图式。
A-A法是指利用目的语中已有的文化图式,准确、全面地表达源语中的文化信息,从而达到翻译源语文化图式的目的。这种方法可以使目的语读者很容易理解文本。然而,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个体,即使在思想上有一定的默契,他们的表达方式也往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利用目的语不同的文化模式来调整译文,以表达源语的文化信息,即A-B法。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差异,有时一种语言中存在的文化图式在另一种语言中是空缺的。因此,为了使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应采用A-Zero法进行翻译,即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图式进行翻译的方法。
二、两英译本对比分析
翻译中的文化图式主要包括三类:文化图式重合、文化图式冲突和文化图式缺省。
(一)文化图式重合
当认知图式与当地文化相关联时,认知图式就会被赋予该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当译者心中有了图式,对源语的理解就容易被激活和填充。在图式的运用下,译者能更好地理解和处理目标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每个个体,即使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但只要他们经历过相同或相似的事件,就会对世界产生相似的理解,形成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图式。也正是这种文化模式,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群体的个体能够相互沟通,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提高不同语言的文化水平。同时,它使译者能够通过文化图式将源语准确地翻译成目的语。
(1)一株香椿树下有三间厦房。[8]43
胡:Under the Chinese toon tree, there were three rooms.(1)胡宗锋:The Abandoned Capital(胡宗锋教授于2018年将其翻译的《废都》英译版The Abandoned City手稿给予笔者进行相关研究)。
Chinese toon tree (Chinese: xiangchun; Latin: toona sinensis) is a member of the mahogany family of trees. Its young leaves can be eaten as a vegetable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lant can be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葛:A curtain hung over the doorway, which lay in the shade of a Chinese toon tree.[9]36
文化负载词“toon tree”指的是一种植物,即红椿树,也就是香椿树。在翻译时,两位译者都采用了A-A法,并在译文中加上了“Chinese”的前缀,易于读者接受。而胡宗锋采用了加注的翻译策略,使具有目的语文化的读者更容易理解这种树在中国的类型和功能。这些细微的变化并不会影响英语读者对原文中文化负载词的理解。
(2)庄之蝶一直坐在那里,气得脸色发青……[8]227
胡: Butterfly Zhuang had been sitting there with a blue face.(2)同上。
葛: Zhuang, who was sitting there looking stern…[9]150
作者在文中用“嘴脸铁青”“脸色发青”等词语形容主人公庄之蝶处在非常生气的状态。两位译者分别用了“blue”和“stern”进行翻译。英语图式中的“blue”可以形象地用来指人被气得脸色发青、发紫,而“stern”则可以指某人很生气或严肃。因此,胡宗锋和葛浩文用A-A法成功地将其转化到英语文化图式中,使西方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状态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二)文化图式冲突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群体,因此文化必然会随着不同的群体产生差异。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民族信仰、风俗习惯,从而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汉语和英语在思维模式上有明显的差异性,二者的表达方式有时看似相同,但其深刻的含义却未必完全相同,有时甚至会出现文化冲突。《废都》中就存在大量的文化图式冲突的文化负载词,译者如何灵活地运用翻译策略才能使目的语读者真正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关键。
(3)听到那堆人里有人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就是这小伙儿!”[8]102
胡:He heard someone say: “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is sure to come. The guy is coming over now.”(3)同上。
葛:“Speak of the devil,” someone said. “That’s him.”[9]73
几乎所有与汉语相关的语言文化负载词都属于文化图式缺省,因为汉语和英语在表达方式和扩展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该俗语却是文化图式冲突的典型例句。西方历史上没有“曹操”这个人物,所以两位译者采用A-B法将中国的文化图式“曹操”转换成了英语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devil”。事实上,这个成语在18世纪初就很流行。当时有一句迷信的话说“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shall appear”,意思是如果你提到魔鬼,魔鬼一定会出现;后来简化为“speak of the devil”。所以在文化图式冲突的情况下,胡宗锋和葛浩文都能够将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图式成功地转化为英语图式。
(4)编辑部果然通知周敏去打杂,好似旱六月落了白雨。[8]19
胡:The editorial board expectedly informed Zhou Ming to do odd job there, which was like a snow fall in dry June for Zhou.(4)同上。
葛: Zhou Min received word from the editorial office to report for work. The news was like a rainsquall on parched summer land.[9]21
在汉语中,文化图式“白雨”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雨如白珠,形容雨势很大;二是冰雹的别称。“旱六月落了白雨”的字面意思是在干旱的六月,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在文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人物周敏终于梦寐以求得到了在编辑部打杂的工作,这个消息就像及时雨一样。因此,葛浩文将“白雨”翻译成“a rainsquall”是更符合原文含义的,身为美国人的葛浩文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5)墙这边说:“是如莲的喜悦吗?一墙之隔,两个世界,我倒羡慕你们……”[8]8
胡:Over the wall he asked, “Is it the delight of a lotus flower. Only a wall between us, but there are two worlds. I admire you…”(5)胡宗锋:The Abandoned Capital(手稿)。
葛:This side said, “Is this the happiness of Nirvana? We are separated only by a wall, but live in two separate worlds. I envy you so…”[9]14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教派非常多。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对与佛教有关的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理解可能略有不同。在中国,佛教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所以在翻译时很难将中国特殊的文化图式移植到其他文化图式中。“如莲的喜悦”是用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喜悦。其中的“莲”与佛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佛教的象征,是许多美好、圣洁事物的隐喻。但如果用“a lotus flower”一词来形容“莲”的字面意思,目的语读者未必能够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葛浩文对该词的翻译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转化,即采用了A-B法将其翻译成了英语读者更能够接受的文化图式“Nirvana”,即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一般指通过修持断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佛教认为,信佛的人,经过长期“修道”,即能“寂灭”一切烦恼,“圆满”一切“清净功德”。这种境界,名为“涅槃”。Nirvana还可以表示“无忧无虑的境界、天堂、极乐世界”。因此该图式更能够准确地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6)那个王婆婆是来过几次,还送了老太太一副黄布裹肚兜儿。[8]149
胡:Old Granny Wang came over several times. She even sent a yellow cummerbund for her mother.(6)同上。
葛:Granny Wang had come several times and brought over a yellow stomacher.[9]100
在中国文化中,“裹肚兜儿”是一个与衣服有关的独特文化图式,它是一种带有刺绣图案的菱形内衣,以保护胸腹。在《废都》的两个英文版本中,胡宗锋和葛浩文采用A-B法分别使用了英语文化图式“cummerbund”和“stomacher”,使“黄布裹肚兜儿”更容易被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但根据《韦氏高阶英语词典》的解释,“cummerbund”是一种宽大的腰带,常与单排扣礼服夹克或燕尾服搭配使用,而“stomacher”则是一种带有刺绣或装饰性珠宝的胸饰,在15—16世纪男女都可使用,后来才成为女性专用的配饰。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负载词“黄布裹肚兜儿”和它相对应的两个英译名词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形态和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宗锋和葛浩文都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没有准确地表达出这个词的含义。
(三)文化图式缺省
英语和汉语都有着各自的演变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出了丰富的词汇,形成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文化的发展和融合中,它们也形成了具有文化内涵的俚语和习语,这些都极大地体现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文化图式缺省是指在一种文化图式中存在,但在另一种文化图式的认知中不存在,因而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当一种文化中特有的事物或文化形象成为其他文化的文化图式缺省时,人们的记忆就会因为没有相应的空缺而无法激活该文化图式,从而导致不同文化间的跨文化交际失败。《废都》是一篇具有陕西地方特色的长篇小说,其中有大量的属于文化图式缺省的文化负载词。方言词汇蕴含着独特的内涵和文化因素,使其充满了浓厚的陕西地域文化色彩[10]7,这就要求译者在图式缺省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翻译策略使得西方读者理解文本。
(7)各浮雕一对麒麟。[8]43
胡:Each bore a pair of qilin in relief.(7)胡宗锋:The Abandoned Capital(手稿)。
A qilin is a mythical Chinese creature, the nature and appearance of which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 through history. The qilin in Zhao’s residence are likely to follow the dominant latter-day representation, which showed them as scaly-skinned beasts, with a lion’s tail, a dragon’s head, antlers and hooves. They were frequently depicted close to entrance doors as they were thought propitious for the arrival of noble figures or teachers. The qilin was said to spread “tranquility” (rui) through the residence.
葛:A pair of unicorns in relief decorated the high bluestone gate pier.[9]36
在中国神兽谱系里,麒麟、凤凰、玄龟和龙是最高等级的团队,《礼记》称之为“四灵”,而麒麟则居“四灵”中的首位。古人视它为神宠、仁宠,是吉祥的象征。对于这种特殊的中国文化图式,胡宗锋采用了音译法的翻译策略并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即“麒麟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生物,它们是有鳞皮的野兽,有狮尾、龙首、鹿角和蹄子。麒麟经常被描绘处在靠近大门的地方,因为它们被认为是预示着贵族人物或教师的到来。麒麟据说能给住宅带来安宁”,使英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它的含义。但葛浩文却用存在于欧洲神话的英语文化图式“unicorn”,即“独角兽”来进行文化转换。事实上,这两种神兽的来源、外形以及象征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葛浩文在翻译文化图式时出现了偏差,而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胡宗锋更能灵活地运用翻译策略,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中特有的文化传递。
(8)周敏说:“得了得了,钟主编是什么人,你别鲁班门前抡大斧!”[8]323
胡:Zhou Min said: “Ok, enough of this. You know who Editor-in-Chief Zhong is, so don’t wave your axe before Luban the master carpenter.”(8)同上。
Luban the master carpenter was an inventor and wood-worker, often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Chinese carpentry.
葛: “That’s enough,” Zhou Min said. “Don’t you know who Mr. Zhong is? Why show off for him?”[9]207
《废都》中有许多具有陕西地方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如果直译,西方读者必然理解困难,并会引起读者的困惑和不解。于是葛浩文采用意译法,即从内容和意义出发, 将这些文化负载词翻译成读者所熟悉的意象和表达方式。但是,作为一个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译者,他有时也无法将中国文化图式准确地转化成英语文化图式。如“班门弄斧”并非“show off”,即“炫耀”的意思那么简单。而胡宗锋采取的是直译加注的方法,通过字面翻译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辞风格及组句形式,并且有非常详细的注释进行补充说明,更大程度上做到了忠实原文,易于读者理解。
(9)山门口贴着一张红纸,上写着:“初一施放焰口法令。”[8]483
胡:On the gate there was a red notice, which read: “On the 1st of the month we will issue rules for the offering of food to starving ghosts.
Offering of food to starving ghosts (Fang yan kou) is a traditional custom and rite in Buddhism. Yan kou is said to be an ugly ghost with a flaming mouth and a bony body.(9)同上。
葛: A sheet of red paper was pasted on the entrance: The Yankou Incantation will be recited on the first of the month.[9]303
“焰口”是佛教用语,形容饿鬼渴望饮食,口吐火焰。寺庙中的和尚们向饿鬼施食就叫“放焰口”。胡宗锋将“焰口法令”意译为“rules for the offering of food to starving ghosts”,并且在注释中详细解释这是一种在佛教中给饿鬼施食的传统习俗和仪式,尽可能地为英语读者描述其文化内涵。葛浩文采取A-Zero法将其译为“The Yankou Incantation”,选择了创造新的文化图式,并且将这一文化负载词用两种翻译策略进行翻译,即音译加直译。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焰口”进行恰当的解释和注释,使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的英语读者无法深刻地理解他的意图和这个词在佛教中的深层含义。因此,前者在传播中国文化图式的过程中更为准确和到位。
(10)青龙、玄武、白虎、腾蛇、勾陈、朱雀。[8]344
胡:Black dragon, Turtle and snake, White tiger ghost, Flying snake,The polar stars and Scarlet bird.(10)胡宗锋:The Abandoned Capital(手稿)。
葛: Green dragon, black turtle-snake,white tiger, winged snake, unicorn and red phoenix.[9]22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的道教占卜中有六种古老的神话生物,即青龙、玄武、白虎、腾蛇、勾陈和朱雀。而每一种生物都有一定的吉凶含义,涉及家庭、事业、财运等各个方面,用来辅助占卜的活动。这些带有宗教文化色彩的文化负载词相当复杂难懂,即使是具有源语文化背景的读者也未必能够准确理解这些含义。因此,在文化图式缺省的情况下,如何让英语读者接受并理解这些文化词汇,对译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挑战。胡宗锋和葛浩文都选择了直译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的语体风格和文化色彩,但是在传递这些词汇所承载的中国文化时就稍显欠缺,若加上注释进行补充说明会更易于读者理解。
三、翻译策略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通过对《废都》中这10例文化负载词英译比较可以看出,在文化图式重合的情况下,两位译者在解码的过程中都能够找到相应的英语文化图式来代替汉语文化图式。虽然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但并不影响英语读者的理解。对文化图式冲突中所包含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比第一种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对于这类文化负载词来说,汉语文化图式的文化内容和内涵与英语文化图式有所不同。所以,两位译者应该充分考虑小说中文化负载词的具体含义,然后用恰当的方式解读其汉语文化图式。两位译者都采用的方法是利用现有的英语文化图式对汉语文化图式进行转换,使英语读者能够更好地接受汉语文化负载词。
经过对比分析发现,在对文化图式缺省的情况下翻译时,两位译者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是对文化负载词进行字面翻译,即直译。几乎所有与方言和俗语有关的汉语语言文化图式在英语图式中都找不到,因此他们会选择在直译的过程中创造和发展新的英语文化图式,为读者简单地阐述和提供文化负载词背后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及其内涵。
虽然两位译者在翻译小说《废都》的文化负载词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翻译策略上的差异更值得注意,特别是文化图式冲突和文化图式缺省这两种情况,最能体现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同理念和技巧。首先,当译者对汉语文化图式进行解码时,若不能完全表达出汉语文化负载词的深层含义,或者无法在英语文化图式中找到合适的词语来翻译汉语文化负载词时,胡宗锋就会采用大量加注释的翻译策略来减小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没有任何注释的葛浩文在其英文版本中就无法准确地翻译文化图式,使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的英语读者不能清楚地理解他的意图,从而无法成功实现文化图式转换的目的所造成的。其次,胡宗锋能够抓住作家的写作目的,找出与汉语文化负载词相一致的文化图式,而葛浩文稍显欠缺。比如,在一些文化中,会用动物来描述人的形象或特征。在汉语文化图式中,经常用文化负载词“驴子”形容某人很笨拙,头脑简单。然而,作为一个美国人,葛浩文并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积淀,无法深刻理解其含义,所以当文化图式发生冲突时,他选择从字面上将其翻译成“a mule”。相反,来自中国的胡宗锋则用双关语“an ass”来充分表达其在作品中的真正含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存在差异性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所造成的。首先,他们对中英文化图式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胡宗锋是一位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译者,同时具备非常高的英译水平,他的版本在解读文化负载词时更忠实于原文。这也是作者贾平凹一直强调的。而葛浩文来自美国,即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但没有源语文化的熏陶,他的双文化能力就稍显欠缺。其次,胡宗锋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和翻译陕西作家小说,就是为了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使陕西文学能够真正“走出去”。葛浩文的翻译也起到了推介中国文化的作用,但是他更强调小说的可读性,因此对部分文化负载词未提供必要的解释性信息,可能会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或不解。
四、结语
目前,对翻译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分析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层面和文本比较,而是要从翻译的角度出发。翻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相互交流、碰撞的过程。对于一个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译者来说,翻译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传递。因此,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对源语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要对目的语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对文化因素处理不当,就会造成误译。正确翻译源语文化因素,对翻译是否成功具有重要意义。胡宗锋和葛浩文两位译者都达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但胡宗锋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能够采取包括直译、意译和直译加注等翻译策略,使英语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和媒介。无论是源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的译者,都应该站在文化平等的立场上,以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为己任,实现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