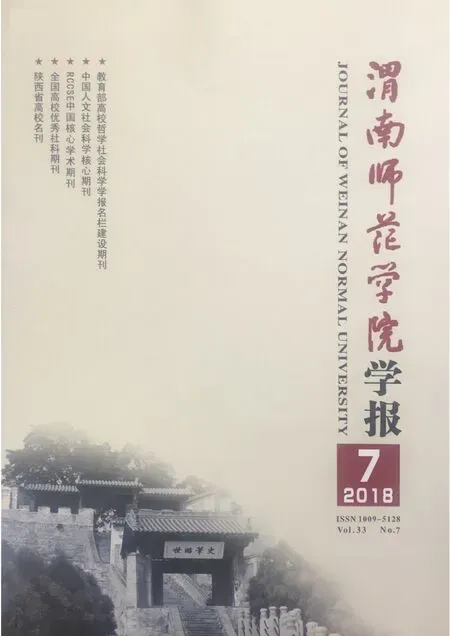论“内圣外王”的关系建构及其哲学反思
韩 文 娟
(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中国古代哲学各学派几乎都讲“内圣外王之道”,中国古代的哲人也都以“内圣外王的人格”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1]138。其中,尤以儒学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先秦原始儒学的思想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内圣外王”主张和充实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话,那么,宋明新儒学则是自觉地以“内圣外王”来标帜儒学,而现代新儒家则是自觉地接受宋明新儒学的“内圣外王”思想,在固守“心性之学”的前提下,根据时代之需来建构容纳科学知识和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概略可见,“内圣外王”不仅是儒家自古及今发展中一以贯之的学术主张,还是儒学宏观内容的基本论域或建构框架,更是儒学理论建构中基本的哲学命题。然而这个哲学命题,其自身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圣”与“王”之间搭建的关系的合理性并没有经过证明。尽管它是儒学甚至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但也仅仅只是一种哲学预设,要经过怀疑和批判来检验其合理性。
一、“内圣外王”的理学诠释
“内圣外王”之说,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庄子》在分析“道术”由“一”分裂为“百家之说”时说:“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这里的“内圣外王”,明显是被视作诸子百家学说分裂前所共同的学说而提出的。但什么是“内圣外王”?《天下篇》以及《庄子》一书并没有给出具体解释。近现代以来,学人根据《天下篇》中“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所传达的思想,将“内圣外王”解释为:认知“道”来修身,运用“道”来治世。*学人都认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中的“一”是“道”。据此推理“内圣外王”就是“内圣:指将道藏于内心。外王:指道显于外王,用道治理天下。”见王世舜《庄子注译》,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456页。尽管由于学人对“道”的理解不完全相同,而对如何修身和治世存有分歧;但是“内圣外王”涵盖的是修身与治世两方面内容,并认为这两方面内容之间有某种紧密的联系,则是非常明确的。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将个人的修身与社会的治理联系起来。
在看到“内圣外王”命题所传达的思想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这一命题所表达的思维模式。这种“内”“外”关系与其说反映的是主体在道德和政治之间一种主观的关系建构,毋宁说是“圣”“王”之间本来蕴涵的一种“内”“外”关系。要明白这一点,有待对“圣”“王”“内”“外”内涵的具体分析来说明。本质地看,“内”与“圣”、“外”与“王”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具有一致性。如果要强调其间的区别的话,“内”与“外”侧重于实践的路径,而“圣”与“王”侧重于实践的目标;实践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或规范着实践路径,即“圣”“王”本身具有这种“内”“外”的意涵。
尽管“内圣外王”命题在先秦已经出现,但是并没有受到当时以及后来儒者的重视,直至北宋之时,理学家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才重新提起了这一命题。据《宋史》记载,程颢在评价理学家邵雍(1011—1077,字尧夫,学者称安乐先生)的学问时,有这样的说辞:“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程颢认为邵雍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学”,他既没有说明什么是“内圣外王”,也没有解释邵雍之学何以是“内圣外王之学”。所以,我们仍然无法究诘“内圣外王”的具体内涵。但问题是程颢为什么仅用“内圣外王”来评价邵雍的学问?要知道在程颢稍前,有胡瑗(993—1059,字翼之,学者称安定先生)、孙复(992—1057,字复明,学者称泰山先生)和石介(1005—1045,字守道,学者称徂徕先生)等被现代学人称为“理学三先生”的理学先驱;在程颢之时,尚有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学者称濂溪先生)和张载(1020—1077,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二位理学创始人。但程颢并不认为这些理学家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学”,而仅仅用之评价邵雍的学问。
然而到了南宋,理学家的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表现比较明显的是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学者称紫阳先生)。朱熹不但认为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而且试图将理学构建成“内圣外王”之学。他认为《大学》标榜的格、致、诚、正皆是“明明德之事”,而修、齐、治、平均为“新民之事”;并认为“明德为本,新民为末”[2]4。在朱熹的思想中,格、致、诚、正等“明明德之事”,其实“皆所以修身也”,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明明德之事”对应的就是“圣”,而相应地,“新民之事”对应的则是“王”。可见,朱熹的上述观点,已经在“圣”“王”之间搭建起了“本”“末”关系,即“本圣末王”。
朱熹在“圣”“王”之间搭建的“本”“末”关系,虽然总体来看,是继承了自《庄子》以来的“内圣外王”思想,但是他改变了“内圣外王”中“圣”与“王”的“内”“外”关系。“内圣外王”中“圣”与“王”的“内”“外”关系并不表示某种偏离或偏向,即没有偏向于“内”,也没有偏向于“外”,它只是强调“圣”“王”并重,应当兼顾,没有轻重之分。但是由于《大学》强调“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所以,在“明德”与“新民”的本末关系中,它明显是重本轻末的;那么,接受《大学》这种思想的朱熹,在建构“本圣末王”时,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视“圣”而轻视“王”。这也出现了“内圣外王”思想中重“圣”轻“王”的学术偏向。
朱熹“本圣末王”说,被其后学继承,进而发展出“体圣用王”说,这可以用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1178—1235,字实夫,学者称西山先生)以体用之维解读和诠释“内圣外王”来说明。真德秀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并进而说:“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用也。”[3]500显而易见,真德秀通过对《大学》的诠释,已经建立起了“圣”“王”之间的体用关系,可称之为“体圣用王”。
“体用”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就中国哲学史来看,在魏晋玄学中已经开始运用[4]149,而比较普遍的使用则在宋明理学时期。“体用”中的“体”一般表述实体,而“用”则相应地表示实体的属性或功能;而且在“体用”范畴的使用中,理学家多以之表示“体用不二”,而反对割裂“体用”。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5]689最能反映这种思想主张。真德秀以体用之维来理解和诠释“内圣外王”,从而使“圣”“王”具有体用关系,即“圣”是实体,而“王”是功用;或者说“圣”是“王”的内在依据,而“王”是“圣”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圣”“王”的“体用不二”是对“圣”“王”本末一体的继承,但同时它对“本圣末王”也有所发展。如果说本末一体仅仅是在一定时间条件下的一体的话,那么,“体用不二”则克服了这种时间上的限制,而实现了永恒的一体。另外,“体”和“用”是共时的,“用”不但不能离“体”而存在,“体”同时也需要“用”来彰显其存在性。显见,“圣”与“王”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加强,显得更为完善。
由于自元已降,朱子学成了官方学说,而且《大学章句》和《大学衍义》成了科举考试的范本,从而使得体用之维诠释的“内圣外王”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学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将“内圣外王”理解和诠释为“体圣用王”。另外,由于“体圣用王”是通过诠释儒家元典《大学》来阐发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人造成《大学》本身就含有“体圣用王”的错觉,从而导致学人们认为儒家本身就主张“内圣外王”之学,而且“内圣外王”之学本质就是“体圣用王”之学。这种认识一直沿承到现代新儒家。
二、“内圣外王”—“明体达用”
从体用之维来理解和诠释“内圣外王”,几乎是有元以来儒者的普遍思想。“内圣外王”蕴涵的这种体用关系,直到明清之际才得以显露,具体表现是明清之际儒者普遍提倡“明体达用”。晚明以来,阳明后学对现成良知的倡导造成儒学的日益空疏。拟补救这种学术弊端的儒者,重新确立儒家本来就标榜的“内圣外王”之学;然而,他们却是以提倡“明体达用”的学术主张来重新树立“内圣外王”之学的。
明清之际的儒者大都提倡“明体达用”,而对“明体达用”的表述,尤以被梁启超誉为“王学后颈”的李颙(1627—1705,字中孚,学人称二曲先生)最具代表性。李颙主张的“明体达用”,具体而言,是“明体适用”。他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6]120显见,李颙的“明体适用”表达的就是“内圣外王”。另外,李颙的“明体适用”就是明清之际儒者普遍高标的“明体达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二者都“以体用区分‘明道存心’的内学和‘经世宰物’的外学,以‘体’为精神之主导,以‘用’为应事之方术”;而且“都十分强调体用、内外之学的统一”[7]。李颙用“明体适用”来表达“内圣外王”,只是明清之际儒者提倡“明体达用”来表达“内圣外王”的一个典型。儒者普遍以“明体达用”来表述“内圣外王”,恰恰彰显的是儒者普遍以体用之维来理解和诠释“内圣外王”。
既然“明体达用”本质上就是“内圣外王”,那么,明清之际的儒者为什么不提倡早已被儒者普遍接受的“内圣外王”,而却要另辟蹊径来标榜“明体达用”?其实,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扩展“外王”的外延。对此,明清之际的著名程朱理学学者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晚号桴亭)说得很清楚,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时所以来迂拙之诮也。”[8]15
陆世仪强调理学或者说儒学要切于世用,即“达用”,他认为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外王”。之所以要提倡“达用”,而非“外王”,那是因为“达用”比“外王”外延广泛,更便于根据时代之需来吸纳相应的内容。我们知道,“外王”毕竟侧重政治,而“达用”还可以包容政治以外的内容,比如陆世仪所说的天文、地理、水利、军事等等。所以,明清之际的儒者乐于称道“明体达用”,尽管本质地看,“明体达用”就是“内圣外王”。
“明体达用”,或者说以体用之维理解和诠释的“内圣外王”,其“外王”(“达用”)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或接纳性,这在近代的“中体西用”思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中体西用”,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标榜“中体西用”论的学人认为“中学”与“西学”“体用不二”,而最终的目的是要用儒学的“外王”来装载“西学”。具体说来,就是洋务派要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具体措施纳入儒家“外王”的学说范围,嗣后的维新派又把“西用”扩大到了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们的这种做法与明末清初提倡“明体达用”的儒者的目的和手段如出一辙。同时,就理论而言,“中体西用”说本质上就是以体用之维理解和诠释的“内圣外王”,或者说“中体西用”本质地看就是“体圣用王”。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对“中体西用”的看法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9767显而易见,张之洞所谓的“中体西用”就是“体圣用王”。
学人无论是提倡“明体达用”,还是“中体西用”,都是在坚持体用之维诠释的“内圣外王”主张的前提下,根据时代之需扩张“外王”的外延。“明体达用”主张者力图将“外王”的外延由政治拓展到天文、地理、水利、军事,而“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则进而将“外王”的外延扩张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君主立宪制。随着“外王”的外延不断拓展,“内圣”的负担也显得愈来愈重,因为在“体圣用王”的思维模式中,“王”是“圣”的功用,前者是由后者开展出来的。如此来看,道德不但要开展出政治,还要开展出天文、地理、水利、军事,甚至还要开展出西方的科学技术,道德真的具有如此丰富的功能吗?这一问题在“中体西用”思潮涌动之时,被有识之士觉察。严复(1854—1921,字几道)就不认可“中体西用”,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0]559但是严复仅仅反对的是中西学问之间的体用架构,而并非“圣”“王”之间的体用关联。难道道德与政治之间就具有体用关系吗?这值得反思。
“明体达用”主张本质地看就是“体圣用王”,但是它又不同于后者。一方面就内容而言,“明体达用”重在强调“达用”,而“体圣用王”重在强调“明体”。自朱熹“本圣末王”思想传播以来,理学家一般都比较重视“内圣”而忽视“外王”,这种偏向发展至晚明的阳明后学达到了极致,他们站在现成良知的立场,高谈“满街都是圣人”,而忽略道德实践和经世致用,故而,明清之际儒者提倡“达用”的目的就在于呼吁理学家归回“外王”,重新重视道德实践和经世致用,从而补救当时儒学发展中出现的空疏无用的弊端。另一方面就思维而言,“明体达用”有以“用”为终极目标的倾向。诚如学人所指出“明体达用”中“明体并非终极目标,是为了转化为外王的功用,这就是达用。”[11]如果说宋代的“体圣用王”偏重“明体”,是在“用”的范围下对“体”的着重探究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明体达用”,则是在“体”的范围下对“用”的着重探究。
《庄子》提出的“内圣外王”,经过儒者创造性的诠释,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内容而言,一方面儒者将“圣”(得“道”)的内涵替换成儒家标榜的仁义之道,“圣”的本质就是德性和德行,而“内圣”就是通过心性修养从而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另一方面,儒者将“王”(以“道”治世)的内涵替换为儒家为政以德的仁政,“外王”就是以德治国,推行仁政。就形式而言,“圣”“王”之间并不明确的“内”“外”关系被儒者诠释为体用关系,使得“圣”必然开出“王”,而“王”必然根于“圣”,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割裂。
三、“内圣外王”—“返本开新”
宋儒倡导的体用之维诠释的“内圣外王”为现代新儒家自觉地继承,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返本开新”。“返本开新”主要是第二代新儒家“由儒学传统之‘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之现代‘外王’”[12]的学术主张。第二代新儒家“返本开新”,有一个让“地球人都知道”的宣告壮举。这就是1958年元旦,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人物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和徐复观在香港的《民主评论》上,联合署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对于“返本开新”,《宣言》中有如下表述:
我们说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该文后来收录在唐君毅《中华文化与当年世界》及周阳山编《当代研究与趋向》等书中。
《宣言》中“由其心性之学”自觉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后还要成为“政治的主体”以及“认识的主体”和“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的表述,就是“返本开新”。“本”指的是儒学传统的“内圣”,“新”指的是“新外王”。1979年,牟宗三于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上所作的《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讲辞中说:“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该文后来收录在唐君毅《中华文化与当年世界》及周阳山编《当代研究与趋向》等书中。该文后来收录在牟宗三《政道与治道》一书中,为增订新版之序言。《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及《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七——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均收录此文,但有近三千字被删去。这明确表明所谓“新外王”是指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
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中所标榜的“新外王”,即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五四”时期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并非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工艺技术,而且也包括与封建蒙昧主义相对立的科学思想;同样,“民主”亦不只是“自由、平等、博爱”和“法律面前,一切平等”的民主思想,还包括人民有参政议政权利的民主权利。[13]354-370新儒家仅仅强调科学技术,而遗弃了科学思想或者说是理性主义,同样,仅仅强调民主思想,而没有具体可供操作的民主权利,就此而言,“新外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外,现代新儒家提倡的以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为内容的“新外王”是由“心性之学”开展出来的或者说生发出来的。在他们看来,“心性之学”要“比科学民主对人类更为切身”,所以,无论他们提倡科学技术,还是民主政治,心性修养仍然是根本。以科学知识为例,他们提倡科学知识,那是以“仁心来提撕科学”,而且“一切科学之价值,都只是为了我们要发展此仁教”[14]156。科学知识不但是由内在的心性来生发,而且提倡科学知识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心性之学”,他们对民主政治的提倡亦复如是。显而易见,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完全沿袭的是前现代儒者所谓的“内圣外王”。这种继承是自觉的,牟宗三明确地表示:“‘内圣外王’一语虽出于《庄子·天下篇》,然以之表象儒家之心愿实最为恰当。”[15]7
正是由于现代新儒家提倡的“返本开新”,从本质来看,就是体用之维的“内圣外王”;所以,批评“返本开新”的学者几乎都拔本塞源地将矛头指向了“内圣外王”。张岱年不认同“返本开新”,原因在于“时至今日,王权久已废除了,再标榜‘内圣外王’,那就不符合今日的时代精神了”[16]917。无独有偶,余英时对“返本开新”的批评,也是抓住了“内圣外王”。他说:“儒学在现代的处境中已失去了这种全面安排秩序的资格,所以‘内圣外王’真成了‘已陈刍狗’,仅可供‘发思古之幽情’,不再有现实的意义了。”[16]917
余英时对“返本开新”的批评很类似于张岱年的批评。他们都看到了“返本开新”的本质——“内圣外王”,从而站在时代的立场,认为“返本开新”不存在赖以生存的时空。显见,余英时对“内圣外王”的批评与张岱年很类似,都是站在现实的立场,来批评“内圣外王”理论的过时性。
另外,也不乏学人对“内圣外王”命题自身的反思和批判,汤一介对“内圣外王”标榜的应将一切社会政治问题都寄托在个人的道德学问的提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原因在于他认为道德学问和政治事务是两个问题,他认为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是行不通的。[17]150-156显见,汤一介已经意识到了“圣”“王”之间的体用关系的不合理性。朱学勤以“老内圣开出新外王”[18]为题,来批判牟宗三等新儒家提倡的“返本开新”,并进而指出“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根本原因在于伦理或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假逻辑”,即由前者根本推理不出后者。至此,儒家搭建在“圣”与“王”之间的体用关系才真正引起了学人的反思和批判。
如前所述,儒家标榜的“内圣外王”,其实是“体圣用王”。“圣”“王”之间的体用关系只是宋儒的主观建构,并没有给出证明,所以体用之维的“内圣外王”纯属独断论。那么,“圣”与“王”之间是否具有这种体用关系?就需要后儒去论证,然而后来儒者却将之悬置起来,只是加以继承和运用,从而使“内圣外王”成了儒家哲学最基本的理论预设。那么,“圣”与“王”到底有无体用关系,或者说,道德与政治之间是否具有实体与功能的关系?无论从思辨和逻辑来看,还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宋明新儒家以体用之维理解和诠释的“内圣外王”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建构,搭建在“圣”与“王”之间的体用关系并非对于客观事实的正确反映,而仅仅只是儒者泛道德主义的一种理论表现。
当我们剔除掉“内圣外王”中附加的体用关系后,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庄子》提出的“内圣外王”?因为它毕竟展现了“圣”“王”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外”关系。李泽厚是这样解释的:“在以儒学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中,由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因素孕育政治因素的交融合一,使‘修身’与‘治平’、‘正心诚意’与‘齐家治国’亦所谓的‘内圣’与‘外王’呈现出两极性的歧异关系。”[19]270
这说明“内圣外王”中“圣”“外”之间的这种歧异关系,是由前古时期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沉淀和发酵所导致的。商代的祖先崇拜,据说有“希冀通过神权来巩固政权,达到神权和政治合一的目的”[20]135。这反映出商代的统治阶层已经有了“神权和政权合一”的观念。西周初期,当“周人将帝作为最高主宰,又赋予帝崇高的美德”时[20]161,“神权和政权合一”就自然成了美德和政权的合一。这就是庄子“内圣外王”主张的思想根源。可见,“内圣外王”其实是古老的文化基因——“神权和政权合一”——在遗传和变异中产生的一种深层的文化结构。显见,从哲学的视阈来看,“内圣外王”作为哲学命题,其体用关系缺失有效论证,从而显得该命题不合理或无效;但是就思想渊源来看,“内圣外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客观性。
四、结语
“内圣外王”作为先秦时的学术命题,经宋儒以“体用”之维诠释之后,被儒者未经批判地接受和继承,从而成了儒者的理论共识和儒学的基本命题。然而这种以“体用”之维诠释的“内圣外王”在“圣”与“王”之间建构的“体用”关系本身需要证明,不然,该命题就属于独断论,而对这一命题不加证明的运用也就只能视为一种理论预设。以理论预设为基础建构的理论体系是十分危险的。具体到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理论来看,这种理论自觉地以宋儒“体用”之维诠释的“内圣外王”为理论基础,而没有对“圣”“王”之间的“体用”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所以,当这种体用关系无效时,“返本开新”自然也就是无效的。这也就不难理解认为被宋儒附加的“体用”关系的“内圣外王”是一种“假逻辑”的学人,直接喊出“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当我们认为儒学是哲学,或者自觉地实现儒学哲学化时,对儒学思想史上的固有命题就不能不反思和批判,从而确定其理论的合理性或有效性。只有以这种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和方法来继承儒学,儒学才有可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5卷 [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 朱熹.大学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真德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4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 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 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J].哲学研究,1987(9):26-29.
[8] 陆世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2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0] 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张立文.内圣外王新释[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1(1):26-29.
[12] 李翔海.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99-105.
[13] 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14]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M].台北:台湾书局,1978.
[1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1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7] 汤一介.返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8] 朱学勤.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从《政道与治道》评新儒家之政治哲学[J].探索与争鸣,1991(6):40-50.
[19]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0] 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