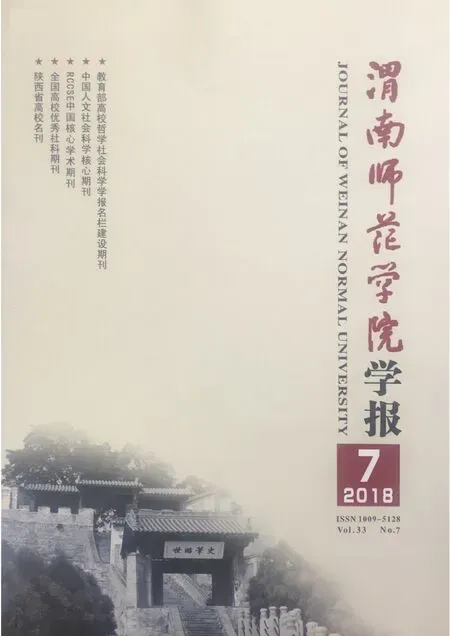贾平凹小说《秦腔》中的乡土文化批判与美学内蕴
张 伟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乡土小说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亦即其早期产生及演进过程中,中国的乡土小说逐渐形成了以鲁迅代表的写实派主流乡土小说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写意派非主流乡土小说两大流派。前者希望以现代文明来改造乡土文明的封建、保守与落后,治疗农民身上的自私、愚昧、麻木与奴性等精神创伤,后者则赞美乡村中的自然美,风俗美与人情美,赞美乡村爱情的纯净、美好,赞美乡土文明中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存方式。由此可见,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写实派与写意派就已分别展现了批判与守望两种不同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姿态,同时也形成了乡土小说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传统被打破,直至“文革”结束前,充斥于各种文学刊物中的所谓农村题材小说,大多属于图解政策,歌功颂德之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极左意识形态的烙印。这种农村题材小说由于缺乏真正的乡土气息与相应的美学风格意蕴,因而可否归入乡土小说的范畴,学界尚存争议,但它们中间很少有能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则并无疑义。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多灾多难的中国终于告别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农村实行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极“左”路线蹂躏下凋敝已久的农村重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因而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乡土小说诸如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张炜的《声音》、陈忠实的《四妹子》以及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等,大多洋溢着某种乐观向上的时代氛围,作家们为农村以及农民的精神风貌所发生的变化而欢欣鼓舞。惜乎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全面铺开且迅猛推进,城市化、商业化、全球化的浪潮来势汹汹,乡村的小农经济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乡土,成了在城市打工的所谓农民工,乡村因此再次变得凋敝萧条。与此同时,乡村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已呈土崩瓦解之势。作为中国当代小说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的大部分作品已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乐观明朗的色调,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大变革时代及城市化阴影下乡土文化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溃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于伦理道德溃败的大环境下的人的命运给予了极大的悲悯。贾平凹的长篇乡土小说力作《秦腔》的主旨即在此。
一、《秦腔》——一曲中国传统乡土文明的挽歌
《秦腔》所描写的清风街本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底蕴深厚,民风淳朴之地。儒家千百年来一直倡导的忠孝仁义礼智廉耻曾经就是清风街人们祖祖辈辈遵循不渝的为人处世原则。如夏家的天字辈就是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物,夏天仁为了挽救病重的母亲,跪地祈求上苍减去自己十年寿命,以换取病母的生命,结果母亲康复而自己果然英年早逝。夏天智深夜到两位哥哥的住宅旁埋下“大力丸”,希望以此保佑他们健康长寿。这一举动虽然不乏迷信成分,但其发自肺腑的兄弟友爱之情却让人感动。而且身为知识分子的夏天智不但热爱秦地数千年乡土文化的结晶——秦腔,还为之奔走呼号,希望重现秦腔当年曾经拥有的辉煌,至少不要走向彻底的没落。非但如此,夏天智还替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夏风买好了宅基地,希望他能落叶归根,延续良好家风。小说中老支书夏天义坚决反对占用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建农贸市场,并且不厌其烦地在儿孙辈以及年轻人中谆谆灌输应当热爱耕地、珍惜耕地的思想。为了在七里沟淤出一片新的耕地,夏天义甚至因山体滑坡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由此可见,清风街老一辈的人们不但恪守着传统的忠孝仁义之道及人伦观念,对于乡土以及乡土文化也有着一份深厚的情感。而下一辈中的白雪对于秦腔的痴迷以及为秦腔振兴事业九死不悔的奉献,也表现了对于乡土文化和精神家园的执着。毫不夸张地说,虽然《秦腔》中的清风街没有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那种人间仙境般的自然山水以及浪漫的田园牧歌情调,但它却以其朴实无华的特点而更像是中国数千年来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因而足以成为乡村人们的灵魂安居之所。但正如当代中国乡村的任何一个角落一样,当城市化、商业化以及全球化无坚不摧的浪潮来临之后,清风街的传统乡土文化也包括千百年来代代传承的乡土伦理道德观念终于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有许多表现,如夏天智的儿子夏风,就对乡土以及代表着乡土文化的秦腔毫无感情,公开声称自己“烦的就是秦腔”,甚至在大年三十不顾一切离家出走,冷酷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妻子白雪以及亲生女儿,此后一直待在省城,甚至不愿意回一趟故乡,直至父亲去世。而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儿媳,常常为了如何分摊赡养父亲的粮食而锱铢必较甚至吵闹不休,父亲死后又为了树碑钱该由谁出之事吵得不可开交,传统的孝道已经被彻底抛弃了。与此同时,赌博、通奸、嫖娼、卖淫、乱伦、贿选等各种丑恶现象也在民风淳朴的清风街泛滥开来。在《秦腔》中我们看到,清风街传统的乡村人伦观念、传统孝道、传统义利观念、传统婚姻观念几乎无不受到巨大冲击而濒于解体。而这也同样是我国当代乡村伦理危机的写照,正如有学者忧心忡忡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历一个从治理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换过程,乡村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伦理颓势。”[1]可以说,在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侵蚀污染下,清风街呈现的是一幅乡民的人格扭曲、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末日景象。道德堕落现象随处可见,乡村的传统美德荡然无存。商品拜物教把人与人之间原本真诚淳朴、古道热肠、守望相助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冷冰冰的利益交换关系。
在《秦腔》中我们还看到,由于年轻人纷纷前往城市打工,乡村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使得土地荒芜甚至杂草丛生,甚至夏天智死后连抬棺材的壮汉都凑不齐,以至于新任村支书夏君亭感慨万端地说:
还真是的,不计算不觉得,一计算这村里没有劳动力么!把他的,咱当村干部哩,就领了些老弱病残么!东街的人手不够,那就请中街西街的。[2]519
这也无疑反映了在强势的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农村已日渐凋敝的凄凉现状。而曾经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秦腔也已经陷入了日落西山的窘境。早在1983年,贾平凹在其散文《秦腔》中曾写道:“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农民“一生最崇敬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国家的领导人,一是当地的秦腔名角”。从上述描写可以看出当年秦腔家喻户晓,是何等的深入人心且广受欢迎,难怪作者贾平凹要由衷地感叹:“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动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她们的家乡交响乐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还能有别的吗?”秦腔是“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它曾让秦川大地上祖祖辈辈的无数农民为之悲,为之喜,为之欢笑,为之落泪,为之陶醉并引以为自豪,可以说是拥有异常深厚的文化渊源与无比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三十年以后,在清风街的第一家星级酒楼开业时,秦腔甚至竞争不过浅薄庸俗的流行歌曲,只好甘拜下风,黯然收场。在小说《秦腔》中,秦腔剧团响应政府号召送戏下乡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但在乡间巡回演出时却观众寥寥,最少时只剩下一个观众,而那个观众之所以留下来竟然是因为怀疑台上的秦腔演员偷了他的钱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纷争,这是何等尴尬的场景!看来秦腔作为一种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且曾深受百姓喜爱而风靡三秦大地的文化艺术真的气数已尽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夏天智对于秦腔虽十分钟爱,但他的孙女翠翠却对秦腔避之唯恐不及,爱上了外来的会弹吉他的流行歌手陈星。而秦腔演员——美丽善良的白雪虽然立志献身秦腔的振兴事业却生不逢时无力回天,甚至沦落到去人家的丧礼上去演唱的地步,她在生下了一个没有肛门的残疾女儿之后又遭遇了被丈夫夏风抛弃的悲剧命运。这其实是一个隐喻,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已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末路,中国的乡土文化与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结合后产生不了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所热切期待的宁馨儿,只能生出文化的畸形儿。正如评论家王必胜指出的:“(《秦腔》)对当今农民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尽情地展示,在时空上,犹如一幅当今清明上河图,一幅全息式的农村风情画。”“在作品中,关中农村,乡里俗事,现代文明之风的浸染,传统道德的羁绊,无不牵动着农村文化的发展与变异,更主要的是,小说把渐行渐远的乡土文脉根系,同渐渐侵袭的现代商业文化风习,在清风街上下进行着不大不小的碰撞,让我们看到了农民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既清晰而又迷茫的联系,也看出作者面对新的文化发展,一种特有的乡土文化情结。”[3]据作者贾平凹的表述,《秦腔》中的清风街的原型即是他的故乡棣花街,他在《秦腔》的后记中写道:
我站在街巷的石滚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2]543
贾平凹对于乡村的颓败以及乡土文化的没落甚至将要消失的命运可谓忧心忡忡甚至痛心疾首,读者们读完《秦腔》之后恐怕也难免黯然神伤。如果说在五四时代的乡土小说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写实派展现了一种对于乡土文明的批判姿态,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写意派展现了一种守望姿态的话,那么贾平凹在《秦腔》中则同时展现了批判与守望两种姿态,批判的是受到了城市文明污染的现实乡土,守望的则是那个日渐远去的民风淳朴、安宁祥和的昔日乡土。作者并非为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守望,只不过由于乡土文明面目全非式的蜕变使得其守望姿态具有了某种悲剧性。应当说,这种批判与守望交融的复杂姿态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当代乡土小说中极具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的独特性、严峻性和复杂性,来自于改变乡土文明的落后面貌与保留乡土文明的淳朴本色这两种要求难以甚至无法兼顾的价值选择困境。时光不能倒流,失去的家园也难以重建。在《秦腔》看似平淡琐碎甚至有些鸡零狗碎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贾平凹因乡土文明正在没落,不知路在何方而生的忧虑、焦灼与迷茫。乡土本是家园的象征,家园残破至此,我们现代人又该何处安放自己漂泊无归的灵魂呢?
二、历史维度的缺失与《秦腔》的美学内蕴
应当说,在当今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乡土文化的溃败乃是其必然的宿命。乡土文化中传统美德的失落固然令人扼腕叹息,但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正如无数哲人都曾指出的那样,文明的每一个进步都要以亵渎曾经神圣的事物为前提。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过:“市场经济撕去了封建社会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4]9而其所著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美国学者艾恺不无感伤地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5]46这种状况的必然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让人悲哀的是,几乎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传统的乡土文明与强势的现代文明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一种堪称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淘汰掉的往往是传统乡土文明中精华的、优秀的核心内容,而保留下来的则往往是传统中落后的、野蛮的、粗鄙的甚至是非人性的东西。亚洲各国就是如此,在亚洲各国本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历时数百年的文化冲突博弈交融过程中,许多美好的值得珍惜的成分被丢弃了,相反本土文明中的一些畸形、野蛮、落后的渣滓与泡沫如吸毒、赌博、人妖、雏妓,则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呈欣欣向荣之势,这些落后的东西与外来的现代文明中丑恶的东西汇成了一股令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疾首的文化浊流。《秦腔》中所叙述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就如有学者在评论这部小说时说的:不知不觉间,乡村生活已然发生了几乎不可逆转的巨变——而且是让人忧心的巨变:不想让它走的一点一点地走了,不想让它来的一点一点地来了——走了的还不仅仅是朴素的信义、道德、风俗、人情,更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精气神;来的也不仅仅是腐败、农贸市场、酒店、卡拉OK、小姐、土地抛荒、农村闹事,来了的更是某种面目不清的未来和对未来把握不住地巨大的惶恐。[6]
小说所描写的这些变化中不就裹挟着传统乡土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各自丑恶成分的混合物吗?无疑这种变化是令人心情沉重的。不过平心而论,在这种变化中也未必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实际上,只要我们不怀着多愁善感之心过分美化传统的乡土文明,就会发现它其实也存在着贫穷、落后、麻木、蒙昧的一面,远非田园牧歌那般美好,至于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所养成的自私、愚昧、奴性等阴暗面,就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站在历史理性的立场,人们有理由认为乡土文明的出路不在于退回到前现代的田园牧歌时代,而是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接受现代文明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理性、人权等新兴价值观念的洗礼。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文明中各种丑恶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不但与传统乡土文明固有的伦理道德准则南辕北辙,即使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上述正面价值观念也是格格不入。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物欲横流和金钱至上等不良社会风潮的泛滥,社会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的出现,与80年代现代精神所否定而尚未完成的对象——中国社会悠久渊深的封建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代中国的最黑暗处,正是中国社会独特的封建和商品资本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现代’得过剩的问题,而是现代性严重不足的问题。”[7]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当代乡土文学的研究者指责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的乡土小说所表现出的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拒斥态度缺乏历史维度,不明白现代文明取代乡土文明乃是历史的进步与必然,“工业文明的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污秽和血,其狰狞可怖的丑恶嘴脸又使作家忘记了它的历史杠杆作用,而陷入了单一的文化批判。”[8]平心而论,研究者们关于《秦腔》及贾平凹的其他乡土小说诸如《高老庄》《土门》缺乏历史维度的指责不无道理。文明的进步必然要亵渎甚至摧毁许多曾经被认为神圣的东西,我们不能为了保留传统美德就心安理得地认为农民应当安于现状,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方式,世世代代受穷下去。虽然除了少数幸运者,绝大多数农民并未通过经商或进城务工等方式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广大农民希望通过融入现代文明追求脱贫致富的权利谁也无法否认。这种追求富裕生活的权利中本身就蕴含了历史进步的维度。
尽管如此,我们却并不像部分乡土小说研究者那样认为缺乏历史维度是《秦腔》在艺术上的缺陷。毕竟,从古到今文学的立场、审美的立场都不应完全等同于历史学的立场,社会学的立场。如果说历史学著作、社会学著作离不开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性审视,那么文学作品执着表达的是人类的情感体验,两者绝不可相互混淆与替代。否则,我们只需拜读《世界史》《人类文明史》《历史大趋势》《社会学原理》之类的史学、社会学著作即可,何必读文学作品呢?实际上,文学应当关注的恰恰是宏伟壮观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问题,人类伦理道德的沦丧问题,人性的异化问题,恰恰是历史进程中渺小脆弱的个体生命所体验到的哀愁、伤痛、无奈、苍凉。人类并不是有了面包和各种高科技产品以及声色犬马的物质享乐就能活下去的,人类还需要精神的家园,而乡土正是人类永恒的家园。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乡土小说而言,‘乡愁’是其经典情感。因为在时光宰制中回望乡土,梦幻、感伤和失落是最自然的情感反应。那久远温情的乡土魂魄,在乡愁中梨花带雨,楚楚动人,正是乡土小说魅力所在。”[9]虽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土文明已经成了一个日渐远去的背影一去不复返了,但贾平凹通过《秦腔》等一系列乡土小说作品为之谱写的那一曲曲挽歌却能深深打动并抚慰我们的心灵。“《秦腔》是一部有大绝望大沉痛大悲悯潜存于其中的优秀作品。”《秦腔》之所以能成为贾平凹成功的作品之一,“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便是作家写作时有着一种情感体验极其刻骨铭心的自我投入”[10]。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维度的欠缺或许正是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独特价值与魅力之所在。许多世界级的大作家,如马克·吐温、福克纳、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沈从文,都在创作中表达了对乡土文明温厚诚挚的爱与眷恋,对光怪陆离、物欲横流的城市文明的厌恶与拒绝。历史维度的缺乏与其说是降低了,不如说是成全了他们的乡土小说作品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超越国界超越时间的,因为他们守护的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与悲悯。马克·吐温、福克纳、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沈从文们如此,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是如此。“现代工业文明打破了传统农业文明的宁静,各种偶然性因素颠覆了传统的‘因果相承、悲欢离合’的戏剧人生,家族、婚姻、国家、民族这些维系人类思想的文化共同体纷纷被解构,人的精神无以寄托。因此,乡土诗意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人类自我拯救意识的反映。”[11]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贾平凹未必不知道自己对乡土文明的深深留恋与当下举国上下都在追求的国家强大、科技先进的现代化目标相悖。作为一位成熟的作家,贾平凹其实绝不会采取一种反对乡土文明现代化的偏颇态度,他很清楚为了改变乡土文明的落后状态需要充分发挥现代城市文明的历史杠杆作用,他只是为传统乡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其淳朴儒雅美好的底蕴日渐失落深感焦虑与困惑而已。在《秦腔》的后记中他说:
我知道,在我的故乡,有许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说,说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和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2]547
现实中的故乡行将远去,没有人能将其挽留住,贾平凹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将故乡珍藏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已,此外还能何为?但我们认为贾平凹先生及读者们也不必过于悲观,也许现实中故乡会变得面目全非甚至丑陋不堪,但当故乡被艺术地保留在文学作品中之后,它就必然会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管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要走多远,故乡作为诗意的精神家园都将永恒地留存在人类灵魂的深处,时时唤起异乡漂泊的游子们的乡愁。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世界不就如此吗?《秦腔》作为中国乡土文明的安魂曲,其美学价值亦在此。
三、结语
一方面,作家们无不希望改变乡土文明的贫穷、落后状况,无不希望改变农民的愚昧、奴性等劣根性,所以20世纪80年代,许多乡土小说作家均曾为农村面貌,农民的精神风貌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所发生的变化欢欣鼓舞。但是,当20世纪90年代后乡土文明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变得日益边缘化且面目全非,道德沦丧之时,作家们又难免为之忧心忡忡甚至哀婉不已。正如孟繁华先生在评论《秦腔》时所说:“《秦腔》的感伤正是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的凭吊,它是一曲关于传统文化的挽歌,也是对‘现代’的叩问和疑惑。”[12]这一点,不独贾平凹是如此,其他许多作家如张炜、张承志等亦是如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农村、农民、农业和民间传统文化及其精神意蕴何去何从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焦虑与阵痛,乡土作家们不可能不在创作中把这种矛盾心态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心态深深折射了处于社会大开放、大变革、大转型时代乡土小说作家们理智与情感的纠结,折射了他们身处乡土传统文明与城市现代文明激烈碰撞冲突交融时代内心深处难以化解的价值困惑。
参考文献:
[1] 胡亚良,邓廷涛.乡土文化与乡村伦理重建[J].发展,2010(11):100.
[2] 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 张胜友,韩兽华,雷达,等.《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北京《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J].当代作家评论,2005(5):36-3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6] 刘志荣.缓慢的流水与惶恐的挽歌——关于贾平凹的《秦腔》[J].文学评论, 2006(2):146-151.
[7] 贺仲明.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以张炜为例[J].文艺争鸣,2000(5):36-39.
[8]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J].文艺研究,2005(8):5-13.
[9] 张懿红.从当代中国大陆乡土小说透视乡土叙事之动力机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4):37-44.
[10] 王春林.乡村世界的凋蔽与传统文化的挽歌——评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8(5):56-64.
[11] 许玉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叙事立场的转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13-116.
[12] 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J].天津社会科学,2009(2):9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