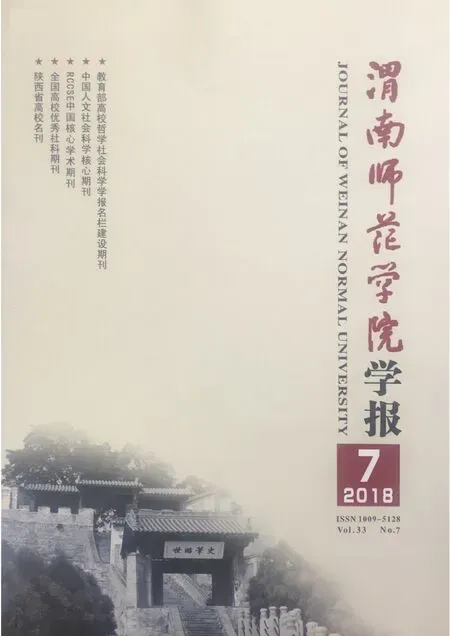“逍遥”与“超人”
——对比中西哲学的人生境界观
刘 梦 璐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27)
庄子和尼采作为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追求一种至高人生境界的哲人,各自凸显了中西方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研究方向与理论体系。然而,出于对生命的热爱,无论是庄子的“逍遥”还是尼采的“超人”,他们都对传统观念做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并致力于转换和重塑。通过把庄子、尼采人生境界的哲学追求纳入同一坐标系并对其论证过程和观点异同加以分析、对比,来进一步了解和比较中西方哲学在人生境界方面的追求和观照,对于我们今天人文精神的培养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庄子的逍遥观和尼采的超人哲学
庄子在《逍遥游》中,首先将大鹏与蜩、学鸠等小动物做了一个比照,以此来区分“小”和“大”。在此基础上强调,不管是体型“较小”,飞翔能力有限的蜩与学鸠,还是“其翼若垂天之云”能借风而行飞到九霄云外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这些“大大、小小”的“飞行者”都因“有所待”而终不能自由,文中的“有待”是指有所依赖,就是说人的诉求或展示要受到一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1]41只要你的施展是有所依赖和凭借的,究其根本就不是自由的。由物及人庄子引出并阐述了“至人不自私,神人不建功立业,圣人不贪图名利”的道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2]24,庄子认为这样的人才能“逍遥”。庄子这里要表达的是对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只要有所凭借就不能达到无所依赖,只要有所依赖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只有放下心中对外物的依赖,追求无待,才能不为外界所扰,遗世而独立,实现真正的逍遥。从表面看,限制逍遥的仿佛是所依赖外物的客观条件,其实在庄子看来真正受限的是人们自身的主观认识,是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从这个角度出发,要实现真正的逍遥,不光是对外物无所依赖,更要寻找一种心灵无所待。那么如何才能从主观的思想束缚中解放自我并寻求一种无所待的心态呢?庄子给出支撑“无待”实现的背后力量是“厚积”,但厚积并不是同“无待”一起实现的,它是“无待”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厚积最初是通过有待的不断积淀而来。于是《逍遥游》在强调“无待”时也在提倡另一种思想,即“厚积”。“厚积”才能借有待而飞,徒有“有待”而无“厚积”也无法飞翔,在“厚积”“有待”而飞的过程中沉淀,最终实现 “厚积”而后“无待”。所以想要将大如鲲鹏之志存于心中就必须积厚,也就是说只有具大因、居大处,才能证大果翔大路。[3]一个人要不断地追求学识的丰富,底蕴的沉淀,内心丰厚了才有能力和可能实现“无待”,厚积才能薄发最终自由。最后,在“厚积”和“无待”的基础上庄子进而提出了最彻底的实现逍遥的方法——“无己”,即从精神上超脱一切主观的、客观的、自然的、社会的限制,泯灭物我的对立,忘记天地,忘记一切,直到忘记自己。“无己”是逍遥游中人生境界观的最高境界,是终极追求。但“无己”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状态,而是升华到大我的根本途径。因为无法忘我因而有所凭借和诉求,也就有了功名利禄,悲欢喜丧的心态,所以忘我是一种伟人的境界,把自己融入世界之中,我即世界,世界即我,从而把为世界上的一切人事服务当作自己本就应该做的,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庄子论证“逍遥”的过程主要通过惠子与庄子的“有用”“无用”辩论,说明不为世所用才能“逍遥”。它体现了庄子在《天下篇》所说的“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4]。他认为天下沉浊,不能讲庄重的话,以危言肆意推衍,以重言体现真实,以寓言阐发道理。这种过程就是用寓言的形式将庄子的思想包含其中,从而含蓄地表达他的逍遥观。
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中借扎拉图斯特拉这一人物来宣扬他的超人哲学。他将超人化为三重意象,分别是大地的意义,清洁污秽人类之流的海洋和点燃人类最伟大体验的闪电。并且抨击了基督教重视来生和灵魂,轻视当下和肉体的思想。通过比较“超人”和“末人”来指出“末人”是病态的人群,他们信奉奴隶道德, 不懂轻蔑,不懂反省自身,他们拥有的只是沉默接受并安于现状,只能“贫乏,龌龊,一种可怜巴巴的舒适”。随后,他继续说道:“人类是连接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不论是越过去、走过去、还是向后回头、伫立发抖都是危险的。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类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他是一种过渡,一种坠落。”[5]36从而表达出人虽然在动物之上但不能止步于此,把它当作目的地、当作终点站,人必须超越自身,成为超人的观点。
尼采借扎拉图斯特拉之口在讲授超人的第一重意象时,指出在上帝存在时,灵魂被过度抬高,以至于“轻蔑地注视肉体,当时以为这种轻蔑高尚无比——它希望肉体孱弱、丑陋、衰迈。灵魂企图以此逃脱肉体和大地”。扎拉图斯特拉认为此时的灵魂只是在一味贬低肉体,也就是过于关注未来而忽视现在,过度赞扬灵魂而忽视肉体。这告诉我们对未来的神化无疑会导致当下的缺席,我们应该从当下入手去认识其本来的意义,而不是将所有的意义都寄托在未来。
在讲授第二重意向时,扎拉图斯特拉一直强调“伟大的蔑视”这一过程,旨在暗示一种反思的,生存论意义上的行动。他认为不懂这伟大蔑视的人是“末人”,“末人”认为的幸福、理智和道德也只是“贫乏、龌龊、一种可怜巴巴的舒适”。其后扎拉图斯特拉说道:末人“间或吃一点毒药,这制造了安逸的梦。但毒药过多又造成安逸的死”[6]103。沉迷于此,无异于服用慢性毒药,它的毒性就是人们一次次地上瘾却又浸淫在自我麻痹的温柔乡中。
尼采用“超人”代替死去的“上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意味着一个神化时代的结束,去神的历史即将展开。人终于摆脱与神学相纠缠的历史,开始自己主导这个世界,实现了从彼岸世界到此岸世界的过渡。
回归到人,主体性本身成为价值设定物,超人替代上帝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超人具有强力意志,而强力意志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强力意志不是一种出于与生俱来的、自发式的、非理性的力量。理性意味着克制,精准,逻辑,生硬,节欲;而强力意志的特性则是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这些特征代表了生命最原初的力量和终于也要回归于生命。强力意志的这些特性当然能够激发人的主体性意识,让人回到自身,回到现实生活,爆发蓬勃的求生欲和与生活斗争的能量。
二、“逍遥”与“超人”对于人生 至高境界的共同追求
从庄子和尼采对至高人生境界的论证过程中,我们能解读到作为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哲人,虽然他们的理论体系植根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与个人经历,但是通过比较我们能看出二人都力图恢复和发扬人之本性,追求自由的人性境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无限向往理想人格。他们在人生至高追求上有着共同观照:
一是庄子的“逍遥”和尼采的“超人”都是虚无论。是对于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至高的人生境界的追求。庄子通过对御风而行的动物的描述,推物及人地阐述了至高的人生境界是实现真正的逍遥:无己无待。然而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尼采用“超人”代替死去的“上帝”,超人也不是具体的人,是一个虚幻的形象,将超人替代上帝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尼采认为超人还没有现实的存在,他是未来人的理想形象。虽然最终诉诸不同的途径,但是两者都是在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企图超越灰暗的现实束缚,追求精神上的新境界。
二是庄子的逍遥和尼采的超人都是诗化的哲人,借助一种寓言故事的形式来表达主要内涵。庄子以大鹏与蜩、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开始,一步一步地进阶到“无所恃”的逍遥境界;而尼采则以扎拉图斯特拉下山试图向众人教导超人开始,赋予扎拉图斯特拉一系列奇遇与遭遇,从而表达超人的真正含义。
三是无论是“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3],达到逍遥状态的庄子,还是不屑于末人认为的幸福,认为理智和道德也只是“贫乏、龌龊、一种可怜巴巴的舒适”。试图成为超人的尼采,他言语中传达出来的都是一种当时时代下的独行者形象。他们批判现实,不愿屈服苟且,无疑为时代发展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庄子沉稳,心物外物悠然地独行,尼采则是充满力量和自信的独行者。
三、“逍遥”与“超人”的各自观照
庄子和尼采在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上有共同性,但各自在所处时代、追求实质时凸显了中西方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理论体系。
(一)观照的背景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统治者却腐朽无能,残酷压榨百姓。正是对这种政治时局的极度失望和反思使得庄子一心想远离污浊的政治和尘世的烦扰,他无力与残暴的统治者斗争,挣脱现实的黑暗,只有以无为来获取心灵的自由和安宁。同时,社会的变动也激发了文人贤士思变的思想,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大批贤士汇聚到各国都城,针砭时弊,各抒己见,阐明政治理想,畅谈人生追求。另外,当时奴隶制度瓦解,封建制度正在形成,加上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带动了商业的发展。这些客观条件给文人志士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社会的巨大变革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实践论题的层出不穷和热烈讨论。
尼采生活在俾斯麦统治时期,他推行军国主义,发动普法战争,建立德意志帝国。过度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人类的精神家园空虚而贫瘠,尼采在其传记中提到对此的看法,他表示“对周遭的一切充满着无上的轻蔑”。并且基督教的发展在尼采看来只是对人的束缚和枷锁,他要重建精神的家园。他高呼“上帝已死”,要“重估一切价值”。因为只要有上帝存在,就给予人们肉体终将一死而灵魂不死的精神安慰,而让人将生活的重心放到死后可能升入的天堂,将现世的活动都当作为进入天堂所为之事。但是在尼采看来上帝的存在不过是强制统治人们的精神形象,人们终将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冷酷。既然上帝已死,那么就有必要重估之前上帝所设定的一切价值取向,但是普通民众没有能力重估一切价值,只有“超人”才能承担这种重任。因为当我们否定上帝,我们便自觉失去了未来。如果不在人之上确立一个更高的超人形象,那么我们便断不了过去又杀不死心中的魔鬼。所以“超人”自然应运而生。
庄子的思想主要是怎么做人,由于个体在这样一个乱世的作用毕竟有限,因此庄子冷漠讽刺又超尘脱俗。而尼采坚信自己的哲学思想能拯救人类精神的危机。
(二)观照的实质
庄子的逍遥既不是完全出世,也不是完全入世。他只是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超脱于世俗,不为外物所累。庄子欣赏以万物齐同的古代道术,他论述自己的思想时也说道是上与造物者同游,下与忘却生死不分始终的人为友。这与他在《内篇·齐物论》中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观念,看起来虽是各不相同,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因为在庄子看来,这种不合是有违万物齐一的道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十分注重自然,并且渴望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它澡雪我们的精神,净化我们的心灵,使人们在现代性“异化”的现实苦难中逐渐觉醒,批判和超越世俗,这就是庄子认为人之为人最为合理的本质,最理想的人生。他推崇一种“合”的理想,试图将自己的身体与精神都与自然成为一体。[7]庄子的逍遥游集中体现了三个特点,首先体现在心灵之游,即心神贯注于某一境地。因为庄子的逍遥游说到底就是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整个世界被幻化为精神自由往来的逍遥之境。这样才能够无所约束、漫无边际、没有目的,才能够在人的精神主观能动性上超越客观现实世界。其次体现在虚无之游,因为它是心灵的漫游,是个体内在的精神运动,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虚无的。而且我们在《庄子》中也可以看到,他所描述的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例如在《逍遥游》里就构造了一种超越现实极富想象力的大鸟,他所描述的这么大的鸟至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见过的。最后体现的自然之游,因为庄子思想是在继承老子无为思想的基础上的,庄子之道乃自然之道。庄子的自然就包含了自由之意,正如他在《田子方》中写的:“无为而才自然矣”。自然的境界就是无为的境界,天人合一,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目的和意图,这也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
庄子的无为是一种超脱遁世,抛弃一切物质享乐,纯粹追求一种逍遥的精神境界。他试图将心灵从外界以及自己本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无我境界。他认为无用乃是大用,他所期待的是随时变化,无肯专为,与大道融为一体,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役。尽管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观点,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不应苛责庄子的选择。他虽然将生死看得很淡,但是他依然珍惜有限的生命,所以转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庄子虽然有对当时时代背景的“破”,但是甚少涉及创新的“立”,他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远离世间纷扰,隐逸山林的孤独者形象。
尼采塑造的超人形象实质上赞颂生命的活力,他的目的是要求力量,也就是个体力量的最大扩张,是在反宗教约束之上对人性的弘扬。他认为强者之中最有统治力和影响力的就是“超人”。超人是具有强力意志的人,是敢于打破传统束缚建造新价值的人。这就要求超人不断向上,超越自身。这是对人生达到一种至高境界的追求和期待。可以说,尼采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肯定生活。这是一段充满奋斗和超越的励志过程,是一个渴望改造世界的强者充满自信的发言。最后甚至发展为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和占有,虽然背离尼采原意,但是这正是原始生命冲动的极端表现。尼采不仅要“破”,更重要的还要“立”,也就是说他不仅反对宗教束缚,还要再造一个重估一切价值之后的新世界。在这种意义上,尼采的超人是一个创造者的形象。
通过比较,庄子和尼采都致力于恢复人之本性,重塑人的生命意义,渴望自由。但庄子的自由是绝对无为的自由,追求内在的心无外物,是内敛的自由。而尼采的自由是反对清静无为,提倡本能意志和生命力,是发散的自由。
(三)观照的途径
庄子认为如果要走向逍遥的境界就要凭借“心斋”和“坐忘”的方式来摒弃一切违背本心的羁绊,达到返璞归真,达到天人合一的逍遥自在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一是体验真知,二是保养精神,三是涵养德行。唯此才能不受主客观条件的约束,无待无己,实现真正的逍遥。所以庄子在《逍遥游》的第一部分阐述过从对比许多不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无己”“无功”“无名”。第二部分紧接着上一部分来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赖的终极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天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在庄子看来,现实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包括人本身都是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没有绝对的自由,所以要想无所依凭就得无己。
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中指出一个个体要经过从骆驼、狮子到小孩的精神蜕变,才能最终成为具有坚强意志的生命强者。具体说来,第一重境界是“骆驼”境界。首先,骆驼有着“能担载的精神”,在沙漠里负重前行,这承受的不仅仅是物化的重量还有生命的重责,它坚韧、隐忍,蕴含着坚忍负重的形象,但似乎缺乏主观能动性,只是被动地听从于命运的安排。尼采认为人类精神追求的初步阶段就是向具有骆驼般坚韧的个性精神和人类精神的过渡。这一过渡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但人生及人类精神的追求不能止步于此,必须超越这一宿命的精神阶段。所以, 尼采要骆驼为了夺得自由做自己的主人,发生了第二次变形变成了狮子。狮子意味着拒绝墨守成规的旧体系去批判传统而获得创造的自由,狮子行动所代表的人类精神价值在于对旧机制的批判和反抗,敢于说“不”,这预示着人类精神自我意识的觉醒。狮子的精神是一种打破精神。狮子精神所代表的就是为获得人类的自由而战,为创造新价值来争取自由性和可能性。狮子的勇气和力量对于毁灭一个旧世界的价值体系是必需的,但是人的生成最重要的环节才刚刚开始。旧的价值体系被摧毁,在这片废墟上需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从这个角度出发,狮子比骆驼具有打破的精神但不具有创造新价值的能力,狮子为创造新的价值提供舞台和可能性,于是,孩子的出现应运而生。孩子预示开始创造新的价值体系。 他抛开了重负的骆驼、在打破了旧体系的狮子的基础上开辟了一番新天地,变成了轻松自由的孩子。精神的“孩子”境界——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自我创造与新生。尼采以“孩子”来隐喻新生的人类精神,因为孩子是人的生命的真正创造与回归。孩子天真烂漫,自由纯真,象征着人的新生,预示着希望和未来。
骆驼的沉默坚韧,狮子的勇猛冲力,孩童的天真烂漫必然导致三者巨大的反差而使生命呈现出差异的生存状态。“精神三变形”就是尼采认为要达到超人境界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
四、从“超人”和“逍遥”人生 境界观看中西哲学的异同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对自己时代主题的响应和对自己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终极性思考和回答。庄子和尼采各自以其对生命状态的解读来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无论是达到逍遥还是成为超人,都表达出中西方哲学对于时代和人性的深度思考,我们通过庄子尼采的人生境界观来提炼和对比中西哲学的观照。第一,中西哲学不是一个固定的范围,而是随着社会实践发展不断变化的一种历史现象。无论是庄子的“逍遥”还是尼采的“超人”都不能离开历史和实践来谈,他们无不具有以往社会历史和实践浓墨重彩的痕迹。第二,中西哲学都受到了政治经济的影响,并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正是对这种政治时局的极度失望和反思使得庄子一心想挣脱现实的黑暗,以无为无待来获取心灵的自由和安宁。而尼采生活的俾斯麦统治时期,俾斯麦推行军国主义,并且基督教的发展在尼采看来只是对人的束缚和枷锁。他高呼“上帝已死”,要“重估一切价值”从而“超人”应运而生。正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让他们的人生观有了时代的痕迹和烙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况。
当然庄子和尼采对人生境界观所映射出的中西哲学思维也有所不同。第一,从庄子追求“无所待”“无己”的状态反映出中国哲学其实相较于西方哲学来说比较侧重于人的德行的修炼,在庄子这里德行的修炼提倡人之道就是无为,顺其自然,做到去伪存真、返璞归真。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他不仅认为追求知识,明辨是非没有必要,还否认用个人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知识的可能性。而西方哲学相比对德行的追求恰恰更重视理性意志。在尼采的三重境界中,人是高于动物的,而把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理解为理性。尼采用“超人”代替死去的“上帝”,是对人的观照的一种回归。这意味着过于夸大和神话灵魂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终于摆脱与神学思想纠缠的历史,开始让人自己主导这个世界,渴望个人自由,要求个性解放,反对教会的桎梏,要求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西方哲学理性主义打下厚重而坚实的基础,从神性回到理性实现了从彼岸世界到此岸世界的过渡。人们的思想从虚空的彼岸世界回到了现实的、理性的此岸,发现了人自身。第二,“逍遥”和“超人”的人生追求折射出西方哲学强调主客二分,中国哲学则主张天人合一,从而更加侧重人事。强调“顺天应物”、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平等。中国哲学谈自然是为了“究天人之际”,为了给人世的理想秩序找出“天上”的依据,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人世的问题。中国哲学几乎总是同政治主张糅合在一起,并以政治主张为归宿。因此庄子在追求个体“无待”的终极自由时在政治上也主张“无为而治”。哲学的功能侧重于人事,从而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的探索,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迎合周围的人事关系上。而西方哲学相对来说强调主客二分,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自身的创造力量和生命价值。西方哲学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人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从尼采的“超人”思想来看,尼采强调要成为拥有“强力意志”的超人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孩子,他预示开始创造新的价值体系,他开辟了一番新天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自我创造与新生,探求一种自然与人的新关系。
总之,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的观照途径的不同反映在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上也不尽相同。这对于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不失为一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思考。我们应该既要保持对生命的热情和自信,也要学习保持一个超然的心境,只有结合两者,我们才能更好地在激情与冷静之间寻得一份平衡。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西哲学在超越各自的“地方性”的局限性的同时,也应回归哲学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性质,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反思和批判、引导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价值和功能。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 许美平.鲲鹏寓言的定位——兼谈一条读《庄》义法[J].中国哲学史,2017(1):12-17.
[4] 王朝华.《逍遥游》主旨论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44-49.
[5] 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 罗森.启蒙的面具: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吴松江,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7] 涂早玲.中国古代“个体”思想的现代阐释——论儒家“君子”之道与庄子“至人”追求的正反合[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9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