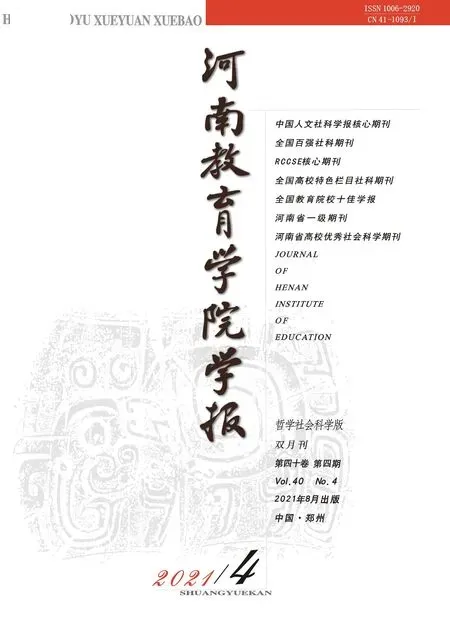“中体西用”概念的嬗变与发展:基于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思考
黄婉迪
一、导语
在“中体西用”的思想的指引下,张之洞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迎来了迅速发展。这反映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对先进技术的追求。与之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相比,“中体西用”的思想更为具体。“中体西用”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对中国知网和相关专著的研习,笔者发现,近三十年来对“中体西用”的理解包括概念审视、对相关理论的争议及对当下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比较清晰的学术发展脉络。
“中体西用”一经提出,就饱受争议。当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中体西用”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被机械化应用;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中体西用”在与其他社会改造思潮的碰撞中受到冲击。在迎接世界体系的时代,相对于早期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主张,“中体西用”思想无疑迈出了一大步。尽管“中体西用”思想饱受批判,但后来的学者都心照不宣地把中西文化交流、立足我国国情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背景,按照文化发展和实业发展两条主线展开讨论。及至新世纪,“马魂、中体、西用”的提出,说明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体西用”已经成为我国发展观的一部分。本文基于近三十年来国内相关研究,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结合文化传播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对“中体西用”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一回顾。
二、“中体”和“西用”的历史交汇与分歧
当张之洞等“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开始社会实践的时候,古老中国对遭遇西方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政治问题的反应非常激烈。当时的社会变革领导者并没有对“中体西用”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许多当代学者试图弄清楚“中体西用”的思想来源并借此认识其实践和发展的悖论。
(一)“中体西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
丁应通认为,“(中体西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与发展性,其学术根基在于‘经世致用’,文化原型在于‘内圣外王’”[1]。路新生认为,“中体西用”承袭了我国“体重用轻”的传统,但是“体”下移为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原先的“用”为西学所替代。[2]郝晏荣进一步指出,“中体西用”挑战了清朝以程朱理学为骨干,以“君尊臣卑”和“华夷之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也正因为如此,“中体西用”并不是政府的指导思想,甚至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3]丁向荣分析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来源、认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4]这些研究成果肯定了“中体西用”的积极意义。
杨锦銮根据“中学”“西学”交错占上风的态势,认为“中体西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5]张国平、吴佩林认为“中体西用”既是思维范式,也是一种文化选择模式。[6]高波考察了以张东荪先生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分析了张东荪对“中体西用”中关于“体”不可分的认识,认为张东荪试图将希腊哲学与儒家思想构架而成的新“体”作为西学东渐后的文化基础。[7]
郝晏荣回顾了上述争议对“中体西用”发展造成的影响。他指出,对“中体西用”的不同理解在学界中各有存续和沿革,比如冯桂芬、梁启超、孙家鼐、廖寿丰、魏光煮、陈宝箴、张元济、盛宣怀、沈寿康等人对西学的热衷;在政府决策方面,康、梁主要关注文化教育领域,而张之洞更重视从政治角度获取对清王朝改革政策的调整。[8]杨锦銮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判断。他认为“中体西用”导致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将重心放在西学上,围绕“西用”的具体论战最终导致了“中体西用”本身的分化。[9]
如此看来,“中体西用”实践展开后,早期执行者的个人理解便已产生了分化,那么,后来者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出现差异也就不足为怪了。学界的评价既有积极评价也有消极评价。积极评价,如丁向荣认为“中体西用”及受其直接影响的洋务运动,并与后来的“民主共和”一道,构成了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部分。[10]消极评价,如余治平认为“中体西用”没有正确认识现代文明的价值,把它降至工具化使用。[11]王哲认为,尽管“中体西用”突破了“华夷之辩”,向引进西学、重视西学的观念转变,但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入,“中体西用”又造成了新的冲突,沦落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和障碍。[12]袁晓晶以“癸卯学制”的构建为例,认为“中体西用”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加重了传统儒学教化思想及其体系的危机。[13]朴商焕、金守庚认为,“中体西用”在发展过程中把西方和近代化、科学看作同一个东西,以实现近代化、发展科学的名义无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同时,对东方传统采取极端保守主义的立场,这两方面共同作用造成了其失败结局。[14]贾小叶反对把“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认为,“洋务运动发生于 19世纪 60至 90年代中期,而‘中体西用’论却形成于甲午战后争;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为目标,没有涉及政治制度层面;‘中体西用’论容纳了学习‘西政’的内容”[15]。
(二)“中体西用”的实践悖论——以张之洞为考察中心
考察以张之洞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对上述争议会有一个更直观的反映。就对“中体西用”的理解和阐释而言,上述“中体西用”论争中存在的概念不清问题在张之洞“参酌中用”、寻求中西“通性”的努力[16]中已经相当明显。张勇以《劝学篇》为例,指出张之洞主张的“中体西用”汇通中西、平衡新旧,有开新风、传播西学的作用,其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具体产业实践和文化转型中具有积极意义。[17]但戚其章认为张之洞关于“中体西用”的很多论述都是含糊其词的,认为选择“会通”还是“补救”是维新派和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文化观上的主要分歧所在,而张之洞主张的“会通”只不过是借“会通”之名行“补救”之实。[18]杨锦銮认为,甲午战争后,张之洞为抵制维新,大力强化“中体”,蓄意限制“西用”,使“中体西用”论蜕变为阻碍西学传播和中学革新的僵化模式;此后,各种诟病纷至沓来,“中体西用”论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19]张昭军认为,张之洞的经世思想虽蕴含着走向近代化的可能,但由于严守“中学为体”,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障碍。[20]
就具体制度实践而言,严加红,任晓兰、王昊认为张之洞通过废除科举制度调节传统社会体制具有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21-22];李欣荣以清末法律修订中张之洞面临舆论和官方的反对为例,指出张之洞的理想在清末丧失了实践的可能性,“中学”在彼时已经不能为体。[23]
不难看出,近三十年来,学者对“中体西用”的研究基本围绕分析“中体”的历史来源、“中体”“西用”的历史交汇、“西用”的历史走向进行。这样的研究达成了很多共识,但在具体的概念、具体的事件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三、“中体西用”成为近代文化转型的策略
“中体西用”在文化和产业发展实践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其影响,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开辟了我国近代重要里程碑。李毅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甚大的重要思想,它预设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想。[24]作为一种理念和价值观,“中体西用”也得到了后人的批判继承,影响了近代的文化理念,促进了近代的文化转型。
(一)“西学东来”下新文化理念的出现
无论是对“中体西用”的反思或者发展,抑或另辟蹊径对“中西”“体用”关系的再反思,都可以看作“中体西用”理念在不同时代的回顾和完善。在中西方交流持续深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种价值观的“中体西用”在“道”的层面得到了认可。刘晶认为,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到张岱年提倡的“综合创新”,再到方克立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是“辩证的否定观”。[25]马亚雄分析了熊十力提出的“体用不二”说及其对“中体西用”的批判。[26]张昊雷关注到全国抗战爆发后冯友兰在中西对比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化、个体化的转向,认为“中体西用”促进了冯友兰通过德体技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追求。[27]刘伟、陈寒鸣指出方克立对张岱年先生倡导的“文化综合创新”进行了深化研究,并深化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基本方法。[28]
从历时的眼光来看,“中体西用”对价值观和学术范式的影响是长久而深入的。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批判的时候,实际上也在促进许多共识的达成和研究范式的形成。雷晓云认为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是导致“中体西用”模式存在内在悖论的文化根据。[29]陆道坤认为“中体西用”指导下创建的新教育体系内“中学”体量仍然过大,新教育的“新”味被淡化,“开放性”被束缚。[30]李丽基于对“中体西用”与“科玄论战”两场论战的分析,指出“中体西用”赋予了西学传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科玄论战”促进了科学社会功能的全面扩张,为科学基础上的文化整合提供了便利。[31]
(二)新文化实践中的“中体西用”
新文化发展和实践默许了 “西学渐来”的客观趋势,学界也十分重视“中体西用”在新文化领域中的实践。
在建筑领域,徐永战、过伟敏分析了张謇“中体西用”的建筑观:“在建筑选址上采用中国传统的地形选择和水势运用思维,兼顾西方建筑的功能性;在建筑的平面布局上使用西式专用空间代替传统的通用空间,但繁复的入口和交通体系暗含南通民居传统布局方式;近代建筑的西式外表体现了传统的开间等级观念,细部的装饰充满中国传统吉祥元素。”[32]
在文学领域,宋剑华认为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的基本性质是“化西”的[33];宁稼雨提出应该把中国神话的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拉回到文学研究的本体中来[34],并且应该用“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观重建中国神话体系的学术范式[35]。
在教育领域,王广义梳理了东北教育近代化过程,指出东北近代教育先后师从日本、欧美,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开展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实现了民族教育自决权[36];郭睿分析了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与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变革的关系,认为“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促进了新教科书对外国翻译作品的选录,这些入选新作品也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国民性格的塑造[37]。
在图书出版和设计领域,蔡顺兴认为“中体西用”造成了清末民国图书设计中“西式结构,中西元素”的主流模式[38];薛娟则认为清末对“体用一致”认识不清造成了对于现代设计思想的盲目取舍,民国的现代化努力也并不完善[39]。
在戏剧领域,李伟认为郭小庄在台湾京剧改革中创作的剧目虽然出自我国古代故事、传说,主题也符合传统伦理,但剧本结构追求情节高潮,表演向追求内心化转变,剧场的舞美和灯光追求现代化,使得其京剧具有“中体西用”的特征[40]。
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和具体行业的发展,传统社会制度的痕迹越来越淡化,影响力也逐步变弱,在“用”的层面,中西文化交流的障碍也随之削弱。于是,学者的研究渐渐将重点转向“中体西用”观念在思想文化领域和价值观层面的影响。随着“中”与“西”、“体”与“用”互动形式的多元化,研究对象变得更加活泼,对其把握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李天纲提出对“中体西用”本义的追寻。[41]在笔者看来,李天纲实际上是寻求在具体情境下解释“中体西用”的内涵。
近百年来中西方充分的交流互动,国内学界的讨论深入,为“马魂、中体、西用”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准备。五四运动时期,中、西、马三大文化思潮在北大交流融会,出现了张岱年所说的“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局面[42]。作为“马魂、中体、西用”提出者,方克立的思考得益于张岱年等人的研究。杜运辉、周德丰梳理了张岱年“综合创新论”对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的影响,认为后者把前者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43]“中体西用”已经开始向一种宏大的发展观靠近。
四、“中体西用”成为一种发展观
从上述的回顾来看,无论是寄希望于用“西学”解放生产力,还是希望通过思想界的解放引领社会的变革,其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协调“中”“西”,使“体”“用”达成一致,将中国从不发达状态中解放出来。
(一)“中体西用”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观
“中体西用”凸显了强烈的发展愿望,反映了当时的先进中国人拯救民族危亡的重大尝试。郝锦花认为“中体西用”是中国文化史上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第一次尝试,对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了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44]如前所述,“中体西用”最重要的意义是为当时的中国现代化改造破了题。甄建均分析了康有为抗衡“中体西用”的“群体变用论”,认为作为戊戌变法的指导思想,“群体变用论”实际上也是追求现代化的重要尝试。[45]李毅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冲击。[46]
从策略来看,“中体西用”拥有明确的行动方案。马克锋认为“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比较完备,反映了东方民族的思想智慧,是20世纪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选择,具有可操作性,应该给予重新评价。[47]王兆祥认为“中体西用”对西方模式和规则的学习是丰富的,但由于客观环境不具备导致失败,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48]这种关于其失败原因的阐述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力,不过后来学者也给上述不足以历史的宽容。马小朝、林春城指出历史现实规定性和思想文化制约性确定了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思维结构。[49-50]
从发展的视角来看,“中体西用”是作为一种发展观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它拥有完备的执行团队,有针对性的目标领域,有规划的策略和付诸实现的行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为自清末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尝试破了题。诚然,有魏、林等人开眼看世界在前,但作为政府行为,张之洞等人的洋务运动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行动。但在这个阶段,社会各界始终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局势裹挟了当时的许多政策,社会的变化也与“中体西用”的本心渐行渐远。客观而言,国门打开的文化效应是无可估量的。后来尽管“中体西用”没有在政府层面被提起,主要局限在学界讨论研究,但中国的发展实践从来也没间断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直到迈入新世纪,“马魂、中体、西用”的提出,才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总结了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的建设事业。
(二)“马魂、中体、西用”的发展
“马魂、中体、西用”由方克立提出,张小平、杨俊峰曾经就此对方克立做过专访。在专访中,方克立基于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进一步解释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步入正轨的历史过程,指出“‘马学为魂’是第一要义,‘中学为体’是中心环节,‘西学为用’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开放品格”[51]。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对“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解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马魂、中体、西用”是一种综合文化观念。李翔海以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体用模式,指出“马魂、中体、西用”是对“综合创新”论的进一步深化。[52]谢青松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取得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之后的客观事实,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和转型的必然选择”[53],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指导性方针,反映了当代中国学者的文化担当意识与文化自觉[54]。杜运辉认为,“马魂、中体、西用”与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既有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又有鲜明的阶段性[55];“马魂、中体、西用”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实现了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和深化,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第三个发展阶段[56]。周可真认为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如何向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转化是尚存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向前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继续深入进行”[57]。第二,“马魂、中体、西用”是一种学术范式。张新宁分析了“马魂、中体、西用”在经济学领域的创新中的意义,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马魂”,“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性和指导性”的“中体”,“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阶段性和自身的缺陷”的“西用”,是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58]洪晓楠、蔡后奇认为该范式既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积极挖掘“中体”和“西用”的积极性成分,实现综合性创新,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魂’”,对“西用”之流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过度融合的问题进行创造性批判。[59]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来看,“马魂、中体、西用”是对冯友兰、张岱年的观点的延续,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外文化交流模式进行理论思考的一种延续。在多元学科发展的今天,许多学科都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如果兼顾体制和文化两个要素,无论是宏观抑或是微观层面的问题,都涉及 “中体西用”这一命题。多元学科的发展为“中体西用”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参考。“马魂、中体、西用”是对建设年代的中国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实践的一种总结。它承接了前辈学者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国文化走向的深切反思,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有深挖的可能,也有存在的生命力。
五、总结和思考
综上所述,“中体西用”在国内经历了三个阶段。草创时期,以张之洞等主持的洋务运动为代表。尽管有开先河的勇气,但囿于当时的客观情况及其现代化的多元态度,“中体西用”在实践中产生了分化。探索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代表。冯友兰、张岱年等人展开的关于文化发展的广泛讨论,在文化如何协调(传统和现代,中学和西学)方面达成了部分统一。这个时期,中西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客观事实。许多领域的新实践,也为上述学者的观点提供了佐证。新时期的磨合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展开了制度、思想、文化和实践一致性的协调研究。贯穿这一历史过程的不是个别学者的理论言说,而是我国人民开展的广泛实践,其中的艰难和成就均有史为证。
“中体西用”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克服自身理论不足和实践障碍,最终成功地促进了中国文化转型,成为一种发展观。在技术层面上,如果把“中体西用”理解成保持本土特色基础上选择本国需要的科技和文化,无论从文化交流上抑或从治理策略上看,都无可非议。这种理解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社会实践中具有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