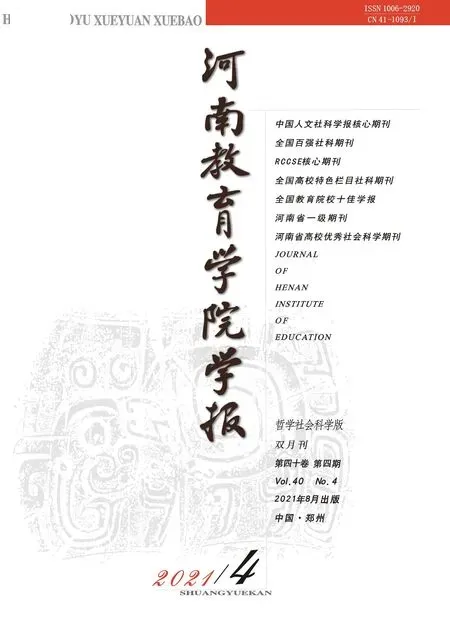由民具变迁引申而来的相关问题讨论
——读《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有感
马丽媛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物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逐渐兴起,它力图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领域关于“物”的研究积累予以梳理和体系化。这一研究方法被引入我国后,形成了诸如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以及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技术与物质文化史(传统手工艺研究)、工艺美术学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领域。[1]
在我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众多分支中,民间日用器具研究比较少见。目前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之少便是最直接的体现。但在实际生活中,民间的生产生活器具则恰恰是构成一个民族、地区、社会物质文化最为基础的部分,是塑造地方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托。在快速城市化、全球化的今天,研究极具地域、民族特色的民间器具,有益于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乡村的振兴与发展、“中国设计”的真正崛起。
孟凡行博士的《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一书基于民具研究的紧迫性,对贵州六枝梭戛乡陇戛寨苗族的民具及其变迁、发展进行了细致研究。作者在对陇戛寨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使用民具组合、民具群的概念,对这一地区的生产器具、生活器具、交通运输器具、文化娱乐器具四大类民具组合进行了细致描绘与分析。《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通过对民具的制作技艺与因素考量,以及民具的使用流通、存储保管、生命史等内容的考察和分析,研究民具与人、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探讨围绕民具所形成的文化及民具文化的传承、变迁与社会环境的变革更新。[2]133-211
作者在“适应与改造——陇戛民具的‘行为’”[2]179-189“接受和拒绝——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博弈”[2]190-205等章节所探讨的问题,以及结语部分对陇戛寨民具未来保护发展方式的讨论都是非常具有包容性、广泛性的当代问题。作者通过大量调查和研究发现,陇戛寨的民具既大量借鉴了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的成果,又保留有自身狩猎文化的特征,这些特点的融合并存主要依托于族群祖先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他们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2]38-45在陇戛民具的当代变迁中,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了民具的变化更替。在与外来物的博弈中,一方面,陇戛寨的苗族人受到了现代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很多传统民具退出了生活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更加便捷高效的现代化机械;另一方面,陇戛寨的苗族人也在改造外来器具,例如对背桶的实用性改造等。陇戛寨民具在这两方面的变化及其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西方文化相异的一切“传统”,如传统物质文化、传统手工技艺、传统乡村文化等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困境,也关系到当前学界和社会的两个热点话题——传统手工技艺的当代转型、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二、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转型
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器具作为前工业时代普遍的生产方式与用具,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是一个民族和地区的历史文脉的记录者与“活化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定地区的人们的特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此种方式的内在变迁。但是,在现代机械化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产品的冲击下,传统手工艺所凝聚的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体系迅速瓦解。如何传承和保护作为民族和地区历史、信仰承载体的传统手工艺,使其能够在当代获得新生,是保持文化多样性和提升国家文化竞争力、设计竞争力的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生发于农耕经济时代的传统手工技艺与传统器具在强调速度与效率的现代工业的影响下,已经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弃。但也正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我们才更加重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塑造,开始从文化意义上关注和反省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传承与转型发展。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的兴起,传统手工技艺作为一种手工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其服务日常生活、满足日常需求的功能已完全被工业技术所取代。笔者认为,传统手工艺在当代的转型发展路径,除了当前如火如荼的旅游文化(表演)产品外,还应有以下两条。
一是与当代设计艺术相结合,设计出满足实用性、增强产品文化属性的产品。根据当下的实践活动,其中又可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一种是将传统手工艺及其载体与如塑料、钢铁、不锈钢等现代材料制品相结合,作为现代产品的装饰性功能存在。在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中,很多地方通过将传统手工技艺运用于农特产品的包装来增加其地域文化属性及产品附加值。另一种结合方式则是将现代设计理念与方式运用于传统手工制品的生产中,提高传统手工艺的附加值,使其在兼具功能性的同时获得更高的价值。在这里,现代设计帮助或者赋予传统手工艺及其制品以更多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传统手工艺则使现代设计更具文化价值与历史底蕴,同时,传统手工艺所具有的差异性、偶然性等特质正好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独特性、个性化的多元追求。
二是与当代艺术联合,成为艺术新载体。手工艺的样式和技术铺陈了一种多样性的媒介资源,这种资源由于其地域性的差异,具有极为丰富的媒介多样性。[3]109在当代,陶瓷、刺绣、剪纸、编织等凭借其纷呈各异的特质与特性,成为越来越多艺术家的观念表达载体,为艺术家个性化、多元化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媒介选择,丰富了艺术的表达形式。传统手工艺凭借其丰富的修辞可能性和文脉差异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实现方式。[3]114
三、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乡村建设是一个高度复杂和综合的问题,它与文化、经济、政治等各因素均有紧密关联,众多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已在开展此方面的研究。《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所描述的陇戛民具在现代的形制变迁、被现代机械的替代等现象,实际是乡村受到城市化冲击、乡村文化受到工业文化冲击的具体表现之一。传统民具在现代的境遇亦是乡村(文化)在当前的境遇。乡村振兴,大致有五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国家的城镇化建设已经完成60%,这表明资本的积累已经足够丰富,城市可以反哺农村;其二,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人口拥入城市,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乡村出现经济凋敝、文化消退现象;其三,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雾霾、拥堵等“城市病”催生了“乡愁”情怀;其四,经济全球化导致文化的全球化,即文化差异性被消解与抹除,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提升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提高文化竞争力是必然选择,关注乡村中的传统手工技艺的发展成为重要任务;其五,由于逆全球化浪潮的再一次出现,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成为经济全面均衡发展的内在需求。
从2005年的“积极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3年的“精准扶贫”到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大量社会力量进入乡村,观察乡村,研究乡村,尝试找寻能够恢复乡村活力、振兴乡村经济的有效路径。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在乡村建构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文明以及现代生活体系,建构农民的“文化自觉”。我们不是要保护乡村的落后状态,乡村也不会一成不变。二是在目前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最直接体现出的一个矛盾便是乡村的内在需求与城市人外观乡村需求之间的差异。很多人在进行乡村建设时是带着一种下行的、怜悯的心理,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感动以及找寻乌托邦式的“乡愁”寄托。我们更应该关注乡村自身内生性的发展需求,推动乡村实现经济、文化形态的当代转型。三是乡村与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经济方面——乡村的发展依赖城市这个大的消费市场,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对乡村的发展有带动作用,当前实现乡村脱贫与振兴的主要路径为依靠城市企业、单位等的资金、人力的大量投入与帮扶;文化方面——乡村对城市文化有向往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模仿行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城市文化优于农村文化。文化具有多样性,不能够单以经济是否发达作为标准来评判一种文化的优劣。农村虽然经济不如城市发达,但是在生态环境方面却明显优于城市,这也是当前乡村旅游经济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陇戛民具,还是传统手工艺,或是千千万万的乡村,其在今天所面对的状况与问题是相似的、共通的,都是在探索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趋势,如何在保持自我本真的同时,实现自身经济、文化的振兴与发展。尽管传统器具与传统手工艺似乎分属不同的文化研究范畴(物质与非物质),但在实际生活中,两者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所面对的问题是一致的。
美国社会学家W.F.Ogburn在《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从物质文化及其变迁与非物质文化及其变迁中,也许可以见到有许多的变迁都是先发生在物质文化里,以后才引起了其他文化的变迁……由于今日物质文化数量大,改变得快,以及可以引起别的社会变迁,使得物质文化在现代社会里,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4]149民具是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民具的变迁必将导致其他文化的变迁。[5]160外来的现代化器具的进入对陇戛寨苗族的传统器具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例如,《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中提到陇戛人对待“现代化”的心态已经开始变化,过去不屑于同族外人联姻的陇戛人开始认为嫁给汉族人是有能力的表现。作者认为这实质上是陇戛人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对于传统手工艺和乡村的发展而言,也是如此。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全球化、城市化所带来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也使得人们对旧有的、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对自身的文化认同度、文化自信度大幅度降低。这也是当前大力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