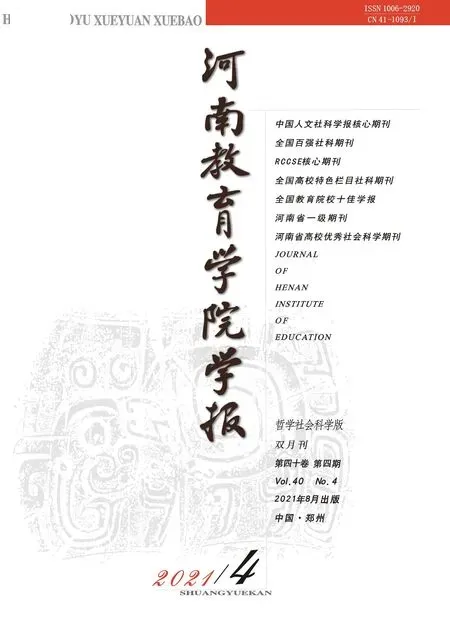公共空间的文化诗性
——苏式二胡人文意涵摭谈
朱磊
一、导语
在非遗传承和保护的语境下,二胡艺术的受关注点由音乐本体延展至文化活动的层面,二胡艺术的文化内涵也超越了传统民间艺术的概念,触及公共艺术的范畴。因此,权衡二胡艺术传统性保护与产业化发展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虽然现代意义上的二胡艺术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历经沧桑巨变的中国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得二胡与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显露出鲜明的历史性与阶段性特征。在这中间,苏式二胡作为苏南社会文化的艺术浓缩,可为论证和考察传统民间艺术所根植的人文景观提供极好的样本。
随着“公共空间”这一理论范式近年来在学界的兴起,苏式二胡的人文意涵得以彰显。首先,二胡作为中国民乐的符号之一,相关研究本身就是集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为一体的文化热点;其次,苏式二胡作为从北方传入,后赶超并引领中国二胡艺术的个案,本身就涵纳了中国的文化演进与公共生活形态;再次,孕育苏式二胡艺术的生动意象与鲜活情感,赋予了苏式二胡公共空间不可化约的诗学意味。简言之,聚焦苏式二胡所依托的人文意涵,解读其公共空间的内驱动力,是探讨二胡艺术作为公共艺术的主要视点。
二、公共空间的文化生态
众所周知,苏南地处吴文化区。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区位划分来看,吴文化应当被划归江南文化;就文化关系而言,吴文化则当属长江文化系统。无论是江南文化还是长江文化,都是大的区域文化概念。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吴文化在系统上应当属于大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文化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商朝末期。《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1]1334据此可知,因周太王欲让位于季历,而同为周太王之子的太伯与仲雍二人远赴当时被中原人称为“蛮夷之地”的江南,并通过纹身和断发的方式来表示不与季历争位,此举使他们受到了江南地区千余家百姓的拥护,太伯被尊称为吴太伯。唐代张守节在为《史记》作注的《史记正义》中进一步写道:“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2]69梅里即今日无锡市梅村,因此无锡当属吴国最早的建都之地。
相较于中原地区的连年战乱,吴地的社会秩序相对平稳。大量北方民众纷纷南迁,不仅为吴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将北方的文化艺术思想传入吴地,其中就包括原本多流传于北方游牧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胡琴。吴地人民在广泛吸收各地区文化传统的同时,注重将其与自身的文化生活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有异于长江流域荆楚文化的吴文化。吴文化在与各地域文化之间保持着内在联系的同时,又凭借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显现出独特的文化个性。
吴文化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三山文化”。这一时期的石制器具形制十分丰富,目前已出土数千件石制品。距今约7 000年,吴地出现了新石器文明,史称“马家浜文化”。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以木作柱、芦苇作墙的地面建筑,并采用磨制较为精细的石制工具。马家浜文化在持续了大约1 000年以后,逐渐演变为“崧泽文化”。[3]52这一时期各类生产工具的制作手艺有了明显改进,并出现了有纹饰或镂空的陶器,但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同时期文物相比,仍有着较大差距。约5 300年前,吴地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最为繁盛的“良渚文化”(或“良渚酋邦”[4]9)时期,大片谷仓遗址证明当时耕作农业较为发达。此外,出土的大量丝织品与雕琢精美的玉器还表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约3 0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此时吴地的文化逐渐分化为“马桥文化区”和“湖熟文化区”,其中湖熟文化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并融合江南越国与中原商朝的文化因素,并最终在吴国建立以后发展成吴地文化。[3]60所以,早期的吴地文化是在多种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与不断更新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太伯称吴王之后,带领当地民众大力兴建基础设施,并将黄河流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吴国百姓。《左传·哀公七年》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5]296,由此可知太伯并未完全照搬周朝礼制来治理吴地,而是结合吴地的地方特色与先民遗制进行了合理的改良。在这个过程中,周文化逐渐与吴地文化融合,吴地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丰富。至春秋末期,楚人伍子胥因其父及长兄被楚平王杀害而避往吴国,凭借杰出的军事才能成为吴国重臣。同时伍子胥还举荐了齐国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孙武向吴王进献了自著兵法并被重用为将。伍子胥与孙武凭借出色的才能成为吴国治国重臣,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齐、楚文化在吴国的传播,实现了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荆楚文化在吴国的融合,延续了吴地文化(以下简称“吴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性特征。
依照文化生态学的观点,地理环境也是塑造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原与荆楚等区域文化地处中国内陆,大部分疆土由山地、平原、丘陵和盆地构成,这种地理构成比较利于修建城邦,因此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源的地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地域环境往往也会造就一种保守、内敛的文化个性。相比较而言,北依长江、东临黄海与东海的吴地,虽有大片的平原和湿润的气候,但临海的地理环境在早先的人类看来是不适合发展文明的,这便是早期吴文化区的生产技术与社会生活水平等方面落后于其他文化区域的原因。但吴文化临海的地域位置与内陆区域相比又有着自身的优势。大海的辽阔与神秘为吴地人民的性格植入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勇气,也逐渐形成了吴文化开放的特征。“秦汉以来,吴地与日本、朝鲜、台湾(地区)、南洋诸地,海上丝绸之路相通,输出中华文化。”[6]在西方文化于近代逐步渗透和深入至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处于东部沿海的吴文化在率先吸纳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以留学的方式远赴国外学习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据记载,清政府于同治十一年(1872)组织了大约120名10~16岁的学童分四批赴美留学,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江浙、广东两地。[7]71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从全国范围内选拔的148名庚款留美生(1)庚款留学生:在中国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署了《辛丑条约》之后,英、美、法、荷等国又相继与清政府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除了偿付债务,其余退还款项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庚款留学生由此产生。中,仅无锡地区就有14名,江浙地区则占了约60%;在赴日留学生中,江浙占了近25%;在晚清赴欧的留学生中,江浙占了30%的比例。[8]37吴地学子凭借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得中西文化交融的风气之先,在留学归国后,利用自身所学促使吴文化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探求与吸纳正是吴文化开放而包容的文化个性在新时代的折射。正是源自这种文化特性,北方的二胡被吴地人民所接纳,并被广泛用于多种传统艺术形式。二胡在吴地获得了比其他地区更快的发展。
三、公共空间的诗性彰显
孕育苏式二胡的苏南,不仅是一个表征文化传播与融合的公共空间,还可作为联结文化制度、教育水平、发展理念的诗性空间。透过苏式二胡的人文意涵,苏南文化艺术公共空间的诗性得以彰显。
之所以将苏南视作诗性的公共空间,关键是苏南的文化艺术在民众生活和地方社会中的运作机制。吴国建立以前,江南地区因地缘因素和长期的文化封闭而一度被中原人士视为“蛮夷”之邦。太伯称王,开启了吴地与中原地区的密切交流,中原文化对吴地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人的智慧与才能也令中原诸邦开始重新审视江南文明。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先后出访鲁、齐、郑、卫、晋等中原诸侯国,观乐评政,品评之间表现出敏锐的感受力和卓绝的判断力,其高深的文化素养令众人为之注目。同时期的吴人言偃,勤奋好学,成为孔子所教七十二贤中唯一的南方弟子,深受孔子喜爱。言偃也用毕生精力来宣扬孔子学说,并致力于音乐教育,这对吴文化及音乐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秦汉时期,吴地出现了朱买臣等文臣,但其文化艺术整体与中原地区仍有较大差距。至六朝时期,依托稳定的社会环境,吴文化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意境与文化特征。这一时期的吴地涌现了六朝“四大家”(曹不兴、张僧繇、陆探微和顾恺之),可谓盛极一时。
唐宋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代表的南方文化迅速发展,“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9]103。吴地大力提倡学校教育,甚至以宅建学,促使学风浓郁,人才辈出。如南宋诗人“四大家”中的范成大与尤袤均出自吴地,而画家、词人及儒者的数量也在全国位居前列。[10]112-115元朝以后,中原文武官员与社会名流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纷纷避往江南隐居,“江南如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11]46。众多文人集聚江南,使得吴文化进一步繁荣。从明朝开始,吴地成为刻书业的中心,“拥有数十百卷文图籍者,多不胜举”[12]133。公、私藏书量之丰富和私人藏书家之多在全国首屈一指,吴晗先生编撰的《江浙藏书家史略》一书共收录江苏藏书家482人,仅吴地就有421人。[13]7-110浓郁的文化氛围助推了人文艺术的全面发展,这一时期的吴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大思想家顾炎武、名列诗文“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文学巨匠冯梦龙、昆曲始祖魏良辅以及山水画家王时敏和王鉴。
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14]26-30除此以外,乾隆也将江苏、浙江称为“人文之薮”(2)乾隆在其五十三年的上谕中说道:“江苏、浙江省分较大,素称人文之薮”。转引自徐吉军《浙江古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载《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133~136页。。时至近代,吴地人文气息浓厚的特征得以进一步展现,所涌现的人才几乎涵盖了社会文化经济的所有领域,如外交家与文学家薛福成、政治家陆定一和秦邦宪、经济学家薛暮桥、国学大师钱穆、科学家华蘅芳、教育家与科学家顾毓琇、文学家钱锺书和杨绛、音乐家刘天华和华彦钧、画家徐悲鸿等。苏南文人最为集中的吴地,被称为人文渊薮,乃实至名归。
名家辈出体现了吴地的人杰地灵,也体现了吴地民众的聪慧好学。得益于浓厚的人文资源,吴文化区域的文化艺术建设拥有了其他地域所不具备的良好环境,这也是北方的二胡能够在吴地得以传播并被充分接受的原因之一。同时,善学与勇于探索的个性也有助于吴地人民敢为人先,在二胡于传统艺术中被广泛应用的基础上提出形制改良与技法拓展,从而整体提升了二胡艺术内涵。
此外,社会的进步与文化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吴地在汉代以前无论是文化发展还是教育水平均落后于中原地区。吴国建立后,虽大力兴建各项基础设施,但文化教育水平与中原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六朝时期,孙吴、东晋以及南朝(宋、齐、梁、陈)相继定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亦首次移至吴地,吴地的经济社会由此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并有力推进了吴地教育的发展。南宋时期,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使得政治经济中心再次由中原地区南下,吴地也借此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文化制度和教育体系,此为吴地文化教育发展的关键阶段。明清时期,吴地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且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带动了原本已有一定基础的教育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各种形式的书院、私塾散落于民间(3)吴地书院自宋元时期便已出现,至明清吴地各州县先后兴建了百余所书院。其中:苏州约有40余所,如和靖书院、学道书院、文正书院等;无锡约有书院50余所,如东林书院、东坡书院、阳羡书院等;镇江约有30余所,如茅山书院、龙山书院等。众多书院中,尤以无锡东林书院最负盛名,历史学家柳诒征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写道:“合宋元明清四代江苏之书院衡之,盖无有过于东林书院者矣。”私塾作为民间私学性质的机构,在吴地也颇为兴盛,仅清末至民国期间,无锡就建有私塾676所,至宣统元年(1909)达866所。以上数据引自高燮初著《吴地文化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大小不一的义学(4)义学是免除学费的学塾。明清时期的吴地兴办了百余所义学学塾,仅无锡县就在乾隆八年(1743)设立了41所义学学塾,较具代表性的有邵氏义学、崇仁义学等。也受到官方与民间资本的支持,在城市和乡村被广泛创办。这一时期,吴地教育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为吴地培养了大批的文人雅士。
同时,沿江临海的地位优势还助吴地得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之势,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最先兴起的地区之一。一方面,吴地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大力兴建新式学堂。在这个过程中,以无锡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国学宗师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写道:“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国,无锡一县最先起。”[15]52光绪二十三年(1897),无锡县杨模、秦谦培等人以日本的学堂体制为参照,经官商集资等渠道筹款兴建了无锡第一所新式学堂——俟实学堂(今连元街小学)。翌年秋,无锡举人裘廷梁和俞复等人联合筹资创办了三等公学堂。至宣统三年(1911),无锡已陆续兴建学堂120余所,学堂数量与办学规模均居全国前列。[16]2559-2565另一方面,吴地还注重在传统教育教学基础上不断求实创新,探索科学的育人模式。如自编教材,由三等公学堂编撰出版的《蒙学读本》被称为中国第一套小学教材,中国也由此开始了系统编辑中小学教材的先河。此外,吴地还大胆突破古代传统观念对女子的限制,使女子教育逐渐由家庭教育向社会教育转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留学日本的侯鸿鉴在归国后出资兴办了竞志女子学校(今东林中学),并开设师范科,为无锡和周边城市培养了大批女性教员。由朱华氏出资创办的鹅湖女校还开设了刺绣科,此后又有志诚、学艺等女校竞相效仿并相继开设,加之宣统元年(1909)由无锡近代教育家顾述之等人创办的无锡女子职业学校[16]2571-2573,女子从事的艺术与技能培养实现了以系统教学的方式传播,使吴地成为近代率先设置艺术素质教育的地区之一。
吴地及时把握历史变迁的机遇并为教育建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近代西学的逐步深入,思想开化、敢为人先的吴地人民率先抓住了教育改革的契机,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教育的有机结合与合理转化。历史学家严耕望曾在《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中写道:“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锡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无怪明清时代中国人才多出江南!”[17]615
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某一特定文化特有的,也是某一具体的区域的人们在文化环境的形成中逐步养成的一系列文化特征的外显。[18]就宏观的文化层面而言,中原文化、黄河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形成相对较晚的吴文化之间应该有诸多相似、共性的文化因素;但若谈及具象的文化特性,因为历史演变、地域位置与人文环境的不同,也自然会有文化内涵上的差异。文化,应该说是一个集继承和创新、借鉴和创造于一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吴文化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在丰富与完善着自身的文化内涵,并结合自身优势逐渐呈现出与其他区域文化不同的文化特性。如果没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内涵,原本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所用的胡琴将难以融入地处江南的吴地;如果没有名家辈出的人文环境与求实创新的文化理念,二胡也难以在苏南得以全面改良。因此,二胡能够在南北文化的交汇中逐渐融入江南吴地并迅速发展,与吴文化本身的文化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苏式二胡的维度聚焦苏南文化艺术的公共空间,可以发现,苏南涵纳了各地域的文化艺术,又在凝聚独特文化个性的同时为维持群体范畴的改革实践提供了平台。而“诗性”在公共空间中彰显,使得苏南文化艺术的范畴进一步延拓,并外化为吴文化兼收并蓄、求实创新的人文意涵。